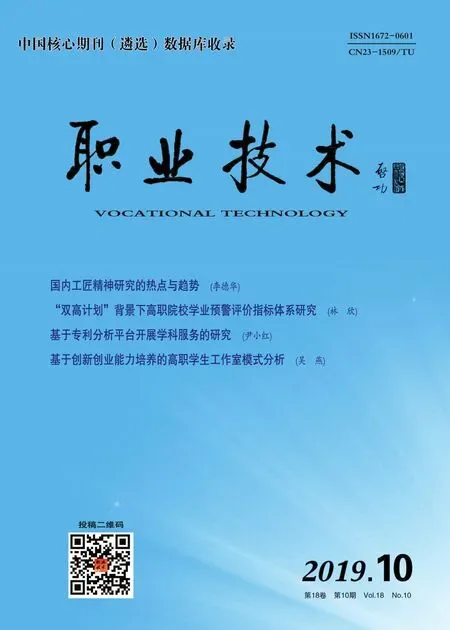论行会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历史缺位与行会平台的搭建
孙明星
(湖南师范大学, 长沙 430100)
0 引言
职业教育一度成为日本、德国促进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可见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性。我国越来越重视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其发展速度和质量仍不容乐观。比较职业教育发展强国,以德国为例,行会地位至关重要,是其职业教育成功的第二法宝。而当下我国行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明显缺位现象,梳理行会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中的缺位,分析其缺位原因,并进而探讨搭建好行会平台,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1 行会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历史缺位
职业教育的发展始于学徒制。中国的职业教育亦始于学徒制。中国传统学徒制是指在职业活动中,通过师傅的传帮带,使艺徒获得与从事职业相关的制作手艺或生产工艺的背景知识和实际工作经验的一种古老的职业训练方法[2]。中国的学徒制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官营手工业学徒制(7-14 世纪)、行会学徒制(15-19世纪)与企业培训学徒制(20 世纪初至中叶)[3]。与欧洲行会在学徒制发展中具有的作用和价值不同,行会在我国学徒制发展的三阶段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位。
第一阶段,官府掌握并控制着手工教育。手工生产是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形式,在封建集权的古代中国,统治集团控制手工生产活动,垄断最为精湛的手工技艺。尤其在封建社会鼎峰的唐宋时期,官营手工业已经具备了系统而完善的学徒培训制度。该阶段,在封建经济的束缚中、在官府强力的控制下,学徒制呈一种封闭状态。而伴随唐宋商品经济萌芽而萌生的行会,也无法脱离官府的管理,它不同于欧洲的自治行会,缺乏本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这种缺失也使其没有能力承担学徒制的管理。欧洲则不同,学徒制与政府无太大关系,由力量强大、组织自治的行会将学徒制制度化,将其纳入管辖范畴、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内部组织制度,由此手工业学徒培训完成了“从私人性质的制度向公共性质的制度过渡”,并使之逐步完善,标志着职业教育的开端[4]。
第二阶段,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行会的出现。封建社会的逐步瓦解打开手工业和学徒制的封闭圈,行会介入学徒制管理,将其作为维护行业健康发展的手段。在经济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行会无法摆脱官府的管理。
第三阶段,从清末中国创办第一所职业学堂开始,职业教育就从零散的学徒制逐渐过渡到系统的教育体系。以黄炎培为代表而兴起的近代职业教育思潮让职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蓄势而发,而行会在19世纪后所发生的变化和衰落也使其参与职业教育的能力再次衰退。在此阶段后期,职业教育系统未完全吞噬学徒制,学校职业教育发展的缓慢性和残缺性使得企业学徒制在该时期兴起和发展,企业内部创立职业培训制度,学校职业教育与企业学徒制并存,行会处于游离二者的尴尬地位。[5]近现代,职业教育纳入正式的教育体系是不可逆的趋势,欧洲也不例外,资本主义工业化冲击着传统行会学徒制,传统行会学徒制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发展,学徒制培训体系被迫改革,厂内培训成为一种有效的解决形式,从而行会学徒制转为在厂培训学徒制。与此同时,国家主义职业教育制度确立,因此人才培养的重任由学校职业教育与在厂培训学徒制共同担负。历经以上管理权的淡化和转移并不意味着欧洲行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无足轻重,相反,欧洲国家清楚认识到行会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不可替代性,因此进入以学校为主的现代职业教育时代仍一直保留行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传统。在欧洲众多国家中,德国行会参与并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成效是值得借鉴的,德国重视行会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可从德国职业教育界最高法律——《联邦职业教育法》窥见一斑。德国从法律的高度对行会的权责进行规定:行会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组织者;行会在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的作用;行会负责职业教育培训的审查与监督。[6]德国职业教育领先于世界得益于健全的法律体系、双元制教育模式等,行会在其中的贡献也不容小觑。
纵观中国行会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不同于欧洲社会,中国真正推动学徒培训走向制度化的主导力量不是行会,而是国家,国家设置专门的机构和职位来掌管百工技巧。行会参与职业教育经历了从“游离于学徒培训之外”到“介入学徒培训”再“游离学徒培训”的发展轨迹[7]。发展至今,中国行会在企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大大减弱,职业教育参与能力也渐被遗忘,而欧洲国家却一直保留行会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德国,行会仍在职业教育中有一席之地,并推动职业教育向前发展。而当前我国行会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微乎甚微,行会为什么在我国未能引起重视,行会是否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意义值得考究。
2 行会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缺位的原因
行会在欧洲职业教育兴起和建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后期国家政府的力量逐渐强大而削弱其主导作用,但行会依旧有其价值。相比之下,当前我国行会的缺位于职业教育的发展,结合行会参与我国职业教育的历程及其现状,进一步探寻其缺位原因。
行会缺位的问题须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去分析。首先谈历史原因。职业教育诞生的逻辑起点应是“技艺的自由”,所谓“技艺的自由”指两方面:一是技艺的形成,它是人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发挥聪明才智而形成的富有技巧性的、难以掌握的武艺、工艺等;二是指自由,它意味着技能拥有者具有充分的人身自由,对技艺的发展和传承有选择和决定的权利。[8]原始的职业教育在于发明、掌握某一技能的人将这一技能以某种形式自发地传授给后人,缺乏这种自由性,职业教育即不存在。以此逻辑起点来看,在封建时期的中国,技艺者是没有自由的,技艺者被君主垄断而仅为其服务,限制其传承,因此中国没有原生职业教育。技艺者自由受限的状况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发生改变,洋务运动中兴办学堂被认为是中国职业教育院校的萌芽。同样,在皇权专制的古代社会,虽然产生了行会,但基于商业和手工业服务于皇权其发展才不会受阻,行会派生于皇权之下,所以中国行会一开始就带有官营性。除了官营性,中国行会还具有原始的宗族性。宗族是古代甚至到现在也是中国社会关系的核心维系方式,而儒家伦理是宗族的核心。古人云,“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商人地位的低下使行会中的商人一方面享受着工商业的果实,另一方面内心又鄙视工商业,仍以“仕途”为宗族荣耀。[9]土生土长的官营性和宗族性使行会发展不如欧洲那样开放和迅猛,更内敛和封闭。因此,从历史角度来讲,我国具有官营和宗族特性的行会以及缺乏原生性的职业教育使得两者关系不紧密,缺少欧洲国家中职业教育与行会的共生关系。
除了以上所述的历史原因,还需要直视当下行会未能参与职业教育的现实原因。我国兴办职业教育的氛围不浓厚、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不健全,行会地位不突出、公信力不高。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受政府指导、依赖于政府的扶持,而在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统管较多的情况下,行会的地位自然受冲击,历史经验亦是如此。就行会本身,缺乏参与教育管理的意识,中国商界向来较少干涉教育,学校大多是国家公立性质。但近年来这种状况逐渐得到改善,私立学校的兴起对行会涉足教育、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观念、社会制度不断迈向现代化,工匠精神不断被丰富和呼吁,行会在此背景下应愈加受重视,其官营性和宗族性在民主、法制的现代社会中也渐渐消退,理应有着良好的发展空间。对于职业教育,我国早已意识到职业教育发展对国家和社会的重要性,长期以大量资金、优惠政策来填补职业教育起步晚、发展慢的空缺。由此可见,现今中国社会为行会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温暖的氛围。但同时面临的现实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仍旧不温不火,陷入多重困境。为改变以上现状,不乏研究者讨论如何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作为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主体,学校、政府和企业成为相关研究中最频繁的关键词,行会却似乎被遗忘。批判性借鉴德国行会参与职业教育的经验,弥补行会缺位、促进行会参与职业教育对突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困境是一种新思路、新办法。
3 搭建行会平台,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为使行会充分发挥其功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3.1 依法设置行会
依法设置行会是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以行会为中介打通政府与企业的联系,制定法律法规去引导和规范行会。如德国的《联邦职业教育法》以及俄罗斯的《俄罗斯联邦工商会法》,都从法律高度明确了行会的职责和地位。我国目前尚无针对行会参与职业教育的立法,有的是一些较为零乱、分散的关于行会的规章制度,主要包括 1997 年国家经贸委《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1999 年《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工商领域协会的若干意见(试行) 》、《关于加强行业协会规范管理和培育发展工作的通知》,2004 年国资委《国资委行业协会工作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以及一些省市出台的关于行业协会管理的法规。[10]立法的缺失是行会职能不明确、动机薄弱、参与度受限等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在我国职业教育相关法律不断趋于健全和完善的过程中也需要将行会相关法律纳入其中,赋予其严肃性、调动其积极性。因此政府应推进行会参与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通过立法,明确行会的性质、职能、运作模式,使行会参与职业教育有理有据。依法设置行会,有助于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3.2 政府搭建平台
无论是行会还是职业教育我国政府都有最高的统筹和协调权力,因此行会和职业教育之间桥梁的搭建依靠政府的力量。首先,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与行会的关系。将目前一些超出政府管理职能或事务性工作转交给行会,让行会承担起职能,以增强行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能力,这既对政府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也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利。因此有必要出台权威性文件,以此规范政府与行会的关系,明确规定政府部门职能转移的范围和事项,如促使有关部门把行业统计、行业规划、行业规范、资格认证前置审查、市场准入资格认定、许可证发放、专题调研和专项工作等工作转移给行会。[11]在此基础上,制定细则阐明行会参与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也对企业和学校作出要求,为行会疏通阻碍,避免其缺乏号召力的尴尬局面。只有在政府的统一监管下,行会才能“扬长避短”,扬其“平衡、传递、沟通、服务”所长,避其“定位不明、职能不晰”所短。
其次,改变政府的经费支持方式。政府的经费支持是行会建设的重要支撑,但若要真正发挥行会的第三方作用,应保持行会原有的商业性质,变直接拨款为购买行为。行会致力于职业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服务性工作将以产品的形式向政府兜售,而政府也据其成效进行购买。这样既可以保证政府经费投入的效率、为行会提供经费保障,又不致使行会的商业化性质转向政府依附性,保持了行会独立性。此外,政府还可以辅助减免税收、提供实用性资源等方式给予行会支持,增强其生存能力。
如上所述政府积极帮助行会搭建与职业教育界或是职业学校的对话平台,共同探讨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与难题,行会才能明确自己的职责、参与职业教育的管理和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在职业教育的前进之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3.3 实现多方联动
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紧靠一己之力是很难实现的,企业、政府、职业学校、行会是参与职业教育的四大主体,它们分别在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以联系的观点来看四位主体,不难发现职业教育突破困境的重要法宝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是:企、政、行、校四方的合作,四位一体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联动机制,互相补充、互相监督。在这样的关系网中以企业为参与主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也为企业的发展储备人才;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在统筹兼顾中实现权力下放;以学校为中心,学校在积极改革发展中整合利用多方资源,以市场为导向突出办学特色;而行会则作为纽带,是政府统筹职业学校的调节剂,使其权力运用恰如其分,是企业与学校的中介,使人才的培养满足社会的需要。行会的纽带作用使企业、政府、学校之间的紧密联系,搭建共同对话的渠道,整合力量,形成多方联动、共同致力于职业教育发展。
4 结语
如何提升职业教育质量水平,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快速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我国行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历程,探寻其缺位的原因和补位的意义,在基于我国国情的前提下提出搭建行会平台,以行会促进职业教育发展是突破职业教育发展困境的一条蹊径。在政府主导平台搭建、完善法律法规为辅助的基础上,发挥行会纽带作用,形成企、政、行、校四方联动参与职业教育必将推进职业教育实现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