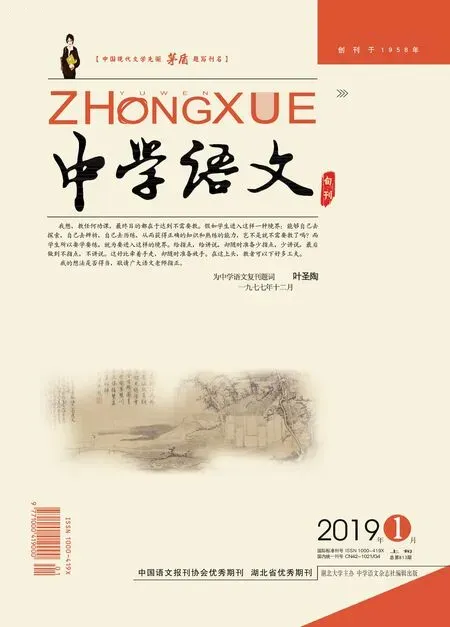意蕴与融通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愚公移山》中的整体思维剖析
徐向顺
[作者通联: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愚公移山》出自战国时列御寇所著的《列子·汤问》。列子,战国前期思想家,其学本源于老子,主张清静无为,是老、庄之外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列子》字里行间表达了崇尚虚静思想,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愚公的形象本质上是道家文化的产物,道家思想构成愚公移山精神的文化底色。”①愚公移山精神蕴含博大的道家思想,大智若愚、以愚为本的智慧境界,至诚至性、天地畅达的自在性灵,逍遥生死、卓然无限的豁达性情,直面艰若、舍取豁达的坚毅行动等等,吸纳了道家文化因子的养分,传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愚公移山的精神,放置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则具有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蕴,阐发出极为深刻的社会性题旨。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做得很不够,诸如《愚公移山》所构建的与现实系统有着密切关联、心心呼应的“现实——神话”系统,“移山”神话所隐含的“天人合一”原始普遍性象征,遭到人们普遍的忽视,或为无意识的冷落;其中所蕴涵的意蕴与融通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及整体思维中的典型思维模式,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破译。基于此,像《愚公移山》这样的古代经典诗文,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探究。
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不探究中国传统哲学;探究中国传统哲学,又不能不探析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传统哲学是通向传统文化宝藏的通道,而传统思维方式更是解开中华文化神秘面纱的钥匙,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处于文化结构的最内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具有稳定形态的东西。一般说来,中国传统哲学把宇宙理解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整体,这种系统整体观是古代哲学家认识、把握客观世界的一种总体观点与基本方式,体现了华夏民族自然认知理论水平所能达到的高度,并构成观念性的理论基础,直接或间接地规定和制约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质。然而,传统哲学的系统整体观却又实实在在地建立在传统整体性思维方式基础上,整体思维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着眼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而理解和规定对象的一种思维原则。”②把天地、人、社会看着密切贯通的一个有机整体,天地人我、人身人心等作为系统要素,统一处于这个整体系统之中且结成相互依存的联系。“天下之物,贞乎一者也”(《易·系辞传下》)。“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老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和核心,在几千年的文化创造、传承、发展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当今人们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整体思维是一种有机循环的整体思维,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组织的有机系统,构成这个整体系统的又有许多小系统,每个系统又由不同部分所构成,整个宇宙自然界就是由这样的部分所构成的系统化整体”③。放眼纵览,自然界万景万物,大到宏观宇宙,小到微观粒子,无一不在循环不殆的整体系统中运行;世间万事万理,小到细事修身,大到治政邦交,无一不在终始恒常的复杂关系中制衡。同样,一篇篇传诵古今的诗文佳作,无一不在遵循整体构思的思维路径,建构“头”“中”“尾”要件齐全的诗文生命体,这三部分的基本结构又须遵循整体性思维模式,“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所谓“凤头、猪肚、豹尾”。《愚公移山》篇幅虽短,全篇只310字,却结构完整,张驰有节,可以说,深谙“六字法”要领。
《愚公移山》开篇“凤头”精要,小巧玲珑,短小精美。开门见“山”,交代所要移动的对象,“太行”“王屋”二山的面积“方七百里”、高度“高万仞”及地理位置,点明故事的背景,简洁明快,直截了当,为下文埋下伏笔。主体“猪肚”丰满、充实、健壮、容量大,情节生姿曲折。以愚公提出移山主张为情节开端;以家人“杂然”争议、商定解决方案,旋即挖土辟山为情节发展;以智叟的笑止、愚公的驳诘构成情节高潮。结尾“豹尾”利索,干练精要,收束有力。以天帝被愚公的诚心感动,派二神将王屋、太行二山背走,愚公移山愿望得以实现收结,照应开头,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蕴含深意,让百世读者揣摩、体悟:移山之功全仗神助,虽非愚公之力,却因愚公至诚,故而不可磨灭。其结构安排贴合,情节采用线性结构,环环紧扣——各情节按时间自然顺序、事件的因果关系顺序连接起来,呈线性延展,由始而终,由开端到结尾,情节一步步向前发展,矛盾冲突引人入胜,情理至臻且扣人心弦,构建一个互为依存、演绎缜密的有机整体。
《愚公移山》文笔不丰,三百余字的短文,暗设“两世——三重因果”关系,写来却是细丝严扣,彼此关合。“两世”:是指愚公生活的现实世界、天帝掌管的神域世界的“两个世界”;“三重因果”:现实世界的“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之“因”,引发愚公立志“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之“果”,这是第一重因果;神域世界的“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帝感其诚”之“因”,于是才牵出“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之“果”,这是第二重因果;现实世界的愚公“毕力平险,”“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寒暑易节,始一反焉”之“因”,引致神域世界的介入,“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并产生“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之“果”,这是第三重因果。第三重因果是前两重因果的交集,并在此形成终结,使看似不相干、彼此独立的现实世界、神域世界里的因果关系得到整合,融汇到更高一级的整体系统中,形成有机关联。一般说来,现实世界的因果联系赋予人们实际的真切感,神域世界的因果关系却充斥大量玄想的虚幻感,而本文在揭示诸多因果关系的局部系统,特别是构建贯通两个世界的第三重因果关系的整体系统中,严格遵循因果律,做到层层相扣,充分展现一个因果相成、逻辑严密的系统整体。
上述论及的结构完整、因果相成,固然呈现了整体性思维的一般特征,而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特征的则是 “天人合一”“阴阳思维”这两个典型思维模式。
一、“天人合一”思维模式
华夏民族经过长时期的观察、领悟,逐渐形成了由 “天—地—人”组成的整体谐和的宇宙观念。“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最高、最为典型的理论形式,也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根本内容之一。
所谓 “天人合一”,“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整体。‘天地以生物为心,’‘道体流行’,具有‘生意’,自然界是一个有结构——功能的统一整体,人则‘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从而能‘为天地立心’,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这一整体的具体体现。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体的对立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二者具有同构性,即可以互相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④换言之,一方面,确认人由天地生成的自然物性,人的生活需服从自然法则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与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呈现形式相异,但本质相通。“乾,天道也,父道也,君道也”(《周易大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泛爱万物, 天地一体也”。(《庄子·天下》)“万物皆一”(《庄子·德充符》)。“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吕氏春秋·有始》)。“天地万物为一体”(王守仁《传习录上》)。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把天、地、自然与人包罗在一起的思维模式,视天地万物由某种特定的机制而相互联结为统一的整体。
在《愚公移山》建构的系统密切、整体关联的寓言世界里,实质上存在两个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子系统——即“愚公辟山”指向的现实系统、“天帝移山”虚构的神话系统。现实系统是作者着力刻画,使用八成五的笔墨,于“否定性”争议中凸显决策的周密性,于“移山”过程中彰显行动的意志力;相比,神话系统叙事简洁,直陈结果,用墨不丰。从表层结构看,神话系统近乎附着于现实系统的貂尾,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实际上,神话系统不仅贯通首尾、统摄全篇,而且居于现实系统之上起着支配和解释机缘的枢纽作用。主人翁虚拟如神,具体表现为:其一,高寿体健——北山愚公“年且九十”,尚能亲力亲为,身先士卒,“率子孙荷担者”,“叩石垦壤”,经受繁重的体力劳动,“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长途搬运,“寒暑易节,始一反焉”;其妻同好健在,年寿齐眉。其二,思维敏捷,愚公头脑清醒,“谋”事句句入情贴理,怼“智叟”逻辑推论缜密,而其妻也不迷糊,尚能“献疑”。这些现实人物远超一般寻常人能耐,他们的身心与体智似乎与神仙异域达成一种通灵、照应,因而可感动“天帝”,派遣两员大力神士,背走王屋、太行二山,了却愚公的心愿。
人(社会)与天(自然)何以通灵、合一?抑或前云的“三重因果”何以贯通“两世”——现实世界、神域世界?从神话特质看,神话作为超现实的幻想形式,与原始文化、原始思维方式相沟通,显现集体潜意识,且能象征性地投射作者主体意识中更为深层的内蕴。原始初民面对神秘不可知的外部世界,抱有普遍的“万物有灵论”,即自然神,如山神、水神等充满整个世界;随着自我意识的加强,人类开始了按照自我的样式来想象、塑造神灵,“愚公移山”故事中,操蛇之神、山神、天帝、夸娥氏之子等诸神被赋予鲜活的存在,并被寄予人格神的特征。当神话题旨与现实意旨具有了相汇通的一面时,天帝用怜悯与帮助的方式解决移山问题,化解愚公的生存危机,便在情理之中。神话形象也是表达神秘感的最好途径,一旦被艺术地想象并高置于神坛,便具有了与人保持某些距离或曰某种隔绝的不可知性,于是就成了神秘性的化身和偶像意义的崇拜物,至于“夸娥氏二子”极具“超自然”本领,“负二山”举重若轻,就不足为奇了。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天’与‘人’的关系实际上具有某种不确定的模糊性质,既不像人格神的绝对主宰,也不像对自然物的征服改造……‘天人合一’,便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的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的顺从崇拜。”⑤
二、“阴阳思维”模式
“阴阳思维”之“阴阳”,是指自然变化中的两种功能或力量,或析为事物具有的两种属性——对峙、统一、变化的功能。阴阳对峙,贯通于天、地、人三才——自然、社会、人身均具阴阳互相对峙的两种势力;阴阳统一,阳依附于阴,阴依附于阳,“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任何阳的一面或阴的一面,都不能离开另一面而单独存在,二者处于互包、互涵、互补、互转之中。阴阳思维将一切事物视为矛盾统一体,没有对立面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体,没有统一体,对立的两方面将无法相互作用,据此应“从事物对立的两端、两方面、两部分,解释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把握事物变化的规律。阴阳思维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思维。”⑥《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揭示事物内在的对立统一,赋予阴阳思维以规律性。《易传》断言更是明晰:“一阴一阳之谓道”,以“阴阳”作为最基本的观念,将阴阳的对峙、变化、统一作为总规律、总原则,进而解说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及其矛盾对立、相反相成。《庄子·天下》即言“易以道阴阳”。北宋张载在进一步阐释的基础上,提出“一物两体”(《正蒙·参两篇》)、阴阳和合的思想,“一”是指对立面的统一,“两体”是指阴阳两个对立面,“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阴阳思维是中国传统整体思维方式的典型模式之一。
需要指出,“阴阳五行”思维模式以阴阳两极建构宇宙生成图式,在推演五行的基础上阐释社会运动规律及其终始循环的命定论特征,为人类思维作出了重要贡献。“阴阳”“五行”的混合、统一,起始于战国时的阴阳家;汉代对阴阳五行学说作了进一步完善,对阴阳概念及其无所不包的特性、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阴阳互相调节维持整体平衡的功能等作了充分的阐说。董仲舒 《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第一次提出一般系统论的理论模式和一般系统的双层结构模型。从时间序列看,列子《愚公移山》先于汉代,因而未将“阴阳五行”思维模型视为整体思维方式予以研究。
“阴阳思维”认识统一体中具有对立面,对立面又存在统一体之中,对立和统一是不可分割的。道家始祖老子:“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阴阳、雌雄、古今、生死、智愚、刚柔等等,所谓无对不成物,世事万物皆是相反相对而存在,进而形成对立统一的“阴阳”合体。出自道家著作《列子·汤问》的《愚公移山》,其原始语境就是殷汤与夏革君臣之间的问答,探讨物之始终、有无极尽、巨细修短等哲学命题,其中“巨细”“修短”“异同”等哲学概念涉及“阴阳”之辩,实属“阴阳思维”。《愚公移山》文本中呈现:智愚、正反、异同、巨细、大小、虚实、有限无限等“阴阳思维”之情状,其中“愚公”——“智叟”划归的“智愚”对立最显著、表现也最充分,由此形成的移山“坚定派”与“阻止派”构成“正反”或“异同”的阵营。在“移山”事件上,愚公身上展示出的坚定不移、坚毅勇为,象征“正面”“正能量”;智叟言行中表达出的畏难缩进、消极对抗,象征“反面”“负能量”。除了这两个不同壁垒构成的整体的“阴阳”对峙外,壁垒内部形成局部的“阴阳”对比,比如在“阻止派”方面,愚公妻质疑式的“献疑”——商榷,而智叟否定性的“笑而止之”——反对;基于出发点不同、表达方式差异,性质判别相异,比如同是对待“愚公移山”事件,操蛇之神是“惧”——害怕,帝“感”而“命”——支持。
在“愚公移山”构建的“天—地—人”庞大体系中,众“人物”分列“天”“地”“人”三才:愚公、子孙荷担者、京城氏之子、愚公妻、智叟——“人”,操蛇之神——“地”,天帝、夸娥氏之子——“天”。先秦以来的学术成就表明,古代便编制了“天—地—人”系统的次序:在“天”——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昼为阳、夜为阴;在“地”——下为阴、上为阳,右为阴、左为阳,西为阴、东为阳;在“人”——尊为阳、卑为阴,德为阳、刑为阴,君为阳、臣为阴,据此,“超自然”神性象征的“天地”——“阳”,屈于自然威力下的“人”——“阴”;“天地”体系里,位尊权重的“帝”——“阳”,位卑的山神即操蛇之神、夸娥氏之子——“阴”。不仅表明自然、社会、人身普遍存在阴阳互相对待的两种势力,而且进一步论证人与天的统一。
《愚公移山》包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精华和深刻的哲学思想,折射出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厚,具有了不以时空为转移的基本内涵,因而能够走出历史的尘埃,闪耀睿智的思想,卓而不群的智慧,至今仍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理解《愚公移山》这篇奇笔异思的先秦之作,需要重返文本产生的原始语境,寻踪探源,领会其在现实系统中言说的表层意义,更须解剖整体系统中融入的文化信息,破译“天人”神话、“阴阳”符号的普遍性的象征内蕴和原始意象的原型模式。否则,将无法窥视列子著述的全貌,更妄论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神的深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