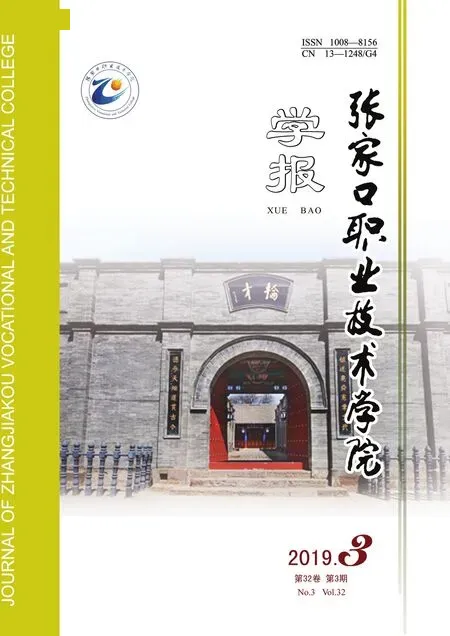三曹诗中的政治抱负与爱国情怀
刘文杰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8)
在中国文学史上, 三曹父子同登文学殿堂,以独特的身份地位从事文学创作实践,并各有名篇传世,他们的人生与国家命运相连,他们的诗歌内容与天下兴亡、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密不可分,他们的诗歌风格是建安文学的主旋律。
一、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和追求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群雄并起,出身卑微的曹操受命镇压黄巾军、加入讨伐董卓联军,收编黄巾军三十万,壮大实力,与群雄争霸,挟天子以令诸侯,凭借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在这过程中,曹操完成了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初心到树立了平天下,统一全国的政治理想和追求,曹操的诗《度关山》、《对酒》明确表达了为天下开创太平时代的政治理想。
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铄贤圣,总统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狱。有燔丹书,无普赦赎。皋陶甫侯,何有失职?嗟哉后世,改制易律。劳民为君,役赋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国,不及唐尧,采椽不斫。世叹伯夷,欲以厉俗。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许由推让,岂有讼曲?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度关山》)
这首诗从“人为贵”民本观点写古代君王治理国家的法则,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提倡节俭、“兼爱尚同”,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雨泽如此,百谷用成。却走马,以粪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对酒》)
《对酒》诗比《度关山》更加细致具体地描述了君贤臣忠,百姓富足,路不拾遗,老有所养的大同社会生活,对汉末皇帝昏庸、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揭露,表达了对政治清明的理想社会的渴望。
曹丕作为曹操次子,受父亲的影响和熏陶,文武双全,志在承父业,做国君,成为曹魏政权的继承人。据他的《典论·自叙》“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生长在戎旅之间,自幼骑马射箭都娴熟精通。曹丕非长子,不是继承人的唯一人选,他为人谨慎,思维理性,在他的诗歌中含蓄的表达了男儿应当建功立业,不要虚度光阴的思想。“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艳歌何尝行》)“夭夭园桃,无子空长。虚美难假,偏轮不行”(煌煌京洛行),曹丕做了皇帝后,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下,少征伐,轻刑罚,薄赋税,倡俭朴,不失为一代明君。
曹植“生于乱、长于军”,才华出众,“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深得父亲爱重,曹操曾考虑立他为太子,但曹植个性率真,重情义,“任性而为,饮酒不节”(《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未能实现。曹植自认为“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薤露行》),人生短促,第一要及时建功立业,“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道“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第二要学孔子流芳百世,“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曹子建政治理想没有实现的机会,但以文学得以传名后世。
二、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
三曹诗中都有描写战乱和民生疾苦的题材,表达忧国忧民之心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叙写了董卓谋权,焚烧洛阳和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
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
这两首诗是汉末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记录和生动写照,明代钟惺评曹操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丕和曹植的描写战乱的诗歌虽不及曹操深刻,但军旅生活,也让他们见识了战争的破坏力。
曹丕的《黎阳作》:
奉辞讨罪遐征,晨过黎山巉峥。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彼桑梓兮伤情。
诗中记述奉命出征,见到百姓家宅凋敝,田园荒芜的凄惨景象而生感伤之情。
曹植《送应氏》: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这首诗是建安十六年,曹植随父西征马超,路过洛阳,与应氏兄弟分别时所作,这时离董卓焚毁洛阳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但曾经繁华的都城,不但没有恢复,变得更加萧条,人烟稀少。
曹丕和曹植诗歌中征人思妇的题材,也从侧面反映了百姓生命朝不保夕,夫妇新婚离别的社会现实。
三、唯才是举,推崇文学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在他身边既有治国用兵之术的政治军事人才,也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人才,形成了邺下文人集团,三曹是这个文人集团的领袖,彬彬之盛,蔚为大观。曹操自己草根出身,在任用人才上,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曾三次下令求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在曹操《短歌行》中表达了对求贤若渴的心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写诗人思念人才,礼遇嘉宾,“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既希望贤才多多益善,为我所用,又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曹丕和曹植在邺下生活期间,与诸多文人雅士“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通过宴饮、校猎、游览、斗鸡、走马等社交活动,吟诗作赋,唱和酬答,兄弟二人身边各聚集了一批文人兼幕僚,结朋党,为争太子之位做准备。曹丕更是将文学的价值和地位提升治国立言的高度,他在《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四、逆境中锲而不舍,慷慨悲歌
古代学者对三曹诗歌的评价颇多,最有影响的当属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的论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之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向多气也。”这段话说明了三曹文学创作的历史背景和诗歌的风格,并指出“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环境,为国为民的政治抱负,形成了三曹慷概悲凉,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也是建安风骨的精髓。在逆境中,三曹诗歌有悲凉、有忧思、有怨恨,但从未表现出绝望,“哀而不伤”,总是化为锲而不舍,积极进取的精神,慷慨悲歌。
在大分裂、大动荡的历史时期,三曹同有家国情怀,但所处地位和身世经历不同,在诗歌创作内容和表达上呈现了差异性,曹操有乱世英雄的慷概沉雄,曹丕有守成之君的缠绵忧思,曹植有诗人的率真华彩,从内容到形式,三曹诗歌开创了建安文学以风骨为特征的艺术审美,引领了文学自觉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