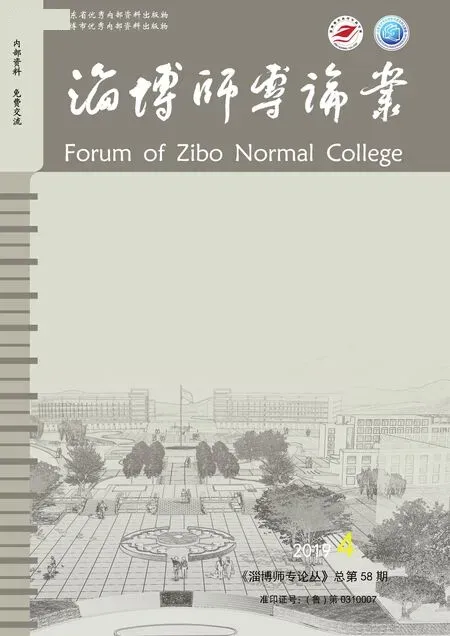《曲江池》与《李娃传》爱情主题的比较
(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唐传奇与元杂剧的创作关系密切,元人石君宝的《李亚仙花酒曲江池》就改编自唐人白行简的《李娃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情节的设计安排上,元杂剧有了自己的创新之处,形成了爱情主题上的同与异。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二者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研究李亚仙人物形象的变迁、小说的爱情主题,以及透过改编的背后,来揭示当时普遍存在的从唐传奇到元杂剧的改编创作共性问题的研究。目前看,研究者们对于二者之间的爱情主题差异成因的分析还不够。因此,本文试图立足于唐代与元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性,探求形成两部作品中爱情主题差异的原因。
一、《曲江池》与《李娃传》爱情主题的相同之处
《曲江池》改编自《李娃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作者的情感价值取向上,都存在着很大的相似之处。我们通过分析两部作品中共有的爱情阻力与动力,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二者在展现爱情主题上的共同之处。
(一)二者爱情的阻力皆来自老鸨的贪婪
《李娃传》讲述的是荥阳生与妓女李娃曲折的爱情故事。《曲江池》中将荥阳生改为郑元和,但故事大致沿袭了《李娃传》中的基本情节,儒生与妓女之间的爱情是二者所反映出来的共同主题。围绕着这一爱情主题的展现上,无论是《李娃传》还是《曲江池》,都塑造了一个贪婪自私的老鸨,盘剥儒生,导致其最后落魄,沦为社会最底层人。围绕二人的感情,老鸨都不同程度地对他们的爱情进行了干预。《李娃传》中老鸨与李娃密谋,耗尽了荥阳生的钱财,致使其以唱挽歌为生,误了考取功名,被其父“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其楚挞之处皆溃烂,秽甚。”[1](P108)当老鸨再次见到荥阳生时,非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反而斥责李娃不该将他收留,“当逐之,奈何令至此?”[1](P108)
同样,在《曲江池》中老鸨的贪婪自私,也成为二人爱情最大的阻碍。尤其是当儒生郑元和落魄之后,老鸨多次与李亚仙争论,心里始终盘算着“他若是见了元和这等穷身法泼命。俺那女儿也死心塌地地与我觅钱。”[2](P268)她反复告诫李亚仙要远离郑元和,言辞中充满了对郑元和的蔑视。在整部杂剧四折中,第二折与第三折中,都用了大量的台词来展示这一矛盾冲突。正如高益荣在《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中所说:“元杂剧的爱情剧里,还有专门写儒生和妓女恋情的,这类剧的模式与才子佳人爱情剧所不同的是,才子佳人所反映的往往是阻碍爱情的阻力来源于门第的悬殊、嫌贫爱富的家长的反对,而士子妓女剧中破坏他们爱情的力量主要是爱钱的鸨母和有钱的商人。”[3](P121)由此可见无论是《李娃传》还是《曲江中》,老鸨的肆意盘剥、贪婪自私,皆是横在儒生与妓女的爱情之间共同的障碍。
(二)二者皆爱情的动力皆来自女子的痴情
无论是《曲江池》还是《李娃传》,两部作品中能够最终将爱情进行到底,最大的动力都来自于女子的痴情。尤其表现在对爱情的追求上,李亚仙与李娃都表现出了坚毅决绝。在《曲江池》中,李亚仙是大胆痴情的,面对贪婪无情的老鸨,她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讽“俺娘呵则是个吃人脑的风流太岁,剥人皮的娘子丧门。油头粉面敲人棍,笑里刀剐皮割肉,绵里针剔髓挑筋。娘使尽虚心冷气,女着些带耍连真,总饶你便通天彻地的郎君,也不彀三朝五日遭瘟。则俺那爱钱娘扮出个凶神,卖笑女伴了些死人,有情郎便是那冤魂。”[2](P267)不仅如此,伴随着故事中双方矛盾的不断激化,李亚仙决然不顾老鸨的辱骂反对,誓死要和郑元和在一起,“我和他埋时一处埋,生时一处生。任凭你恶叉白赖寻争竞,常拚个同归青冢抛金缕,更休想重上红楼理玉筝。”[2](P272)在郑元和遭遇了父亲的殴打,奄奄一息时,为了能够照顾郑元和,李亚仙毅然决定自己为自己赎身。李亚仙在双方爱情中积极主动,始终保持着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生活的决心。
同样,在《李娃传》中,当李娃再次见到受父亲毒打,奄奄一息的荥阳生时,李娃表现出了深切的关心与自责。面对老鸨的极力反对,李娃也不再是对她言听计从,充当她觅钱的工具,而是毅然提出抗议,表现出愿意为他而自己赎身的决绝,“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踬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况欺天负人,鬼神不佑,无自贻其殃也。某为姥子,迨今有二十岁矣。计其赀,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余,愿计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赎身,当与此子别卜所诣”[1](P108)。李娃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果决与痴情。
李娃与李亚仙,虽同为妓女,身份卑微,但她们都有着独立的人格尊严,敢于同恶势力斗争,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成为二者感情能够维持下去的最大动力。因此,在爱情主题的展现上,李娃与老鸨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于强化作品的主题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二者的爱情皆属于“才子佳人”型叙事模式
两部作品主题最大的共同之处,还在于都具有一定的反礼教性,歌颂了理想的爱情,反映人们美好的愿望。《李娃传》中,李娃本是青楼歌女,虽然得到荥阳生的追求,甘愿为他放弃考取功名,但她终究是风尘女子,按照当时儒家规定的伦理道德,她与荥阳生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在封建礼教面前,李娃没有选择的权利。同样《曲江池》中的李亚仙与李娃一样,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当爱情遇到了来自外界的阻力,是选择妥协还是选择斗争到底,两部作品均给出了同样的答复。李娃与李亚仙都大胆地迈出了这一步,面对穷困潦倒的书生时,不仅没有嫌弃他,反而顶着老鸨的刁难、反对,敢于向恶势力抗议,自己为自己赎身。如上面提到的女子的痴情,成了这两部作品爱情的最大动力。在这样的爱情中,女子的身份虽一直不被认可,但作者也在尽全力塑造她们的与众不同。两部作品中都提到故事最后,男子功成名就归来,女子表现出了异常的识大体。李娃选择远离荥阳生,李亚仙规劝书生父子二人和好,最终二人皆得到了封建家长的认可,双双都得以收获圆满的爱情。这是封建礼教作出的妥协,也是相同主题之下,创作者对于男女这份美好爱情的赞美,表达了自己最美好的祝愿。
此外,两部作品在爱情的变现方式上,依然属于传统的才子佳人戏曲模式。李亚仙与李娃虽为风尘女子,但皆异于寻常人,不仅模样出众,而且才艺超群,可以称得上是“佳人”。荥阳生与郑元和从小家境殷实、饱读诗书,身上肩负着科举的重任,自然可以算得上“才子”。正如《诗经·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才子遇见佳人自然会成就一段佳话,只是这段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会经历艰难险阻。李娃与李亚仙的爱情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阻挠,只有凭借着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积极地争取,最终才可能收获圆满。这样的结局虽然带有创作者浓郁的理想色彩,认为美好的爱情是可以战胜封建礼教,获得世人的接受和认可的,但这完全符合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并没有脱离才子佳人戏曲模式之窠臼。所以,两部作品都借助着传统“才子佳人戏曲”的模式,传达着创作者共同的爱情理想。
二、《曲江池》与《李娃传》爱情主题的不同之处
尽管《曲江池》与《李娃传》在爱情的主题上有相同的展现,但是就唐代与元代文人的社会处境来看,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两部作品在爱情主题上又呈现出着各不相同的特点。
(一)《李娃传》注重对现实世界的探索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盛期,文人士子们虽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但门阀士族制度的存在,依然是挡在文人理想与现实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一方面《李娃传》中试图通过塑造李娃这一妓女形象,让她在与士子的爱情上,能够出足够大胆地去追求,再以惯常的才子佳人式叙事模式,让故事拥有大团圆式的结局,一反以往的门第氏族联姻,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门阀士族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小说在情节的安排上,仍然表现出了对理教的妥协与让步。李娃虽然大胆、具有反抗精神,愿意摆脱自己的妓女身份,帮助荥阳生考取功名。但是,当荥阳生功成名就归来之时,出于身份地位的悬殊,李娃表现出了妥协和退缩。“其年遇大比,诏徵四方之隽。生应直言极谏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参军。三事以降,皆其友也。将之官,娃谓生曰:今之复子本躯,某不相负也。愿以残年,归养小姥。君当结媛鼎族,以奉蒸尝。中外婚媾,无自黩也。勉思自爱,某従此去矣。”[1](P109)荥阳生也没有提出挽留,甚至对于父亲当日的责罚,父子再次见面之时,已经忘掉了这一切,又能够和好如初,父子之间严格地遵守着父为子纲的伦理道德规范。多重主题相互交织着的,始终都没有摆脱封建礼教对于人性的束缚。《李娃传》在妥协与对抗的交织中,虽有着对男女爱情积极探索的一面,展现了封建礼教之下,文人士子们压抑挣扎的内心,但并没有彻底突破封建牢笼的束缚,仅仅只是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曲江池》注重对理想世界的虚构
石君宝借助《曲江池》为知识分子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正如幺叔仪在《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中提到:“尽管元代书生几乎没有蟾宫折桂和结婚姻于高门的可能性,但在爱情剧中,他们又无不克服重重障碍,仕宦上一举成名,爱情上如愿以偿。杂剧作家们在真实地揭示书生穷愁潦倒和为世俗鄙薄的同时,又为他们编织了爱情与仕宦统一的轻飘飘的美梦,聊以寄托不平、感伤、失望等等极其复杂的心理。”[4](P52)所以相较于《李娃传》主题的多元展示,《曲江池》所表达的主题则相对鲜明很多。石君宝为我们塑造了敢于大胆追求自己婚姻幸福的李亚仙,“如今奶奶年已六十岁了,情愿将亚仙身边所有,计算还你,勾过二十年衣食之用,赎我亚仙之身,与元和另寻房屋居住,教他用心温习经书,待到来年选场,必称其志。”[2](P272)作为青楼女子的她,敢于为自己赎身的愿景,传达出了她过人的胆识。面对郑元和父子反目,她表现得非常识大体,对郑元和进行劝说“今幸得一举登科,荣宗耀祖,妾亦叨享花诰为夫人县君,而使天下皆称郑元和有背父之名,犯逆天之罪,无不归咎于妾,使妾更何颜面可立人间?不若就厌衣的裙刀,寻个自尽处罢!”[2](P275)李亚仙以死相逼,主动承担过错,对郑元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使令父子二人得以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在与郑元和的爱情上,李亚仙占据着主动,始终在积极地争取,虽身为青楼女子却异于青楼女子,她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郑父的认可,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女子的不幸正是源于地位的卑贱,身为妓女的李亚仙却能够反转自己的命运,得到世人们的赞许,这足以证明了《曲江池》浓厚的理想色彩。此外,与荥阳生不同,郑元和的身上也体现着一定的自我意识。表现的尤为明显的是,在他沦落为靠唱挽歌为生时,不仅没有得到父亲的帮助和谅解,反而遭到了他的殴打与羞辱,这极大刺伤了他的自尊心。当再次见到自己的父亲时,他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从今以后,皆托天地之蔽佑,仗夫人之余生,与父亲有何干属?而欲相认乎?恩已断矣!义已绝矣,请夫人勿复再言。”[2](P275)在面对封建家长的淫威之下,郑元和走了一条异于荥阳生的道路,他不再是软弱的接受父亲殴打自己屈辱的现实,而是在自己考取功名之后,再次见到的父亲时公然的挑战。同样,在重视尊卑等级秩序的封建社会里,敢于封建家长权威,这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关于两部作品的主题,一个是积极地探索,反抗中交织着妥协,一个是作家为文人士子,编织了一个仕途与爱情皆成的美梦。他们在自我权利的追求上,各自所表现的又是各不相同的。
三、《曲江池》与《李娃传》爱情主题差异的原因
一定的时代背景影响着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心理的差异性,又在文学作品中得以直接的展现。我们可以通过对时代背景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的分析,探索造成同一题材的两部作品爱情主题所存在的巨大差异的原因。
(一)截然不同的社会背景
一定的时代有一定的文学作品。《李娃传》与《曲江池》在主题上所表现出的巨大不同,主要是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决定的。唐朝与元代,文人士子们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唐代是一个重视科举取仕的朝代,读书求取功名,是众多文人们长期以来的夙愿,也是家族对他们的期待,文人士子们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李娃传》的开篇写到:“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隽朗有词藻,迥然不群,深为时辈推伏。其父爱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应乡赋秀才举,将行,乃盛其服玩车马之饰,计其京师薪储之费。谓之曰:吾观尔之才,当一战而霸。今备二载之用,且丰尔之给,将为其志也。”[1](P103)荥阳生的父亲对他的科举之路寄予了厚望,科举致仕是当时文人士子们必须遵守的传统儒家道德规范。不仅如此,在《李娃传》诞生的唐朝时期,理学得到极大地发展,理教不断强化对人们的束缚,因此妓女在当时是不被士人们所接受的,文人与妓女也只能逢场作戏。表现在唐传奇中,虽然李娃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最终却不得已向封建理教妥协,选择离开荥阳生。她尽管最终得到了认可,还被皇帝册封为汧国夫人,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处理,也只是表达了作者最美好的诉求,毕竟仅限于文学创作之中,现实社会是断然不被接受的。
但是到了元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由于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影响上,并没有唐朝那样明显,从杂剧中可以窥见文人士子的地位、以及女性的地位在发生着变化。在对于个人幸福以及自我权利的争取过程中,元代人们表现的更为决绝和大胆。在《曲江池》中,对于父亲的无情,郑元和向父权提出了挑战,在他中举以后,在态度上他表现出了自己的愤怒,这在重视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封建时代是不被接受的。由此可见,封建礼教在元代的影响,在被弱化。幺叔仪在《元人杂剧与元代社会》中也曾提到:“他们在进入中原之前,刚刚脱离氏族社会不久,思想文化都处于比较幼稚和简单阶段。”[4](P45)也正是有了这一变化,李亚仙在追求个人的幸福之路上,才能够表现得义无反顾。因此,表现在杂剧中,除了来自于老鸨的反对,对于阻挠二人情感的其他势力都没有体现。尤其是故事的结尾,固然是皆大欢喜,仅仅只用了一首词作为结束:“亲莫亲父子周全,爱莫爱夫妇团圆。郑元和风流学士,李亚仙绝代婵娟。曲池前偶逢情赏,杏园后益显心坚。早遂了跳龙门桂枝高折,空余下莲花落乐府流传”[2](P276)。与唐传奇中历经波折终成正果不同,《曲江池》中荥阳生考取了功名,实现了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在理想的结局中实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人生之路。从这里也能够明显的感知,元代与唐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不同,最终导致了《李娃传》与《曲江池》虽为同源之水、同根之木,但也在相同之中变现出了巨大的不同。
(二)各自不同的创作心理
一定的社会制度也影响着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形成了作家的创作心理。《李娃传》的创作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上升期唐朝,传奇中的荥阳生和众多其他的儒生一样,也都必须走科举致仕的道路。因而即使是在儒生落魄以后,创作者为他设置的出路仍然是依靠科举,这也是时代的必然。《曲江池》也在极力地想走一条和之前相同的道路,然而毕竟朝代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大不如从前,即使通过科举考试,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此时统治者的重用。因而表现在作品中,剧作家为儒生编织了一个美丽的梦,也实现了仕途与爱情的统一。但《李娃传》在故事的安排上,始终没有摆脱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李娃作为一个风尘女子,按照礼教她是无法和儒生在一起的,即使她帮助了荥阳生,她的内心也是选择放弃的。此外,还有郑父所表现出的封建家长制,始终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因而在故事的结尾,作者为他们设计了一个理想的结局,李娃与荥阳生的爱情得到了郑父的认可。荥阳生的科举致仕之路,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还实现了封妻与荫子,但这依旧是按照传统的儒家意义上的规划来走的。正如程毅中在《唐代小说史》中提到:“《李娃传》的喜剧结尾,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并没有削弱多少整个故事的现实主义风格。”[5](P136)作家的创作心理,影响着作品主题的表达。《曲江池》的作者也设计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郑元和中举归来,在李亚仙的劝说下,父子和好如初,一家人幸福地在一起。写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并未涉及他们的身后事。因为元代文人地位的低下,作者极力地展现了敢于突破封建礼教的人物形象,同时,给予了李亚仙深厚的期望,希望通过她来改变儒生的尴尬境遇。这也反映了社会地位的变化对创者的创者心理产生的巨大影响。
总之,《曲江池》与《李娃传》都试图通过对情节的差异性刻画,爱情主题的差异性表现,来展示文人士子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的遭遇,同时也寄予着自己的人生诉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