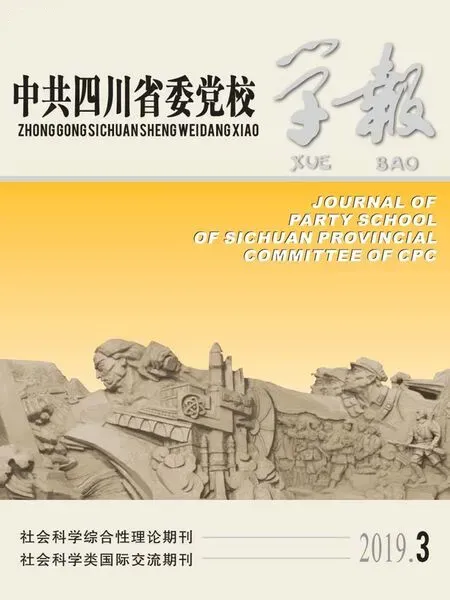长征时期红军在川康藏区的筹粮纪律
陈 红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 100091;中共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陕西西安 710008)
始终严守铁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1947年6月,朱德在冀中军区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回顾了红军的优良传统,特别提到纪律问题,并说“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1]红军长征在川康藏区的筹粮纪律,生动地诠释了朱德的这一论断。川康藏区粮食极度匮乏,面对严酷的生存威胁,红军依然能够严格遵守筹粮纪律,赢得了藏区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可以说,红军在川康藏区的筹粮纪律,是红军纪律建设的光辉典范。因此,有必要对长征时期红军在川康藏区的筹粮纪律进行深入探讨。
一、粮食问题是红军在川康藏区的突出难题
川康藏区是红军长征途经地域最广、聚集人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所处环境最艰险的少数民族地区。1935年5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三大主力在川康藏区的马尔康、若尔盖、黑水、小金、红原、松潘、茂县、康定、丹巴等地经过和停驻长达16个月。在此期间,粮食问题成为红军长征在川康藏区的突出难题,直接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
红军在川康藏区的粮食供应问题异常严峻。据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回忆 :“这一带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地区,部队严重缺粮,我们几乎天天为粮食发愁。”[2]邓颖超回忆 :“长征队伍进入四川西北部藏族地区时……粮食就更困难。只好尽力寻找各种能吃的东西来吃:挖野菜,吃死马肉,把皮带、皮包等煮了吃。”[3]甚至连红军总司令朱德也亲自带人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认识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带回来,分类洗干净,煮着吃。[4]严酷的生存环境,致使部队因饥饿、疾病、掉队而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以不负担战斗任务的一军团直属队为例,在从懋功到毛儿盖的行军途中,18天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近百分之十。[5]缺粮、断粮严重威胁红军的生命,直接关系到部队的生死存亡。
红军在川康藏区的粮食供应之所以如此严峻,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川康藏区社会经济条件落后。川康藏区地处高寒,受自然条件的限制,这里人烟稀少,生产力水平低下,物产不丰,其生活资源情况仅能在低水平上维持当地人民自给自足的生活。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共十万人在四川懋功实现会师,大量红军的涌入,其每天的粮食消耗远远超出了藏区的承受能力。第二,藏民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国民党利用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地方土司向藏族群众作反动宣传,污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劫掠奸淫,对于一切宗教,无不毁灭净尽”[6]。当地反动政府颁布惩治条例,规定“凡帮助红军引路者,帮助红军作通司者,或卖粮食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实行坚壁清野者,则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如不听从其指挥同红军作战者,亦作‘叛逆论’”。[7]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所到之处藏民纷纷逃避,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红军筹粮必然十分困难。第三,红军队伍庞大且驻留时间长。红一、四方面军进入川康藏区后,很快便认识到这里粮食缺乏,加之没有群众基础,不能养大兵,不宜成为根据地。既然川西北地区不适于创建新苏区,那么尽快确定战略方向,摆脱于己不利的被动局面,是红军破解生存危机的关键。然而,围绕红军发展的新的战略方向,张国焘与中共中央发生严重分歧。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张国焘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或者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为了统一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并确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新战略方针。但是,会后张国焘却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不执行军委计划。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反对,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方针和为执行北上方针而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中央又相继召开了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巴西会议,重申北上方针,力促张国焘行动。为此,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停留了近三个月,无疑加重了粮食供应的危机。1935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到10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南越夹金山进行天、芦、名、雅战役,约九万红军在该地区境内又停留一个多月,近2万留守部队和后方机关、医院等在大小金川地区驻扎近10个月。1936年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5万红军又用一个月时间从川康藏区过境北上。红军队伍庞大且驻留时间长,面对如此大的粮食需求,只能维持粮食自给的川康藏区自然难以承受,筹粮的艰巨性不言而喻。
然而,数万红军面临严重的饥饿乃至生存威胁,粮食必须筹集。因此,红军只能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粮食。据萧锋回忆,“各单位找粮的办法很多,尤其是工兵连,挖地窖的办法多”。[8]李德也回忆道 :“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9]时任11团团长王平也回忆说 :“当时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10]在广阔荒凉的藏民区,粮食就是生命。红军的筹粮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与民争食的客观现实。于是,“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11]原本就很紧张的民族关系更易演化为民族冲突,在诺那活佛和土司头人的鼓动和指挥下,藏民采取各种方式进攻、袭击红军,有的组成骑兵队伍,在草原上流动作战;有的隐匿山林,向红军打冷枪;有的专门捕捉杀害红军的伤员和掉队者。[12]因粮食问题而导致的民族冲突和矛盾更加激化。
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及时制定符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川康藏区实际的筹粮政策,平衡藏民利益与红军粮食供应需要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严格的纪律保证筹粮政策的落实,规范粮食征收人员的筹粮活动,成为红军在藏区筹粮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长征时期红军在川康藏区的筹粮纪律
(一)明确筹粮的政策纪律
为有效、规范地筹集粮食,红军颁布了一系列体现党的民族政策的指示、训令和办法,规定了部队在藏族地区筹粮的基本政策、工作纪律和筹粮方法。1935年6月25日,红军总政治部颁布《关于收集粮食事的通知》,对购买粮食的政策界限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的向群众作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同意不应强迫购买”。[13]7月1日,周恩来、朱德和张闻天等发布《中央决议售粮政策》,再次强调不得侵犯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除没收反动头目的粮食外,其他应照价收买。[14]但由于藏民实行坚壁清野,购买粮食难度很大,筹粮远未达到预期的效果。7月3日,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提出克服粮食困难是“具有严重的战略意义的任务”,要求采用没收、搜山、收买等一切方法筹粮,对纪律的强调更为严厉。要求“严禁侵犯群众尤其是番人、回人的一点利益。绝对禁止强买粮食,私人买粮食,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等。搜山所得的粮食,必须切实查明所有者,如系群众和番人、回人的,必须一律给足代价,现钱缺乏时,应以茶叶等物付价,或给卖主以购买凭单开明所买之物,令其到理番或杂谷脑将单换取同样价值之茶叶,或等待将来红军派人持现钱调回该凭单。此种凭单师以上之政治部才有权印发并须保留存根。”[15]7月5日,中革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筹措粮食的办法致各军团电,再次重申了上述筹粮政策,并强调“搜山时应特别注意纪律,并严禁私匿不报”。[16]
由于川康藏区粮食极度匮乏,红军还一度面临过无现粮可买、可借的困境,部队不得已采取了用割地里青稞的办法来筹集粮食。为统一、有计划地收集粮食,不引起藏民的反感,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收割番人麦子问题的通令》,严格规范红军战士的割麦行动。《通令》要求,“各部队只有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等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只收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熟的麦子及洋芋等”“严格禁止私人到田中去拔麦子和青菜,禁止马匹放到田中去吃麦子”等。[17]可以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通令》最大程度降低了对藏民利益的损害。
总之,红军在藏区的筹粮政策充分体现了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一方面,通过统一、规范征集粮食的办法以及自愿、公平的买卖政策,兼顾了藏区群众的利益和部队的粮食供应需要。另一方面,尽可能从土司头人等剥削者手中征集粮食,尽量少牺牲普通藏民的利益。这些基本的筹粮纪律,红军在川康藏区的整个筹粮活动中曾多次强调。
(二)保证筹粮纪律的执行
筹粮纪律制定后,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是关键。为此,红军采取多种措施确保筹粮纪律的严格执行。第一,反复进行纪律教育。红军第一军政治部集中抓纪律整顿,在干部中,以师及军直为单位,召集排以上干部、党的支委、小组长,由军政首长亲自上课,上课后以连或营为单位进行讨论;在战斗员中,依照纪律问题的政治课材料,以团或连为单位上了三次政治课,并利用军人大会或早晚点名时间着重进行教育。[18]红二方面军将红军对番民的政治纪律作为教材“上过课”,并且“在关于征集给养的补充指示中又加以解释补充,在收集给养时提出如何尽量不侵犯群众利益与反对脱离群众的行为,并在各种会议中均提出过很多次”。[19]第二,批驳红军中存在的错误思想。除了正面倡导遵守筹粮纪律外,还必须对一些错误理论进行批驳。如针对在少数人中流行的“红军不能等群众回来了再吃饭,不侵犯群众是迂腐之谈,不侵犯群众就没有饭吃”的错误理论,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些少数同志已经在困难的面前动摇和发狂,忘记了红军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是红军生命所依托的基础”。[20]第三,严格监督与检查筹粮活动。红军为确保纪律的严格执行,专门设立了纪律检查队并经常检查。政治军事机关也常派人检查纪律执行情况,连队还专门设立检查员分配党团员负责保障纪律的执行。[21]割麦筹粮时,总政治部要求各政治机关和指导员不仅要详细传达与解释《关于收割番人麦子问题的通令》,而且要每日派人去检查,对于严重违反《通令》的人,送裁判所裁决。[22]
(三)严惩违反筹粮纪律的行为
在具体的筹粮实践中,尽管大部分红军都能够遵守各项筹粮政策和纪律规定,但仍发生了个别违反纪律的情况。如搜集粮食群众不在家而不放价条,借搜山、收集粮食等名义擅入民家乱翻、乱拿、乱捉人、烧房子,侵扰寺院等。对于这些违反纪律的现象,若放任不管,必然会使群众越跑越远,加强藏民对红军的坚壁清野和仇视态度。因此,红军不惜采取严厉措施,惩罚违反筹粮纪律的行为。红四方面军规定,对违反纪律的行为,“不惜严厉制裁直至枪决”[23];红二方面军“曾禁闭违犯纪律的分子举行公审,在组织上处罚对违反纪律的直接负责者”。[24]据黄克诚回忆,“有的同志饿得受不住,偶尔会发生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25]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贺子珍的弟弟、毛泽东的妻弟贺敏仁。长征时贺敏仁是一个红小鬼,在一个团当司号员。来到藏区后,由于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和几个战士偷偷地进到一座喇嘛寺,想找点吃的。吃的没找到,但发现了一些铜板和银元,贺敏仁竟违反纪律,擅自拿了一些银元想换些粮食吃,其所在师部得知此事后,为严肃军纪,下令将贺敏仁枪毙。[26]采取这样的惩治措施,今天看来似乎过于严厉,但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长征那种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只有保持铁的纪律,才能对所有红军战士起到强烈的引导和警示作用,才能保证命令的坚决贯彻执行,才能赢得群众支持,保证红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长征时期红军在川康藏区筹粮纪律的成效
长征时期,红军在川康藏区严格执行筹粮纪律,争取到了少数民族广大群众和上层爱国人士的支持,勉强解决了红军在川康地区的生存问题,最终赢得了长征的胜利。红军在川康地区的筹粮纪律,是红军纪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藏区工作打下了基础。
红军严明的筹粮纪律,维系了部队的粮食供给。由于党和红军制定了正确的筹粮政策和严明的纪律,加之红军领导干部反复督促和以身作则,使藏区民众看到了红军的诚意和秋毫不犯的严格军纪。因此,广大藏民愿意将粮食卖给红军,甚至赠送给红军。在这方面,藏族民众给予红军的帮助是巨大的,沿途为红军提供住宿、粮食、衣物不计其数。如四川阿坝人民“共为红军筹集粮食2000万至3000万斤,大小牲畜20万头,土盐5000余斤,还有大量干牛肉、猪膘、食油、蔬菜等。”[27]在黑水的售粮群众中,最多的一户售粮达三百斤至四百斤。石碉楼罗丁寨藏民苍克扎等人与该寨五十八户人家商量确定,每户售给红军面粉七十斤,共达四千斤。子木河、瓦岗寨、维古、色尔古等,许多藏民联户集粮售献给红军。黑水和茂县邻近的大、小瓜子寨及赤不苏沿河两岸共有十七座水磨,日夜为红军磨面,历时一月多,共磨面粉十五万斤左右,并由当地群众运送到维古三军团筹粮队安排分配。[28]尽管这一时期,部队的物质生活依然十分艰苦,因粮食严重缺乏而造成红军减员现象依然存在,但这却是藏区人民节衣缩食的口粮,藏族同胞为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这一牺牲是值得的,这些粮食维系了部队的供给,保存了党和红军的精华,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藏区群众对红军的粮食支援,党的领导人始终难以忘怀并心存感激。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对埃德加·斯诺说 :“这是我们欠下的唯一外债”“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那些东西。”[29]邓小平1950年7月21日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评价说 :“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慌了,没有办法……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30]
红军严明的筹粮纪律,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长征以前,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基本没有什么了解,对红军的民族政策更不知晓。据许世友回忆,进入藏区后,“社情极其复杂,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的统治和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的煽动下,民族隔阂较深,使我们红军在这一地区难以站稳脚跟”。[31]面对这一局面,红军通过发布安民布告、散发传单、张贴或錾刻标语、召开群众会议、通司(翻译)做工作等方式大力宣传红军的政策,使藏族群众对党和红军的主张有所了解。伴随着红军持续、深入地开展工作,特别是通过诸如筹粮工作这样的具体实践,红军以言行一致的宣传和行动瓦解了国民党的污蔑言论和不实宣传,使广大的少数民族同胞消除了对红军的疑惧和隔阂,知晓了红军的民族政策和宗旨主张。事实上,党和军队的纪律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真正紧贴作战、生活实际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规范。红军在藏族地区粮食供应发生极大困难,出现绝粮乃至饿死的严重情况下,仍然坚守严格的政策界限,严禁侵犯藏区群众的利益,让藏族同胞看到红军是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为民服务、为民打仗的军队,不同于以往的军阀部队,不仅赢得了藏族上层和宗教界人士的支持,而且树立了红军在藏区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藏区的影响。长征也真正起到了播种机、宣传队的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力将继续延续下去,为以后中国共产党较好地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打下了基础。
红军严明的筹粮纪律,锤炼了红军铁的意志和作风。一般来说,部队在流动作战、粮食供应不足、面临生存威胁的情况下,最容易发生破坏群众纪律的现象,而不加约束或约束不力导致军纪败坏、军民对立乃至全军覆灭的先例,在中外战史上屡见不鲜。这也是国民党这一时期调整军事部署,将红军围困在川康藏区的目的。然而,红军凭借坚定的信仰和严明的纪律,严格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和民族宗教政策,经受住了饥饿乃至死亡的严峻考验。当然,在此期间,红军也经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困苦,为了生存和革命,不得不采取打野生动物、挖草根、挖野菜、剥树皮等方式来充饥,甚至皮张革履、死牛烂马、“神仙土”和马粪中残留的粮粒,也成为了战士果腹的“食物”。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军在筹粮活动中依然尽一切可能减少对藏民利益的侵犯,尊重藏民群众的宗教、风俗和习惯,严格执行筹粮纪律。比如,红一方面军四团在黑水筹粮时,战士们偶然发现一喇嘛寺的“泥塑”中装有面粉,搬回来准备吃时,筹粮委员会来了命令,说要保护喇嘛庙,就是国民党军队砸烂的“泥塑”也不能动。于是,战士们只好原封不动地把“泥塑”送还了寺庙。[32]严格的党纪军纪,进一步锤炼了红军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优良的工作作风,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红军克敌制胜、走向胜利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