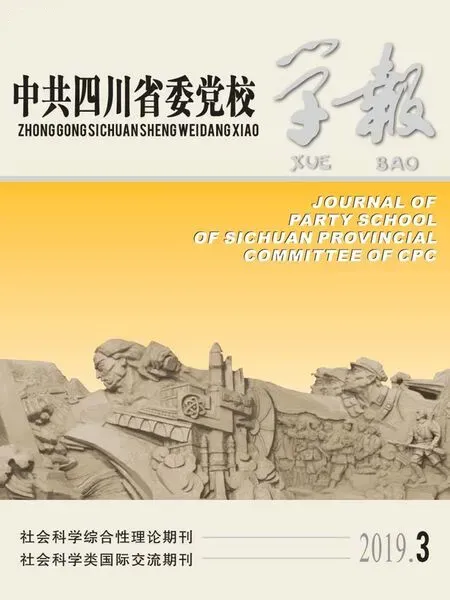“忠”德的传统阐释与现代转换
彭龙富
(中共娄底市委党校,湖南娄底 417000)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君子文化中,“忠”是极为重要的德目。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精心培育和反复塑造的正面人格,即是被历代中国人广泛尊崇的“君子人格”。而“忠勇孝悌廉”“仁义礼智信”及“温良恭俭让”等为人处世的伦理规范、美好品德,最终沉淀、融入和升华到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身上。无疑,“忠”德被视为君子的重要品格之一,理所当然也跻身传统主流道德行列。作为一种重要品格和主流道德,“忠”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丰富的内涵。相对于今天的品格与道德,传统之“忠”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如同对待传统文化,对待“忠”德也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现代转换。
一、 “忠”德的传统阐释
《说文解字》中说 :“忠者,敬也,尽心曰忠。”从造字也可知,忠,存心居中,正直不偏,古以不懈于心为敬,故忠从心;又以中有不偏不倚之意,忠为正直之德,故从中声。“忠”的基本要求是“尽心”,尽心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但人和事往往是相连的,故对他人、对国家等,始终如一、竭尽心力,都谓之“忠”。为便于讨论,大致将忠的对象分为人和事。从人的角度,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向上的层面,如国君、帝王、主子等;平等的层面,如朋友、亲戚、同辈等;向内的层面,即自我。从事的角度,也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对国家的忠,二是对职事的忠,三是对言行的忠。
(一) 从人的角度:忠于君王、忠于他人、忠于自我
1. 忠于君王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君(王、帝)为中心,实行君权至上和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忠的第一功能,是政治使命。因为事君对于主体道德有着极高的要求,所以孔子主张从两个方面践行“忠君之道”:一方面“事君尽礼”,即按照礼的规定来事君,做到“敬其事而后其食”与“勿欺也,而犯之”;另一方面“事君以道”,“道”是“礼”之上的更高道德范畴。孔子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因而孔子的“事君”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对君的绝对服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这种尊“道”而不屈“势”的选择,体现了君子人格的独立精神与独特价值。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事君”问题上讲利君,讲顺从,帮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荀子的“忠君”同样不是唯唯诺诺式的“忠”,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为己贼也”(《荀子˙臣道》)。也就是说,臣子劝谏、苦诤、辅助、匡正国君,固然是为了利君,但君有明君、暗君之分,所以“从道不从君”。可见,荀子与孔子的“忠君”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在历史的变迁中,“忠君”思想被不断修正和强化,“随着儒家伦理被选择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本身已经取得作为社会政治生活、法律制度和臣民日常伦理生活与道德行为之普遍指南和规范的社会合法性,由此也成为了支配人们道德生活的主导伦理”。[1] 129到宋元以后,“忠”远远超越孝、节、义等众德,日益成为桎梏人的精神枷锁和钳制人的思想工具。“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韩非子˙忠孝》)“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子˙忠孝》)“一马不鞴双鞍,忠臣不事二主”(《名贤集》)“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二;此人道之大伦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资治通鉴》),诸多言论强调的无不是“忠君”的专一性、绝对性,以至于言君必称忠,尽忠近乎愚。如果抛开阶级性不谈,历史上伊尹、箕子、比干、子胥、平原君、信陵君、诸葛亮、狄仁杰、文天祥、方孝孺、曾国藩等,大都因忠而名扬后世。而庆父、赵高、梁翼、董卓、来俊臣、安禄山、李林甫、魏忠贤、吴三桂等,大多因奸而臭名昭著。史上纵横一时、勇冠三军的吕布之所以为世人所不耻,根本原因在于不忠不义。吕布杀丁原、诛董卓、叛刘备、勾袁术,所作所为皆为个人私利而罔顾道义。陈寿认为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覆,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三国志》),可谓允当。吕布“为世人所不齿的真正原因乃是其弑杀故主的行径严重触犯了当时社会上盛行的忠君观念,而非仅仅因其‘轻于去就’”。[2]
2. 忠于他人
《论语》里说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话强调的是对他人的忠诚。如果把“忠君”视为一种政治使命,那么“忠人”则可视为一种道德使命。前者是向上的层面,后者是平等的层面。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忠”,侧重于人际交往的尽心尽力、一心一意。这个范畴的“忠”,往往与“信”相连,与“恕”对接,故常有“忠信”“忠恕”的说法。忠信,忠诚信实,如“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发”(《朱子语类》)“非忠不立,非信不固”(《国语·晋语二》)“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朋党论》)。忠与信是相互补充、相互映衬的关系。早在先秦时期,忠信便作为一种交际原则,广泛应用于交际,并成为君子的重要品格之一。后经历代思想家、教育家的宣扬,忠信始终被视为高尚的品格加以推崇。忠恕,忠诚宽恕,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作为儒家伦理范畴,同样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而且强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实际上都是“忠恕”。忠与恕是相互规定、相互包容的关系,即“你希望人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人”,而不是对自己一套标准,对别人一套标准。如果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另当别论。所以,“忠恕之道”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对自己多限制,而不是对他人多要求,强调在实际接人待物中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自己的要求是“忠”,对他人的态度是“恕”。因此,这个“忠恕”兑现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消解对私己的偏执,从而保证人我、人物各在其身的限度内有所成就的过程。无论是忠信还是忠恕,前提都是与他人相处或交往时要“忠”,即心无二心、意无二意。
3. 忠于自我
在“忠”德的解读与实践上,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古代政治体制中发展出来的为臣之道——策名委质,策名委质,致死无二;另一种则是先秦儒家所讲习论说的待人处世之道——诚身明善,从道守义。”[3] 246亦即前文所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忠和平等主体之间的“忠”。然而,在这两种类型之外,还有自我对自我的“忠”。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始终缺乏对于个体的足够重视。长期以来,由于专制主义横行、等级秩序森严、封建礼教禁锢、公私领域模糊等因素,几乎不存在“独立个体”,更遑论“个体意识”。特别是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主张“格万物以强调社会个体对纲常伦理的绝对遵守,将个体人心与天伦大道合一,把个体情欲完全从社会理性中驱逐,以道德理性充斥人心,从而将血肉之躯彻底变成理性大道支配下的木偶神雕”。[4]在这样的大背景、大环境下,“自我”的空间,“心灵”的空间,也就几近于无。虽然个体一度被忽略、排挤和压迫,但不同历史时期还是存在个体的觉醒、挣扎和反抗。如,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且不论这个“矩”是自然之道、天地之道,还是三纲五常、清规戒律,虽然“不逾”,但至少一定程度上“从心所欲”了。而道家的创始人和思想奠基者老子,“忠于内心”更为明显。老子曾经提到过君子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道德经》)这里,老子认为一国的统治者,应当“静”、“重”,而不是“轻”、“躁”。在老子心里,“君子”还强过“万乘之主”。“万乘之主”轻率而失去根本,急躁而丧失主导,“这种轻躁的作风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立身行事,草率盲动,一无效准”。(陈鼓应语)而“君子”不同,他们“虽有荣观,燕处超然”。这种人生态度,实际上就是自我对自我的忠。换言之,因为君子具有“燕处超然”的心态和能力,在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时,也就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不会因外物的好坏和自我的得失而或喜或悲。无疑,能够抵达这样的境界,主体与客体是“忠于”的关系,是“忠于自我”。荀子也说 :“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荀子·非十二子第六》)也就是说,君子的为人处世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立身立业坚持操守是自发的、自觉的、自律的,而不是为了让别人尊重自己、相信自己、任用自己才“作之不止”。正因为君子能够忠于自己,忠于内心,所以不为荣誉所诱惑,不被诽谤所吓退,遵循道义来做事,严肃地端正自己。如果不忠于自己,不忠于内心,往往被外界事物所左右,或趋利避害、乘风扬帆,或见异思迁、背信弃义,也就不是真正的君子,而成了“伪君子”。人们常说“言为心声”“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名副其实”等,一方是“言”“知”“表”“名”,另一方是“心”“行”“里”“实”,两方是吻合的、一致的,此方“忠于”彼方;相反,“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貌合神离”“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等,一方是“口”“阳”“貌”“栈道”,另一方是“心”“阴”“神”“陈仓”,两方是错位的、背离的,此方“不忠”彼方。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特意指出“忠己”的概念,但对自我的“忠”理应是传统“忠”德的一部分。
(二) 从事的角度:忠于国家、忠于职事、忠于承诺
“忠”德不仅施于主体及主体以外的人,还应施于主体所在的国家,主体所从事的工作,主体所许下的承诺等。因此,忠于国家、忠于职事、忠于承诺等,是“忠”德的另一组成部分。
1. 忠于国家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家国情怀的培养。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家国思想,可谓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千百年来,关于家国的诗词名句代代相传,传唱不息。“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屈原《国殇》)“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曲》)“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岑参《送人赴安西》)“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飞《满江红·写怀》)“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陆游《病起书怀》)“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齧空林”(郑思肖《二砺》)“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郑成功《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寸寸山河寸寸金,侉离分裂力谁任”(黄遵宪《赠梁任父母同年》),字里行间渗透的无不是强烈的家国情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家国思想,中国人群体意识里被灌输了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特别是在礼崩乐坏、内忧外患、救亡图存之际,从君子名流、仁人志士到黎民百姓、贩夫走卒,无不挺身而出,慷慨赴义。为了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独立,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者大有人在。他们顾大义、重气节,义不负心、忠不惜死,书写了一曲曲悲壮的忠义之歌,表现了对国家、民族的大忠大义。由于历代统治者把“忠”作为重要的政治手段拉拢人心、维护秩序,致使中国传统社会的家长与家族、君王与天下往往是合为一体的。因此,对父的忠、对君的等同于对家的忠、对国的忠。当“君”幻化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象征,忠君实际上是忠国,爱君实际上是爱国。所以,历史上的“忠国”、“爱国”,阶级性、局限性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自孟子起,就有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之后同样有人主张社稷、天下在君主、皇帝之先,比君主、皇帝要重;再到后来,忠国与忠君的区别也就更多、更大。如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就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应该始终将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社会的价值标准“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为此,王夫之提出了“仁植义育”、“扶长中夏”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维护中世纪君主专制的纲常名教发出了强力的冲击,这一思想虽然“表现出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但它以民族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世纪的君主专制思想,反映出早期启蒙思潮理论上的深邃”。[5]经过中国现代思想的新陈代谢,“忠君”意义上的“忠”逐渐被舍弃,而“忠国”意义上的“忠”却不断创新与发展,呈现蓬勃的生命力。
2. 忠于职守
传统的“忠”德也包括对职业、事业的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第十四章》)“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庄子·达生》)“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二程·粹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后出师表》),虽然明里无一“忠”字,但道理却都是忠于职业、事业,即凡做一件事情便全副精力集中到事上,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忠经》里的《冢臣章》《百工章》《守宰章》《兆人章》等,其实就是古人的职业道德规范,如“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成。冢臣于君,可谓一体,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岂惟奉君忘身,徇国忘家,正色直辞,临难死节而已矣”(《忠经·冢臣章第三》)“是故只承君之法度,行孝悌于其家,服勤稼穑,以供王职,此兆人之忠也”。(《忠经·兆人章第六》)特别是对于官员,更强调忠于职守。如果“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汉书·朱云传》),则被讥为“尸位素餐”。明代吕坤说 :“古之居民,上者治一邑则任一邑之重,治一郡则任一郡之全,治天卞则任天下之重。朝夕思虑其事,日夜经纪其务,一物失所不遑安席,事失理不遑安食。限于才者求尽吾心,限于势者求满吾分。”(《呻吟语·卷二》)如果愧于“君之付托、民之仰望”,却又“食君之禄,享民之奉”,那实在是恬不知耻。历史上的李冰、张衡、徐霞客、郦道元、李时珍、宋应星等,都是忠于职守的典范。无论士农,还是工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和职责,“君子尽忠,则尽其心,小人尽忠,则尽其力。尽力者,则止其身,尽心者,则洪于远”。(《忠经·尽忠章第十八》)如果“天下尽忠”,则“淳化而行也”。
3. 忠于言行
中国古人十分看重言行一致,强调说到做到、立言立行。因此,一诺千金、一言九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都是对不食言、守信用的褒扬。而轻诺寡信之人、出尔反尔之人、朝令夕改之人,多为世人所鄙夷。古人强调“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言必行,行必果”(《论语·子路》),说明“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既然答应了、同意了,就要去履行、去兑现,否则就是“不忠”。孔子认为花言巧语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朱子也说“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朱子集注》)。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言语修饰得非常好,说话时脸色容貌形态装出非常善良的样子,让别人以为是个善人,是个君子,其实是居心叵测、虚伪狡诈。这种人,本心之德已经亡失,一旦原形毕露,必然遭到唾弃。而且,中国传统文化里还主张“以正辅人谓之忠,以邪导人谓之佞”,(《盐铁论·刺议第二十六》)即“用正道帮助人叫做忠诚,用邪道引诱人叫做伪善”。强调“为人谋忠”的同时还“教人以善”,这种“忠善”极大地凸显了传统“忠”德所蕴含的“正能量”,至今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二、“忠”德的现代转换
“忠”德是中国君子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现代社会,对待“忠”德如同对待君子文化、传统文化一样,必须“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坚持实践观点、矛盾观点,使之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对接、互鉴和贯通,从而实现现代转换。
(一)利用传统“忠”德培育爱国为民的高尚情操
“忠君”意义上的“忠”,经过几千年的道德变迁,特别是进入近代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土崩瓦解已被舍弃。但“忠”的对象可以从“君”置换为“民”,“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不能不要的……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6]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依靠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才能推进历史、改变历史,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重则失国”。(《大学》)同样,君可以不要,国不能不要。传统的“忠”德十分关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弘扬“天下为公”“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个中包含的爱国意识、爱国观念,与现代的爱国意识、爱国观念是高度契合的。传统的国家与现代的国家,在地理层面、政治层面、民族层面、文化层面等层面,有着重大的区别。不同历史时期,爱国的内涵也不一样。但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捍卫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等,无论什么时候都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现代社会的爱国,“体现了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揭示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的家园及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和荣誉感的统一,从本质上是个人对祖国价值的全面认同,爱国土、爱民族、爱国家这三种情感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自然情感、社会情感和政治情感的高度统一”。[7]“爱国主义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民族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8]1进入新时代,作为中华儿女,应当自觉培育爱国为民的高尚情操,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人民,做有益于社会的人。
(二)利用传统“忠”德培育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
历史上,忠于职守的例子不胜枚举,“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安书》)这里,司马迁的原意是,《周易》《春秋》《离骚》等大都是圣贤为抒发郁闷而作。但换一个角度,如果诸位圣贤无心思“作”、不坚持“作”,怕是也无“作”流传后世。以司马迁自己为例,也是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才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才成了“天地间第一等人”。不然,因李陵之祸而含冤入狱,遭受宫刑,司马迁纵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也是难以忍辱含垢十四载、奋笔疾书百余篇。这种坚持,理所当然谓之“忠”。在传统的道德语境中,对待职业、事业尽心竭力、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恪尽职守等乃是忠的表现。这种“忠”德,体现了中国古人对美好生活和事业的一种执着和追求。尽管古人大都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角度来谈忠于职守,但如果赋予忠以时代的新内容,忠勤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忠于职守”可以转换为对岗位的热爱、对职业的敬重,亦即“爱岗敬业”。众所周知,“人类总是在具体的职业生活中通过自身的实践和探索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一实践和探索的过程既表现为人类突破自身存在局限性以及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需要,也表现为人类对外在客观世界以及借以改变外在客观世界,实现自身价值最直接的方式——职业劳动——的一种基本态度。就此而言,作为人类职业生活中一项普遍的道德要求,‘敬业’不仅关涉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更关涉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9]“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荀子·议兵》)任何领域任何行业的从业者,都应具有爱岗敬业的职业道德,发扬“干一行,爱一行”的精神,才有利于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实现。
(三) 利用传统“忠”德培育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职守、忠于自我等,种种“忠”的背后,也是忠于理想信念。历史上,屈原是忠君爱国为民的典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楚国重要的政治家。为了复兴楚国,屈原将生死置之度外,无论是对楚怀王提出忠告、希望,还是举贤授能、变革图强,都是对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坚守和追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正因为怀有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屈原不断追求,不畏艰险,才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千百年来,执着于理想、忠诚于信念,始终是中华儿女人生舞台上的主旋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理想信念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理想信念不仅关系到个人思想灵魂的成长健全,更关系到社会民族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一个人有了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就有了精神寄托、人生动力和努力方向。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存在理想信念有无的问题,只有自觉还是盲目,清晰还是模糊,高尚还是卑微,坚定还是动摇,先进还是落后的区别。崇高的、坚定的、先进的理想信念,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和个人发展有着重要的方向指引和动力支撑作用。”[10]忠于这样的理想信念,能够砥砺优良品质,掌握真才实学,练就过硬本领,成就杰出事业,正所谓“功崇惟志,业广唯勤”(《尚书·周书》)。反之,有的人拒绝理想信念,漠视理想信念,导致精神空虚、底线失守,进而在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滑坡、生活上堕落,不仅个人发展一败涂地,还影响到家庭、社会和国家。近年,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思潮纷繁激荡,思想变化碰撞交锋,如果缺失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不正确、不纯洁,抑或原本正确的、纯洁的理想信念发生动摇、走向蜕变,也就容易心迷意乱、出轨离辄,严重者还身败名裂、祸国殃民。因此,只有忠于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才能“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南西北风”。(郑燮《竹石》)
(四) 利用传统“忠”德培育诚信友善的美好品质
传统的“忠”德里,忠信、忠恕占有一定的比重,并长期视为人际交往的美德法则、责任伦理和道德要求。虽然传统的“忠信之道”“忠恕之道”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从人际交往的角度以及从人性相通的层面讨论,这种信、恕的为人处世原则用于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同样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传统的“忠信”可以转化为真实做人,即光明磊落、坦荡心正;诚恳待人,即态度真诚,行为无欺;重诺守信,即说到做到,忠于托付。而传统的“忠恕”可以转化为对人友善,即没有利益交往时,做到与人为善,言谈举止亲切近人;有利益交往时,做到推己及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发生利益冲突时,做到宽宏大量,不占便宜不怕吃亏。诚信是处事的金律,友善是和谐的纽带。坚持诚信友善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该培育诚信友善的美好品质,倡导人人以诚信待人,人人以友善待人,最终利人利己、利国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