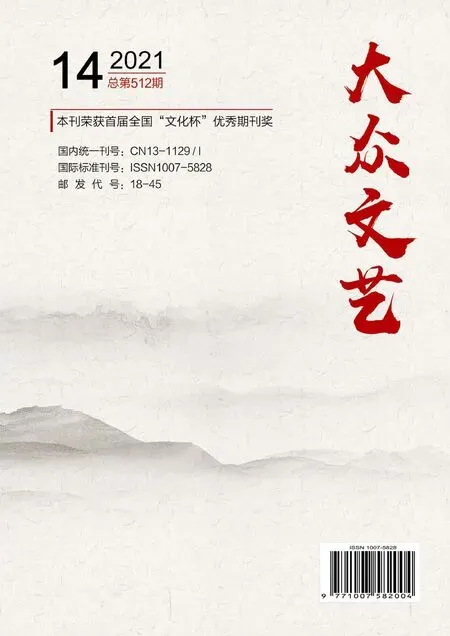严遵《老子指归》“神明”释义
陈一鸣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 173000)
西汉中末期社会矛盾加剧,政治危机日益深重,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背景中,严遵通过《老子指归》一书,申明自己的志向,借此表达对生命及社会的关怀。蜀郡有一位叫罗冲的富豪问严遵“君何以不仕者?”严遵回答说:“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财货和名声是损神杀身之物,会损害“神”和“身”,因此,严遵选择遁世以保存“神”与“身”。可见,“神”在严遵的养生之道中占有重要地位。《老子指归》中亦有多处论及“神”或“神明”,一般认为,“神”为“神明”之略称。1“神”不仅是养生之要,在宇宙生成论中,“神明”是沟通“德”与“太和”的中间环节;就个体生命而言,“神明”是生命之本,是保存自我的关键;就治国理政来说,君主秉受“神明”,才能体百姓之心,察天下之情。
一、“神明”与“气”
《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指归》释“二”为“神明”,“二物并兴,妙妙纤微;生生存存,因物变化;滑淖无形,生息不衰;光耀玄冥,无向无存;包裹天地,莫睹其元;不可逐以声,不可逃以形:谓之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智力不能接而威德不能运者,谓之二”(《卷二·道生一篇》)。从状态来看,“神明”无形、无声,其作用却不可忽视,存于物中则物存,离物而去则物亡。如何理解“神明”呢?
一般认为,“神明”是一种“气”。而这种“气”类似于《管子·四篇》中所述的“精气”,此观点参采王德有《<老子指归>自然观初探》一文。
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於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於胸中,谓之圣人。2
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3
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4
…为天地始、阴阳祖宗,在物物存,去物物亡:无以名之,号曰神明。生於太虚,长於无物,禀而不衰,授而不屈,动极无穷,静极恍惚;大无不包,小无不入,周流无物之外,经历有有之内…为道先倡,物以疏瞿,受多者圣智,得少者痴愚。(《卷七·生也柔弱篇》)
身之所以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卷三·圣人无常心篇》)
神明…存物物存,去物物亡…。(《卷二·道生一篇》)
《管子》中论述“精气”时提到:万物都有精气,万物依赖精气而获得生命;在地生成五谷,在天聚为众星。精气流散在天地间,便称为天地精神;藏储在胸中,便成为圣人智慧。从“精气”与“身”的关系来说,“精气”在“身”,往来无定,神妙莫测。失掉它则身心必乱,得到它则身心自理。从生命的形成来看,“精气”是生命的根本,有了“精气”就能获得生命,有了生命就能思考,有了思考就能生出智慧,有了智慧便能体悟处身行事之道了。
严遵论述“神明”,从状态上是“滑淖无形”,从范围来看,“神明”周流于无物存在的境界之外,流历于有物存在的领域之内,秉受“神明”多的人则有智慧,反之,痴愚。从生命本质来看,身体之所以成为的身体,是因为“我”的存在,而“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住进了“我”的身体,“神明”是生命之“我”存在的本质。从万物存在来说,“神明”是万物存在的根据,“神明”存在则物存在,“神明”离去则物亡。
《管子·四篇》亦有关于“神明”、“神”、“精”等论述都是指“精气”,“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5,“精也者,气之精也者”6,从“精气”和“神明”的状态、流布范围、生命本质及万物之存在来看,它们的特征与功用相似。《指归》中又把“神明”称为“神气”,“夫无形无声而使物自然者,道与神也;有形有声而使物自然者,地与天也。神道荡荡而化,天地默默而告;荡而无所不化,默而无所不告;神气相抟,感动相报”(《卷六·言甚易知篇》)。严遵把这种滑淖无形、变化纤微、与物糅和、弥漫空间的气称之为“神气”,而《指归》中的“神”和“神气”即“神明”。
“道德神明、清浊太和,浑同沦而为体,万物以形”(《卷三·出生入死篇》)。《指归》认为道德神明、清浊太和、天地万物都是由气的变化连通一体的,郑万耕认为道德神明、清浊太和分属“浑沌一气”的不同阶段,而所谓“神明”是“阴阳二气的功能和作用”7,万物生成过程中,从“浑沌一气”的状态进而由阴阳二气交互作用,又相互离异而分化出来,“阳出阴入,与道卷舒”(《卷二·至柔篇》),事物发展随阳而出随阴而入,与道一起卷曲展舒。《指归》把“神明”与“阳气”并论,“神明、阳气,生物之根也”(《卷七·生也柔弱篇》),“柔弱和顺,长生之具而神明、阳气之所托也”(《卷七·生也柔弱篇》)。严遵把神明与阳气并论,申明它们的作用,是生物之根,生命长生之依托。
由此可知,“神明”即气,“神明”在万物生化过程中由阴阳二气演化出“太和”,间接生化天地万物,但它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无处不在,是万物生命之本,阴阳二气交互作用,万物凭此生长消息。
二、存“神”以成物
严遵借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范式构建了自己的宇宙生成论,同时给“一”、“二”、“三”赋予了具体内容,提出“天地所由,物类所以:道为之元,德为之始,神明为宗,太和为祖”(《卷一·上德不德篇》),“一”、“二”、“三”分别对应“德”、“神明”、“太和”。严遵继承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描绘了宇宙发展的总趋势。在这个宇宙生成模式中,“神明”蕴含两层含义,从万物生成来看,“神明”是连接“德”与“太和”的中间环节;从万物存在来看,“神明”是万物存在之根本。
严遵把宇宙发展过程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称之为虚无,第二阶段称之为实有。天地都是由虚无阶段演化来的,“万物之生也,皆元于虚,始于无”《卷二·道生一篇》,虚无阶段又进一步划分为“道”、“德”、“神明”、“太和”四个阶段。“道”是极度的虚无,《指归》称之为“无无无之无”或“虚之虚”,“道虚之虚,故能生一”(《卷二·道生一篇》)。“一”是相对的无,《指归》称之为“无无之无”或“虚”,“一以虚,故能生二”(《卷二·道生二篇》)。“二”是又次一等的无,《指归》称之为“无之无”(《卷二·道生一篇》)。“三”是更次一等的无,《指归》称之为“无”,“三以无,故能生万物”(《卷二·道生一篇》)。“道”、“德”、“神明”、“太和”都处虚无阶段,从状态上看都是无形,然细究,却有分别,“虚”、“无”的性质逐渐减少。《指归》又说:“形因於气,气因於和,和因於神明,神明因於道德,道德因於自然,万物以存”(《卷二·道生一篇》)。万物演化过程中,“神明”是必经阶段,称之为“无之无”,是比“德”更次一等的“无”,其再次演化生成“太和”,不与万物发生勾连。从这一层面看,“神明”是“无”,具有“生万物”的作用。
《指归》又对“神明”作用做了说明。“有虚之虚者开导禀受,无然然者而然不能然也;有虚者陶冶变化,始生生者而生不能生也;有无之无者而神明不能改,造存存者而存不能存也;有无者纤微玄妙,动成成者而成不能成也”(《卷二·道生一篇》)。在万物生化过程中,“道”、“德”、“神明”、“太和”扮演各自的功用,“有虚之虚者”指“道”,不被造就而用以造就其他;“始生生者”指“一”,生育万物的始端;“有无之无者”指“二”即“神明”,使万物得以存在;“动成成者”指“三”即“太和”,能够成就万物。万物生化过程中,“道”的作用是“然”,万物生化所要遵循的法则,“神之所以存我者,道使然也”《卷三·圣人无常心篇》;“神”之所以留在“我”身上,是“道”使它这样的。“德”的作用是“生”;“神明”的作用是“存”;“太和”的作用是“成”。“神明”是万物存在的基础,“存物物存,去物物亡”(《卷二·道生一篇》)。“神明”存于物中则物存,离物而去则物亡。
“神明”与“道”类似,从万物生成来看,都是“无”,能够生成万物;从万物存在来看,“神明”与“道”都是万物之纲纪,万物依托“神明”得以生存,依循“道”之法则而运行。
三、养“神”以贵身
“存物物存,去物物亡”(《卷二·道生一篇》)。“神明”是万物得以存在的根据,对个体生命而言,“神明”又是“我”之生命来源。“我之所以为我者,岂我也哉?我犹为身者非身。身之所以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卷三·圣人无常心篇》)。“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原因,不在于“我”自己,就好比身体存在的原因不在身体本身一样。身体存在的原因是由于“我”的存在,“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神”住进了“我”的身体,“神”之所以留存于“我”是因为“道”使它这样。严遵把“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神明”。在严遵看来,“神明”是个体生命自我意识的觉醒。
严遵重视贵身,重视协调“神明”与形体的关系,认为形体的存在是生命之我存在的前提。“道德神明、清浊太和,混同沦而为体,万物以形。形之所托,英英荣荣,不睹其字,号之曰生…得之者存,失之者亡…夫生之於形也,神为之蒂,精为之根,营爽为宫室,九窍为户门,聪明为候使,情意为乘舆,魂魄为左右,血气为卒徒”(《卷三·出生入死篇》)。严遵阐述了“生”、“形”、“神”三者之间的关系:道德神明、清浊太和,混同合为一体,万物借之成形,形体所依托的,给它起名叫做“生”,生即生命,万物得到它便得以生存,失去它便灭亡;生命进入形体之中,“神明”做它的蒂,精气做它的根。以此,“神明”是万物生之蒂,生是万物形之所依,是万物存在的前提,因此,对于形体的留存和保持而言,最根本的是要保存“神明”,严遵曰:“存身之道莫急乎养神”(《卷六·民不畏威篇》),存身之道的关键在于保存“神明。”
那么,怎样保存神明呢?《指归》说:“神明圣智者,常生之主也;柔弱虚静者,神明之府也”(《卷七·生也柔弱篇》)。神明圣智是长生的支柱,柔弱与虚静是“神明”的府库,说明最适合神明留存的住所是柔弱虚静的状态,人的身心虚静柔弱,“神明”就会居留保持,如果刚强造作,“神明”就会离去。严遵认为保存“神明”最多的是“赤子”,“赤子之为物也…无为无事,无意无心,不求道德,不积精神;既不思虑,又无障截,神气不作,聪明无识;柔弱虚静,魂魄无事;乐无乐之乐,安无欲之欲”(《卷四·含德之厚篇》)。刚出生的婴儿“神明”充足,因为它无所作为无所事事,没有意念没有心计,不浪费精神,不思虑,神气专一,故能保持柔弱虚静,进而保存“神明”。《指归》又说:“人始生也,骨弱筋柔,血气流行,心意专一,神气和平;面有荣华,身体润光,动作和悦,百节坚精;时日生息,旬月聪明。和则?神居之也”(《卷七·生也柔弱篇》)。刚出生的婴儿之所以骨弱筋柔,血气流行,心意专一,神气和平;面有荣光,身体润光,关节韧密;日日发育,月月聪明,是因为“神明”的留存。可见,严遵认为“赤子”柔弱、虚静、无欲,是保存“神明”的典范。
严遵认为存身之要是保存“神明”,而名与货是损神杀身之物,必须要舍弃。《指归》说:“得名得货,道德不居,神明不留,大命以绝,天不能救…无名之名,生我之宅也;有名之名,丧我之橐也。无货之货,养我之福也;有货之货,丧我之贼也…名利与身,若炭与冰,形性相反,势不俱然。名终体极、身存世昌者,天下无之”(《卷二·名身孰亲篇》)。得到了名与货,道德就不再居住了,神明就不再留存了,命因此灭亡,而天都不能救助;养身就要舍弃名利,名利与身就像是炭与冰,两者不可共存,对于荣名至极而形体安泰、身体存留而世代姣好的事情,天下是没有的。严遵主张“无名之名”与“无货之货”,反对“有名之名”与“有货之货”,前者是生命之住宅,是养生之祥福;后者是亡生之空囊,是亡生之寇贼。可见,严遵未必是反对“名”与“货”本身,而是反对将“名”与“货”当做个人的价值追求与努力方向,这会扰乱心意,使思虑不止,继而消耗“神明”,损害生命。因此,要以一颗“赤子”之心对待“名”与“利”,体验虚无,顺应自然,才能保存“神明”,此乃存身之要也。
由此,养身就要养神,赤子之心为我们提供借鉴,抛弃功名利禄之心,抛弃思虑,抛弃执念,保持内心的虚空、清静,“神明”就会进住、久留,生命便会旺盛、长久。
四、守“神”以治国
《老子指归》中设立了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人格,其中的核心代表为“圣人”。“道德之意,天地之心,安生乐息,憎恶杀伤,故命圣人为万物王”(《卷五·善为道者》),“圣人”顺应自然,感知道德、神明、太和、天地万物之变化,体察道德之意、天地之心,所以授命圣人为万物之王。在严遵的外王思想中,君主是否顺应道德、神明、太和,直接关系国家和人民的生死存亡,根据这一标准,严遵将君主划分为上德之君、下德之君、上仁之君、上义之君和上礼之君。
“上德之君,性受道之纤妙,命得一之精微,性命同於自然,情意体於神明,动作伦於太和,取舍合乎天心”(《卷一·上德不德篇》)。
“下德之君,性受道之正气,命得一之下中,性命比於自然,情意几於神明,动作近於太和,取予体於至德”。
“上仁之君,性醇粹而清明、皓白而博通。心意虚静,神气和顺,管领天地,无不包裹;睹微得要,以有知无,养生处德,爱民如子”。
“上义之君,性和平正,而达通情,察究利害,辩智聪明;心如规矩,志如尺衡,平静如水,正直如绳”。
“上礼之君,性和而情柔,心疏而志欲,举事则阴阳,发号顺四时…绝人所不能以,强人所不能行,劳神伤性,事众费烦,乱得以治,危得以宁”。
上德之君、下德之君、上仁之君、上义之君、上礼之君所禀之性不同,上德之君完全顺应自然,情意体验神明,动作与太和相合;下德之君含合自然、神明、太和的程度有所降低,严遵用“比”、“几”、“近”来形容,而上仁之君、上义之君、上礼之君的行为顺应自然、神明、太和的程度又逐渐降低,离大道渐远,功业层次逐渐下降,则天下不得太平。由此可见,君主治世要顺应自然,合乎道德、神明、太和,体验大道,达到圣人境界,方可使天下追随相应。
“地狭民少,兵寡食鲜,意妙欲微,神明是守,与天相参,视物如子,盛德化隆,恩深泽厚…国为雌下,诸侯信之,比於赤子,天下往之,若归父母”(《卷二·至柔篇》)。圣人是治国成功的典范,圣人信守神明,自然无为,即使是地狭民少、国力衰弱的小国也能使诸侯信服,百姓响应。那么,如何保有“神明”?严遵的治国理念是内圣外王哲学,主张反身治心,《指归》说:“成败存亡,求之于身”(《卷六·民不畏威篇》),“欲治天下,还反其身,…弃捐天下,先有其身,养身积和,以治其心。心为身主,身为国心,天下应之,若性自然”(《卷一·上士闻道篇》)。严遵认为要治国,先治身,所说的“反其身”、“求之于身”,指的是要回归虚静无欲、清静自然的本心,继而使“神明”留存,合乎大道。“明王圣主,损欲以虚心,虚心以平神,平神以知道,得道以正心,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法,正法以正名,正名以正国”(《卷四·以正治国篇》)。因此,明王圣主治国首先要治身,治身就要虚其心,才能平其神;正心才能正身,正法才能匡正其名,匡正名分以正其国。
圣人守“神”,不思不虑、无智无巧、真淳朴实,以此治理天下,自然能遵循大道,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圣人之为君也,…不知以因道,不欲以应天,无为以道世,无事以养民,玄玄默默,使化自得,…空虚寂泊,使物自然”(《卷二·不出户篇》),“(圣人)不言而宇内治,无为而天下已”(《卷六·知不知篇》)。圣人治世,以虚静无欲之心应对外物,内心守气专神,以一种最根源、最纯净、最真朴的本始状态来治事理物,达到不治而人自治,不理而物自理的境界。
五、小结
《老子指归》中的“神明”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神明”即气,从万物生成来看,“神明”是万物生成的先决条件,其次留存于万物,是万物得以生存的根据;于个人生命而言,“神明”是生命的本质,保持内心的虚静无欲,“神明”自然会来,养身的重点在于存养“神明”;对圣王君主来说,要治国,先治身,身为国之本,而“神明”又为存身之要,故圣人治国不思不虑、虚无淡泊以存其“神”,顺应自然,达到无为而治。
注释:
1.王德有.《老子指归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页.
2.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9-90页.
3.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0页.
4.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8页.
5.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8页.
6.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0页.
7.郑万耕.《严君平哲学思想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48-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