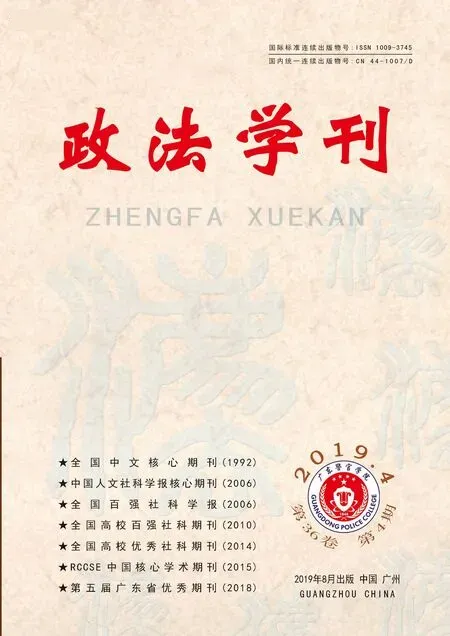国际商事仲裁依职权适用商人法法律依据探析
杨梦莎
(天津大学 法学院,天津 300072)
现代商人法在国内法庭持续面临着适用程度低下的困境。尽管依托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现代商人法为准据法已经得到了各国立法和司法的普遍承认,成为其得以适用的主要法律依据之一。但受制于国内法官法律选择职权的限制,在缺乏当事人明示或默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国内法院惯用国际私法指引的国内法作为准据法,而现代商人法等非国内法法源往往处于辅助性法源地位。因而正如比利时学者奥·兰多(Ole Lando)所言,商人法能否被法院适用可能关键争议并不是在于探讨其是否属于独立的法律渊源或法律体系,而与法官的裁判职权存在密切联系。[1]
商人法的适用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已有较为丰富的前期研究。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现代商人法的适用程度与司法审判职权两者的关系视角,试图论证现代商人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程度高低与审判自由裁量权息息相关这一结论。通过对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律选择制度进行理论梳理和实证考察可得,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律选择依据经历了从仲裁所在地法—仲裁冲突法—仲裁实体法的模式转变,这一过程伴随着仲裁员选法职权的扩张,决定了现代商人法法律渊源适用范围的相应拓展。同时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所特有适用“贸易惯例”和“公允及善良原则”的规定,则成为现代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予以适用的更为灵活法律依据。而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授权仲裁庭可依职权主动适用现代商人法解决案件争议,这一差异成为现代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比例远远高于国内法庭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仲裁所在地法依据
当缺乏当事人法律选择合意时,不同于国内法庭必须确定地遵守本国冲突法规范选择准据法的做法,仲裁机构的实体法选择问题一直存在理论和实践争议。早期传统观点认为,仲裁实体法选择的依据是仲裁所在地法(arbitral forum),即仲裁程序依然受到仲裁所在地国内法的约束。[2]34-35这种仲裁所在地法理论所倡导的属地主义原则的合理性越来越受到学者的质疑,其被批评为将仲裁权视为变相的司法权,使得仲裁庭在行使仲裁权的过程中只能严格遵守仲裁地国家法律,极大限制了仲裁员的权力,阻碍了纠纷的公正及时解决,也限制了仲裁制度的发展。[3]300-347尤其在现代国际商事制度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在缺乏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时认定商事争议准据法为仲裁庭所在地法律的判断,已不再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推定。[4]165-166尽管对仲裁所在地法理论存在质疑和批评,其仍然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商事仲裁实践,许多仲裁庭仍然主要依据仲裁所在地法作为法律选择的依据。①AB Götaverken v. General National Maritime Transport Company (GMTC),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2977, 2978 and 3033, 1978. Austrian franchisor v. South African franchisee,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 5460,1987.
仲裁所在法理论最大程度上制约了仲裁庭的法律选择职权,与此同时限制了现代商人法法律渊源的可适用范围。当仲裁庭被要求同国内法庭一样受到冲突法在内的法院地法(lex fori)约束时,国内法对现代商人法的态度和适用规定将同样左右着仲裁庭的法律选择方式。而目前国内法对作为非国家法的现代商人法普遍采取保守的态度,冲突法范式主导的国内法律选择方式也与现代商人法所倡导的实体法法律选择方式相背离。正如弗兰西斯·曼因(Francis Mann)所言,当国际商事仲裁应当建立与仲裁地的联系时,仲裁员就有义务查明并适用仲裁地的冲突法和程序法,因而戈德曼提出的“跨国实体规则”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适用空间狭窄。[5]具体而言,在仲裁所在地法法律依据下现代商人法的可适用范围被仅仅局限于并入国内法的国际商事条约法源,而国际商事惯例、一般法律原则等非国内法法源则无法被国内冲突法规范作为准据法所选择,依然处于补充性法源的边缘地位。
此外,以仲裁所在地法为选法依据,使得仲裁庭同仲裁所在地法院一样,只将国际商事条约以与对该国生效国内法的相同方式予以适用,这在事实上同样会限制国际商事条约的适用空间。以CISG为例,在仲裁所在地法理论前提下,仲裁庭主要依据CISG第1条1款a款直接适用公约,而并不是以仲裁规则法律选择的授权为出发点。[6]例如,2002年匈牙利工商会仲裁庭审理的99144号案件②Hungar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Court of Arbitration Award VB 99144, 1 January 2000.、2002年ICC仲裁院审理的“机械案”③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 11333, 2002.等仲裁裁决说理部分,仲裁庭就直接依据了CISG第1条1款a款作为适用公约的法律依据,而并未从仲裁规则本身找寻公约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于法院具有适用CISG等国际商事条约的义务,仲裁庭应依据仲裁规则中的法律选择方式适用公约,后者可能包括通过仲裁规则或仲裁法规定的冲突规则而依据CISG第1条1款b项适用公约,或将其作为现代商人法法律渊源予以直接适用。[7]这种法律依据的差异会极大限制公约的间接适用或作为国际商事惯例予以适用的可能。例如我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以下简称CIETAC)在适用现代商人法法源方面就主要受到国内法的影响。在适用以CISG为代表的国际商事条约方面,大部分CIETAC仲裁裁决采用了与我国法院相同的法律依据,即直接并且单独依据CISG规定本身。[8]值得肯定的是,据佩斯大学CISG数据库统计,CIETAC贡献了大量适用公约案例,具有自动适用公约的良好传统。但深入考察CIETAC适用CISG的仲裁裁决,我们发现在缺乏当事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CIETAC判例较少对CISG适用的法律依据进行明确说理,而是在案件情形满足CISG适用条件的情况下直接选择适用公约。[9]大部分CIETAC仲裁裁决关于准据法选择的法律推理都采用了与法院判决相似的语言表述,“由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并未协议选择准据法,买卖双方当事人营业地位于不同公约缔约国,并且当事人并未明确排除CISG的适用,因而CISG适用于本案争议”。[10]并且由于我国作出了CISG第95条下公约间接适用方式的保留,CIETAC同样较少如其他仲裁机构一样以国际私法为依据适用CISG。因此可以看出,CIETAC在选择适用CISG时实质上是采用了同国内法院完全一致的适用方法,而CIETAC自身的仲裁规则并未在仲裁裁决法律说理部分体现。
因此,仲裁所在法依据极大限制了现代商人法法源的适用范围。即使国际商事条约可以被作为国内法法源予以适用,但仲裁所在法依据也限制其间接适用或作为国际商事惯例等其他适用路径。仲裁庭适用国际商事条约应当主要出于对其作为通行国际商事规则权威地位的认可,这一区别有必要在仲裁裁决当中予以体现。
二、仲裁冲突法依据
由于仲裁所在地法理论限制了仲裁制度的独立发展,因此主张国际商事仲裁制度摆脱国内法支配的“非国内法”理论得以产生和发展。在“非国内法”理论影响下,现代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在仲裁庭实体法选择方面集中表现为弱化仲裁所在地法的主导作用,赋予仲裁员在缺乏当事人法律选择时拥有确定“适当”(appropriate)冲突规则的自由。这使得仲裁庭实体法选择的法律依据不再局限于仲裁地法,而可依据仲裁庭自身的仲裁规则予以确定的仲裁冲突法(arbitral conflict of laws)选择法律。目前主要国际和国内仲裁规则的实体法律选择都采取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与仲裁员冲突规则自由选择权的立法模式。这种仲裁法律选择间接方法(voie indirecte)的立法规定可追溯至1961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7条第1款,“如果当事人没有决定应适用的法律,仲裁员可按照其认为可适用的冲突规则的规定,适用某种准据法”。此外,1975年的《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3.3条、2006年UNCITRAL《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第2款等也规定,在当事人并未作出实体法律选择的情况下,仲裁员应选择“适当冲突规则”确定准据法。
显然,仲裁冲突法依据仍未摆脱法律选择的冲突法范式,而仅仅是解除了仲裁员必须适用法院地冲突法的束缚,这与现代商人法自治性特征所决定的实体法律选择路径仍存在冲突。那么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仲裁冲突法能否成为现代商人法适用的法律依据,国际商会仲裁院的仲裁实践给出了特殊的回答。通过考察ICC仲裁裁决我们发现,ICC仲裁庭在适用现代商人法时并没有对适用何种冲突规则进行直接说理,而是通过对“冲突规则”进行扩大化解释,实现了对现代商人法事实上的直接适用。
1992年,ICC仲裁庭裁决了第一个将CISG独立作为准据法的案例——“酒店建材案”。①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 7153, 1992.不同于先前许多案例中仲裁员参考CISG规定或援引CISG用以支持国内法说理的做法,ICC仲裁庭终于等来了真正落入CISG调整范围的商事争议,并将其由辅助性法源提升为独立适用的准据法。该案中,营业地位于澳大利亚的卖方与营业地位于南斯拉夫的买方之间订立了供应并安装酒店建材的合同。合同中包含授权“仲裁和准据法”的条款,但双方并未约定任何准据法。“根据仲裁庭的确信,CISG适用于当事人缺乏准据法协议的本案中。”仲裁庭首先考察了CISG的可适用性问题,双方合同订立时CISG对澳大利亚和南斯拉夫生效,并且合同争议也属于CISG调整范围,因而仲裁庭认为根据CISG第1条1款a项规定CISG直接适用于该案。仲裁庭紧接着面临的是CISG适用的法律依据问题,依据当时生效的1975年《国际商会调解和仲裁规则》第13条规定,仲裁员在当事人未选择准据法时,应当依据第13.3条适用冲突规则选择的法律。仲裁庭认为,第13.3条中的“冲突规则”(rule of conflict)是国际法的通用(general)表达,而不是一种仅给予冲突法以优先权的狭义(narrow)表达。因而第13.3条并不狭隘地要求仲裁员仅仅诉诸冲突法规则。紧接着仲裁庭巧妙的分析了CISG第1条的性质问题,其认为虽然CISG第1条主要规定公约自身的适用条件,并且不像一般冲突规则旨在解决不同法律之间的竞争问题,但该条实质上可以视为表达了一种真正的冲突规则。因而该案仲裁庭认为依据CISG第1条与仲裁规则第13.3条中适用“冲突规则”的表述并不冲突,因而直接决定了适用CISG。另一例证是1997年ICC仲裁院审理的“玻璃制品案”,该案中仲裁员同样依据1975年《国际商会调解和仲裁规则》第13.3条实现了对CISG的直接适用。②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 8962 of September 1997.该案涉及营业地位于罗马尼亚的卖方与意大利买方之间签订的玻璃制品合同所产生的争议。由于买卖合同中并未规定合同准据法问题,仲裁员决定应当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3.3条选择法律。该案仲裁庭认为第13.3条授予了仲裁员自由选择准据法的权力,并且认为该案符合CISG第1条1款a项的适用条件。可见,该案仲裁庭采用将CISG视为由“冲突规则”指定准据法的方法,以解决ICC适用CISG是否适当的问题。
以上案例说明,虽然仲裁冲突法法律依据在立法层面没有跳脱“冲突规则”的思维定式,依然较大程度上制约着仲裁庭对现代商人法的直接适用,但仲裁庭通过扩大化法律解释的方式开始对传统的“冲突规则”定义予以重构,使得仲裁庭的法律选择视野开始由国内法扩展到了国际法层面。其对CISG第1条特殊“冲突规则”性质的判断,也极具指导意义。ICC仲裁庭已经认识到,统一法的适用理念与传统冲突法选法理念虽然存在差异,但实质都是法律选择的方式。正是认识到这一点,该案仲裁庭实现了统一法和国际私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协调。
三、仲裁实体法依据
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律选择采用冲突法范式的正当性持续受到学者质疑,其被视为与仲裁便利性特征和国际商事争议的国际性特征存在冲突。仲裁庭能够被委派裁决争议,则意味着同时授权其确定作出裁决应依据的法律,除非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打破这种假设。[11]126-127随着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建立,一些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开始进一步扩大仲裁员的自由裁量权,赋予其直接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力。例如,1998年《国际商会调解与仲裁规则》第17条有关仲裁实体法律适用规则删除了仲裁庭适用冲突规则选择法律的表述,而是规定在当事人没有对实体法律作出约定时,适用仲裁员认为适当的“法律规则”。“法律规则”(rule of law)措辞区别于“法律”(law),意味着法律选择的范围不仅包括国内法,商人法等其他非国内法渊源也被包含其中。并且这一修订绕开了使用“冲突规则”的措辞,则意味着仲裁庭不再必须使用冲突法方法,而可以直接决定其认为应当适用的实体法律。类似的,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496条、1986年《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54条第2款、2000年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则》第28条第1款、2001年《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第22条第1款、2010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5条第1款、2013年《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27条第2款等都作出了适用“法律规则”的规定。
仲裁实体法依据极大便利了仲裁员法律选择的灵活性,仲裁员无需再依赖冲突规则的选法工具,仲裁员可以直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规则。[12]这说明仲裁庭并不再满足于寻找空间地理意义上适当的法这一较低层次目标的实现,而是致力于寻找实质意义上最好的解决方法。[13]虽然这些仲裁规则中并未明确提及参照“商人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条款可以解释为对商人法的承认,并授权在国际商事争议中适用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开始建立自己特殊的争端解决方式和规则的趋势下,现代商人法将能够被直接适用而无需诉诸冲突法方法。[14]商人法理论可以视为国际商事仲裁最大程度上规避冲突法原则所作出努力的表现,商人法理论实质上表达的就是仲裁员脱离仲裁地法律适用的自由裁量权,而商人法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替代性争议解决方法。[15]
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选择的这一改革无疑更加激励了适用现代商人法的仲裁实践,除CISG等国际商事条约以外的一般法律原则、示范法、法律重述等非国内法法律渊源开始具有了直接法律适用依据。例如,在1999年ICC审理的“印钞案”中,仲裁员就依据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7条为依据适用了Unidroit《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并具体解释了为何该案中选择《通则》满足了适用恰当“法律规则”的要求。仲裁庭认为,当事人并未明确选择法律就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具有并不想将案件争议诉诸特定国内法的意图。因此,仲裁庭认为在缺乏当事人明确法律选择的情况下,“国际合同的一般标准和规则”(general standards and rules)是解决该案争议最为适当的法律规则。仲裁庭进一步解释到,“国际合同的一般标准和规则”并不直接规定在特定国际条约当中,Unidroit《通则》则是对国际商事合同一般标准和原则的明确编纂,因而应予适用。①Dulces Luisi, S.A. de C.V. v. Seoul International Co. Ltd. y Seoulia Confectionery Co. ,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Case No. 9474, 1999.再如,2001年ICC审理的10422号仲裁案中,仲裁庭再次直接适用了《通则》这一商人法法源。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并未协议选择法律但要求将合同争议交由中立立法调整,仲裁庭认为双方当事人的这一要求意味着其不愿将其争议诉诸国内法的意图,因而根据ICC仲裁规则仲裁庭可以选择适当“法律规则”的授权,选择作为“国际合同一般原则和规则”《通则》作为准据法无疑是恰当的。①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 10422 , 2001.而在2004年ICC审理的13012号仲裁案中,在双方当事人并未协议选择法律并各自主张适用本国国内法,仲裁庭认为当事人所主张的确定准据法的连接点因素并不具有说服力,因而仲裁庭依据ICC仲裁规则第17条1款规定,认为裁决应基于商人法的基础规则和贸易惯例,并主要援引了Unidroit《通则》的相关规定。②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 13012 , 2004.
因而通过以上案例可见,仲裁员在缺乏当事人法律选择或当事人不愿或不能诉诸国内法的情况下,通常认为选择现代商人法是最为适当的。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实体法律选择依据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仲裁员的可以依职权适用商人法法源,扫除了来自选法职权方面的障碍。
四、“贸易惯例”依据
国际商事仲裁与国内商事仲裁存在的显著区别之一,是其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需求使得仲裁员在实体法律选择方面并不再局限于国内法的适用,国际商事惯例等非国内法法源同样可以被仲裁员依职权主动适用。目前许多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中都规定,仲裁庭“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考虑“贸易惯例”(trade usage)。例如UNCITRAL《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5条第3款规定,“所有案件中”,仲裁庭均应“考虑到适用于有关交易的任何贸易惯例”。1961年《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如果当事人没有决定应适用的法律,仲裁员可按照其认为可适用的冲突规则的规定,适用某种准据法…仲裁员均应考虑到合同条款和贸易惯例”。此外,1975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3条第5款、UNCITRAL《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第4款、1981年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496条、1986年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54条、2000年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则》第29条第2款也存在相似规定。
大多数学者对该条款的解读为,考虑“贸易惯例”措辞是对仲裁员直接适用现代商人法的授权。但从“考虑商事惯例”规定文义本身,并不能够明显看出国际商事惯例与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之间的关系地位问题,因而关于这一规定学者存在不同的理解。一些仲裁案例中,仲裁员在当事人并未协议选择法律,但援用Incoterms和UCP等国际商事习惯的前提下,推断出当事人愿意将争议诉诸国际贸易惯例的意图。③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 8502, 1996.即仲裁员适用贸易惯例的自由裁量权仍应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而另一部分学者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解释,认为这一规定不仅仅意味着承认了现代商人法的适用,更为关键的是“在任何情况下”的措辞赋予了仲裁庭不必以当事人授权为其进行公正裁决的前提条件。换言之,仲裁庭可以在当事人已经协议作出合同准据法选择的情况下,仍依据“商事惯例”进行裁决。例如法国学者富尔查特(Fouchard)认为,适用国际商事惯例是仲裁员的根本义务,国内法庭并不可能知晓全部商事惯例,因而当事人必须提供商事惯例在其之间存在的证据,而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员被默认为应当知晓商事仲裁惯例,无论当事人是否接受,适用国际商事惯例属于仲裁庭本身的义务。这种观点被一些国际商事仲裁实践所印证。例如,在2001年ICC审理的11051号仲裁案中,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了意大利法作为合同争议准据法,仲裁员在适用意大利法的同时补充到,“适用意大利法与适用相关国际贸易惯例是相一致的,Unidroit《通则》正是对国际贸易惯例的一种表达”,因而仲裁庭在存在当事人协议选择法律的情况下,依然同时适用了作为现代商人法法源的《通则》。④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 11051, 2001.因此,仲裁法规则中“考虑贸易惯例”的授权使得现代商人法在国际仲裁中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仲裁员得以重点关注和考察现代商人法的可适用性。
五、“公允及善良原则”依据
另一个国际商事仲裁适用现代商人法所特有的法律依据是仲裁制度的“公允及善良原则”。国际商事仲裁的“友好仲裁”(amiables compositeurs)制度,是指仲裁庭可以在当事人授权的情况下,在认为适用严格法律规则会导致不公平结果的情况下,不适用严格的法律规则而是在“公允及善良原则”(ex aequo et bono)指导下,依据仲裁员所认为的公平标准进行裁决的制度。友好仲裁对严格适用法律规则提供了一种公平的修正,但“公允及善良原则”是否能够成为扩大国际商事仲裁员自由裁量权以实现现代商人法适用的法律依据,学者之间存在不同观点。
一些学者对此持有肯定态度,例如菲利普·德·李(Filip De Ly)认为虽然友好仲裁制度在实践中并不常适用,但该制度却与现代商人法法源的适用密切相关,其可能成为现代商人法一般法律原则、国际商事惯例和跨国实体规则适用的“跳板”。[16]122-123虽然在法国、荷兰等直接给予仲裁员宽泛自由裁量权的国家,不适用冲突规则不能等同于友好仲裁,但在其他没有授权直接法律选择方法的国家,拒绝适用冲突规则可能等同于进行了友好仲裁。法国学者洛坎(Loquin)也将友好仲裁与现代商人法的适用联系在了一起,其认为当存在当事人法律选择时商人法规则仅能够通过准据法的选择而被适用,但在缺乏当事人法律选择时,友好仲裁能够授权仲裁员直接适用商人法规则而无需诉诸冲突法分析。但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态度,认为仲裁员适用国际商事条约、国际商事一般法律原则的依据不可能是“公允及善良原则”,尽管该原则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仲裁员拥有宽泛的自由裁量权。[17]206-207因为该原则的主要作用是为了保障仲裁员以追求裁决公正性为目的,能够忽视已有法律规则或超出仲裁协议范围做出个案裁决。因而只要仲裁员确实基于法律规则做出裁决,其都并不是在行使“公允及善良原则”赋予其的自由裁量权,无论这种法律规则的性质如何、适用方式如何。因此,国际商事条约、国际商事一般法律原则属于现代商人法法律规则,因而适用这些现代商人法法律规则的裁决不应当被视为是“公允及善良原则”行使的结果。
这种将“公允及善良原则”行使结果狭隘地理解为超法律规则的适用并不妥当。更为本质地应当看到,该原则的核心是保障仲裁员不受严格法律适用的限制,因而并不必须地排除某些法律规则的适用。[18]因此,虽然友好仲裁或“善良及公允原则”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商人法的概念,但仲裁规则或仲裁法授权友好仲裁的仲裁庭,确实可将其作为商人法适用的法律途径。[19]实践证明,被视为赋予仲裁员最大程度自由裁量权的“公允及善良原则”确实成为适用商人法或一般法律原则的重要法律依据。[20]例如,在ICC仲裁庭审理的8874号案件中,当事人授权仲裁员进行友好仲裁并根据“公平原则”解决合同争议,仲裁员最终参考了Unidroit《通则》。①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Case No. 8874, 1996.因此,“公允及善良原则”是对仲裁员适用商人法的授权,当商人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争议最为恰当的法律渊源时,援用商人法等同于履行了仲裁员公平裁决的义务。
结论
以上研究表明,国际商事仲裁员法律选择职权范围与现代商人法的适用程度呈现出正相关性。尤其在国际商事仲裁与国内仲裁相分离的趋势之下,国际商事仲裁实体法适用规则呈现出非国内法化和非冲突法化的特征,仲裁员在实体法选择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进一步扩张。一些现代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不仅赋予了仲裁员选择适当冲突规则的自由,甚至承认了仲裁员拥有直接适用法律的权力。这些国际商事仲裁规则的改革无疑极大便利了现代商人法法源的适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冲突规则及国内法的束缚,使得国际商事仲裁庭能够积极主动适用更为契合国际商贸需求特点的现代商人法渊源。但应当承认,目前大部分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并未像法国荷兰一样走的那样远,而仍然停留在冲突法法律选择范式之下。但这并未影响仲裁员在实践中采用灵活的法律解释方法,找到现代商人法法源适用的“突破口”。即使是在最为保守的冲突法适用范式下,仲裁庭同样通过扩大化解释“冲突规则”“贸易惯例”和“公允及善良原则”的方式,确立了现代商人法适用的法律依据,虽然此时现代商人法的适用程度和范围会受到仲裁规则的不同限制。而这些灵活多样法律适用模式都以仲裁员倾向于适用现代商人法法源的内心确信为前提,以现代商人法的优越性和国际性为保障,以仲裁规则授权的仲裁员自由裁量权为法律基础。
因此,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员法律选择自由裁量权是仲裁员得以发挥法律适用主观能动性的现实基础,并与现代商人法法源适用程度呈正相关性。随着现代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独立发展,仲裁规则法律适用模式将越来越契合现代商人法的直接适用法律方法倾向,在仲裁规则立法层面解除仲裁员法律适用方面的约束,从而使其真正以满足国际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