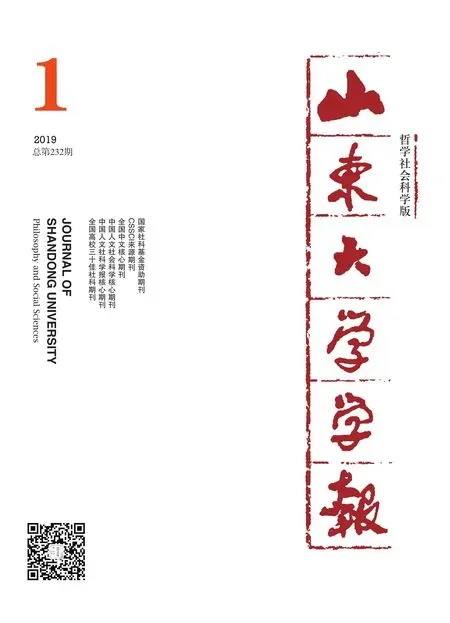真理的形式:从伽达默尔到图根哈特
刘 岱 傅永军
真理是诠释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也是较为独特的概念之一,如格朗丹(Jean Grondin)所言,诠释学“不追问历史认识或日常认识的可能性的理论上先验的条件,而是探究在理解中经常‘发生的’东西”,故而与传统哲学和英美哲学所谈论的真或真理有着显著的不同注让·格朗丹:《诠释学真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概念》,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导论”第1页。。尤其是海德格尔早期的“实际性”(Faktizität)观念再次受到重视后,真理在诠释学意义上基本上等同于人类的理解的普遍性。由此,诠释学真理具有了某种先验的形式特质。这一形式特质,主要体现为“解蔽”(Entbergung)。
海德格尔哲学因其自身独特的诉求和结构安排,在强调“解蔽”的同时,选择性地将真理概念藏而不谈。伽达默尔则通过深度发掘海德格尔哲学中的诠释学成分,让被掩藏起来的真理重新开始呈现。更关键的是,经过他的努力,真理概念开始具有了明确的形式。这一形式在伽达默尔那里截然不同于传统的真理形式以及科学的形式,甚至可以说这一形式逻辑上是在先的。伽达默尔的真理形式启迪了未来诠释学的发展,同时因为英美哲学对诠释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诠释学家乐意介入这一话题,其中较为重要的人物是图根哈特(Ernst Tugendhat),其代表思想是形式语义学。笔者将在本文揭示,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到图根哈特,真理概念由消隐到以清晰的形式呈现的进程。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真理概念的重要性,并分析海德格尔在真理问题上所遇到的理论困境。第二部分介绍伽达默尔通过对诠释学方法论的强调而提出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让真理有了渐趋明朗的形式。不过,因为态度的折衷,伽达默尔没有完全实现所设定的目标。第三部分则分析图根哈特的形式语义学,探讨他如何纠正伽达默尔遗留下的问题,并如何通过语义分析的方法,让真理的形式得到更明确的规定,表明“形式语义学是存在论的自然继承人”注Santiago Zabala, The Remains of Being: Hermeneutic Ontology after Metaphys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p.87.。
一、海德格尔“隐匿的真理”
“真理作为陈述的性质这最终观点在伽达默尔——属于海德格尔的后继者——那里被略过而避而不谈。”[注]让·格朗丹:《诠释学真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概念》,第6页。实际上,伽达默尔之所以少谈真理,并非不重视真理,而是担心陷入科学主义的真理观。传统上科学的真理观大致分为三种,即符合论的、融贯论的和约定论的。它们都是基于主体和客体的符合关系来探讨真理如何可能,而这种探讨方式根本上无法满足海德格尔理想中的最原始、最真实和最客观的真理观念。这种真理观也就是他在《存在与时间》里所创造的“存在的真(真理)意味着是‘去揭示的’”[注]Mar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by Joan Stambaug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0, p.210.的真理观。按照达尔斯特伦(Daniel Dahlstrom)“真理概念实质上是自反的和本体论的。为了实现对真理的充分分析,它必须对其自身以及其所预设的存在的意义做出说明”[注]Daniel O. Dahlstrom, Heidegger’s Concept of Tru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xvii.的说法,海德格尔实质上要将传统的真理观转变为更为基础的“存在的真理”[注]理查德·E.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28页。观。后者提倡的“去揭示的”存在,可免于证实原则(verification rule)的束缚,直接触及真理本身,也就是真理的明见性(Evidenz)。如此一来,真理概念就跳出了传统真理观的范畴,展示了自身的本真性。
海德格尔之所以能意识到这种本真的真理,来自于他对希腊词“alêtheia”所做的存在论意义上的词源学追问。alêtheia这个词由前缀a和词根lêtheia组成,前者表示“非”,后者是“遮蔽”,整个词由此意味着“去遮蔽”,甚至可以进一步衍变为一种无蔽的状态。不过,按照托马斯·希恩(Thomas Sheehan)的说法,从源头上讲alêtheia的意义有三种相似含义:(1)由人的“世界—开放状态”维持的意义;(2)处于与日常的意向性的相互关系中的事物的前理论的有意义状态;(3)作为充实的意向性一种形式的命题之理论的—断定的正确性[注]参见托马斯·希恩:《事实状态与Ereignis》,周炼译,《世界哲学》2013年第5期。。他对此的解释是,第一种意义是“敞开”,显然是海德格尔的;第三种意义是命题和事物充分符合的产物,但并不因此意味着它不重要;第二种则稍显隐晦,笔者将放在后面讨论它。
可以说,alêtheia自身并不拘泥于海德格尔所设定的形式,它至少还能包含另外两种。不过按照希恩的分析,要想无害地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最好是使用“Sinn”或“Bedeutung”(可理解性或意义),而非真理[注]托马斯·希恩:《事实状态与Ereignis》,周炼译,《世界哲学》2013年第5期。。希恩的见解是得到海德格尔本人支持的,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一文中,海德格尔说:

追根究底,海德格尔并非完全回避对真理方法的谈论,他充其量只是描画了一种抽象的可能,即笼统地谈论消除传统真理概念对存在论哲学的重要性,并不涉及具体的方法和内容[注]达尔斯特伦(Daniel O. Dahlstrom)在《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中将海德格尔的方法称为“形式指引”(formal indications)。。他似乎由此向我们发出了召唤,召唤可期的真理形式的出现。对诠释学而言,要响应海德格尔的这一召唤,在笔者看来,所运用的方法至少要应对两个要求:一是如海德格尔所言,“哲学是任何时候都必须为了自己重新实现存在的事件”[注]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90.,因此回归源初的真理要基于存在的不断重现;二是这一方法必然要体现此在存在的历史性。
关于第一点,笔者认为,海德格尔哲学源于对“存在”的独特发问,真理问题也要以此为契机。所以,一个妥善的真理形式的提出,应立足于对存在的妥善安置。关于第二点,《存在与时间》之后,此在的地位愈来愈被边缘化,通常与存在概念连在一起,作为“此在的存在”的整体被讨论。此在存在的历史性有两种面相:一种是此在“必须被视为处于世界历史的具体事件之流的语境中”;一种是“用时间化(时机化)或时间结构来定义历史性:通过此在[注]原文将Dasein译为“缘在”,为了保持文本一致,改为“此在”。抛投(筹划)自身于它作为一整体存在的最切己的可能性”[注]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3页。。后者是对此在的生存论处境的一种抽象描述,差不多对应着此在的“在世存在”状态。海德格尔历史性的这两种内涵相互抵牾,很难被调和。诠释学的真理永远是过去、现在的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事件,所以唯有消除历史性自身内含的矛盾,才能进入有效的讨论。
响应海德格尔这一召唤的哲学家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都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即伽达默尔和图根哈特。前者被认为较好地遵守了海德格尔的主体思想,“成功地统一了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前后两个时期并把它们置于一种统一的诠释学框架之内”[注]让·格朗丹:《诠释学真理?论伽达默尔的真理概念》,第10页。;而后者则对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有着较为严厉的批评,并且力图将其放在语义分析的范围内加以妥善处理。在笔者看来,从伽达默尔到图根哈特的发展路径代表着诠释学的一个积极方向,即将真理收拢于较为明确的形式之下,也就是瓦提莫(Gianni Vattimo)说的“当代诠释学的任务似乎在于,由源始灵感出发,用比过去更为完善和明确的形式进行表达”[注]Santiago Zabala, The Remains of Being: Hermeneutic Ontology after Metaphysics, p.98.。
二、伽达默尔:对话与真理
一般而言,伽达默尔更倾向于整体考察海德格尔思想。在他看来,从诠释学角度出发,海德格尔的前后期思想实质上是融贯一致的,这种一致表现在海德格尔早期的实际性解释学精神在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被传达和延续。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海德格尔,就要回到他这一思想源头上去。
依海德格尔所言,“实际性”(Faktizität; Facticity)是“作为其存在特征(Seinscharacter)来追问的本己的此在”[注]马丁·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0页。,希恩将之解释为“指称‘人之在先地被抛入给予意义的能力中’的词,因而也被用于指称人理解这样那样的事物的能力”[注]托马斯·希恩:《事实状态与Ereignis》,周炼译,《世界哲学》2013年第5期。。在海德格尔那里,实际性概念自身带有批判性,与“无家可归”(Unheimlichkeit)、“沉沦”(Afallendes)等紧密相关,意指要从某种容易出错的处境返回人本真的在世生存状态。所谓出错的处境可等同于“出错的共同体”(falsified community),也就是“人从某种出错的共同体返回到单独的个人”[注]参见P. Christopher Smith, “Destruction-Konstruktion: Heidegger, Gadamer, Ricoeur”, in Francis J. Mootz Ⅲ and George H. Taylor(eds.), Gadamer and Ricoeur: Critical Horizons for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London: Continuum, 2011, p.21.;而伽达默尔虽然继承了海德格尔对实际性基本特征的描述,即人的被抛状态,但他并不认为存在着会出错的共同体,实情恰恰相反,要走出被抛状态,人就应当“从特殊的自我返回文化的共同体”[注]P. Christopher Smith, “Destruction-Konstruktion: Heidegger, Gadamer, Ricoeur”, p.21.。
所以,在对“实际性”的理解上,他们产生了基础性的分歧。对海德格尔而言,“实际性”是处于被抛状态中的抽象个人对本真能在的领会;而对伽达默尔而言,“实际性”则是个人处于共同体中以实现本真的在世生存。之所以会产生这一分歧,源于海德格尔对历史性的第二个表述。其中,海德格尔关注的是不受共同体侵扰的个体的生存,这势必将在如何把个体从共同体中抽离这一难题上碰壁。换言之,海德格尔无法说明如何能从纷繁复杂的人类历史情境中实现个人的本真在世。只能说,这一本真的在世生存是海德格尔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进行观察并运用现象论证所获得的成果。这个成果是可信的,但从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到这一成果的获得,其过程依然有待更透彻的澄清。
伽达默尔赋予真理以明确形式的工作恰恰就是由此开始的。对他而言,这一工作的关键在于重新寻求哲学讨论的出发点。他的做法是回到胡塞尔现象学,更具体地说是回到胡塞尔的方法论。他在《真理与方法》中说:
这包含着一个哲学方法论的问题,在对这本书的许多批评里都提出过……确凿无疑的是,我这本书在方法上就是现象学的。[注]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trans.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 London: Continuum, 2004, xxxii.
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论遵循“面向事情本身”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从事“本质的还原”,也就是通过“直观”还原事情本质,因此也可以被称为本质直观的方法[注]胡塞尔1925年的《现象学的心理学》一文对本质直观方法作了彻底反思,后来被编入《经验与判断》一书中。。尽管伽达默尔并未完全局限于胡塞尔方法论的框架内,但多斯塔尔认为,“胡塞尔一方面帮助伽达默尔清理了通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诠释学本体论的路径,另一方面又为他为《真理与方法》中所发展出的理解理论奠定了基础”[注]Robert J. Dostal, “Gadamer’s Relation to Heidegger and Phenomenology”, in Robert J. Dostal (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da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53.。
由此可知,伽达默尔之所以积极借助胡塞尔哲学,目的就在于构建一种兼顾存在本体论和现象学方法的诠释学方案。伽达默尔对这一方案最终能否成功缺乏信心,因此其哲学中处处可见妥协和模糊的影子,但并不影响他将这方面的工作一直进行下去。
这项工作可以表述为“此在的生存结构也必须要在对历史传统的理解当中得到表达”[注]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254.,也可以用前面所引用的史密斯的那句话“从特殊的自我返回文化的共同体”进行表述。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角度出发,海德格尔的此在被抛状态实际上就是人之理解所在的真实的历史处境。也就是说,诠释学只认可海德格尔历史性的第一个含义,即“世界历史的具体事件之流”,那是人唯一可以设身处地的场所,其他任何抽象的历史和空间概念都只不过是对它进行理解和分析的成果而已。伽达默尔就是要直接从这种对人有所遮蔽的具体历史境遇入手,稳妥地将实际性的真理实现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掌握一种胡塞尔意义上的、不可被怀疑的通达真理的方法。它必须不同于科学的方法论,因为其并非要教给人们一种屡试不爽的工具,而是教会人们最基本的实践原则,或者说教会人们面对复杂的历史境况如何开始一种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它所要传达的是一种近似于胡塞尔“生活世界”(Lebenswelt)概念的东西,它非主题化、非客观化,而且顾及着人生命体验的直观。更重要的是,它是自由的、开放的,其他任何方法包括科学方法都可以被进一步囊括进来。由它所展现的,恰好就是希恩解释alêtheia时所给出的第二种有意义的状态。它既然属于alêtheia内涵的一部分,当然也就可以被看作是“真理”。

由这种真理形式继续推导下去(效果历史意识),就将顺理成章地认为,凡通过对话游戏得到的结果都可被视为真的,这势必引出所谓的“相对主义的幽灵”[注]Eduardo J. Echeverrial, “Gadamer’s Hermeneu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Relativism”, in Kevin J. Vanhoozer, James K. A. Smith, and Bruce Ellis Benson (eds.), Hermeneutics at the Crossroad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51.。内格尔(Thomas Nagel)、特里格(Roger Trigg)以及尼科尔斯(Aidan Nichols)等从人的理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方面就此进行了论证。总而言之,在许多哲学家眼里,伽达默尔哲学要么被归入“简单的相对主义”(simple relativism),比如赫希(E.D Hirsch),要么被归入于“复杂的相对主义”(sophisticated relativism),比如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和斯托特(Jeffrey Stout)[注]Eduardo J. Echeverrial, “Gadamer’s Hermeneutics and the Question of Relativism”, p.52.,很难形成所有人都承认的普遍的实际性真理。
伽达默尔自己想必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为了避免相对主义缺陷,他必须紧紧抓住存在概念,断定对话的真理形式之所以可能,根本上在于存在在人的理解中的现身。也就是说,伽达默尔被迫要削弱乃至放弃诠释学的开放性,转而打造一个以游戏-对话的真理形式为开端、以存在本体论为目的的闭合的诠释学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要调和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内在张力,唯一办法就是预定诠释学方法和基础存在论是内在一致的,并以语言为中介去论证这一可能性。伽达默尔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几乎就围绕它展开。伽达默尔的解决方案无疑存在勉强之处,用存在论承接真理概念的做法,无异于真理的冗余理论,不能真正改变真理概念在海德格尔哲学中被搁置的命运,实质上是对海德格尔真理态度的一种默认。
尽管如此,伽达默尔在真理的形式安排上又是成果显著的,他为真理找到了一种最自由和开放的形式,即对话。依照扎巴拉的观点,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由对话所开启的就是伽达默尔在《自述》中所宣称的“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这领域存在于根本的语言性或语言相关性中……并且这样诠释学的普遍性就可以得到证明”[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卷二,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06页。。如此一来,尽管他慷慨地迁就了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但同时诠释学的讨论也被彻底牵引到语言当中来了。这个变化如此之绝对,以至于伽达默尔哲学常被视为“泛语言主义”(panlinguisticism)而饱受指责。在此意义上,被保留下来的存在概念,惟有放在语言中其性质和地位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判断。今后诠释学的任务将聚焦于语言,伽达默尔甚至指出了推进这一事业的合适人选,其中之一就是图根哈特[注]Santiago Zabala, The Remains of Being: Hermeneutic Ontology after Metaphysics, p.86.。
三、图根哈特:形式语义学与真值条件句
如前所述,伽达默尔将诠释学的讨论彻底牵引到语言当中了。这一趋势实质上接续了17世纪就开始的德国哲学的“语言转向”,而经过现象学的洗礼以及英美哲学语言转向的影响,到了图根哈特,其作用变得更加明显,体现为对形式语义学的强调。我们很有必要对形式语义学这一重要概念先作一番说明。
形式语义学,除了一般的意义外,对图根哈特还有更为特殊的意味。就像他所说的:
一方面,形式语义学承担着语言分析的任务:它作为语义学,分析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与存在论在同一意义上,都是形式的。而且正因为它消除了本体论无法内在解决的弱点,所以能主张自己是存在本体论的合法继承人。[注]Santiago Zabala, The Remains of Being: Hermeneutic Ontology after Metaphysics, p.31.
由此可见,形式语义学不仅是一种语义分析的技术或方法,而且是对海德格尔存在本体论的继承。这种继承体现在,它将继续对“存在”的追问,从而保留一种“形式的主题”,使自身“仍可具备某个统一的结构与中心”[注]Ernst Tugendhat, Traditional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trans.by P. A. Gor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5.。这种统一的结构对图根哈特而言,决不能是海德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论断[注]图根哈特认为海德格尔哲学依然是形而上学,这一判断常会引发争议。,它必须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和实践。这就要求人们在语言是存在的唯一形式这一前提下,重新看待和分析存在概念本身。
对图根哈特来说,存在论自身一开始就存在着关键的弱点,只不过被海德格尔等人所忽视。按图根哈特的说法,这个弱点就是,存在本体论深陷于一种“视觉隐喻”(the metaphor of seeing)之中。《自我意识和自我限定》专门讨论了视觉隐喻,认为它是指“人们使用一个词,同时期望其他人会以某种方式明白这个词被用来意味什么”[注]Ernst Tugendhat,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 trans.by Paul Stern, Mass: the MIT Press, 1986. p.30.;被期待的方式就是“看”,即总是要用看到某个对象的样式来确定语词的意义正确与否。这是一种基础性的隐喻,“人们运用其他隐喻时都不得不先诉诸于它”[注]Ernst Tugendhat,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 p.30.。
这个隐喻几乎支配了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思考,其影响不可避免地也波及到了现象学,这首先体现在胡塞尔的哲学中。他的意向性观念总是要先验地指向某个直观对象,即便这个对象可能是不明确的,或者只是一种单纯的意识结构或状态。海德格尔似乎意识到了胡塞尔哲学的问题,将现象学的研究对象转移到存在上来,但他并未因此真正摆脱视觉隐喻的束缚,因为他终究也只是将传统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转化成了“这儿有什么的问题”。他巧妙地回避了传统哲学对存在问题的误解,但在关系到存在的对立面“无”(nothingness)或“非存在”(nonbeing)时,因为预设了“存在”的缺失,从而使“存在”又成为可被人们“思维”的对象[注]尽管“存在”本身是不可被直接思考的。。而“思维”(thinking)概念,依图根哈特所言,在古希腊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巴门尼德哲学中,所起的就是知觉(perception)的功能[注]Santiago Zabala, the Hermeneutic Natur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A Study of Ernst Tugendhat, trans.by The Author with Michael Haskel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59.。由此,“海德格尔就仍是在像传统哲学那样,以‘无内容的直观’(contentless intuition)方式去探求存在的本质”[注]Santiago Zabala, the Hermeneutic Natur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A Study of Ernst Tugendhat, p.59.,使存在又成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因此才使存在可以成为所有人去共同追问的对象。以存在本体论为基础的伽达默尔诠释学,自然也无可避免地会受困于此。
这一视觉隐喻促使海德格尔未经反思就预设存在概念具有统一的意义[注]Santiago Zabala, the Hermeneutic Natur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A Study of Ernst Tugendhat, p.57.。从语义学出发,作为Being的存在原本是系动词to be的分词形式,后者除了具有存在的意思外,还可以作为系词和等号使用。海德格尔延续了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将存在的意义凌驾于其他两个之上,使其成为所有哲学概念中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个。如果用主谓关系(predication)来表达,存在就是所有谓词中最根本的那一个。图根哈特认为,对存在这种论断虽然符合了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对象的要求,但却违背了存在背后的语义学本质。因为我们单纯从语言分析出发,并不能得到上述结论,唯一能得出这一结论的办法是,将“存在”和“无”(nonbeing)看作两个对立的概念。但如果它们是对立的,如何又能得出结论认为存在是所有概念中的最根本的呢?由此,显然会陷入理论的自相矛盾。所以,要消除视觉隐喻对传统哲学乃至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首先就要放弃预设存在具有统一的意义。那么,并不具有统一意义的存在又该是什么呢?


图根哈特在与扎巴拉的对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
与海德格尔讨论《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这篇论文时我曾说过,他不该用无蔽的真理(unverbogenheit truth)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似乎有所触动,但依然执着于无蔽的奥义。我想表明的是,日常的真理概念作为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一旦被抛弃,将后患无穷。[注]Santiago Zabala, “The Dissolution of Ontology into Formal Semantics: A Dialogue with Ernst Tugendhat”, in The Hermeneutic Natur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03.
对图根哈特而言,虽然存在作为无蔽的真理的基础这一事实被否定,但存在对真理的重要性却并未降低。现在,存在的关键作用发生了转变,从一个本体论的指引维度变为对真理形式的构造。前面讨论伽达默尔的真理时已说明,因为存在本体论的限制,他的真理观念呈现为闭合的结构,并不符合诠释学完全开放的精神。图根哈特重置了存在的功能,可以期待的一个前景是,这一闭合的真理系统将很有可能被打破。在笔者看来,图根哈特的工作确实实现了这一点。
存在对真理形式的构造性功能,集中体现在命题的真值条件的形成上。这里所说的真值条件,是指“在假设句(if-sentence)中的条件表达”[注]Ernst Tugendhat, Traditional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199.,而假设句的典型就是塔斯基的T语句,即“对所有p而言,‘p’是真命题,当且仅当p”[注]Alfred Tarski, Logic, Semantics, Metamathematics: Papers from 1923 to 1938, trans.by J. H. Woodge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p.159.。大多数哲学家倾向于用符合论来说明T语句,而图根哈特则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说:“如果某人使用断定句‘p’(如果他保证p为真),那么他就要保证上述公式的条件从句所指称的条件得到了满足。”[注]Ernst Tugendhat, Traditional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199.为了使这个说法更清楚,图根哈特作了两点说明:一是所指称的条件与其使用的正确(correctness)与否无关;二是所指称条件的满足取决于表达式自身[注]Ernst Tugendhat, Traditional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199.。很显然,图根哈特对“真理”和“正确”(correctness)作了区分,“正确”是针对语句在具体语境和交往活动中的使用而下的判断,“真理”则完全是就命题自身的意义而言的。比如“海德堡失火了”,尽管真实的海德堡并没有失火,但这个命题依然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存在的断定活动形成了真理的最基本的形式,即假设句。这个形式相比伽达默尔的真理形式具有明确的优点:
第一,存在作为断定句的断定活动,可以依照语法规则派生出假设句(真理形式),进而派生出更为复杂的真值表达式。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作为适用于所有语句的肯定活动,使命题的变化具有完全的开放性。由此,真理不再表现为一个封闭的结构。
第二,图根哈特是在元语言的意义上讨论真理形式的,相较伽达默尔基于日常语言的“对话”,其形式上更为素朴(Naïve)[注]图根哈特认为,是伽达默尔的论文《语义学和诠释学》(1972)搭建了诠释学通向分析哲学的桥梁。。就像扎巴拉对图根哈特《古代的和现代的伦理学》的援引,“诠释学经验必须源自前—诠释学的(pre-hermeneutical)、素朴的经验。我相信,唯有坚持真理要相应于素朴经验这一决然断定,相对主义才能被避免”[注]Santiago Zabala, the Hermeneutic Natur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A Study of Ernst Tugendhat, p.40.。
值得一提的是,处理真理形式的问题时,图根哈特与伽达默尔的着力点是不同的。伽达默尔更关注前述两个要求的第二个,即存在的历史性,而图根哈特则先从第一个要求,即存在视角着手,而就存在论哲学而言,存在问题无疑更为根本。尽管如此,图根哈特并未忽视历史性方面的要求。他所说的历史性依然是指历史性的第一个内涵,即“必须被视为处于世界历史的具体事件之流的语境中”。因为已经消除了对象相关的视觉隐喻,所以这里的历史语境完全是针对语言现象而言的,不再讨论脱离语境的个体和一般的存在。这种思考被图根哈特称为实践辨明(practical justification)的哲学[注]Ernst Tugendhat, Traditional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77.,其中实践的意思较为独特,主要是指“理论活动”(theoretical action)[注]Ernst Tugendhat, Traditional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77.,颇相似于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活动发生于语法的空间—时间序列内,空间构成物理对象(material object),时间则由事件(event)组成,它们结合起来又形成语境或情境(situation)。语句的最基本形式就是前面所说的断定句,它们在情境中是以类(sortal)的用法为基础的。断定句和类的基本形式都是主谓式,所以语句在情境中的理论活动差不多相当于一种真值运算,逻辑上最终会实现一种认同的机制(the mechanism of identification)。图根哈特有时也将上述过程描述为游戏,遵照规则行动的语言游戏。因为没有存在本体论和对象的支持,这种游戏活动就需借助证实规则(the rule of verification)“确定谓词是否合用”[注]Ernst Tugendhat, Traditional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370.。这里的证实规则在于真值条件的满足,实质上更强调一种逻辑的可证实性在语言现象中能有多种表现形式,比如维特根斯坦的治疗理论(therapy)。从事这种语言游戏,与从事伽达默尔的对话游戏一样,都是在现象学意义上面向事情本身。它们的差别在于,伽达默尔的游戏依然追求必然性和统一性,图根哈特的游戏则放弃了这种追求,将进一步的自主权交给了语言。图根哈特的做法无疑是受到了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的影响,他希望凭借对语言的理解,改进对实在或现象的认识。因此,图根哈特的真理形式不仅仅是对真理的一种说明,而且是一种用以描述现象的新方法,具有较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四、结语
真理无疑是哲学史上不可被忽视的概念,伽达默尔和图根哈特的工作就是将它从存在本体论的阴影下重新发掘出来,这是西方哲学在语言转向影响下势必要出现的结果。不难看到,经过他们的努力,真理概念以越来越明确的形式呈现在理解者面前。更值得重视的是,真理由此不再被理解为一种要被认识的对象,或者“探究的目标”[注]理查德·罗蒂:《真理与进步》,杨玉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导言”第4页。,而是一种现象学意义的、质朴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自由形式。这一形式自身无内容,不能被定义,却能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将真理实现出来,因此它不能是科学意义上的形式,不能是黑格尔本体论意义上的形式,也不能在胡塞尔先天主体性意义上进行讨论,纯粹只能是语言的产物;唯有凭借语言的功能和构造,才有上述可能。所以,伽达默尔虽然忠实于海德格尔哲学,却因为真理问题不自觉地走上了与后者相背离的道路;在同一条道路上,图根哈特通过语言分析的方法,重置了存在的功能,解除了存在的中心地位,恢复了真理概念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如果回到希恩对alêtheia的分析,图根哈特实际上也就是恢复了“无蔽”概念中真理的自主性,这在词源学意义上可视为对海德格尔“误读”的一次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