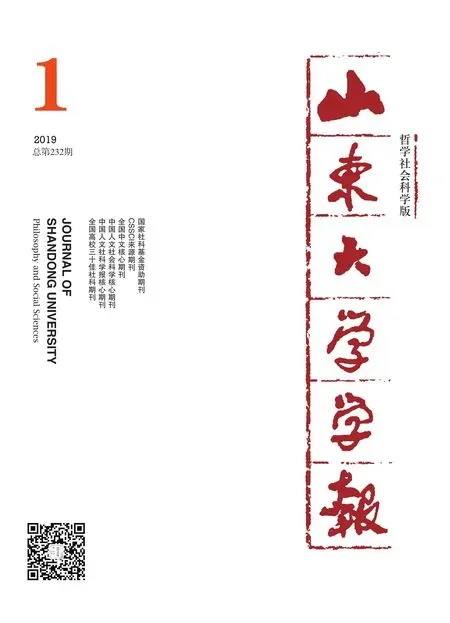节日的意义在于肯定世界
——西方文化理论视角下的阐释
刘广伟 单世联


一、理解节日的基本思路
节日是人类古老的文明传统。尽管系统的节日理论研究不多,但长久以来也未曾被忽视。比如,歌德在《意大利游记》中就阐发了节日快乐的获得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之间的相关性;荷尔德林(Hölderlin)在其有关节日的诗歌中强调了神圣的重要性;巴赫金与特纳(Turner)将节庆活动的顺利开展归因于各类象征手法,等等。其中一项基本共识是,节日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它是人类的“自由活动”。
不可否认,文化研究界借由自由活动阐发节日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古希腊哲学传统的启发。比如柏拉图的《斐德罗篇》《法律篇》《斐莱布篇》,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等等,都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谈话内容。在他们看来,节日唯有作为一种自由活动时才具有了非凡的意义;而自由活动正是人类实现幸福,获得“理智快乐”的主要途径。


以《游戏的人》闻名于世的赫伊津哈(Huizinga)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他看来,节日与游戏不仅都具有自由活动的基本属性,甚至根本就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现方式。为此,他还特意归纳了两者的一致性:“两者都宣告日常生活的停顿。两者都笼罩在欢乐的氛围之中,当然这并非必要条件,因为节日还可以是严肃的。两者都有时空范围的限定。两者都把严格的规则和真正的自由结合起来。一句话,节日和游戏有共同的特征,两者似乎都和舞蹈有密切的关系。”[注]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对于赫伊津哈的观点,德国哲学家皮柏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赫伊津哈从一开始就夸大了游戏的范畴,从而误判了游戏的实质:脱离节日,单纯的游戏根本就不能被归类为自由活动,因为它并不具备“意义在于自身”这个条件。具体来说,“一项行动之所以被认为是有意义的,其决定因素在于该行动的内容和目标,而非其表现的方式”[注]皮柏:《节庆、休闲与文化》,黄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0页。。而评价一项活动的内容和目标是否具有意义,关键要看此二者是否具有严肃性。反观游戏,虽然也有一定的严肃性,但这仅指向规则,而与内容和目标无涉。
事实上,赫伊津哈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证明游戏具有严肃性,他甚至几次三番将宗教节日的“庄严肃穆气氛”强加于游戏之上,不过始终未有实质的突破:“‘什么是游戏?’‘什么是严肃?’这两个问题和我们捉迷藏并迷惑我们,直到本书的结尾。”[注]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第245页。所以,事实或许就如皮柏所言:“游戏多半只是一种活动方式,或可曰表现的特定方式,决定其属性的是‘形式’而非其它。”[注]皮柏:《节庆、休闲与文化》,第10页。进言之,游戏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自由活动,其之所以也能引发理智的快乐,大概是由于它与节日有着密切的关联。
但是,我们仍不能就此将节日等同于自由活动,更不能将“可以引发理智的快乐”作为分析节日自身意义的唯一参照。因为在游戏之外,还有一种活动也被划归到了自由活动的范畴——它就是审美。
将审美正式纳入自由活动的范畴,要归功于18世纪末以来西方美学的发展。贡献最为突出的主要有三人,分别是康德、席勒和伽达默尔。其中,前二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理论的开创者和先行者,而真正帮助我们将节日与审美区别开来的是伽达默尔。通过分析他们的相关理论,或许可以对进一步认识节日有所助益。
具体而言,康德第一次将“游戏”概念引入审美领域,并以此开启了审美作为自由活动的讨论。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艺术与手工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的精髓是自由,而后者是被强迫的,正是在自由这一点上,艺术与游戏是相通的[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16页。。席勒紧随其后,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将“游戏冲动”(Spieltrieb)作为人性完整的象征,并视其为美的起源[注]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游戏与审美的内在一致性。
但是皮柏已经指出,单纯的游戏无法作为自由活动,所以,仅凭审美与游戏的一致性将审美界定为自由活动,似乎并不可取。其实关于审美的自由活动属性,康德在阐述审美判断的四个契机时就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在所有这三种愉悦方式(快适、善、美)中唯有对美的鉴赏的愉悦才是一种无利害的和自由的愉悦”[注]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页。。而古希腊的论述中也有许多相关的证据。例如,柏拉图在讨论节日与游戏的恩赐时就曾讲到迷狂,“最大的赐福也是通过迷狂的方式降临的,迷狂确实是上苍的恩赐”[注]《柏拉图全集》第2卷,第157页。。这里的迷狂主要涉及预言术、赎罪除灾仪式、诗人(诗歌)和爱情,其中,优秀的诗人(诗歌)便是通过诗神缪斯的迷狂而实现的——这无疑也是审美的范畴。再如,亚里士多德在有关音乐的对话中,也曾将音乐作为一种目的在于自身的活动加以讨论。由此可见,将审美界定为自由活动并非现代学者的空穴来风。
当然,伽达默尔在借用节日讨论审美的时间性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审美与自由活动的内在联系。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此,而是提供了一种区分节日与审美的可能。首先,节日是以定期重返(wiederkehr)的方式被庆祝的,而重返有别于重复,即它不只包涵着回顾,也蕴涵着变迁。进而在节日的时间中,人与节日不仅是“同在”(mitanwesenheit)——同时存在于某一时空——的关系,更是一种“共在”(dabeisein)的关系—— “谁共在于某物,谁就完全知道该物本来是怎样的”[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83页。。此外,人与节日“共在”还意味着,人在了解节日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参与到节日中来,并最终促成节日的变迁。
通过提出“共在”,伽达默尔试图说明的是,节日时间中的“共在”关系同时也是审美活动开展的条件,在这一点上,它们并无二致。不过,在谈到诗与美学的问题时他又说道:“如果有什么与一起节日的经验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不允许人与他人分隔开来。节日就是共同体的经验,就是共同体自身以其最完美的形式来表现。节日总是一切人的。”[注]Gadamer H G, Gesammelte Werke, vol. 8, sthetik und Poetik,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93, p.130.此即是强调节日的共享性,进而通过共享性的提出,节日与审美也就得以区别了。
具体而言,审美判断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单称判断仍是其首要特性,即存在普遍的美,却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美。相较之下,节日参与者对于节日的认知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还表现在了参与庆祝活动的过程中,正是集体的共同参与才促成了节日的变迁。进一步讲,节日不仅是集体的财富,也是集体创造的结果,进而由此产生的快乐必然也是集体共享的。显然,与审美相较,节日的意义更具社会性,这或许也是巴赫金(Bakhtin)之所以将节日奉为“人类文化极其重要的第一性形式”的原因[注]《巴赫金全集》第6卷,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综上,要想区别节日与其他人类活动,只消考虑其能否提供“共享的理智快乐”。而“共享的理智快乐”既然体现了节日的唯一性,且与幸福有着密切的关联,自然也可以被视作节日的意义。但需要说明的是,提供共享的理智快乐只是理想节日的属性,其在现实世界中仍有许多限制条件,所以这还不是节日最终的意义。
二、节日之所以为节日:从爱到肯定世界
有关节日最终意义的研究,我们认为皮柏的《节庆、休闲与文化》最具解释力。不过,鉴于他的论述思路与本文有异,故在此有必要结合以上结论作进一步阐释。
大致而言,皮柏主要回答了两个问题:节日是如何获得“本身就具有意义”的内在性质的;这种条件的成立最终意味着什么。而这恰好可以与 “理智快乐”和“共享”这两个条件相呼应。
第一个问题,节日如何才能获得“本身就具有意义”的内在性质呢?据前文所述,自由活动之所以获得了自身的意义,关键在于它涵盖了合于最好德性的沉思,进而由自由活动引发的快乐才是理智的。但是,如果就此将“沉思”作为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沉思”几乎就是“节制”的代名词。此外,亚里士多德也已经指出,人们并不会单纯为沉思而放弃工作。对于这个问题,皮柏给出的答案是“爱”——因为节日中有值得喜爱之物使人甘愿节制、甚至奉献。
首先,爱是参与节庆活动的目的。节日与单纯的沉思活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使人真正行动起来。根据Aquinas的观点,“凡主动者皆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行动。目的是每人所愿望和所爱的。因此,无论哪个主动者,无论做什么,显然是出于某种爱”[注]Aquinas T, Summa Theologiae, Rome: Leonine edition, 1882, p.6.。进而,人们之所以放下工作参与到节日中来,显然也是出于爱。其次,爱是节日欢乐的理由。在皮柏看来,“欢乐的理由总是一样的:拥有或是获得了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现在实际得到的,希望在将来能得到的,或是在过去的回忆中得到的”[注]皮柏:《节庆、休闲与文化》,第24页。。过节之所以比平常快乐,正是因为节日提供了更加值得喜爱的事物。再次,节日具有值得被爱的属性。人之所以喜爱某物,主要在于两个条件,即自身的匮乏感与欲望获得之物的稀缺性。节日无疑就是此二者的综合体。一方面,作为日常工作中插入的特例,节日自身就是稀缺的;另一方面,“奴隶的工作”带给人的永远都是匮乏感而非满足感,而这种匮乏感只有在节日到来时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最后,节日中的节制就是爱的表现。节制与节俭截然相反,前者约束的是对于外在的欲求,后者约束的是对于劳动成果的挥霍。最大的节制也不是停止欲求,而是在此基础上的无偿馈赠,亦即奉献或牺牲。“无偿馈赠的根据就是爱,因为我们是由于我们希望一个人好才把某件事物无偿地赠送给他的。所以,我们首先给予他的便是我们借以希望他好的那种爱。因此,爱显然具有第一赠品的本性,通过它所有无偿的赠品都被赠送了出去。”[注]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集第2-3卷,段德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54页。反观节日,不仅包含着互相祝福、赠送礼物、摆酒宴客等双向馈赠行为,也充斥着酬神、祭祖与各种浪费行为——在法国思想家巴塔耶(Bataille)那里,浪费就是人类对自然恩赐的回馈。
因此,“爱”无疑就是节日可以引发理智快乐的前提。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爱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往往会随着阅历的增长而消减。台湾散文家琹涵就曾针对“年味儿变淡”发出这样的感慨:“新年,永远都是属于孩童的。”[注]琹涵:《慢享古典诗词的节日滋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页。所以,为了维持爱的能力,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下都有相应的调节机制。比如,亚里士多德与西方经院哲学就倡导通过“默观”来培养爱的能力,中国传统思想则强调向内观照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但是,即便个人有爱的能力,且获得了所爱之物,若无人分享,也很难使快乐最大化。恰如北宋理学奠基者程颢诗中所叹:“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注]程颢《春日偶成》,载于北京大学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7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229页。春日里与自然交融使“我”感到快乐,但由于“时人”不能体会“我”的快乐,“我”的美好心境也就被打乱了。由此而来的第二个问题是:节日如何才能具备“共享性”?
皮柏虽未直接提出类似“节日的共享性”的概念,但在将节日“本身就具有意义”的内在性质归结为“爱”之前,他就已经指出,过节的重点不是怎么安排节庆,而是如何找一批能尽兴欢乐的人来参加[注]皮柏:《节庆、休闲与文化》,第13页。。这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共享”之于节日的重要性——节日归根到底是“众乐乐”的场合。不仅如此,他还归纳出了三种可能的用以保障节日共享性的内在结构,创意感、纪念性与特定意义,并分别考察了它们与“共享”的关系。
其一,那种单纯通过创意促成的节日,由于无法提供一种可供参与庆祝者共同分享的实际经验,进而无法承担起节日的共享性。创意性的节日在当代文化经济、文化产业的背景下随处可见。事实上,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类节日就已经比比皆是了:“打开那些尘封的节日档案纸匣。其丰富多彩就能让人眼前一亮:青年节,胜利节,老年节,农业节,伉俪节,共和国节,人民主权节……没完没了的节日!各地都在庆祝节日:甚至最小的区镇一年也有几个节日,甚至一个月就有几个节日;彩旗飘扬,鼓声激荡,木工画工应招齐聚,歌曲反复颂唱,节目精心安排。”[注]奥祖夫:《革命节日》,第26页。这些节日几乎穷尽了其设计者和组织者们的所有想象力,但是它们不但没能传承下来,反而成为“无聊”的代名词。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并不在于数以千计的“自由之树”(trees of liberty)栽种活动不够盛大,也不能归咎于弗朗索瓦·约瑟夫·戈塞克(Francois Joseph Gossec)的创作,而是因为创意只能营造一种外在的形式,却不能为庆祝提供实质性的内容。换言之,这些节日虽看似热闹非凡,却往往使参与者不得要领。
其二,纪念日虽然提供了可供共享的实际经验,但如果所纪念的事物不再作为目前仍在运作的历史实在,那么它就无法当作节日被庆祝。不可否认,许多宗教性纪念日,诸如复活节、圣诞节、万圣节等,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成就了伟大的节日。但在全球化、消费主义盛行与宗教世俗化了的现代社会,这些节日的纪念意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淡化了。究其所以,过去的事物已经与当下发展着的历史脱节,人们不仅不再为过去感到光荣,更很难从中获得鼓舞。有关此,目光敏锐的歌德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两年就已经有所觉察,“最近几天热闹非凡,但是没有发自内心的快乐。其实,碧空如洗,日暖风和,天公作美,内心不快,怪不得老天爷”[注]歌德:《意大利游记》,赵乾龙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64页。。在歌德看来,即便还只是社会变革的前夕,由旧势力(教会)组织的节日就已经像极了“蠢事”。
其三,诸如诞生、结婚、返乡等特定事件,不仅常被视作节日的原型,也保障了自身作为经验的有效性,但前提是其意义不被参与者否定。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就曾指出,所有关于存在的拷问与反思,都将把人引向虚无——这无疑是一种意义的否定形式。而任何时候反思所把握的东西,就是具体行为本身,即一系列特殊的、有特定日子的欲望[注]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691页。。所以依照萨特的看法,所有特定事件本身就是荒谬的,自然也没有庆祝的必要。萨特的“虚无主义”对当代所谓的后现代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很难不去接受许多人对特定事件的意义持否定态度的事实。
总而言之,虽然这三种共享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为节日营造了欢乐的氛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作为节日欢乐的理由而自存。正如前文所述,节日之所以可以带给人们以理智的快乐,是因为人们从中获得了他们喜爱的东西。所以,真正成就了节日的并非这一系列外在的东西,而是参与到节日中的人——他们必须为自己的“喜爱”创造出一个绝对的条件。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节日内在的意义结构不被否定呢?在此,皮柏借鉴了尼采的观点并指出:任何事都关涉着存在的整体,所以不否定任何事的存在基础,就意味着必须赞同每一件事;这种赞同不仅涉及个体对自身和世界的赞同,在节庆中它还需成为一种涉及广泛存在的集体认同——这便是“肯定世界”。

我的心一直对新事物总是着迷的,对于一切都是以孩童般的欢乐去接受,甚至可以说,是以天使般的欢乐去接受的,因为这种无忧无虑的享受确实有点像天堂里的那种宁静的幸福。草地上的午餐,凉亭下的夜饮,采摘瓜果,收获葡萄,灯下和仆人一起剥麻,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真正的节日。[注]卢梭:《卢梭论戏剧》,王子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314页。
当然,“肯定世界”是节日文化价值的概念性表达,而节日本身则是丰富的活动形式。所以,接下来仍有必要结合其他人的理论与实际的历史经验,对该理论加以验证。
三、肯定叙事诸形式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注]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5.。肯定世界其实同样属于“意义”的范畴,即唯有现象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投射到观念的领域时,肯定世界才有可能与人的意识发生联系并成为一种诉求。所以,肯定世界的关键并不在于承认客观事物的存在,而是如何处理现象世界和意义世界之间的关系。常识和科学作为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纽带,虽然体现着人的认知力,但不能否认的是,不论人怎样努力穷尽这个世界的“真实”,都无法摆脱来自人性的“隐蔽的、无可消除的醉意”,比如爱、想象力以及既有文化对人的塑造等等[注]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2页。。为此,文明人类还发明了一系列超验的叙事并将它们规定为全部实在,以回答现象世界中所涉及的形而上问题与其他未解之谜。然而,由于这些叙事并不能在现实的世界中得到验证,进而也就与意义世界中可验证的部分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
当然,意义世界的二元性并不意味着世界永远无法被肯定。为了满足自身的形而上学需求,人类还发明了一系列可以暂时解除意义世界二元冲突的肯定叙事,并通过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更为普遍的节日将世界的总体性呈现在人们面前。不过在此之前,人们首先会借助一些想象出来的形象,以达到更为直观地表征意义世界二元性的目的。

通过将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对立起来,尼采发现了第一种、也是唯一一种存在过的肯定世界的形式,那就是古希腊悲剧。具体而言,在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曾以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为依据对艺术形式进行了区分。其中,作为光明之神的阿波罗使万物呈现“美的外观”或“美的假象”,与其相对应的是注重“外观/假象”的造型艺术;而作为酒神的狄奥尼索斯,因为总是处在迷醉的状态,即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中,进而与其对应的艺术形式就是音乐。相较而言,个体可以通过阿波罗提供的外观/假象实现自我的肯定,而狄奥尼索斯却会使人在迷醉中反思这种肯定。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如果说前者指向的是一种被建构/渲染的、看似确切的宏大叙事,那么,后者则指向一种企图摆脱假象并回归本真(存在母体)的自然冲动。总之,无论作为艺术原则还是认识原则,此二者都是天然难以调和的。不过,谢林却在艺术的最高成就中看到了这两种力量的结合;而尼采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艺术就是古希腊悲剧。
当希腊第一个抒情诗人阿尔基洛科斯阿波罗对吕坎伯斯的女儿表明自己疯狂的爱恋,而同时又表明自己的蔑视时,在我们面前放纵而陶醉地跳舞的并不是他自己的激情:我们看到的是狄奥尼索斯及其女祭司,我们看到的是酩酊的狂热者阿尔基洛科斯醉入梦乡——正如欧里皮得斯在《酒神的伴侣》中为我们描写的,日当正午,他睡在阿尔卑斯高山的牧场上——:而现在,阿波罗向他走来,用月桂枝触摸着他。于是,这位中了狄奥尼索斯音乐魔法的沉睡诗人,仿佛周身迸发出形象的火花,那就是抒情诗,其最高的发展形态叫做悲剧与戏剧酒神颂歌。[注]尼采:《悲剧的诞生》,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页。
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作为肯定形式的悲剧只不过昙花一现。进入到苏格拉底的时代,外观被规定为理性把握的对象(相、理念),与此同时,这种理性变成了德性并与幸福等同了起来。所以,到了古希腊后期,赞美狄奥尼索斯的大酒神节被禁止了;古希腊、古罗马人进而将崇拜的目光转向了其对立面——阿波罗。对于这一过程,海德格尔(Heidegger)称之为“脱落(跌落)”:“此在从它本身跌入它本身中,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与虚无中”[注]海德格尔:《存在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07页。。这也与尼采后期的观点基本一致。概括言之,意义世界曾经平衡而融洽的二元关系被打破——假象取代了真实,虽直观明确,但已很难再被深刻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为艺术原则的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在悲剧消亡后已无绝对优劣之分,但在尼采看来,他们作为肯定原则的两者,依旧缺一不可。其中,成日与酒、性、女人相伴的狄奥尼索斯,即集中体现了人对自身肉体(生命)的肯定。但是,苏格拉底片面地将阿波罗规定为理性的对象,其结果不仅是对狄奥尼索斯的否定,也是对生命价值的否定。因此,狄奥尼索斯作为生命的肯定者,必须反对苏格拉底。与此同时,狄奥尼索斯这个形象也就理所当然地由一种审美原则变成了一种肯定生命的原则——这也是继《悲剧的诞生》后尼采思想的重要转折。
然而,如果以肯定生命为目标,仅仅反对苏格拉底是不够的。通过尼采思想生涯的最后两部著作——《狄奥尼索斯颂歌》和《瞧,这个人》——可以看出,他已经将矛头转向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所宣扬的是一种比苏格拉底更为彻底的否定原则:他将此岸世界建构成一个赎罪的场所,进而不仅否定了一切审美的价值,也彻底否定了生命的价值。而从这个角度讲,狄奥尼索斯若要反对“被钉十字架者”,就必须坚定地站在否定生命的对立面,即把自己发展成为一种肯定生命的最高原则。
那么,什么才算得上“肯定生命的最高原则”呢?在尼采看来,首先是“毁灭”,而后是“重生”——只有如此,人才能获得幸福,进而生命的价值才能真正被肯定。具体而言,简单地以一种生命原则取代另一种生命原则,并不足以改变意义世界既有的二元结构,其结果无非是意义世界中二元双方的另一种失衡。所以,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摧毁旧的世界(意义)格局,进而在这个废墟中迎接新世界的诞生。反观狄奥尼索斯,这个传说中被赫拉杀害并毁掉尸身,后灵魂投生塞墨勒体内并获得重生的奥林匹斯之神,完全符合尼采“毁灭—重生”的肯定逻辑,那么狄奥尼索斯无疑也可以作为最高的肯定原则。
概括言之,从苏格拉底到耶稣基督的漫长历史中,否定生命的原则一直在西方的意义世界中占绝对上风;而要真正从这个“否定的泥沼”中挣脱,就必须经历由“毁灭”到“重生”的过程。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尼采还使用了一种更为形象的比喻,即著名的“精神三变”。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篇第一节,尼采就谈到了精神的“三种变形”:首先是骆驼,即一种身处虚无主义的负重精神;其次是狮子,即提出怀疑并说出“我愿、我要”的、充满破坏精神的权力意志;最后是小孩,即“一个新开端,一种游戏,一个自传的轮子,一种原初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页。。“骆驼”“狮子”“小孩”即分别对应了肯定世界所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等待、毁灭、重生。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尼采的思想中,最高的肯定公式并非充满力量的“狮子”,而是“小孩”——一种回到最初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回顾近代西方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得不感叹尼采伟大的洞见:从启蒙到当代,无疑正是由“狮子”向“小孩”过渡的过程。当然,其最终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毁灭—重生”的肯定逻辑并非只存在于有关历史进程的想象中,事实上它早已在现代人所熟知的节日中有过深刻的体现。
其中,中世纪欧洲的狂欢节无疑是最能体现尼采肯定逻辑的节日之一。但需要说明的是,狂欢节的伟大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能作为所有节日的范本。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节日’这个概念。我们把它与娱乐相联系。在另一个时代它是与恐惧和忧虑相关的。我们称之为‘诙谐’和‘幽默’的东西肯定不存在于别的时代。它们常常是不断变化的”[注]维特根斯坦:《文化和价值》,黄正东、唐少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所以,在此考察狂欢节并不是为了分析理想的节日形态及其构成,而是为了回答节日是如何使“肯定世界”成为可能的。
对于这一问题,以研究狂欢节而闻名遐迩的巴赫金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象征”——正是借助象征的手段,狂欢节才得以为生活在“黑暗中世纪”的人们建构出一个“肯定”的乌托邦。
首先,象征的庆祝方式保障了节日的秩序与基本安全,一系列庆祝活动进而可以获得当局的许可。狂欢节无疑是离经叛道的,在拉伯雷的小说中,诸如“血战”“切割”“焚烧”“死亡”“杀戮”“殴打”“诅咒”“辱骂”等狂欢意象几乎充斥于整个节日时空。但相关的庆祝活动不但往往秩序井然,甚至还得到了教会与当局的许可。究其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烘托出节日的气氛,所有的活动都必须尽量做到生动有趣。这就不仅要有一套严密的规范架构,以保障活动的顺利开展,而且需要大量专业演员经过提前排演,以保障活动的效果。比如,“诉讼国”的居民执达吏们,其主要谋生手段就是在节日中挨打。
其次,通过象征的方式,人们不仅可以反抗现实的秩序,甚至可以用各种方式将其摧毁。比如在狂欢节的经典节目“小丑式的国王”中,人们会将小丑化装成国王,而后花钱对其进行殴打和羞辱,最后再撕下其国王的面具。在这一过程中,活动参与者通过象征的方式,实际上便完成了对那个虽然存在于想象中,但又无比确定的真实国王的羞辱——国王就是小丑;而面具被撕下的那一刻,他便被“脱冕”了——人民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正如巴赫金所言:“在拉伯雷的小说里,怒骂从不具有单纯私人谩骂的性质;它们是包罗万象的,并且归根结底总是瞄准最高点。”[注]《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239页。
再次,通过象征,生命的“永恒轮回”得以昭示,“肯定世界”成为可能。在尼采那里,“永恒轮回”就是最高的肯定公式。而巴赫金所搜集的一系列“肉体收割”形象,就无一不体现着“永恒轮回”的哲理。比如“殴打”过后,血会变成酒,死亡会变成新生。此外,“吞食”与“生育”也是重要的“永恒轮回”意象。比如在“宰牲节”,孕妇嘉佳美丽因吃多了牛肠而脱肛,进而被误认为要分娩;又因接生婆误诊,使胎盘的包皮被撑破,并最终导致孩子从她的左耳里钻了出来。在这一系列怪诞的形象之中,胎盘的毁灭和孩子的新生联系了起来;脱出的大肠、被吃的牛肚子,与嘉佳美丽生育着的肚子联系了起来;接着,这一切又与生命的循环联系了起来,“透过嘉佳美丽吞食的和生育的肚子,我们可以看到吞食和诞生万物的大地之腹,也可以看到永恒再生的人民的身躯”[注]《巴赫金全集》第6卷,第256页。。
狂欢节以其深刻的象征性似乎使古希腊悲剧在中世纪的欧洲再次上演了,它们是如此的相似,“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激烈的爆发从一种危险的激动情绪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就是这样理解的):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成为永恒的生成乐趣本身——那种也把毁灭的乐趣包含于自身之中的乐趣”[注]尼采:《偶像的黄昏》,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00页。。此外,皮柏的“肯定世界”理论也由此得到了初步验证:节日最大的意义是肯定世界,也只有肯定世界才能成就伟大而欢乐的节日。
四、以肯定世界解释节日文化
将“肯定世界”作为节日之所以为节日的根本意义,是西方学者结合自身文化传统而给出的最后的、根本的说明。虽然由此一根本到具体的节日活动还需要有许多中间性的论述,但在节日普遍呈现出空心化、表象化特征的今天,“肯定世界”无疑为倡导节日文化价值的回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具体而言,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肯定世界”作为一种节日理论,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不可否认,皮柏因受自身天主教背景的影响,将肯定世界的动因归结为基督教信仰[注]在世界范围内,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以《圣经》为经典,故又被统称为基督教。,这也就使该理论的普遍性难免遭受质疑。具体而言,在《肯定世界》一文中,皮柏一直对非基督教信仰获得节日快乐的可能性持保留态度,并在文章多处反复强调节日快乐与基督教信仰的关联性。但是,基督教经典《马可福音》给出的解答却是“信仰使人快乐”。要知道,信仰是多元的,并非宗教的专有名词,在“宗教信仰”外还存在着“原始信仰”“哲学信仰”和“政治信仰”。此外,信仰是普遍的,在贺麟看来:“有人类就有信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东方人也有这方面的思考(对终极本原的思考)。”[注]唐逸:《幽谷的风:文化批评》,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而叔本华也曾直言,人类是“形而上学的动物”(animal metaphysicum),“形而上学需求紧随在人类的生理需求之后”,而大多数人只能通过信仰来满足这一需求[注]叔本华:《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齐格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8、170、174页。。由此可见,如果基督教信仰可以作为肯定世界的动因,那么其他信仰同样可以。
进一步讲,肯定世界实际上就是信仰被确认的结果,而节日就是信仰被确认的方式与场所。因此,无论哪种文化,持何种信仰,“肯定世界”与节日的关系都是不容置疑的。具体而言,信仰虽然可以为形而上学的问题提供一种解释,但它们毕竟无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因此这些问题的出路往往被置于彼岸世界,以使生活在此岸世界中的人难以考证与感知。当然,信仰的维系不能仅仅依靠固执的信众,全然脱离现实的信仰是不会长久的。为此,它们还必须借助一些特定的方式向人们证明自己所言非虚,而节日因具有欢乐与深刻的属性,也就成为了信仰证明自身的主要场所之一。比如,柏拉图就曾这样解释节日的由来:“诸神怜悯我们人类命运之艰辛与不幸,指定了一系列的节庆来缓解这种瘟疫,除了指派缪斯,她们的领袖是阿波罗,还把狄奥尼修斯(狄奥尼索斯)赐给我们,与我们共享这些节日以及诸神带给节日的精神养料。”[注]《柏拉图全集》第3卷,第399页。如此一来,参与者就将节日的快乐与其所信仰之物联系了起来,进而对其给定的解答更加确信;而信仰诸元素同时也被纳入到了节日的庆祝活动中,并不断丰富着节日的形式:信仰与节日相辅相成,最终使世界得以被肯定。由此可见,“肯定世界”作为节日的意义具有深刻的普遍性,自然也可以通过转换后用来解释中国的节日。
其二,“肯定世界”不仅指明了当代节日前进的方向,也揭示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曾几何时,人们认为现象世界是无法直接被肯定的,除非它在自身之外拥有一种总体性的表达,进而肯定这种总体性的力量,也就意味着肯定了整个世界。在西方,“上帝”显然就曾作为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力量,且即便是极力倡导打破牢固的上帝叙事的康德,也没能从根本上否定其存在。究其所以,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近代哲学预设了两个不容置疑的前提:人作为被造物在本质上注定作为有限者而存在;现象只是假象(schein),而本质才是存在的真理。所以他认为,“唯有上帝才赋予一切认识以真理”[注]谢林:《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页。,否则被认识的表象就无法被证明客观存在。康德显然继承了笛卡尔的怀疑论,因为根据《纯粹理性批判》的判断,先验理性是不容置疑的,即在思维和广延之间必然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人的思维要想逾越这个鸿沟就必须求助于一个中介者。纵使康德不愿将这个中介者规定为上帝,然而正如谢林(Schelling)所言:“这个未知的东西如果不是上帝,还能是什么呢?”[注]谢林:《近代哲学史》,第97页。事实上,康德后来也作出了妥协,“人们相信上帝的存在是绝对必要的,但人们证明上帝的存在却并不同样必要”[注]康德:《康德论上帝与宗教》,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
不过,绝对的上帝叙事最终还是在黑格尔那里被解构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指出,思维和广延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鸿沟——“本质就是自己过去了的或内在的存在”[注]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43页。。此即是说,认识行为可以仅是“精神”和“客体”关系,作为中介者的上帝其实并没有存在的必要。在黑格尔之外,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现象学的继承,也不断壮大着倡导由现象直达本质(共相)的现象学哲学声势。在此背景下,“肯定上帝就是肯定世界”的话语逻辑显然已经无法成立了。
不可否认,只有上帝叙事被解构,现代化进程才得以跨出实质性的一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人的形而上学需求一直存在,如果不能继“上帝”之后发展出一种新的总体性,人势必会陷入世界无法被肯定的焦虑中。然而现实是,在凭借反思的力量解构了旧的总体性以后,启蒙理性自己也被囚禁在了反思中并倒退为知性,这也就意味着它已经不再涉及形而上学的问题,进而也无法生发出任何具有总体性的叙事。所以我们看到,无法“肯定”已经成为现代节日的通病。与此同时,现代性也因片面地强调“进步”而深受诟病。为此,后现代理论家反复强调通过文化艺术为世界重新赋魅的必要性,其中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节日。因为黑格尔就曾断言,虽然现实中的科学理性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如果“理性宗教”能够出现在节庆和崇拜中,它就有可能获得引领道德的宗教性[注]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页。。此外,哈贝马斯甚至乐观地认为,在启蒙理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新的总体性,并非没有可能。由此可见,探索当代节日“肯定世界”的可能,就不仅仅关乎节日自身的存续,更寓于反思和修正现代性问题的时代命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