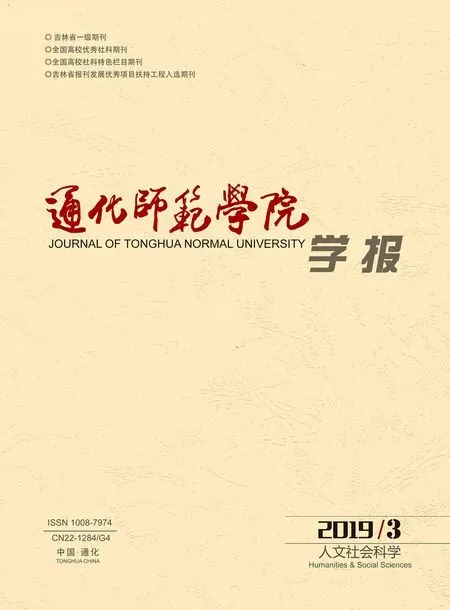《三国史记》人物类型探析
秦升阳,李春祥
《三国史记》[1]是朝鲜古籍中的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1145年(高丽仁宗23年),金富轼奉高丽仁宗之命,撰修《三国史记》。本书采录了《尚书》《春秋》《左传》《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通典》《古今郡国志》《风俗通》《括地志》等中国古代典籍及一些朝鲜古籍中的相关史料。《三国史记》全书共50卷,分别为:本纪28卷(包括新罗本纪12卷、高句丽本纪10卷、百济本纪6卷),年表3卷,志9卷,列传10卷,叙述了新罗(前57—935年)、高句丽(前37年—668年)、百济(前18年—660年)三个政权的历史。作为纪传体断代史,《三国史记》的史学价值不言而喻,但从文学角度看,其本纪所记载56个新罗王、28个高句丽王、31个百济王和列传所记载的52个人物(不包括附传人物),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目前学界已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2]。金富轼所塑造的这些生动鲜活的不同人物形象,呈现出不同的人物类型特征。以人物类型理论为指导,探讨《三国史记》的人物类型特征,对于深入探究《三国史记》的文学价值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人物类型理论概述
中国古代已经产生了人物类型理论的萌芽。如墨子的“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故举天下恶名加之,谓之暴王”[3]的理论,可视为中国古代人物类型理论的发端。[4]中国古代人物类型理论一直处在发展过程当中,如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的“意境理论”对诗、词的境界创造也作了不同类型的划分。从魏晋志怪小说开始,中国叙事文学逐渐发展,此后的唐传奇、宋代话本、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人物类型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人物类型理论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如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认为:“欲劝人为孝,则举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纪,则不必尽有其事,凡属孝亲所应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犹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5]这反映了我国古代小说家、戏剧家将人物类型理论当作塑造各类人物类型的重要创作原则,这一创作原则对于我国古代丰富的小说、戏剧等文学成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产生了许多典型的人物类型,如《三国演义》中智慧的艺术典型诸葛亮、阴险奸诈的艺术典型曹操、忠义的艺术典型关云长便是突出的代表。
古希腊人物类型理论的产生当首推亚里士多德,他将悲剧中人物的类型分为“高尚的人”和“鄙劣的人”,认为“较为严肃的诗人摹仿高尚的行为或高尚的人的行为,而较为平庸粗俗之辈则摹仿那些鄙劣的人的行为”[6],这是西方最早的关于人物类型的阐述。也有学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人物类型理论的创始人,也是18世纪以后的理论家完善类型理论,强调类型中的个性特征的起源”[7],在典型理论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典型就是类型,同时又主张类型的人物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古罗马的贺拉斯提出了人物性格创造的“定型论”,他将亚里士多德人物性格的类型定型化,贺拉斯的这一理论对西方文论界影响很大。17世纪法国的文学理论家布瓦洛赞同贺拉斯的人物理论观点,他在《诗的艺术》里主张模仿古典,表现“自然人性”,认为“写阿加门农应把他写成骄横自私,写伊尼阿斯要显出他敬畏神祉,写每个人都要抱着他的本性不移。”[8]这种新古典主义类型论在18世纪受到一些理论家的批评。法国文学理论家狄德罗强调表现人物类型中的个性特征,对新古典主义类型论中只重视类型的普遍性、把类型定型化的倾向持否定态度。歌德受到狄德罗的影响,提出要在特殊中表现一般,通过创造一个显出特征的生命力的整体来反映世界。黑格尔强调类型中的典型,人物典型被称作“理想性格”或“理想人物”(ideal character),主要从理念出发来阐明典型。19世纪的别林斯基更多地从形象出发去阐明典型,强调人物典型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他认为“每一个典型对于读者都是似曾相识的不相识者。”[9]巴尔扎克提出“典型是类型的样本,因此,在这种或者那种典型和他的许许多多同时代人之间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点”,“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往往必须掌握几个相似的人物。”[10]他侧重在人物类型中表现个别人物的个性。
到了20世纪,文学角度的人物类型理论以1927年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观点最具代表性,福斯特“将人物分成扁平的和圆形的两种”,扁平人物是“依循着一个单纯的理念或性质而被创造出来”,“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个句子描述殆尽”[11],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是咸亨酒店中“站着喝酒的唯一的人”,孔乙己便是一个典型的扁平人物;圆形人物“可以适合任何情节的要求”,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是一个集单纯、美丽、聪明、轻浮、孱弱、大胆于一身的“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给人以新奇之感”“绝不刻板枯燥”“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活泼的生命”[11]的圆形人物。福斯特可谓现代人物类型理论的奠基人,对这一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学者对人物类型理论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北京大学申丹教授提出了“功能性人物”和“心理性人物”的二分法,她认为“功能性”人物是“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或‘行动素'”,“心理性”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12],这种观点已经注意到了人物在情节中的功能,是对福斯特人物类型理论的完善和补充。更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将人物划分为“功能性人物”和“审美性人物”[13]两种类型。“功能性人物”是指在文本的叙述中起着一定调节或控制作用的人物,如《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布留金,他讲出了别里科夫的故事,在故事情节中起到了调节叙事情节发展的功能。“心理性人物”是指在文本中的叙述中充分展示其心理活动,甚至潜意识本能的人物,如《墙上的斑点》中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理性人物”,一个墙上的斑点使他展开了一系列联想,这些心理活动构成了故事的主线。“审美性人物”是指文本在叙述中突现其审美形态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包括描述人物外在行为的“扁平人物”“圆形人物”和描述人物心理活动的“心理性人物”。
上述人物类型理论是从文论角度所作的简要叙述,这一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纯粹的文学作品,对于探讨史学著作中的人物类型同样适用,下面将借助人物类型理论,并在借鉴他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学的角度对《三国史记》本纪和列传人物类型进行初步探索。
二、《三国史记》本纪人物类型分析
《三国史记》本纪记载了56个新罗王、28个高句丽王和31个百济王,共计115个国王。这些国王是以本纪的形式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记载,但从国王的行事中又能体现出其文学上人物类型的某些特点,其中既有所谓的“扁平人物”“圆形人物”,同时也有描述人物心理活动的“心理性人物”。
这些国王中大多数属于“可以用一个句子描述殆尽”的“扁平人物”类型,如新罗始祖赫居世“娶妃以德”,倭人欲犯边,因“闻始祖有神德,乃还;乐浪人将兵来侵,见边人夜户不扃,露积被野,相谓曰:‘此方民不相盗,可谓有道之国。吾侪潜师而袭之,无异于盗,得不愧乎?'乃引还。”另外赫居世不趁他国有丧征之,曰:“幸人之灾,不仁也。”乃遣使吊慰;新罗南解次次雄,“民饥,发仓廪救之。”由于国君有德,上天都会相助,“倭人来侵,流星夜坠敌营”,吓退敌兵;新罗儒理尼师今“存问,鳏寡、孤独、老病不能自活者,给养之。于是,邻国百姓闻而来者,众矣。”高句丽东川王,“王性宽仁,王后欲试王心,候王出游,使人截王路马鬣。王还曰:‘马无鬣可怜。'又令侍者进食时,阳覆羹于王衣,亦不怒。”新罗味邹尼师今“七年(268),春夏不雨。会群臣於南堂,亲问政刑得失。又遣使五人,巡问百姓苦患……十五年(276),春二月,臣寮请改作宫室,上重劳人,不从。”新罗婆娑尼师今“省用而爱民,国人嘉之。”从这些国王的行事中可以看出,他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有德之君。因为有德,不仅百姓受益,甚至上天也暗中相助,保护国家不被敌人侵犯。
除了有德之君外,还有一些国君也属于这“扁平”类型的人物,如新罗脱解尼师“望杨山下瓠公宅,以为吉地,设诡计,以取而居之。”是一个聪明而狡诈的国君;新罗讫解尼师今“状貌俊异,心胆明敏,为事异於常流。”新罗智证麻立干“三年(502)春三月,下令禁殉葬。前国王薨,则殉以男女各五人,至是禁焉。”这是一个尊重生命的开明的国王。还有心地善良的新罗真兴王,他信奉佛教,在位期间“许人出家为僧尼奉佛。”尤其是“三十七年(576)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遂简美女二人,一曰南毛,一曰俊贞。聚徒三百余人,二女争娟相妒。俊贞引南毛於私第,强劝酒至醉,曳而投河水以杀之。俊贞伏诛,徒人失和罢散。其后,更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真兴王的这一从善良角度进行的改革,将原本充满仇恨和杀戮“源花”组织变成了为新罗培养贤能之人并略带浪漫色彩的花郎徒组织。而高句丽烽上王则是一个不听劝谏的刚愎自用,最后落得个自经的下场的国王,“九年(300)八月,王发国内男女年十五已上,修理宫室,民乏于食,困于役,因之以流亡。仓助利谏曰:‘天灾荐至,年谷不登,黎民失所,壮者流离四方,老幼转乎沟壑……大王曾是不思,驱饥饿之人,困木石之役,甚乖为民父母之意。'王愠曰:‘君者,百姓之所瞻望也。宫室不壮丽,无以示威重。今国相盖欲谤寡人,以干百姓之誉也。'助利曰:‘君不恤民,非仁也;臣不谏君,非忠也。臣既承乏国相,不敢不言,岂敢干誉乎!'王笑曰:‘国相欲为百姓死耶?冀无复言。'助利知王之不悛,且畏及害,退与群臣同谋废之,迎乙弗为王。王知不免,自经。”高句丽慕本王是一个残暴的国王,“为人暴戾不仁,不恤国事,百姓怨之……王日增暴虐,居常坐人,卧则枕人。人或动摇杀无赦。臣有谏者,弯弓射之。”最后的下场是被大臣杜鲁刺杀。
新罗圣德王性格宽和仁厚,是一个一心与唐结好甘愿做唐属国的国王类型,他在位36年,共计39次遣使入唐贺正或献方物,与唐保持良好的附属国关系。除了敬献方物外,其给唐帝的上表也极为谦恭:“臣乡居海曲,地处遐陬,元无泉客之珍,本乏宝人之货。敢将方产之物,尘渎天官,驽蹇之才,滓秽龙厩。窃方燕豕,敢类楚鸡。深觉腼颜,弥增战汗。”频繁的贺正、献方物、上表令唐玄宗非常感动。玄宗降书曰:“卿每承正朔,朝贡阙庭,言念所怀,深可嘉尚。又得所进杂物等。并逾越沧波,跋涉草莽,物既精丽,深表卿心。今赐卿锦袍、金带及彩素共二千匹,以答诚献,至宜领也。”圣德王的这种执着单一的性格也影响了后来的新罗国王,此后的新罗景德王、恵恭王都成为一心与唐结好朝贡的新罗王。
相当于“圆形人物”的国王类型要少一些,但有三位颇具特点,一是新罗照知麻立干,二是新罗文武王,三是高句丽琉璃明王。新罗照知麻立干“幼有孝行,谦恭自守,人咸服之。”但在“王二十二年(500)秋九月,王幸捺巳郡。郡人波路有女子,名曰碧花,年十六岁,真国色也。其父衣之以锦绣,置以色绢献王。王以为馈食,开见之,然幼女,而不纳。及还宫,思念不已,再三微行,往其家幸之。路经古郡,宿於老妪之家,因问曰:‘今之人以国王为何如主乎?'妪对曰:‘众以为圣人,妾独疑之。何者?窃闻王幸捺巳之女,屡微服而来。夫龙为鱼服,为渔者所制。今王以万乘之位,不自慎重,此而为圣,孰非圣乎?'王闻之大惭,则潜逆其女,置於别室,至生一子。”照知麻立干当王之前“谦恭自守”,颇有美名,但当王后,在美色的诱惑与圣王的美名之间,他选择了前者,放弃了拥有已久的圣王美名。这种品行的变化表现了照知麻立干具有一点“圆形人物”的特色。新罗文武王是一个性格怪癖的王,他是《三国史记》所记115个国王中唯一一个有爱恋男童之癖的国王,“八年(668)冬十月二十五日,王还国,次褥突驿,国原仕臣龙长大阿餐私设筵,飨王及诸侍从。及乐作,奈麻紧周子能晏,年十五岁,呈加耶之舞。”文武王见能晏长得“容仪端丽”,便将能晏召到自己近前,以手抚摸能晏之背,然后“以金盏劝酒,赐币帛颇厚。”在对大唐的态度上,则阳奉阴违,表面恭敬,实则我行我素。“九年(669)春正月,唐僧法安来,传天子命,求磁石。夏五月,遣祗珍山级餐等入唐,献磁石二箱。又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餐入唐谢罪。”一方面文武王对唐有求必应,另一方面则暗中“擅取百济土地遗民”,同时封高句丽大臣渊静土之子安胜为高句丽王,其册曰:“谨遣使一吉餐金须弥山等,就披策、命公为高句丽王。公宜抚集遗民,绍兴旧绪,永为邻国,事同昆弟,敬哉敬哉。兼送粳米二千石,甲具马一匹,绫五匹,绢细布各十匹,绵十五称,王其领之。”结果唐高宗大怒,“诏削王官爵。”当时唐灭高句丽势头正盛,为避免与高句丽有同样的下场,文武王对唐表面上十分谦卑,以麻痹唐高宗,暗中却网罗高句丽余部,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与唐朝抗衡。
高句丽琉璃明王的“圆形人物”特点要比文武王显著一些,他幼时顽皮,当王以后多情、残忍、凶狠。幼年顽皮,“出游陌上弹雀,误破汲水妇人瓦器。妇人骂曰:‘此儿无父,故顽如此。'”当王后,又很多情,“三年(前17)冬十月,王妃松氏薨。王更娶二女以继室,一曰禾姬,鹘川人之女也;一曰雉姬,汉人之女也,二女争宠不相和,雉姬惭恨亡归。王闻之,策马追之,雉姬怒不还。王尝息树下,见黄鸟飞集,乃感而歌曰:‘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琉璃明王还残忍、凶狠,“十九年(前1)秋八月,郊豕逸。王使托利、斯卑追之,至长屋泽中得之,以刀断其脚筋。王闻之怒曰:‘祭天之牲,岂可伤也?'遂投二人坑中杀之。”同时对太子也痛下杀手,“王遣人谓(太子)解明曰:‘吾迁都,欲安民以固邦业。汝不我随,而恃刚力,结怨于邻国,为子之道,其若是乎?'乃赐剑使自裁。太子乃往砺津东原,以枪插地,走马触之而死,时年二十一岁。”如此杀害太子,令金富轼都慨然论曰:“今王始未尝教之,及其恶成,疾之已甚,杀之而后已。可谓父不父,子不子矣。”
小说中的“心理性人物”可以充分展现其心理活动,像《墙上的斑点》中的“我”那样以心理活动展开故事情节。《三国史记》中关于国王心理活动的描写并不充分,但在具体行事过程中体现了其心理活动,可以看作是“心理性人物”。如高句丽山上王和新罗敬顺王便是如此。山上王是一个借助王嫂于氏当上高句丽王的人,“初,故国川王之薨也,王后于氏秘不发丧,便往延优(故国川王之弟)之宅。延优起衣冠,迎门入座宴饮。王后曰:‘大王薨,无子,发歧作长当嗣,而谓妾有异心,暴慢无礼,是以见叔。'于是,延优加礼。”对于王嫂于氏的突然到来和故国川王的突然去世,山上王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似乎看到了平日里心中仰慕的王嫂于氏和高高在上的王位离自己越来越近了,这种激动而复杂的心理活动通过下面的行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宴饮过程中,延优“亲自操刀割肉,误伤其指”,于氏“将归,谓延优曰:‘夜深恐有不虞,子其送我至宫。'延优从之”,并与“王后执手入宫。”延优取得王位以后00000,立于氏为后,但其心中是不甘心“不复更娶”的,于是借夜梦给自己“更娶”寻找借口。“七年(203)春三月,王以无子,祷于山川。是月十五夜,梦天谓曰:‘吾令汝少后生男勿忧。'王觉语群臣曰:‘梦天语我谆谆如此,而无少后奈何?'巴素对曰:‘天命不可测,王其待之。'”在“十二年(208)冬十一月,郊豕逸,掌者追之,至酒桶村,踯躅不能捉。有一女子,年二十许,色美而艳,笑而前执之,然后追者得之。王闻而异之,欲见其女。微行,夜至女家。使侍人说之,其家知王来,不敢拒。王入室,召其女,欲御之。女告曰:‘大王之命,不敢避。若幸而有子,愿不见遗。'王诺之。至丙夜,王起还宫。”这段记载说明山上王既顾及王后于氏又要暗中临幸民女,这一举动将山上王即位前后在这件事上的心理活动充分展现出来。
新罗敬顺王是一个明大义的亡国之君。当新罗行将灭亡,国土日蹙,甄萱与高丽大军不断吞灭新罗国土的时候,敬顺王感到亡国的脚步迫近,在国家之名、王位与人民的生命安危之间,敬顺王经过多次的心理斗争,最后做出了痛苦的抉择,归顺王建。931年,敬顺王与王建见面,商讨新罗归顺之事,敬顺王置宴于临海殿,“酒酣王言曰:‘吾以不天,寝致祸乱。甄萱恣行不义,丧我国家,何痛如之。'因泫然涕泣。左右无不呜咽,太祖亦流涕慰藉。”935年,敬顺王“乃与群下谋举土降太祖。群臣之议,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王子曰:‘国之存亡,必有天命,只合与忠臣义士,收合民心自固,力尽而后已。岂宜以一千年社稷,一旦轻以与人。'王曰:‘孤危若此,势不能全。既不能强,又不能弱,至使无辜之民,肝脑涂地,吾所不能忍也。'乃使侍郎金封休赍书,请降于太祖。王子哭泣辞王,径归皆骨山。倚岩为屋,麻衣草食,以终其身。”在归顺那天,“王率百寮,发自王都,归于太祖。香车、宝马连亘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观者如堵。”这里虽然没有描写敬顺王心理怎么想的,但通过这些描写,生动地再现了沿途新罗百姓亲视昨日的国王,如今落得亡国之君的境地,金富轼以“道路填咽,观者如堵”反衬了此时新罗王悲凉的心情。
三、《三国史记》列传人物类型分析
《三国史记》中共记载了52个列传人物(不包括附传人物),其中有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的政治、军事、平民人物,既有在战场上为国效死的英雄,也有为了保全自己把妻子献给国王的懦夫,还有弑君、反叛的国之逆臣,许多人物的描写十分精彩,人物类型特点突出,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这52个列传人物中属于“扁平人物”类型的最多,这类人物中,在战场上勇于效死的英雄比较多,他们都是秉承为国献身的宗旨,壮烈殉国,如新罗将领奚论,是一个秉承父志为国效死的勇士。“至建福三十五年(618),奚论为金山幢主,与汉山州都督边品兴师,袭岑城,取之。百济闻之,举兵来,奚论等逆之。兵既相交,奚论谓诸将曰:‘昔吾父殒身于此,我今亦与百济人战于此,是我死日也。'遂以短兵赴敌,杀数人而死。”新罗僧徒骤徒,在百济来攻的时候,脱去僧衣,“乃诣兵部,请属三千幢,遂随军赴敌场。及旗鼓相当,持枪剑突阵力斗,杀贼数人而死。”新罗将军品日之子官昌,“仪表都雅,少而为花郎,善与人交。唐显庆五年(660),王出师与唐将军侵百济,以官昌为副将。至黄山之野,两兵相对。父品日谓曰:‘尔虽幼年有志气,今日是立功名,取富贵之时,其可无勇乎!'官昌曰:‘唯。'即上马横枪,直捣敌阵。驰杀数人,而彼众我寡,为贼所虏。生致百济元帅阶伯前。阶伯俾脱胄,爱其少且勇,不忍加害,乃叹曰:‘新罗多奇士,少年尚如此,况壮士乎!'乃许生还,官昌曰:‘向吾入贼中,不能斩将搴旗,深所恨也。再入必能成功。'以手掬井水,饮讫,再突贼阵疾斗。阶伯擒斩首,系马鞍送之。品日执其首,袖拭血曰:‘吾儿面目如生,能死于王事,无所悔矣。'”新罗将领金歆运,“永徽六年(655),太宗大王愤百济与高句丽梗边,谋伐之。及出师,以歆运为郎幢大监。”战斗中,“歆运拔剑挥之。与贼斗,杀数人而死。”新罗将领竹竹,善德王“王十一年(642),百济将军允忠领兵来攻其城。竹竹收残卒,闭城门自拒。舍知龙石谓竹竹曰:‘今兵势如此,必不得全,不若生降以图后效。'答曰:‘君言当矣。而吾父名我以竹竹者,使我岁寒不凋,可折而不可屈。岂可畏死而生降乎!'遂力战至城陷,与龙石同死。”新罗将领匹夫,为七重城下县令。高句丽发兵来围七重城。“匹夫守且战二十余日,贼将见我士卒尽诚斗不内顾,谓不可猝拔,便欲引还。逆臣大奈麻比歃密遣人告贼以城内食尽力穷,若攻之必降。贼遂复战。匹夫知之,拔剑斩比歃首,投之城外。乃告军士曰:‘忠臣义士,死且不屈。勉哉努力,城之存亡,在此一战。'乃奋拳一呼,病者皆起,争先登。而士气疲乏,死伤过半。贼乘风纵火,攻城突入。匹夫与上干本宿、谋支、美齐等向贼对射,飞矢如雨支体穿破,血流至踵,乃仆而死。”百济将军阶伯,“唐显庆五年(660)庚申,高宗以苏定方为神丘道大总管,率师济海,与新罗伐百济。阶伯简死士五千人拒之曰:‘以一国之人,当唐罗之大兵,国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吾妻孥没为奴婢,与其生辱,不如死快。'遂尽杀之。至黄山之野,设三营,遇新罗兵,将战,誓众曰:‘昔句践以五千人破吴七十万众,今之日宜各奋励决胜,以报国恩。'遂鏖战,无不以一当千,罗兵乃却。如是进退至四合,力屈以死。”这些战死沙场的英雄,其壮烈的事迹无不令人动容。
《三国史记》中文字最多的人物列传是金庾信传,他是一位重要的新罗将领,也属于“扁平人物”类型,金庾信“年十七岁,见高句丽、百济、靺鞨侵轶国疆,”就“慷慨有平寇贼之志。”成为将领后,作战不惧生死,在“建福四十六年(629),率兵攻高句丽娘臂城……庾信……乃跨马拔剑,跳坑出入贼阵,斩将军,提其首而来。”表现了作战不惧生死的性格。为了国家的战事,三过家门而不入,645年,“信从外地归家,但因战事紧急,三过家门而不入。”又善于用计谋,在唐苏定方率领20万大军前来灭百济的时候,信为押梁州军主,为了试探民心是否可用,信“若无意于军事,饮酒作乐,屡经旬月。州人以庾信为庸将,讥谤之曰:‘众人安居日久,力有余,可以一战,而将军慵惰,如之何!‘庾信闻之,知民可用,告大王曰:‘今观民心,可以有事。请伐百济以报大梁之役。'”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将金庾信塑造成一个一心为国、善于计谋、作战勇敢的正面人物形象。
此外,“扁平人物”类型的人物还有许多,如勇敢而有智谋,临危不乱,集勇敢、智慧、富有军事才能于一身的英雄人物形象高句丽大臣乙支文德;言而有信、知恩图报的新罗将领居柒夫;少年便有报国之志、有一颗仁慈之心又极重友情的新罗将领斯多含;一心为国、苦心劝谏的新罗良臣金后稷;类似于荆轲的高句丽英雄人物纽由;天资温良,以孝顺为时所称熊川州板积乡人向德、菁州人圣觉、韩歧部百姓连权女子孝女知恩;自知必死而不避之,“死非其所,可谓轻泰山于鸿毛者也”的近乎呆板愚蠢的沙梁宫舍人剑君等等,都是人物性格单一执着,并极具自己的特点的类型。
《三国史记》列传中属于“圆形人物”的类型人物主要有三个:弓裔、甄萱、丕宁子。新罗景文王膺廉之子弓裔,后高句丽的建立者,少年时孝顺、懂事,因为“生而有齿,且光焰异常,恐将来不利于国家……王敕中使抵其家杀之,使者取于襁褓中,投之楼下。乳婢窃捧之,误以手触眇其一目,抱而逃窜,劬劳养育。年十余岁,游戏不止。其婢告之曰:‘子之生也,见弃于国。予不忍,窃养以至今日。而子之狂如此,必为人所知。则予与子俱不免。为之奈何?'弓裔泣曰:‘若然,则吾逝矣。无为母忧。'便去世达寺……祝发为僧,自号善宗。”但当他称王后,却变成一个穷奢极欲、残忍的人,“善宗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被方袍,又自述经二十余卷,其言妖妄,皆不经之事。时或正坐讲说,僧释聪谓曰:‘皆邪说怪谈,不可以训。'善宗闻之怒,铁椎打杀之。”后来甚至将夫人康氏残害致死。“贞明元年(915),夫人康氏以王多行非法,正色谏之。王恶之曰:‘汝与他人奸,何耶?'康氏曰:‘安有此事?'王曰:‘我以神通观之。'以烈火热铁杵,撞其阴,杀之,及其两儿。尔后多疑急怒,诸寮佐将吏,下至平民,无辜受戮者,频频有之。斧壤,铁圆之人,不胜其毒焉。”
后百济的建立者甄萱,年轻时“体貌雄奇,志气倜傥不凡”“喜得人心”,但对战败的新罗国王却残忍加害,暴露他性格中阴暗残忍的一面,天成二年(927)秋九月,“萱猝入新罗王都。时王与夫人嫔御出游鲍石亭,置酒娱乐。贼至,狼狈不知所为,与夫人归城南离宫。诸侍从臣寮及宫女伶官皆陷没于乱兵。萱纵兵大掠,使人捉王,至前戕之。便入居宫中,强引夫人乱之。”
丕宁子是一位新罗勇士,最后也英勇战死疆场,与其他勇士不同的是,丕宁子既有为国而死之心,又有为家庭考虑的一点私心,表现了一个平常人的平凡思维,真德王元年(654),百济以大兵来攻茂山等城,丕宁子随金庾信率军迎敌,出战前,丕宁子“谓奴合节曰:‘吾今日上为国家,下为知己死之。吾子举真虽幼年,有壮志,必欲与之俱死,若父子并命,则家人其将畴依?汝其与举真好收吾骸骨归,以慰母心。'言毕,即鞭马横槊,突贼阵,格杀数人而死。举真望之欲去,合节请曰:‘大人有言,令合节与阿郎还家,安慰夫人。今子负父命,弃母慈,可谓孝乎!'执马辔不放。举真曰:‘见父死而苟存,岂所谓孝子乎!'即以剑击折合节臂,奔入敌中战死。合节曰:‘私天崩矣,不死何为!'亦交锋而死。”一幕何其悲壮的父、子、仆三勇士慨然赴死的英雄画面,表现了作为一个有着妻子儿女的平凡人的丕宁子,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既要为国而死,又在这生死关头流露出挂念妻儿的令人不禁泪落的感人亲情。
《三国史记》列传中属于“心理性人物”的主要有盖苏文和都弥。盖苏文是高句丽大臣,他“自云生水中以惑众。”仪表雄伟,意气豪逸,但同时又善于伪装、凶狠和残暴。“其父东部或云西部大人大对卢死,盖苏文当嗣,而国人以性忍暴恶之,不得立。”在这种情况下,“苏文顿首谢众,请摄职,如有不可,虽废无悔。”众臣被盖苏文的虚伪所欺骗,“众哀之,遂许嗣位。”但后来众臣认为盖苏文凶残不道,“诸大人与王密议欲诛,事泄。”结果“苏文悉集部兵,若将校阅者,并盛陈酒馔于城南,召诸大臣共临视。宾至,尽杀之,凡百余人。驰入宫,弑王,断为数段,弃之沟中。立王弟之子臧为王。自为莫离支,其官如唐兵部尚书兼中书令职也。”此后盖苏文彻底撕去了自己“意气豪逸”的伪装,“于是号令远近,专制国事。甚有威严,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每上下马,当令贵人武将伏地而履之。出行必布队伍,前导者长呼,则人皆奔迸,不避坑谷。国人甚苦之。”
都弥是一个百济盖娄王时的编户小民,“其妻美丽,亦有节行,为时人所称。”荒淫的盖娄王闻听之后,召都弥与语曰:“凡妇人之德,虽以贞洁为先,若在幽昏无人之处,诱之以巧言,则能不动心者,鲜矣乎!”都弥“对曰:‘人之情不可测也。而若臣之妻者,虽死无贰者也。'王欲试之,留都弥以事。”都弥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而且远近闻名,盖娄王问他这些话,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面对这种情况,都弥进行着复杂的思想斗争,一面是盖娄王的淫威,一面是美丽的妻子,一面是自己的一己私利,思考的结果是面对强大的国王,都弥将自己的妻子扔到了一边,去迎合盖娄王的心意,将自己的妻子拿来比喻,主动给盖娄王一个可乘之机,将美丽的妻子奉献给国王。在危险到来之际,都弥可耻地选择了屈服。也许都弥想以此保全自身,因为他知道违背君意的后果,希望以此保全自己,把全部的危险和耻辱无情地留给妻子一个人独自面对和承担,反映了都弥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将美丽的妻子当作换取自己安全的筹码。结果是都弥的妻子以智慧和勇敢独自应对盖娄王的淫威和胁迫,最终得以全身而逃,盖娄王终于未能得逞,都弥自己也被盖娄王矐去双眸,未能保全自己。妻子后来在泉城岛上遇到都弥,不仅没有因都弥双目失明而抛弃他,还“掘草根以吃,遂与同舟,至高句丽山之下。丽人哀之,丐以衣食。遂苟活,终于羁旅。”和美丽、智慧、勇敢、善良的妻子相比,都弥显得那么丑陋、愚蠢、自私和猥琐,这显著的对比虽然通过都弥与盖娄王的对话表现出来,但这种表现却是都弥复杂心理活动带来的结果。而金富轼却评价都弥:“虽编户小民,而颇知义理。”不知金富轼所说的这个“义理”是什么“义理”,难道是将自己的妻子无偿献给国王就是“知义理”?真是令人费解。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人物类型的相关理论研究《三国史记》中的人物类型,虽然不免有生搬硬套和以偏概全之嫌,同时《三国史记》中所谓的“扁平人物”“圆形人物”“心理性人物”的人物类型特征亦不像纯粹的文学作品那样鲜明和丰满,至于像“功能性人物”和“审美性人物”这种更为复杂的文学人物类型在《三国史记》中更是难以找到,尽管如此,如上文所述,许多《三国史记》人物类型还是颇具特色的,如丕宁子的平民性格本色、都弥妻子的坚贞勇敢的性格、盖娄王的好色性格等等,都是很有人物类型特点的。性格决定类型,每一种人物类型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许多《三国史记》本纪、列传中的人物基本能达到黑格尔所说的人物“要有一个丰富充实的心胸,而这心胸中要有一种本身得到定性的有关本质的情致,完全渗透到整个内心世界”[14]这一性格特征。《三国史记》中大多数本纪和列传的字数都比较少,而这比较少的文字又能体现出多种人物的类型特征,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物本身具有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和金富轼较高的文学修养密切相关。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记表》中说道:“是以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星。”[15]史家“三长”是刘知几提出的一个优秀史家所具备的三个条件,其中的“史才”便是指写史的表达能力,金富轼以史家“三长”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认真效法学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的著史方法,在本纪、列传的记述中最大程度地展现了自己的史学和文学才能,为后人呈现了一部人物类型相对丰富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从而使《三国史记》在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的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