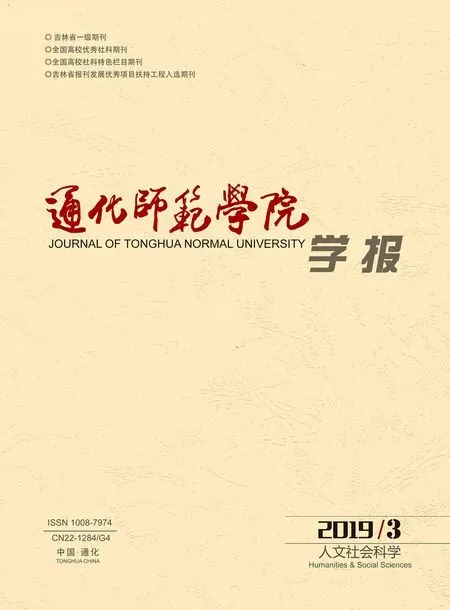从范畴理论视角看“姓”是不典型的关系动词
崔山佳
一、引言
关系动词又称“同动词、系词、联系动词、判断词、判断动词、分类动词”等,是汉语动词中较为特殊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类词。[1]
马建忠[2]、王力[3]、吕叔湘[4]、赵元任[5]、张静[6]、刘月华等[7]等对关系动词作过研究,但把“姓”当作关系动词,是赵元任于1979年在其《汉语口语语法》中最早提出来的。
关系动词与一般动词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的个性。袁毓林[8]说,不允许宾语悬空的动词大都是关系动词,如“属于、成为、不及、不如、不比、姓、是、号称、等于、具有……”,它们的句法特点是:一般不能重叠,不能带“着、了、过”等体标记;其主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施事,其宾语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事,宾语不能省去。在这段文字后有一注释:参考吕叔湘主编《现代汉语八百词》[9]第25∼26页。可见,袁毓林的看法主要来自吕叔湘。
沈家煊[10]引用了袁毓林的观点:据袁毓林,汉语中有一些动词跟宾语结合十分紧密,不允许宾语脱离而悬空,如“属于、成为、不及、不如、姓、是、等于、具有、号称”等动词,它们的宾语就不能移到句首充当话题。
张宝林说,鉴定关系动词有5条标准:(1)关系动词的语义功能是对其前后两个成分之间的同一或类属关系加以肯定或认定,这种肯定或认定没有动作性,是相对静止的、没有发展变化的;(2)一般不带动态助词“了”“着”“过”;(3)一般不能重叠;(4)一般用“不”表示否定;(5)不能带表示幅度或次数的数量词语。[1]
张宝林又说,这5条标准当中,第(1)条语义功能标准是决定性的,凡不符合此条的,即可判定其不是关系动词,后四条是句法功能标准,其中第(5)条具有决定性作用,不符合这一条的,也不是关系动词。因此,(1)(5)两条是判定关系动词的必备条件,即必须同时满足这两条标准的动词才能是关系动词,其他三条标准可用作参考[1]。
“关系动词”也有说作“粘宾动词”。张斌[11]301说:“但有些动词必须带宾语,称为粘宾动词。”张宝林[12]78说作“连宾动词”,说它是“必须带宾语,宾语不能省略的动词”。李英哲等[13]128叫“命名(指称)动词”。林祥楣[14]216说,“姓”等动词必须带宾语。
针对上面学者所提出的关系动词语法特点和几条标准,我们从范畴理论的角度谈一下看法。我们知道,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范畴理论又分经典范畴理论与原型范畴理论,两者有明显的不同。经典范畴理论主张具有共同特征的事物才能列为同一范畴,Witt-genstein用“家族相似性”来描述一个范畴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后来,以Rosch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家进一步证实了在范畴化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原型,把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自然范畴称为原型范畴,建立了原型范畴理论。这一理论将语义范畴分为“中心”和“边缘”。[15]“姓”虽然是一个关系动词,但却是一个特殊的关系动词,用原型范畴理论作一番探讨,可以显示其独特的个性。(本文下面所说的范畴理论都指原型范畴理论。)
二、“姓”的宾语可悬空
袁毓林说:“姓”跟宾语结合十分紧密,不允许宾语脱离而悬空。其实,“姓”允许宾语脱离而悬空。关于这方面的语料可参见崔山佳《现代汉语“潜显”现象研究》[16]和《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17]。此外,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也有例子(该语料库有“综合”“文学”“报刊”“微博”“科技文献”“古汉语”等),如:
(1)欣然说完转身想走,到了门口,又回头:“你叫什么名字?郝君?一下错了两个,第一,姓错了,应该姓‘坏’,第二,叫‘君’。你连人都不是!”(郁秀《花季雨季》)
(2)“诸葛先生没有姓错,他当得起。”(温瑞安《大侠萧秋水》)
(3)果然,马哥没姓错,和化腾隔着鄱阳湖互相呼应啊。(微博)
(4)一名打手双手叉腰,劈面拦住冷笑一声问:“小子,你姓杜?”他知道是找麻烦的来了,冷笑道:“怎么,姓错了么?”“姓杜没错,杜天磊?”(云中岳《草莽芳华》)
(5)可是,突然他心里一跳,忙停步回过了身:“姑娘姓什么?”大姑娘一张娇靥绷得紧紧的,道:“姓欧阳,难道我姓错了么?”(独孤红《报恩剑》)
(6)白胖小胡子看了看他,一点头道:“倒不失为快人快语,就冲朋友你这句话儿,老实说,朋友你姓错了姓,只要不是排在‘赵’、‘钱’、‘孙’后头那个字,小号对朋友你绝不是这样。”(宦海江湖《宦海江湖》)
(7)丁谓唯一可惜的就是自己姓错了姓,若是姓赵,岂不是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吗?(夏言冰《大宋之天子门生》)
(8)韦小宝肚里暗笑:“原来这小娘是个小傻瓜,沐王府的人木头木脑,果然没姓错了这个姓。”(金庸《鹿鼎记》)
(9)我抬头看看那家伙:“你谁啊?”通红一张军官证就杵到了我眼前,中尉,姓……真是想把你那姓写出来知道不?你这家伙的姓真是没姓错了!整个就是一……了算了,好歹你也是我上司,你现在还在里面熬着呢,我也就不触你霉头了,免得你带人来找我麻烦!(流浪的军刀《愤怒的子弹》)
(10)黑衣人道:“想套出老夫的话?嘿!反正你其将死,说说也是不妨,你是姓左,当老夫不知么?又与钱百锋那厮……”他话声忽然中断,左冰紧问道;“我姓左又怎么了!难道我还姓错了?”黑衣人道:“没有姓错,但你那老子左白秋嘛,嘿嘿……”(上官鼎《侠骨残肢》)
(11)“他娘的!”飞天豹脸红脖子粗:“消息上说,妙手灵官黄升平的秘窟在淮安附近,偏偏你姓黄……”“你是条猪!太爷姓黄也姓错了?”(云中岳《魔剑惊龙》)
(12)“你姓得不对。”公孙英存心呕人。“我姓又姓错了?”“姓沈的就不该吃水饭。”“什么?少庄主……”“沈又读沉,沉没的沉,你懂不懂?你姓沈的驾船,不沉船才有鬼。”(云中岳《四海鹰扬》)
(13)印象最深的是珍惜亲情,爱情的忒修斯,得到神的眷顾……所以,珍惜身边的亲人个爱人吧…姓错了。(微博)
(14)阿有便冷笑道:“你晓得你那新岳家姓甚?”戴春道:“说是姓杨,莫非姓错了?”(清·俞万春《荡寇志》第97回)
“姓错”的“错”是补语,有的后面也带宾语,如例(7)∼例(9),后面有宾语“姓”,但更多的是“姓错”后面无宾语,这些例子中的“姓”宾语悬空了。例(12)的“太爷姓黄也姓错了”,是动词拷贝句,后面也未带宾语。张宝林关于关系动词的第1条标准是说“姓”前后都要有名词,但“姓错”后面不带宾语的更多,因此,“姓”不符合这条标准。张宝林在其《汉语教学参考语法》中说到“连宾动词”,说它是“必须带宾语、宾语不能省略的动词”,例子中有“姓(王)”。这同样是不对的。
也有“姓对”,“对”也是补语。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有如下例子:
(15)我一看到郑太我就觉得我姓对了。(微博)
(16)姓胡真是姓对了宠物一只。(微博)
(17)好好吃窑子里出来的姓干姓对了。(微博)
(18)知道我脾胃不怎么好的原因了吗?(我这辈子姓对了,但我不随便赖人的。)(微博)
但“姓对”的可接受度远不如“姓错”,在“文学”“报刊”“古汉语”中都未找到例子,北京大学CCL语料库也未找到例子。
“姓”后“宾语悬空”的另一用法是“姓得R”,“得”是补语标记,“R”是补语。崔山佳在《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中举有不少例子。下面也是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中的例子,如:
(19)老主任笑起来,用力扇了两下扇子,“……长得不一般,家境不一般,连姓都姓得不一般。……”(狼小京《怨灵》)
(20)“……姓是姓——姓牛!因为姓得不大那个,很少被人提起。”(张天翼《稀松的恋爱故事》)
(21)“这只怪他姓得不好。”(张远山《通天塔》)
(22)我说:“如果叫大费叔叔和小费叔叔,你们的姓又姓得太不好!”“我们的姓怎么姓得不好了?”(琼瑶《一帘幽梦》)
(23)“……刚才查了一下,这东京都内也有两个姓由美吉的。知道?”“知道。”她说,“……姓氏姓得奇特,到一个地方往往首先查电话簿,都成了习惯,到一处查一处——由美吉、由美吉地。……”(村上春树《舞舞舞》)
(24)“……我姓冷。”姓得好!人如其姓。(凌淑芬《不肯上车的新娘》)
(25)第一个跃上心头的续集主角,当然就是那对姓得很“冷”的“兄妹”喽!(凌淑芬《俏皮小妞》)
(26)我们姓“杨”,就跟我们在肉上直插一双筷子一样,我们姓“杨”姓得很久了,久远得让我们都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了,我们这个姓的人记性好差啊!(力夫《快乐之书》)
(27)任我行道:“在下姓得不好,名字也取得不好。我既姓了个‘任’,又叫作‘我行’。……”(金庸《笑傲江湖》)
(28)“你姓得不对。”公孙英存心呕人。(云中岳《四海鹰扬》)
(29)老板站在一边说:哟,姓得再好,也在给我打工。(谢宗玉《谢宗玉文集》)
(30)我又向司徒千钟道:“司徒兄,你也不必谢我,我之所以救你,是因为你的姓姓得好,与我夫人是本家。”(昊帝残魂《梦幻倚天》)
(31)燕西笑道:“这个姓姓得好,可惜这名字太不漂亮。”(张恨水《金粉世家》)
(32)这人姓得好,名字也取得好,这么几声大喝,确有雷震之威。(金庸《鹿鼎记》)
(33)段誉道:“啊,水木清华,婉兮清扬。姓得好,名字也好。”(金庸《天龙八部》)
(34)秦日丰哈哈大笑:“姓得好,名字也好,模样儿也一流!”(林阡《南宋风烟路涉道》)
(35)唯一名不见经传,江湖明友少闻的人,只有太湖水寨派来的那氏兄弟,姓得怪,人也怪,江湖朋友从未听人说及那氏双雄其人其事,算是江湖无名之辈。(云中岳《情天炼狱》)
(36)“也要姓得成才行呀!”“怎么姓不成?胡是我的姓,我自己作主,哪个敢说一句话?”(高阳《胡雪岩-平步青云》)
(37)莫启哲松了一口气,他姓莫姓得挺好,还不想改姓,心道:“勃起支斤怎么会让我联想起世界……,我明白了,这是一种世界品牌的药,非常厉害!……”(锐利《猎国记》)
(38)李沅芷噗嗤一笑,说道:“他们姓得真好,绰号也好,可不是一对无常鬼吗?”(金庸《书剑恩仇录》)
(39)“有意思,丁一丁二,姓得简单,名字更简单,他老子大概只会数数,要是再多生两个,丁三丁四一路排下去的确省事,不必读书识字,画杠子也可以把姓名画出来。”(陈青云《怪侠古二少爷》)
(40)“你说她那个姓,不是穆桂英的穆,而是羡慕的慕,怎么姓得这么怪?……”(刘心武《钟鼓楼》)
(41)琼奶奶,好人哪,但是百家姓里真没人敢姓琼,没人敢姓得那么幸福美丽那么夸张,那么独一无二。(乔瑜《大生活》)
(42)女儿听了,一脸惊奇:“真巧哦,他跟他爸爸姓得一样,我也跟我爸爸姓得一样!”(微博)
(43)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转给等篮球打得好,不如我爹姓得好。(微博)
(44)摺我发起了一个投票,地址如果你谁能取一个万能的、霸气侧漏的、意义反转的、还震住姓得尴尬的名字?(微博)
(45)王道士道:“不瞒二爷的话,大凡道士总姓不得王,姓了王,拿起妖来便有些咬手。”(清·归锄子《红楼梦补》第47回)
以上可见,“姓”后的宾语可悬空。从标记理论看,“得”是补语标记,“姓得”后只能是补语,而不可能是宾语,比起上面“姓错”既有带宾语(即宾语不悬空),又有不带宾语(即宾语悬空)来,“宾语悬空”更彻底。“姓得R”更不符合张宝林的第1条标准。
朱德熙[18]根据组合形式的差别把汉语的述补结构分为组合式和粘合式两种,组合式述补结构中有助词“得”,而粘合式述补结构中则没有。郭继懋等[19]说,“姓错”属于朱德熙所说的粘合式述补结构,而“姓得R”属组合式述补结构。
三、“姓”后可带时态助词
“姓”作为关系动词,其后又可以带时态助词“着”“了”“过”。
关于“姓”后带“了”,崔山佳在1991年[20]和1995年[21]分别著文作了论述,并列举了现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一些例子。关于“姓”后带“过”,崔山佳在2015年出版的专著中也有过讨论。“姓”后带“着”例子少一些。与“姓+着”“姓+过”相比,以“姓+了”为最多,“姓+过”只是现当代作品才有,而“姓+了”近代汉语已有,现已与一般动作动词不相上下,而且发展势头不减。这说明“姓+了”是显性语法现象,“姓+过”也已演变为显性语法现象。下面重点讨论一下“姓+着”的语言现象。
“姓+着”在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有不少例子,如:
(1)我说有关系,因为我们上有他们的基因,流着他们的血,姓着他们的姓。(“综合”微博)
(2)他无法想象别人的儿子取代自己的儿子成天生活在一起;他不能容忍那将成天与自己生活在一起的新的“儿子”姓着别人的姓,而那姓着自己姓的真正的儿子却很可能与别一个毫不相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况且,这个姓着别个男人姓的男孩对他仿佛有着一种无名的仇视,他很难想象他们将怎样和平共处,如果这样的局面一旦发生的话。(阿待《枪惑》)
(3)温老三道:“柳花娘,只要你说一声,他会听你的,奶不让他姓温,一直姓着王,岂不是要他做一世杂种?”(东方玉《泉会侠踪》)
(4)我也很痛苦,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是我满都固勒的种子,他姓着我的姓,流着我的血。(邓一光《风从脚下过》)
(5)“我可什么也不欠他的,自幼我姓着母亲的姓。”(亦舒《喜宝》)
(6)他这女人,吃着旁人的饭,住着旁人的房子,姓着旁人的姓。(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7)除了听见同桌的人互相呼唤名字以外,他什么也没听到,只象醉鬼一样固执的私忖着,怎么有这样多的法国人姓着外国姓:又是法兰德的,又是德国的,又是犹太的,又是近东各国的,又是英国的,又是西班牙化的美国姓……(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8)李昭与胡耀邦在延安时结婚,他们有三子一女,四个孩子却姓着三个姓,两个儿子姓胡,女儿姓李,还有一个儿子姓刘。(齐鲁《胡耀邦传奇》)
(9)这个兵部尚书虽然姓着两张口,名为好问,又带一张口,对官场上的消息到处打听,固然十分灵通,对自己的业务却懒得去问。(徐兴业《金瓯缺》)
(10)脚踏中国的土地,姓着中国人的姓,叫着中国人的名字,说着中国人的汉语,用中国汉字写文章,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中国学生学中国文学,按中国人的方式和习俗生活,为什么这个陈芳明就不把自己看成是中国人,而是把中国人看成是外国人,把当时的中国政府看成是外国政府呢?(赵遐秋等《“文学台独”面面观》)
(11)郭英道:“……他们宁可把女儿逼得跳河,也不肯把女儿嫁给我,据我所知,我的子女可能还不少,只是都姓着人家的姓,管别人叫老子。”(司马紫烟《鹫与鹰》)
(12)爷爷嗓子眼儿里再次响起了小哨,用手电照着土墙上的豁口,喘着气说:“……桑园不管大小,还姓着张哩!……”(张一弓《远去的驿站》)
(13)“……利克斯,你姓着萨利埃里,你是我的弟弟,这一点始终不变,明白吗?……”(九鱼《亡灵持政》)
(14)洪过心中着实踌躇下,仔细盘算了自己个前阵子杀光的女真贵戚之中,有没有什么姓着温敦的人家,发觉没有后,又暗自握了握袖口里的短刃,这才转头看向随后下来的温敦。(血裔《宋伐》)
(15)我们姓着同样的姓氏、喜爱着同一个人、那就是缘分!(微博)
(16)当时金大老爷荐他来的时候,老爷听说是姓业,就想起这个姓字来,只有个堂班姓着这么冷僻的姓,只该做鸟居。那知安东倒有在庠朋友,也姓着这个怪姓。(清·天公《最近官场秘密史》卷13)
关于关系动词后带时态助词,笔者曾在一篇科技文献中看到下面一段话:
我们认为,关系动词一般不能带时态助词,但不排除例外,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有的关系动词可以有条件地带上时态助词。比如“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生只用一个姓;但就某一个人而言,也许会因种种原因而改姓,因而会有“从那时起他就姓了王了”“现在他还姓着王呢”“他从来就没姓过王”之类的句子。此种情况应视为例外,不能因此就认为“姓”不是关系动词,也不能因此认为关系动词可以任意带动态助词。如果一个动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带上动态助词,那就表明它有动态、涉及了时间,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关系动词了。(科技文献)
照作者的意思,“姓”虽后面可带“了”“着”“过”,但“此种情况应视为例外”。我们以为,就整个关系动词来说,说后带“了”“着”“过”是“例外”,还说得过去,但就“姓”本身来说,后面带“了”“着”“过”并不是少数,而是大量的,是常态的。
有的“姓着”前后又有其他“V着”,如上文例(4)后面有“流着”,例(6)前面有“吃着”“住着”,例(10)后面有“叫着”“说着”,例(15)后面有“喜爱着”,可以说是一种“感染”,是类推;但大量的例子是独用“姓+着”,说明“姓+着”脱离具体语言环境也是可以独立运用的。由此看来,与后带“了”“过”一样,“姓+着”也是一种常态,不应算是“例外”。
综上所述,“姓”后面可带“了”“过”“着”,我们觉得并不“新奇”,可见,“姓”虽然是关系动词,但从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来看,显然是不典型的关系动词,就其能经常带“了”“过”“着”来看,更像是一般的动词。
四、“姓”可带数量短语
关系动词的第5条标准是“不能带表示幅度或次数的数量词语”。以“姓”为例,如不能说“姓一次王”。我们认为,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但也有例外。通过语料搜集,我们发现,“姓”与“过”结合在一起,其后可带数量短语,例子还是很多的。如:
俞敦雨(1986)[22]的文章中举了如下例子。
(1)开始听了这话,我感到有点局促,鲁迅先生看出了我的窘态,就亲切地问我是不是姓唐,我告诉他这是我的真实姓名,他就哈哈地笑着对我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唐弢《琐忆》)
崔山佳的文章中也有例子,如:
(2)但阿Q也的确是姓过一回赵的,虽然未庄的赵老太爷是断断不信:“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大雪封山《都是名人之后》,2004年2月6日)
北京语言大学BBC语料库也有例子,如:
(3)但“我”同鲁迅先生初次见面,一下子还适应不了鲁迅的这种口吻,于是显出了一种紧张和窘迫来。敏感的鲁迅立刻掉转话头,亲切地问他“你真个姓唐吗?”并高兴地说他自己也姓过一回唐的。(科技文献)
(4)所以,作者虽感内疚,很想向鲁迅先生“当面致个歉意”,却又“不敢去见”。出乎意料的是当作者和鲁迅先生“不期而遇”后,先生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亲切地和他交谈,还风趣地说:“我也姓过一回唐”,还“呵呵地笑了起来”。(科技文献)
(5)这样,悲哀的祥林嫂、猥琐的闰土、迂腐的孔乙己、愚昧的华老栓、“似乎姓过一回赵”的阿Q们,经历无数次灵魂的洗涤、精神的炼狱,我们的国民素质将会有飞跃般的升华,恰似从涅中再生的凤凰,国家和民族都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技文献)
(6)至于我曾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过一回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启功: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30日)
(7)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启功: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30日)
“百度贴吧”也有“我也是姓过一回龚的”的话。“新浪博客”也有“这里有两种传说:一种是我们家曾姓过一回贺”“我的确也姓过一回游的”的话。
以上是“姓过”后带“一回”数量短语的例子。“一回”的“回”是动量词,“一回”是动量性质的数量短语,作“姓过”的补语。下面是“姓过”带其他类型的数量短语的例子。
(8)这大好中原曾经姓过刘,也曾姓杨姓李,甚至连复姓司马的人家也曾拥有过这个天下,为什么它不会姓一次程呢?(龙一《暗探》)
上例说明“姓一次X”偶尔也可说。
(9)阿仁低头答道:“……后来,又在一甄姓的汉财主家里干活儿,也跟着姓过几天儿‘甄’的,可究竟自己个儿姓什么,还真的不知道呢……”(朵拉《清殇·独宠天下》,书包网2010年2月23日)
(10)刘丽颔首笑道:“差不多罢,我妈姓胡,我也姓过几年胡的。”(孔林鸟《遁入懵懂》之七,2000年11月17日)
“几天”的“天”和“几年”的“年”都是时间量词,而时间量词一般作补语,其性质与动量词更接近。
也有后带名量词的,如:
(11)她丈夫姓了一个怪姓:党,也总给我很“党性”的感觉。(杨牧《死过一回之后》)
以上可见,“姓过”后面可带数量词作补语,虽数量不多,但却是存在的。显然,“姓”也不符合张宝林所说的第5条标准。由此也证明,“姓”不是典型的关系动词。
五、“姓”可带趋向动词“起来”
“姓”还能带趋向动词“起来”。崔山佳[23]举有如下例子:
(1)在她领导之下的一批妇女干部,为了不暴露姓氏,使敌人无法捉摸,大家都姓起李来了……(白朗《一面光荣的旗帜》)
(2)梅公子惊问道:“……为何姓起木来?”(清·隺市道人《醒风流》第9回)
崔山佳[24]277又举有2例:
(3)霍生道:“他是贾老爷女儿,怎么平白姓起郦来?”(清·澹园《燕子笺》第14回)
(4)(小生)他是王书吏,怎么又姓起胡来?(清·唐英《面缸笑》第4出)
例(1)是现代作品,例(2)∼ 例(4)是近代汉语作品,有白话小说,有戏曲。
崔山佳在《汉语语法历时与共时比较研究》中还举有33例,既有现当代作品,又有近代汉语作品,文体更多样。
下面的例子来自北京语言大学BBC语料库:
(5)白少辉心中暗暗好笑,自己一再改姓换名,如今又姓起罗来了,一面点头道:“夫人设想周到,在下自当从命。”(东方玉《九转箫》)
(6)而方形的孔与圆形的钱又可同时更多容纳与图形有关的其它社会文化观念,例如流通与稳定这种钱的基本功能、圆滑与方正这类人的社会品格、周边与中心这类位置观念正是如此,才会出现了“孔方兄”这样的钱之称谓,使得钱也随孔夫子般地姓起“孔”来,适应了儒家倡导的文化精神。(《中国平面设计三:铜钱设计》)
(7)聂燕玲感激望了他一眼,寒羞低头,抚弄着衣角,低低说道:“洗兄,谢谢你——”古沛心下一动,暗道:“怎么我倒又姓起‘洗’来了?……”(上官鼎《血海深仇》)
(8)圈子里的人噤若寒蝉,谈‘胡’色变”,以致于“文艺创作的心理也发生了奇特的变化”,许多文艺作品中的重要反面人物都姓起“胡”来,如《战斗的青春》中有胡文玉,《智取威虎山》中有胡彪(“文革”开始后一度改为“胡标”,林彪垮台后又改为“胡彪”),《沙家浜》中有胡传葵,《闪闪的红星》中有胡汉三,等等。(王彬彬《往事何堪哀》)
(9)王立宝痛哭流涕道:“……啥时候姓起‘王’来?……”(我是老小白《大风起兮云飞扬》)
(10)……借罗锅爷爷的荫凉,也跟着姓起沈来!(我是老小白《大风起兮云飞扬》)
(11)萧翎摇着头,道:“就更不对了,那北天尊者之女,乃复姓百里,单名一个冰字,怎的会姓起陆来了。”(卧龙生《金剑雕翎》)
(12)秦始皇下令全国搜捕主谋及刺客,姬公子逃亡隐匿于江苏下邳,更名改姓,从此才姓起张来。(《向张良学点什么》,《厦门晚报》2000-5-15)
(13)40年后,国有企业却纷纷改换门庭,争先恐后地姓起了“私”。
(14)空冀此时笑作一团,笑止了道:“散客兄,怎么你姓起毛来?……”(清·网珠生《人海潮》)
(15)梅小姐接来一看,暗暗惊讶道:“……名儿虽同,为何却姓起黄来?”(清·花溪逸士《岭南逸史》)
“姓”后带趋向动词又与一般动词有很大不同,它一般只能是“姓起X来”,即“起来”要拆开来,中间嵌入具体的姓氏,而一般动词有“爬起来”等说法。而且,“姓”所带的趋向动词大多是“起来”,不像一般动词有众多趋向动词。“姓”后虽也有单独带“起”的,但很少,目前只发现例(13)1例。
张伯江[25]132说,汉语动词虽然缺少形态语言中的合理性,却也不乏范畴性的外化表现形式。总结前辈关于动词“动作性”和“时间性”特征的相关结论,把汉语动词的范畴性等级描述如下:
高范畴性形式:
a.带时体标记“了”“过”等
b.带趋向补语“起来”“下去”“上来”等
c.动词重叠
中范畴性形式:
d.带动量成分“一下”“一回”“两眼”等
e.带结果补语
f.带有指的宾语名词
低范畴性形式:
g.带无指的宾语名词
h.无界动词
i.动名词形式,即可受“N的”修饰根据上面“高范畴性形式”中的3点,“姓”符合“a”种、“b”种2点,“中范畴性形式”中的3点,“姓”符合“d”种、“e”种 2点。也就是说,“姓”既符合“高范畴性形式”中的三分之二项,也符合“中范畴性形式”中的三分之二项,确实较特殊。
六、“姓”的“示姓(性)”用法
“姓”还有“示姓(性)”,后面所带宾语不是具体的一个个“姓”,而是其他名词。从语法角度来看,“姓”作为动词的搭配对象是超常搭配,就修辞角度来看,是一种修辞格。如改革开放初期的“姓资”“姓无”的争议,现在的“党媒姓党”等,用的是“示姓(性)”。“示姓(性)”有给人或事物拟一个姓氏,以突出他(它)们的性质、特点或归属,并收到“姓”字本义之外多种修辞义的效果。最早研究“示姓”的文章有谭永祥[26]、林文金[27]、唐松波等[28],以后又有崔山佳[29]、王志生[30]、段忠林[31]、杨春霖等[32]、黄建霖[33]、张开勤等[34]、傅惠钧[35]、吕福中[36]、谭学纯[37]等。这些学者大多认为“示姓(性)”是“新兴”辞格。谭永祥[38]31、谭学纯等把它称作“拟姓”。如:
(1)政府工作人员姓“清贫”。(《北京晚报》1988年12月23日)
(2)杂文姓杂。(夏衍《杂文三忌》)
(3)苦恼之一:现在当校长既要姓“教”,又要姓“钱”,没钱校长生活在愁城里。(《光明日报》1988年8月28日)
唐松波等在“示姓(性)”条中举有3条民歌,如:
(4)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有人来捉我,除非是神仙。
(5)太阳落西又出来,水打船移岸不运;站起撂倒不改姓,老子祖辈都姓红。
(6)老子本姓强,住在巴山上,要我不革命,西方出太阳。
上面3例均选自《川陕苏区红色歌谣选》,虽不知其确切时间,但出自解放前却是无疑的。
“示姓(性)”这一修辞格最早产生于何时,崔山佳通过查阅古代文献对此作出了推论。1993年,崔山佳在明清小说《醒世姻缘传》和《西游记》中发现了“示姓”的使用案例。[29]到2008年,又分别在南宋、唐代乃至隋初的文献中发现了“示姓”的用例。至此,将“示姓”的产生时间最早推到了隋唐时期。下面是这些文献中的用例情况。
(7)主曰:“恁么则姓韩也。”师闻乃曰:“得恁么不识好恶!若是夏时对他,便是姓热。”(《五灯会元》卷5)
(8)上堂,举:“李刺史问药山:‘何姓?’山曰:‘正是时。’李罔测。乃问院主:‘某甲适来问长老何姓,答道正是时,的当是姓甚么?’主曰:‘只是姓韩。’山闻曰:‘若六月对他,便道姓热也。’”(《五灯会元》卷14)
例(7)“夏时对他”的“夏时”,是对“韩”的谐音“寒”来说的,“姓韩”就是“姓寒”。正因此,才有“若是夏时对他,便是姓热”,“姓热”是“示姓”。例(8)有“若六月对他,便道姓热也”,“姓热”也是“示姓”。
(9)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长老底秤。”泉喝曰:“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五灯会元》卷17)
上例有“秤天下长老底秤”,故“姓秤”也是“示姓”。
(10)(末)三打不回头,状元那里人?姓甚名谁?(净)姓成,名都府。(末)住在那里?(净)住在张州协县。(末)你胡说!莫是成都府人,姓张名协?(《张协状元》第28出)
虽“成”是姓,但上面与“都府”连起来看,是“成都府”,他是“成都府”人,“成”也是“示姓”。
文言作品也有,如:
(11)县令妇姓伍也。他日,会诸官之妇。既相见,县令妇问赞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陆。次问主簿夫人何姓,答曰姓漆。县令妇勃然入内,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县令闻之遽入,问其妇,妇曰:“赞府妇云姓陆,主簿妇云姓漆,以吾姓伍,故相弄耳。余官妇赖吾不问,必曰姓八、姓九。”县令大笑曰:“人各有姓,何如此?”复令其妇出。(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10)
《封氏闻见记》是唐代笔记小说。“伍”“陆”“漆”都是姓,但“八”“九”虽是姓(《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39]都收有“姓”的义项),但这里却不是姓,而是“仿词”兼“示姓”:伍/五→陆/六→漆/七→八→九,都是数字,“姓伍”“姓陆”“姓柒”“姓八”“姓九”都是“示姓”。
据目前所掌握材料来看,《启颜录》已有,如:
(12)动筩后来问博士曰:“先生,天有何姓?”博士曰:“天姓高。”动筩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学他蜀臣秦密,本非新义。正经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须假托旧事。”博士云:“不知何经之上得有天姓?”动筩云:“先生全不读书,《孝经》亦似不见,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见《孝经》云:‘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岂不是天姓?”高祖大笑。(《论难》)
(13)隋朝有一人姓马,一人姓王,二人尝聚宴谈笑。姓马者遂嘲王字曰:“王是你,元来本姓二,为你漫走来,将丁钉你鼻。”姓王者即嘲马字曰:“马是你,元来本姓匡,拗你尾子东北出,背上负王郎。”遂一时大笑。(《嘲诮》)
例(12)的“高”确实是姓,但“姓高”的“高”是“高处”义,也应是“示姓”。至于“姓也”,那完全是“示姓”,因它是“性也”的谐音。例(13)的“二”也是姓,唐代有一姓名叫“二从直”的,为唐玄宗宫中中尉,但这里是针对“王”来说,也应是“示姓”。“匡”也是姓,但这里的“匡”是针对繁体的“馬”来说,也应是“示姓”。
《启颜录》多半为隋初侯白草创,后人续加增益,比《封氏闻见记》要早,比南宋的《五灯会元》《张协状元》更要早得多。可见,“示姓”至迟在唐代已产生。
古代的“示姓”大多有幽默风趣的特点,有的就是插科打诨,显示了对话者的聪明、敏捷,有脑筋急转变的思维敏捷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丝毫不逊于东方朔。
“示姓”的“姓”其搭配功能大大提高,搭配对象不但是具体的“姓”,也可以是一般名词,甚至是抽象名词。这就使其与一般的关系动词或是典型的关系动词有很大不同,而与一般动词接近,甚至其搭配能力超过一些一般动词。
七、结语
从上面的众多例子来看,“姓”虽是关系动词,但从范畴理论来看,“姓”不是典型的关系动词,因从“宾语悬空”和能后带“了”“过”“着”,“姓过”能后带“一回”,“姓”能带“一次”来看,有一般动词的特点。特别是后带“了”和“过”的高额使用情况,就绝对不是“例外”。沈家煊认为,既然语言的范畴是非离散的,边界是模糊的,语言成分不是绝对的属于或不属于某个范畴,而是在属于某个范畴的典型性程度上形成一个连续体,语言的规律也就不可能是绝对的,只能体现为一种概率或倾向性。[10]17他认为,一个词类的确定是凭一些自然聚合在一起的特征,但它们并不是什么必要和充分条件。一个词类的典型成员具备这些特征的全部或大部分,非典型成员只具备这些特征的一小部分。因此词类的边界不是明确的而是模糊的,词类和词类之间不是离散的而是连续的,对词有定类这句话的理解不能绝对化。[10]282所以,范畴的各个成员其地位不是均等的,完全具备这一束特征的是典型的成员,只具备其中一部分特征的是程度不等的非典型成员。[10]349宗守云[40]43说,范畴成员是异质的、复杂的。同一范畴内的成员,地位是不平等的,有的很典型,有的比较典型,有的不典型,因此情形是复杂的。吴为善[41]35-36说,综合 Rosch、Lakoff、Taylor以及 Ungerer&Schmid的论述,原型理论具有四个基本要点,其中第二点是:自然类各成员地位并不平等,其中有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的区别,典型与非典型形成一个非离散性的连续统。最典型的成员最具有原型性(prototypicality),与较差、最差的成员之间,可有等级差异。第三点是:范畴中原型性更高的成员具有更多的与同类其他成员共有的属性,并具有更少的与相邻类别的成员共有的属性;也就是说原型成员最大限度地区别于其他范畴的原型成员。而非原型成员(或曰边缘成员)则相反,它们与其他成员共有的属性较少,而与相邻范畴共有一些属性。因此,自然类的往往是模糊的,相邻范畴常常不是由严格的边界截然分开,其边缘成员往往互相渗透、交叉。
上述说法正可用于“姓”,“姓”虽是关系动词,却是很不典型的关系动词,它与其他关系动词的共性相对较少,而与一般动词倒有不少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