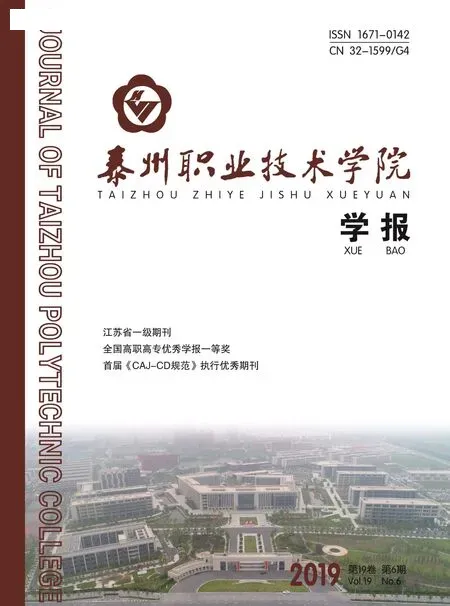债权人与债务人配偶权利平衡论
凌 晨,吴千里
(1.泰州学院;2.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主体,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号召全民创业、大众创新,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催生了大量的市场主体。作为金融主体的银行鉴于保障资金安全的考虑,在接受市场主体的融资申请时会提出相对严苛的条件,导致有些私企和个体工商户融资难。与此同时百姓为了追求资产的保值增值,将自有资金投放给中小企业市场主体成为一种正常现象。但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制约,大量债务纠纷频发。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成为我国基层法院的重要工作内容。诉讼中,债权人往往诉请债务人夫妻共同偿还借款。但很多债务人配偶之前并不知晓债务存在,坚持以不知情或没有用到这笔钱作为抗辩理由,拒绝还款。两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债权人权益和债务人配偶权益保护的失衡,成为争议的关键,也是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1 权利失衡的根源
1.1 资本的逐利性
投资强调回报,将资金借给需要的企业或个人成为债权人的重要选项。为规范引导民间借贷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年息在24%及以下为合法利益,在24%至36%之间为自然利息,双方意思自治,法律不干涉。但超过36%部分构成暴利,法律不予支持。逐利是资本的天性,也是资本在社会各行业不断流动的内在动力,是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驱动,但资本的运行如失去法律的制约,将成为洪水猛兽。因此在发挥民间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必须约束抑制其不良因素。多年前,中小企业甚多的浙江省产生“P2P”、小额贷款公司等融资模式,国家一度予以鼓励,但因为资金管理环节、债务催讨环节存在严重问题,在当下扫黑除恶中逐步销声匿迹。这充分说明,民间资本的追逐利润必须受到严格监管,否则再好的融资模式也是昙花一现。
1.2 法律保护价值的选择
在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保护价值选择上,法律侧重保护债权人,以维护交易安全,鼓励债权人将自有资金投放市场,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夫妻在离婚时应当共同偿还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这确定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基本原则。但在实践中还有很多争议,因为共同生活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为了共同生活的需要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另外一种是在夫妻共同生活居住期间产生的债务,尤其是以一方名义举债产生的债务。我国经济在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各种民间借贷大量发生,司法实践中存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需要进行规范,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 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 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债权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债务人配偶可以在两个方面积极举证,以免除自己的还款责任。一是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二是能够证明该债务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三款规定情形。
1.3 社会信用体系的破坏
市场经济发展使交易不再局限于熟人之间,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使陌生人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多。但市场主体法治意识淡薄,社会诚信体系遭到破坏,“假离婚,真逃债”等恶意逃债行为不断产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2008 年我国遭遇金融危机,国家为拉动经济,鼓励民企扩大生产规模,各种小额贷款和各类担保公司应运而生,但此类贷款行为非常不规范,出现职业放贷人,发生暴力逃债和套路贷等各种行为,导致债务人配偶一方被大量举债,社会矛盾丛生。2018~2020年,中央在全国范围开展涉黑涉恶专项治理,2019年10月21日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国家四部门将两年内向不特定主体发放贷款超过10次的职业放贷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罪,堪称史上对民间借贷行为的最严规制,高利贷等职业放贷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2 债务人配偶权利分析
从民间借贷角度,债务人配偶权利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是外部权利抗辩,其应当享有与债务人共同的抗辩权,主要有借贷资金是否实际给付,利息是否约定清楚,是否存在套路贷、债权人是否存在虚假诉讼等针对债权本身的抗辩。这种权利抗辩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是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的,配偶的抗辩程度与债务人一致,或基本不作抗辩。另一种是夫妻感情不和,债务发生在两者分居时期,债务人配偶一般聘请律师代理作积极抗辩,不愿承担任何责任。即使判决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也认为其合法利益受损,依然上诉和上访。
第二是来自于夫妻之间的内部抗辩权。主要是借贷对象的选择权、借贷知情权和借贷规模决定权。由于借贷关系属于特殊的资金关系,在涉及民间借贷时,债务人选择空间很小,能获得贷款保证债务人企业正常运转符合债务人夫妻的目的和利益。但对于债务人将借款用于赌博、婚外情以及其他高利贷的行为,要求债务人配偶承担高利贷或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违反社会公平正义,同时实体经济的合理利润无法长期支付高息,所以债务人配偶积极行使这种抗辩权,往往有较好的效果。有人认为债务人配偶没有参与举债,事后支付利息的行为属于侵犯配偶的知情权,并认为法院对于事后追认的扩大解读[1],事实上实现了从配偶的“同意”向配偶的“简单知情”的过渡。但笔者认为,即使其在债务形成前不知晓,但债务人配偶支付利息构成追认,符合合同法的要求。因为债务人配偶既然向债权人通过银行转账或有证人证明其向债权人以现金方式支付借贷利息的,该债务就应当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是否为共同生活所需,已不重要。
3 债权人与债务人配偶权利的调整
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法律规范需要适应当前的婚姻家庭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在民间借贷规模化背景下,债权人利益过度保护,导致债务人配偶权利受损,已经引起社会治安事件,频频冲击社会稳定。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调整已经具备客观基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婚姻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和订立合同的基本要求,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所负的债务。从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角度,夫妻双方共债共签是基本原则。夫妻一方事后以包括通过电话、手机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各种形式予以追认,符合合同法意思表示一致规则。此项规定既充分反映合同法律确定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成立的交易规则[2],同时对夫妻之间特殊身份关系给予了肯定。且也提示债权人即使债务形成时由于各种因素不能做到共债共签,但只要能在债务形成以后取得债务人配偶各种形式的认可,该债务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存在特殊身份联系,司法解释强调夫妻共同债务形成时的“共债共签”原则,实际为民事商事主体确定了新的民间借贷行为规范,要求债权人加强风险防范。这样既可以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可能防止夫妻一方“被负债”情况发生,也可以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对于保障交易安全和债务人配偶合法权益,都具有实践意义。
4 债权人与债务人配偶权利的平衡及再构
我国民法典正在编撰过程中,我们需要借此机会协调处理债权人、债务人和其配偶的三者利益,以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最高法院【2018】2号司法解释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通过分配举证责任,将债务人配偶一方的利益进行充分保护[3]。
但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在适用该条款时,为避免二审改判,采用最严格审查标准,要求债权人必须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明,而2018 年1 月之前发生的民间借贷行为,很多债权人无法做到让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债共签,也很难充分举证,故往往判决由债务人个人承担责任,引发债权人不满,认为在债务形成时,法律无此规定,最高法院新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帮助了明知或应当知晓债务方式且举债对其有益的债务人配偶逃避债务。这条规定能引导债权人在债务形成时尽到充分的谨慎注意义务,但这将增加民间借贷成本,降低经济活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民间借贷的发生,导致民间资本不能通过民间借贷形式进入社会生产经营的各个领域。因此笔者建议在司法解释确定规则的前提下,应当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清偿范围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坚持公平与效率结合原则,以平衡各方经济利益。
首先共债共签为民间借贷发生之基本原则,同时有事后追认意思表示或共同还款行为的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此两种情形应由夫妻共同偿还债务,偿还责任财产包括夫妻个人财产和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以及将来取得的全部财产,以确保债权人利益最大化。
其次,在债权人只能证明债务人配偶知情或应当知情,且该笔债务并没有用于违法行为,债务人配偶可以直接或间接受益该债务的,法律应当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配偶两者并重。即应以债务人个人全部财产和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为限承担责任,不包括债务人配偶婚前个人财产和夫妻离婚后的个人财产。
最后,如果债务人配偶举证其对该债务毫不知晓,且根本不可能基于家庭共同生活受益,债权人在债务形成时可以通知债务人配偶而不告知,则应判决此债务为债务人个人债务,由债务人个人偿还。
综上,民间借贷关系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家庭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我们应当加强对此方面研究,以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