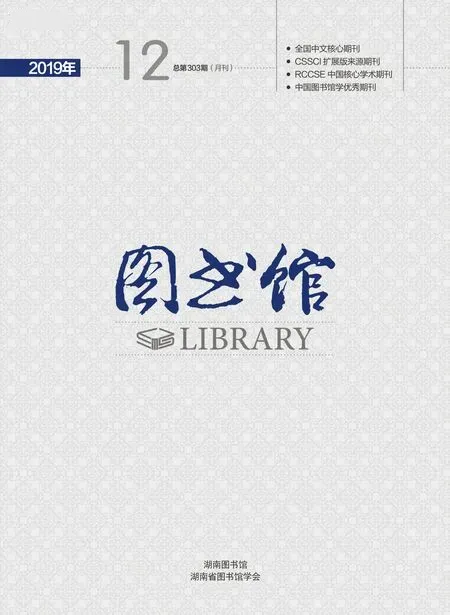敏感主题口述史不可回避的伦理与司法冲突
蔡 屏
(华东政法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0042)
笔者于2018年6月25日在中国知网共检索出1 718篇与口述史相关的文章,就检索结果来看,文章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口述史工作流程、地方特色口述史建设以及口述史伦理等领域,而涉及敏感主题口述史(以下简称敏感口述史)以及口述史伦理与司法冲突的研究几乎没有。笔者认为,敏感口述史是口述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其内容敏感,且往往与受访者的隐私密切相关等原因,使得隐私保护的程度与范围成为引发口述史伦理与司法冲突的主要导火索。如何在口述史伦理与司法证据采信之间寻求平衡点、建立口述史伦理行为规范、制定相关的口述史法规等,是我国业界工作者在未来需要着重关注与研究的课题,以促进我国口述史全面、健康发展。
文章在详细阐述轰动全世界的“麦康维尔谋杀案(Murder of Jean McConville)”的司法取证过程,以及因该司法取证过程而引发的全球图书馆界、档案界和口述史界大讨论的“波士顿学院口述史贝尔法斯特项目(Boston College Oral History Belfast Project,简称BP)”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同一个事件站在双方不同的立场而引发的矛盾冲突之症结,并由此提出了敏感口述史在未来建设过程中需注重两个方面内容的考量:①重新定义“知情同意”伦理道德要素;②在特定情况下,法律需适当考虑个人利益优先原则,应优先保护受访者隐私等建议。
1 事件冲突回顾
1.1 “麦康维尔谋杀案”司法取证
英国北爱尔兰警方指控原爱尔兰共和军政治翼领导人、爱尔兰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涉嫌于1972年12月下令杀害一名有10个孩子的“英国女间谍”——琼·麦康维尔并秘密埋葬她,但亚当斯极力否认该指控。因警方对其犯罪行为所掌握的证据不足,只能任由他逍遥法外。某爱尔兰共和军问题研究专家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除非格里·亚当斯自己崩溃并认罪,亲口说‘是我干的’,否则我认为他们(北爱尔兰警方)不大可能有办法起诉他。”
时隔数年,北爱尔兰警方终于在2010年找到了司法取证突破口。警方发现在英国和爱尔兰电视台均播出了由美国波士顿学院主持开展的原爱尔兰共和军口述史(即贝尔法斯特项目)中的两份已逝受访者的录音,其中一位受访者休斯曾是亚当斯的亲信,在录音中他提到:“下令处死那个女人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现在是新芬党党首(即格里·亚当斯)。我没有下令处死那个女人。他下的令。根据命令,我带领一支行动队‘逮捕’了麦康维尔,而她的命运则由亚当斯与后来接替他出任爱尔兰共和军驻贝尔法斯特指挥官的艾弗·贝尔之间的政策争论决定。贝尔主张把麦康维尔的尸体公之于众,以警告那些可能考虑帮助英国政府的人,而亚当斯要求保守杀死麦康维尔的秘密。麦康维尔的尸体最终被秘密埋葬。”
北爱尔兰警方认为该两份录音均可作为指控格里·亚当斯下令谋杀琼·麦康维尔的犯罪证据。通过英美双方的司法互助协议,美国联邦检察官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协助英国官方获取绑架与谋杀麦康维尔信息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该法院于2011年5月和8月先后两次向波士顿学院伯恩斯图书馆(Burns Library)发出了传票,要求贝尔法斯特项目组交出所有涉案的原共和军录音。针对法院传票,波士顿学院、口述史界、图书馆界、档案界等均表达了强烈反对的意见。在提交给法院的辩词中,波士顿学院强调了保守口述史秘密的重要性不仅仅出于简单维护学院本身的利益,更是出于保护受访者的自身安全。但根据美国联邦证据法案规定,所有涉案相关证据都可以被采纳。这意味着在美国只要与案件相关的信息都可以进入审判程序[1]。经过一场在美国历时两年的官司后,北爱尔兰警方最终通过司法途径如愿从波士顿学院获得与该案件相关的所有录音带。
根据这些录音,尤其是贝尔本人的录音,北爱尔兰警方逮捕了贝尔并以涉嫌帮助杀死麦康维尔为由起诉他。因为贝尔还活着,他的录音成为指控亚当斯的有力证据[2]。
1.2 波士顿学院口述史—贝尔法斯特项目(BP)
贝尔法斯特项目是由爱尔兰共和军前成员安东尼·麦金太尔(Anthony McIntyre)和记者埃德·莫洛尼发起,由美国波士顿学院主持开展并采集爱尔兰共和军原成员口述史的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口述历史访谈来记录和保存那些参与长达30年的北爱尔兰冲突双方(共和派和忠诚派准军事组织)前军事成员的故事与经历[3],其中包括了大量暗杀、阴谋、控告等内容。这些内容事关受访者的隐私和安危,甚至会危及他人。但该项目之所以能顺利开展,关键取决于两大要素即受访者给予项目组的充分信任和项目组给予受访者隐私安全保护的承诺。为使受访者足够信任项目组,项目组在采访前与受访者分别签订了具有知情同意性质的协议书,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限制条件为:采访录音必须在受访者授权同意或在其离世后才能公布;对口述史访谈材料须秘密保存,以便保护受访者的人身和隐私安全等。
该项目从2001年开始启动至2006年结束,历时6年。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参与该项目的两位受访者相继离世,根据知情同意协议书的规定,这两位已逝受访者的口述史访谈资料可以对外公开。鉴于此,该项目发起人莫洛尼在他的著作《坟墓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Grave)中摘录了这两位受访者的访谈录音内容,且于第二年被翻拍成纪录片;随后又有一位参与BP项目的受访者多勒·普莱斯(Dolours Price),违反其所签署的协议,向某报纸透露了相关采访信息[4]。上述两个行为将BP项目推向了风口浪尖之上,不仅使该项目中与琼·麦康维尔谋杀案件相关的所有访谈资料成为了司法证据,而且也严重影响了未离世受访者的人身安全,重创了项目组与受访者之间来之不易的信任。
2 事件分析
上述事件是美国现代口述史学有史以来有关法律与伦理相冲突影响最为深远的司法事件。笔者将从伦理角度和司法角度对该事件进行深入剖析,从而重新认识口述史在实践中所应遵循的伦理规范——“知情同意”和法律意义上的隐私权、司法证据采信等问题。
2.1 理论要素分析
上述两事件的关键点主要在于口述史伦理规范——知情同意、隐私保护以及口述史访谈资料是否具有司法取证豁免权等。笔者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详细分析与论述。
2.1.1 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属于伦理规范的范畴。伦理规范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5]。因口述史的采访对象是具体的“人”,需要采访者融入到受访者的生活经历和情感历程中,以期获取其行为背后的历史意义,因此采访互动关系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6]。
美国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简称OHA)专门针对口述史实践制定了《口述历史的原则和最优实践》(Principles for Oral History and Best Practices for Oral History)等伦理规范[7]。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规范原则即是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起源于医疗领域,涉及医患之间相关信息的获取与分享,与患者“知”的权利相关,它影响着患者对治疗方案的判断,是对弱势患者的一种保护。随着时代的发展,“知情同意”不再局限于医疗领域,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行业,知情同意就会发挥它保护信息不对称中的弱势一方的权益,如:食品安全、互联网征信等领域。
知情同意在口述史中的重要性。敏感口述史一般涉及的是受访者的隐私或不宜公开的事件信息,因此在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口述史专业领域方面,作为采访者而言,他属于信息不对称中的强势一方,因此,他需向受访者告知因采访引起的可能对其不利的一切影响因素;在采访内容方面,作为受访者而言,他属于信息不对称中的强势一方,是采访内容的亲历者或见证者,因此,他需以谨慎的态度,客观、公正、如实地对待采访内容。因此,“知情同意”在确保敏感口述史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上显得尤为重要。
知情同意在口述史中的特殊性。知情同意一般以书面协议形式呈现。信息不对称的弱势一方根据知情同意书所述内容,来决定是否同意另一方的行为。若弱势一方在协议书上签字,则表明在法律意义上,信息弱势一方是知道协议所呈现的内容并予以接受的(常见于医疗术前协议书)。
在口述史的实践中,知情同意一般也是以协议书的方式呈现。采访者在遵守“行为善意”的原则基础上,和受访者进行连续的、相互作用的平等对话沟通,充分体现对受访者的尊重,这不仅需要尊重受访者的人格,以平等主体对待,而且要尊重受访者的自主选择权,如有权终止采访的权利、尊重受访者的隐私权,根据他们的意愿选择公开、有条件的公开或完全不公开、尊重他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等[8]。
但笔者认为,对于敏感口述史而言,这种知情同意模式还不足以保护受访者,它只是遵循知情同意伦理规范的起点。真正意义上的知情同意不能仅止步于口述史项目准备阶段协议书的签字上,而更应该贯穿于整个采访过程以及口述史资料的使用过程,需长期承担告知的义务和隐私保护义务。
2.1.2 隐私与隐私权保护
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公开或被他人知悉的秘密,隐私的内容包括个人的健康状况、生理缺陷和残疾、婚恋纠纷、财产状况、私人日记、信函、生活习惯、丑闻或劣迹、销售伪劣产品、特殊的社会关系、领导行踪、对敏感问题的看法等。隐私权就是公民享有的不愿公开的个人生活秘密和个人生活自由的人格权利,是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活动[9]。很多国家都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出台了相关政策,如英国1998年《数据保护法》界定了受特殊保护的“敏感个人数据”、美国和欧盟出台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等。
2.1.3 视听资料在司法证据采信中的界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八种形式的证据,其中第四项是“视听资料”,即录音录像资料证据,所以它是法律允许的证据形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规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该条款对视听资料做了明确的限制,要求必须是以合法手段取得、有其他证据佐证且无疑点。只要满足上述三个要求,视听资料就能被法院或检察院采信。
2.2 事件冲突要素分析
在对上述事件所涉及的理论要素进行解释以及明确其对敏感口述史的作用后,笔者根据这些要素来具体分析它们在事件中如何引发了伦理与司法冲突。
2.2.1 个人隐私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
纵观整个事件,其冲突本质实为利益冲突,是个人隐私保护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冲突。对于BP项目而言,对受访者的隐私保护及人身安全的承诺,这属于个人隐私利益范畴;对于英国法院而言,追查谋杀麦康维尔女士的嫌疑犯是其责任,属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范畴。虽然各国都有隐私权保护的专门法律,但都规定了例外,即这些法条不适用于:公共安全、国家安全、国家在刑法领域的活动中所涉及的个人数据[10]。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成为隐私权保护中的一个正当抗辩事由。在现实中,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法律准许使用他人的肖像,准许将他人的个人信息和活动公之于众(因为法律上的隐私是指与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密,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就不再是法律保护的范围)[11]。
简言之,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将无条件让位于公共利益。这就是英国法院可以依法不予保护BP项目与受访者签订的知情同意协议书,坚决要求BP项目组交出与该案相关的26人录音的法律依据。
2.2.2 口述史资料与司法证据采信冲突
敏感口述史资料是在平等主体之间相互信任的条件下,由受访者叙述,采访者通过数字技术记录并于后期将谈话内容转换成文字,在征得受访者对文字内容认可的情况下而形成的一种访谈资料,如实反映了受访者所述内容与观点。
能被法院采信的证据只需满足三个条件即可,即通过合法的手段收集到的且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的无疑点证据,其形式包括视听资料。
对于上述案件而言,BP项目中有26人分别对麦康维尔谋杀事件进行了详述,这些口述史资料不仅是通过合法手段加以采集的、无疑点的采访资料,且各个受访者所述内容也可以相互佐证,这完全符合法院对证据采信的要求。
法院在认定有值得采信的证据存在时,它可以利用隐私权保护的例外条例即保护公共利益的抗辩理由收集证据,拥有证据的单位或个人则必须无条件配合,予以支持,这正是文章所述两个案件中所呈现出来的双方所持立场冲突之所在。即使BP项目组提出了保护受访者人身安全、维护波士顿学院名誉,甚至重创口述史的发展等理由,但这都无法抗衡法律的核心宗旨——保护公众利益,最终不得不交出这26人的口述史资料。
2.2.3 口述史的知情同意与隐私保护冲突
知情同意是对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界定,即知情权和同意权。知情权即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方有向弱势方告知的义务;同意权则指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有权根据告知内容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在现阶段,一般在行为实施前以书面协议和签字的形式来确认是否进行了“知情同意”流程。但是,对于敏感口述史来说,笔者认为这远远不够,知情同意必须贯穿整个过程的始末。
在上述案件中,正是因为莫洛尼公开发布了两份已故受访者的采访内容,才引发了传票案。莫洛尼公开发布这两位已故受访者口述史资料的行为本身并没有违反受访者与项目组在采访前所签订的知情同意协议内容。但是由于公布的这两份采访资料与其他24位受访者均是围绕“参与秘密谋杀麦康维尔行动”而展开的,可见,他们的受访内容之间存在着密切相关性,这也就意味着,公布了这两位离世老兵的口述史资料其实也是变相地公布了其他24位老兵的口述史资料及其隐私,这无疑侵犯了其他受访者的隐私保护权利。笔者认为,莫洛尼在公布这两份口述史资料之前,须履行告知其他24位老兵的义务,并需征得所有老兵的同意,才可以公布,即在受访过程结束后,项目组仍须保护24位老兵的知情同意权。如果其中任何一位老兵表达了不同意,则该2份口述史资料均不得公开,即使这2份口述史资料公布条件符合当事人签订的条约内容。假如莫洛尼遵循了这样的知情同意保护要求的话,所有参与该项目的老兵们就不会遭受隐私权的侵犯,传票案也不会发生,更不会对图书馆界、档案界和口述史界产生如此大的破坏力,将口述史推入有史以来最困难的境地。
3 思考与建议
经过对上述案例的详细分析,我们充分认识到了影响敏感口述史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在国法之下,制订有利于行业发展的伦理规范。在我国,存在涉及与敏感口述史相关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尚未建立全国性口述史管理机构及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化制度、人民法律意识普遍淡薄、缺乏独立思想和平等精神[12]等现实状况,因此,我国敏感口述史的发展道路就显得尤为波折。这就要求业界需深入分析与总结国外口述史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及经验,极力促进我国敏感口述史的顺利发展。通过对美国口述史发展的研究和上述两个案例的分析,笔者对我国敏感口述史工作的开展,有以下几点建议:
3.1 建立全国性口述史管理机构
美国1967年成立了口述历史协会(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简称OHA),这标志着美国口述史领域有了一个行业统领,为美国的口述史研究机构提供了一个便捷的沟通、交流平台。OHA担负起了对口述史行业一系列行业标准和规范制定者的角色,如1979年出台的《口述历史评估指南》(Evaluation Guidelines),在经过1989年和2000年两次修订后[13]于2009年10月最终修订为《口述历史的原则和最优实践》(Principles for Oral History and Best Practices for Oral History)[7]。为美国的口述历史从业者提供了原则和标准参照与制约,同时,为了促进口述史行业发展,制定了多种形式的奖项激励措施。
而我国尚无全国性的专业性强的口述史管理机构,因而口述史的研究与实践缺乏行业规范与标准,不能为口述史的从业者提供沟通与交流的平台,无法代表口述史界对外行使本行业的自身权益。所以,笔者认为,我国需要尽快建立口述史管理机构,以保证口述史的长期发展。
3.2 建立口述史伦理规范制度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一个组织内的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它具有指导性和约束性、鞭策性和激励性、规范性和程序性。无论何种行业,都需要有与其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口述史领域同样需要。
3.2.1 项目实践流程需法律化和规范化
BP项目引起最大争议的问题是波士顿学院在计划阶段没有征求必要的法律建议,在实践阶段没有严格进行伦理审查和监管。
法律具有至上权威,其核心价值是更好地保证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因此,任何人都需无条件遵守法律规则,需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从事活动。当法律规则与社会主流价值产生冲突时,为了维护和尊重法律的权威性,我们必须服从法律[14]。因此,在开展敏感口述史工作之前,需就采访主题可能会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向专业法律人士咨询,获取法律建议,并在工作要求中得以体现,从而避免其后续实践行为与法律相冲突;在开展敏感口述史实践过程中,需高度重视伦理审查和监督程序且需贯穿整个过程。实施伦理审查和监督的目的有二:一是使受访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二是确保敏感口述史实践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3.2.2 建立匿名制度
在新闻行业,为了保护消息来源的隐私和安全,在发布新闻时都会隐去与该新闻有关的个人信息,这已成为世界媒体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因为当记者在调查一些不法现象时,只有保护消息来源,保证消息源的人身安全,才能够取得消息来源的信任。如果他们透露消息来源,将失去提供消息者的信任,从而损害整个新闻事业[15]。
由于敏感口述史私密性极高,不宜对外公开,其内容都是经过采访者不断努力,持续经营与受访者的联系,取得受访者足够信任,并在得到采访者“不对外公布与其个人相关信息”的承诺后,敏感口述史才有可能得以实践。但是,口述史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用于相关领域的研究。因此,敏感口述史资料也无法完全避免不为他人研究所用。
笔者认为,敏感口述史可以借鉴新闻行业保护信息来源的道德规范,建立匿名制度。只记录受访者的口述事件,而隐去与其相关的个人信息,如姓名、地址、籍贯、年龄等等。如果由于采访方单方面违反匿名规定而给受访方造成伤害或损失,法院可以责成采访方给予相应的补偿。
3.2.3 建立永久性的知情同意机制
笔者认为,在敏感口述史的实践活动中,知情同意不能仅仅停留在项目预备阶段,仅以“签字”作为保障受访者知情同意的最终结果。高度私密性决定了隐私权保护成为敏感口述史得以顺利发展的首要因素。即使项目开展之前双方采取以在知情同意书上的“签字”作为“告知”与“同意”的确认,但这也不能成为知情同意的终点。采访项目组能保证在采访过程中不会泄露受访者隐私和采访内容,但这无法确保采访结束后,当采访信息转录成文字,成为口述史资料之后,因各种无法预测的因素而不得不公开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建立永久性的知情同意机制,要求口述史项目组无论是在准备阶段、实践阶段还是资料保存阶段,均需承担“知情同意”责任,一旦出现与之相关情况时,均需及时告知受访者以及与内容有联系的其他受访者,只有在征得受访者们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利用受访者的口述资料。项目组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知情同意机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侵犯隐私权的风险。
3.3 制定隐私权保护的专门法
“有法可依”是我国发展口述史的必经之路。在我国,因为没有专门法的保障,很多有故事的人不敢参与口述史,更别提参与涉及敏感主题的口述史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情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也就是说我国法律规定任何公民都有作证的义务。一旦敏感主题口述史资料为司法所需时,受访者必须承担作证的义务,这完全违背了受访者在受访前要求保护其隐私的意愿。
虽然我国在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和进展,但相关法律分布比较零散,没有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一些重要的部门法,尤其是民法,未能全面正确地贯彻宪法中保护公民隐私的原则性规定,而且我国尚未制定一部包括隐私保护在内的个人信息保护法[16]。
因此,为了促进我国口述史特别是敏感口述史的发展,需要加快制订保护公民隐私权的专门法,正如王利明教授所建议的,我国应该制定一部《人格权法》,在其中设立专门的章节对隐私权进行完整的制度性规定[17]。笔者认为,在制定专门法时也需适当体现个人利益优先原则,比如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对当事人的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在司法公开与个人隐私产生冲突时,应倾向于对当事人个人的隐私尊重与保护,尊重他们的意志与人格,保障其隐私权。
3.4 口述史教育系统化
行业能得以持续发展离不开专业人才的培养。虽然自2000年以来,我国口述史有了很大发展,但支持其长足发展的有生力量即人才,却未受到足够重视。虽然在高校,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于1996年开设了“口述史学研究”课程,被认为是中国高校认可口述历史成为研究学科的里程碑[18],但后继者寥寥,特别是初、中等教育中,有关口述教育的教学实践尤为缺失。
笔者认为,为促进我国口述史的健康发展,需在全国教育系统中推进口述教育,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开设与该区域历史、文化、人文等相关的、具有该地一定特色的口述教育课程或定期为学生普及口述访谈知识,组织学生研讨,形成口述教育的多样性,为口述史工作培养后续人才[19]。
4 结语
“麦康维尔谋杀案”和“美国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传票案”其实是同一事件两个角度的叙述,前者从司法的角度认为维护公共利益是法律的核心职责,后者从口述史的伦理角度认为要想口述史得到蓬勃发展,必须要遵守伦理规范。作为口述史特别是涉及敏感主题的口述史工作人员,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法律和伦理规范之间找到平衡点,在维护法律权威性的同时也能促进口述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