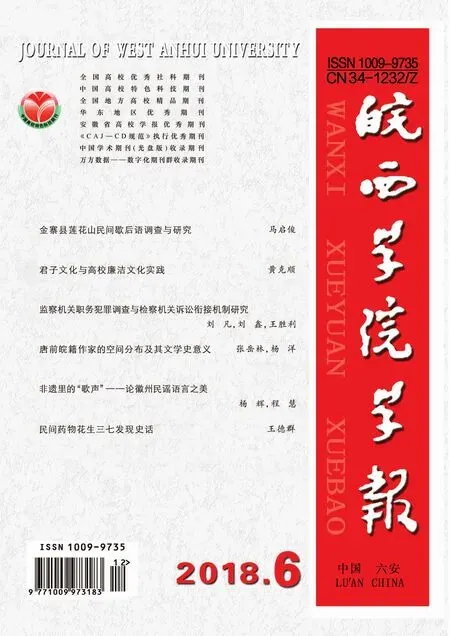唐前皖籍作家的空间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
张岳林,杨 洋
(皖西学院 文化与传媒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一、问题的提出
作家的地理分布和活动空间,构成了文学生成的场域,其空间展开方式使得文学史呈现非线性演进状态。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空集合里,各种文学因素的碰撞,各种文体的交相呈现,和作家的空间流动等,都显示出文学史嬗变的空间维度。
目前,统计古代作家籍属的著作主要有两种,即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曹道衡、曾枣庄等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谭著“上起李耳,以讫近代。凡姓名见于各家文学史及各史《文苑传》,或其文学著作为各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所收者,靡不收录”(《例言》)[1](P2)。曹道衡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唐前从宽,“1.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2.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3.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文而生平可考者;4.许穆夫人、寺人孟子等传统记载中以之为诗人者”(《凡例》)[2](P1)。两相比较,谭著显然偏严,所收属于主流或影响较大的作家;曹著则稍宽,比如许穆夫人、寺人孟子、家父等早期群体文学时期的人物也被收入。本论文以曹著为主,参照谭著。按曹著所收,唐前皖籍作家共57人(谭著52人),占其总数1316人(另有234人籍贯不详)的4.41%,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数。具体情况如表1。
二、皖籍作家的空间构成
统计以上作家籍属可知,汉代7人全是沛国人。相,1人;洨,1人;龙亢,2人;蒙2人;谯,1人。这显示沛国地区皖籍作家兴起的地域性与承续性。
三国晋时期:沛国谯,12人;竹邑,2人;谯郡铚县,4人;萧,1人;汝南郡固始,1人;庐江灊,3人。这是谯郡地区文学人才大兴时期,形成了当时的全国文学中心。同时呈现沿大别山向南分布的新变化。
东晋至隋时期:谯郡,1人;铚县,2人;龙亢,1人;沛国相,8人;临淮,1人;蒙县,2人;临泉,1人;庐江灊(霍山),5人;庐江灊(六安),3人;舒城,1人;当涂,1人。此时,淮河一线仍占优势,但大别山庐江灊地呈兴起之势,呈现明显向南流动的趋势。当然,这与晋室东迁,此地成为北方向南迁徙的通道有关。
总体上说,唐前皖籍作家沛国(郡)作家人数占绝对优势,达到35人,占比61.41%。其他梁国蒙人4人,占比7.02%。庐江六安6人,占比10.53%。庐江霍山5人,占比8.77%。再以沛国来说,谯郡以14人雄踞榜首,并成为时代的标杆,把中国文学推进到新的高度。从其分布格局来说,皖籍作家兴起于淮河流域,以改变中国文学史版图的气概开启文学书写的旅程。建安魏晋时期,成为皖籍作家影响中国文学史的最重要时刻。随着晋室东迁,皖籍作家逐渐南迁,对贯通中国文学南北交流的通道,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表1 汉代皖籍作家信息表

表2 魏晋皖籍作家信息表

表3 东晋南北朝皖籍作家信息表

续表
当然,由于文献记载与保存等问题,皖籍作家的数量不止于此。还有像老子、庄子这类籍属存在争议的作家,以及大量迁居皖地的作家,他们的写作都与安徽地域有关,是地域文学中的特殊风景。
三、皖籍作家兴起的成因
(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安徽纵跨两大河流域,淮河以北是淮河平原,江淮之间是丘陵地带,皖南则是山区,西边大别山纵贯南北,这成就了“安徽连贯东西、融会南北,左江浙,右湖北,上接中原,下邻江西。长江淮河穿省而过将安徽切成比较均匀的三大块。淮北平原属典型的北方,皖南山区是标准的南方,江淮之间是南北过渡地带。全省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适宜农耕”的空间图景[3](P251),使其居于中国文化和经济的南北、东西枢纽的通道位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淮河平原地势平坦,水网发达,交通便利,物产丰富,是皖省境内最发达地区。以亳州为例,“居涡河之上游,为皖北之门户”,“县境平衍,绝无山岭,仅东南有邱阜数处,巍然独立。西北有虎头岗,蜿蜒数里,屏障县城。……道路平坦,交通尚称便利”,“按亳县之水,上接宋陈,下达淮泗。涡为大,西淝次之,东明次之,宋唐等河又次之。自涡以下,几为河者,一十有八”[4](P3-4)。这里物产丰富,而且早就开始使用青铜器。“涡阳这次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青铜农具和工具,更从实物资料方面说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确实广泛使用过青铜农具,至少在淮河流域是如此。”[5](P24-30)同时筑塘修坝,大兴水利,如孙叔敖主持修筑芍陂,使得这里成为重要的农业区。
(二)交通便利
江河本就是古代重要的交通通道,安徽有两大河横穿,水系发达,加之淮河平原地势平坦,春秋以来成为连接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早在三代时期,六安作为皋陶及其后代的封地,就是部族联络的重要地带;大禹在涂山会盟天下诸侯、治水,标示出部族东移的步伐。春秋混战以来,中原居民南迁,楚兴起以后北上,安徽都是主要的通道之一。如州来(寿春)至九江一带是春秋时期楚吴争斗的交通要冲。而楚迁都寿春,安徽成为楚文化东移的主要区域。
随着春秋战国中原的动荡和汉以来与匈奴的民族矛盾的加剧,北方人口南迁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东晋的南迁,则是第一次高潮,而安徽就是其迁徙的主要的通道。据谭其骧先生统计,永嘉至宋(刘)初,北方人口四次大规模南迁,达90万之众,占全国540万人口的六分之一。另《南史》列传728人中有506人原籍是北方人[6](P206-229)。曾大兴统计了一份外籍自东汉至隋迁居皖省的名单,人数多达位49位,如唐林、裴松之等[7](P18-103)。当然,安徽人也加入了这迁徙的大军,如谯国戴氏移居会稽、谯国桓氏移居宣城等,对迁入地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至于迁徙对文学的影响,班固早已关注: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吴、粤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8](P1328)。《楚辞》的渊源便与这一地理环境有关。李则纲说:“从历史发展来说,楚国势力未达到淮河流域以前,叫作‘南音’;楚国势力达到淮河流域以后,才叫‘楚辞’‘楚歌’。‘楚辞’和‘南音’是一脉相承;楚辞和楚歌,是一物异名。”[9](P28)可见此地恰恰是《楚辞》生成的重要文化空间。
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庄子、《淮南子》、桐城文派、徽州的宗族等都与各时期的迁徙有关。而文翁治蜀兴文教,影响巴蜀文化的发展,是安徽文化对外流播的成功案例。再如《宋书·沈怀文传》:隐士雷次宗被征居钟山,后南还庐岳,何尚之设祖道,文义之士毕集,为连句诗,怀文所作尤美,辞高一座[10](P2102)。举行文士雅集联句,有益文学事业的传播。因此,正是在迁徙流动中的交流、融合与播散,才成就了安徽文学、文化的大观。
(三)文化的开拓与交融
安徽文化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从皋陶时代起就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建构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1、融合南北而偏于南方文化的文化基因
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安徽居于中原中心的边缘地带。虽一直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如皋陶的礼、法文化,大禹在涂山治水,本身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但偏居南方(相对中原),是其基本的空间版图定位。本地早期居民被称为“淮夷”,是有别于中原之华夏诸族的。关于南方歌诗最早的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11](P334-335)这涂山“南音”就在安徽境内淮河地区。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周南》《召南》都是受其影响才产生的。当然,安徽不是被动地接受楚文化的影响,而是参与楚文化的东扩,发挥了自己的建构作用。一般认为“楚文化有六要素:一是青铜铸造工艺;二是丝质工艺和刺绣工艺;三是髹漆工艺;四是老庄哲学;五是屈原诗歌和庄子散文;六是美术和乐舞。楚文化这六要素之形成,都与江淮文化有密切关系。”[12](P351)这六要素的发展与成熟都与安徽有关。以此为基因,对此后安徽文化、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影响深远。
2、创新性
创新是文化的生命,也是文化活力的彰显。安徽文化表现出的创新性,在中国文化的建构中是相当突出的。皋陶立“法”,创立中国古代司法,开启了中国司法史。大禹治水、娶涂山氏之女,为启建立夏朝奠定了基础。老庄、管子言道,在儒家之外,别开中国思想史新天地。嵇康著《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发扬玄学,指摘六经,非议名教,在玄学中独树一帜。张良等助刘邦兴汉,完成国家一统,真正实现国家意义层面的中华统一。在南北文化交融中出现了《淮南子》这类著作,达到汉代思想、文化、学术的新高度。东汉桓谭、魏晋南北朝嵇康的玄思,何氏的经学,薛莹的史学,华佗、曹翕的医学(《解寒食散方》)等都是时代思想、文化、学术的精华所在。“南音”的远古歌唱,三曹诗歌的新时代等举不胜举,在在说明了安徽文化的创新能力。
3、包容性
一般认为古代安徽没有形成统一的徽文化,这与齐鲁文化、关中文化、晋文化等相比,似乎是一点缺憾。从原因来说,主要与安徽独特的地理空间有关。安徽被淮河、长江分隔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或政权,今天的安徽是明清时期才形成的。但正因为这一特点,安徽文化反而显现出包容性的特征。西南的楚文化、东南的吴越文化、北方的中原文化、东北的齐鲁文化等都被吸纳进安徽文化中,由此显现出安徽文化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只不过淮北多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北方文化的特征较为明显;皖南则接近江浙,尤其皖南形成了徽文化,是安徽文化走向近代的基石。
4、变而有常,持守有度
如果说中国文化以强大的伦理内核表现出其稳定性的话,安徽文化相对来说则显现出易变的特点。这由前述的安徽文化的创新性即可体现。自觉的独立意识、对正统的超越,善于吸纳一切有益的因素发展自身,但又持守有度,从而表现出与时俱进,常常独领风骚的气度。皋陶立法,老庄求道,嵇康悟玄,曹丕论文,朱子阐理,戴震考据,桐城义法等,无不体现着变而有常,持守法度的特点。而这是陈独秀、胡适等能引领中国思想、学术现代化的历史根源。
(四)地缘家族的兴起
作家的批量出现,与地缘家族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这不仅因为家族总是地缘的,更在于家族是政治、文化、教育、学术、文学写作等的基础,是把一切影响作家生成因素关联在一起的结构性力量。而安徽地缘家族在中国文化史上一直具有强大的气场。自东汉至清出现过近二十个世家,如东汉庐江舒人周氏、庐江松滋(宿松)陈氏,晋代庐江灊(潜山)人杜氏,魏晋南北朝潜山何氏仕族等[13](P2)。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亳州曹氏,不仅改变了中国政治版图,更改变了中国文学版图。曹氏作家或具备写作能力的凡6代14人,占比24.14%[14](P8-14),在唐前皖籍作家中遥遥领先,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第一个文学家族。庐江灊(潜山)人何氏6人(一门入史传达60人),占比10.34%。嵇康家族5人,占比8.62%。刘氏家族6人,占比10.34%。从有记载的皖籍作家的出现来看,家族性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这些家族重视教育、学术和文学写作,如曹操雅爱诗章,登高必赋。再如何氏之所以人才辈出,正在于其家族对文教、学术的重视。如何尚之著《退居赋》;何佟之著《礼义》等文百余篇;何之元著《梁典》30卷;何琦著《三国评论》百许篇行于世;何偃注《庄子·逍遥游》;何胤在东山讲学,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1卷,注《周易》10卷、《毛诗总集》6卷、《毛诗隐义》10卷、《礼记隐义》20卷、《礼答问》55卷等[13](P2)。一门学问,令人赞叹。还有夏恭讲学,“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人。”[15](P1761 )可见皖籍作家对教育的重视。
由此言之,唐前皖籍作家主要集中在淮河区域与沿大别山的庐江灊等地,正是地理与家族相结合的案例。
四、皖籍作家兴起的文学史意义
皖籍作家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位置,不仅具有自己的特色,还呈现出某种特殊性。既前后相继,又跨越式汇聚,从而演绎出一幅特殊的文学图景。由于行政区域的安徽是明代以后的事,唐前皖籍作家在不同时代隶属不同的州郡。但大体说来仍可划分为淮河文化区、长江文化区,以及两个文化区的交界地带——合肥等江淮地区。就唐前皖籍作家这一布局特点来说,它显示出文学史空间流动的一定规律。
(一)区域文学对文学史线性描述的改变
区域文学呈版块状辐射,打破了文体、题材、作家前后相继的文学史描述方式,而是呈群体的、多种文体并呈的方式展开。如建安群体,在这个群落中,既有经典作家,如三曹,也有曹氏家族群体,以及围绕三曹建立的文学集团。其文学活动既有个人的激情展示,也有文学集团的文会,文学成为一种组织活动,如曹丕兄弟与王粲等人的同题共赋。因此,建安文学的声音有主旋律,更有大量的和声。显然,这不是建安时代对前代文学史直线的继承,而是特定地域、家族、政治、文化、教育、交通等的一次碰撞,是中原与江汉两大板块之外,出现的新的文学版块,对文学主题、文体、风格、批评、作家身份等的一次新的地理发现。比如曹操以四言诗开启这个时代,何以不是直承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而是跳跃到《诗经》呢?从本质言之,曹操写作四言是对经学的形似认同和实用性超越。其断裂的意义大于连续的意义。重要的是,皖籍作家集中出现,一批中小作家、潜在的写作者浮现出来,显现出区域文学生态的丰富状态。
(二)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的不重合凸显文化区域的影响力
文学史上,齐鲁文化、关中文化、吴越文化等与其历史直至现代的行政区域是基本一致的。但安徽在明清以前行政区域与文化区域两者是不统一的,淮北带有北方文化的色彩,皖南具有江南文化的气质。这造成作家籍属统计的困难,比如以下作家在谭著和曹著中分属安徽或江苏,但从文化圈看他们属于同一文学生态圈,文学活动在各自生活时期多有交集,如刘伶、丁廙、丁仪、唐林、桓范、刘弘、何充、桓嗣等。重要的是,这一区域是楚文化东移后在安徽发展起来的新系统,吸收了当时本地区地方文化的养分。即以庄子论,从文化归属来说,也应归于安徽淮河文化区域,而不属于河南所在的中原文化圈。还有刘安的文学活动也是在淮南取得的。因此,作家籍属研究不能局限于行政区划,可以考虑文化圈和文学生态的实际关系,尤其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发现作家之间的关联[16](P75),考察其对文学发生的影响,意义可能更大一些。这应是作家籍属研究的特殊案例。
由此,当以三曹为代表的皖籍作家强势崛起,其形成的区域文化场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直至改变中国文学的空间格局。
(三)诗人身份的凸显奠定了诗文在中国文学史的本体地位
魏晋时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的转型时期,魏晋文学被认为是开新时代,构成了魏晋诗歌艺术系统,而这都有赖于作家诗人身份的确立。论者注意到,“东南地区的文化人有一个特点,即经学人才较少而文学人才较多。两汉时,东南地区(包括沛国、楚国、会稽、吴郡、广陵、临淮等地)的经学博士只有19人,仅占全国总数的11.5%,而文学家则有50人(其中西汉27人,东汉23人),占全国总数的26%。”[7](P35)那么,何以东南文学人才多于经学人才呢?除了地理风习对人的性情影响等因素,更与东南人才所处的文化空间位置及其形成的“内部眼界”有关。钱志熙把魏晋作为群体诗学与个体诗学转化的分水岭[17](P16),而个体诗学的成熟有赖于作家诗人身份的确立。建安、三国以来,皖籍作家的兴起恰恰加速了文学史的这个转变。当时写诗已不同于经学领域的“诗经”,“汉末的‘三曹’和‘建安七子’”,“不知名的诗人更不知有多少,这说明‘诗’已经从‘经’的神圣殿堂下降为文人们的基本技能之一”[18](P207)。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史上作家诗人身份的确立,是与汉末、建安时期皖籍作家的兴起相联系的。
笔者提出诗人身份概念,以区别于文人身份概念。文人身份的标志指的是文人趣味的形成,但有文人趣味,不一定会成为作家,比如大批学问家,故文人身份这个概念有点宽泛。而诗人身份不仅具有文人趣味,更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诗性精神,并通过诗文写作显现其诗性自我,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诗人身份。这一身份的凸显,有助于确立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核心地位。曹操“雅爱诗章,登高必赋”,彰显强烈的诗人自我;曹丕视“文章,经国之大业”,并以“气”论文,同样明确显示对诗人身份的肯定;曹植虽然说“诗赋小道”,欲施展抱负,却反而显现出摆脱不掉的诗人身份困惑。李春青注意到建安、魏晋诗人群体一直存在身份冲突的问题,建安诗人群体的这种身份冲突[19](P24),恰恰是诗人身份得以建构的历史机缘。至少,以三曹为核心的建安诗人在这个历史刻度上,把诗人身份、诗人意识大大地强化了。
当然,诗人身份与文人身份大体上是同构的,更准确地说其是文人身份的一重特殊的身份。不同在于,诗人不仅具有文人趣味,更在于多“气”,所谓“文以气为主”,“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20](P32),即与地理相关的气性、才情,彰显着诗人主体源于地域文化的内在精神风貌和个性气质。王延寿云:“嗟乎!诗人之兴,感物而作,故奚斯颂僖,歌其路寝,而功绩存乎辞,德音昭乎声。物以赋显,事以颂宣,匪赋匪颂,将何述焉。”[21](P75)这段话不仅强调了诗人“感物”的创作心理,而且把诗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赋予了其诗人身份。而诗人“感物”的心理结构总是与其生长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相联系的,即使他以后宦游,故乡的地理环境与文化环境都是构成其心理结构的基础。所以曹丕论文注意到作家与地理的关系:“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22](P234)。曹植也认为:“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与杨祖德书》)[23](P141)而淮河流域及其相对关中、中原的空间位置与文化场域,是三曹形成不同于“齐气”等的独特个性气质的地理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或可说是对诗人身份的理论自觉。
重要的是,作家诗人身份的确立与文人诗的发展在汉末、建安、魏晋是同步的。五七言诗等新诗体的出现,除了诗史、音乐、文化等原因,还应与诗人身份及其诗人气质有关。特定地域文化在此起到了文化生成的结构性作用,这才是历史长时段的应有含义,而其总是与特定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比如黄河中下游、江南、徽州等。梁启超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也。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位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24](P4259)此说虽显笼统,但南方文化与音乐对文体的影响是深刻的。淮河流域文化以楚文化为底色,包容吸纳北方文化,这对五七言、辞赋等文体的发展具有内在的意义。它改变了此前经史的核心地位,使得诗文由此成为作家言说的经典方式,获得文学史的本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