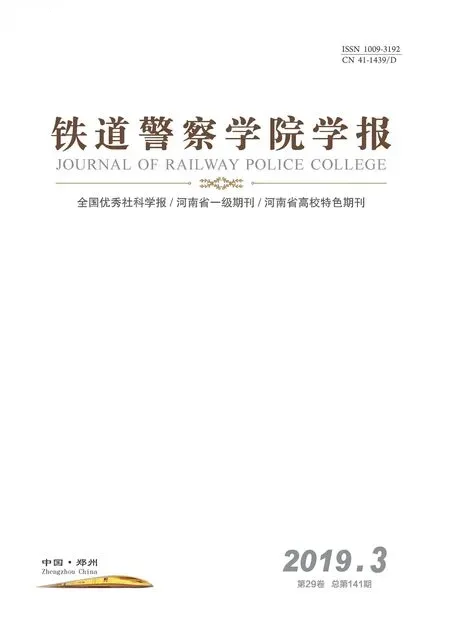西方警务现代性的发轫与成长
胡建刚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治安学系,江苏 南京210000)
西方警务现代性的特征包括职业性、专业性、快速反应机制与法治性等四个纬度,这也构成现代警务演化的四个阶段。在警务史上,英国率先孕育着一场警务革命,突破了警察镇压职能原始的单向惩戒选择。1829年,当时担任英国内政大臣的罗伯特·比尔组建了伦敦大都市警察,成立的新警察体制影响了世界各国的警务发展,标志着警务运行开始了职业性的阶段。随后美国的理查德·西尔威斯特和奥古斯特·沃尔默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警务的专业性的发展,由于他们的努力,公众和议院也逐渐认可了警务专业性。20 世纪的上半叶,汽车、车载无线电台和电话这三项成果在警务工作中的应用与普及,建立起“公众报警求助——警察局接警并调度指挥——街区巡逻车及巡警快速赶往现场处置、解决”这一影响至今的警务快速反应机制。20世纪后半期,由于集团腐败和滥用警察权力等因素,警察合法性不断削弱,警察权的使用越来越受到争议。20世纪80年代以后,警务改革的重点转向打击警察滥用警察权的执法犯法行为,试图加大对警察执法的监督控制,提升警察行为的合法性。
一、从镇压者到“宝贝型”警察:警务职业性的开始
1828 年4 月,乔治·坎宁去世后,英国组成了以威灵顿勋爵为首的政府,罗伯特·比尔回到内政部,担任内政大臣,开始了新一轮的伦敦警察改革的探索。当时的伦敦,社会治安十分严峻。1828 年2 月28日,比尔敦促议会再次建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大伦敦地区的治安状况。该委员会成员由25 名代表组成,主席由牛津大学校长伊斯特科特(T.G.B.Estcout)担任。经过详细调研,委员会最终在1828年7 月11 日向下院提交了调查报告。报告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说明伦敦犯罪率增加的情况。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犯罪都增加了,尤其是偷窃牛和马,被定罪的总人数以年均55%的速度增加,去除人口增长因素,实际增长36%。第二部分是关于大伦敦警务实施。报告建议建立一支由内政大臣直接控制的警察厅,管理所有的警察和负责整个伦敦及城郊地区,解除地方法官负责的警务性工作,新建立的警察费用一部分由公共财政支出,一部分由教区承担[1]。
在建立委员会的同时,比尔表达了以圣保罗(St Paul)大教堂为中心半径10 英里的区域内实施警察改革的计划。1829年4月15日,比尔向下议院提交了他最终的议案,获顺利通过,1829 年6 月5日,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将这一法案提交上院讨论通过。当月国王乔治四世正式签署“改进大伦敦及附近地区警察法案”(Act for Improving the Police In and Near the Metropolis),简称《伦敦大都市警察法》,比尔多年致力于建立职业化警察体制终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19世纪30年代,英国各城市的组织与行政仍然与中世纪时的情况类似,大多数城市政府由所谓的“限制自治团体”(Close Corporation)控制,这个团体由市长、市参议、市议员和自由民共同组成,有处理一切城市事务的权限。《市镇自治机关法》(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s Act)1835 年7 月经下院,9 月经上院反复辩论后通过。该法案76 条规定了各自治市建立与伦敦大都市警察类似的体制。在利物浦,建立了一支360 人的警察队伍,1848 年增加到800多人。在曼彻斯特,建立了一支360人的警察队伍,1848 年增加到450 人。布里斯托、伯明翰、谢菲尔德等也有类似的发展[2]。
由于1835 年法令只要求在享有自治权的城镇建立警察,而那些没有自治权的城镇不包括在内,而且很多郡也没有纳入其中,解决这一瓶颈得益于1839 年出台的《郡警察法》(the County Police Act,1839—1840)。
1836年10月,查德威克向首相墨尔本及内政大臣约翰·拉塞尔提议,任命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乡村警察建设的方案,该调查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认为:大量流窜的小偷及流浪者从伦敦及其他大城市进入乡村地区,威胁乡村的治安秩序;提议建立一支领薪的职业警察队伍进行治理。该报告认为,警察应该进行训练,或来自军队;招募的警察应该与服务地无任何私人联系;警察应定期在各地区进行轮岗;警察执行地方任务时必须服从地方指挥,打击跨区域流窜犯时必须服从最高负责行政当局的总体指挥。从交易成本来看,这样一支警察队伍每年费用低于50万英镑,而挽回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万英镑[3]。
1839 年《郡警察法》与皇家委员会报告中所提的方案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不同:一是《郡警察法》没有提及在警察委员会领导下建立单一、全国性的警察队伍,它只是一项选择性提议,如果各郡自愿,允许它们各自建立单独的警察力量。二是关于常规警察的经费问题,鉴于1830年代辉格党的财政困境及考虑到地方法官的认可度,该法规定建立及维护其正常工作的经费由郡独自承担[4]。
1839年《郡警察法》的实施范围非常有限,1856年《郡与自治市警察法》(the County and Borough Act of 1856)做了相应补充。该法规定所有郡和自治市都必须建立自己的警察组织,郡和自治市的警察组建与管理由地方政府和各郡、市警察局长共同负责,中央对各郡和自治市警察没有直接指挥权,但有一定的监督和控制权。自此,从大伦敦警察厅到乡镇的警察机构逐渐形成统一的警察制度,中央和地方开始成为分管警察机构的共同伙伴,在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财政控制下,地方当局和警察局长共同管理和指挥全国统一的正规警察机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警察局长三位一体的警察领导体制由此逐渐确立,该结构成为随后一百多年来英国警察制度的基石。
在当时,由于法国建立了一支队伍作为国王镇压人民的工具,英国民众担心建立起来的警察组织会破坏朝野力量的平衡而不利于人民,议会也害怕警察会增强执政者的中央控制能力,而这两者恰好动摇了英国的基本信条: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罗伯特·比尔也认可这种疑虑的价值,他同意边沁的观点“规制和惩戒自身就是一种罪过”“预防犯罪胜于惩罚罪犯”,在承认警察本身就是一种恶的同时,基于现实持续高涨的犯罪率,比尔认为,相比警察的恶,罪犯更可恨。如果不尽快成立警察,将无法遏制城市犯罪,公众将陆续变成犯罪的牺牲品。有目共睹的治安秩序混乱和对犯罪的恐惧使比尔的提案获得议员的支持,为了保证地方政府对警察的有效控制,对警务运行进行立法规范确有必要。最终,在首相威灵顿公爵的支持下,比尔成功地说服了国会。
英国成立的新警察体制影响了世界各国的警务发展,它标志着警务运行开始了职业性的阶段,英国警务模式运行的原则包括12个方面:
(1)警察应当像军队一样,成为一支独立的纪律性很强的专业执法队伍。
(2)政府必须能控制警察机构,对其进行有效的警务管理。
(3)对警察工作的绩效考核是看犯罪率的降低。
(4)警察必须定期公布犯罪信息。
(5)警力安排必须以犯罪发生的时空进行科学配置。
(6)警察执法时必须彬彬有礼。
(7)警察要凭借形象来获取公众的尊重。
(8)为了保证警察执法的效果,注重优秀人才的招募和进行警务技能的培训。
(9)警察执法时必须佩戴警号,这是为了便于公众的监督和投诉。
(10)警察机构必须接近公众。
(11)警察上岗之前必须接受培训和见习。
(12)警察队伍自身的犯罪情况必须向公众披露。
比尔提议,高级警官直接从下级警员和警官中选拔,而不是从上流社会知名人士中任命,这样可以避免警察队伍傲慢的态度和优越感,使之成为一支公民的服务者而非统治者。1829年“普通警务须知”要求基层警员,“他应当态度和蔼、关心每一个人,而不管其地位、阶层……他应谨记:一个合格警官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善于抑制情绪,不因任何语言与威胁而有丝毫撼动;这种平和的态度与坚韧的精神定会对旁观者产生感召力,而赢得其支持”。武装化的警察使得民众愤怒和恐惧,从而割裂警民关系,使得警察孤立无援。“警察民众化,民众才会警察化”,警民双方才能建立真正的互动型的合作关系。随着英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复杂与尖锐,其社会治安状况也呈现出恶化趋势,这使得警察任务越来越危险,警察平民化的原则却几乎未有动摇,倒是那些警察武装化、军事化的提议经常受到社会甚至当局的谴责。19 世纪中期,瓦丁顿(Horatio Waddington)代表内务部在一份首都警察武装化的建议书上批示:“这是一个严肃问题,却似乎颇值得内阁研究。过去一直有这样的提议,却总是遭到拒绝。在我看来,其严重违宪。”路易斯爵士(Sir George Cornewall Lewis)则以“此人的想法太伟大了,但我倒希望那些警员们多想想如何使用木板,而非步枪”这样的嘲讽口吻回应一位警察局长的“武装化”意见[5]。
警察的首要目标是预防犯罪,警察应对所有阶层的民众给予同样的保护、关心[6]。以此为共识,英国公众越来越强化了这样一种理念:警察是法律的奴仆、自由的卫士,而非独裁政权以及维护其“正统”的工具[7]。英国传统社会也认为,政府的秘密刺探与鼓励告密是对自由的重大侵害,故其现代警务中也强烈排斥秘密警察行径。1832年,伦敦一名警官因欲以化装等秘密侦查手段来对付左翼的“全国政治联盟”,结果被议会调查,最终被当局开除。1848 年欧洲革命后,包括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内的欧洲大陆许多进步人士流亡英国寻求庇护,大陆国家欲借1851年伦敦博览会之机,派本国警察对这些政治异己者进行侦控,尽管伦敦警察采取了一些配合措施,但英国当局却坚持这种行径须通过外交渠道,而反对警方私自行动[8]。
仅仅从时间上来看待近代警务模式的演化,法国要比英国起步早,但由于法国大革命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太大,执政者当局为了恢复治安秩序和统治格局,将警察作为政府的控制工具,忽视了预防犯罪和服务公众,表现出来的完全是赤裸裸的惩罚性。因此,从贝力(Bay Ley,1985)提出了现代警察的三个特征——属于公众、专门化与职业化(public、specialized and professional)——的标准分析,法国近代警察制度虽然时间上早于英国,但在警务模式演进历程的坐标上,英国的警务实践更符合社会变革的诉求,因而被西方警学界公认为现代警察制度发轫的坐标,英国警察也因彬彬有礼的绅士形象而获得“宝贝”警察的美誉。
二、政治化与反政治化的博弈:走向专业性道路的警务
罗伯特·比尔创设的英国新警察始创了警务的职业性模式,在弱化原始警务的惩戒性职能的同时渗透了社会服务的思想,但由于路径的依赖性,直至19 世纪末,警务的运行深深被政治所羁绊:任命警官、选择警察、晋升警衔等都要受制于执政党的干预,政治性因素甚至影响到警察日常巡逻执勤和逮捕拘押的执法活动。
以美国为例,当时美国警察效率低下,缺乏训练、腐败成风,地方政治对警察以及警务产生诸多不良的影响,能够控制足够选票的集团都有可能控制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了提供工作、结交权贵、贪污受贿和获得利益的场所。当时美国地方政治实行所谓的“政治分肥制(The Spoils System)”,即将公职委派给获胜政党支持者的制度,因此,在经过民众选举后获胜一方,拥有很大的人事安排权,为了便于控制,不仅将该党成员安排在警察局的领导岗位,而且对普通警察也安插其支持者,致使日常警务的备勤都随着执政党的轮换更替而左右摇摆不定,也造成警察队伍的不稳定、招募标准低、人员素质差等问题。
当时根本就没有选拔警察人员的标准可言,个人的身体条件、年龄大小或是道德品质都不是成为警察的障碍,唯一录用的标准是是否隶属于该集团。这样选拔出来的警察是政治恩惠的产物,因此警察队伍的组成完全是美国城市中集团政治的缩影,同时,警察的职位也成为各政治集团极力攫取的“宝物”,捍卫警察的职位不仅成为个人踏上社会阶梯的重要一步,更重要的是,穿上警服和代表法律同时意味着所隶属的集团的成功。为此,各个集团都在为取得警察职位而奋斗,当时美国大多数警察局为爱尔兰人所掌握,但美籍德国人在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密尔沃基和圣·路易斯得到一席之地,黑人在共和党的政治支持下成功地在芝加哥和其他一些城市取得了立足。早来的移民集团不遗余力地防止新来的移民集团取得警察职位,以阻止他们在社会阶层中的上升。
警察巡逻主要靠步行,由于没有有效的指挥和监督机制,警察局长实际上无法有效地指挥和管理其属下,真正的控制权掌握在各个警区的警长手中,这不仅造成统一的警政思想难以全面贯彻实施,更为基层警察的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许多城市,警察根本无法巡查城市的所有地方,时间一长,警察脱离工作岗位实际上已习以为常了,利用执勤的机会泡在沙龙和理发店里消磨时间,不仅如此,他们在接受贿赂后,允许赌博、卖淫嫖娼和非法经营酒业,定期受贿的钱由该地区的警察分享,长官也不例外。警察常为得到晋升而进行贿赂,为晋升而付出的代价将由更多的贪污来进行弥补。
19世纪后期,政府当局也曾经尝试着提高警务运行的效率和警察执法的质量,但效果不是很显著,警察的工作状况一直没有多大改观,改变的不过是警察局的控制权从一个政党转移到另一个政党而已。警务运行的低效率以及警察权力的腐败,真正根源在于党派之争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个问题如果从根本上解决,唯有“警察脱离政治(政党),政治(政党)脱离警察”,警察队伍在政党之间保持中立。
为了消除警察队伍中的裙带关系,1883年通过了《彭德尔顿法案》(the Pendleton Act),但直到1900年才有效实施,这标志着政治分肥制的结束。20世纪初,改革的新观念带给警务运行的新机制,管理主义思潮在探索警务如何适应社会现代化的变革过程中引入了警察专业性的概念,而推进美国警察专业性运动的两名最突出的领军人物是理查德·西尔威斯特(Richard Sylvester)和奥古斯特·沃尔默(August Vollmer)。
在20世纪以前,美国警察没有一个有效的专业性组织,在1871 年曾举行过一次警长会议,但直到1893年全国警长联盟才正式成立,后改名为国际警长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简称IACP),从1898 年到1915 年,西尔威斯特任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局长,1901年到1915年任国际警长协会主席。作为警长协会的领导人,他把这个组织变成了倡导警察专业化的主要代言人和传播警务模式新思想的阵地。他主张:
(1)引进军事化管理,树立尚武精神。在这之前,警察是毫无军事意识的,疲疲沓沓,纪律松懈。为了培养警察服务公众、保护公众、打击犯罪的使命感和职业信念,警察局开展了军事化训练并组建了军乐队,希望借助军事模式来给警察注入必要的纪律和加强警察的使命感,并向社会广泛宣传警察战士的形象,这种使命感意味着警察认真执行法律任务,它反过来又更加强调了对打击犯罪的专门技术和单位的设立与培训。
(2)增加新的专业性警务部门。原有的业务部门有巡逻和刑事犯罪调查,根据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又增加了毒品犯罪、交通管理、犯罪帮派、犯罪情报信息、法庭科学、警察教育训练等新的部门。
(3)提高入警选拔的条件,使警察真正成为高素质的执法力量。
(4)警察局选用具有管理知识、经验和能力的人担任领导职务,并运用科学的行政管理理论、原则和方法对警察进行管理和指导警务工作,为了进一步削弱政治的影响,警察行政长官的职务应该相对稳定和有保障,保证若干年不变。
(5)撤销、关闭原有街区和选区的警署,在警察局指挥部装置集中管理的档案系统,所有指挥、监督和管理警察、警务的权力集中到警察局局长的手中,采用这个办法是为了打破选区政客的政治权力的影响,避免各个街区各自为政。
奥古斯特·沃尔默比理查德·西尔威斯特更有名望,在推进警察专业性发展的初期,曾经做过洛杉矶市警察局局长,由于在警学理论和警务实践上的杰出成就,被美国警界尊为现代美国警察的奠基人[9]。
奥古斯特·沃尔默率先强调警察必须接受高等教育。在当时,大多数警察就连高中毕业文凭都没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建议,警察是否必须拥有学士学位的主张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对高等教育是否警察职业资格的必需条件,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沃尔默真正的关心是警察的“高智商”,他的意图很明显,是想提高警察的整体素质和人文精神来改变传统警察木讷和呆滞的形象,用当时的智商测试的条件和方法来比较,底特律警察平均智商是55,而沃尔默选拔的警察智商平均是147。沃尔默大力提倡聘用女性当警察,因为他相信女性比男性智商高。他也是第一个聘用黑人来执法的人。
但是当时大学或学院不能提供警察所需的课程,不知道对社会学或犯罪学选择哪方面的内容才能符合警察工作的需要。1908年,沃尔默在伯克利市创办了美国警察史上第一所警察学校,他设计了警察教学的课程体系,有骑自行车、照相、法学、生物学和化学、统计学、演讲术、社会学、心理学、变态心理学、警察行政学等,由包括他在内的高级警官和从大学聘请的教授给新警员上课。在其影响之下,美国许多地方警察局相继建立了正规的警察学校,联邦调查局还建立了国家学院,一些社会上的大学也开办了警察行政学或刑事司法学系。
在IACP 会议上,沃尔默倡导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警察训练的标准化和执法的规范化。这样,通过建立和提高警员的录用标准,并对新警员进行严格正规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化技能训练,使美国各地方警察局警察人员的各方面素质,尤其是专业执法的素质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他提出建立一个统一的犯罪报告制度(a Uniform Crime Reporting system ,简称UCR)防止警察执法的随意性和腐败。
奥古斯特·沃尔默积极倡导将科技成果运用到警务工作中,1916 年,他在伯克利市创建了美国第一个刑事科学实验室,由专业的刑事技术专家和法医对犯罪证据进行科学分析和鉴定。1921年,他又最先把测谎仪用于该局的犯罪侦查工作中,并始终坚信这是代替刑讯逼供的最佳科学侦查方法。
理查德·西尔威斯特和奥古斯特·沃尔默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警务的专业化发展,由于他们的努力,公众和议院也逐渐认可了警务专业性,对警察在现代警务中的地位树立了三个方面的认识:第一,警察是警务运行的主体和打击罪犯的专家;第二,警务运行需要排除行政干预和政党的干涉;第三,要提升警务的运行效率必须通过提高专业性技术来实现。在崛起的中产阶层的支持下,不断推新的技术革命和卓有成效的领导也推动了警务运行机制的变革。这一时期,警务的专业性改革集中体现在内部的管理上,诸如调整内部结构、提高人员质量、不断更新设备和建立更多的经营式运作程序。
德国警察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一直以来,德国由于受到“警察国”理念的影响,警察任务相当广泛,不仅包括排除危害,也从事保护以及促进一般福祉。普鲁士一般邦法于1797 年颁布,其规定警察任务不同于国家任务,将福利措施排除在警察任务之外,而将警察任务定义为“为维持公共安宁、安全与秩序,为排除对公众或个人现时之危害而设的营造物[10]”。但由于路径的依赖性,德国警察职能广泛的扩张性在19世纪中叶之前依然存在。1848 年“三月革命”后,现代意义上的“形式警察”才初显雏形,而到了20世纪才逐渐形成所谓的“专业警政”。
三、快速反应的警务机制:成就警察的机动性
1919 年,沃尔斯特德法案(theVolstead Act,俗称the 18th Amendment or Prohibition,即禁酒令)公布,在法案最初实施阶段一度使警察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公众并不愿意放弃酒精的刺激,警察不得不凭借高压手段和计谋来保证法案能正常地贯彻下去。紧接着1930 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失业人数剧增,城市治安状况恶化,有组织的团伙犯罪增多,新的犯罪形式层出不穷,飙车一族的出现、枪战、绑架勒索、抢银行等使警察疲于奔命、手忙脚乱。公众渴望警察能成为打击犯罪的斗士,为打击犯罪,警察必须更有效率。时世造就英雄,20 世纪的上半叶,汽车、车载无线电台和电话这三项成果在警务工作中的应用与普及,对警务模式的发展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些城市警察局已经尝试将汽车用于巡逻,20世纪20 年代以后,使用汽车巡逻得到很快发展,奥古斯特·沃尔默的得意门生O.W.威尔逊在任威奇塔市警察局局长期间(1928—1939),撰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关于巡逻车巡逻的小册子《巡逻力量的布置》,论述如何运用巡逻车有效地进行巡逻勤务,将警察巡逻勤务引入科学理论的指导。
当警察巡逻车配备了无线电台以后,警务的运行更是机动灵活,警务的调度人员不仅能知道警车的巡逻位置和周边治安状况,还能在遇到紧急事件的发生时迅速调集警车前往出事地点,这样,极大提高了警务覆盖的区域、机动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当时,电话在美国日常生活中已相当普及了,但只有当警察的巡逻车上有了车载无线电台之后,警务的运行才真正能同时接受公众的报警求助和指挥中心的即时指挥,建立起“公众报警求助——警察局接警并调度指挥——街区巡逻车及巡警快速赶往现场处置、解决”这一影响深远的警务快速反应机制与模式,被誉为“第三次警务革命”。这次警务革命将警察作为打击犯罪的战士角色推向了鼎盛时期,机械化的巡逻成为警务日常执勤的主要方式,这种警务模式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机械化巡逻促使了警察亚文化的发展,第二,机械化的巡逻恶化了警察与公众的关系。
堪萨斯市警察局做的一项实验表明,大多数情况下,快速反应并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严重暴力犯罪不是靠快速反应机制可以阻止和消除的,统计数字表明,快速反应机制对三分之二的案件没有成效。警察对犯罪的发生快速反应,若增加现场逮捕嫌疑犯的概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是否能及时报警和警务指挥中心迅速调度警力赶赴现场,问题就在于公众是否有意识地积极去打报警电话。直接推论的结果就是唤醒公众打击犯罪的责任心有助于及时有效地通知警方,并为指挥中心调度警力赢得时间。市民报警时间而不是警察部门的反应时间,对于现场抓获罪犯及当场确定目击证人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超过90%的犯罪案件中,市民往往要等待5-10 分钟才会报警,这就使警察快速反应抓获罪犯的想法成为泡影[11]。
相比之下,如果公众受到对犯罪快速反应的号召和得到良好的培训,周围社区成员要比警察来得迅速和有效。当犯罪发生时,在警察赶来之前,社区成员首先作出快速反应,阻止犯罪的继续,减少进一步的损失,弥补警察作出快速反应之前的真空。因此,光靠警察快速反应是远远不够的,首先要发动公众进行有效的报警,并在警察赶到之前能有一些建设性的行动。
四、合法性的缘起:改变警察的亚文化
威廉·A·韦斯特利(William A. Westley,1970)首先提出警察亚文化(police subculture)的概念。所谓亚文化,指某一文化群体所属次级团体的成员共有的独特信念、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与社会主流文化相对应,一种亚文化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如同性恋亚文化、移民亚文化、青少年犯罪亚文化等。
韦斯特利在研究印第安纳州警察时发现,73%的警察认为公众不信任他们。公众不理解警察,警察也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即使是社会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如检察官、律师、记者等也对警察充满着怀疑和敌意。面对社会强大的压力,警察通过自我认同和增加内部的凝聚力来抵抗外界的质疑和不友好,这导致警察团体普遍存在着强调保守秘密和采用暴力的亚文化倾向。“警察相互支持以谋求道义上的同情,他们认为,保守团体间的秘密是警察抵御外界最好的盾牌”。看到同伴执法犯法时,警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是明知同伴贪污受贿,大多数警察也选择了沉默,而滥用暴力更是警察宣泄自身压力最常选择的途径,尤其是个人自尊或自我实现受到挑战时[12]。
按照英加迪(Inciardi,1990)的观点,警察亚文化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保护社会的“安全蓝色防线”,这样一种认知使得警察充满着抗衡强暴、匡扶正义的布道感,他们把打击犯罪看作是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公众的守护神,是正义、智慧和道德的化身。然而这种布道的意识形态在给警察带来荣誉感的同时,也造就了警察多疑、玩世不恭和狂妄自大的负面性格[13]。
正如美国警察培训手册所强调的那样,“一定要保持警惕,猜疑是健康的警察态度”。猜疑是警察的职业病,源于不断搜寻问题、调查潜在危险,警察总是对一切持怀疑的态度和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这种心理定式不仅仅是警察工作中自发的,而且经过长时间的职业生涯会不断得到强化。
由于总是处于接触社会的阴暗面,面对犯罪分子的狡诈和凶狠残暴,警察不得不变得冷漠无情和玩世不恭,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侦破,并非所有的罪犯都能被绳之以法,当一切成为流水作业的惯例时,神圣的布道感也就被彻底打破。抓住罪犯已经由社会的服务感逐渐转变为一种追逐猎物后的满足感和胜利感。对于案件破不了的无可奈何或是刑事司法体制的缺陷使得罪犯逍遥法外,警察洞察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大彻大悟之后,不仅不相信人性,甚至也不相信社会,玩世不恭成为警察得以心理平衡的挡箭牌:“落入法网的罪有应得,逃脱惩罚的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警察的专横、粗暴和狂妄自大源自职业化的定格,从1829 年罗伯特·比尔创立伦敦大都市警察开始,警察就逐渐被塑造成执法的权威。在经历过专业化运动的洗礼后,警察工作不再是普通人可以胜任的,它需要融合法律、科学以及警务技战术等多种知识技能,警务行为被建构成一项职业性极高的任务,警察不仅被视为控制犯罪专家,而且是“打击犯罪”的战士。专业化推进的极致形成了警察相对独立甚至封闭的管理态势[14]。
斯科尔尼克(Skolnick,1994)强调,内部的团结与外部的孤独感正是警察矛盾境界的写照。警察对外的孤独感来自过度专业化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内部团结,一方面是对外部敌意的对抗,另一方面也需要用集体的合力来抵御[15]。
警察亚文化的负面影响在警察具体执法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集团腐败和滥用警察权力。20世纪后半期,警察合法性不断削弱,警察权的使用越来越受到争议[16]。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伦敦警察厅内部的两起涉及警察腐败的大案,一起涉及毒品犯罪集团,侦探总督察凯拉赫(Kelaher)伪造大量的证据;另一起卷入淫秽出版集团,涉嫌贪污和受贿,两个案件都暴露出警察系统性的集体渎职行为,导致许多高级警官的入狱。
内政大臣雷金纳·麦·德宁(Reginald Maudling)任命素有“廉洁”著称的罗伯特·马克(Robert Mark)担任总监来发动对警察腐败的战斗。马克随即开始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他新组建一个专门部门来调查所有针对警察的投诉和控告;由专业警官来主管苏格兰场的刑侦部门;授权高级官员监管所有部门侦探;频繁安排侦探轮岗,并和媒体培养相互沟通和更开放的关系。在这一系列改革浪潮的冲击下,约有500名警察离开了警察机构。
毫无疑问,大量丑闻被揭露毁坏了警察作为公正无私、严明纪律执法者的传统形象,警察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1960 年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显示,有46.9%的民众认为警察不会有受贿行为的发生,而1981年政策研究机构对伦敦市民的调查数据表明,这一数字下降到14%。
20世纪80年代以后,警务改革的重点转向打击警察滥用警察权的执法犯法行为。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案件证据法》(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出台,它的颁布旨在控制警察执法的自由裁量权,事实上,由于陋习累积至深,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早期,警察滥用职权案件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这是因为对以往警察渎职案件的调查所致。1989 年10 月,上诉法庭经过审理,推翻了1974 年爱尔兰四青年被判终身监禁的案件基尔福四人案(Guildford Four),重新调查到的证据表明,当时负责案件侦破的警察在审理过程中作了伪证。1990年3月,上诉法庭宣布免除因1974年爆炸事件定罪马奎尔等七人案(Maguire Seven)案件的罪责;1991 年3 月,因1975 年爆炸事件定罪的布里明翰等六人(Brirmingham Six)被宣布无罪。最具悲剧性的要数斯特凡·基什科(Stefan Kiszko)一案,被告在1976 年被判谋杀一名11 岁女孩,办案警察隐瞒了被告不可能杀人的证据,导致基什科在狱中被关押了16年。
一系列冤案得以昭雪,民众的恐慌也随之加深,英国政府最后成立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Criminal Justice),由朗西曼(Runciman)出任主席,试图加大对警察执法的监督控制,提升警察行为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