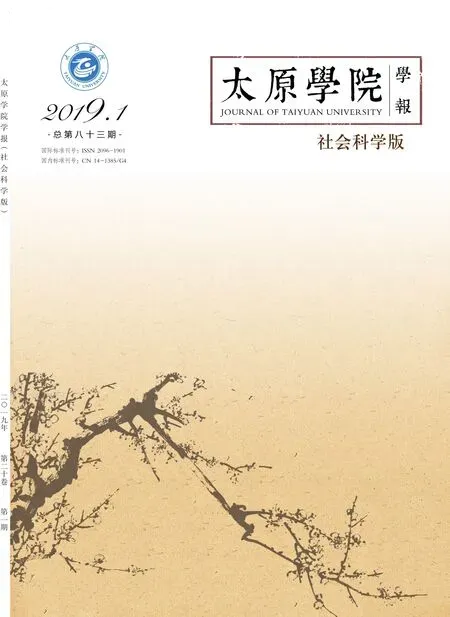从凌濛初“二拍”看晚明士人群像
王园园
(河南大学 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河南 开封475001)
凌蒙初(1580-1644),明末著名小说家,一生致力于通俗小说的创作,著作颇丰,其中以“二拍”影响最大。“二拍”自问世后,学界已对其婚恋观、女性形象、僧尼形象、晚明商人地位及商业活动等做了深入全面的研究,但对于士人形象及其对晚明社会生活的影响,论者尚少。既有研究成果如:程丽群《论“三言二拍”中的士人形象》通过比较“三言二拍”与前代文学叙事中的士人形象,彰显了晚明士人儒商杂糅的典范品格和独特形象。[1]刘海涛《从“二拍”看晚明“贫士”的生存状态》则主要通过“二拍”观照了晚明“贫士”的生存、仕进、婚姻等生活窘境和精神状态。[2]伏漫戈《二拍人物研究》[3]、曲玉《“二拍”人物形象探析》[4]、卢捷《落魄文人出路的理想探索——略论“三言”“二拍”中的秀才形象》[5]等文从婚恋观念、经济活动、宗教信仰等方面对“二拍”中的商人、士人、官员、僧道等人物形象做了分别描述。基于此,兹以历史主义的研究路径,结合晚明时代背景,借助“二拍”对晚明士人的精彩描述和生动刻画,着重观察“二拍”中晚明士人的多重形象、多样品性和多元生态,以期理清其极具时代特性的科举情怀、治生方式和婚恋观念,进而窥察“二拍”士人形象和现世士人之间的奇妙联系,展示晚明复杂多变的生活景象和社会势态。
一、“二拍”中晚明士人的形象与品性
(一)“二拍”中的士人类型
“二拍”凡78卷,据笔者初步统计,文中刻画的士人有240个,尚未取得功名,“少年饱学,人品端方”的士人是凌濛初笔下的主角。如《酒下酒赵妮媪迷花》中的贾秀才,“青年饱学,才智过人”[6]58;《盐官邑老魔魅色》中的刘德远,“名家之子,少年饱学”[6]260。而官僚士人在“二拍”中亦常载录,盖凌氏旨在抒发清官情节,申诉现世司法之不公,故“二拍”中多数官员是以“青天”形象出现。如《西山观设箓度亡魂》中刘达生识破其母吴氏与黄知观奸情,吴氏恼羞成怒,将其告官,府尹李杰查实奸情,杖死黄氏,表扬达生,吴氏也幡然悔悟。《赵五虎合计挑家衅莫大郎立地散神奸》中太守唐篆识破赵家五虎的诡计,严惩赵家五虎,还莫小三清白。此外,致仕家居的乡宦在“二拍”中也时常出现,如《顾阿秀喜舍檀那物》中的高纳麟,《李克让竟达空函》中的刘元普以及《青楼市探人踪》中的杨佥宪等,从他们身上可以管窥晚明乡宦的特性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明代科举取士人数渐增,但官员任用数量并未发生显著改变,这就造成明代士人“什三在官而什七在野”[7]的局面。数量庞大的士人居住乡里,必然会对地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晚明乡宦极为重视乡评,士大夫致仕归家后,与乡人比邻而居,其生活言行人人得见,人人能言,这极大地约束了乡宦的行为。如《顾阿秀喜舍檀那物》中曾任御史大夫,后退居姑苏的高纳麟,其已查明同乡顾阿秀兄弟的强盗行为,但却因是居乡官员,不敢妄自动手,唯恐背上“干谒公府”的骂名。但即使他们自身谨言慎行,由于其特殊身份,依旧吸引了无数人前赴后继地投靠,吹捧奉承,以便在日后寻求庇佑。如高纳麟最喜欢书画,乡人想要奉承他,故愿出高价买芙蓉画献与他。[6]290
同样,由于乡宦的特殊身份,其周围聚集有大量的附庸者,且晚明乡宦居乡期间蓄奴成风,对当时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些奴仆主要负责帮助主家催逼收集地租、经营典当店铺,掌有极大的权限和对民众的话语权,故这些奴仆极容易狐假虎威,为祸乡里。如晚明宜兴民变就是因陈一教和徐廷锡的家奴借势欺压百姓而起,这一现象在“二拍”中也有体现。《李克让竟达空函》中的刘元普致仕后广行善事,仗义疏财,但其家任事者“只顾肥家,不存公道,大斗小秤,倾剥百姓,以致小民愁怨”。[6]208因此,纵使刘元普一心行善,也无法避免其家奴狐假虎威、为祸乡里,更何况那些恣意妄为的乡宦,他们“极田宅之广丽,夸马仆之盛强,橐金珠,积锦绮,矜器玩,美服食,穷老年心志耳目之嗜好”[8],如《青楼市探人踪》中的杨佥宪,回乡后终日在家设谋运局,为非作歹。其兄死后,图谋断送侄儿性命,占有其财产。面对前来讨回“礼物”的张贡生,他恼羞成怒,直接将张贡生害死,其贪赃枉法、私害性命的行为将当时为祸乡里的乡宦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二)“二拍”中士人之容貌——英俊潇洒
凌氏在“二拍”中多以赞扬的态度来描写士人,他们容貌英俊,博学多才,如《闻人生野战翠浮庵》中的闻人嘉“面似潘安,才同子健”“少年英俊,又且气质闲雅,风流潇洒”[6]374。《李将军错认舅》中的金定“生来俊雅,又兼赋性聪明”;[9]73《满少卿饥附饱飏》中的满生“生的一表人才,风流可喜”[9]132。
凌氏在“二拍”中对士人的外貌、学识大加褒扬,一方面是因其对士人群体的偏爱,但更多是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从科举层面而言,因涉及国家形象,自唐代起,对科举士人的容貌便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唐代士人科举及第后,只是取得了入仕的“出身”,要真正获得官职,还须参加铨试,而铨试就包括身、言、书、判,分别取其“体貌丰伟、言辞辩证、楷法遒美、文理优长”,因此若一个应试的举子面貌丑陋,是无法通过铨选授官的。明建国后,在选拔状元时,士人的容貌也成为重要参考因素。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首次殿试,原拟为状元的郭翀因相貌丑陋,与状元之位失之交臂,而吴宗伯却因仪容俊雅被提为状元。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建文帝将体貌丰伟的胡广提为状元,取代初拟为状元的王艮。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浙江贡士丰熙,殿试策论极佳,被拟为状元,但因他“不良于行”,仪容不佳,孝宗将其降为榜眼。上行下效,明代选拔状元注重外貌的风气使得士人更加注重仪容仪表,而通俗小说中刻画的士人也大多是仪容俊雅,青春貌美,甚至出现了鲜明的女性化特征。“二拍”作为明朝广为流传的通俗小说,自然无法免俗。
从才子佳人故事发展的需要而言,才子不仅需要满腹诗书,容貌俊俏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学富五车但面貌丑陋的士人,注定无法成为故事的主角。《闻人生野战浮翠庵》中静观初次看见闻人嘉时,“世间有这般美少年,莫非天仙下降?人生一世,但得恁地一个,便把终身许他,岂不是一对好姻缘?”[6]375静观在完全不了解闻人嘉的才学和品质的情况下,便对其芳心暗许,所注重的不过是容貌俊俏罢了。《小道人一着饶天下》中“王秀才看了谢天乡容貌,谢天香看了王秀才仪表,两相企羡”[9]13,显然一见钟情,大多缘于容貌。因此,“二拍”中对士人形象的大肆褒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二拍”中士人的外貌与人品并不始终成正比。如上文提及的满生一表人才,风流倜傥,未遇时节,得焦大郎资助,娶其女焦文姬为妻,登第为官后,转眼将焦文姬抛之脑后,复娶宦室女为妻,其忘恩负义、寡恩廉耻的行为与其容貌之盛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二拍”中士人之品性——精明圆滑
士人是传统社会的“四民之首”,其人品、性格一直为世人所关注,是社会风气的投影,同时也是引导社会行为的标杆。“二拍”中的士人依旧具有传统社会所推崇的优良品格,同时他们也不再死守士人之清高,每天与“之乎者也”为伴,而是勇于面对真实的社会人生,努力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如在《卫朝奉狠心盘贵产》中,贾秀才的好友李生的房子被昭庆寺的寺僧慧空强占,李生无家可归,贾秀才出银给李生去赎回房屋,但慧空拒绝让李生原价赎回。于是贾秀才巧施计谋,假扮慧空调戏对楼的妇人,致使慧空被赶出李生家,贾秀才乘机将房屋赎回。同卷中的陈秀才因借债将房屋抵押给卫朝奉,同样是赎回时遇到卫朝奉的百般抵赖,陈秀才认为“卫朝奉这厮恁般恃强!若与他经官动府,虽是理上说我不过,未必处得畅快”[6]151,于是巧施计谋,他让家仆陈禄假装投靠卫朝奉,乘机将一条死人腿埋于卫朝奉的院子里,此后他再派家仆以抓捕陈禄为由,挖出死人腿,以此要挟卫朝奉让他原价将房屋赎回。无论是贾秀才还是陈秀才都放弃了“以理服人”的传统规范,而是采取世俗化的诡诈手段对付奸巧的慧空和卫朝奉,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最好体现。且凌氏在描写二人结局时,贾秀才后来得以高中,直做到内阁学士,而陈秀才不仅将家财赚回,后亦举孝廉,不仕而终。“二拍”全文贯穿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贾秀才和陈秀才能够有着圆满的结局,意味着其行为都不违反当时的社会准则,相反他们通过自身的才智取回本属于自己的财产,在世人眼中可能更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此外《酒下酒赵媳迷花》中贾秀才的妻子巫娘子被赵尼姑和卜良骗奸,贾秀才并未报官,而是使计杀掉老尼和小尼,嫁祸卜良,这样既维护了巫娘子的名声,又大仇得报。可见“二拍”中的士人不再迂腐不知变通,而是善于在多变的社会中保全自己,他们身上少了书生意气,多了些世俗烟火之感和小市民的狡黠聪敏。而且,即使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在晚明社会,贾秀才为报仇,让巫娘子假装约会卜良,乘机咬下舌尖的行为也可以称得上是惊世骇俗。但是凌氏对贾秀才却完全没有负面的评价,而是用“青年饱学、才智过人”[6]58、“见识高强、干事果决”[6]66等褒义词来形容他,从中可见凌氏对对传统理学思想的突破。
二、“二拍”中晚明士人的生计与生活
晚明社会变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士人生计的贫困化。自明初以来,无论是读书还是科举,都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支撑。王世贞曾在《觚不觚录》中记载,他当年仅会试前后的费用,就花费了三百两银子,而同年家贫者也用了百来两银子,而后更是涨到六七百两之多[10],如此高昂的费用,对于普通家庭可谓是天文数字。所以无论是为了维持生计,还是为了继续科考,士人都必须有相当的财富作为后盾。但与之相矛盾的是,大部分读书追求科举,以期改变命运的士人,生活都比较困窘。自正、嘉以后,社会日变,商品经济发展导致消费观念转变,科举竞争压力增加,如何维持生计以及能否继续追求科举,成为大部分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日益窘迫的生活使得越来越多的士人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治生”这一敏感话题,“安贫乐道”的思想也逐渐转变为“安贫故勤,安贫故俭,勤俭者,贫士之素也”“故学者之为生计,亦安贫而已矣”[11]。
(一)治生之道
“二拍”中的士人,同样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维持生计。按照治生方式,可以将其分为依靠家庭经济生活的士人、依靠接济勉强度日的士人、通过处馆维持生计的士人和弃儒经商的士人。那些家庭条件优越的士人,只凭借先辈所留下的财产就可以活得逍遥自在。如《张溜儿熟布迷魂局》中的沈灿若,少年英锐,家私丰裕,完全无需为生计所愁,平时与志趣相投的好友,或以诗酒娱心,或以山水纵目,放荡不羁,无所顾忌。《卫朝奉狠心盘贵产》中的贾秀才家私巨万,不仅自己生活无忧,而且能够慷慨助人。《诉穷汉暂掌别人钱》中的周荣祖,也正是因为先世广有家财,才能毫无顾虑地读书应举。而那些依靠接济或者家庭其他成员辛勤劳作来维持生活的士人虽然难免受气,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的甚至会招致家人的奚落,在家中毫无地位可言,但至少不用为生计疲于奔波。如《通闺闼坚心灯火》中的寒酸秀才赵琮,一心追求科举,家贫无以为继,靠着妻父度日,最终科举及第;《占家财狠婿妒侄》中引孙自小父母双亡,家私荡尽,又是个读书之人,不晓得别做生理,也只是靠着伯父的接济勉强度日。
相比这些生计有保障可以一心读书的士人,那些既没有家庭遗产可以继承又无法受到亲朋好友接济的士人,则是在坚持追求科举的过程中还要兼顾营生。“二拍”中的的士人多选择以“馆谷为生”来维持生计,如《韩秀才乘乱聘娇妻》中的韩师愈,“虽是满腹文章,却当不过家道消乏,在人家处馆,勉强糊口”。[6]96《李克让竟达空函》中的秀才萧王宾,胸藏锦绣,“因家贫,在近处人家处馆。”[6]206这些士人虽然早出晚归,有的甚至长期不能归家,但至少能够养家糊口,不至衣食无落。《赵六老舐犊丧残生》中赵六老为赵聪延请的饱学秀才,“每年除束脩五十金,节仪、供给不断”[6]130。李延昰《南吴旧话录》载:“得五十金则经年八口之家可以免乱心曲。”[12]每年五十金的束脩即可不为生计发愁又可安心备举,故许多士人都希图到富实之家处馆来维持生计,而这又进一步加深了士人内部激烈的生存竞争。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富实之家才有延师意,求托者已麋集其门。”[13]《同窗友认假作真》对这一现象有所影射,田百禄与学中的秀才商量要给儿子田盂沂寻一个馆坐,众秀才访得大姓张氏要请馆宾,遂将盂沂力荐于张氏。一个“力荐”便将寻求坐馆之艰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谋生的艰难使士人的生活举步维艰,加及晚明商品经济活跃,人们对于商业的看法逐渐改变,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指出很多地方“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者,皆能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14]张居正也充分肯定了商业的作用,强调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因此一部分家贫无以供给或者仕进无门的士人逐渐开始选择弃儒经商。如《姚滴珠避羞惹羞》中姚滴珠的夫家潘家“虽是个旧姓人家,却是个破落户,相公潘甲虽是人物也有几分象样,已自弃儒为商”[6]16。《叠居奇程客得助》中徽州商人程宰,世代儒门,少时习读诗书,后以经商为业,此中固有徽州重商之风俗影响,也盖与习儒难以维持生计有关。
(二)生活观念之变革
晚明士人生计之艰难使得越来越多的士人放弃读书人的清高,开始寻求不同的方式以维持生活,其思想也随之改观。而晚明阳明心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观念盛行一时,其所提倡的“关注个体、解放个性”使得一部分士人不再一味地将自己限制在传统道德体系之内,而是更加关注内心的追求与现实生活,这一改变在晚明士人婚姻观上表现得较为明显。
“二拍”中以士人婚恋为话题的作品占主导地位。因为爱情是人类能够体验到的最为普遍的激情,而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更是一直以来为人们所追捧,所以文学作品不描写普通人生活则已,但凡提及,男女之情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表现领域。但“二拍”中最重要的并非才子佳人之间的风花雪月,而是其中所流露出的士人对于婚姻的看法,晚明士人自愿“入赘”妻家和愿以妓女为妻妾就是在晚明剧变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令人瞩目的变化。
入赘婚,就是指男女结婚后,男方到女家落户的现象,男子一旦入赘妻家,子孙后代也是取女方姓氏。在古代社会,赘婿的地位是十分低的,为世人所不齿的,所以古代愿意入赘的男子并不多。秦汉时,赘婿被视为“七科”之一,常被谪发补充兵源,《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衙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15]3854张宴对“七科谪”作出注解,即包括“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壻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凡七科也。”[15]3855直到明初,赘婿的地位依然未发生较大改变,且明王朝对赘婿设有明确的规定,《大明会典》记载:“令官吏人等奏告改名复姓,自幼过房乞养或入赘与人,因从外姓报入户籍。”[16]108《皇明留台奏议》中亦有所提及:“所谓入赘者,以贫不能糊口而借资于妻家,使相臣之,子而入赘,天下皆不得子其子矣。”[17]135迄至晚明,世人对“入赘”的看法发生了显著变化。李用中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上《乞肃法纪申公论疏》,其中提到首辅申时行之子申用嘉通过入赘的方式获得乌程籍,并参加科举,得以中第,李用中认为申用嘉此举为冒籍。而申用嘉自辩:“吾入赘乌程,即可乌程籍,非冒籍者比矣。”[17]135在此申用嘉的行为是否为冒籍我们先不予探讨,但申时行的家族在当时是实至名归的名门大族,其子申用嘉以入赘的方式取得以乌程籍应试的资格,面对他人诘问,申用嘉丝毫不以“入赘”为耻。上行下效,从中可以管窥晚明士人入赘即使未成常事,但也并不少见,社会对此容忍度日增。
“二拍”中亦有大量自愿入赘妻家的士人,如《李将军错认舅》中刘翠翠一心想要嫁给金定,奈何金家家道贫穷,出不起聘礼,刘家父母便提出:“他家既然不足,我女儿到他家里,只怕难过日子,除非招入我每家里做个赘婿,这才使得。”[9]74而金家则是毫不推脱,应允不迭。金定赘入刘家,虽是家贫出不起聘礼,但从金家的态度中也可看出此时社会对于“入赘”也不再要求严苛。《满少卿饥附饱飏》中焦大郎因只有一女焦文姬,故想在本处寻个读书人,赘在家中,照管暮年。当焦大郎撞破文姬与满生私情之后,对满生说:“汝若不嫌地远,索性赘入我家,做了女婿,养我终生。”[9]136满生听后,满心欢喜,丝毫不觉得赘入妻家是件丢人之事。且满生虽是投奔旧识不成流落在外,受到焦大郎的接济,但毕竟自家也是淮南大族,世有显宦,与金家的出身毕竟不一,但二者对于入赘的态度是相似的,丝毫不以为耻。如果说金定与满生同意入赘皆是因为家贫(满生虽出自大族,但家资已被其败光),那《张员外义抚螟蛉子》中的刘安住,其义父广有田宅,够他一生受用,完全不用委屈自己入赘妻家。据笔者初步统计,“二拍”中刻画的士人,明确指出入赘妻家的有7人,按说这些士人都是熟读四书五经之人,“入赘”一事在古代为人所不齿,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入赘”妻家,这其中固有些许夸张成分,但也可见晚明社会“入赘”一事虽不能说是稀松平常,至少并不如历史上那么为人所唾弃。
晚明时期士人与妓女的交游与婚恋关系,也构成了晚明一道奇特的风景。晚明时期在商品经济活跃、阳明心学盛行等因素的影响下,向往个性,追求自我意识的风潮在社会上席卷开来,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社会的理念。商传先生认为晚明是一个追求人文主义的时代,其核心便是以人为本。[18]这一理念投射到士人身上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抛却传统礼教,无视世俗非议,大胆追逐才华出众的名妓,甚至情愿迎娶名妓为妻妾。如冒辟疆在董小宛脱籍后与其喜结良缘,钱谦益更是以匹嫡之礼迎娶柳如是。这一点在“二拍”中也有所体现,《硬勘案大儒争闲气》中的秀才陈亮,赋性慷慨,有意要娶妓女赵娟,两个人商量了几番,也彼此乐意。《赵司户千里遗音》中赵不敏与名妓苏盼奴情投意合,但阴差阳错之下两人天各一方,不能相见,害相思病而亡,死前将盼奴的妹妹苏小娟托付给堂兄赵不器,成就二人姻缘,赵不器与苏小娟伉俪终老。《小道人一着饶天下》中王维翰与上厅行首(即官妓中班行之首)谢天香以书法相交,两相企羡,在乡里父老的撮合下结为夫妇,偕老终身。
“二拍”中的士人与名妓交游,始于慕其姿色,又以诗文书画等文化活动为纽带,两情相悦,情到浓处时便愿娶妓女为妻妾,固然这其中不乏有夸张和想象的成分,但也是晚明社会生活和士人反叛传统的开放观念的生动反映。无论是对于“入赘”妻家的习以为常,还是对于娶妓为妻妾的离经叛道,都体现了晚明时期士人独特的婚姻观,他们不再以传统伦理束缚自身,而是大胆追求幸福,只要两人相爱,那么无论是“入赘”还是娶妓为妻妾,都已经不是他们所看重的了。
三、“二拍”中晚明士人的科考与仕途
即使晚明商品经济活跃,商业地位有所提高,士人生活日益贫困化,部分士人甚至因为生活所迫放弃举业,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直接武断地认为晚明士人就不重视科举,从整个明代来说,弃学经商之风也并未动摇科举的地位。
(一)科举之路
“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学而优则仕”这一理念自古以来便坚定不移地存在于士人心中,科举也因此成为士人特殊的生存方式以及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一个贫士,只要金榜题名,就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二拍”中也指出科举在中国古代举足轻重的地位,“世间唯有科举,可以使贱的立贵,贫的立富;难分难解的冤仇,可以立消;极险极危的道路,可以立平。”[6]305如《通闺闼坚心灯火》中的赵琮本是个寒酸秀才,屡试不中,宗族中没有一个不轻薄他的,一朝及第,亲友态度立变,讨好吹捧,个个争先,顷刻之间的变化,令人叹为观止。同卷张幼谦家向罗仁卿求娶罗惜惜时,罗仁卿回道:“若他要来求我家女儿,除非会及第做官,便与他了。”[6]309张幼谦家虽世代儒家但是家道艰难,罗仁卿家虽是白屋人家但家事富厚。在晚明社会,财富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张家虽是书香门第,但想要求娶罗家的女儿也绝对算是高攀。而在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下,只要张幼谦科举及第,罗仁卿便愿意将女儿下嫁给张幼谦,可见当时社会对科举的重视。当张幼谦与罗惜惜无媒媾和被罗仁卿夫妇抓奸,告到县衙,眼看一对有情人将被拆散,魂断一方,张幼谦乡试得中的消息使得事情出现转机,最终张幼谦被衙门释放,与罗惜惜终成眷属。
从上述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科举成功对于士人人生的影响,明初尚能三途并用,许多名公大臣不由科甲出身,也能替朝廷建功立业,青史留名。迨至晚明时期,不由科举进入官场之人,很难谋得好的差使,其仕进之途也更是困难重重。钱谦益曾说过:“今天下独重进士科,以进士起家者,譬如洛阳之花,一出于畦塍则以享朱门幄帘之奉,其由他途者,则不能也。”[19]凌氏同样借《华阴道独逢异客》中李生之口述说了当时社会对科举入仕之推崇:“一歇了手,终身是个不第举子。就侥幸官职高贵,也说不响了。”[6]440明代不仅对参加科举人员的身份限制相对减少,而且又有很多的优待政策,例如“两榜乡绅,无论官阶及田之多寡,决无签役之事”[20],不仅“见任及以礼致仕官员,照例优免杂泛差徭”[17]224,生员一旦登科便迅速发展为田连阡陌、家藏万贯的富豪。这些政策上的倾斜,使一大批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科举之中。张岱《夜航船》序言中记载:“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20]从中可管窥晚明社会对科举之推崇,凌氏在“二拍”中指明“如今世人一肚皮势力念头,见一个人新中了举人、进士,生得女儿,便有人抢来定他为媳,生得男儿,便有人捱来许他为婿。”[6]94因此晚明时期虽然因为商品经济繁荣,人们的思想发生改变,有部分士人甚至因为种种原因放弃科举,但这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晚明的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历史的发展依旧具有其惯有的稳定性,从整个晚明社会来说,弃学之风并未能够对科举制度起到明显的冲击作用,世人对于科举入仕依旧十分推崇,这在“二拍”中也有明显表现。如《赵六老舐犊丧残生》中赵聪六七岁时,赵六老便为其延请老成名师,等十四岁读完经书后,家事耗尽,更是不惜借贷延师。此外,“二拍”中还有许多故事发生在举子赴考之中。如《程元玉店肆代偿钱》中“崔妾白练”的故事背景就是崔慎思在应进士举的过程中;《闻人生野战翠浮庵》中闻人嘉也是在赴考途中与静观相遇。“二拍”中大量科举情节的出现,既是凌氏“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体现,也反映了明代重视科举的时代特色。
伴随着对科举推崇之风的兴起,参与科考人数激增,士人群体也随之扩大,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社会化,但也给科举体制带来了沉重的压力。投身科举的人数过多和录取比例的偏低,容易导致士人对科举制度失去信心,心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甚至产生“要想科举及第,只凭借命中福分罢了”[6]432的消极思想,以及走捷径而获得科举成功的幻想。如《华阴道独逢异客》中注定中举的有人相助的,有鬼帮衬的,而有那不该中的,任你考前做好万全准备,也终是不得中的。此外,上述故事还从侧面表现了晚明科场舞弊之风的盛行。商传先生在宁波的讲座《是谁误读了晚明史》中曾说过:“存在这样的考试,即使管理再严,也无法禁绝舞弊之事的发生。”何举人偶遇大主考的书办而得到考题得以高中;浙江士子交白卷遇到弥封所两个进士知县“技痒”帮答题得以高中;李君科举屡试不第,酒馆遇到侍郎家的公子卖考题而得以高中。以上种种表面上是在说命中注定得以高中,即使没有与之匹配的才华,也有鬼神相助,实际揭露了晚明科场舞弊之风的盛行。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环境中,无“关系”的基层士人更难有所寸进。凌氏在“二拍”中借笔下士人之口将对科场黑暗的愤懑、无奈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却说那梁宗师是个不识文字的人,又且极贪,又且极要奉承乡官及上司。前日考过杭、嘉、湖,无一人不骂他的,几乎吃秀才们打了。曾编着几句口号到:‘道前梁铺,中人姓富,出卖生儒,不误主顾。’又有一个对到:‘公子笑欣欣,喜弟喜兄都入学;童生愁惨惨,恨祖恨父不登科。’”[6]97可见,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科举的公平性受到严重的摧残,以致出现“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22]的局面。在明朝重科举之风气的推动下,士人对科举成功的期盼已达到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但晚明科举流通机制的壅滞、竞争压力的加重与科举公正性的破坏,又使士人清醒地认识到科举及第的困难,以致产生是命运而非才能决定能否中举的消极思想和企图走捷径获取成功的幻想。
(二)为官之途
然而,即使士人能够通过竞争激烈的科考取得功名,此后也并不能高枕无忧、一帆风顺,科举及第只是通向官场的第一步。为官后首先要解决的依旧是生计问题,明代官员的俸禄十分微薄,且大明宝钞因不设抄本,发行额度没有限制,迅速贬值,实际上进一步减少了官员的工资,后期虽然宝钞废除,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晚明奢靡、竟奢之风盛行,官员工资完全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如《李克让竟达空函》中的李逊喜中新科进士,授钱塘县尹,为人清方,然而到任不到一个月得病去世,所遗留的财产甚至不足以安顿妻子的生活。同书卷的襄阳刺史裴安卿,一心要做个好官,死后甚至需要女儿卖身葬父。此困窘之状况让许多人望而生畏,故很多官员走上了贪污受贿的道路,但这一旦被发现轻者从此无缘官场,重者流放死刑也比比皆是。
此外,晚明官员的升迁之路也十分不易,统治阶级对钱财索需无度,大肆进行卖官鬻爵,这在整个社会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地方官为了获得更好、更快的升迁方式,不惜重金贿赂朝廷官员。许多官员入京等待选官都会带上许多财产,以便能够顺便谋得较好的官职,如《沈将仕三千买笑钱》中的沈将仕在赴京听调的过程中就带了许多金银宝货在身边。《赵县君乔送黄柑》中的宣教郎吴约自韶州录曹赴吏部磨勘,“家本富裕,又兼久在南方,蓄积奇货颇多,尽带在身边随行”[9]165。小说中虽未直接点明他们给官员行贿,但入京选官时带上大量的金银珠宝,奇珍异货,如果说只是为了在京期间的生活,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而《华阴道独逢异客》中李君的父亲是松滋令,家事颇饶,带着宦囊到京营求升迁,因病死客邸、宦囊一空导致门户萧条。小说中对这一情节的描写很能反映现实生活,李君家本家资颇厚,但因其父亲宦囊丢失就门户萧条,说明李君的父亲随身带着一笔不小的财产,而到京营求升迁带着巨额财产肯定是为了在官场上打通关节,以寻求机会。除了用钱财为自己开辟一条宽广的仕途外,在官场上有一定的人脉关系也会让仕途变得更加顺利。如上文所提及的刘达生后来因为府尹的一力抬举,官途坦荡,仕宦而终。《李克让竟达空函》中的李彦青才同子建,潜心经史,一心希图上进,得刘元普扶持进入国子学,后状元及第,一路仕途坦荡。而那些既无财产又无人脉的士人,即使选授了官位,一般也不尽如人意。
由上可见,由于晚明士人贫困化以及官场腐败的日益严重,士人的科举与仕进之途日益艰难,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的士人坚持着科举入仕的道路。“二拍”虽然是话本小说,不可否认其内容具有一定的夸张成分。但其作者处于晚明这样一个大时代中,作为晚明时期士人的一份子,他对于晚明科举与士人仕途的看法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而且小说对于士人的生活处境,具有更加深刻的刻画,能够让我们对于晚明士人的科举与仕途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
四、结语
“二拍”问世以来便风靡一时,它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极大追捧正在于其对社会百态的真实反映。“二拍”中的士人与传统小说中的士人有着明显差异,他们不再高高在上,不知人间疾苦,而是走下神坛,具有了世俗人的特性。“二拍”中的士人依旧拥有俊秀的外貌,渊博的学识,传统社会所推崇的品格在他们身上依旧有所体现,但他们又多了一些小市民的狡黠和聪敏。在晚明这样一个激荡变革的时代,他们能够善于运用智谋保全自己。在这样一个变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他们既守有传统士人的信念,孜孜不倦地追求科举入仕,但同时他们也能面对现实社会,通过不同方式来维持生活。在婚恋问题上,他们勇于追求爱情,只要两情相悦,他们并不在意是“娶妻入门”还是“入赘妻家”,而在与名妓交往时,他们敢于抛却传统礼教,无视世俗非议,愿以才情出众、气质高雅的名妓为妻妾。“二拍”中士人的特性既是凌濛初生活感悟和价值观的表现,同时也是世俗社会士人形象在小说中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