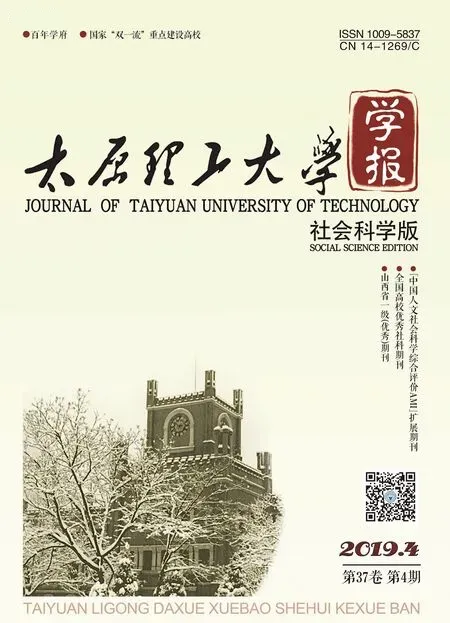孝道中的经与权:从“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谈起
樊智宁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孝作为一种德性在人的自身修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孝经·开宗明义》有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1]2545可见,在儒家看来,孝不仅是培养其他德性的根基,同时也是人伦教化的本源。许慎《说文解字》释孝曰:“善事父母者也,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2]171从文字训诂上来看,孝的本义强调子女应当侍奉父母的起居,秉承父母的命令。《尔雅·释训》亦曰:“善父母为孝。”[1]2591儒家所倡导的孝道就是重视孝德、提倡孝行,并且逐步将其理论化、体系化,形成一套理念和规范。
然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孝道往往会遇到许多伦理困境,即当孝道与其他的事物或价值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人们应当如何抉择才能应对这类复杂的问题。在儒家看来,这就涉及了经权思想。所谓经者,“织也”[2]272,原意指编织物的纵向线,后引申为天地之间恒久不变、颠扑不破的原则。所谓权者,“黄华木也……一曰反常”[2]112,原意指常用于秤杆和锤柄的黄华木,后引申为权衡和权变,也有与常事相反的意思。具体到孝道而言,孝道之经,就是要求子女应当敬重、关爱、顺从父母;孝道之权,就是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中,子女可以通过变通的方式解决孝道与其他事物的矛盾。对儒家所倡导的孝道,人们往往将其理解为诸如“卧冰求鲤”“埋儿奉母”“卖身葬父”等极端行为,实际上这都是对孝道的误解和偏见。儒家所倡导的孝道绝不是对父母无条件地言听计从、逆来顺受,更不可能赞同以伤害自己身体和儿女为代价来侍奉父母。相反,这些行为都是儒家所反对的愚孝。在《春秋》中有“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之经文,结合“春秋三传”对这段经文的解释和《礼记》中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对儒家所倡导的孝道及其经权问题略作管窥。
一、晋献公杀子与申生愚孝
“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之经文见于鲁僖公五年,经文背后的历史事件则是晋国太子申生遭骊姬诬陷蒙上意图弑父之名,晋献公亦听信骊姬的谗言欲杀死申生。《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了申生从出逃到自杀的传文。
大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1]1793-1793。
次年春,晋献公使人赴鲁告知杀世子申生之故。《春秋》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之经文斥责晋献公,恶其杀子之行。《谷梁传·僖公五年》释曰:“目晋侯斥杀,恶晋侯也。”[1]2393《谷梁传》认为,《春秋》书“晋侯”目的在于贬斥晋献公杀死申生,以表达圣人对晋献公的厌恶。杜预承接《左传》对这一事件本末的记叙后,解经曰:“称晋侯,恶用谗”[3],即《春秋》书“晋侯”是厌恶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罔杀了申生。但是,杜预的解释依然有含混不清的地方,他没有解释《春秋》究竟是从君臣关系的角度还是父子关系的角度批评晋献公。对此,《公羊传》的解释最为明确。《公羊传·僖公五年》释曰:“曷为直称晋侯以杀?杀世子母弟,直称君者,甚之也。”[1]2250《公羊传》指出,晋献公的罪恶在于杀死世子。因此《春秋》直书“晋侯”,其用意在于谴责晋献公杀子,这是基于父子关系角度的批评。除了批评晋献公之外,儒家对申生的做法也不认同。晋献公杀子的罪名之所以成立,申生也难辞其咎。《礼记·檀弓上》有一段“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的记载,其中折射出了儒家对申生所作所为的批评。
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盖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弑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于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爱其死。虽然,吾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也[1]1276-1277。
《礼记》中的这段叙述与《左传》大体相似。从申生与他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两点。其一,申生在自己能够自证清白的情况下甘愿背负不孝的罪名,他不忍看到父亲伤心,坚持他自己所谓的孝道。其二,申生在可以出奔他国的情况下选择留守国内,顺从父亲的命令甘心受戮。由于这两点,使得申生的谥号为“恭”而非“孝”。郑玄注曰:“言行如此,可以为恭,于孝则未之有。”[1]1277孔颖达更加深入地讨论申生的谥号问题,阐明儒家对申生的批评。其疏曰:“父不义也,孝子不陷亲于不义,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杀子之恶。虽心存孝,而于理终非,故不曰孝,但谥为恭,以其顺于父事而已。”[1]1277换言之,晋献公误信谗言欲杀申生本已属于不义之举,申生应当在父亲面前申辩或是立即逃亡他国避祸,而非拘泥于孝道致使晋献公杀子成为现实。因此,在儒家看来申生的行为只能算是顺从父命,只能谥其为“恭”而不能谥其为“孝”。
结合“春秋三传”对“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的解释和《礼记》中“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的记载,能够发现儒家对晋献公和申生都是持批评态度的。《春秋》憎恶晋献公听信谗言犯下杀子的罪行,《礼记》则否定了申生的愚孝,并且,申生的愚孝与晋献公杀子是一对因果关系,正是申生的愚孝使得晋献公杀子成为现实。质言之,《春秋》通过直书“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来“借事明义”。国君杀世子之所以罪大恶极也是基于“亲亲”之义的角度做出评判。
二、基于“亲亲”之义的归咎
汉儒解《春秋》以公羊学为盛,在公羊家看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的书法是《春秋》基于“亲亲”之义归咎于晋献公,董仲舒首开此种解释的先河。他在其《春秋繁露·王道》中有论曰:“杀世子母弟直称君,明失亲亲也。”[4]115董仲舒是汉代治公羊学之大家,在其之后的汉代公羊学家基本继承了董仲舒的观点。杨终云:“《春秋》杀太子母弟,直称君甚恶之者,坐失教也。”[5]何休对《公羊传·僖公五年》相应的传文作注,亦曰:“甚之者,甚恶杀亲亲也。《春秋》公子贯于先君,唯世子与母弟以今君录,亲亲也。今舍国体,直称君,知以亲亲责之”[6]396。与君臣、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不同,父子和兄弟属于“天伦”。换言之,这两种关系不需要通过人为地构建,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子和兄弟这两种伦理关系比君臣、夫妇、朋友更为基础。因此,《春秋》对于杀死世子与母弟的行为深恶痛绝。事实上,春秋时期国君杀死世子与母弟的事件屡见不鲜,《春秋》的书法也与“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相同。鲁隐公元年、鲁襄公二十六年、鲁襄公三十年皆有经文从此例,如“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1]2198。“秋,宋公杀其世子痤。”[1]2311“天王杀其弟年夫。”[1]2313-2314
郑庄公杀弟(1)“郑伯克段于鄢”事例中,郑庄公虽未实际上杀死弟弟共叔段,但《公羊传》认为“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左传》认为“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杜预注左氏此解曰:“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于杀,难言其奔。”《谷梁传》认为“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三《传》观点相同,皆以郑庄公实有杀死共叔段之心,故《春秋》从其意,以杀母弟例书之。、宋平公杀子、晋献公杀子及周景王杀弟(2)清人苏與以为“世子痤、年夫事不详《传》。以直称君之例推之,则痤与年夫同为无恶。莒杀意恢不称君,则知罪在意恢。《春秋》之义,贵人道,防乱端,二者并重。义在防乱,则虽季子杀母兄,亦为之讳。义在重人,则虽天王杀弟,同直称爵”。此说恐不尽然。《公羊传·襄二十六年》何休注云:“座有罪,故平公书葬。”徐彦疏曰:“《春秋》之例,君杀无罪大夫及枉杀世子者,皆不书葬,以明其合绝,是以申生无罪,不书献公之葬,至昭十一年经云‘叔弓如宋,葬宋平公’者,正以痤有罪故也。”故知是否直称君爵与公子是否有罪无涉,凡杀世子与母弟者皆直称君爵。这四条经文皆以书国名和爵位的体例彰显国君杀世子或母弟之恶。因此,清人苏與论曰:“是知子弟无罪,父兄不得杀子弟。虽有罪,父兄抑不忍辞其咎,所以明失亲亲也。圣人仁天下之义,至此而尽矣”[4]115。至于国君杀死世子之事(3)何休《公羊传·隐公七年》注曰:“《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表明《春秋》尚质,重亲亲,故而对公子与母弟甚为亲厚。本文仅讨论公子,故对母弟问题不再赘述。,《春秋》之所以“亲亲”之义大张其恶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国君杀死世子相当于断绝先君之嗣。陈立《公羊义疏》注引包氏慎言曰:“杀太子者,不得入先君之兆,绝先祖之嗣,故绝之于先祖也。”[7]1116由于以农业耕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和以血缘亲族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中国古代的家庭与社会制度带有浓厚的宗法制的色彩。在传统社会中的个人不但肩负家族血脉的传承,同时本身也是家族血脉的传承者,传宗接代就成了传统中国人家庭生活的头等大事,也是个人对家族最大的责任和义务。父亲如果杀死自己的子嗣,尤其是嫡长子,这对于家族的传承是十分不利的。在宗法关系的观点上来看相当于自绝于先祖,切断宗族延续的血脉。此外,按照周代宗法和分封制度,诸公子中的嫡长子是世子,直接继承国君之位,是未来的一国之主。其余诸子或分封至各地或为卿大夫,他们世代成为巩卫公室的公族。嫡长子继承制需要强化世子的地位,削弱其余诸子的力量。正是这种强干弱枝的制度保证了嫡庶分明,才能维持公室宗族内部的相对稳定。如果国君杀死世子,那么势必导致其余诸子和公族争夺君位,这种情况对国家社稷而言是相当不利的。
其二,国君杀死世子也是弃绝天道、违背天理的行为。《白虎通·诛伐》有云:“父煞其子当诛何?以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皆天所生也,讬父母气而生耳。王者以养长而教之,故父不得专也。”[8]《白虎通》是从自然领域和政治领域两个角度讨论父杀其子为什么应当被诛伐的。从自然领域的角度来看,万物皆是从天地之间阴阳二气化生而成,其中以人最得天地灵秀。每个人都是自然界所造化而成,借助父母之精气来到这个世界。诚然父母对子女有生养和教化的恩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子女是父母的私有物或附属品,父母没有专擅之权任意剥夺子女的性命,换言之,只有作为自然本身的天才有权剥夺人的性命。从政治领域的角度来看,人不仅为父母的子女,同时也是天子的子民。作为天的代言人,只有天子能够享有专杀之权。《公羊传·襄公三十年》何休注曰:“王者得专杀。书者,恶失亲亲也。”[6]892徐彦疏曰:“诸侯之义,不得专杀大夫。若大夫有罪而杀之者,皆恶于专杀,是以书见。今此天王也,自得专杀,若杀大夫,宜不书之,书者,以其未王而杀母弟,失亲亲,故恶而书也。”[6]892从何休与徐彦对《春秋》天子和诸侯专杀大夫书例,可以看出专杀之权仅属于天子。由此可见,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无论在自然领域还是政治领域都是有恶的。
“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之例中,申生并非全无罪责。对此,汉儒同样基于“亲亲”之义归咎申生,他们认为申生之愚孝实为不孝,申生之不孝则在于陷父不义。《左传·桓公十六年》有卫宣公杀其世子急子一事,汉儒将其与申生之死相联系。
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将杀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于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杀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请杀我乎!”又杀之[1]1758。
急子与申生所面临的困境相同,但是他与申生都选择顺从父命。司马迁曰:“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或兄弟相灭,亦独何哉?”[9]在司马迁看来,由于急子和申生的愚孝,他们都需要为父亲杀子这类悲剧承担责任。此外,在《孔子家语·六本》中有“曾子耘瓜”的典故,对陷亲不义之罪亦有所发挥。曾子耘瓜时误把瓜藤耘断,其父曾皙暴怒,杖责曾子。曾子挺身受杖直至昏死,孔子闻知此事便不让曾子进门,曾子向孔子求解。孔子曰:“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释“不孝有三”引汉儒赵岐所注,曰“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也”[11]292。由此可见,在面对父母之命与自身性命的伦理困境中,汉儒强调子女应以自身性命为重,反对所谓的恪守孝道。因为一旦父母由于子女的逆来顺受而夺去子女的性命,这种愚孝就成为陷父不义、有损“亲亲”的不孝之举。
综上所述,汉儒以“亲亲”之义归咎晋献公与申生在于他们“杀子”和“愚孝”断绝了父子之伦。然而对于儒家的“五伦”来说,父子之伦在一定程度上是最为根本、最为核心的伦理关系。父子之伦相对于其他四伦具有两个特点,即必然性与普遍性。所谓必然性不单是指父子之伦是自然而然的产生,不需要人为构建,而且指它是每个人必然与生俱来的。在自然而然产生的两种伦理关系中,父子之伦比兄弟之伦更为根本,父子之伦是兄弟之伦的前提,兄弟之伦也需要依附于父子之伦才得以存在。所谓普遍性是指父子之伦不仅是人与生俱来的,并且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兄弟、夫妻、朋友和君臣这些伦理关系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这些伦理关系往往由具体的家庭生活情况和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而父子之伦并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只要人类不断地自然繁衍,父子之伦是普遍必然存在的。
三、守经与行权:伦理困境的解决方案
儒家对经权问题的涉及可以追溯至孔子。在《论语·子罕》中,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1]249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此条引程颐之言曰:“权,称锤也,所以称物而知轻重者也。可与权,谓能权轻重,使合义也。”[11]116这是儒家最先提出关于“权”的说法。作为儒家解决伦理困境的理论,经权思想被应用于诸多领域,关于孝道的问题亦无出其右。
(一)守经:孝道中的“顺从父命”
儒家的孝和孝道自孔子和孟子以来一直与“顺从父命”相关联。譬如“无违父命”“从于父志”“无改父道”等观念都与孝和孝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现当代,人们对儒家的孝和孝道依然持相同的看法。蔡元培论孔子之“孝”时曾言:“夫至以继志述事为孝,则一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皆得统摄于其中矣。”[12]张锡勤论及儒家的孝道时亦认为“孝道乃是建立在父子人格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它要求子女对父母必须顺从”[13]。诚然,儒家的孝在其本源的含义上的确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孝道也确实强调子女对父母单方面的顺从,我们从儒家的根源性经典中就能看到诸多类似的例证,如“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1]2471“违命不孝,弃事不忠。”[1]1789“从命不忿,微谏不倦,劳而不怨,可谓孝矣。”[1]1620“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1]2723
可以看到,儒家的这些经典皆有以“不违”“从命”“顺亲”等词语定义孝,使得孝被称为“顺德”,孝道的内涵被也认为是“顺从父命”。按照此种定义来衡量“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之事,申生自尽虽然有损“亲亲”之义,但他不违父命绝对称得上是孝子。这就与《礼记》的记载以及汉儒的观点产生了矛盾。
然而,儒家正是用经权思想来解决这一矛盾。与正常父子关系不同,“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这一案例具有其特殊性,即申生处于一个伦理困境之中。因此,申生就不能依照常规的准则践行孝道。换言之,顺从父命是在正常情况下践行孝道的方式,是守经;保全自身性命则是在申生所处的特殊情况下践行孝道的方式,是行权。
儒家思想具有明显的实践哲学的特征,它所讨论的问题不仅是抽象的理论论证,对于日用伦常来说,也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作用。因此,儒家在孝道的问题不可能没有考虑到实际生活的具体情况及其应对方式,更不可能迂腐到要求子女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顺从父母之命。譬如荀子就对子女可以不从父母之命的情况有所论述。
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14]。
所谓“衷”者,善也。荀子列出了子女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从命”,即从命则“亲危”“亲辱”和“禽兽”。在正常的情况下子女顺从父母之命是孝,忤逆父母则是“不子”。在以上三种情况下子女还选择顺从父母之命,那么子女就是行不善之事了。在“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之事中,申生自尽在荀子看来属于“从命则禽兽”的范畴。因此,申生顺从父命便不是践行孝道而是不善之举。
儒家主张以守经和行权的方式践行孝道并非是将孝道割裂。从守经的视角审视孝道的内涵,我们还能够发现孝不仅是顺从父母之命,它同样包含了保全自身性命的内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保全自身性命是实现一切孝行的基础。《论语·泰伯》有一章关于曾子的事例。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1]2486
后世的解读认为此章是讲曾子终其一生践行孝道,直到自己临终前亦不忘教导门下弟子。曾子令弟子们开启被衾确认他的手足是否俱在,就是在阐明孝道之义在于不能毁伤自己的身体。曾子又引《诗》告诫弟子,就是在阐明子女应当时时戒惧、谨小慎微,切不可轻易毁伤身体。孝道的这一含义在《孝经》中则得到深层次地发挥。《孝经·开宗明义》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2545在《孝经》的这段文字中有两次提到了孝道之始的问题。其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是基于自然状态与生命状态视角的论断。邢昺注曰:“夫为人子者,先能全身而后能行其道也。”[1]2545换言之,子女只有先保全自身的性命才有可能完成之后的各种孝行。如果人自身都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中,或是由于肉体的残缺而不能活动,那么人是不能够亲身践行孝道。其二,“夫孝,始于事亲”,这是基于道德行为视角的论断。《孟子·离娄上》有言:“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1]2722孝是一种德性,实践这种德性的行为在于能“事亲”,“事亲”的前提则是“守身”。结合《孝经》和《孟子》的内容,儒家所谓的孝道之始,一言以蔽之,“守身”也。
孝和孝道尽管在儒家看来确实包含了顺从父母之命的含义,但是这只是在父母之命合乎于道义情况下的守经,不能够将其作为普遍化的伦理规范理解。孝和孝道作为可实践的伦理规范是不可能脱离具体情况的,在这些具体情况中儒家支持以行权的方式践行孝道。此外,顺从父母之命也只是孝道的一个方面,孝道也有强调“守身”的内容,并且在儒家看来,“守身”比顺从父母之命更为重要。
(二)行权:孝道中的“反经为善”
考察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在孔子提出“权”的说法后,对行权问题的讨论在孟子和《公羊传》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吴震认为行权问题“主要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孟子的‘嫂溺援之以手,权也’,一是《公羊传》‘权者反于经’”[15]24。其中,孟子最先论及“经”与“权”的辩证关系。在《孟子·离娄上》中,孟子与淳于髡之间有一段关于“男女授受不亲”和“嫂溺援之以手”的问答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1]2722
孟子的这段话不难理解,“男女授受不亲”是人伦之大防、世间之常理,是“经”也。“嫂溺,援之以手”则是以救人性命为目的,从而避轻就重的选择,是“权”也。质言之,孟子认为行权乃是在人们遇到伦理困境的时候可以进行变通的原则,是人们在道德行为实践中应当被正视的应变方法。此外,《公羊传》对经权问题也有具体的讨论。
鲁桓公十一年,《春秋》有“宋人执郑祭仲”之经文,《公羊传》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对“祭仲行权”(4)关于“祭仲行权”之褒贬问题可谓聚讼纷纭。《左传》仅述其事,并未作价值判断。杜预注曰:“不称行人,听迫胁以逐君,罪之也。”亦并未言及“行权”。《谷梁传》曰:“祭仲易其事,权在祭仲也。死君难,臣道也。今立恶而黜正,恶祭仲也。”范宁注曰:“易辞,言废立在己。”故而《谷梁传》言祭仲之“权”乃是掌权之义,与“行权”无涉。三《传》中唯有《公羊传》言及“行权”,并以“祭仲行权”为贤。有所论述。祭仲是郑国的大夫,郑庄公去世后他遵从庄公遗命拥立太子忽即位,是为郑昭公。然而,宋庄公支持郑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突。于是,宋庄公派人引诱祭仲至宋国并扣押了他。宋庄公要挟祭仲驱逐郑昭公改立公子突为君。祭仲考虑到如果此时不听从宋庄公的要求,郑昭公君位不仅不保,郑国的江山社稷也危在旦夕。于是,祭仲以行权的方式答应了宋庄公的要求,立公子突为君,是为郑厉公,郑昭公因此也逃亡卫国。对此,《公羊传》论曰:
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1]2220。
《公羊传》的这段话对行权提出三个具体的规定。
其一,“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这是《公羊传》对行权的基本定义。这个定义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行为内容上来看,行权的具体行为与守经相反;另一方面,从行为的后果上来看,行权所造成的结果必须是良善的。
其二,“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舍”。何休注云:“设,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6]173何休这里的“死亡”并非是指祭仲的生死,而是指郑昭公和郑国社稷的存亡。换言之,行权只考虑结果是否会给行权对象带来“死亡”,但是行权是否要考虑行权人的“死亡”,《公羊传》和何休都没有讨论。清儒陈立则对这个问题做出解答,其疏曰:“如杀身成仁之属,有死无二,不得藉权自饰”[7]584。显然,在行权人和行权对象都面临生死存亡的矛盾之时,行权只考虑行权对象而不考虑行权人自身。
其三,“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这是从行为方式的视角上对行权进行规定。《公羊传》认为行权可以在行权人自我贬损的基础上进行,但不能够以损害他人的方式行权。质言之,行权不能将他人当作手段,他人在行权的具体行为中只能被当作行权对象,即作为目的而存在。
按照上述的三条规定审视“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之事,申生无论是选择自我辩解还是出奔他国,都符合儒家的行权。首先,申生的两个选择皆与“顺从父命”相悖,属于“反经”;同时,申生既能保全自身性命又不至于陷父不义,是良善的结果。其次,申生的两个选择都不会造成父亲和国家处于“死亡”的局面。再次,申生选择出奔可能让自身蒙受污名,但这属于自我贬损,并不危害他人。因此,申生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辩解或出奔他国的方式行权,从而实现孝道。
综上所述,孝道中的行权可以理解为“反经为善”,这是解决子女面临顺从父母之命与保全自身性命产生矛盾时的解决方案。此外,行权同样可以用于解决其他的伦理困境。然而《公羊传》所言之行权在后世的解读中往往被曲解。由于片面地强调“反经”,忽视“善”的结果,使得行权在具体实践中“有可能背离纲常伦理而沦为权术或权谋”[15]。实际上,汉儒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警觉。《春秋繁露·玉英》曰:
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钜经耳[4]76-77。
虽然董仲舒所讨论的“权”是关于《春秋》对诸侯之褒贬,但是在普遍的人伦日用领域也同样适用。由于行权带有一定谲诈的可能性,容易被人误用,故而董仲舒划分“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以规制行权。在“可以然之域”允许行权,“不可以然之域”只能守经。总而言之,守经和行权其目的都是追求至善。行权是填补守经所难以产生效用的领域,所以“权”与“经”的精神是内在同一的。
(三)汉宋经权思想的区别与孝道的变化
汉儒与宋儒经权思想的区别甚大,宋儒批评汉儒以“反经合道”释“权”,使得“经”与“权”彼此分化、相互对立,守经和行权成为两种各自独立、不相干涉的行为。因此,宋儒认为汉儒对“权”的理解势必导致行权成为追求权术和权谋,经权思想也沦为阴谋之论。宋儒的经权思想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论语·子罕》“可与立,未可与权”曰:
程子曰:“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愚按:先儒误以此章连下文“偏其反而”为一章,故有反经合道之说。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11]116。
程颐和朱熹皆以为汉儒误读孔子“未可与权”之义,也皆反对汉儒“反经”之说。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程颐认为“权只是经”,守经和行权是一回事。朱熹对程颐的观点有所保留,他认为依照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的说法,守经和行权作为实际的道德行为还是应当有所区别的。这里首先分析程颐“权只是经”的观点。
古今多错用权字,才说权,便是变诈或权术。不知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权只是秤锤,称量轻重。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16]234。
世之学者,未尝知权之义,于理所不可,则姑曰从权,是以权为变诈之术而已也。夫临事之际,权轻重而处之以合于义,是之谓权,岂拂经之道哉?[16]1176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对程颐的“权只是经”做出以下总结。其一,“权”并非是与“经”相对的事物,而是衡量行为是否合乎道义的尺度。行权指的也不是与守经相反的行为,而是指在实践具体行为之前审视行为是否正当的过程。其二,“权”应用的范围是“经”所不及之处。换言之,“权”是“经”的派生,行权的目的亦非是应对伦理困境,而是为了守经。其三,“权”需要合于义,而所谓的义就是“经”所规定的正当行为,这就使得行权成为守经的附庸,二者不再是能够等量齐观的关系。再看朱熹对“经”与“权”关系的论述。
以义权之,而后得中。义似称,权是将这称去称量,中是物得其平处[17]987。
但经有不可行处,而至于用权,此权所以合经也,如汤、武事,伊、周事,嫂溺则援事[17]987。
权者,乃是到这地头,道理合当恁地做,故虽异于经,而实亦经也[17]988。
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17]989。
权与经固是两义,然论权而全离乎经,则不是。盖权是不常用底物事。[17]991
以上几个例子基本能够体现朱熹的经权思想,尽管朱熹批评“伊川说‘权只是经’,恐也未尽”[17]992,也曾说“汉儒说‘反经合道’,此语亦未甚病”[17]992。朱熹的态度看似暧昧不清,实则立场鲜明。他对“经”与“权”的论述基本按照程颐的思路展开的,其结论一言以蔽之,“权亦是经”。
然而,程颐和朱熹评价汉儒的经权思想解释皆有失偏颇。汉儒对“权”的定义是“反于经,然后有善者”,程颐和朱熹只关注“反经”却忽略了“善”。换言之,他们将汉儒“反经为善”错误地理解成“反经合道”,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只在毫厘之间。前者关注的是“反经”所造成的结果,后者关注的则更倾向于“反经”的动机。行为的结果易于评判,行为的动机则难以揣度,这也是为何“反经合道”会沦为权术、权谋的原因所在。此外,考察经权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反经合道”释“权”的并非汉儒,而是曹魏的王弼。他在解释“巽以行权”时注曰:“权,反经而合道。”[1]89质言之,程颐的“权只是经”和朱熹的“权亦是经”是由于误解汉儒“反经为善”所造成的。从他们对“经”与“权”的理解就可以管窥宋儒的经权思想,这种思想具体到孝和孝道之上也对其含义的变化产生影响。
在汉儒看来,“顺从父命”是孝道中的守经,保全自身是孝道中的行权。但是按照宋儒的经权思想将“权”与“经”看作一事,也就意味着子女行权将会消解融入“顺从父命”之中,这也使得孝和孝道在宋代之后逐渐僵化、极端,以下试举两例。张载《西铭》曰:
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18]。
张载列举禹、颍考叔、舜、申生、曾子和伯奇(5)伯奇之事见于曹植《令禽恶鸟论》:“昔尹吉甫用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事与“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相类。之事例,他对申生、曾子和伯奇宁死不违父命的行为表示赞赏,这就与汉儒的观点大相径庭。又罗从彦与陈了翁关于舜事亲的对话:
昔罗先生语此云:“知为天下无不是底父母。”了翁闻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后天下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于见其有不是处耳!”[19]
罗从彦认为世间父母没有不对的,陈了翁深以为然,并认为只有顺从父母才能安定天下,避免君臣父子相残。换言之,亦如程颐所言:“孝弟,顺德也,故不犯上,岂有逆理乱常之事?”[16]1133
综上所述,由于宋儒误解汉儒对“权”的理解,他们以将“权”等同于“经”的方式反驳“反经”之说。具体到道德行为的实践中,孝和孝道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因此,自宋代开始以“顺”释“孝”逐渐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主流,孝道也逐渐体现家长专制、剥夺子女独立人格的特点。
四、结语
孝和孝道在儒家伦理思想的最初含义中并非只强调子女对父母的顺从,同时也强调子女应当保全自己的性命。关于“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一事,《春秋》恶晋献公杀子,《礼记》评价申生不孝,实际上都是儒家基于“亲亲”之义的角度谴责他们违背人性和天道。此外,从《左传》和《礼记》的相关文字也不难看出,儒家也以经权思想给申生提供了能够解决伦理困境的方案。
儒家的经权思想一方面强调行为必须带来良善的结果,另一方面又包含“你要这样行动,把不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做目的,而绝不只是用作手段”[20]这种康德式的道德律令。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断定儒家的经权思想属于规范伦理学。但不可否认的是,儒家的经权思想的确带有后果主义和道义论的某些特征,并且它还将原本针锋相对的两种学说的部分内容综合在一起。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儒家的经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和两种规范伦理学的矛盾,其作为解决伦理困境的方案亦具有相应的特色和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