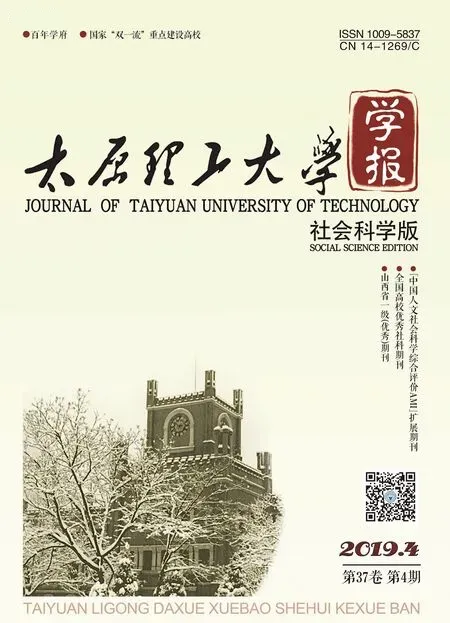朱熹“权”说论辨
刘小红
(宝鸡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朱熹言“权”承汉儒与程颐之权论,其“权”思想较之以往最具思辨性与体系性。他通过权与义、中、道的意义关联,对权之内涵做了深入的论解,但是其权说终究囿于其理学思想体系而有诸多不足与弊矢。
一、“经权亦须有辨”
可以说,朱熹论“权”基本上是通过对汉儒与程颐权论的臧否而展开的,通观其论,其中隐微曲折处颇多。对汉儒之权论,他一方面认为其“反经合道”之说,“程子非之,是矣”;另一方面又强调“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1]。在此意义上,朱熹认为“如汉儒说‘反经合道’,此语亦未甚病”[2]。朱熹此一表述看似“矛盾”,实则有其内在逻辑理路可循。在朱熹看来,汉儒与程颐之“权”论各有其合理点,亦有其不足之处,而朱熹则统合二者,合二为一,形成自己的“经权”理论系统。
程颐以“权便是经”为论,其发论之由在于对汉儒“权”论所生发之消极面的洞识,“古今多错用权字,才说权,便是变诈或权术”[3]。汉儒“反经”之说虽强调“合道”,但在实际应用之中却未能为“反经”做一明晰之界定,故而,“反经”或有之,“合道”则未必。因此,所谓的“反经合道”多是借托词。诚如张南轩所言:“后世窃权之名以自立,甚至于君臣父子之大伦,荡弃而不顾。曰吾用权也,不亦悲夫!”[4]有鉴于此,程颐强调“论事须著用权。不知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3]。程颐“权便是经”之论,意在反转汉儒“权”论之弊端,以“经”为行“权”做一规范,从而使其不离于道,所以程颐又言“能用权乃知道”。对程颐之“权便是经”论,朱熹深知其用意,“伊川见汉儒只管言反经是权,恐后世无忌惮者皆得借权以自饰,因有此论耳”[2]。就内容而言,朱熹一方面认为,“权者,乃是到这地头,道理合当恁地做,故虽异于经,而实亦经也。……伊川谓‘权只是经’,意亦如此”[2]。所谓“异于经”,当是指形式而言,毕竟经与权有不同之处,权是以另一不同于经之面目而呈现于世人。朱熹举例,冬日当以火取暖,但气温升高,使扇当风亦可,若前者为冬日所为之“经”的话,那么,后者就是“权”了。二者虽有异,但就其实而言,“亦经也”。无论是以火取暖,还是使扇当风都是为了身体之舒适,形式不同但实质无异。可见,二者是不离而合的,“经”是“权”的内涵本质,“权”是“经”的外在表现,故而,“合于权,便是经在其中”。因此,程颐之“权便是经”有其合理处。但另一方面,朱熹又认为程颐“但说‘经’字太重,若偏了”[2]。“伊川说‘经、权’字,将经做个大底物事,经却包得那个权,此说本好。只是据圣人说‘可与立,未可与权’,须是还他是两个字,经自是经,权自是权。若如伊川说,便用废了那‘权’字始得。只是虽是权,依旧不离那经,权只是经之变。……今须晓得孔子说,又晓伊川之说,方得。若相把做一说,如两脚相并,便行不得。须还他是两双脚,虽是两双,依旧是脚。”[2]就内在价值理念而言,经权在道德实践上是一致的,行权也就是行经,所以朱熹对程颐之“权便是经”论持赞同的态度,但“权便是经”的表述容易遮蔽二者在形式范域上的差异,造成对权的错解,以致以权代经,把权看作是经的一种常态,这有可能造成消极的后果。“权”虽合于“经”,但“权”毕竟是“权”,经权二者的范域是有其分界的,内在价值理念的一致并不意味着二者完全等同。所以朱熹认为,“晓得程子说底,得知权也是常理,晓不得他说底,经权却鹘突了。某之说,非是异于程子之说,只是须与他分别,经是经,权是权。……权是碍着经行不得处,方使用得,然却依前是前理,只是不可数数用。如‘舜不告而娶’,岂不是怪差事?以孟子观之,那时合如此处。然使人人不告而娶,岂不乱大伦?所以不可常用”[2]。在朱熹看来,“权”虽具合当性,但并不表明其可以像经一样作为日常之行为方式。毕竟,内在价值的相通不能掩盖其相异之实,经是常行之则,权则是暂行之法,故而不能以“权”代经。如“不告而娶”虽然合于“权”道,但亦只能是在个别情境中的个别行为,不能把其作为可以常行常为的规则。如果变“权”为“经”,不仅不是“经”道的体现,更有可能破坏“经”道之价值理念。在朱熹看来,依程颐之理路,确当的解说须是:“伊川先生所谓‘权便是经’,亦少分别。须是分别经、权自是两物;道德合于权,便自与经无异,如此说乃可”[2]。我们不仅需要知经、权之同,亦要明经、权之异,如此说方才是周通完满。
如果说程颐之失在于其反汉儒之“反经合道”的同时,又进入另一个极端,造成“权与经又却是一个,略无分别”[2]的话,那么在朱熹看来,“如汉儒之说权,却自晓然”[2]。当然,这里所谓之“晓然”是针对程颐经权无别而言,“汉儒‘反经合道’之说,却说得‘经、权’两字分晓”[2]。汉儒以“反经合道”言“权”,就其实而言是有其合理性的。“《公羊》以‘反经合道’为权,伊川以为非。若平看,反经亦未为不是。且如君臣兄弟,是天地之常经,不可易者。汤武之诛桀纣,却是以臣弑君;周公之诛管蔡,却是以弟杀兄,岂不是反经?但时节到这里,道理当恁地做,虽然反经,却自合道理。但反经而不合道理,则不可。若合道理,亦何害于经乎?”[2]虽说“经”为万世不可移易者,但以“时”而论“反经”亦不为不是。朱熹注意到在“时”之境遇中,“经”之行为方式的可转换性。“经”之“不易”是从历时性角度而言,其理念所体现之价值内涵是人所必须严守者,但在共时性之具体情境中,不易之经所面对变易之事时,则需以“变”来实现“不易”。这也就为行“权”找到了其合理性之依据。当然,“虽然反经,却自合道理”。这亦是行“权”所必须者,就此一点而言,朱熹肯定汉儒权论之合理意义;但另一方面,其弊端亦不容忽视,“汉儒谓‘权者,反经合道’,却是权与经全然相反”[2]。如果说程颐之经权相同论是以经权合一,那么汉儒之经权则正相反,视经权为二。在朱熹看来,这二者都有其可非难处,尤其是汉儒之弊,反于经之“权” 易于“一向流于变诈”,使得“权”仅成为权变、权谋、权术之代名词,而与其本义愈来愈偏离。
总之,对汉儒与程颐之“权”论,朱熹各论得失而不偏不倚,“汉儒谓‘反经合道’为权,伊川说‘权是经所不及者’。权与经固是两义,然论权而全离乎经,则不是。……大抵汉儒说权,是离了个经说;伊川说权,便道只在经里面。且如周公诛管蔡,与唐太宗杀建成、元吉,其推刃于同气者虽同,而所以杀之者则异。盖管蔡与商之遗民谋危王室,此是得罪于天下,得罪于宗庙,盖不得不诛之也。若太宗,则分明争天下。故周公可以谓之权,而太宗则不可也”[2]。汉儒以“反经”说“权”,却往往“反”而不“合”,但“反经”亦蕴含一定的合理性;程颐以“经”论“权”,虽去了汉儒之弊,然以“经”包“权”,而致经、权不分。朱熹合两是而去两非,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经、权”理论体系。
二、朱熹之“权”论
朱熹之“权”论体系是通过三个方面得以展开的:就经权关系言,“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就“权”与“义”“中”“道”之关系言,“以义权之,而后得中”,“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就行“权”之方式言,“见其动而不见其形”。
如前所言,汉儒与程颐所论之经权关系各有得失,朱熹去其蔽而取其利,对经权关系进行了辩证的论述。“经自经,权自权。但经有不可行处,而至于用权,此权所以合经也。如汤、武事,伊、周事,嫂溺则援事。常如春风和日暖,固好;变如迅雷烈风。若无迅雷烈风,则都旱了,不可以为常。”[2]首先,经与权自是不同,虽然行权亦合于道,二者本质相同,但就行为之范域而言,经是常行常为者,而权只能是行“经”所未至者。此一分疏为经、权划定分界,以避免经、权各失其情。其次,“伊川又云:‘权是经所不及者。’此说方尽。经只是一个大纲,权是那精微曲折处。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是经常之道,如何动得?其间有该不尽处,须是用权”[2]。朱熹很清楚在一个社会中,“经”只是保持个人与社会之间有序、稳定、和谐的整体关系之规范性架构,它具有纲领性,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丰富性又会使我们在行“经”时须面临重重挑战,其不能完全构成全部的现实生活,因此,就需要“权”来弥补“经”之不足,进而实现“经”之价值精神指向。就此一点而言,“权” 异于“经” 而又同于“经”:就相异处说,“权”是“经之所不及处”,“经”涵括万事却不能尽净无遗,而其“精微曲折处”须得行“权”以补足;就相同处说,二者虽有分界,可指向却殊途而同归,“经”所向者,道也,“权”所向者,亦道也。同异之间,我们还须明晓,何以“权”可补“经之所不及”?只因“权处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朱熹举例说“如君子小人,君子固当用,小人固当去。然方当小人进用时,猝乍要用君子,也未得。当其根深蒂固时,便要去他,即为所害。这里须是斟酌时宜,便知个缓急深浅,始得”[2]。由此亦可见得经、权关系的另一面向,行“权”之考量实是高于行“经”。“经”之所行只需依规矩即可,而行“权”则要“斟酌时宜”。可以说,“时”是“权”之一重要内涵关键点,而这一点在“经”之中表现并不明显。概而言之,朱熹把经权关系定位为“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2]。此论当是极有见地,一言可以涵盖汉儒与程颐之“权”说,既说明了二者之同,又标明二者之异。
就经、权关系言,不论是“反”,还是“合”,更多的指涉于形式层面,而其内在理论依据则与“义”“中”“道”相关联。“义”“中”“道”这些颇具理学色彩范畴的加入使朱熹“权”思想之理论体系得以建立。
朱熹解“可与权”为“遭变事而知其宜”,所谓“宜”,即“义”也。“义”作为一个范畴虽然含义复杂,但其基本义如东汉刘熙言:“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释名·释言语》)求得事物“合宜”似乎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为行为合理性所寻找的契合点,不论是宜于情,还是宜于理,都会使行为性质得以保障,这也是儒家对复杂情境之中行为选择的理性思考。“义”对“权”的介入,为“权”的合理性做了内在的理论支撑。“经自是义,权亦是义,义字兼经、权而用之。”[2]有此“义”,则权得以与经地位相侔,二者所行都是为了事物之“宜”。所以,“义当守经,则守经;义当用权,则用权”[2]。经、权置于“义”之视角下,使“权”无异于“经”,这也是朱熹等宋明理学家对“权”论的发展之一。
若再深究一层,“义”之所在亦是“道”之所在,汉儒言“反经合道”当是窥得“权”与“道”之相通处。朱熹当然亦明晰此理,“权……便是合道,故反经亦须合道也”[2]。朱熹之道是得于天而具于心的,是万世不易之则,如君令臣从,父慈子孝之属。毫无疑问,经是以道为价值导向之行为准则,而权虽异于经,然就实质言,其亦指向于道,如若非此,则易流于权术、权诈之类。所以,朱熹言“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2]。道贯经、权,是从至高之理念层面来统领二者,这也显示出二者之同。另外,道贯经、权亦指道须通过经、权来体现。朱熹曰:“盖经者,只是存得个大法,正当的道理而已。盖精微曲折处,固非经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事有不得已处,经所行不得处,也只得反经,依旧不离乎经耳,所以贵乎权也。”[2]经有所不足而须济之以权,经、权合力方才使道之意蕴展现无遗。
在儒家视野中,合于“义”“道”即是得于“中”,所以朱熹又以“中”言“权”。“权是时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2]如果说“义”是儒家对行为效果的评价,那么“中”则是行为之本真价值理念。在朱熹眼中,“中”更多的是一个动态的价值理念,“盖凡物皆有两端,……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1]。所谓“中”,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标准,而是在动态的衡量中所体现之价值理念。就此一点言,“执经”以求“中”,只是“胶于一定之中”,并不能完全至“中”。反观“权”,其所体现的“权其轻重而适其平”的特点与“中”之义是完全吻合的,权是“随事以取中”。故而朱熹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1]由此我们愈来愈可以体味到“权”之于“义”“道”的重要性。仅就内涵言,“经”是合于“义”,适于“道”,得于“中”的,但当其落实于实践,行“经”所体现者就不能完全于此了。盖经有所长亦有所短,然经之不足,权可以做一补足,由此一点看,“权”虽异于“经”,但更合于“义”,适于“道”,得于“中”。
至于义、道、中于“权”之意义,韦政通先生言之甚明,“汉儒仅说‘反经合道为权’,朱子进一步追问此如何可能?解答这个问题,单靠‘这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还不足以为权变的行为在理论上提出明确的指导,这方面的理论效果得益于义、中或时中概念的介入,以及与权的关系的讨论才逐渐发展出来。这些概念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经朱子的结合,遂成为解决经权问题的核心理论”[5]。换言之,先秦至汉唐间,诸家论“权”基本上是在权、经(礼)、道之间往复辩诘,到宋明始得以“义”“中”等加以介入,这使“权”在理论深度上得以提升,也使其作为一个范畴具有了成为体系的理论架构。朱熹集其大者,综而论之,使“权”之新面貌得以呈现。
朱熹论“权”的另一特色是以《易》解“权”,“才卿问:‘巽以行权’。曰:‘权之用,便是如此。见得道理精熟后,于物之精微委曲处无处不入,所以说巽以行权’”[2]。 “巽”与“权”的关联,为“权”之内涵接引入新内容。朱熹通过对《易》之“巽以行权”的解读来说明行权方式之特征。按《集注》所引,洪兴祖曰:“易九卦,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1]。所谓“九卦”,即“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儒家将其比附为九德,朱熹依次解之为“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易,必谨乎此,然后其德有以为基而立也。谦者,自卑而尊人,又为礼者之所当执持而不可失者也。……复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变而常且久;惩忿窒欲以修身;迁善改过以长善;困以自验其力;井以不变其所;然后能巽顺于理,以制事变也”[6]。自立于礼始,儒家修身、进德、践道能力逐步得以提升,而最高之境,当为“顺于理,以制事变”。儒家所追求者,不仅是明道于心,更重要的是行道于世,因此,不能不强调践行能力,而“巽”德当为此方面之内容。另外,“巽以行权”所体现者,是行权方式之特别处,“问:‘巽称而隐’,‘隐’字何训?曰:‘隐,不见也。如风之动物,无物不入,但见其动而不见其形。权之用,亦尤是也’”[2]。如果说行“经”是为光明正大而显于世,那么行“权”则不然。就经权关系言,在朱熹看来,“权”只是对“经”之隐微曲折处作一补充,故难言其“大”,更不可能“显”;就权之特性而言,“权也难说”,毕竟它不会像经那般有清晰之界定与明确之方式。基于此,行“权”只能是“隐然”而作,“权是隐然做底物事,若显然底做,却不成行权”[2]。
总而言之,就理论体系而言,建基于汉儒与程颐之上的朱熹“权”说,不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超前人。它具有一个立体的架构,既有形上的内在联结,又有形下的理论考量。不过,这并不表明朱熹之“权”说是完满融通的,其“权”体系受制于理学背景限制而难以脱其窠臼,此一点后面将会论及。
三、朱熹之行“权”
如前所言,“权”具有极强的实践面向,因此理论之外所须面对者就是如何来行“权”。对权朱熹认为,“权也是难说。故夫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到得可与权时节,也是地位太煞高了也”[2]。毫无疑问,自孔子提出“权”以来,行“权”何以能成为一个绕不过的问题之所在。虽然诸家基本上都认同“权”为儒家实践领域所不可或缺者,权是达道之径,但又都谨慎于此,毕竟,权所蕴含的“反经”意义使其不能作为一种常行之法。如果说“经”是众人与学者皆能循之之规则,那么对“权”,赋予其可行者则须极度审慎了。所以,朱熹一再强调,“须是圣人,方可与权。若以颜子之贤,恐也不敢议此”[2]。但另一面,若细观朱子言论,其实他把行“权”分为两个层次——虽然很是勉强,但又难以回避。
“问:‘可与立,未可与权’,看来‘权’字亦有两样。伊川以权只是经,盖每日事事物物上称量个轻重处置,此权也,权而不离乎经也。若论尧舜禅逊,汤武放伐,此又是大底权,是所谓‘反经合道’者也。曰:‘只一般,但有大小之异耳。如尧舜之禅逊是逊,与人逊一盆水也是逊;汤武放伐是争,争一个弹丸也是争。……大小不同而已矣。’”[2]朱熹一直以“权”为“经”之所济,所以对行“权”颇谨慎,从其所举行“权”之例中也可看出此一点。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伊尹放太甲,这些都是行权之典型,此种“权”每时隔六七百年才会发生一次。但如果只有这样所为才可称得上是行权的话,那么“权”的价值与意义将会大打折扣——行“权”只能被置于极小范围之内而成为特例,因而其不会具有任何践行之积极意义。朱熹应是注意到这一问题,所以他在弟子的追问之下也认为“但有大小之异耳”:就其“大”而言,是汤武放伐;就其“小”而言,则是礼有常变。朱熹言“权”往往只论其大而忽视其小,这也常常被后人所诟病。不过,虽然朱熹于“小”少有论及,但在其生活之中却不乏实例来说明他是如何行“权”之“小”的。
所谓权之“小”,是指经权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之呈现,毕竟这也是“权”本身所应含之意向。在此一境遇中,经、权关系被具体化为礼、权关系。对礼朱熹认为,“礼有经,有变。经者,常也;变者,常之变也”[2]。相对于经、权关系的抽象性,礼之常变更具现实意义。朱熹在生活之中经常碰到如何行“变礼”的事情,通过他对此的态度与方式,颇可窥视到其“权”说的某些意涵。
例一,或问:“设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丧服用僧道,火化,则如何?”(朱子)曰:“公如何?”曰:“只得不从。”曰:“其它都是皮毛事,若决如此做,从之也无妨,惟火化则不可。”泳曰:“火化则是残父母之遗骸。”曰:“此话若将与丧服浮屠一道说,则是未识轻重在。”[2]在此一事件中,朱熹所面对者有二。其一,行丧以礼,其二,遵父之命。依儒家之丧制,有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但当“父要循俗制”时,则面临一矛盾境况:父命与丧制不符,是遵父命还是依丧制?如果只听父命,虽然做到了孝,却违背了礼制;反之,不听父命依礼而行则有违孝道。有见于此,朱熹不是简单地择一而行,而是做了合理之分析。礼制不可全守,父命不可全遵,而应适当依情而定。“丧服用僧道”虽不符礼制,但只是小节,可以遵父命而行,但使用火化就为不可了,毕竟在儒家看来父母之身体发肤重于一切。朱熹做如此之处断,既顾及父亲之情,又兼及儒家之礼,可谓情礼兼顾而不失其常。诚如杨慧杰所言,“只要能把握道德的大原则,次要的原则在遇到困难时,不妨斟酌轻重,暂予舍弃,这就是行权”[7]。这也是朱熹“权”论之“义”原则,凡事只要合于“义”就为可行,而不必事事处处守礼循规。
例二,因论丧服,曰:“今人吉服皆以变古,独丧服必欲从古,恐不相称”。闳祖云:“虽是如此,但古礼已废,幸此丧服尚有古制,不犹愈于俱亡乎?”直卿亦以为然。先生曰:“‘礼,时为大。’某尝谓,衣冠本以便身,古人亦未必一一有义。又是逐时增添,名物愈繁。若要可行,须是酌古之制,去其重复,使之简易,然后可。”[2]在儒家,古礼的典范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传承着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素:尊尊、亲亲。吉服与丧服所代表之意义亦在于此。但在朱熹看来,“礼,时为大”。衣冠只是一种形式,它要随时代变换而发生改变,因此,所谓“古制”亦因“时”而变。如前所述,“时”是“权”之重要内涵之一,朱熹以“时”变礼的思想其实就是以“权”行礼。就内在而言,礼所代表的价值理念可以不变,但礼之外在形式须是随时顺情而不断适应新情境。
简言之,就行“权”面向而言,朱熹把它分为两个层次,所谓“权”有大小之异:其“大”者,“圣人亦罕言之”;其“小”者,常人可知而行之。但需注意的是,朱熹把行权的焦点放在了前者,后者仅仅是存而不论。或许这与其理学体系有关联,而由其所生之弊失亦隐含其中。
四、朱熹“权”说之蔽失
朱熹所论所述从理论背景来看,与他理学体系相承接,因此他的“权”说也深具此一面向之烙印,而这一点也影响到其“权”说相关论点,造成某种不可挽回之弊失。
众所周知,朱熹思想的核心范畴是“理”,此“理”为一绝对而超越之实在,是一切存在之价值的终极根源。其呈现于人,则是人伦纲常之大本,是只可顺而成之,复而明之的常经。在朱熹的思想世界中,以“理”为价值根源的伦理纲常(经)只能恪守,甚少有可以悖反纲常的理论空间。虽然朱熹理论上认为,汉儒“反经”之说“却自晓然”,但终究与其思想义理之内在精神不相契合。汉儒以经权并存,如董仲舒所言:“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8]。经、权(反经)二者于现实实践中具有同样的合法性。但朱熹之“权”说,主要侧重于强调“经”在现实中所起到的维持社会纲常的作用,虽然他不能完全否认权(反经)的必要性,但他却尽量弱化甚至遮盖“权”在社会实践中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他说“经便是大经,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者。……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间却煞有曲折。……使大纲既正,则其它节目皆可举。若不先此大纲,则其它细碎工夫如何做”[2]?在朱熹思想中,经的地位是绝对而神圣的,是绝少可以有偏反、悖逆存在的。朱熹一味强调“经”的重要性,虽然他也认为“其间却煞有曲折”,但他更认为,只要持守好大经大纲,就可纲举而目张了。至于事情之“曲折”处,是在守经之基础上的“细碎工夫”。对于朱熹来说,权论只是其思想的一点,他对“权”的解读更多的是放在其整个理学思想框架之下进行的。在以绝对而超越之“理”为价值根源的“经”面前,“权”所具有的理论空间极为有限。朱熹“权”论所标明的内在思想指向是,经(伦理纲常)是社会存在的本质,经虽然不能涵括全部社会生活,但只有恪守经道才可以实现本质意义的存在,至于“权”只是作一微末之补充,是不得已而为之者。
在此一理路之下,行“权”似乎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如汤、武事,伊、周事”。而可以行权的主体“须是圣人,方可与权”[2]。朱熹此说基本上使行“权”仅仅变为理论上所悬置的可能,在现实之中,作为个体的行“权”合法性几乎不存在。
古贺煌说:“朱子……说权,犹觉过于太重也。权有大小轻重,圣人说未可与权,亦只是大概说其难,不必至权之极处,恐不可引汤武放伐,伊尹放太甲。果然权之为物,只可数百千年中偶一行之,殆为虚设。”[9]此说可谓中肯。就孔孟言,“权”于其思想有着重要的作用,“权”作为一种由学与思而达至的实践智慧,具有因时而变、因情而变的内在品质,此一品质既是对现有规范的遵从,也是对主体自我价值的认可,它具有无限的创造性,是历史价值与现实情境的有机融合,可以使儒家之价值理想更好地落实于现实。然朱熹之“权”思想遮蔽、消解了“权”之创造性的积极方面,而“一旦在社会领域内适当引入新颖性的自发创造行为不足以对抗形式化行为的惯性力量的时候,僵化、独断的道德主义就产生了”[10]。当朱熹的思想成为统治者的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其重“经”轻“权”之论使“经”于社会原本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发生了偏向,其作用由规范变为禁锢,由稳定变为僵化。清戴震于此颇有批评:“孟子言‘执一无权’,至后儒又增一‘执理无权’者矣。”[11]而“执理无权”不免会造成“以理杀人” 的恶果。
虽然仅就理论而言,朱熹之“权”说面面俱到,少有差次,但在其理学背景之下,“权”只能屈从于“理”(经),成为一个虚设,这也让“权”所表现出的理论活力消解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