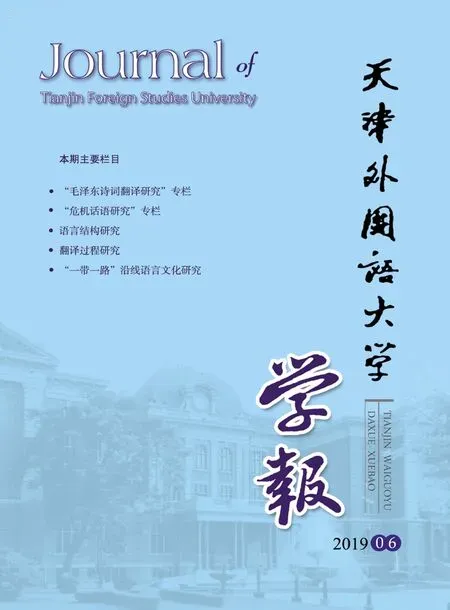后殖民翻译书写中的记忆建构
刘全国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1978年,《东方主义》(Orientalism)出版问世,赛义德(Said,1978:231)在书中指出:“东方主义话语背后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1992年,尼兰贾娜(Niranjana,1992:2)在专著《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中指出:“翻译从来就是展现不同语言、文化和种族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场域,其本质是一种政治行为。”斯皮瓦克(Spivak)、巴巴(Bhabha)等也从后殖民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关注权力与话语、文化与霸权以及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逐步奠定了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基础,标志着后殖民翻译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译文生成的外部因素及译文生成后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解构作用,他们倡导使用异化手段重现本民族文化的印记,通过杂合等方法创造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平等对话的空间,并通过翻译中的记忆建构,重构翻译中译者与读者的身份认同、译文和源语文化的文化认同。
记忆是人类的一种心智活动,是记忆主体对过去活动、感受和经验的印象积累和叠加。记忆不是静止封闭的,相反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变量,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累积发展。记忆并不是历史经验的简单重现,而是一种集体反思性的构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记忆包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等。巴巴(Bhabha,1994:63)认为,“记忆绝不是安静的内省或回想行为,它是一种痛苦的重组或再次成为成员的过程,它把肢解的过去组合起来以便理解今天的创伤。”同时,巴巴坚持使用混杂(hybridity)手段在第三空间(third space)中进行文化翻译,尽量保持源语文化的特性以满足目标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心理期待。尼兰贾娜则通过解读印度殖民者的文本和译本,认为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是重读/重写历史的过程。因此,她提倡使用重译(retranslation)等方式重新解读和翻译印度及其他殖民地文本,以保留殖民地的民族特色及本土文化等方面的记忆(Nirajana,1992:154)。罗选民(2017:124-125)也在其新著《翻译与中国现代性》中阐释了记忆与翻译的关系:“我认为,它们具有共生的关系。翻译的文本需要依靠集体记忆来完成。如在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时,译者面临的不仅仅是原作,还有原作背后形形色色的因素,如前文本、语义场、社会习俗、评论。此外,译者还要考虑译入语的社会文化因素、以前的译本、目标语读者的文化心理期待等等。由于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活动,所以,它必然要考虑文本的协调性和文本的可持续性。如果翻译活动不能产生翻译的经典,它就无法在集体记忆中存活,从而也无法成为仪式、庆典或固化媒介,最终会为人们所遗忘或抛弃。”
学者王宁认为(2009:117-152),在后殖民语境下,东西方的民族记忆在政治关系和文化权利的博弈中被扭曲。在西方视野中,东方是一个懒惰、无知、愚昧的形象,同时东方本身又充满了无限的神秘色彩。在后殖民语境下,为了改变西方对东方的历史偏见、重塑东方形象并唤起东方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与文化记忆,强化东方集体历史记忆来凸显自身的族裔归属感和文化身份,通过翻译书写来改变和修正西方对东方的形象记忆,成为后殖民翻译的现实旨趣和文化使命。在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记忆建构是关涉译者与读者身份认知、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认同以及翻译语境等维度的多维建构过程。
二、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译者记忆对其主体性的建构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实施者,是译文读者和原文作者进行沟通的中介与桥梁,译者的地位与身份是翻译研究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译者在不同的隐喻中被冠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如仆人、叛逆者、隐形人、创造者和不忠的美人等。在作者、译者与读者的三元关系中,译者长期屈尊于源语作者和译文读者,既要忠实于作者,又要服务于读者(孙会军、赵小江,1998:35-37)。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查明建、田雨,2003:19-25)。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是一个能动的主体,是自身主体性的建构者。
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是弱势文化抵制西方国家文化霸权的有效途径,是唤起殖民地人民民族身份记忆和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手段。在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译者必须对自身主体性的身份重新审视和建构。罗宾逊(Robinson,1991:xiii)的《译者的登场》(The Translator’s Turn)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的基础上颠覆了长期以来作者、译者与读者的关系,倡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现身翻译过程,并实现三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在殖民主义语境下,为了顺应译入语文化,尊重和满足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译者主要采取归化(domestication)策略对源语文本进行翻译。然而,殖民语境下的译者并不是追求隐身的真实表达,而是通过归化策略追求翻译文本与接受语话语方式的深度契合,并通过接受语文化的文化图式和价值规范对源语文本进行文化改写。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书写并非主张弱化译者的主体建构作用,而是通过置换译者的文化身份认同,解构殖民翻译的文化权利关系,揭示文化的不平等关系及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的文化殖民现实(蒋林,2008:146-151)。
后殖民语境下译者主体性的记忆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记忆包括本土形象、民族身份及文化意识等诸多因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有一个清醒的定位,不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同谋,而是本民族文化记忆的唤起者、保护者和建构者。译者不应消极被动地隐身于译文背后,而应积极主动地现身于译文当中,通过恰当的方式在译文中表现译者个体和群体的本土记忆、民族记忆和文化记忆,再现其记忆图式。译者与原文作者不再是主仆关系,而是交融和再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是译者基于个体和民族记忆对原文的主体建构与再现。
需要指出的是,译者在通过翻译行为再现其记忆图式时也在完成其记忆模式的拼贴和重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身份的构建。“过去的、未来的,都在自我所身处的此刻统一起来,而其产生的特殊效果,也就是我作为个人所最终觅得的身份!”(詹明信,1997:472)译者从自身的记忆出发,通过翻译文本选择、记忆选择、策略选择、文化选择等方式建构其记忆图式,在翻译书写中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是后殖民语境下记忆对译者主体性建构的基本路径。
三、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读者记忆对其心理预期的建构
法国学者斯珀伯和英国学者威尔逊(Sperber&Wilson,2001:29-40)认为,翻译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译者在充分了解原文作者的信息内容和交际意图的基础上,对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及心理预期进行推理,从而准确地传递原文作者的信息内容与交际意图。在翻译活动中,译文读者是翻译信息传播信息的终端,也是译文品质的评价者。译文读者不仅受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和社会背景等外部变量的影响,也深受文化素养、理解水平、兴趣爱好等内部变量的制约。为增进译文的接受程度,译者会根据自己的记忆和预设,对译文读者的心理预期进行评估和建构,充分解读译文读者的要求,了解他们的审美心理,使译文为译文读者所接受。
在殖民语境下,翻译书写主要以强势文化为中心,忽略甚至扭曲了弱势文化的形象与记忆。正如赛义德(Said,1978:6)所言,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偏见由来已久,西方人所认识的东方是已经被殖民文化篡改过的东方,是缺乏东方文化因素及民族特色的、被归化了的东方。随着东西方交流的不断增多,西方对东方的了解越来越多,很多西方读者对记忆中的东方形象产生了怀疑,同时他们也更加渴望了解真正的东方。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译者基于自身的记忆,迎合西方读者对东方形象的认知转型与心理预期,通过异化(foreignization)策略,对源语文本进行改写,瓦解译文读者关于东方的记忆,重建真实的东方形象。由此可见,在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译者在评估译文读者心理预期的基础上,通过译本选择和策略选择、改变译文读者的记忆图式和期待视野,实现对译文读者心理预期的建构。
四、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译者记忆对其民族身份的建构
1990年,巴巴(Bhabha,1990:1)出版了论文集《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民族就如同叙述一样,在神话的时代往往失去自己的源头,只有在心灵的目光中才能全然意识到自己的视野。这样一种民族或叙述的形象似乎显得不可能地罗曼蒂克并且极具隐喻性,但正是从政治思想和文学语言的那些传统中,西方才出现了作为强有力的历史观念的民族。”巴巴对民族神话和民族本质论进行了深入的解构,他倡导使用杂合手段在第三空间中进行文化翻译,实现民族文化身份的构建。与译者文化身份相比,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更为宽广、更为博大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是一个民族对于自身民族特性和认同范式的集体记忆,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由于长期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殖民时期的译者在对东方文化进行翻译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他们刻意描写出一个愚昧、落后、无知的东方民族形象(张景华,2004:99-104)。随着政治殖民关系的终结,殖民地国家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开始追求自己民族身份的建构和认同。在西方政治殖民统治终结之后,西方殖民者继续实施文化殖民,企图泯灭原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文化,使殖民时期东方和西方的记忆关系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在西方强势文化推行文化殖民的过程中,许多来自弱势文化的译者成了文化殖民的同谋,他们贬低本土文化、崇拜西方文化,对本民族文化进行自我殖民。
在民族文化意识高涨的后殖民时期,越来越多的翻译理论家和译者开始关注翻译书写的民族特性,通过翻译这一跨语际、跨文化书写实践,瓦解殖民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歪曲记忆,力图重构东方记忆与形象。尼兰贾娜强调通过重译(retranslation)来改变西方人对印度民族形象的记忆,从而对印度的民族文化进行重新塑造。在研究早期爱尔兰文学作品的英译过程中,铁木志科(Tymoczko,2004:17)通过对爱尔兰民族文学遗产(如爱尔兰英雄传奇故事等)英译策略的深入探究,认为“翻译不再是简单的帝国主义集中地,同样也是抵抗和民族建构的场所,常被用于塑造民族文化的长久历史,并证明爱尔兰的历史源头远远早于殖民主义为其定义的历史”。通过民族文化遗产的翻译,不仅表达了爱尔兰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与文化压迫的反抗,而且唤起了他们的民族记忆与民族精神,为民族解放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
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的桥梁。后殖民翻译书写中对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的记忆改写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居于弱势文化的译者避免自我殖民的手段,更是消解强势文化霸权、实现民族独立和文化平等的利器。
五、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译者记忆对译文认知语境的建构
自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到翻译学科以来,语境概念已经成为功能翻译研究、语义翻译研究和认知翻译研究等领域共同关注研究的问题。李运兴(2007:17-23)认为,翻译面对的是两种文化中的两套语境参数,译文是在两套参数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生成的。在格特(Gutt)创建的认知语境模式中,语境被用于指称交际参与者对外部世界的某种假设,即认知环境。这一概念包括三个方面:来自物理世界的可感知的信息、从记忆中可检索到的信息以及可以从以上两个来源中推知的信息(Gutt,1991:27)。格特所说的从记忆中可检索到的信息就是指译者记忆中构成译文认知语境的基础和起点,经过拼合、加工和重组表现为译者记忆中的语境结构与图式。
在后殖民翻译中,译者记忆对语境的建构不仅表现为译者对记忆信息的检索、拼合、加工和重组,而且还涉及译者的源语文化意识、目标语文化认同等语境心理。通过后殖民翻译书写,彰显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消解与反抗,修复民族记忆和文化图式。后殖民翻译的认知语境建构包括语符、语用及文化三个维度。
首先,语符维度包括词、语篇、话语、体裁以及相互间的语码转换,是语境构成的最基本要素。语符是文化的载体,是翻译的基本内容。在后殖民语境下,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与精神的载体,是民族文化记忆的桥梁与纽带。后殖民译者在翻译书写中通过保留民族语言的语言特征,努力将民族语言记忆再现在目标语境中。语符是一切民族语言记忆的基础与起点,是翻译书写语境建构的基体。
其次,语用维度涉及两种语言在语码转化中的交际力,是语码成功转化的必要条件。在翻译语码转化过程中,不仅要实现言内信息的转化,更要实现言外之意的传递。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特殊的张力(如横组合力与纵聚合力),在后殖民翻译过程中,这种张力因两种语言和文化权势地位的差异更加明显,使后殖民翻译成为富集张力的语用场所。在后殖民翻译语境下,译者在对译入语认知语境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在语用维度进行翻译时,最大限度地保留或放大源语文本在译入语语境中的文本张力,建构不同于译入语读者期待的认知语境,使译入语读者获得新奇意外的阅读体验,达到建构译文认知语境的目的。在翻译实践中,在译入语认知语境中再现这种张力,唤起殖民地人民对本民族语言魅力与精华的回忆,保护本族语言的完整性与平等性。
再次,文化维度是语用维度和语符维度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相互博弈的场所。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历史沿革、民族精神、文化基体等诸多方面。后殖民语境下,文化是记忆建构的核心,译者通过在跨文化翻译书写中复制本民族文化要素、传递文化精神和再现文化图式,力图在目标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记忆,抵御强势文化的侵蚀,构建多元共存、平等交流的文化图式。
六、后殖民翻译书写中译者记忆对文化认同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末期兴起的后殖民理论,以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契合了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范式,因而推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文化语境下,翻译不再是被动的语义转化,而是能动的文化阐释和建构(郭建中,2000:23)。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书写和文化认同密不可分,文化认同建构是翻译书写中记忆建构的核心内容。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之一,文化认同是对人类文化倾向性的共识和认可。文化身份认同是特定文化中的主体对自己文化归属和本质的确认和肯定,是带有特殊族裔和文化特征的概念(刘佳,2014:34)。文化认同是对一个群体的文化的整体认知和趋同,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它是凝聚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心理基础。
在后殖民语境下,文化认同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学问题,而是打上了民族文化融合和对抗的痕迹和烙印。“文化认同涉及排斥和包含,首先表现为划界的问题。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认同,成为一个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个体而言,往往是从文化集体无意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记忆的。”(王富,2017:39)译者群体和个体在翻译书写中找寻群体和个体身份记忆,对自身进行文化定位,并运用翻译策略对这种文化进行阐释、筛选、重组和强化,正是在后殖民翻译书写过程中完成了对族群和个体文化认同的巩固和强化。
如前所述,在政治殖民终结后,权力差异与由此产生的张力仍长期存在。国家为了巩固其霸权地位,利用强势文化继续对弱势文化进行文化殖民。但随着多元文化理论的不断普及,弱势文化开始关注本民族的文化意识,并提出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文化认同问题的提出是对文化霸权的抗争,是对弱势文化生存权的维护,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呼唤(崔新建,2004:102-107)。作为后殖民时期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接触的纽带与桥梁,后殖民翻译书写注重对民族传统、历史传统、风俗传统等记忆内容的保存与再现。后殖民翻译书写通过对传统记忆图式的再现,唤起人们的民族文化意识,将民族文化声音传递到目标语文化中去,逐步实现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达到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目的。由此可见,后殖民翻译书写中的记忆建构是实现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是文化认同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结语
在后殖民翻译书写实践中,记忆是一个动态、开放、多元的参与性变量,记忆建构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在微观层面,译者通过自身的文化身份的记忆对译者的主体意识进行建构,并通过强化民族记忆,引导和改变译文读者对源语文化的记忆,实现对译文读者心理预期的建构。在宏观层面,译者通过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选择瓦解译入语读者对译者民族身份的记忆,并力图还原读者对译出语民族形象的记忆,对其民族身份进行重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对源语语符、语用和文化等特征的复制和再现,实现对目标语语境的记忆建构,并通过对文化传统、民族意识和文化历史记忆的唤醒和强化,对民族文化认同进行建构和强化。在后殖民语境下,译者的个体和集体记忆是影响其文本选择、策略选择、改写程度和表达效果的重要变量,对译者主体性、读者心理预期、民族身份、翻译语境以及文化认同等因素都有着重要的建构作用。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