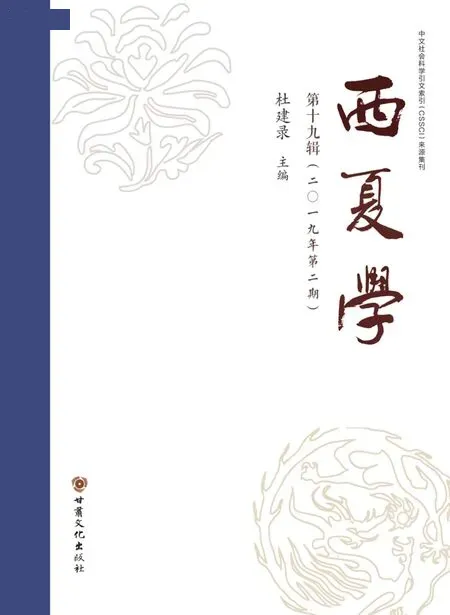飞来峰第90龛大势至菩萨头冠宝瓶及与西夏渊源关系考
席鑫洋
杭州飞来峰第90龛元代大势至菩萨像(见图1)高136厘米①杭州市历史博物馆等编,高念华主编:《飞来峰造像》,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为青年女相,宝冠精美繁复,装饰主体为某种植物纹样,据推测可能是卷草纹宝冠。宝冠正中饰有莲花,自莲花上生出宝瓶一支,瓶颈上有明显十字形状,瓶后有半圆形佛光和火焰纹,瓶底莲花左右侧有太阳花,呈对称分布,卷草纹中间缀有牡丹,菩萨坠有耳铛,头冠与龛后壁融为一体,向两侧延展(见图2)。菩萨面相圆润端庄,额面宽广,双眼微睁,鼻梁修长,略微带有笑意;颈上戴有项圈,上身袒露,胸前饰有双层璎珞,左手夹莲花做说法印,右手垂至膝下做与愿印,衣饰为汉式对襟开衫,腹前系对称帔帛,垂至龛前为悬裳座,灵动飘逸,结全跏趺坐于台上。左手莲花于菩萨肩颈处盛开,莲颈自然弯曲,莲花以荷叶为托,造型立体,莲花之上还缀有新开的嫩叶,似在随风飘摇,婀娜多姿。
从该龛造像的各种图像元素来看,显然是一龛较为典型的汉式菩萨造像。而对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研究历来集中于梵式像及相关的梵汉交融问题,因此对于第90龛,至今尚未见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探讨。编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湖石窟艺术》一书,仅以“元人造像”四字对该龛进行了收录①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西湖石窟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56年,“图四五”,第59页。;稍晚出版的《杭州元代石窟艺术》,对它也只是用“菩萨”二字加以描述②黄涌泉编:《杭州元代石窟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图47”,第65页。;直到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西湖石窟》里,才正式认定为“元代飞来峰大势至菩萨像”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湖石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图171”,第171页。,并在“图版说明”部分进行了简短的图像解说;对该龛较为详尽的介绍,始于廖旸的《飞来峰元代石刻造像内容叙录》④廖旸:《飞来峰元代石刻造像内容叙录》,谢继胜等著:《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157—158页。(该文撰成于本世纪初,但直至2014年才正式出版);而关于该龛造像的研究,总体上仍然是缺失的,即使是作为目前飞来峰造像研究集成之作的《汉藏瑰宝:杭州飞来峰造像研究》一书,也只是对该龛何以被判断为大势至菩萨像作了简要说明⑤赖天兵:《汉藏瑰宝:杭州飞来峰造像研究》,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23页。。尽管该龛在研究界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只要我们细心留意杭州地区自五代吴越国以来的大势至菩萨像并加以对比,就很容易发现飞来峰第90龛大势至菩萨头冠上的宝瓶造型,显得颇为特别,可能还需要详加辨析。

图1 飞来峰第90龛大势至菩萨像
一、第90龛大势至菩萨头冠中状如十字般的独特宝瓶样式
飞来峰第90龛像所在的位置,上下多有树木遮挡,日光难以直射,一旦遇到雨天,龛顶部雨水渗落至佛冠。可能是诸如此类的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菩萨宝冠正中的宝瓶造型受到一定损坏,瓶身下部无法辨别。即使如此,也并不妨碍我们观察该宝瓶的整体造型,整个宝冠正中雕饰的宝瓶远看仿佛是一个小型的十字架一般,十字形瓶颈的顶端呈细小圆球状,十字底端则连结着半个已经受损的圆形瓶(见图2)。

图2 飞来峰第90龛头部破损宝瓶
据赖天兵在《汉藏瑰宝》中的说法,飞来峰至今可清晰辨识的大势至菩萨共有6尊,其中5尊以西方三圣的组像出现,只有第90龛的大势至菩萨单独出现。除开第90龛元代大势至菩萨单尊像之外,另外5尊分别是:第2龛为五代吴越国时期造像,位置较高,现有图像细节难以辨认;第10龛为后周广顺元年(951)造像,损毁非常严重;第16龛也是五代吴越国造像,也损毁严重;第59龛为元代汉式的西方三圣造像(根据题记,系至元年间由杨思谅夫妇发心施造),体量较大,而且大势至菩萨头冠饰装饰还保存得比较完整,宝瓶造型也尚在(见图3),因此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第98龛为1292年雕造的元代汉式造像,也是以西方三圣的组像形式出现,体量也较大,其中右胁侍大势至菩萨坐像的宝冠上亦饰宝瓶,不过该造像整体破裂严重(见图4)。

图4 飞来峰第98龛大势至菩萨像
因此,在下文的分析过程中,除了重点参考第90龛造像之外,我们主要考察对象为第59龛和第98龛,尤其是保存较为完好的第59龛大势至菩萨冠饰。仔细对第59龛中的大势至菩萨头冠中的宝瓶进行观察,会发现它非常接近第90龛里见到的那种独特的十字宝瓶样式,它瓶颈细长,顶端覆球形盖子,瓶颈下部瓶腹之上有喇叭口,与瓶颈交叉呈十字状,瓶腹圆润饱满立于菩萨宝冠中央的荷花之上(见图3)。

图3 飞来峰第59龛大势至头部宝瓶(席鑫洋摄于2018.12.29)
以上对相关图像的考察表明,第90龛里出现的这种宝瓶样式,即使在飞来峰也并不是孤例。然而我们知道,这种样式在后来的明清造像中已经不常见了。那么,这种早已在明清造像中失传的宝瓶样式,为何会在元代飞来峰造像中反复出现呢?此种独特的宝瓶造型的渊源又在何处呢?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发掘。
二、佛教典籍、佛教图像中关于宝瓶的一般性考察
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中,有这样的记载:“若有欲观观世音菩萨者,先观顶上肉髻,次观天冠,其余众相,亦次第观之,悉令明了,如观掌中。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①释净宗编订:《净土文献丛刊·净土三经》,岳麓书社,2012年,第94页。从中我们可以得知,菩萨头上的肉髻、宝冠是判断菩萨身份的重要依据,而宝冠在佛教中具有智慧、光明、庄严佛法的作用。元代的飞来峰造像无疑是极为严肃的,我们对包括第90龛在内的飞来峰元代造像进行考察时,有必要对相关的经典依据与佛教史传统进行一番简要的梳理,如此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前面所述及的宝瓶问题。
军持,梵文Knudikā,又作“君持”、“军迟”、“君墀”、“君持”、“捃稚迦”等,意译为瓶、澡瓶、水瓶。“此乃梵天、千手观音等之持物,亦为大乘比丘常持十八物之一。”①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3957页。
汉语文献里关于军持的最早记载,可能来自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其中说道:“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来多,即斫緪断。商人大怖,命在须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财货掷着水中。法显亦以君墀及澡罐并余物弃掷海中,但恐商人掷去经、像。”②[晋]法显:《佛国记》,明崇祯津逮秘书本,第41页。其中的“君墀”就是“军持”。从《佛国记》的上述记载里,我们大致可以还原这个故事的概貌:僧人法显搭乘的商船遇到风暴的袭击,大家都争相往小船上挤,小船可能因负载过重而倾覆,危机之时,法显把军持澡灌都抛入海中,以减轻船身的重量。由此我们猜测,法显东渡时“君墀”、“澡灌”是携带在身边日常之物,随身携带的“君墀”可能有洗漱与饮水的作用,但是当船将要面临倾覆时,他只好将“君墀”、“澡灌”抛入海里。
根据《翻译名义集》中“犍椎道具篇”的记载 :“军迟,此云瓶……西域尼畜军持,僧畜澡灌,谓双口澡灌。”③[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七,四部丛刊景宋刊本,第208页。从图像上来看,古代的军持(见图5)④郝丽君:《中国古代的军持》,《大众考古》2015年第8期,第61页。在造型上与净瓶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军持颈部略粗,而净瓶颈部细长;军持腹部多为球形腹,而净瓶则是丰肩弧腹下收或斜直腹;净瓶明显是单口,长颈,瓶腹上并无单独开口,而军持则瓶腹部还有开口,或为普通漏斗形或者象形开口。因此,或许并不能把军持跟我们所谈论的宝瓶或净瓶完全等同。

图5 中国古代的军持
根据唐代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第六条的记载:“凡水分净触。瓶有二枚。净者咸用瓦瓷。触者任兼铜铁。净拟非时饮用,触乃便利所须!净则净手方持,必须安著净处!触乃触手随执,可于触处置之。”⑤[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年,第36页。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凡瓶可分为“净瓶”与“触瓶”两种:净瓶也就是作饮水用的,多用瓷、瓦烧制而成,平时也应当置于干净卫生的地方,而触瓶则是用来洗漱的,用铜铁铸成,置于随手可得之处,故称之为触瓶。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当年法显东渡遭遇风浪时
(一)军持与净瓶
抛入海中的应该是“触瓶”而不是“净瓶”,因为漂流在海上时盥洗的器具也许可以丢弃,但装有饮用淡水的净瓶应该是不会丢弃的。
另据有研究者所作的分析:“军持传入中国以后,净瓶和触瓶逐渐被混淆……净瓶与触瓶的混用,也意味着军持与净瓶的混用,所以后来的佛教典籍常常将二者等同。”①郝丽君:《中国古代的军持》,《大众考古》2015年第8期,第62页。也就是说,“军持”是一个具有统称性质的上位概念,其含义要更广一些,包括了“净瓶”和“触瓶”。只不过传入中国之后,因为汉语中的“军持”、“净瓶”常常混用,其含义上的差别才逐渐被人们所忽略。
(二)宝瓶与净瓶
“宝瓶”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器物概念,其大致含义为:“宝瓶,音译军持。又作贤瓶、德瓶、如意瓶、吉祥瓶、阏伽瓶。于密教,盛装阏伽之瓶,特称为阏伽瓶。其余之名称总为美称德号。又灌顶时持用之宝瓶,则称为灌顶瓶。宝瓶即置五宝、五谷、五药、五香等二十种物,并满盛净水之香水瓶,瓶口插宝华、妙华为盖,瓶颈系彩帛以作装饰。宝瓶显地大之形,地大乃‘阿字本不生’之位,即表征众生本有的净菩提心之理德。……瓶之质材可有金、银、铜、玻璃、瓦等多种,而依天息灾所译微妙大曼拏罗经卷一等载,因修法种类之不同,瓶之种类、色相亦均有所不同。宝瓶并为诸尊之手持物。”②宽忍主编:《佛学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华文国际出版公司, 1993年,第892页。根据《佛说观无量寿经》里的记载:“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涂,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名大势至。”又云:“……顶上肉髻,如钵头摩华。于肉髻上,有一宝瓶,盛诸光明,普现佛事。”③[刘宋]疆良耶舍译:《佛说观无量寿经》,《大正藏》第12册,第344页。也就是说,对大势至菩萨头冠当中、肉髻之上所装饰的瓶子,称之为“宝瓶”。
而根据唐代慧琳所撰的《一切经音译》: “君持,经中或作军迟,此云瓶也,谓双口澡罐。”④[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五十九,《大正藏》第54册,第699页。另据北宋所编的《祖庭事苑》中关于《四分律》的记载:“有比丘,遇无水处,水或有虫,渴杀。佛知制戒。令持触净二瓶,以护命故。”⑤陈士强:《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47页。可见,无论“宝瓶”还是“军持”都只是一个统称,泛指瓶器。在佛教密宗里,宝瓶属于一种法器,在一些典礼和仪轨中经常用到。不仅在密宗里,在整个佛教图像中,宝瓶也常常作为法器,见于不同菩萨的手中。宝瓶也可以用来盛五谷或香水,瓶口可以插花或柳枝,这时候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净瓶”就基本上是同义词了,而且宝瓶的材质及装饰花纹也极为多样。
我们可以推测,“宝瓶”本身是一个跟“军持”类似的总称,它可以包括净瓶在内,同时在使用习惯上有有一定的差别,具体地说就是:“净瓶”更加生活化与日常化,可以是佛教徒的日常起居用品,有时候则是一个与“触瓶”相对应的概念;而“宝瓶”则多见于佛教的典礼与法器中,相对而言是一个更具有宗教象征意味的概念。
(三)持宝瓶的几个主要身份:观音、弥勒、婆罗门
在从印度到中国的佛教图像史中,跟“宝瓶”相关联的一些身份,除了前文已述及的大势至菩萨以宝冠上饰宝瓶作为标志之外,还有观音、弥勒、婆罗门等,都有可能是手持宝瓶的形象。
1.观音菩萨及不明身份菩萨手持宝瓶
古代典籍中关于观音持宝瓶(军持)的说法有很多。如唐人李华所撰的《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就有:“观音大圣,在月轮中,手执军持,注水于地中,感咽于双树之下。”①[唐]李华撰:《玄宗朝翻经三藏善无畏赠鸿胪卿行状》,《大正藏》第50册,第291页。后来随着观音信仰在中国民间的普及,手持宝瓶(净瓶)的观音形象颇为深入人心,甚至成为观音形象的基本标志之一。这一点当无须赘述。
有一些尚不能完全确定身份的菩萨造像(当然也存在着是观音像的可能),也有手持宝瓶的形象。新疆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第21窟窟顶就绘有持净瓶菩萨(见图6)。②《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新疆壁画艺术》卷四《库木吐喇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第19页。此壁画位于主室穹窿顶,菩萨头戴宝冠,步摇前垂,黑发编起披于肩头两侧,发上饰有宝珠。菩萨髻珠中央为圆形,辫发垂肩。左壁屈曲置于腹部,之间夹持长颈净瓶供养(见图7),右手举至肩部,掌心向上,作持印契,手指向右侧。菩萨双目微睁目光向下,细眉八字胡,面部安然自在,上身袒露,脖戴项圈,臂饰腕钏,胸前垂有“U”形璎珞,左肩部有图腾样式,帔帛为赭色,自身后环绕自身前,一端缚于腰上,一段飘摇至左臂,菩萨下身着绿裙。菩萨整体风格典雅华贵,神态安详若有所思。

图6 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第21窟主室穹顶的菩萨

图7 库木吐喇第21窟主室穹顶的菩萨手持净瓶
该菩萨将宝瓶握于食指与中指之间,手心朝向身体,由于菩萨手部遮挡,因此瓶颈往上无法清晰辨别。值得注意的是,瓶腹为斜直腹有平底低足,瓶腹上也没有开口。且瓶颈处有一活动圆环,从图像上可以看到,菩萨的左手拇指边有伞状圆盘露出一角,其余被菩萨手部遮挡。宝瓶上分为四层次,各有不同图案纹饰。其中瓶颈上的圆环,与莫高窟初唐第335窟主室西壁观音之净瓶颈上的圆环(见图8)③史忠平、马莉:《莫高窟唐代观音画像中的净瓶造型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年第1期,第69页。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不过其余如瓶口、瓶身、瓶足等俱不相同。

图8 莫高窟初唐第 335 窟主室西壁观音之净瓶
一般认为,在库木吐喇石窟,“21窟穹窿顶的菩萨像便是早期壁画风格的典型代表”④《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新疆壁画艺术》卷四《库木吐喇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3页。,那么,这龛造像可能是库木吐喇石窟早期南北朝时期的造像风格,其造像样式可能受到了犍陀罗艺术影响,而库木吐喇地理位置又比较特殊,是古丝绸之路上距离龟兹古国都城最近的一处大型石窟,其艺术特征必定也融合了龟兹佛教艺术的特点。
2.弥勒菩萨手持宝瓶
在大乘佛教体系中,弥勒菩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新译弥帝隶、梅低梨、每怛哩等,为菩萨之姓,译为慈氏。名阿逸多,译义无能胜。或言阿逸多为姓,弥勒为名。生于南天竺婆罗门家,继释迦如来之佛位,为补处菩萨。先佛入灭,生于兜率内院,彼经四千岁,即人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下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正觉,名弥勒佛。……弥勒菩萨之形像,据《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及《大孔雀明王画像坛场仪轨》载,身呈金色,左手持军持,右手掌向外上扬,作施无畏之势。”①林克智编著:《实用净土宗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340页。据说弥勒出生于古印度的一个婆罗门家庭,与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他在释迦牟尼涅槃之前先行圆寂,升入兜率天内院,直到人间过了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才会再次应化降生人间,并在龙华树下得道成佛。弥勒的形象则是通体金色,左手持宝瓶,右手掌则向外上扬。日本根津美术馆就藏有一尊早期的弥勒菩萨,大约是公元3世纪上半叶的作品(见图9)。
据此我们可以得知,最晚在贵霜王朝步入衰落、笈多王朝诞生之前,弥勒造像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如同佛教经典里所记载的那样,早期的弥勒菩萨造像,左手持有宝瓶。而且,从日本根津美术馆所藏的这尊弥勒菩萨像来看,其面貌造型具有较为明显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特征,应当是深受古希腊、罗马美术影响,形象俊秀英挺,气度雍容,躯体、四肢比例匀称。其左手食指与中指夹紧宝瓶短颈,拇指按压于瓶颈之上的小钮,宝瓶的瓶身则雕刻有繁复精美的花纹(见图10)。
早期弥勒像中的宝瓶样式,以及握持宝瓶的手式基本相同,都是用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瓶颈,大拇指按压瓶盖,而宝瓶的瓶颈通常略短,瓶腹也没有出现开口或流,瓶腹为圆形球腹或丰肩斜直腹,瓶底有圆形圈足。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的一尊雕造于公元2-4世纪的弥勒立像,亦左手持瓶,与前述特征相似(见图11、图12)。

图11、图12 弥勒菩萨立像(2-4世纪,片岩,高104厘米,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及其局部图
3.婆罗门手持宝瓶
宝瓶或军持,在最终演变成为佛教的法器或象征物之前,原本是作为一种生活器具而存在的。因此,在一些佛教题材的美术作品中,有时候也会出现古印度婆罗门身份手持宝瓶的形象。根据《大唐西域记》第七卷所述,“八国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罗门蜜涂瓶内,分授诸王,而婆罗门持瓶以归,既得所粘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内,因以名焉。”①[唐]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586页。其中就出现了关于婆罗门持宝瓶的记载。而在《大唐西域记》的记述中,此类宝瓶是用来盛装、保存佛舍利的。

图9、图10 弥勒菩萨立像(约3世纪上半叶,高148.5厘米,片岩,现藏日本根津美术馆)及其局部图
在新疆库木吐喇石窟,就有类似的婆罗门手持宝瓶壁画图像出现(见图13)。该图像原本位于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第22窟穹窿顶外缘内隅,目前收藏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该窟为穹窿顶方形。穹窿顶相间有佛和菩萨立像。这是靠近前壁角隅的画面,边饰蔓藤卷草纹图案,中央绘坐佛,身光外有立佛。”②《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新疆壁画艺术》卷四《库木吐喇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26页。而壁画中的这身婆罗门像头发花白,胡须茂密,耳朵挂有耳铛,两臂上绘有相同环形纹饰。交脚坐于佛的左侧,络腋由后肩斜披至胸前,腰着短裙,右手持瓶,由于手指部分剥落,猜测可能是食指与中指夹瓶颈,瓶颈较前文弥勒手持瓶较长,瓶身分为三层绘有不同样式花纹,瓶身无开口或流,同时瓶口处的颜料也一并被破坏,无法辨识(见图14)。左手似结说法印与胸前,眼睛往左侧佛的位置看去,若有所思。有一人坐于其身后,手持花环。有研究者认为,“谷口区的第22龛是库木吐喇现存最早的洞窟”①《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新疆壁画艺术》卷四《库木吐喇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年,第3页。。其年代应当与前文曾经提到过的新疆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21窟菩萨的造像时间相近,大体上属于同一时期所绘制。
至此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在佛教典籍还是在相关的佛教图像中,此类宝瓶的造型及其功用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跟宝瓶相关的图像主体身份也不仅仅是大势至菩萨,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观音、弥勒等菩萨以及婆罗门等造像题材中,在某些时候,甚至也存在于燃灯佛、地藏菩萨的手中。

图13、图14 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22窟穹窿顶外缘内隅的 婆罗门手持宝瓶图(今藏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及其局部
三、飞来峰状如十字般的宝瓶图像或源自西夏
(一)早期此种宝瓶图像曾辐射至中原地区,但影响较有限
前述这种宝瓶样式,随着早期佛教图像传入中原,也曾经产生过一些影响。如洛阳龙门石窟万佛沟西段北崖上方“卢征龛”内的“等身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就是其中一例。②龙门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14页。该菩萨有圆形头光,上有火焰纹,头有高髻,鬓发纹作波状,双耳饰有耳铛,面相丰润,胸前有璎珞,缀以宝珠,腹上璎珞串珠交叉。下身着裙,帔帛由两肩绕至身前左手腕处。左手提净瓶,右手已残。虽然万佛沟的这龛救苦观世音菩萨像手中的宝瓶已经损毁,但我们还是能够根据残像辨别出瓶身的轮廓,瓶身底部有圆柱形的圈足直接于瓶腹连接,瓶腹圆润,上接有短颈,颈上有小盖,盖上接有细长孔。菩萨的持瓶方式则是食指和中夹住颈部伞状瓶口,无名指自然下垂。(参见图15、图16)

图15 救苦观音像龛 观音像(局部)

图16 救苦观音像龛 观音像(线描)
此外,现藏于日本藤井友邻博物馆的一尊具有明显健陀罗风格的陕西三原菩萨立像(据传出土于我国陕西省三原县),也出现了类似的手持宝瓶造型(见图17),“因此像无铭文,作者根据造像风格及古印度手持水瓶的图像特征,将其定名十六国时期弥勒菩萨像。这尊金铜佛弥勒菩萨立像高达33.3厘米,属于公元四世纪前后的作品。像顶束扇形发髻,发辫垂肩,留须,眉间有白毫,佩戴项圈、胸前粗大璎珞和腕钏,右手施无畏印,左手屈伸、仰掌,指间挟瓶,身披帔帛,衣褶方硬犀利,着希腊式缀珠凉鞋。”①刘慧:《陕西三原金铜弥勒菩萨立像图像特征考》,《数位时尚(新视觉艺术)》2011年第5期,第9页。虽然这尊弥勒菩萨左手的宝瓶瓶腹部分已经被破坏,但瓶肩部分还是保存了下来,可以猜想此瓶或为球形瓶腹或为宽肩收腹,同时还可看到瓶颈部分与其上部短直形口(见图18)。这种瓶颈上方的短直形口,和前面提到的龙门石窟救苦观世音菩萨像的宝瓶样式基本相同。

图17 菩萨立像(现藏日本藤井友邻博物馆)

图18 菩萨左手持瓶(局部图)
不过,这种宝瓶样式后来似乎并未在内地广泛流传,其产生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随着佛教美术中许多饰品、器物的本土化,此类宝瓶在汉地佛教造像中也就显得较为少见。而在杭州乃至整个浙江地区的五代吴越国时期和两宋时期造像遗存中,几乎都无法看到它的踪影。从这一点来看,飞来峰元代造像中的这种宝瓶样式,应该另有渊源。

图19、图20 黑水城出土西夏绢本彩绘菩萨像及其局部
(二)飞来峰大势至菩萨冠中宝瓶与西夏黑水城同类文物的比较分析
目前能够找到的与杭州飞来峰第90龛大势至菩萨头冠上的此种宝瓶造型近似、同时在年代上又相距最近的图像实例,主要出现在西夏地区。
在西夏黑水城的出土文物中,有一幅绢本彩绘菩萨像(见图19),“这尊大势至菩萨绘于12-13世纪,材质为绢本彩绘(X2441)。”①金雅声、[俄]谢苗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大势至菩萨头部之上有一个伞形华盖,华盖由云彩和植物交织而成,华盖底部的植物叶茎上缀有类似于璎珞和经幡的挂饰。菩萨有淡蓝色圆形头光,头光周围有一圈卷曲的火舌似在随风拂动。其身后还有圆形背光,由中央向边缘延伸,边缘为白色,中间透明。大势至菩萨结跏趺坐于天蓝色莲座之上,莲座底部生出黄白色云彩与背景色融为一体,大势至菩萨乘云端坐于绿色的海上,海上漂浮着均匀的细浪。菩萨肩上的红色帔帛由两侧自然下垂至身前,浮于莲座上随风摇摆,类似于飞来峰的“悬裳座”,同时菩萨周身的衣物随风起伏,富于神韵。菩萨的莲花座通体为蓝色,莲花叶片由内至外变化有色彩渐变,花瓣以三片为一组,莲叶边缘有细云纹,造型瘦长,花瓣紧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菩萨头顶宝冠的卷草纹与飞来峰第90龛类似。同时,宝冠上的植物样式、种类也均与飞来峰第90龛非常相似。不过,明显不同的是,西夏黑水城大势至宝冠正中有一方台,方台之上生出莲花,莲花正中有宝瓶样式。其宝瓶有椭圆形佛光,与飞来峰第90龛大势至菩萨头冠上宝瓶的样式基本相同,瓶腹斜收,而且有圆形圈足向外,瓶有细长颈,颈上有伞形盖,盖上接直口(见图20)。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凡是在黑水城出土的大势至菩萨像,不论是作为单尊还是以胁侍身份出现,其宝冠上都无一例外地具有这种看起来状如十字的宝瓶样式。在《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说法:“黑水城的佛像中,凡‘接引图’题材的大势至,其标志都是宝瓶。”②金雅声、[俄]谢苗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这里的“接引图”指的是佛教净土宗里的“来迎图”,这是净土宗的一个重要场景。根据净土宗经典《佛说十往生阿弥陀佛国经》记载:“若有众生深信是经,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彼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即遣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是二十五菩萨拥护行者,若行、若住、若坐、若卧、若昼、若夜,一切时、一切处,不令恶鬼恶神得其便也。”①[宋]宗晓撰:《乐邦文类》,《大正藏》第47册,第160页。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只要口念阿弥陀佛并诚心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就会派遣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侍者及其他一些大菩萨,前来接引此人。在黑水城出土的“阿弥陀佛来迎图”中,有一幅保存得较为完好的作品(编号:X2411),“绘于13世纪,材质为麻布彩绘”②金雅声、[俄]谢苗诺夫主编:《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参见图21、图22)。画面的左下角是一个男性供养人,观音菩萨正手捧莲花作接引状,他的身子微微前倾,大势至菩萨则低头看着化生童子。在黑水城出土文物中,还有大约10幅左右同样题材构图的“阿弥陀佛来迎图”,其中的大势至菩萨宝冠当中都有相同样式的宝瓶,这表明,这种宝瓶造型在西夏佛教艺术中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图21、图22 西夏黑水城出土的阿弥陀佛来迎图
这种宝瓶样式究竟是存在于西夏的现实生活中,还是仅仅是西夏从某处继承的造像风格,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宝瓶样式在西夏佛教艺术作品里多有出现,这点是确凿无疑的。而飞来峰大势至菩萨冠中的宝瓶与黑水城出土西夏同类佛教艺术品在造型特征上的高度相似性,又指向了一个极大的可能,即:飞来峰第90龛大势至菩萨头冠上的此种宝瓶,有可能源自西夏。
即使抛开宝瓶样式不谈,飞来峰的大势至菩萨题材造像本身就有可能是西夏佛教艺术影响下的产物。我们知道,除了第90龛元代单尊大势至菩萨像以外,第59龛西方三圣中的大势至菩萨头冠上也有类似的宝瓶造型,而不论是第90龛单尊像,还是第59龛三圣组像,都是汉式造像;同样,西夏的此种宝瓶造型也是既出现在单尊大势至题材中,也出现在西方三圣组像的大势至题材中,而且在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并行的西夏,我们目前可查考到的这种宝瓶样式全部出现在汉式佛教图像当中。更进一步地说,飞来峰的大势至菩萨造像,基本上都是以西方三圣胁侍的面貌出现的,像第90龛这种单尊的大势至菩萨,不仅在飞来峰仅此一尊,就是在范围更广的内地造像中也并不多见。因此早就有学者指出:“单从题材来看,飞来峰单独供养大势至像或有受西夏影响的可能。”①赖天兵:《汉藏瑰宝:杭州飞来峰造像研究》,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283页。
(三)此种宝瓶图像在元代前后的流传,应与蒙古人对特定地区的军事征服进程有关
在西夏流传较广的某种佛教图像造型样式,为什么在元代时会对相距如此遥远的杭州飞来峰造像产生影响呢?这一点早就有不少学者作过相关研究,从1205年蒙古第一次进攻西夏,直到1227年西夏灭亡,蒙古共对西夏进行过6次征讨,并最终以西夏亡国告终。虽然战争期间西夏人遭到大肆屠杀,但忽必烈继位后改变了原先的政策,将西夏人归为色目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②徐悦:《蒙元时期西夏遗民高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58页。而且西夏遗民中有不少僧人通晓西夏、汉、藏、等语言,从元朝甫一建立,就不断有西夏人在元朝中央与地方的机构中担任要职。③汤开健:《元代西夏人物表》,《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第53页;汤开健:《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甘肃民族研究》1987年第1、2期,第10页;徐悦:《蒙元时期西夏遗民高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59页。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元军攻占临安,次年,“世祖诏命亢吉祥、怜真加加瓦亚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九《世祖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第188页。,这里的“怜真加加瓦亚”即是党项人杨琏真伽,而“江南总摄”则负责统领和处理与前朝关系密切的江南佛教僧众。而根据赖天兵的考证,杨琏真伽曾居住于飞来峰西侧的永福寺,并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升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一职,此记载亦与飞来峰第39、40龛题记“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所”相呼应⑤赖天兵:《汉藏瑰宝:杭州飞来峰造像研究》,文物出版社, 2015年,第120页。。学界一般认为飞来峰元代造像的鼎盛期,正是在杨琏真伽任职杭州之时。因此早有学者指出,飞来峰梵式造像在雕造时“将西夏的造像风格融入其中”,许多作品继承了西夏时期的“余韵”。⑥谢继胜等著:《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第42、44页。而对飞来峰第59龛、第90龛中的大势至菩萨头冠中宝瓶样式所作的考察表明,在飞来峰的汉式造像中同样存在着西夏元素的影响。
类似的宝瓶样式不仅随着蒙古人的军事征服和西夏人的南下而影响了杭州飞来峰,也随着蒙古人的军事进程在其他地方有一定的传播。如现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一尊朝鲜高丽时代(大约为中国的宋元时期)的千手观音菩萨坐像(见图23),“高58厘米,铸铁打制,施以金箔,从像底木制板的铭文可知,造像来自朝鲜东方寺”⑦林保尧编著:《佛像大观》,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94页。。根据《大悲心陀罗尼经》中的说法,千手观音,“四十手所持之物或所呈之手相各为:施无畏、日精摩尼、月精摩尼、宝弓、宝箭、军持、杨柳枝、白拂、宝瓶、傍牌……各手之功德成就法及印言等,一一具载于经轨中。于莲华部诸尊之中,此尊为最胜之尊,故又称莲华王。”①林克智编著:《实用净土宗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44页也就是说,“军持”是千手观音的手持物之一。从图像上可见,千手观音左侧、右侧各有一手持军持或宝瓶:右侧宝瓶为丰肩斜直腹,瓶底有短足与瓶身相连,上接细长颈,颈上有盖;左侧军持与右侧最明显不同在于瓶颈部的伞状圆盘,其余基本相同,左侧军持无瓶盖,有圈足。(见图24、图25)而这尊高丽时代千手观音坐像手持法器中的宝瓶喇叭口,与本文第三部分提到的龙门石窟救苦观世音像及陕西三原菩萨立像所持宝瓶瓶颈上方的短直形口明显不同,这也表明高丽时代的这种宝瓶并不是来源于中国汉地早期曾经存在的宝瓶图式。

图23 千手观音坐像

图24 观音右手持瓶

图25 观音左手持瓶
据说高丽时代的这尊造像可能与密教的传播有关。这尊菩萨头戴宝冠,宝冠之上双手供持一尊结跏趺坐的阿弥陀佛像。有学者认为,“特别是在高丽,因为当时蒙古人进攻侵占所造成的混乱期,促使此种造像达于极盛。”②林保尧编著:《佛像大观》,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96页。
四、关于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宝瓶图像来源问题
在西夏佛教艺术中大量存在的这种宝瓶样式,与河西地区的佛教文化传播有关。早在盛唐时期敦煌莫高窟就有相似的宝瓶图像。莫高窟大圣地藏菩萨像就是一幅持宝瓶地藏菩萨绢画(见图26),其基本情况为:“绢本设色,高63.7厘米,宽17厘米。英国博物馆藏。这件作品最初是作为像幡使用的。旁有题记‘南无大圣地藏菩萨’。地藏信仰在唐代十分流行,与别的菩萨不同,地藏的形象是僧人装束,身披田像袈裟,右手持净瓶。画面不仅人物形象写实,对袈裟纹理质感的描绘也非常细致入微。”①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艺术——莫高窟》,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5年,第151页。画面中地藏菩萨右手中指和无名指夹瓶,宝瓶为椭圆形腹,颈部有伞状圆盘,圆盘上复有锥形细长小颈,瓶腹下有莲花状圈足,圈足与瓶腹通过小颈相连。瓶腹上端有花纹,下端有环形纹,中间无花纹。地藏菩萨右手提净水瓶于身前,左手在其上,掌心向下。由此可见,此类瓶子造型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作为一种菩萨手持的法器在这个地区存在了。

图26 莫高窟手持宝瓶的地藏菩萨(盛唐时期)
此外,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也存在着早于西夏的类似宝瓶样式。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8窟左甬道外侧壁的一尊菩萨像②《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新疆壁画艺术》卷六《柏孜克里克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第32页。(见图27),头戴宝冠,垂发披肩,结跏趺坐于菩提树下,上身袒露,右肩着帔帛从胸前绕至左臂,胸前挂饰黑白相间嵌有宝珠,与内地其他佛教样式大为不同。耳坠有圆形耳铛,两臂上有臂钏,手腕有手环,右手作说法印,左手托一宝瓶。宝瓶为椭圆形球腹,瓶身分为三层饰以简单花纹,瓶底似有圆形圈足,瓶颈较短较细,有圆形盘状盖,瓶腹上无开口或流,整幅图色调古朴,造型粗壮有力。杨富学曾经指出,“经俄国学者奥登堡的仔细研究,此洞始被确认为摩尼教洞窟。”日本学者森安孝夫进一步研究认为:第 38窟原为佛教洞窟,当回鹘人西迁后才被改造成摩尼教窟,后来,随着摩尼教的衰落,该窟再改回佛教窟。”③杨富学:《高昌回鹘摩尼教稽考》,《敦煌研究》2014年第2期,第73页。根据《中国新疆壁画艺术》里的说法:“第38窟的上部壁画经过后代重绘,但下部壁画是开窟时原作。”④《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新疆壁画艺术》卷六《柏孜克里克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第35页。该壁画位于第38窟左甬道外侧壁,应该属于开窟时期最早的壁画,未经过重新绘制。有研究者指出:“高昌石窟创始于4世纪,废弃于15世纪中叶,因此我们猜测此窟壁画可能绘于4世纪左右,可能受到3世纪传入回鹘的摩尼教(明教)的影响。”①柳洪亮、李肖:《高昌石窟壁画艺术》,《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新疆壁画艺术》卷六《柏孜克里克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第12页。即38窟壁画受过两种宗教的影响,最初可能是佛教,后来是摩尼教,上部壁画系摩尼教兴盛以后重绘,但下部壁画为开窟时原作,体现了早期的佛教风格。因此,该壁画中的菩萨左手所托的这种宝瓶样式应该是佛教中的一种法器造型。

图27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38窟 左甬道外侧壁的菩萨像
库木吐喇石窟第45窟右甬道外侧壁的大势至菩萨图像②《中国新疆壁画艺术》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新疆壁画艺术》卷四《库木吐喇石窟》,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见图28)中的宝瓶,则体现出了与西夏此类宝瓶更明显的相似性,可能与西夏宝瓶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这尊大势至菩萨颈戴项圈,胸前饰璎珞,两手戴腕钏,肩披红色帔帛,腰结带,下身着褐色长裙。菩萨有双层环形头光,头戴鲜花花冠,其花冠跟飞来峰第90龛和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大势至菩萨像相比,显得较为简单。头梳发髻,卷发垂肩,花冠正中绘宝瓶宝瓶有椭圆形赫色佛光,其宝瓶样式与黑水城出土西夏绢本及飞来峰第90龛菩萨冠中的宝瓶样式基本相同。右臂屈置胸前,左手也提一宝瓶,该宝瓶为球形腹,长颈,有伞形盖,盖上有细小口,瓶底有喇叭形圈足。大势至菩萨大拇指按压瓶盖,中指无名指夹瓶颈。

图28 库木吐喇石窟第45窟右甬道外侧壁大势至菩萨 (菩萨宝冠宝瓶与左手宝瓶印刷辨识度不够)
由于唐统一西域以后,将安西都护府设于龟兹,期间大量汉人从中原地区来到龟兹,他们信仰大乘佛教,特别是信仰大乘佛教的“西方净土”③苏思铭:《龟兹弥陀净土信仰流播初探》,《西部学刊》2017年第5期,第55页。。正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汉传大乘佛教向龟兹的回传,库木吐喇石窟第45窟右甬道外侧壁的大势至菩萨图像可能就跟这一大背景存在着一定的关联。而无论是柏孜克里克石窟、库木吐喇石窟还是敦煌莫高窟乃至黑水城,都位于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多元文化的交汇处。结合前文对黑水城、敦煌、柏孜克里克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等地出现的同类宝瓶图像所进行的考察,毫无疑问,丝绸之路上的这种高度繁荣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正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西夏佛教艺术中的宝瓶图像来源。
五、结语
一直以来,学界关于飞来峰梵式造像的来源主要存在着三种说法——以赖天兵为代表的波罗艺术说,以谢继胜为代表的西夏艺术说,以张强民为代表的萨迦艺术说。然而,对飞来峰元代汉式造像的渊源问题,相对而言讨论较少。通过对飞来峰第90龛大势至菩萨头冠上的宝瓶造型进行认真考察,根据现有相关图像的比对考证,同时结合宝瓶的相关源流线索来看,飞来峰造像无疑受到了西夏佛教艺术的影响。由于此种宝瓶样式的传播路线与丝绸之路基本吻合,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西夏佛教艺术中的这种宝瓶样式又是受到了丝绸之路沿线新疆、敦煌等地的宝瓶图像样式影响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