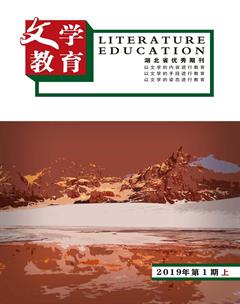苏轼在雷州、儋州的行迹与东坡书院的兴起
内容摘要:苏轼两次路经雷州,又寓居儋州三年有余,直接引发了雷州文明书院和儋州载酒堂的兴建。二者皆因苏轼而兴,因苏轼而名,亦皆被世人习称为东坡书院。随着东坡书院的诞生与发展,雷州、儋州两地文教渐开,原先被视为畏途的“蛮夷之地”,终有“海滨邹鲁”之称。
关键词:苏轼 雷州 儋州 文明书院 载酒堂
宋绍圣四年(1097),苏轼由惠州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儋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获赦内迁廉州。此间,苏轼在儋州生活三年,又两次经过雷州。苏轼在雷州和儋州的行迹,以及他倡兴书院、兴教重文的诸多事迹,皆班班可考。
一.苏轼在雷州的行迹与文明书院的创建
哲宗亲政以后,新党得势,对旧党恶意打击,苏轼等旧党人物皆被罢职外放。绍圣四年(1097),苏轼从广东惠州被贬往海南儋州,雷州乃是必经之路。几乎同时,其弟苏辙也从江西筠州被贬往雷州。当苏轼抵达广西梧州时,得知苏辙已经到达藤州,便日夜兼程赶往藤州,于5月11日与苏辙相会于藤州。随后,兄弟俩由藤州一路同行到雷州。对于这段行程,苏轼专门有诗记叙,诗名《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此外,其《和陶止酒》引言:“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1]“丁丑”,即1097年。
苏轼在雷州的行迹向来众说纷纭,再加上民间文学的再创作,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通过对苏轼诗文集、方志等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确认,苏轼在雷州的主要活动行迹有:与弟苏辙在雷城游罗湖(今西湖),拜谒天宁寺并题写“万山第一”的匾额;雷守张逢在苏轼要渡海去儋州时,派人送到海岸渡口;北返时于递角场(今角尾湾五里乡)登岸,在徐闻拜谒伏波庙并做碑文;在兴廉村净行院住宿,并赋诗两首。其他如到高州游览冼夫人庙并题诗、二进荔枝村致其改名“苏二村”等则不足为信,张学松、彭洁莹《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文学遗产》2011年第4期)一文中有详细论述。
以下将详细介绍苏轼北返时住宿净行院的事迹,这与文明书院的建立有着直接关系。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五月中旬苏轼就接到了移廉州安置的告命。他六月二十日渡海,二十一日到徐闻,二十四日在雷城会晤好友张敦礼等后,二十五日便离开雷城。途中遭遇大雨,在兴廉村净行院住宿下来。他为净行院书写过碑文,可惜如今已不复存在。此外,他还在此写了两首诗,一首为《雨夜宿净行院》:“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淼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另一首为《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枅。当门冽碧井,洗我两足泥。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
据后世文献载录,苏轼不仅曾在净行院住宿一晚,还会晤了乡民陈梦英,并与陈梦英谈及“文明之详”。由此,当地在净行院建“文明书院”以为纪念。道光《遂溪县志》卷3:“文明书院,在县西南八都乐民所城内。宋元符三年苏公轼南迁(按,“南迁”当为“北返”),由儋徙廉,道经双村,宿净行院。四顾山川,谓乡民陈梦英曰:‘斯地景胜,当有文明之祥。既去月余,瑞芝生其地。诸儒遂即其地建书院,匾曰‘文明。宋末毁于兵。元泰定元年提举庐让复建,未就而去。至顺辛未,彭从龙重修……岁久倾圮。国朝修复。”万历《雷州府志》卷21也有类似记载。
历经风雨近千年,文明书院虽数次倾圮,但屡废屡建,至今尚存。今人所编《湛江市地名志》第六编“文化地名”对其建筑规模、结构、环境等有详细描述:“文明书院,在遂溪县遂城镇西南58公里乐民所城东南角……为纪念苏轼而建。占地约120平方米,宽约13米,深约8米,高约8米。坐西向东,背大海,砖木结构,为一幢两层古式楼阁。正中是大厅,大厅墙壁正中镶嵌有一块汉玉石碑,石碑内刻有苏东坡遗像,遗像左上角刻‘苏文忠公遗像六个字。两侧为厢房,均有樓阁,楼下为读书地方,楼上为宿舍。古榕遮天;院后修竹滴翠,风景秀丽。”撰写此文前,笔者曾实地探访,其主体建筑仍在,楼阁宿舍已不复存。
据文献载录,苏轼除了在兴廉村净行院住宿一晚以外,还曾经在石城县(今廉江市)的寺庙三清堂中住宿一晚,并“燃松赋诗”,后人因建松明书院。但苏轼现存作品中,并无与石城三清堂“燃松赋诗”相关者。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苏轼在三清堂住宿一晚是有可能的,“燃松”亦有可能,“赋诗”则未必有过。仅管如此,后人仰慕苏轼之名,依托苏轼行迹以建松明书院,与在兴廉村净行院建文明书院一样都是可以理解的。苏轼声名远播,其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世人无不景仰。后人在他住过的寺院兴建书院,不足为奇。一则表示对他的纪念,二则借其声名以兴文教,鼓励民众向学。
相较而言,文明书院的影响远超松明书院,与苏轼的联系也更紧密,世人习称为东坡书院。
二.苏轼在儋州的行迹与载酒堂的创建
前文已述,绍圣四年(1097)苏轼从广东惠州被贬往海南儋州。苏轼此次被贬的原因,颇为荒谬。宋人王象之在《舆地广记》中记载,苏轼在惠州写了一首表现个人贬居生活的诗,名曰《纵笔》,正是这首诗给苏轼招来再贬之祸。今天看来,《纵笔》一诗的内容颇耐人回味,“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写其憔悴与苦病,“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则言其平和与放达,而全诗的落脚点在后两句。在苏轼的政敌看来,这样一种近乎无事的从容与放达自然是不可容忍。难怪这首诗传至京城后,被当权一派添油加醋,致使苏轼再贬。
海南远离大陆,是唐宋时期朝廷流贬罪人最为遥远的地方,历来被贬谪流放的文人志士看做南蛮瘴炎之地中的绝地。因与内陆隔着一道琼州海峡,孤立成海外一座孤岛,导致百姓接收外界信息困难,文明未开。
在到达海南昌化军(儋州)后,苏轼上了一封《到昌化军谢表》,其间明确汇报了他从惠州到儋州的时间:“今年(按,指1097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责授臣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臣寻于当月十九日起离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军讫者。”[2]七月二日,苏轼到达儋州。气候湿热,处境艰难,病无药,居无室,种种惨况,不一而足。时新任昌化军军使张中不忍,将伦江驿略作修整,给苏轼父子居住。
然而好景不长,元符元年(1098)4月,湖南提举常平官董必察访岭南,在雷州听闻苏轼住在昌化军官衙,专门遣使渡海,将刚刚安顿下来不久的苏轼从昌化军官衙中轰出,军使张中亦受此牵连,被撤职罢官。老迈的苏轼流离失所,凄凉之极。当地黎、汉百姓听闻此事,群起相助,帮助苏轼在城南的桄榔林建起几间陋室,名其为“桄榔庵”。
苏轼居儋三年有余,一直与民同乐,教导当地黎、汉人民团结,敷扬文教,促进当地文化教育发展,移风易俗,改造当地陋习,为当地士人百姓造福。到了元符三年(1100),哲宗驾崩,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徽宗深感党派之纷争难平,为巩固统治,开始以调停的姿态对待新、旧两党,宣布实施不偏不倚的政治策略,此前被逐的元祐党人开始获准内迁。于是,6月30日,苏轼便渡海,开始北返。
苏轼寓儋,对当地最大的贡献莫过于文化教育。文化教育离不开与苏轼有密切联系的海南东坡书院,亦即载酒堂。载酒堂始建于何时,众多纷纭。据儋县相关资料记载,载酒堂始建于元符元年(1098)春,作为苏轼传道授业、以文会友之地。军使张中邀苏东坡同访黎子云,当时座中有人建议在黎子云旧宅涧上建屋,作为以文相会之所。东坡欣然同意,解衣带头醵钱,并取《汉书·杨雄传》“载酒问字”的典故,命名为载酒堂。[3]此为普遍说法。然苏轼《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序文云:“儋人黎子云兄弟,居城东南,躬农圃之旁,偶与军使张中同访之,居临大池,水木幽茂,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予亦欣然同之,名其屋曰‘载酒堂。”从序文来看,“坐客欲为醵钱作屋”中“欲”字表达的是一种想法,一种打算,并未言已建成。若已建成,苏轼定会有所记载,或在书信中提及,但目前并未发现任何苏轼在载酒堂以酒会诗、以文会友之相关记载或诗文。上述诗中所描述之“临他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仅为诗人即兴想象的情景,是对日后载酒堂建成场景的一种想象。
据现有文献,载酒堂实际建成当在苏轼去世二百余年后的元泰定年间。元代延祐四年(1317),金海北海南肃政廉访司事大都军行部巡视儋州时,在桄榔庵旧址建东坡祠,以祭祀苏轼,修庑廊两间供本州弟子研读书经,并栽植桄榔为林,重立桄榔庵碑铭。祠建成不久,即圮。七、八年后,即元泰定间,“南宁军(即儋州)军判彭震卿将东坡祠始迁于城东”,更名为“载酒堂”,世人习称为东坡书院。
虽然载酒堂并未在苏轼寓儋之时建成,但苏轼在儋三年有余,于文教贡献巨大。《琼台记事录》载:“宋苏文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三.文明书院与载酒堂对雷州、儋州两地文化发展的影响
苏轼流寓雷州的时间并不长,只是从惠州到儋州的路上及由海南北返时两次路过而已,但对雷州的文化发展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苏轼在雷州驻足过的地方,都被百姓们保护起来,更以其之名兴建了文明书院。苏轼作为当时名重天下的第一才子,无疑在民众和士子中具有极大的感召性和影响力,以其之名兴建文明书院,极大地增强了雷州文化的底蕴。苏轼在净行院题诗二首,使得苏轼精神在雷州的传播、雷州民众对苏轼的尊崇有了可感的凭据和依托,其影响是潜移默化且持久深远的。
苏轼谪居儋州期间,坚守了一个士大夫的高尚情操,积极作为,讲学明道,传播文明。他面对物质匮乏、文化落后的儋州,经过短短的三年,大力倡兴文教,使儋州在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诸方面都有了明显改观和长足进步。在苏轼寓儋期间,从其游的秀才姜唐佐成为海南第一位举人;在苏轼离儋数年后,儋州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位进士。载酒堂虽非苏轼居儋时所建,但其兴建乃是当地士民为了纪念苏轼为儋州所做的贡献,其存在是儋州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书院之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汉晋时期的“精舍”。《后汉书·党锢列传》载:“(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4]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传道授业的教育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对中国古代教育文化事业的进步、民俗民风的培植以及思维习惯与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雷州文明书院、儋州载酒堂皆因苏轼而兴,因苏轼而名,亦皆被世人习称为东坡书院,借由东坡书院这一载体,世人得以不断体悟和学习苏轼虽遭贬谪、却能在穷途末路中不断磨练精神与心志的节操和气性。
如果说雷州、儋州带给苏轼的是精神的升华,那么苏轼带给这两地的便是新的文化气象。当他选择以“箕子”作为自我存在形态时,那里便成了他实践大道的理想之地。“天其以我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随着东坡书院的诞生与发展,雷州、儋州两地文教渐开,原先被视为畏途的“蛮夷之地”,终有“海滨邹鲁”之称。
参考文献
[1]苏轼.苏诗补注[M].查慎行补注,王友胜点校.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2]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儋县东坡书院管理处.桄榔庵东坡书院历代诗选[C].儋县:儋县文化馆,1986.
[4]唐亚阳,吴增礼.中国书院德育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项目基金:广东海洋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湛江、海南两处东坡书院的比较研究”(编号CXXL2017142)。
(作者介绍:蔡梓沂,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1154班学生。本文指导教师:邓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