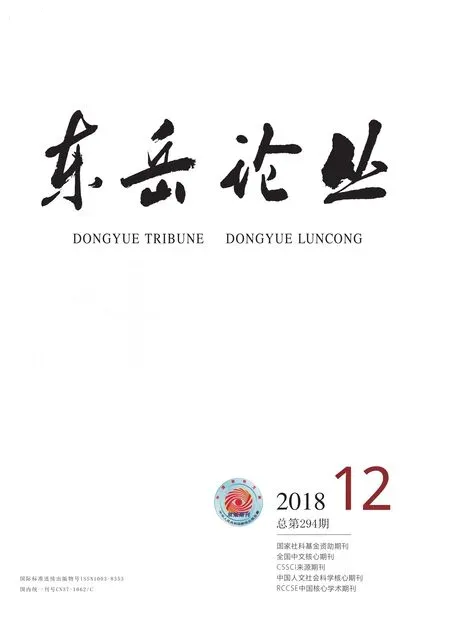得圣人之意者为多
——元儒郑玉对《春秋》的诠释及其意义
刘 俊
(西安交通大学 哲学系,陕西 西安 710049)
元代国运不及百年,却创造出多达122部的《春秋》学著作,且集纂疏、集编、笺证、通旨、经疑等注疏形式为一体,形成大师云集、著述宏富、新见纷呈、成就斐然的《春秋》学系统。而这其中,则以精于《春秋》的郑玉最为杰出,他不盲从,亦不轻信权威,对以往的《春秋》学注解提出诸多有创见性的质疑,开创“阙疑”体例,尊重原典,当阙则阙,卓然自成一家。然囿于前贤往圣对元代经学“无足可观”的成见,学界对包括郑玉在内的元代学者的《春秋》学一直研究不深,关注不够,这与其内在的学术价值是严重不相匹配的。故深入文本,以元代最具创造力和代表性的《春秋》学大家郑玉为研究对象,就成为我们重新认识元代《春秋》学价值的重要突破口。
一、郑玉学术源流和特质
郑玉(1298-1358),字子美,世居徽州歙县,敏悟嗜学,博通六经,尤精《春秋》[注]。《元史·郑玉传》称其“覃思六经,尤邃于《春秋》。”(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432页。)郑玉是师山学派的创始人,门人为其建“师山书院”,世称之为“师山先生”。就郑玉的学术渊源而言,黄宗羲称郑玉为“晦庵续传,象山五传[注]。黄宗羲:《宋元学案·师山学案》卷九十四,第3123页。郑玉自述:
余十数岁时蒙昧未有知识,于前言往行无所择。独闻人诵朱子之言,则疑其出于吾口也;闻人言朱子之道,则疑其发于吾心也。好之既深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于是乎取正[注]郑玉:《师山集·馀力稿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17册,1986年版,第4页。
好友汪克宽亦说:
(郑玉)才十岁,闻人诵朱子之言,则喜其契于吾心也;闻人论朱子之道,则喜其契于吾身也。于是日诵《四书》,玩味朱子之说而抽绎之,沉潜反复,久而融会贯通,得其旨趣。……因是于恻隐之发,体认涵养,造诣深矣。[注]汪克宽:《师山先生郑公行状》,《全元文》卷一五九七,第176页。
从郑玉自述以及他人所言可以看出,郑玉虽未亲炙朱子门下,但其青少年阶段是在朱子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度过的,后以倡导、维护、阐发朱子学为己任,逐渐对朱子涵养致知之学融会贯通,这与郑玉生活的地域学术有莫大关联。郑玉世居徽州歙县,此地区处于“新安理学”的核心影响范围。众所周知,“新安理学”的学派特色便是唯程朱是尊,一方面崇尚儒家伦理思想,如孟子的仁义礼智信,另一方面,致力于朱子的涵养致知之学。在此地域学术的背景下,郑玉深谙朱子之道亦在情理之中,故黄宗羲称郑玉为“晦翁续传”[注]黄宗羲:《宋元学案·师山学案》卷九十四,第3123页,第3125页。,对于其承接、延续朱子的学脉在学统上加以肯定。
但在师承上来看,郑玉毋庸置疑是陆学中人。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记载郑玉与陆九渊的学术传承关系:“郑师山之学于淳安也,尝曰:‘朝阳先生,吾师之。复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资而事之’。”[注]黄宗羲:《宋元学案·慈湖学案·隐君洪复翁先生震老》卷七十四,第2515页。此处朝阳为吴暾,复翁为洪震老,大之为夏溥。吴暾、洪震老为夏希贤的门生,夏溥则为希贤的儿子。希贤从学于史弥坚,弥坚学于慈湖杨简,慈湖则是象山门人。

也就是说,同为元代“和会朱陆”的代表人物,吴澄是以陆九渊之学为根基,而郑玉则是以朱子学为底色。可见,徽州宗朱氛围对郑玉的影响远远胜过其师门传授,这一影响亦在其《春秋阙疑》中得到明确体现。
二、开创《春秋》学“阙疑”体例
郑玉毕生以研究《春秋》为务,尽平生精力注解《春秋》,即使在其被俘、行将就义之时,仍念念不忘其《春秋阙疑》,可见其用力之深,用功之勤。以至于是时学者徐尊生高赞道:
先生所以著述之意甚公且平,如此只“阙疑”二字,所见已自过人。世儒说《春秋》其病皆在乎不能“阙疑”,而欲凿空杜撰,是以说愈巧,而圣人之心愈不可见也。[注]郑玉:《师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17册,第113页,第17页。
从徐氏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郑玉仅仅在《春秋》学上所开创的“阙疑”体例就足以超越众说,更何况其“阙疑”并非毫无根据,随意质疑,而是“甚公且平”。郑玉之所以以“阙疑”为体例,乃在于他认为两宋以来所开创的“舍弃注疏,专求义理”的解经方式较之汉唐注疏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肆意解经”,他说:

这段引文可以被视为郑玉作《春秋阙疑》的原则,他认为一方面经典词简而义深,绝非浅见臆说可以获知;另一方面经典岁月日久,残缺甚多,更非凭空想象可以增补,因此勉强会通不如阙所当阙,以保持尊重原典的治学态度。正是在这种治经原则的贯彻下,郑玉成就卓然自成一家的传世经典《春秋阙疑》。在此书中,主要包括四类“阙疑”:
其一,“经有脱误无从质证”[注]郑玉:《师山集》卷三,第16-17页,第17页。,即经有脱简则阙疑,反对穿凿附会强加解释。如《春秋·隐公二年》经文“纪子伯、莒子盟于密”,郑玉解释:
程子曰:阙也。胡氏曰:甲戌己丑夏五,纪子伯、莒子盟于密之类。或曰本据旧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传受承误而不敢增者也,阙疑而慎言,其余可矣,必曲为之说则凿矣。[注]郑玉:《春秋阙疑》卷一,第12页,第6页,第14页。
郑玉认为《春秋》词简义奥,微言大义非浅见臆说所能阐发,此处阙文可能是孔子依据鲁旧史修定《春秋》时,本身“不能益者”。后在传世的过程中,先儒不敢妄自补经,故阙疑至今。

郑玉于经文之下列举三传之解释:“君氏”,《左传》作“声子”,即隐公生母,并根据当时的丧葬礼制作了说明。《公》《谷》二传皆认为“君氏”是“天子之大夫”,但立足点不同:《春秋》有“外大夫不卒”的原则,《谷》解释此经破例记载的原因;《公》则侧重于解释“尹氏”称谓原则。郑玉以“三说不同”、无从考据为由阙疑,对三传只是引用并不作出优劣评价。


《春秋》中对于诸如杞、滕、薛之类小诸侯国君主的称谓很混乱,或称侯或称伯或称子,可能是历史上传抄《春秋》过程中的笔误,无从考证,故今阙疑。
其四,于诛、讨之事,“不敢轻信传文曲相附会”[注]郑玉:《春秋阙疑原序》,第3页。,即《春秋》中与诛、讨相关的军事外交事件,前辈学者往往过分阐发其中的大义,如“尊王”“攘夷”“正名”等,郑玉反对穿凿附会,主张阙疑。如《春秋·桓公十六年》经文“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郑玉在“愚按”后指出,诸侯的列序自有定制,体现尊卑秩序。同年春正月诸侯会于曹时,蔡侯位序列于卫侯前,夏四月伐郑时,卫却先于蔡。当世之人猜测蔡自此依附楚国,《春秋》贬之,故在位序上位于卫之后。郑玉认为此乃臆说,指出“蔡之从楚亦无岁月之可考,岂在是岁正月至四月之间乎?姑阙之以俟知者。”[注]郑玉:《春秋阙疑》卷五,第74页。认为因年代久远,蔡国是否从楚从史料上已无从考证,故此处阙疑。
郑玉所开创的《春秋》学“阙疑”体例乃是在宋儒“肆意解经”泛滥的风气下,针对时弊而做出的矫正、创新之举,这在当时义理之学风行之际是难能可贵的,保持了必要的清醒和理性。
三、质疑前解,兼取程朱
郑玉在作《春秋阙疑》时,首先对以往的《春秋》经解进行回溯和反思,他一方面质疑以往的注解,另一方面却对程、朱的《春秋》学多有回护和兼取。就质疑来说,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首先,对《三传》解经颇有微词。朱子认为《左传》侧重史实,《公》《谷》专注义理阐发,在这点上,郑玉与朱熹的观点一致,并且在继承朱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三传各自的优劣:
至于三家之传,《左氏》虽若详于事,其失也夸;《公》、《谷》虽或明于理,其失也鄙。及观其著作之意,则若故为异同之辞而非有一定不可易之说。[注]郑玉:《春秋阙疑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63册,第3页。
余观《左传》所载皆鲁史旧文,明白可信。及丘明稍加隐括,附以议论,然后事迹泯灭,是非乖谬。春秋之旨始有不可得而考者矣。及《公羊》、《谷梁》定为义例之说,但有不合则曰:此圣人之微意也。一切舍事实而求之空言,使圣人笔削之妙下同刻吏弄法之文,而仲尼之志亦复不可见矣。然则《春秋》之不明,三传蔽之也。[注]郑玉:《读欧阳公赵盾许止弑君论》,《师山集》卷二,第12页,第12页。
圣人之义,词简义深,本非后世儒者所能测识,然圣人之意本欲使与鲁史并行,学者求事之本末于史,而观理之曲直于经也。史则如今世吏人之文案,经则如前代主者之朱书。惜乎鲁史不存,犹赖《左传》可以考其大概,然意左氏当时所见鲁史已无全文,故于其残阙则妄为之说以补之,是以间有本末颠倒、是非错缪之失,而经之微旨不复可见。此春秋之大恨也。”[注]郑玉:《春秋阙疑》卷一,第4页。
分析上述引文,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其一,三传各有侧重,《左传》解经侧重于补充史实,于义理则涉及不多。而《公》《谷》则注重阐释经之大义,然于叙述史实则不甚在意,二者皆有偏颇;其二,孔子通过笔削鲁旧史,将《春秋》大义寓于其中,词简义深,本就不易理解。故最初孔子将鲁史之《春秋》与圣人笔削之《春秋》并行于世,学者可探求史实于前者,得微言大义于后者,只是鲁旧史渐次不传,而《春秋》亦失之参考;其三,讨论史与经的关系,在郑玉看来史好比今世吏人之文案,经则是帝王之朱书,二者之间存在纲与目的关系。但是由于鲁旧史逐渐不传,“史”的角色由《左传》接续以考经之梗概,但《左传》本身即已存在史料残缺、理解谬误之不足,故《春秋》之微言大义亦不复可见。
于解经过程中,郑玉亦具体批判三传之说。如:
1.恒公元年经文“春王正月,公即位。”郑玉:“《公羊》所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子以母贵之说非,与此徇惠公失礼而为之辞,非春秋法也。……《公羊》又肆为邪说,而传之汉朝又引为邪议而用之,夫妇之大伦乱矣。《春秋》明著桓罪以示王法,正人伦,存天理,训后世,不可以邪汨之也。”[注]郑玉:《春秋阙疑》卷三,第39页。

第1例,郑玉批判《公羊》:《公羊》认为《春秋》有“继弑君不言即位”的原则,此处破例书“公即位”,《何休公羊经传解诂》解释:“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恶,直而不显,讳而不盈。”郑玉却认为《公羊》对《春秋》“书桓公即位”一事做出的解释并非《春秋》之本义,而是为惠公失礼避讳,批评《公羊》之解释为邪说,乱夫妇之大伦。
第2例,郑玉批判《左传》:赵盾、许止之事即《左传·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左传·召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春秋》中皆书“弑”,最初并无“不讨贼”、“不尝药”之文。《左传》中界定其二人之罪,认为赵盾“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注]郑玉:《春秋阙疑》卷二十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63册,第300页。。因史书中无许止弑父的记载而有饮药之语,故托孔子之言“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注]郑玉:《春秋阙疑》卷三十七,第557页。,后《公》《谷》从而和之,后世学者亦多以“不讨贼”“不尝药”批之,掩盖赵盾、许止弑君之罪行。郑玉认为赵盾虽非亲弑,实为弑君主谋;而许止若无弑父,父死即可居丧即位,无须弃父之丧而奔他国,从而推论其进毒以鸩其父,父死而奔则是因弑君而避讨,由此可见《左传》之言误导后世学者。
除对最初的《三传》进行质疑和批判之外,郑玉对三传之后诸家之说亦进行反思和质疑。历史上《春秋》学研究一直未曾中断,然在郑玉看来自汉以降,儒者治《春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足。汉学以灾异、谶纬解经而不知《春秋》之经世致用,唐宋学者又借诠释经典阐述自己的思想主张,故《春秋》之说杂乱。再加上郑玉所认同的儒家道统中的圣人程颐、朱子并无系统的《春秋》学著作传世,故而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他不得不质疑众家之说,如《春秋·僖公五年》经文“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郑玉对家铉翁、孙觉、张洽的观点依次点评,指出家铉翁认为申生处人道之变虽欲不死,然终不可得;而在孙觉看来,圣人斥责晋侯而申生亦有罪,世无不可为之事,如舜事瞽叟尽力为之。郑玉反对二者观点,认为“申生能为众人之事而不能为圣人之事”[注]郑玉:《春秋阙疑》卷十三,第160页。。程颐、朱熹虽未有系统成文的《春秋》学著作,但却提出基本的观念和论断,成为后世尊崇程朱的学者研究《春秋》学的原则和范式。郑玉对程朱的《春秋》学在羽翼的基础上多有修正。在如何看待《春秋》上,程颐反对以“史”看《春秋》,认为“《春秋》之书,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后,相因既备,周道衰,而圣人虑后世圣人不作,大道遂坠,故作此一书。”[注]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3页。而朱子则恰恰相反,他认为应该以史学的眼光看待《春秋》[注]问:“《春秋》当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样看。”(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8页。)。郑玉则赞赏程颐之说,反对朱子之说,认为“《春秋》见夫子之大用,盖体天地之道而无遗,具帝王之法而有征。”[注]郑玉:《春秋阙疑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63册,第2页。而在《春秋》的“褒贬”上,郑玉则是赞赏朱子之说:“圣人光明正大,不应一二字加褒贬于人”[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48页。,也就是说,郑玉认同朱子的《春秋》不能以“一字”论褒贬的说法,并在其《春秋阙疑》中秉承始终。程、朱之间的《春秋》学是有明显差异的,作为尊崇两者的郑玉,如何抉择便成为不得不回应的问题,郑玉采取的是折衷、兼取的态度。总的来说,郑玉对前人诸解不轻信,不盲从,依据史实进行质疑和矫正,即使对他所尊崇的程、朱,亦是客观审视,当信则信,当疑则疑,择取有当。
四、经传互证,相互发明
程颐说:“经为断,传为案。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注]俞皋:《程子朱子说春秋纲领》,《春秋集传释义大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6页。由于《春秋》中所载事迹年代久远,或因叙事简略,或因存在脱简,某些经文存在不易理解之处,故学者以传之史实对经文前因后果加以解释,试图让经文阅读起来更加明晰。同时,又以经文考察诸传之错讹,而此经传互证之法目的则在于更好地阐释经之义旨、得圣人之意。郑玉在诠释《春秋》时即贯彻了这一原则。
其一,经有残缺则考察诸传。
郑玉于《春秋》学研究上亦体现其谨慎的治经态度,经有残缺则考察诸传,取诸传合于理的解释以补经之不足。此处经过考证,《春秋阙疑》中承担以传补经职能的“传”基本可以认定为《左传》。现列举以下四例对郑玉以传补经进行阐释:
1.成公六年经文“卫孙良夫帅师侵宋”,郑玉:“《传》称:晋、卫、郑人与伊雒[注]当时居住在伊水、洛水一带的外族,统称为“伊雒”。、陆浑[注]杜预注:“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西北。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至今为陆浑县也。计此去辛有过百年,而云不及百年,传举其事验,不必其年信。”(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4页。)之戎侵宋,而经独书:卫孙良夫者,岂此举卫志也欤。”[注]郑玉:《春秋阙疑》卷二十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6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2页。
2.襄公十八年经文“夏,晋人执卫行人石买”,郑玉:“经书:晋人执卫行人石买,而传云: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执孙蒯于纯留。夫晋之执石买虽因其伐曹之故,然所以执之则因其来聘而遂执之耳,非以其罪而执之于其国也,故经以行人书之,石买既为行人至晋,孙蒯何缘与之同行而亦被执乎?盖传因伐曹之事实孙蒯、石买之所为,故附会而为此言耳。”[注]郑玉:《春秋阙疑》卷三十一,第442页,第445页。

4.召公十九年经文“夏五月戊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郑玉:“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太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左氏曰: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焉可也。’故先儒以为止不尝药加以大恶而不得辞。今愚以传考之,饮止药而卒则是进毒以鸩其父矣,父死而奔则是弑君而避讨矣。苟非其弑父,死之后居丧即位,自有常礼,岂有弃父之丧而奔他国者乎?左氏因史无弑父之文而有饮药之语,又从而推之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于是《公羊》、《谷梁》益得以肆其支离之说,而许止弑父之迹几泯矣。”[注]郑玉:《春秋阙疑》卷三十七,第557页。
第1例,《春秋》经文只记载卫国孙良夫帅师侵宋,而《左传》记载因宋拒绝参加盟会,卫国孙良夫、宁相会同晋国伯宗、夏阳说,以及伊、洛之戎、陆浑蛮氏一起侵伐宋国,并且记载战争详细情况,以传补经。
第2例,经文中仅记载晋人捉拿卫行人石买,而《左传》中记载因曹国被侵之故,晋国捉拿卫行人石买于长子、孙蒯于纯留,并进一步解释虽石买被执缘于其伐曹,然直接导火索是其来聘之时礼节失当,故《春秋》以“行人”书之。同时亦解释孙蒯被执的缘由,《左传》以为伐曹之事实孙蒯、石买所为。如此,《左传》则于史实上对经文有所补充。
第3例,经文记载鲁国取邾国之土地,而《左传》记载“疆我田”,即划定鲁国与邾国的疆界,鲁国以划分疆界为名取得邾国的土地,郑玉认为书“取邾田”体现《春秋》笔削之义,寓褒贬于其中。
第4例,《左传》书“弑”,因史料中无许止弑父之记载而有饮药之语,故托孔子之言“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公》《谷》沿用此说法,后世学者亦多以“不尝药”罪之,掩盖许止弑父之罪行。郑玉“以传考之”,指责此次事件并非“不尝药”所导致的无意之失,而是有意图谋。
其二,传有谬误则稽考诸经。
若传有错讹,郑玉则稽考诸经以证传之谬误,如庄公十七年经文“春,齐人执郑詹”,郑玉解释:
左氏以为郑不朝公,《谷》则以詹为郑佞人。然以经考之,齐、郑同盟于幽在去年之十二月,至是才踰月尔,安得便责其不朝也。若以为佞人,文无所据,况郑之佞人,齐何缘执之?当是以事来聘,应对失辞或礼貌悖慢而见执尔。[注]郑玉:《春秋阙疑》卷八,第111页。
《左传》《谷》于此经处就郑人詹为何被执于齐国的缘由存在分歧,《左传》归之为“郑不朝公”,《谷》则认为詹为郑国奸佞之人。郑玉“以经考之”,推翻《左传》《谷》的判断,并给出自己的解释,以其来聘齐时应对失辞或无礼,故见执于齐。
此处还涉及“以经考之”中“经”的指向问题。前文以传补经,据考证“传”专指《左传》;而此处以经证传,“经”不仅指《春秋》,还包括其他诸经,如《诗经》《周易》等。如僖公二年经文“春王正月,城楚丘”,郑玉解释:
齐桓公城夷仪以安邢城,楚丘以迁卫,皆全之于倾危、奔溃之余,不失兴灭继绝之义,非有专封无王之事也。以经考之,既无封卫之迹,以诗《木瓜》考之,亦不过言其欲报之厚而未尝有封之之语,先儒特因诗之小序有“齐桓救而封之”之说遂起专封之论,今只当以经为正,论其城筑之是非不当,经外立意,言其专封之有罪也。”[注]郑玉:《春秋阙疑》卷十三,第150页。
卫国最初建都于朝歌,为戎所灭,齐桓公帮助君死国灭的卫国于楚丘建立新都。先儒以“齐桓救而封之”之说诟病齐侯代天子行分封之职。郑玉对前人之说提出质疑,以《春秋》经文考之,认为齐侯此举实为“兴灭继绝”之义举,不存在“专封”“无王”之事。后又以《诗经·木瓜》考之,以之为“报之厚而未尝有封之之语”。郑玉这种经传互证的方式显豁出其研治经学不惧繁难、力求客观的审慎态度,这在《春秋》学史上是颇具新意的,更在元末学界成为实事求是研求经典的标杆。
结 语
作为元代《春秋》学史上的典范之作,郑玉的《春秋阙疑》可谓是融合程朱所确立的治《春秋》原则而成,将程、朱未发之论以专书的形式呈现出来,当然并非是承宋儒遗韵,守程朱门户,而是取法有当,多有创见。尤其是其“当阙则阙,疑经有据”的客观的治经精神为后世称赞和沿用,故不仅得到是时学者“甚公且平”的高赞,更受到四库馆臣“平心静气,得圣人之意者为多”[注]郑玉:《春秋阙疑》提要,第1页。的赞许。自北宋转变治经原则,由汉唐重视的注疏之学转为凸显经文义理,郑玉的《春秋阙疑》可谓是胡安国《春秋传》之后又一理学视域研治《春秋》学的扛鼎之作,但不同的是,他着意将走向肆意的义理解经方式拉回客观、平正、理性的轨道上,以求最大程度地尊重经典。总之,郑玉的《春秋阙疑》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元代《春秋》学的独特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尤其是其开创的“阙疑”体例,依傍其卓绝的学术影响,成为后世学者研治经典的典范,这就无可置疑的驳斥了那种不加细究,人云亦云地以“无足可观”给元代经学贴上标签的做法,为我们重新认识和定位元代经学的价值和地位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