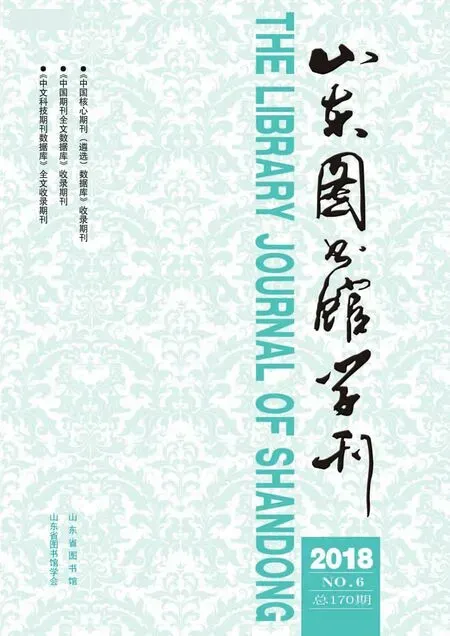庾信集成书及版本考论
刘 明
(国家图书馆,北京 100081)
庾信集是重要的六朝时期文人集之一,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由于作者生活经历的关系,也相应地反映在集子的文本面貌中。即北周宇文逌序二十卷本属“入北”之作的汇编本,而宋代以来的重编本则亦收录南朝诗文在内。其二,由于宋代不重六朝骈文的学术背景,使得庾信集在宋代出现诗集本和所谓的“略集”本,均自二十卷本抽出诗或诗赋重编,形成庾信集流传中的诗集本和诗文合编本两种文本系统。诗文合编本以明汪士贤本为最早,是在作为六朝旧集的二十卷本基本退出流通领域的背景下,明人努力重建庾信集文本的结果。此后的张燮和张溥,以及大致同时期的屠隆均延续了这种路径。其中以张燮本最为完备精审,宜为整理庾信集的底本。
1 庾信集的编撰和流传
庾信是南北朝后期重要的作家,历仕南朝梁及北朝西魏、北周和隋四朝,诗文创作也相应地分为“仕南”和“入北”两个阶段。仕南朝时,《周书》本传称徐、庾父子四人“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客居北朝后,本传云:“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谢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自余文人,莫有逮者。”[1]尽管恩隆礼遇不减南朝,但诗文创作有别于“绮艳”之体,所谓:“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2]之所以介绍庾信前后两个生活阶段,目的是交待他的集子编撰也区别为两个阶段(两者之间的诗文互不包含)。特别是今本庾信集中,主要收录“入北”之时创作的诗文,但也含有“仕南”时所作,表明属后人集合两阶段之作的重编本。
据北周宇文逌《庾开府集序》,庾信在南朝梁太清之乱前,即“京都莫不传诵”时期,已编有集子十四卷。惜该集“值太清罹乱,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军火,一字无遗”,印证庾信尽管身处梁末离乱,仍不辍诗文创作,也续有结集之编。至于序所称的“一字无遗”指的是这些创作于南朝的作品未能在北周时期的北方得以流传,而非并没有在后世流传下来。如《春赋》及《奉和山池》(梁简文帝有《山池》诗)、《将命至邺》二首和《和咏舞》(梁简文帝有《咏舞》诗)诸诗,即均作于仕南朝为东宫学士之时。虽然集子遭到损毁,但仍有部分作品得以在南方流传(与抄本时代的传抄和作品的传诵有关),特别是在隋统一后由南传至北方而保存下来(根据《隋志》和两《唐志》的著录,当并未编入集子,而是保存在其它文献中)。
庾信在北朝的创作,赖所编集子而使相当一部分诗文保存至今。宇文序称:“今之所撰,止入魏已来,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分成两帙,附之后尔。余与子山夙期款密,情均缟纻,契比金兰。欲予制序,聊命翰札,幸无愧色。非有绚章,方当贻范搢绅、悬诸日月焉。”按此序撰写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时信年六十有七。关于集子的编撰,清人倪璠《注释庾集题辞》云:“自滕逌撰集于新野”,“逌之所撰,自魏及周,著述裁二十卷。其南朝旧作,盖阙如也。”认为庾信集乃宇文逌编定,今人多承其说。许逸民先生即称:“《庾信集》最早编成于北周大象元年,是由北周滕王宇文逌编定的。”[3]又有学者称:“由宇文逌出力编辑的二十卷本文集是庾信作品最早的集成本。”[4]细读宇文序,同时证以庾信《谢滕王集序启》,可知宇文逌实际仅撰写集序。“今之所撰”诸语乃述庾信集之貌,而不是说集子是自己所编。序文还透露了庾信家族存在“家世集”(指祖上数代编有文集,语出《梁书·王筠传》)的事实,所谓“或昭或穆,七世举秀才;且珪且璋,五代有文集”,属于南朝典型的文学世家。
宇文序中的二十卷本庾信集乃庾信自编其集,仅收“入北”后历西魏、北周两朝所撰诗文,编完后请宇文逌赐撰《集序》。《谢滕王集序启》即云:“信启伏览制,垂赐集序……故知假人延誉,重于连城。借人羽毛,荣于尺玉。溟池九万里,无踰此泽之深。华山五千仞,终愧斯恩之重。”庾信本人也为赵王宇文招撰写过《赵国公集序》,同样也只是撰写集子的序言。这涉及围绕在庾信身边的一个文学集团,包括“雅好文学”的明帝宇文毓和武帝宇文邕,及作为皇族贵胄的宇文招和滕王宇文逌,营造出“特蒙恩礼”和“布衣之交”的氛围。根据《隋志》的著录,明帝和赵王、滕王均有集,以编集子作为总结诗文创作的方式。《北史·文苑·庾信传》称“有文集二十卷”,即此庾信自编、宇文逌撰序之本(《周书》本传不言有文集事)。史料表明庾信集备受喜好,《北史·魏澹传》云:“废太子勇深礼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称博物。”[5]惜注本早已亡佚。
《隋志》著录庾信集二十一卷,小注称“并录”,则含“目录”一卷在内,实即本传所载庾信编二十卷本(以下简称“庾信编本”)。当然这是唐初秘阁藏本庾信集的记录,不一定完全符合庾信编本之貌。原因是大象元年至隋开皇元年(581)庾信卒尚有两年,其间应有新作未收入集中,故《隋志》著录本或是涵盖了新作诗文的编本,仍釐分为二十卷本。两《唐志》均著录为二十卷(《新唐志》乃据抄自《旧唐志》),则又不计目录一卷在内(《旧唐志》的体例是目录或计或不计)。而倪璠《注释庾集题辞》云:“及隋文帝平陈,所得逸文,增多一卷,故《隋书·经籍志》称集二十一卷。其所摭拾者,大抵扬都十四卷之遗也。”又云:“《旧唐书·志》有集二十卷,与本传合,要称其滕王所撰也”,“庾集在于周、隋,有此二本矣”。受其影响,许逸民先生也说:“有人认为增多的一卷,乃是隋平陈后所得的南朝旧作。新、旧《唐志》又谓《庾信集》二十卷,这或者是将隋二十一卷本重新加以编次的结果。”[6]这是不准确的,《隋志》小注明确称“并录”,则溢出之一卷指目录一卷殆无疑义。再者,隋唐时期流传的二十卷本,即便考虑又编入了新作诗文(应该不包括南朝所作诗文在内),就其主体而言仍是大象元年编定的二十卷本,不存在重新编次的情况。《才调集》载崔涂《读庾信集》一首,其中有两句诗云:“唯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崔涂所读之本当即《旧唐志》著录本。“杨柳曲”,今本作“杨柳歌”。
检北宋《崇文总目》未著录庾信集,推断秘阁未有藏本(根据南宋《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均有著录,推测北宋时期尚有庾信集民间传本)。倪璠《注释庾集题辞》云:“世之所谓《庾开府集》,本宋太宗诸臣所辑,分类鸠聚,后人抄撰成书,故其中多不诠次。”不太清楚倪氏此说的依据。按明朱承爵刻本《庾开府诗集》卷首有《庾开府诗集序》一篇,未署作年,疑此序为宋人所撰(详见下文所述)。倪氏之说或据自此序。
至南宋,《郡斋读书志》著录庾信集为二十卷,称:“集有滕王逌序。”[7]序文和卷第皆相合,当即庾信编本。《遂初堂书目》亦著录,不题卷数。郑樵《通志·艺文略》除著录二十一卷本庾信集外,尚著录《略集》三卷。或称:“三卷本称作是略本,疑为二十一卷本的节选本。”[8]按宋代似已刻庾信诗集(据《庾开府诗集序》推测),疑此《略集》为庾信诗集或诗赋合编之集,乃选刻自二十卷本庾信集,与宋代重古文的学术背景有关。《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为二十卷,云:“今集止自入魏以来新作,而《哀江南赋》实为首冠。”[9]“《哀江南赋》实为首冠”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此赋为庾信集中最佳之篇,再者就是集子的第一篇是该赋。

现存明代庾信集版本有明嘉靖刻《六朝诗集》本《庾开府集》二卷(以下简称“《六朝诗集》本”),系翻刻宋本,反映的是宋代所编庾信诗集的文本面貌。明德十六年(1521)朱承爵存余堂刻《庾开府诗集》四卷本(以下简称“朱承爵本”),是现存最早的庾信诗集单行版本。此后有朱曰藩刻《庾开府诗集》六卷本(以下简称“朱曰藩本”),与前两种皆为庾信诗集编本。庾信诗文合编,现存最早的是汪士贤编《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其后的《汉魏六朝诸家文集》本和《汉魏诸名家集》本庾信集皆以此本为底本重刻(或重印),篇目相同。天启、崇祯间张燮编《七十二家集》本(以下简称“张燮本”)则以汪本为基础,又辑录庾信其它诗文而成,属最为精审完备的本子。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即据自张燮本。还有大致万历间屠隆编刻《徐庾集》本(以下简称“屠隆本”),在篇目上与张燮本基本相同,个别非庾信之作收入其中。
2 庾信集的诗集本系统
庾信集分为诗集本和诗文合编本两种文本形态。诗集本编在宋代,从《六朝诗集》本载有庾信南朝之作,如《和山池》《将命至邺》等,印证诗集以当时所传二十卷本庾信集中的诗作为基础,又附入南朝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几首南朝作品不管是该本还是朱承爵本均附在卷末部分,再次佐证南朝作品属附入的文本属性,也可推知经宋人重编的“诗集”不宜再视为二十卷本六朝旧集的面貌。恰如倪璠所称:“今集中多杂南朝旧作,又非滕王故本矣。”至于明人所编的诗文合编本,乃依据诗集又辑补各体文章而成,许逸民先生称:“今天我们尚能看到的《庾集》早期刊本,就是在宋钞(刊)诗集本的基础上,经明人钞撮《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而成编的。”[13]在重构庾信集文本的过程中,作为六朝旧集的二十卷本庾信集在明代尚有存世,由于秘藏内阁,即便是私藏亦极为罕秘,而并未得以利用。
兹略述诗集本系统中的各本如下:
2.1 朱承爵本
此本现藏国家图书馆(编目书号3540),凡四卷,行款版式为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中镌“庾集”和卷次及叶次。卷端题“庾开府诗集卷一”,次行低十二格题“庾信子山”。卷首有《庾开府诗集序》,卷四末有正德辛巳(1521)朱承爵跋。书末副叶有朱笔题跋,署“述古堂识”,当属过录钱曾跋。书中有朱笔眉批,内容是评点庾信诗的风格特色,颇具参考价值。
按朱承爵跋称:“右集止录其诗,而文不载,观序末引少陵语为正,其刻在唐之后无疑……余因重刻其集于存余堂,故识其略云。”知该本系朱承爵以旧本为底本而重刻,而据刻之“旧本”的成书(或刊印)时间,朱承爵据序引杜甫“清新庾开府”之语而定为“唐之后”。钱曾跋亦申朱氏此说,均未确定具体的时间,缘于《庾开府诗集序》未署作年。细读全序,几乎通篇乃抄撮庾信史传,惟末句云:“尤善工诗,杜子美谓‘清新庾开府’者是也。”考虑到此序所撰并无甚水准可言,推测出自书贾之手,当为宋时所刻。
该本收诗一百六十六篇,其中有四篇系重出,实际为一百六十二篇,另加“乐歌”六篇,总为一百六十八篇(另卷四末补抄《七夕》诗一首不计在内,诗云:“牵牛悲,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值仙槎。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著明季花。”载赵均本《玉台新咏》卷八,略有文字差异)。四篇重出之诗均在卷四,即《从军行》,又见于卷二《同卢记室从军》;《咏春》诗,又见于同卷《五言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之五;《奉梨》诗,又见于卷三亦题“奉梨”;《奉和平邺》诗,又见于卷二《奉和平邺应诏》。尽管属重出之诗,但相校存在文字上的差异,如《咏春》“寂绝想桃源”“狭树分花径”两句,《五言咏画屏风诗》“想”作“到”“树”作“石”。《奉和平邺》“飞风扫邺尘”句,《奉和平邺应诏》“飞风”作“风飞”“邺尘”作“邺城”。推断集子的重编者实际意识到了诗篇重出的问题,由于异文的存在而仍选择收入集中。
2.2 《六朝诗集》本
此本行款版式为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版心中镌“庾集”和卷次及叶次。卷端题“庾开府集卷上”,凡两卷。该本不收《奉和平邺》《咏春》和《从军行》三首重出之诗,其余篇目与朱承爵本相同,总为一百六十九篇。
以该本与朱承爵本相校,存在差异:其一,诗题不同,如卷三《奉报穷秋寄隐士》,《六朝诗集》本“奉报”作“春殿”;卷四《听歌》,《六朝诗集》本作“听歌一绝”。其二,篇次不同,如该本《西门豹庙》后接“乐歌”,次《望渭水》;而朱承爵本则直接接《望渭水》。根据朱承爵本保留的校语,《六朝诗集》本庾信诗集在刊刻中参校过朱本。如卷四《燕歌行》“寒雁丁丁渡辽水”,校语称“丁丁”两字“一作嗈嗈”,《六朝诗集》本校语同;同卷《舞》“讵见地中生”,校语称“生”字“《类聚》作是”,《六朝诗集》本校语同;同卷《奉和同泰寺浮屠》“烟露晚犹滴”,校语称“烟”字“一作轻”、“晚犹”两字“一作晚盘”,《六朝诗集》本校语同。这些校语并非朱承爵所加,而是作为底本的“宋本”即如此,印证南宋末刊刻《六朝诗集》中的庾信诗集选择朱本(准确地说是重刻所据的宋本)为底本。更为直接的证据是《六朝诗集》本卷下《徵调曲六首》其三“浮鼋则东海可属”,校语称“属”字“一作厉”,朱本恰即作“厉”。但校勘表明(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例,朱承爵本为底本,另校以朱曰藩本、张燮本、屠隆本和《诗纪》,以明各本之关系),《六朝诗集》本同时作了校订而存在异文,如:
其一“惊飞每失林”,《六朝诗集》本“飞”作“羽”,曰藩本、张燮本(有校语,“一作羽”,《诗纪》同)、屠隆本、《诗纪》同朱本。
其三“连横遂不连”,《六朝诗集》本“横”作“衡”,曰藩本同朱本,张燮本、屠隆本、《诗纪》同《六朝诗集》本。
其五“唯彼涂穷恸”,《六朝诗集》本“涂穷”作“穷达”,曰藩本、《诗纪》同朱本,张燮本作“穷途”,屠隆本同。
其六“移住华阳下”,《六朝诗集》本作“移往华阴下”,曰藩本作“移住华阴下”,张燮本、屠隆本、《诗纪》同。
其十五“梯冲已鹤烈”,《六朝诗集》本“烈”作“列”,曰藩本、张燮本、屠隆本、《诗纪》同。
其十五“空庭多枉魂”,《六朝诗集》本“庭”作“亭”,曰藩本、张燮本、屠隆本、《诗纪》同。
其十九“浮云飘马足”,《六朝诗集》本“浮”作“轻”,曰藩同朱本,张燮本、屠隆本、《诗纪》同《六朝诗集》本。
其二十一“横石五三片”,《六朝诗集》本“五三”作“三五”,曰藩本、张燮本、屠隆本、《诗纪》同。
其二十七“白露水银团”,《六朝诗集》本“团”作“圆”,曰藩本、张燮本、屠隆本、《诗纪》同朱本。
推断庾信诗集尽管以朱承爵本(反映的宋本面貌)为祖本,但由于《六朝诗集》本校订的结果反而形成两种版本系统,朱曰藩本之后各本在诗集文本的选择上参互校订,并不单纯地祖述某一本。从张燮本的校语同《诗纪》,推断该本中的诗集更多地是直接参据《诗纪》而成。
此外,《六朝诗集》本和朱承爵本也均保留有相互未载的校语,如朱本卷一《宫调曲五首》其二“年祥庆百灵”,校语称“祥”字“一作期”;《六朝诗集》本作“祥”,即未载此校语。又《六朝诗集》本卷上《奉和赵王美人春日》“红输被角斜”,校语称:“输被一作输帔。”朱本即作“输被”,未载校语。上述两例表明宋代尚有其它版本的庾信集流传。
2.3 朱曰藩本
此本现藏国家图书馆(编目书号11146),凡六卷,行款版式为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中镌“庾开府集”和卷次及叶次。卷端题“庾开府诗集卷一”。卷首有朱曰藩《庾开府诗集序》,次《周书庾信传》。
按朱曰藩序云:“予家故有抄本庾信诗二卷,卷次无序且篇章重复,字画舛脱,盖好事家所藏备种数者尔。”所言旧抄本庾信诗疑即《六朝诗集》本《庾开府集》两卷,该本恰存在个别诗篇如《奉梨》诗的重复。至于“字画舛脱”,《六朝诗集》本如《和王少保遥伤周处士》“昔余任冠盖”句,各本“任”均作“仕”;《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八“漫漫疑行海”,“疑”为“拟(擬)”之讹等。朱序又云:“因取是本为之校雠,本内《周圆丘》《方泽》《五帝》《宗庙》《大袷》《五声调曲》诸乐章,则考之《隋书·音乐志》、郭茂倩《乐府诗集》等书。五、七言诸诗则考之《艺文类聚》《初学记》《文苑英华》等书,凡增入诗十二首,非信诗删去者二首,窜正字三百四十有奇,其不可考者姑仍之,釐为六卷,可缮写。”推知该本以《六朝诗集》本为底本,又据它书参校补辑庾信诗篇而成。
《六朝诗集》本收诗一百六十九篇,其中《奉梨》重出实际一百六十八篇,与朱承爵本篇目相同。朱曰藩明确称“增入诗十二首”,经核检,即卷二“乐府”《昭君怨》增益第一首,卷四增益《咏园花》一篇,卷五增益《庭前枯树》《镜》《捣衣》《对雨》《奉命使北初渡瓜步江》五篇,卷六增益《集池雁二首》《和回文》《咏桂》《咏杏花》《秋夜望单飞雁》五篇,总为增益诗十一篇又一首,即朱曰藩本收诗一百七十九篇。至于序所称“删去者二首”,即《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删去《昨夜》和《捣衣》两首。但《六朝诗集》本中的《望月》和《和裴仪同秋日》两篇则未载。有的诗篇刻有小注,如卷四《和颖公秋夜》篇题下小注称:“《初学》作上官仪诗。”与序“考之《初学记》”之书恰相印证。朱曰藩本可谓收录庾信诗较为完备的本子,但也有学者称存在“校勘粗疏,篇目时见重出”的问题。[14]
3 庾信集的诗文合编本系统
大致明万历开始至天启、崇祯间,出现重编庾信诗文集的高潮,目的是重构庾信诗文合编的文本,而非仅局限于诗集。特别是在二十卷本庾信集难以进入广泛的流通领域的情况下(藏在内府,或秘为私人所藏),阅读、研究等各种需求促成重构诗文集是相当必要的。现存最早的一部合编本是汪士贤编本(以下简称“汪士贤本”),即《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由汪氏刻在明万历、天启年间。此后的《汉魏诸名家集》本和《汉魏六朝诸家文集》本庾信集皆据自《二十一名家本》,而系于不同的丛编中,反映明中后期六朝人文集的受欢迎程度。汪士贤之后的张燮,在篇目的辑录上逾于汪本,但也不宜藉此而忽视汪本“导夫先路”的文献价值。万历、天启间屠隆也编刻有庾信集,在诸本中篇目中最多(存在误收非庾信之作);且有屠氏本人的评点,有裨参考。
3.1 汪士贤本
汪士贤编刻《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本,卷端题“明新安汪士贤校”,无序跋。未检得汪士贤之前编庾信集(诗文合编)的记载,推断即出自汪氏编校。篇目同《诸名家集》本和《诸家文集》本,两本卷端均题有“明新安汪士贤校”字样,印证均以《二十一名家集》本为底本(《诸名家集》本系重印,《诸家文集》本则属重刻)。兹以《诸家文集》本为例(现藏国家图书馆,编目书号259)。该本凡十二卷,行款版式为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白鱼尾。版心上镌“庾开府集”,中镌卷次和叶次。卷首有《庾开府集目录》。卷端题“庾开府集卷第一”,次行、第三行均低九格分别题“周新野庾信著”“明新安汪士贤校”。
据目录,卷一收赋七篇,卷二至七收乐府、诗和乐歌一百八十篇(实际为一百七十九篇,《赋得集池雁》《咏雁》两篇即朱曰藩本中的《集池雁二首》一篇),卷八表八篇、文三篇和铭十篇,卷九至十碑十三篇,卷十一至十二墓志铭二十一篇、传一篇,总为二百四十三篇,去掉两篇非庾信之作的《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和《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实际为二百四十一篇。
顺带一提《诸名家集》本,该本卷首有天启丙寅(1626)王元懋《庾开府集序》,云:“近纵读汉魏梁宋诸集,至开府一编。”所读“汉魏梁宋诸集”即汪士贤编本《汉魏六朝二十一名家集》。另有内扉页,题“袁中郎先生订正”,则复经袁宏道校。
3.2 张燮本
此本系《七十二家集》本(现藏国家图书馆,编目书号A01785),行款版式为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上镌“庾开府集”,中镌卷次和叶次。卷端题“庾开府集卷之一”,次行、第三行均低八格分别题“周新野庾信子山著”“明闽漳张燮绍和纂”。卷首有天启元年张燮《重纂庾开府集序》,次宇文逌《庾开府集序》《庾开府集目录》。据目录,该本卷一至二为赋,卷三至六为诗(共计一百八十篇,其中《赋得集池雁》《咏雁》两篇即朱曰藩本中的《集池雁二首》一篇,故实际为一百七十九篇,篇目同朱曰藩本),卷七为表,卷八收录启、书、移文、教和连珠诸体文章,卷九收录序、碑、铭、赞诸体文章,卷十至十二收录神道碑,卷十三收录神道碑和传体文章,卷十四至十六为墓志铭,总计收诗文二百七十六篇。
按张燮序云:“旧刻开府集,亥豕特甚,诸体多阙,因为参错诸选本,细较之而补其未备,用成全豹。旧刻彭城夫人及伯母东平夫人二墓文,盖杨盈川笔也。庸人误收而浅人沿之,冒署子山名入选,大误观者,今为删去。”汪士贤编本恰有序所提及的《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和《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两篇,故“旧刻开府集”即指汪士贤本(尽管屠本亦收此两篇,但张燮本应该并未参据屠本,详下文所述)。卷末附录有“纠谬”,云:“二作载《文苑英华》,列在庾信诸编之后,而不署姓名,世遂误沿为庾集。余初窃疑之,及阅鹏程夫人祖父俱仕隋,伯母东平夫人称祖仕后周,父仕皇朝,则又属周以后人矣。然尚未知出阿谁手也。细阅伯母志后云‘炯忝为太子司直,不获就展’,乃悟为初唐杨炯之作。”也可知张燮本乃据自汪士贤本,又补辑庾信诗文而成。补辑情况如下:赋增益八篇,即《春赋》《七夕赋》《荡子赋》《象戏赋》《镜赋》《灯赋》《对烛赋》和《鸳鸯赋》;表增益四篇,即《贺传位皇太子表》《请功臣袭封表》《为杞公让宗师骠骑表》和《进象经赋表》;增益《温汤碑》一篇。另增设赞、启、书、教、连珠和序诸体文章二十二篇,总为增益三十五篇。在选文上,庾信“仕南”和“入北”的作品均收入集中。整理庾信集,应以张燮本为底本,取其诗文详备且考订精审。
3.3 屠隆本
此本行款版式为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白鱼尾。版心上镌“庾子山集”,中镌卷次和所载篇目的文体名,下镌叶次。卷端题“庾子山集卷一”,次行低三格题“北周新野庾信著,明东海屠隆评”。该本收录庾信诗一百八十二篇(其中《赋得集池雁》《咏雁》两篇即朱曰藩本中的《集池雁二首》,实际为一百八十一篇),比朱曰藩本和张燮本增益两篇,即《赠周处士》和《寻周处士弘让》。另收录非庾信所作的两篇墓志铭,其余赋及各体文章篇目同张燮本。有学者认为屠本是在汪本的“基础之上增补而成的”[15],从篇目情况而言符合实际,更重要的是需要梳理屠本和张燮本的关系。或称:“即使屠本、张本不是嫡系相沿,也应有密切的关系。在张燮‘参错诸选本’之际,也许屠本正是其中之一吧,与汪本也应有源流关系。”[16]从张燮本未收两首诗推测张本并未直接参据屠隆本,同样屠隆本照例误收墓志铭两篇,印证屠本也未参据张燮本。故屠本应该是在汪士贤本基础上独立成编,与张燮本并不存在相互参校辑补的关系。
4 结语
通过本文的梳理,初步得出以下五条结论:(一)由于庾信经历“仕南”和“入北”两个阶段,诗文创作也相应地有所区别,故梳理庾信集要注重根据诗文收录情况界定集子的面貌。作为六朝旧集的宇文逌序二十卷本迄明尚存,诗文仅收“入北”时期的创作。而宋人以来的重编本则兼及南朝诗文。(二)宇文逌序二十卷本乃庾信自编其集,并非出自宇文逌之编,宇文逌仅撰《集序》。至于《隋志》著录的二十一卷本,乃合目录一卷在内,并非收录南朝诗文而溢出一卷。(三)庾信集分为诗集本和诗文合编本两种文本形态。诗集本包括明朱承爵本、《六朝诗集》本和朱曰藩本三种,前两种反映的是宋代的诗集文本面貌,朱曰藩本以《六朝诗集》本为底本又参校辑补庾信诗篇而成。(四)庾信诗文合编本以明汪士贤本为最早,但存在误收庾信文入集的不足。此后的张燮本即据该本又辑补庾信诗文而成编,属最为完备精审的本子。整理庾信集,应以张燮本为底本。(五)屠隆本是在汪士贤本基础上独立成编,与张燮本并不存在相互参校辑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