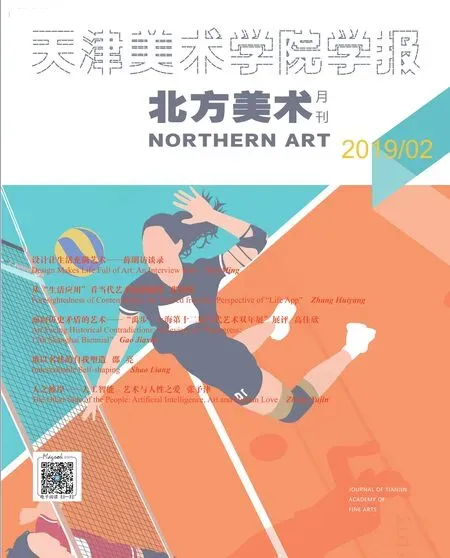谈数字网络语境下的后读图时代
薛 峰/Xue Feng
所谓读图时代,通常是指特定时期内,图像代替文字或与文字同时成为主流的信息传播载体。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在文字出现之前,图画即是人们记载和传播文化信息的方式;而信息从图画向文字的转化,则是信息符号由模拟性向抽象性转换的一个重要过程。
据记载,人类用岩画的方式来表现日常生活、纪录事件、表达情感与愿望的历史约在四万年前就出现了;随着文明的进化,文字成为文化及文献的正统,直到摄影技术出现,影像、声音逐渐成为被认可的文献类型;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之后,数字传播技术带来了信息多形态融合,即一种区别于文字权威、以视觉为主导、以网络为媒介的讯息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化普及。从符号学的角度理解,从文字文本到图像,再到具有了时间性与运动性的影像文本,无非都是不同的信息符号;文字是抽象的,图形是具象的,文字是有着不同“心理印记”的能指,图像则是模拟性的具象化再现。
正如彭亚非在《读图时代》中指出:在当前,以视觉化图像为主导的媒介传播已经形成一种全面覆盖性的状态。[1]这显然是一种视觉文本的“复兴”,因此相对之前不同的时期,我们正处于“后读图时代”。
一、信息形态的转变——语言视听化
正如丹尼艾尔·阿里洪在《电影语言的语法》中指出,“图像”有着“巨大的说服力”,而动态影像化的视听语言则相比较静态的图片具备更生动和丰富的表现力。因为解码难度的降低,这无疑将受众接受信息的过程转换为一种更舒适的状态。
敦煌莫高窟中有大量佛教“经变”壁画,即将文字佛经中的各种教义和理论具象化为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与事件情节,并以绘画的方式记载在洞窟的墙壁上,这主要用于向当时文化普及程度并不高的社会进行宣讲与传播——这种推广与传播正是利用图像符号的“模拟性”特征,让教众摆脱了文字阅读能力的制约,以直观的方式理解教义;而时隔千年,随着敦煌莫高窟“数字敦煌”计划的推进,2014年8月1日,敦煌研究院的敦煌数字展示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巨大的环幕电影院中,人们可以坐在椅子上,以全方位的视角,通过数字动画影像,参观和体验“虚拟洞窟”,其中《千年莫高》和《梦幻佛宫》两部片长均为20分钟的电影,分别以8K的数字画质展示了敦煌莫高窟历史成因、发展过程及其经典佛窟中的彩塑和壁画艺术。[2]
可以想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身处于现代科技文明中的人们已经对当年“壁画”信息的读解方式日益生疏,无论造型的审美标准、法则还是壁画叙事的逻辑,甚至是壁画中出现的各种道具、行为的图像,都与现代生活失去了文化的平等性,从而也失去了“能指”定义中“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于是几乎在全世界的人文景观游览中,“导游讲解”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需要使用抽象性的文字语言来对我们眼前充满陌生感的“图像模拟”符号进行进一步的解说和传达。至今在莫高窟的游览过程中,导游最主要的责任就是利用移动的手电光按照壁画的顺序,以一种类蒙太奇的方法向游客进行讲解,其过程大大延长了游客在洞窟中的时间,带来二氧化碳排放对壁画的加速破坏。而数字敦煌的推出,则是将这种类蒙太奇真正转换为更加全面的电影语言:绘画图像在数字技术中成为动画,在音乐与解说中形成全方位的信息系统,类似于上帝视角的视觉化表现让洞窟的各种细节都一览无余。不仅如此,之后的洞窟的实地游览环节则让观众将刚刚从影像里得出的理解与现实进行对应,从而收获充分的体验感。
由此可见,从图像到影像,“数字敦煌”项目的出现,正是人类文明从读图时代发展到后读图时代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影像的表述促进了符号模拟性、索引性以及抽象性的相互补充与转换,其丰富的表达方式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递的个体到达率与大众普及率。
二、信息接受的转变——阅读体验化
在前面所提到的数字敦煌的案例中,我们除了看到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之外,换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其背后阅读行为的改变,这种行为的改变毋庸置疑建立在数字化技术基础之上。事实还不止如此,如果说360度的环形巨幕让真实旅行中的“游客”身份临时转换为一种“观众”的话,那么越来越多的程序交互技术则让更多的“观众”转换为“游客”的身份。数字敦煌还推出了手机版VR虚拟现实程序,点开社交软件,配合VR设备,即可通过手机对莫高窟的洞窟进行沉浸体验式的游览,观众从现实空间行进到不同虚拟的数字空间并自主式地完成感官化的体验式游览。
(一)感官与心理认知的同步
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虚拟游历式的体验感是当前数字技术所获得的应用性成果,并且产生从感官到心理的多层次影响与作用。
此处所说的体验感,就是指人们通过人机交互设备让视听感官、心理甚至触觉处于动态影像与声音元素共同构建出的数字化环境,从而得到一种身心沉浸的感受。因此体验感可以说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条件:一个是穿行游历在不同的空间,一个是行为化的信息交互。
此处的空间,也被称为“赛博空间”。1982年加拿大的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在小说《全息玫瑰碎片》(Burning Chrome)中首次提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名词,该词由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两个单词组合而成,后被广泛引用于命名计算机以及计算机网络里的虚拟现实,并成为哲学与计算机领域中的抽象概念——这一概念也成为互联网时代时空关系探讨的重要理念。[3]
显然,虚拟的空间并不是指具有实际物理意义的空间,而是由数字网络中不同的IP地址、数字信息将现实世界中的用户连接起来,并构建一种包含时间在内的多维度的信息交互空间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以自己为空间坐标从而展开对各种信息的阅读和传播,但是这种主体认定的方式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被重新界定,文字、图形、影像的信息与每个使用者的真实空间与虚拟空间充分混合,人们不再只是处于信息的外围,而是始终掌握着进入信息内部实施改写的钥匙;用户沿着不同的信息点跳跃式地行进,从而完成自己的知识积累,形成体系与结构——信息的用户始终不停地在不同的非实体景观中穿行,并与现实世界中的空间逻辑进行潜意识中的对应,从而构建一种心理层面的交互。
这种思维方式下的体验感的比较接近于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理论中提出的“游牧”理论:将“思想置于一个平滑空间之中,没有认识所要遵循的方法,没有有组织的规划平面,任由思想驰骋于外部关系的荒野”[4]。
(二)现实行为的规训
说到行为,《汉典》中将其解释为“举止行动;指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出来的外表活动”,而所谓行为化的信息交互则特指在现代电子信息终端设备条件下的一种更倾向于感官式和行为参与式的阅读行为。
从如今已经非常普遍的智能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设备中所运行的程序性交互阅读方式来看,以触摸屏幕的方式参与到阅读中去成为一个典型的行为特征,这体现出后读图时代对现代文明发展方式的重要影响:信息和知识的阅读由脑力劳动扩展到与身体行为相互融合的新领域。这恰恰符合了麦克卢汉的观点,他认为伴随着媒介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人的感官能力是一个“统和”——“分化”——“再统合”形成的过程: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部落文化中的人们以口语相传,因此是以听觉为主体感知牵引全部的感觉协作工作,身体与所处的外部自然环境处于一种平衡的、相互统一的状态当中;但随着文字以及印刷媒介的出现,文化原有的整体性被抽离,逐渐凸显出一种有赖于视觉的细节化特征,因而人们的眼睛孤立地发挥作用,观察的是一种比较单一的具有连续性但又是局部化的客观世界,所以在人类文明从口头语言发展到文字系统时代的过程中,仅仅是视觉文化在人类感觉集束中的延伸与扩张。进入现代电子媒介时代之后,电视继而扩展了视觉与听觉,声画结合的影像甚至扩展了人们的触觉感知,从而回到一种“感觉平衡”的状态。
三、信息交互的转变——感觉统合化
我们从上文可以看见麦克卢汉的时代局限性,电视在视听元素的基础上对触觉的一种影响应该只是心理层面的一种感觉记忆,客观地说是一种错觉;然而,麦克卢汉对于感觉的再统合之说仍旧是非常具有洞见性的,因为随着数字交互技术的发展,各种虚拟信息交互中的现实体验性正在被快速地强化。如,SONY出品的PlayStation游戏机,很早就在手柄研发上添加了力回馈触感的技术,这让坐在电视前的电视玩家能在游戏中更好地真实体验到打击的力量以及某些特有的行动感受;而以苹果iPhone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手机则将这一研究方向进行了更为纵深的拓展,“力反馈”以一种现实与虚拟相结合的方式更为细腻地传递给用户,如,自第一代产品起,苹果其独特的手指操控技术在手机行业引起了强烈反响。2007年苹果公司向专利部门申请了一项新型手指触摸操纵专利,描述了一种应用在虚拟键盘中的力反馈技术,以应用在手机或者其他随身设备当中。将这项技术应用之后,人们在使用软键盘进行输入的时候会感受到与真实按键相近似的回弹触感。这种“触感”由设备内部的硬件及系统中的视觉动画、声音共同协作而成,从而给了用户在使用设备进行信息阅读与交互时前所未有的体验感。[5]
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文字印刷时代对视觉感官的特别要求造成了人们的感觉分离,从而使人对事物抽象及深层次的领域展开探知,形成对环境的巨大的主动性改造作用;但感觉的分离却也会造成人情感的分离,造成人的总体感觉能力失衡或下降。如此,从上述的苹果技术案例来看,人们在科技文明极度发达的今天,不遗余力地投入巨大资源似乎只为找回我们在漫长的文字时代不小心丢失的“触觉”。当今,虚拟现实技术可谓一日千里,用户终端由PC发展到各种形态的移动终端再发展到各类诸如眼镜、手表、头盔等更为符合人们日常行动的可穿戴设施;网络世界的文本叙事也早已进入了以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MR(混合现实)为代表的前沿领域,而具有工业4.0之称的三维打印技术与互联网相互融合形成“物联网”理念,也已经让虚拟数字化的非实体资产快速转化为实体性的“客观事物”——从视听觉到触觉,从虚拟到实体,从理念到现实,科技正在以不可遏制的步伐来实现人类自我感觉系统的再次平衡。
综上所述,“后读图时代”表面是媒介技术的变化带来的结果,深层原因却是媒介作为人体延伸理论中的一种人类自身对体验感觉平衡的天然诉求。纵观科技发展史,这个由卫星信息及光缆技术构建起来的新读图时代才刚刚拉开帷幕,伴随着人工智能及各种可穿戴技术的演进,一种将虚拟与现实进一步深度混合的文化生态正在形成。
正如当今的“动画”一词的定义从“ANIMATION”(动画片)被转换到“MOTION GRAPHIC”(动态图形)层面上探讨一样,视听类图像不再只是特指某种单一的艺术类型,而是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度的碰撞与渗融。未来文化概念和范式如何重构?这是后读图时代给我们设下的一个充满期待的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