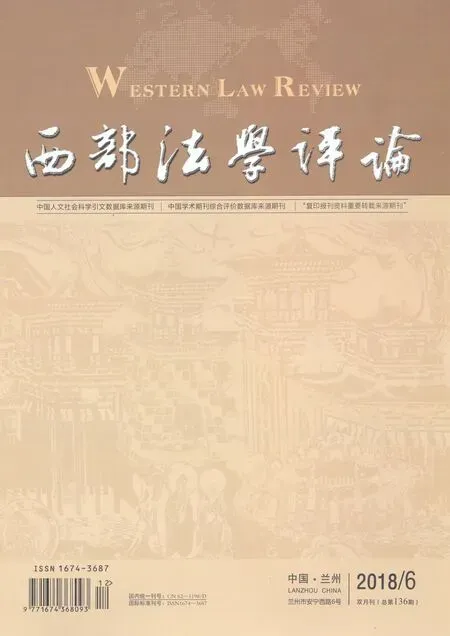试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性质
迟方旭,王 媛
《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七条规定:“国家建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精神象征,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其名称、碑题、碑文、浮雕、图形、标志等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伴随草案的公布,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而又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草案的此项规定明确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地位,为保护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代表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并进而保护英雄烈士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法理根据和法律依据。笔者赞同这一普遍看法,但同时也注意到,草案的该项规定只是指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地位,即指明其应受法律保护以及受法律保护的具体范围,但并未涉及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性质。笔者认为,在法理和法律上明确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性质,是确定其法律地位和保护其不受侵害的根本所在,也是给予其特定法律保护方法的基本前提,意义不言而喻。为此,笔者认为,遵循民法的基本法理,并立基于《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的立法目的,应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性质界定为“整体人格物”。
一、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法律上的“物”
首先,人民英雄纪念碑系民法意义上的“物”。根据物权法的基本法理,民法意义上的物一般应当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特征:存在于人身之外、占据一定空间、能满足于人们的社会需要、能为人所支配与控制且能与他物区分开来。显而易见,作为存在于人体之外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其特有的空间形象矗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之上,承载国家和人们缅怀、纪念英雄烈士的精神寄托,系民法意义上的物当属无疑。由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法律性质首先表现为民法上的“物”,因此,法律对通常意义上“物”的规定,也完全适用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与传统民法上的物相比,还具有一些人格以及情感方面的特征,而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也使得物与人格的界限不再是泾渭分明,物的人格化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愈加明显。
(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实体法规定
由于民法重视物自身的经济价值,忽视了人对物所具有的感情、认可等精神利益,从而多多少少地有悖于民法是以人为中心的市民社会之法这种性质。[注]参见郭卫华等:《中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314—321页。在物权法中,没有将类似于人民英雄纪念碑这类的物予以明确的规定,而多的是保护物权所有人财产利益的法律条文,显然与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相悖。在物之上,是否只存在财产利益?是否存在其他比财产利益更加值得保护的利益?随着社会的进步,司法实践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对于物的损失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的内容不再只是关于财产利益的赔偿,更加注重对精神损害的赔偿。例如,将父母双亲的遗照交给照相馆翻印,由于照相馆的疏忽,将该照片丢失,遗照的所有权人有权请求照相馆赔偿其精神损失,在这种情形发生时,照片本身的经济利益并不高,但是在照片之上所蕴含的情感利益却是其他物所不能代替的,父母双亲的遗照与普通照片不同,该物的丢失将给所有权人带来非常大的情感上的伤害。如果照相馆仅仅赔偿所有权人的经济损失,这违反了法律上的公平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完全忽略了对人格精神利益的保护,也无法达到保护所有人权利的目的。由此可见,物的利益已不只局限于财产利益,还有除了财产利益以外与人格因素紧密相连的精神利益,人与物的二元划分理论已经出现了分歧,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商品化已是既存的事实,物的人格要素不能再被忽略,与此相对应的精神利益也需要相关法律予以保护,这种精神利益依附于物之上,一般明显超过物的经济价值,并且有精神利益的物的灭失往往会给物的所有人带来较大的情感损害。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物,但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仅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在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和“人人平等”的法律观念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物不再仅具有财产价值,其之上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正在成为人们拥有该物的原因所在。
(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所有权分析
如在通常的物之上可以建立所有权,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上亦可建立所有权;对通常的物给予的排除妨碍或消除危险、损害赔偿等保护方法,也可适用于对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保护等等。一般来说,物的所有权人对自己的私有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所有权人亦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所有权与一般物的所有权相比,还是存在一些差别。
第一,就所有权主体而言,物的所有权人是一定的、明确的,其所有权人一般是个体,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上的所有权是基于国家的物权而存在的,其所有权主体一般是国家。第二,就物权的实现方式而言,一般物的所有权人可以将其通过出租、买卖等方式来获得经济收益,而人民英雄纪念碑属于全民所有,具有纪念意义与精神价值,不得将其通过出租、买卖等方式用作经济用途。第三,就处分方式而言,一般物的所有权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如何处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所有权人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意志,还有整个社会和所有人民的意志,并结合社会公共利益方才可以决定如何处分。第四,就善意取得制度而言,虽然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属于物,但就物之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却不能适用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上,善意取得制度的设立是为了保证交易安全以及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由于这里的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都是经济利益,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上的精神利益早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利益,且人民英雄纪念碑特指的是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是不允许进入市场流通的,显然,在物之上的一些制度并不适用于人民英雄纪念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物,但与传统意义上的物又有所差别。人民英雄纪念碑由两部分内容组成,分别是精神利益部分和财产利益部分。就精神利益部分而言,是由国家、社会以及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所享有的,因此,有侵害行为发生时,将意味着对多个群体造成伤害。近日在俄罗斯伊热夫斯克市中心的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儿女军人荣誉城市纪念碑遭涂鸦,破坏者在纪念壁上写“政府”和“灭亡”等字样,这些人破坏了纪念碑的一部分,即纪念碑壁,纪念碑上刻有苏联英雄们的姓名。[注]《俄罗斯纪念碑被涂鸦 写有“政府灭亡”字样》http://news.163.com/14/0311/10/9N23E37V00014JB6.html,2018年4月9日访问。对于城市纪念碑的破坏行为,不仅对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损害,还对在纪念碑之上刻有名字的苏联英雄的近亲属造成精神上的伤害。就财产利益部分而言,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所有权应由国家享有,侵害人民英雄纪念碑将面临着对国有资产的赔偿。

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人格物”
其次,正如上述,更为重要也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它尚具有自身特有的、通常的物所并不具备的法律特征,由此可称之为“人格物”。人格物是一种既具有人格属性又具有物的属性的特殊的“物”,又称为“人格财产”。它与人格紧密相连,由其灭失所造成的痛苦也无法通过替代物予以补救。日常生活中的遗体遗骨以及骨灰盒、父母双亲的遗照等等,虽然均系以民法上物的形式藉以存在,但其所拥有或体现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物,在其之上所蕴含的物的所有人的特殊情感,是物的所有人用来怀念、回想某段特殊而又难忘的情感记忆,因其灭失从而致使物的所有人所遭受的痛苦,无法通过与其类似的其他替代物来予以弥补。拉丁(Margatet Jane Radin)认为如若某物的损失所造成的痛苦不能通过财物的替代得到减轻,那么这项物品就与某人的人格密切相关,而很多情形下,物的“人格”形成就是感情依恋的结果。[注]Margatet Jane Radin.Property and Personhood.34STAN.L.REV.957,1982:957-981.转引自周煜:《“人格物”是一个伪命题吗?——基于行为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就此而言,“人格物”虽为物,但却蕴含着物的所有人的情感,从而具有浓郁的人格气息,成为一种显著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物的一种特殊的物。
(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内涵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的精神象征,它的价值和意义已不仅表现为作为物的一项财产,更是表现为国家和人民精神寄托之所在,其法律性质为“人格物”的结论自然不难得出。因此,就人民英雄纪念碑之所以为人格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出:
第一,用途方面。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英雄烈士而修建的,即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上是有精神寄托的,不同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普通消耗物,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并蕴含了人格利益。
第二,该纪念碑修建所依据的特定事实。人民英雄纪念碑所依据的特定事实是近现代以来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甚至奉献了生命的特定群体已经去世且无法复生,该群体的死亡意味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具有了人格利益。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无私奉献,我们才能享受和平年代的美好生活,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上见证了他们对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蕴含了国家和人民对他们的感恩之情,这种情感寄托于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中,不能被其他物所替代,该碑的损失将会对整个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情感上的伤害。
第三,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上所蕴含的情感价值。人民英雄纪念碑较普通石碑而言,表达的是对特殊群体的缅怀,蕴含着国家和人民对于该群体的情感,这种情感价值在普通石碑上是不存在的,普通石碑的毁损灭失并不会使人们感到精神上的痛苦,其损失表现于财产方面,而对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来说,由于在其之中蕴含了情感价值,它的毁损灭失会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并且难以补救。因此,物本身的价值对人的重要作用是形成人格物的重要考量因素。[注]冷传莉:《论人格物的界定与动态发展》,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第四,物所放置的特定场所、时间。根据草案第七条的规定,人民英雄纪念碑特指的是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同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建成 ,1958年5月1日揭幕,196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就人民英雄纪念碑所放置的特定场所来说,其被放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并位于天安门广场之内,而天安门广场是国家举办重大的、具有全国性活动的场所,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放置于此,由此可见其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意义之重大。就人民英雄纪念碑所放置的时间来说,1958年至今已有60年的时间,不仅年代久远,而且其建成的时间正值新中国建设的初期,人民刚刚摆脱了战争的痛苦和腐朽的统治,全民投入建设新中国的热潮之中,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立也是对当时国家和人民的一种鼓舞。因此,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上的精神价值十分突出,并较财产价值来说,具有独立价值且在受到侵害时难以得到充分的救济。黑格尔也指出,那些非常接近人格一端的物品受到损害,任何赔偿都不能达到“公平”。[注][美]罗伯特·P·墨杰斯、彼特·S·迈乃尔、马克·A·莱姆斯、托马斯·M·乔德:《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张清、彭霞、尹雪梅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二)侵害人民英雄纪念碑行为对应的责任承担方式
当然,对此种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人格物”的侵害,不仅侵害了所有权人的物权,同时还构成了对所有权人情感利益的侵害;侵权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自然不限于财产性责任,也可引发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从而在侵害物权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情形出现时,所对应的解决方式也是不同的。《物权法》第三十二条至三十八条规定了物权的保护方式,即在物权受到侵害时,权利人可以通过请求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以及损害赔偿等方式来救济,毋庸置疑,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属于物,自然也适用物权法之中对于通常意义上的物或一般物的保护,但一般物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保护方式在适用上存在明显差别,即《物权法》中对于通常意义上的物或一般物的保护方式并不能够使人民英雄纪念碑得到充分保护,还需要诸如精神损害赔偿、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救济方式,具言之:
第一,在通常意义上的物或一般物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适用方式上,通常意义上的物或一般物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侵害人返还原物。返还原物后仍具有原物的功能,还可以正常使用,这是在最大程度上对权利人予以救济,但人民英雄纪念碑被侵害人转移脱离权利人的占有之后,再将其恢复至原有形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此时,侵害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行为性质已不同于侵害一般物,甚至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就损害赔偿的保护方式,在适用上也有所不同。一般物的价值是确定的,在侵害人对一般物造成损害时,只需就损害的程度进行确定从而赔偿相应的数额即可,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所表现的物的存在形式(即石碑),它的价值还表现为“人格物”之上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远远超过了物的价值。因此,在侵害人对人民英雄纪念碑造成侵害时,权利人想要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来请求救济,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的难度较大,不仅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而且权利人是否能够通过侵害人的损害赔偿得到充分的救济,也是存在质疑的。
第三,就《物权法》现存的物权保护方式难以对侵害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行为予以充分救济。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有别于一般物的“人格物”,其中的人格因素远远大于物质因素,法律应偏重对其人格因素受损的方面予以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规定,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显然,人民英雄纪念碑属于上述法条中所提到的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毁损时,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而对于一般的、不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来说,通常不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虽然在《解释》中提到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赋予物品所有人可以以侵权为由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这种赔偿通常是被确定为具体的财产来予以救济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物品所有权人进行补偿,可是在特定纪念物品之上(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例),不仅蕴含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的利益,还有英雄烈士的利益,即死者的利益,有的侵害行为(如侮辱、诽谤、毁损等)往往会对英雄烈士等的人格利益造成损害,此时可以通过责令侵害人通过公开赔礼道歉等方式,使英雄烈士等的名誉、荣誉得到恢复,从而使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中所涉及的人格利益得到较为完整的救济。
从总体上讲,由于缺乏民法理论的支持,《解释》的规定事实上只是针对部分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财产的简单规则,不能有效调整其他具有共同属性的财产。[注]冷传莉:《民法上人格物的确立及其保护》,载《法学》2007年第7期。因此,物权法并没有将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纳入到物权保护的具体条文之中。
三、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整体人格物”
再次,人民英雄纪念碑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格物”,而系蕴含整体人格的“整体人格物”。根据“人格物”所承载或蕴含的人格主体类型或所有权人类型,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人格物”分为与个人有关的人格物,与家庭、家族有关的人格物,与社会组织有关的人格物,以及国家之物或文物以及特殊人格物(如:尸体、遗骸、遗骨、骨灰、祖坟等)。[注]冷传莉:《论人格物之实体与程序制度的建构》,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将人格物分为至亲的遗留或者遗物,特定信息的载体,荣誉的载体或某些特殊事件的见证,长时间使用的东西,奢侈品,珍爱的宠物,机器人或拟人机械,人类基因以及对仇人的物品。[注]周煜:《“人格物”是一个伪命题吗?——基于行为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分类,都涉及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者是个人利益,因此可以将“人格物”划分为“个体人格物”和“整体人格物”。
(一)人格物的分类依据
所谓“个体人格物”是指基于私人物权从而物所体现的人格或精神利益具有私人利益属性的“人格物”,而“整体人格物”则是基于国家或集体的物权从而物所体现的人格或精神利益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人格物”。前者所体现的,是对私人物权和私人情感利益的确认和保护;后者所体现的,是对国家或集体物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确认和保护。换言之,对“个体人格物”的侵害,法律所保护的是私人的物权和私人的情感利益;而对“整体人格物”的侵害,法律所保护的则是国家和集体的物权以及社会的、公共的情感利益。人民英雄纪念碑系为国家和人民(这里的人民既包括当时的,也包括将来的)而建,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英雄烈士的永久性纪念设施,其所承载的记忆、所寄托的情感和所体现的人格,是全体人民的记忆、情感和人格;于此而言,它是最典型的“整体人格物”。
(2)“个体人格物”与“整体人格物”
就人民英雄纪念碑与骨灰盒、父母双亲的遗照相比较,其相同点表现在:均为有体物,均具有唯一性、特殊性,以及均具有人格因素。不同点表现在:
第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人格因素所对应的主体具有广泛性,而骨灰盒、父母的遗照所对应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都通过人民英雄纪念碑来缅怀英雄烈士,并且铭记如今的自由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而骨灰盒以及父母的遗照对应的主体是逝者的继承人或具有特殊情感的亲属,这些继承人和亲属都是特定的,是有一定范围限制的,与逝者无关的人灭失了逝者的骨灰盒或遗照,并不会感到痛苦,即对于特定的人来说是人格物,对于除了这些特定的人以外的其他人来说,与一般的物无异。
第二,稳定性存在差异。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理论,随着一个物品的使用,其价值会不断耗损。这种耗损最终可能导致物品的主要部件因为磨损等不可避免的过程而失去功能,或者因为技术更新等原因,使得产品失去了被继续使用的必要,这个过程叫做折旧。[注][美]萨缪尔森《微观经济学》(第19版),萧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116页。而人格物与一般物的价值损耗规律是不同的,人格物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具有价值。不仅一般物与人格物的稳定性存在差异,个人人格物与整体人格物的稳定性也存在差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稳定性更强,国家对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置是永久性的,其存在是为了让人民世世代代缅怀为国家作出牺牲和贡献的英雄烈士,这种尊敬之情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的。而骨灰盒及父母双亲的遗照这类个人人格物,虽然可能会随着香火的延续而代代相传,但其稳定性远比不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比如,在家庭的搬迁过程中,可能造成骨灰盒或父母双亲遗照的丢失或灭失;同时,若不重视对骨灰盒、遗照的保护,这类物品极易受到破坏,而失去其原有的样貌;再次,随着时间的流逝,年代越为久远的亲属,可能对已逝长辈的情感越来越淡薄,这类物品所具有的人格因素也随之越来越少。
第三,人格物的转化性。作为整体人格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唯一的,特指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之上所蕴含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是确定的、一定的,而像父母双亲的遗照这类的个体人格物,因其具有唯一性才可被称之为人格物,若是该遗照又通过其他亲属的赠与或是在房间的某个角落被找到类似的,则父母双亲遗照的性质将从人格物转化成为一般物,便不再具有人格物之上的特殊属性,也不得向侵害人要求高额的精神损失费用。而人民英雄纪念碑通过法律的规定、被放置的特定的时间地点等因素,其所存在的形式和法律属性是被固定了的,很难发生像个体人格物转化成为一般物的情形。侵害人对人民英雄纪念碑造成的侵害,无论其主观上为故意还是过失,也不论在什么年代,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上的赔偿都是较大的。
第四,法律对个体人格物与整体人格物的保护程度不同。在草案中,国家对于人民英雄纪念碑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分别是第七条的第三款规定:人民英雄纪念碑及其名称、碑题、碑文、浮雕、图形、标志等受法律保护;以及第八条的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和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对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对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依法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而对于骨灰及父母双亲遗照等个人人格物的保护,实践中多以使侵害人向被害人赔偿精神损失的方式予以解决。
第五,信息对称的程度不同。人民英雄纪念碑这类整体人格物,因为其本身所放置的时间、地点,使其具有了相应的公示性,其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是众所周知的;而一般人格物的公示性较差,但从外观上看,与一般普通物品无异,只有与该物品有特殊情感的人才知道其之上的价值所在。由此,损害个体人格物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可能是过失,并不知道该物品对于特定人的意义与价值,此时,侵权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将对其所承担的责任大小有所影响。对于作为整体人格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来说,无论侵权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其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不会有较大的差别。
第六,侵害的法益与造成的影响不同。就“整体人格物”的侵权行为而言,该行为侵害的是整个国家或者集体的财产权和情感利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并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就“个人人格物”而言,侵权行为侵害的是特定权利人的财产权和特殊情感利益,虽然也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但受侵害的群体较小,没有对社会产生较大的不良影响。
(三)人格物与“人格利益”
不论是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代表的整体人格物,还是以骨灰、父母双亲遗照为代表的个体人格物,我们不难发现,人格物多与死者的人格利益息息相关。虽然,在人格物损害纠纷中,权利人多主张的是对自己精神利益造成损害的赔偿,但是在侵害行为发生后,不只是对权利人造成了损害,对于人格物的原有人或是相关人也会造成损害。举出这样一个例子,甲生前是形象良好的明星,在大众之中有较强的号召力,乙是甲的独生女,在搬家的过程中不慎将甲的遗照遗失,并被丙拾得,丙将该照片卖于丁公司,丁公司把甲的遗照用于商业展览与宣传。在该案例中,不仅是遗照现有权利人乙的利益受到了侵犯,遗照原有人甲的肖像和姓名也受到了侵犯。诚如德国联邦法院在Mephisto案(BGHZ 50,133)所强调:唯有当个人能够信赖其生活形象于死后仍受维护,不被重大侵害,并在此种期待中生活时,宪法所保障之人的尊严及个人在生存期间的自由发展始能获得充分的实践。[注]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9页。
对于涉及人格物纠纷的案件中,我们是否有必要对死者人格利益也予以救济呢?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原告是否提出了对人格物相关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诉讼请求,根据《民事诉讼法》中之不告不理原则,只有当事人在诉讼请求中主张了,法院才会予以审查。
第二,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有些涉及人格物的案件中,侵害人的行为不会对人格物相对应的死者人格利益造成伤害,或者伤害程度很小,此时,没有必要单独就死者人格利益予以救济,在对人格物现有人赔偿时,也能对死者人格利益予以一定程度上的救济。
第三,在涉及整体人格物的案件中,例如,行为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做出一些亵渎、侮辱性行为时,人民英雄纪念碑之中所缅怀的英雄烈士等的人格利益显然受到了侵害,此时,侵害人不仅侵害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缅怀的英雄烈士等的逝者人格利益,还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普通民众的情感,均造成了伤害。日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从环球网、网易、凤凰网等多家网站获悉,两名男子近日身着侵华日军军装在南京紫金山抗战遗址摆拍合影。他们头戴侵华日军军帽,其中一男子手持军刀,另一人拿着带刺刀的步枪,上面绑着日本“武运长久”旗。[注]《两名男子穿日军军装摆拍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谴责》,http://news.youth.cn/sh/201802/t20180222_11429341.htm,2018年4月10日访问。这两名男子的行为引起了公愤,遭到了社会的谴责,纪念馆方面认为其是拿民族的伤痕开玩笑,最后南京警方对两名涉案人分别予以行政拘留十五日。该两名男子的行为,是对整体人格物——南京紫金山抗战遗址的侵害,也是对为我国革命战争时期作出巨大贡献的英雄烈士以及被敌方惨忍杀害的无辜民众的亵渎、侮辱行为,分别对英雄烈士、已逝无辜民众以及国家、社会、逝者的近亲属的利益造成了侵害。
(四)人格物的保护方式
就“个体人格物”和“整体人格物”的保护方式来说,“整体人格物”尚且可以通过《解释》第四条予以救济,“整体人格物”属于第四条中所提到的“具有人格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但对于遗体、遗骨、骨灰等的处理,《解释》并没有将其归入具有人格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之中,而是在第三条规定: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的,其近亲属因该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笔者认为,遗体、遗骨、骨灰和父母双亲的遗照均属于“个人人格物”,它们都是以物的形式藉以存在的,并蕴含了物的所有人的特殊情感。将遗体、遗骨以及骨灰等纳入人格物的范畴,更有利于明确其法律性质,从而更好地救济权利人的权利和精神利益。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若人格物为国家之物或者文物之类的,则其管理和处分不仅必须符合国有资产管理和处分的规定,有关文物的管理和处分还必须符合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否则违规处理不仅可能构成人格物的民事侵权,严重者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注]同前引[7]。即对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保护上,不仅可以通过民事法律来予以救济,还应结合国有资产管理的处分规定以及文物保护法等,毁灭、损害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整体人格物”的行为,较侵害“个人人格物”的行为来说,侵权人所需要承担责任的种类更为多样,分别涉及到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以及行政责任等,这与“整体人格物”之上所蕴含的特殊的情感利益有关。
综合上文的分析,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人格物的救济可以通过《物权法》中关于物的保护方式、《解释》之中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的保护方式来予以救济,虽然在物权法中没有将人格物纳入其体系之中,但笔者认为:人格物是物,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物,是对人与物的二元论的挑战,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理念的更新,法律具有了越来越关注人本身的趋势。人格物是现实存在的并且经常会在实践中产生纠纷的,不能仅依据《解释》来救济相关受侵害主体的利益,就算将人格物纳入物权法的体系之中,物权法关注的还是物的财产利益,而人格物最为显著的特征为精神利益远远超出物质利益,也不能予以充分的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