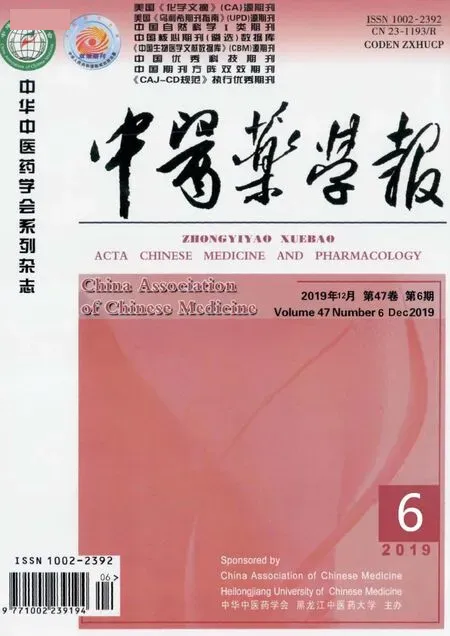马王堆医书方剂用方特色及其价值研究
戴子凌,雷霆,赵群菊,胡方林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208)
马王堆医籍文献中,计有方剂学的著作有4种,包括《五十二病方》现存医方283个、《养生方》现存88个药方、《杂疗方》可辨认药方38个、《胎产书》现存21方[1-3]。以《五十二病方》代表,记载了马王堆医书按疾病分类组合、方剂剂型、制剂、煎药方法、服用方法、服用时间、服用禁忌及所反映的功能、配伍、辨病辨证经验、医治法令规律等方剂学内容,初步体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理、法、方、药”具备的中医学诊疗思维方法。所载医方古朴而广泛,选方用药特色鲜明,反映了先秦时期方剂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1 五十二病方
1.1 用方特色
1.1.1 《五十二病方》是先民在劳动中积累的宝贵医疗经验,在群众实践中得到验证
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以上四本医疗方剂中,方剂数量现存能查最为丰富、涉猎的医疗范围也最广的属《五十二病方》。书中同一药物名称、同一疾病疗法存有差异性,甚至字的书写前后亦不尽相同,不少条文后附有“良”“令”(“良”的假借)“已验”“尝试”(曾试用有效)等字样[4]。如《五十二病方·蚖篇》载有一方:“煮鹿肉若野彘肉,……,饮汁,良。”《五十二病方·諸伤篇》治金傷止痛一方:“取鼢鼠,……,至不痛而止。令。”又如《五十二病方·胻燎篇》治小腿烧伤一方:“夏日取堇枼,……,皆以口咀而封之。……,此皆已验。”后附注上述字样,此不一一赘述。这些条文标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五十二病方》应是人们在实践中长期搜集整理而成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成果,是一部注重经验的实用型方书。
1.1.2 单方为主,复方为辅,反映了方剂形成中,早期阶段临证处方用药原始而古朴的特色
全书现存可考的189方中,一、两味组成的方剂分别为110方、45方,占总医方数的80%,可见方的组成单味、两味药为主,基本属于单方性质[5]。医方中记载了不少“荅”类、“稻”类、“麦”类、“艾”“椒”“薤白”“甘草”“冬葵子”“彘”“鼬鼠”等常见动植物类药物单独或两味药组合应用的经验,用药简便中或有“五谷为养”“五菜为充”及“五畜为益”的讲究。不难窥见方剂形成阶段中,早期注重简便廉验原始而古朴的特质,也是其较马王堆其他医籍方剂内容更为淳朴的地方。
1.1.3 单方到复方,组成及加减之法反映了方剂应用中“辨证施治”思想和“立法遣方”意识的萌芽
《五十二病方》收集的药方少则一味药,多至七味组成,三、四味药及以上组成的复方虽未几,但组成、药量药味的加减变化已初步具备了立法遣方的意识,部分复方临证化裁运用的实例被记载。如《五十二病方·睢(疽)病篇》以白蔹为主治疗疽病[4]:对于药味增减的方剂配伍有如下4方加减变化:一方是以“白蔹”和“罢合”两药治嗌疽,一方是以“白蔹”“黄芪”及“黄芩”三药治血疽初起,一方是以“白蔹”“黄芪”“芍药”及“甘草”四药治未溃疽病,还有一方是以“白蔹”“芍药”“黄芪”“姜”“椒”“桂”及“茱萸”七药治已溃疽病;对于药量增减的方剂配伍如上所述:治疗已溃疽病以白蔹、黄芪为主药,若骨疽,倍白蔹,肉疽,倍黄芪,肾疽,则倍芍药的具体运用涉及七味药的加减化裁。虽说此种加减化裁运用的实例记载较罕见,却可看出医疗方剂已摆脱了用单味药治病的初级阶段,开始应用两味及以上药物配伍组合的复方,是早期传统中医辨证施治,随证化裁的临证诊疗经验的提炼。单味药向多味药配伍运用是单味药功用进一步强化扩大,调整偏向的重要途径,反映了早期方剂的发展与进步。
1.2 价值研究
1.2.1 《五十二病方》是湖湘区域乃至全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医方著作
其一是从文字的抄写年代来看。据考证[4],帛书《五十二病方》的字体虽大体属类秦系小篆文字,却不同于标准小篆,文字结构和秦铭文“草率”颇为相似,部分写法还出现在秦统一前的文字中,与帛书《老子》甲本明显带有篆刻意味的隶书又不尽相同。帛书《五十二病方》的卷尾使用空白处补加医方,目录中并未见类似于“噬”的标题出现,但这些行的字体却与帛书《老子》甲本相似,如“解”“暴”“弱”(《老子》甲本32行、138行、166行)的文字,“此”“之”写法更是相同。由此观之,《五十二病方》的誊写年代应早于《老子》甲本,虽然后者的誊写年代存有争议,但综合分析不晚于汉初,故前者的誊写年代应不晚于秦汉之际。其二,从医、巫斗争的程度上来分析。春秋之际,是医、巫均衡酣烈斗争的时期[6],《五十二病方》所载医方与祝由相关的29首,仅占全书10%左右,整体而言,治病以医药占主导,经历“天命、天道、道气”观念的演变,自然哲学从巫术中逐渐分离,可见《病方》成书年代应在春秋后战国之际;其三,就其内容来看,部分方药及(或)其医疗用途为后世医学著作所不载,或所载同名方药主治不同。如《五十二病方》载有“茯苓、茜草”治皮肤病的单方,而不见于其他医籍,用治癃病的“景天”在《神农本草经》中却只记载可用于治疗火疮、火热等症[7]。又如“诸伤”“蚖”“疣”“癃”“痈”“巢者”等名,涉及蛇咬犬啮、“蝎子螫伤”“淋病”“腹股沟疝”和“小儿惊风”等方面的治疗方法在后世医籍不为所见,所载内容弥补了我国医学史的缺憾。《五十二病方》出土长沙马王堆,地属汉代荆楚区域,虽不能完全确定此书为荆楚人所作,却也通过某些侧面展现了先秦湖湘医学的面貌,亦可由此窥见湖湘医学之渊源,这部历史悠久的医方专书对于湖湘中医药学乃至我国医药学史的钻研意义匪浅。
1.2.2 《五十二病方》医方的基本内容,开始反映先秦时期处方用药的整体外观
《五十二病方》载有方剂的分类、组合、剂型、制剂、用药法度及所反映的功用、配伍、辨病辨证经验、治疗法则等内容。如在分类上,以病列方,全书五十二种疾病按当时的分科诊治范围统计:属疡医的33种、疾医的19种,绝大部分病一问即知、一望即得[8]。可见分类简朴。在组合上,变方灵巧,联合使用。与《内经》中联合使用的医方占全书2/3相比,《五十二病方》207个联合使用法占全方总数283个的3/4,相比《内经》医方内容更进一步,一定程度上为先秦之后药物及方剂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其制剂与用法,精巧实用,赋形于剂,剂型分类综合了疾病轻重缓急、寒热虚实、病者体质、年龄等因素,并涉及天然药物、食疗、药末、丸、水、酒、醋、动物油脂类以及其他赋形剂[4]。在剂型计量上,有菜品、鲜草枝叶类的“个”“把”“束”,有粮、液类的“合”“升”“斗”,果品类的“实”“颗”,粉末类的“撮”“节”等[4]。与汉代通用的“株”“分”“钱”“两”“斤”等常见度量单位相比,大量估量和计算单位的使用,使得《五十二病方》方剂剂型剂量更显雏形,这在后世医方中亦有迹可循,《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不少计量单位就有这样的模型[8]。在治疗法度上,“随证立法,依法选方”,综合了“汗、消、清、温、补”等法的单用及联合使用,“法中有法、法不外发”的精髓融汇于其中。由此可见《五十二病方》不仅方药兼备,且理法内寓,初步体现了先秦时期处方用药的整体外观。
1.2.3 《五十二病方》所载方药内容反映了荆楚地方特色
其一是载有常见于湖湘地区的疾病。如医方记载了治蛇或蜥蜴咬伤内容,见于《五十二病方·蚖篇》第51~62条。《蛭蝕篇》原文49~50条记载了治疗水蛭、山蛭、蚂蟥咬伤的医方。另有“蛊”(血吸虫、丝虫类似病)等地方病名见于书中。其二是某些医方药物列有湖湘俗称,医书中记有湖南方言。《五十二病方·牝痔篇》:“青蒿者,荆名曰萩”,又“者,荆名曰盧(卢)茹”。又《尔雅·释地》言:“汉南曰荆州。”即相当于今湖南、湖北等地。萩、卢茹均是青蒿、在湖湘地区的称法[9]。还有《五十二病方·婴儿索痉篇》原文24条中特指“蚂蚁穴丘土”方言的“封”字,在西汉杨雄《方言·卷十》一书有记载有:“封,场也。楚郢以南,蚁上谓之封。”是有关荆楚的方言[10]。因此书撰写于西汉,内载楚郢以南为长沙马王堆汉墓与江陵张家山汉墓所在,故此处“封”,应是蚂蚁穴丘土之物。其三是考察不少药物的产地在荆楚一带。《五十二病方》中不少医方载有罢合(百合)、白蔹、地肤子及酸浆之类的药名。《名医别录》考据了相关药物的产地:百合为“荆州”、白蔹在“衡山”,地肤子、酸浆生产于“荆楚”[11]。可见不少药物生长于湖湘或江南一带。
2 养生方
2.1 用方特色
2.1.1 《养生方》用方命名思维方法直接明了,多依方剂的用途、制用方式等来命名
如“用少方”,主治男子精液短少,阴部寒冷等症候[12];“益甘方”“益甘”为增益,甘美之意,有提升女子新陈代谢,增进阴道正常分泌的效应[12];“巾方”,即用布巾涂抹药膏、浸泡药液后,制成“药巾”供外用[12];“洒方”,在《说文水部》一书里解释为:“洒,涤也。”意为男子外用的洗药方,以药水洒洗男子,使其强健有力等等[12]。可见当时人们在用方命名上开门见山,直接明了。其用方命名之法可见一斑。
2.1.2 《养生方》善用辛温、滋补,重视方药与症的关系
如:常服桂、姜、细辛、藁本、防风、紫苑等辛温药物,稻米、麦、蘖等谷物熬成的粥糜及家禽家畜、蛇、蜂类动物性滋补品[13],可见当时是十分强调温补的,或许可以此推断,当时有不少人体虚易感寒症。这可能与当时的地理气候、生活条件、身体素质和疾病流行等因素密切相关。可见古人已经非常重视方药与症的关系。
2.2 价值研究
2.2.1 体现了“聚精、养气、存神”的中医养生理论核心
《养生方》中的导引、房中术,药物、饮食调理法富含养生理论,其将中医养生的核心归结为“聚精、养气和存神”三方面。条文89“有气则生,无气则死……”指出了精、气、神对于人体生命的重要性[4]。此外,第91条“……益生者食也,损生者色也……”指出性生活处理不当致罹患疾病及早衰短寿[4],莫若“欲修长生之道,在乎不伤不损”罢了。又黄帝询问曹熬、容成等人:“民何得而生,何得而死?”[14]此无外乎摄精存神调气之道。“精”“气”“神”作为中医专有名词,是先秦哲、医交融的产物。其中人身之“精气”指的机体的“津液”“血液”“营卫”这些精粹内涵,还包括具有生殖作用的相关物质;而“神气”则是显露于外的精神与气色。保养精、气、神是驱邪扶正、益寿延年的重要原则,内寓于《养生方》摄生益寿的精神内涵里。
2.2.2 总结了重要的养生方法
除导引图外,《养生方》中载有某些导引养生法的文字。如《养生方·食引篇》载有“食引:利益氣。食飲恒移音動之。卧,又引之。故曰:飲有教誨之。右引而曲左足”[4]。此条文所在导引法似与《十问》之“八问”篇所载“觉寝而引阴”有一定关系[4]。本篇目取义不详,或兼食疗与导引二义。此外,还涉及了调摄性功能障碍的药物医治经验等。
2.2.3 不乏药物养生的方药
滋阴壮阳如:治男子阳痿之“老不起方、不起方”,治精液短少伴阴部寒冷症候的“用少方”[4],提升女子新陈代谢及增进内分泌机能,调整肾阴与肾阳的均衡,刺激阴起阳益的“益甘方”,增强女性生殖机能的医方的“勺 (灼) 方” 等[15];延年增寿如“益寿”篇,服食“泰山、少室之骈石,醇酒浸渍后的脱骨马脯肉及煅乌喙等”[4];增进体力如“治力”篇之治力方、“益力”篇之益力方等”[4];滋养理中如“醪利中”篇之补益中气醪酒方等[4];疾行善趋如“走”篇之健步方,“疾行”篇之快步行走法等[4]。养生补益多为房中医方。
3 胎产书
3.1 用方特色
《胎产书》中服食“九宗之草”延嗣,依据病证与药物的特性进行选方用药。对于此处,帛书整理小组注曰:“疑即《尔雅·释草》轨鬷。一说,九宗为山名,在今湖北孝感境。”[16]据已有文献记载推断“九宗之草”或为“韭菜类似物”[17]。“九宗之草”现虽无法考证确属何物,但当时人们渴求孕育子嗣,将许多繁殖力旺盛的植物赋予神秘的功能,来作为宜子的灵物,或正因此“九宗之草”具有分蘖多、繁殖力盛的性能,是以古人给它取名之。由此可见古人多依据病证与药物的特性进行选方用药。而从“夫妻共以酒,饮之”的服用方法中亦可窥测古人已意识到不孕有男女双方的原因,反映了当时的胎孕医疗思维的进步。
3.2 价值研究
《胎产书》关于胎教的认识大大提早了胎教文字的记载年代,是我国目前出土最早的妇产科著作[15]。追溯产前教育的历史,并非详尽无遗,但《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中皆有“逐月养胎”的说法和方药记载,一度被认为是胎教相关内容的最早记录[4]。帛书前半部“禹問幼頻篇”询问胚胎形成和产妇调养法,类似于《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中所载“十月养胎法”,记载了胎儿逐月生长发育特征和养护事宜,其内容则更为古朴,现存二十一方,包括安胎、保产及求子嗣等[18]。马王堆医书《胎产书》的出土,其实物证据大大提早了胎教文字的记载年代。因此,这本类似于古医籍《产经》有关胎产的妇产方技专书,应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专论妇产科的著作,其对求子、养胎、产后处理等有关胎产的宜忌有一定的见解。
4 杂疗方
4.1 用方特色
《杂疗方》中,强调“恒服”,体现中医因时摄生、择时施法的时间医学思想。如“益内利中修方”有言“始饮,饮一卵,明日饮二卵,【明日】饮三卵;其明日复饮二卵,明日饮一卵。恒到三卵而【却,却】到一卵复【益】。意即饮醇酒鸡卵按五天一个循环,第一、二、三天分别吃一个,两个,三个,到第四天改吃两个,第五天又恢复到吃一个。也就是说,每五天吃九个鸡蛋,如此周而复始,往复循环。同时“恒以二、八月朔日始服”,此两月正值仲春、仲秋,春分、秋分两节气亦分别安排在这两个月里,是春、秋二季最适中的时节。帛书认为,“服之二时”,即连续春、秋两季服用,可“使人面不焦,口唇不干,利中益内”,因而强调“恒服”[19]。古人讲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由此可见,此种服法可能与时令恰好相适应,体现中医因时摄生、择时施法顺应自然阴阳变化规律的时间医学思想。别致讲究的服食法,亦反映了当时人民服用方药注重保健的风俗习惯。
4.2 价值研究
《杂疗方》是独自成卷的帛书,并以资料汇编的形式呈现,是一部重在讲述养生内容的方剂学医著[20]。从出土的资料来看,主要包括了增强男女性功能的方法,盖标“内加”者,属男性性机能补益方,盖标“约”者,属补益女性性机能处方;产后埋藏胞衣的方法;强身益内、抗老延年的方法以及预防和治疗蜮、蛇等毒虫咬伤的方法。还有“桃枝”“喷”“呼”“吙”“涂”“摩”等内容,讲述了“用桃枝避邪”“喷水”“呼号呼气”“用土块吙药物摩擦患处”等禁咒医疗方法。这些医方著作所载内容繁琐复杂无疑具备了资料汇编的性质,集房中药物养治、食疗、禁咒于一体。因文字残损,能辨认药物医方亦有限,但不乏独到的医药记载,如“女萝”“石脂”“鳖”等为本书独载,未见于《五十二病方》等其他马王堆医籍文献中。纵观全书,方药的运用强调养生保健,注重性机能疾病的防治,对中医养生学和性医学的价值贡献不菲。
5 小结
综上,马王堆医籍文献方剂内容颇丰,临床应用涉及到内、外、妇、儿、骨伤、五官、养生及性医学诸科[21-25],医方内容古朴而广泛,初步体现了中医诊疗“理、法、方、药”从理论到实践的思维方法,临证选方用药理法内寓、特色鲜明,反映了先秦时期方剂学的一个重要侧面——其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初露端倪,方药学体系初步建立,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形成发展扎下了根基,可为现代医学方药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相关参考。先秦两汉是中医方剂药物学及其学术体系的奠基时期,笔者认为,通过研读,梳理先秦两汉时期与马王堆医书方剂相关的医药文献、充分挖掘马王堆医书方剂的配伍、功效、用药法度等内容,探索马王堆医书方剂内容的潜在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意义非是囿于古方今用,或能从马王堆医书的用方经验中重新解读先贤处方用药的思路,提炼方法和规律,丰富方剂学学科内涵,以指导现代医疗实践。然而,从目前收集的数据来看,国内外对马王堆医学文献方剂领域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其研究内容多限于对药物的单纯解析,尚缺乏对整体方剂内容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马王堆医书方剂特色不得以充分体现。介于“马王堆医书”出土时所载文献内容已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书中出现的众多药物未在《神农本草经》中体现,如今,亦无从考证,研究马王堆医学书籍方剂内容困难重重,马王堆医学文献的特殊性决定了此领域的研究应是漫长又曲折的过程,还得循序渐进,徐徐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