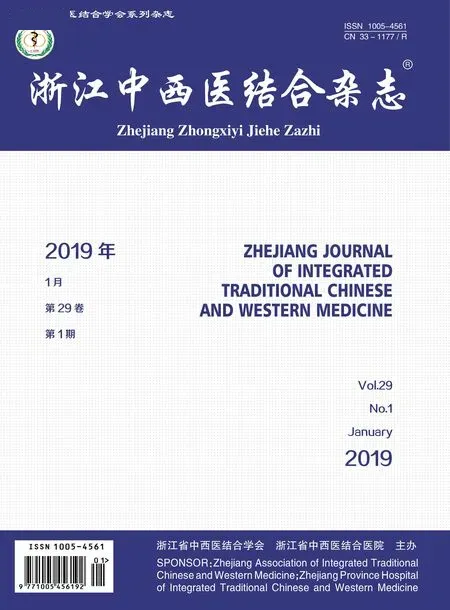吴玉生辨治肝癌经验
季兴祖 周敏华 刘忠达 李 权 刘笑静 张尊敬
作者单位:浙江省丽水市中医院肿瘤科(季兴祖,周敏华,刘忠达,李权,刘笑静)、感染科(张尊敬)(丽水 323000)
肝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及死亡率均仅次于肺癌,位居第2位[1]。肝癌起病隐匿,早期难以发现及诊断,且恶性程度高,进展迅速,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属中晚期,失去手术最佳切除时机,而放化疗及介入等治疗对肝癌的疗效不理想,中医药成为治疗肝癌的重要手段之一。吴玉生教授系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专注于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工作已逾30载,擅长中医药治疗肝癌,强调“辨病-辨证-辨症”诊治思路,临床疗效显著。笔者有幸跟师侍诊,临证遣方,获益匪浅,现将临床跟诊心得总结如下,以飨同道。
1 立足病机,主张肝郁脾虚为肝癌之主要病机
中医对肿瘤的认识渊源久远,但中医古籍中并无肝癌之病名,根据临床表现,归属于“肝积”、“癥积”、“臌胀”等范畴。吴老师参验历代各医家之论说,结合自身临证体会,认为肝癌的病位在肝,与脾脏密切相关。肝主疏泄,若情志不舒,肝失疏泄,气机郁滞,则津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痰湿等病理产物随之而生。瘀血、痰湿既是病理产物,亦是致病因素,郁久化热,热极生火,火毒日久凝结成积。而肝脾为相克之脏,肝气郁滞,横克脾土,脾失健运而痰湿内生,痰湿郁久化热,湿热蕴结,瘀毒内生。因此,肝郁脾虚乃肝癌发病之主要病机,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痰瘀热毒之症。
2 辨病、辨证、辨症论治三位一体,层次分明
2.1 辨病论治,取西医病名之所长,避中医病名之所短 肝癌中医病名繁杂,且众多病名以症状命名,为肝癌明确诊断、确立理法方药以及总结经验均带来一定困难,而西医病名、病位、病理明确,临床诊断统一。因此,中医辨治肝癌时辨病论治尤为重要,取现代西医病名之所长,避中医病名之所短,力求诊断之明确。吴老师倡导治疗肝癌首应“辨病论治”,根据肝癌“肝郁脾虚”之主要病机,并结合临证经验,自拟肝癌经验方,临床疗效确切。具体方药:柴胡、白芍、枳壳各 15g,太子参 30g,白术 5g,砂仁(后下)6g,五爪龙、薏苡仁各30g,甘草6g,全蝎5g,预知子、白花蛇舌草各30g,郁金15g。本方根据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汤为基础方化裁。方中以柴胡疏肝解郁为主,配合枳壳、郁金、预知子疏肝行气止痛,助柴胡以复肝用;白芍养血敛阴、缓急止痛以补肝体;太子参、白术、薏苡仁、砂仁、甘草益气健脾,既可实脾土以防肝病传变,亦可补气生血以助养血柔肝;五爪龙、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更以全蝎攻毒散结,以加强抗癌之功。本方补肝体,疏肝用,气血并治,肝脾同调,并且辨病选用具有抗癌解毒的中药,最终达到邪去正安的疗效。
2.2 辨证论治,抓住本质,确立治疗原则 根据患者的体质以及临床症状,吴老师在辨病的基础上将肝癌辨证分型为肝热血瘀型、肝盛脾虚型、肝肾阴虚型。肝热血瘀型治以清肝解毒、祛瘀消癥,可用基础方结合龙胆泻肝汤(《医方集解》)、下瘀血汤(《金匮要略》)化裁;肝盛脾虚型治以健脾益气、泻肝消癥,可用基础方结合茵陈蒿汤(《伤寒论》)化裁;肝肾阴虚型治以滋阴柔肝、凉血软坚,可用基础方结合一贯煎(《柳州医话》)化裁。
2.3 辨症论治,突出主症,明确治疗方向 肝癌急症、兼症繁多,以血证、脑病、鼓胀、黄疸、呕吐等多见。“辨症论治”的主要优势在于能迅速突出主症,明确治疗方向,以最快速度及最大程度缓解患者的主要痛苦,体现了“急则治其标”的重要思想。鼓胀者,症见腹部胀大、皮色苍黄、脉络显露等,加用中满分消散加减健脾行气、清热利湿,再佐以活血通络;血证者,症见呕血、便血等,因脾气亏虚致脾不统血者加用归脾汤以益气健脾、摄血止血,因肝火犯胃致迫血妄行者加用龙胆泻肝汤合十炭散以清肝泻火、凉血止血;表情淡漠、神昏或烦躁者,临证时多因痰热上蒙清窍,吴老师喜用安宫牛黄丸以清热涤痰、开窍醒神;若因肝血不足、清窍失养者可用甘麦大枣汤合人参鳖甲汤加减以养心安神、益肝活血;黄疸者,阳黄者方选茵陈蒿汤,阴黄者方选茵陈五苓散;呕吐者,症见嗳气、纳呆、反酸等,可方选旋覆代赭汤加减以疏肝降气、和胃止呕。
3 补肝体,疏肝用,体用同调
“体阴而用阳”是对肝脏生理特性的高度概括。肝主藏血,血属阴,故肝体为阴;肝主疏泄,性喜条达,主升主动,故肝用为阳。肝体阴柔,而其用阳刚,刚柔相济,阴阳调和,则肝的生理功能如常。正如清代名医叶天士于《临证指南医案》中所云:“肝为风木之脏,因有相火内寄,体阴用阳,其性刚,主动,主升,全赖神水以涵之,血液以濡之,肺金清素下降之令以平之,中宫敦阜之土气以培之,则刚劲之质,而为柔和之体,遂其条达畅茂之性,何病之有!”另外,肝体与肝用互根互用,不断地相互资生、促进,两者关系也体现“阴在内,阳之守了;阳在外,阴之使也”的观点。吴老师认为,肝癌以“肝郁脾虚”为主要病机,临床易出现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等肝用太过之实证,治以疏肝用,同时柔肝体以助肝用;阴血不足之肝体不足之虚证,治以补肝体,同时助肝用以益肝体。吴老师将“体用同调”理念广泛应用于肝癌临证实践中,临证时善用柴胡、青皮、陈皮、川楝子、麦芽、薄荷、茵陈等辛散之品以疏肝用,白芍、枸杞、酸枣仁、麦冬、当归、生地等酸甘之品补肝用,体用兼顾,阴阳调和,疏肝气而不耗伤肝阴,养阴血而不敛滞肝气。
4 顾护脾(胃)气贯穿治疗始终
《难经》曰:“肝病之所以难治,传其所胜也。”肝癌发病,病位在肝,而肝木易克脾土,故肝癌患者常并见纳呆、倦怠乏力、腹胀、恶心、呕吐、便溏等脾虚之象,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而脾胃同为后天之本,应脾胃并重;并且“肝郁脾虚”乃肝癌发病之主要病机,故推崇顾护脾胃之气贯穿治疗始终。吴老师顾护脾胃,常综合“健脾、理气、消导”三方面,以奏恢复脾胃运化升降之效。健脾理气药性偏温,吴老师喜用陈皮、炒白术、党参、山药、薏苡仁、茯苓、半夏、丁香等,既可奏“脾旺而不受邪”之效,亦可预防滋阴柔肝之品过于滋腻碍胃;消导之品喜用焦三仙、鸡内金、莱菔子等消积导滞助运。
5 擅用虫类,直攻病穴,疗效确切
吴鞠通曰:“以食血之虫,飞者走络中气分,走者走络中血分,可谓无微不入,无坚不破。”虫类药物为血肉有情之品,性善走行,其性猛而力专,直攻病穴,有软坚散结抗肿瘤的独特疗效,吴老师临证喜用全蝎、蜈蚣、土鳖虫、鳖甲等多数已被现代药理学实验证明有良好的抗肿瘤作用的虫类药物,其机制与调控癌相关基因 C-myc、N-ras、p53、PTEN 的表达、增强荷瘤小鼠的特异性免疫功能和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等相关[2-3]。吴老师指出,肝癌患者正气不足乃发病之根本,且因目前国内医疗条件限制,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属晚期,正气虚损,临证时不可一味攻伐,综合评估患者体质状况,在辨病辨证的基础上配以虫类药物,注意攻伐不可太过,应严格遵循“衰其大半而止”原则,严格把握用量、用法及疗程。
6 病案举隅
患者刘某,男,72岁,退休,2015年3月2日初诊。患者“体检发现肝右叶小肝癌1个月”就诊于吴玉生教授处。病史:患者1个月前体检时查腹部彩超提示“肝脏占位”,遂行肝脏CT平扫+增强示“肝右叶膈顶部小肝癌”。患者因惧怕手术及介入治疗,求治于中医。刻下:患者神疲乏力,腹胀,口干,口苦不著,胃纳欠佳,二便调,舌红,苔黄,脉弦滑略数。证属肝郁脾虚,湿热内蕴,治以健脾柔肝、清热祛湿,拟方:柴胡、白芍、枳壳各 15g,太子参 30g,白术 5g,砂仁(后下)6g,五爪龙、薏苡仁、预知子、白花蛇舌草、八月扎各30g,甘草6g,郁金、茵陈、焦山楂、焦神曲各15g,佛手 10g。1天 1剂,水煎服,连服 14天。2015年3月15日二诊:药后患者精神好转,腹胀缓解,仍感口干、胃纳差,舌淡,苔少,脉细弦。上方去郁金、茵陈、八月扎、佛手,加沙参、生地、麦冬各15g。1天1剂,水煎服,连服14天。2015年3月28日三诊:药后口干缓解,胃纳尚可,无腹胀,舌淡,苔白,脉细弦。上方去沙参、麦冬,加全蝎5g,炙鳖甲10g,山慈菇10g。1天1 剂,水煎服,连服14天。患者坚持中医药治疗,至今已2年6个月,现一般情况良好,稍感腹胀,胃纳稍差,余无明显不适。
按:该患者虽为早期肝癌,但年老,体质虚弱,无法耐受手术、介入等治疗,遂至吴玉生教授门诊寻求中医药治疗。吴老师认为,肝脏病机总属本虚标实,“肝郁脾虚”乃其主要病机;初诊时证属肝郁脾虚,湿热内蕴,治以健脾柔肝、清热祛湿,予肝癌基础方去全蝎,加用茵陈清湿利湿,焦山楂、焦神曲健脾消积导滞以助运化,八月扎、佛手疏肝理气,黄芪健脾益气,脾旺而不受邪,经研究证明,黄芪总皂苷可抑制小鼠肝癌H22肿瘤细胞的增殖,其机制可能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关[4]。二诊时,精神好转,腹胀之症缓解,但显示肝阴亏虚之象,故前方去郁金、茵陈、八月扎、佛手,加沙参、生地、麦冬以养阴血。三诊时,患者阴血得养,正气尚足,去沙参、麦冬,加全蝎、灸鳖甲、山慈菇抗癌解毒,终达带瘤生存之效。
7 结语
肝癌为我国高发的恶性肿瘤,其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五年生存率约5%~6%左右,且大多数肝癌患者确诊时即为不可手术者[5]。中医药在肝癌的全程治疗中均可发挥作用,其目的在于减轻手术、化疗、介入等有效抗肿瘤手段的不良反应,提高肝癌患者耐受性,对于晚期肝癌以控制肿瘤相关症状、带瘤生存、提高生活质量等为主。吴玉生教授辨治肝癌,结合自身临证经验,认为肝癌的主要病机是“肝郁脾虚”,强调“辨病-辨证-辨症”的肝癌诊治思路;根据肝脏“体阴而用阳”生理特点,强调“补肝体、疏肝用、体用同调”的治疗理论;临证时倡导始终顾护后天之本,同时善于运用效猛力强的虫类药物,临床疗效显著。吴玉生教授治疗肝癌疗效显著,其临床经验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