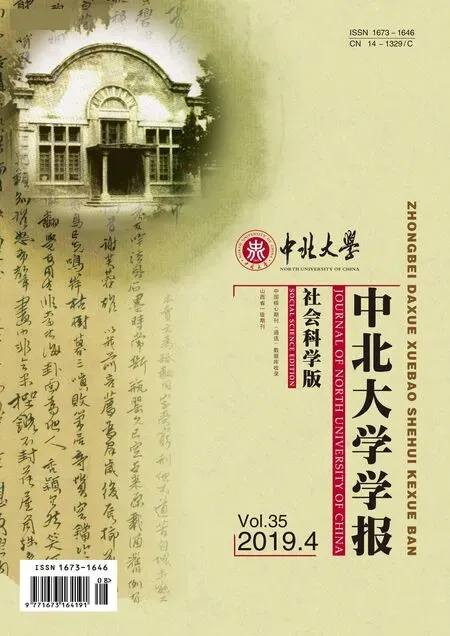略论理学对宋元易代之际南方儒士心态影响
——以吴澄为中心
花 兴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00)
0 引 言
关于宋元易代之际南方士人的心态,在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 徐子方《元代文人心态史》、 杨亮《从拒绝到认同——以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立场转变为中心》等著作中已有论述,但理学在其中的具体作用还较少有人论及,今以元代儒宗吴澄为中心,探讨理学对当时儒士心态的具体影响。
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晚字伯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元代著名学者。南宋咸淳六年(1270年)乡贡中选,次年礼部试下第,授徒山中,同学程钜夫题其室曰“草庐”,学者遂称其为草庐先生。吴澄30岁时宋亡,入元后至元武宗时应征出仕,先后任国子监丞、 翰林学士等,泰定中告病返乡,元统元年(1333年)病逝,有《易纂言》《春秋纂言》《吴文正公集》等著作传世。吴澄青年时经历了由热心科举至醉心理学的转变,是宋元鼎革的亲历者,集中体现了南方儒士在元初复杂情势下的心态变化。
1 南宋末年理学影响下的真儒与科举仕途的挣扎选择
南宋之季,理学的复兴促使一些儒士对科举之学进行深刻反思,这可能是理学对宋末儒士心态影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南宋理宗之后,理学得到提倡,有人称真德秀等理学中人为“真儒”,如周密《癸辛杂识》所云:“真文忠负一时重望,端平更化,人傒其来,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意谓真儒一用,必有建明。”[1]前集但当时科举仍从旧制,时文之学仍然盛行于世,宋季学者王柏在《答何师尹》中曾云:“今之士,舍科举之外,无他学也。”[2]卷十七对于许多士子来说,科举仍是第一选择,但也有些士人在接触理学后,开始鄙弃科举时文之学,如吴澄。
吴澄乃科举世家,据其《年谱》:“(景定)五年(1264年)甲子秋,侍大父如郡城。时大父赴乡试。”[3]附录可知其祖父至晚年仍积极参加乡贡考试,极重视科名,其《谒赵判簿书》云:“家贫不能从师,惟大父家庭之训是闻。幼年颇以能属文而见知于人,然当时所能者举业而已,未闻道也。年十有六始知举业之外有所谓圣贤之学者,而吾未之学,于是始厌科举之业。”[4]67可知吴澄少年所学乃科举之学,在接触理学后转而不满于科举之学,想要致力理学,并对当时学风大加批判:
今世之儒所学者,果何学也?要不过工时文,猎科第,取温饱而已。呜呼,陋矣哉!或稍有见识,与之言及圣贤之学,其刻薄者则笑之曰“迂阔”,其忠厚者亦不过曰“可施之议论而难形诸践履”。至于矫诈者,则又窃取其名以欺世。吁!圣贤之学皆切己事,而乃曰“迂阔”; 圣贤之学正在躬行,而乃曰“但可施之议论”; 圣贤之学,不诚无物,为己为人间不容发,而乃窃取其名以欺世,皆圣贤之所不胜诛也。斯人也,纵或擢高第,登显仕,愚不知,朝廷亦何用于若人哉。[4]67
此时吴澄年仅19岁,如引文所说,已经致力理学三年了,据危素《年谱》,此时吴澄已经校正《孝经》并为之作《外传》十篇,又成《皇极经世续书》,并作《道统图并叙》,可以说对理学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深度。经过对理学更深入的研究,他进一步从制度面反思当时的科举制度,如他自己所说:
必欲为周、 程、 张、 邵、 朱,而又推此道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也。试尝实用其力于此,则豁然似有所见,坦然若甚易行,以为天之生我也,似不偶然也。吾又何忍自弃?于是益务加勉,以穷尽天下之理。虽力小任重,如蚊负山,所学固未敢自是,然自料所见则加于人一等矣。”[4]67
吴澄认为自己确实走对了道路,认为天之所以使其降生于世便是为了承道统以尧舜其君民,由内圣而外王。
吴澄之家并非显宦,无法以门荫出仕,参加科举几乎是其入仕的唯一机会,所以吴澄终究还是在咸淳六年(1270年)参加了科举,并且乡贡中选,但从其《谢张教》看,参加科举是为了求一个终结而非投身仕途,其所思所想还在于理学。他说:
有如今秋,驰逐万人之场,而相角一日之技,非曰欲以谋利禄,而梯显荣也。公欲进对天子之庭,以摅其致君泽民之蕴; 私欲释去举业之累,以遂其读书修己之心而已。倘得直言天下事于大廷,亲策之晨以少吐平时所学之万一,然后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则澄之志愿得矣。俟其德器成就达,可行之天下而后行之,庶乎不至于上负天子而下误苍生也。……若夫幸科第之就手,慕荣途而动心,则非愚之所志。[5]680-681
可知,吴澄参加科举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致君尧舜是儒者的天职,可以说“修齐”最终也是为了“治平”。年轻的吴澄也有指点江山的愿望,也欲“直言天下事于大廷”,以“少吐平时所学之万一”。如前所言,除了科举吴澄几乎没有在天子执政面前表达自己所思所感的机会,因而他愿意参加科举; 另一方面,吴澄幼时由其祖父教养,吴澄自叙也明确地说“澄生五年而读书,七年而能声对,九年而能诗赋,十有三年而科举之文尽通。”[5]680也就是说,吴澄自幼从事于声对、 诗赋、 属文,可谓以科举之学传家。参加科举乃是吴澄的家族使命,其在《谢佥幕》中明确说道:“有如今秋承亲之命而投应举之牒。”[5]684因此,对于科举,吴澄确实希望能够中选。但细究其实,当时吴澄的志向并不在仕途,如《谢张教》所说,封侯拜相并非吴澄所愿,“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才是是其平生至愿。吴澄认为兼济天下是“公”,是作为儒者的义务,是出于儒者的天职。吴澄达成此志的方式与常人不同,从所谓“进对天子之庭,以摅其致君泽民之蕴” “直言天下事于大廷,亲策之晨以少吐平时所学之万一”,可以看出,当时吴澄对自己的定位是一名建议者,并非决定者,更非实施者。也就是说,即使中选,吴澄也准备退而私居读书。直到“俟其德器成就,达可行之天下而后行之,庶乎不至于上负天子而下误苍生也”之后,也就是学有大成之后再重新出仕教化士人。所以参加科举对于当时的吴澄来说是一种了结,也是传达其想法的一个途径。所以,与其他人一样,吴澄愿意中举,但绝非以科举仕途为奋斗一生的事业,其后来一次不中就退居山野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从上述内容看,理学确实影响了吴澄对科举仕途的看法,在接触理学以后吴澄不再专意于科举之学,虽然参加了科举,但其参加科举只是为了结家庭夙愿,也给自己一次发声的机会,是一次了结,所以他下第后便不再有科举之念,专意理学。
2 入元之初守节与出仕的艰难选择
至元十二年(1276年),谢太后下诏投降,江南大部投降内附,至元十五年(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南宋彻底宣告灭亡。
面对新朝慷慨赴义或者远遁山林,是理学浸润下的儒者的一个重要选择,前人论述已多,如刘静《宋末元初江南遗民群体的崛起、 分化及原因寻绎》、 王尤清《宋遗民形成之因论析》等,在讨论宋遗民成因时均认为理学的涵养是重要因素,兹不赘言。除此外,在朝代更迭的大背景下,理学对士人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
首先,对于许多士人来说,理学是他们面对新朝继续生存的重要支柱。如吴澄,自宋咸淳七年(1270年)后便一直乡居著述,从事理学研究,宋亡后依然如此,宋元鼎革并没有改变他投身理学的愿望,对他个人的冲击并不太大。选择隐居,或著书或教授,其意图除与新朝保持距离外,也有延续道统的深意。入元以后,吴澄应郑松之请隐居布水谷。据危素《年谱》,此期“十八年(1281年)辛巳,留布水谷纂次诸经注释,《孝经章句》成。十九年(1282年)壬午,留布水谷较《易》《书》《诗》《春秋》,修正《仪礼》《小戴》《大戴记》成。”[3]附录可知在宋亡的前几年,吴澄一直在隐居著述,值得注意的是,邀请吴澄共同隐居的是郑松,郑松是坚定的反元人士,吴澄《前乡贡进士郑君墓碣》云:“既革命,犹有图兴复者檄君为助。君以民兵应之,其卒勇敢,独能与大军遇,多所杀获。俄而卒战死者众,遂溃,君避入溪洞,遇赦乃出。”[3]卷七四郑松在宋亡之后还有过实际的起兵抵抗行为,有些研究者据此认为,吴澄虽无直接参与,但也有反元之志。如《吴澄评传》云:“(吴澄)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抗元斗争,但吴澄却与一些抗元分子过从甚密。……吴澄在这种遗世独立的情况下,做着这种寂寞的经学工作,既有完成他自己‘绍朱子之统’理想的动机,同时也不无保存延续故国文化传统之意。”[6]5当然吴澄并没有参与实际的反抗活动,相比于郑松等人,吴澄对于自己有着明确的定位,其所有的个人理想与故国之思都寄托在理学的传承上,可以说,理学对于吴澄等易代儒者的影响相当深远。
吴澄是幸运的,许多不幸的儒者在残酷的战争中几乎家破人亡,如赵复,元破德安后,赵复九族俱残,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云》:“行及水裔,见已被发脱屦,仰天而祝,盖少须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与众已同祸矣。爰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经学,实赖鸣之。”[7] 卷三四可知,在生死存亡之际,正是为了继绝兴废,传递道统,赵复才绝了自杀之念。无论幸与不幸,幸存下来的儒者都将理学或者儒学当成他们生存的重要支柱,教授著述并以此为生。
其次,从某种程度来说,理学是易代儒士接受新朝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当然不是说理学教人变节,而是在南宋已经注定恢复无望的背景下,元廷重视理学从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儒士的期待,给了这些士人一个与新朝合作的理由。
宋元战争持续近五十年,无论上层还是民间,对双方军力差距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在元军突破襄阳南下后,虽也有文天祥等积极起兵抵抗,但面对元军强大的军力,许多地方直接投降的原因。再加上灭宋之初,元世祖积极减免南方的苛捐杂税,稳定人心,易代之初的南方士人基本接受了南宋无法挽回的事实。当然承认不代表遗忘,元初有些士人对宋之所以亡进行反思,而在诸多原因中,宋廷重科举时文是相当重要的一条,这种反思是相当普遍的,除前引之王柏、 吴澄对士人只知有时文不满外,有陆学背景的刘壎也是如此,刘壎(1240-1319年)字起潜,号水云村,江西南丰人,有《水云村稿》《隐居通议》等著作传世。《宋元学案》等在述及陆学门人时并未列入刘壎,但从刘壎的文章可知,刘壎确实心向陆学,如其《隐居通议》卷一评论朱、 陆二人时云:“要之,陆学终非朱所及也。”[8]卷一其《答友人论时文书》,云:
夫士禀虚灵清贵之性,当务高明光大之学。然为昔之士沈薶于卑近而不获超卓于高远者,盖宋朝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智之材、 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于此。不为此,不名为士,不得齿荐绅大夫。是以皇皇焉竭蹶以趋,白头黄册,翡翠兰苕,至有终老而不识高明之境者,可哀也。……而比岁襄围六年,如火益热。即使刮绝浮虚,一意救国,犹恐不蔇。士大夫沈痼积习,君亡之不恤,而时文乃不可一日废也。痛念癸酉之春,樊城暴骨,杀气蔽天。樊陷而襄亦失矣,壮士大马如云,轻舟利楫如神。敌已刻日渡江吞东南,我方放解试,明年春又放省试。朝士惟谈某经义好,某赋佳。举吾国之精神、 工力一萃于文,而家国则置度外。是夏又放类试,至秋参注甫毕,而阳罗血战,浮尸蔽江。未几,上流失守,国随以亡,乃与南唐无异。悲夫!爱文而不爱国,恤士类之不得试,而不恤庙社之为墟!由是言之,斯文也,在今日为背时之文,在当日为亡国之具,夫安忍言之![9]221-222
此书虽名为《答友人论时文书》,但刘壎讨论的并不是时文写作的心得,而是由批判时文入手反思整个南宋朝野对待科举的态度。他认为南宋太重科举时文,虽可由此“束缚天下英俊,使归于一途”,但“非工时文,无以发身而行志,虽有明智之材、 雄杰之士,亦必折抑而局于此”,如果是太平时节,束缚天下英俊尚可减少事端,平稳治道,重镇襄阳被围,国家势如累卵,而朝廷之公卿仍在讨论科举,一边是血流漂杵的战场,一边是撰写时文的考场,在这极度荒谬的对比下,终于襄阳失守,国破家亡。宋亡的原因很多,科举时文在其中的比重也许不到刘壎所说的“亡国之具”的程度,但从刘壎的论述看,当时儒士无论朱学还是陆学,都对此有所反思也是不争的事实。而此前元廷已于大都立国子学,反对诗赋之学,提倡实学,以朱子学教授其间,影响颇大。中央国子学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教育机构,对于朱学门人占据极大优势的故宋儒者来说,国子学以朱子学为主要教授内容,自然意义非凡,更能引起对新朝的认同。
随着元廷统治的稳固,许多原本隐居不仕者逐渐开始与元廷合作,而这种合作的方式多以出任各地儒学教官的形式实现。元得地江南后,广设学校,除路府州县之儒学外,还设有相当多的书院,《元史·选举志》云:
至元十九年夏四月,命云南诸路皆建学以祀先圣。二十三年二月,帝御德兴府行宫,诏江南学校旧有学田,复给之以养士。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栗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凡师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 命于礼部及行省及宣慰司者,曰学正、 山长、 学录、 教谕,路、 州、 县及书院置之。[10] 2032-2033
如此多的书院学校,自然需要更多的教师,对于故宋儒者来说,担任教官毕竟与直接出仕不同,吴澄在《答姜教授书》中说:
澄迂避人也,于仕素非所欲,亦非所谙,散职何庸冒处林林时俊之右?它无能焉,唯曰一豪有所希觊、 浸渔于学校以益其私,则决不为耳。近年贪浊成风,在在而然。行之不以为非,言之不以为耻。阝舀溺至此,盖有为也。……教养,重事也,诏旨每诣谆焉,思之能无旷缺乎?协力齐心,整治而扶树之,俾实交底于成,而毋徇虚文以为欺。[4]24-25
此书作于大德十年(1306年),此前吴澄应董士选推荐赴京,但因赴官较晚,抵京时其职位已委任他人,当时已是冬季,不便南下,于是吴澄于大德七年(1303年)返乡。至大德八年(1304年)时,董士选认为“委任他人”一事非朝廷待臣之礼,乃奏请任吴澄为江西儒学副提举,此书作于吴澄赴任之初。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吴澄第一次实任元代的官职,是学官,且在吴澄看来,学官与其他官职不同,是“散职”,可见相较于其他官职,学官确实更容易被故宋儒者接受。另外从“教养,重事也”可以看出,对于吴澄这样的儒者来说,出任教官似乎有着天然的正当性,许衡在出任国子祭酒时也由衷地说“此吾事也”[10]3727。究其根本,儒家自孔子起便以教育为自家事,出任学官,心理负担确实要小许多。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儒者都与吴澄一样,时时以传道受业为己任,即使是出于生存考虑,教官也是一个较易接受的选择。故宋士人中,戴表元、 白珽、 方凤、 胡炳文、 邓文原、 王义山、 张楧等先后出任教官,如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所说:“这些遗民之所以要出任学官,大多又还与生计所迫、 饥寒所驱有关。”[11]122这些儒士确实如方勇先生所说,大多出于生活无奈,戴表元《送陈养晦赴松阳校官》云:“书生不用世,什九隐儒官。抱璞岂不佳,居贫良独难。”[12]382张楧也“殆迫于家贫亲老,将为禄仕计耳。”(陆文圭《送张菊存序》)[13]526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出任教官并非如有些学者说的,是南宋遗民故将其看成特殊的隐逸形式。出任教官大多需要有人推荐,吴澄是得董士选推荐,刘壎也是得“当路交荐”(吴澄《故延平路儒学教授南丰刘君墓表》)[3]卷七一,卢挚敦聘姚云的书信更一时传为美谈。但就任之后官场交际、 逢迎上官在所不免,如以此为隐反而适得其反,所以对于心恋故国者来说,可能更多是出于生活所迫。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促使遗民与元廷接触的一个重要步骤,其中固然有人担任几年教官后便终老乡里,如戴表元等,但也有逐渐接受元廷,登上高位的,如邓文原。对于戴表元、 邓文原等儒者来说,这种转变虽与理学理论本身无涉,但与元廷推广理学有关。
另外,对于普通儒者来说,元廷广设学校,讲授理学也促进其接受新朝。元廷推广理学,一方面说明官方接受了儒家的传统,另一方面也给普通儒者带来了心理归属感。如《宋元学案》卷八八云:
欧阳龙生,字成叔,忠叟子。……十有七年,浏有文靖书院,祠龟山杨时,沦废已久。部使者至,谋复其旧,授先生为山长。升堂讲《孟子》“承三圣”章,言龟山传周、 程学,而及豫章延平、 紫阳朱子,实承道统,其功可配孟子。山林老儒,闻讲道之复,至为出涕。秩满改本州教授,迁道州路教授,朔望率诸生谒濂溪祠,祠东为西山精舍,祠蔡元定先生。[14]2967-2968
欧阳龙生(1252-1308年),浏阳人,元著名文士欧阳玄之父。至元十七年(1280年)为宋亡的第二年,此时欧阳龙生出任文靖书院山长,重上讲席,旁听者闻重讲理学,潸然泪下。这些潸然泪下者为“山林老儒”,大多为普通儒者,他们激动流泪的原因应该是多重的,儒家自古以来就崇尚“以夏变夷”,害怕变成披发文身的所谓“夷狄之人”,如姚燧《序江汉先生死生》所说,赵复初见姚枢时云:“江汉先生见公戎服而髯,不以华人士子遇之。至帐中,见陈琴书,愕然曰:‘回纥亦知事此耶’?”[7]卷三四对于消息闭塞的普通儒者来说,见到民族多样的北方军队,自然担心以夷变夏,而此时欧阳龙生在大战过后,在官方的支持下重立文靖书院,自然起到安定儒者之心的作用。再加上其所讲为理学道统之说,推崇曾在浏阳任职、 有功于浏阳的杨时,其象征意义与实际效果自然非同凡响。
3 结 语
在宋元鼎革之际,理学对于故宋儒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让文天祥、 谢翱等人坚守节义,另一方面也让许多学者对南宋以科举时文选试有了深刻的不满和反思,在入元之初,出于传递道统的考虑,许多儒者经历了隐居到担任教官的变化,那些没有出仕的普通儒者也由于南方大规模的开办学校、 设立书院而逐渐归心。这种种变化都与理学及元廷推广理学有关。
那么为什么同是理学门徒,有人选择成仁,有人选择传道呢?这与个人经历有关,也与本人定位有关,以文天祥与吴澄二人来讲,二人都是理学中人,文天祥作为欧阳守道的弟子被《宋元学案》列入巽斋学案,而《宋元学案》为吴澄立草庐学案,是有元一代之儒宗。但从个人经历来看,文天祥为宋末状元,又曾担任宰相,既承大恩,又守土有责; 吴澄生年晚文天祥十三年,宋亡前未曾做官,也未进士及第。从自身定位来讲,文天祥一直心系家国天下; 而吴澄自少年时便心在理学,慨然以道统自任,其《谒赵判薄书》云:“必欲为周、 程、 张、 邵、 朱,而又推此道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也。”[4]67显然,二人经历不同,自我定位不同,最后的选择也不同。所以同被理学影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者,坚守节义,不与新朝合作; 以传递道统为己任者,则为师儒,为教官,积极传播理学。即使是仅为温饱仕禄的人,也能通过担任教官谋生,甚至有人通过担任教官走上仕途成为显宦。北方的统治秩序对于南方儒者来说充满了未知,通过他们熟悉的儒学与之拉近距离有了接触之后,心态自然也随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