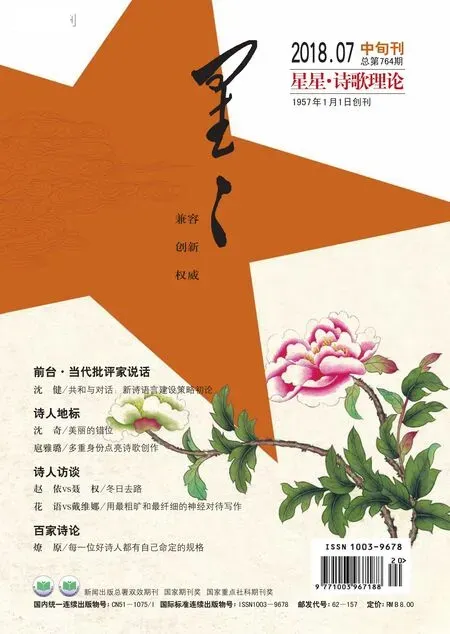美丽的错位
——郑愁予论
沈 奇
一
中国新诗,在台湾自五十年代初,在大陆自七十年代末,经由半个多世纪的拓殖与扩展之宏大进程后,已逼临一个全面反思、总结的整合时代。空前的繁荣之下,是空前的驳杂;各种主义纷争、流派纷呈之后,是新的无所适从。尘埃落定,我们终于发现,一些看似很新的命题实则早已在“传统”中解决,而一些很“传统”的命题依然成为今天的挑战——而几乎所有的命题,都须要站在今天的立场重新予以审视、梳理、定位和再出发。
正是在这一时空背景下,我步入台湾著名诗人郑愁予的诗歌世界,沉浸在新奇而又悠长的诗与诗学的漫步之中。
这真是一种新奇的漫步——在对“后现代”式的喧哗领略以后,在为各种样态的实验诗的冲击所淹没以后,在只谈“重要的”、“创新的”、“探索性的”、“现代性的”而很少谈及“美的”各种批评话语的缠绕以后,尤其是在被各种层出不穷的“主义”轰炸得头昏脑胀以后,来到这葱茏幽美的“梦土”般的小世界,顿觉鲜气扑人,芬芳满怀——“突然,秋垂落其飘带,解其锦囊:/摇摆在整个大平原上的小手都握了黄金”(《晚云》·1954),且闻“一腔苍古的男声”“沿着每颗星托钵归来”(《梵音》·1957)……于是,一颗烦乱的心得以安宁,而一些为喧嚣所磨钝了的纤细的感觉,也得以深切的战栗和共振——一切的声音,一切的色彩,一切的形式,皆“云石一般的温柔,花梦一般的香暖,月露一般的清凉的肉感——”,“它的颜色是妩媚的,它的姿态是招展的,它的温馨却是低微而清澈的钟声,带来深沉永久的意义。”[1]
我知道,作为读者,我比他最早的欣赏者晚了几十年,而他不但在当年使无数诗爱者为之迷醉为之疯魔,乃至可以说造就了一代新的“诗歌族群”,而且,在今天的阅读中,仍是那样鲜活和清越,激起新的回声和涟漪。仅从版本来看,我所读到的《郑愁予诗集Ⅰ:一九五一—一九六八》,已是台湾洪范版第五十一印(初版于1979年9月)!这一印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使我想到瓦雷里(Paul Valéry)的一句话:“有些作品是被读众创造的,另一种却创造了它的读众。”显然,为诗人郑愁予所创造的读众,已成为一支绵延不绝的“诗歌族群”,而作为批评家的我,更需要追寻的是:是什么支撑了这种“绵延”?在这一“支撑”背后,又包含着怎样的启示于今天的诗歌步程?
尤其是,在各种主义的纷争之后,所谓新诗的“传统”是什么?所谓汉诗的“现代化”是什么?而由此回视郑愁予的存在,又是什么——
是精致的仿古工艺,还是再造的古典辉煌?
是复辟的逍遥抒情,还是重铸的浪漫情怀?
是唯美矫情的“乌托邦”,还是诗性生命的“新牧场”?
是早已远逝且该归闭了的陈旧精神空间之回光返照,还是依然恒在常新之隐秘精神世界的先声夺人?
总之,是美丽的“错误”还是美丽的“错位”?
实则,当我们对一位诗人提出如许多盘诘与思考时,本身就先已证明:这不但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人。
二
要对郑愁予所创造的诗歌世界,作一番定位之论,实非易事。因为我们很快会发现:他所深入的,或许正是当代主流诗歌走向准备退出的;他所拓殖的领域,或许正是当代主流诗歌走向所要否弃的。至少,我们很难轻易将他归位于哪一种主义,或指认他是哪一诗派的嫡裔。我们顶多可以依稀分辨出某些影响,而这影响也已化为诗人的血液与呼吸之中,成为自在而非投影。
于是有了我这个特殊的命名:错位。
这里的“错”是指错开,一种疏离于主流诗潮的别开生面,一种在裂隙和夹缝中独自拓殖的另一片“家园”。这里的“位”是指主位,亦即那些可以被我们指认且冠以各种“主义”之称的诗歌位格,这些位格所确立的诗歌立场,在郑愁予的作品中,都难以找到恰切的确认——他是独在的,无论在当年,还是在今天,他一直是一位只能称之为“错位”的诗人。正是这种“错位”,奠定了诗人在整个现代汉语新诗史中独有的地位,而对这种“错位”的深一步追问,更有着别具意味的诗学价值。
在展开探讨之前,我从仅有的一点外围资料中,注意到台湾诗界当年的评价:根据《阳光小集》第十号“谁是大诗人”的评析,郑愁予被称为“惟美抒情诗人之一”,他所得的评语是:“抒情浪漫,贴切可亲,自然朴实与技巧成熟的作品都很动人,声韵最美,流传也最广,开创了现代诗的情诗境界,是台湾最佳抒情诗人,其作品以情感人,适合青少年做梦,但不够冷静审视,后期作品尤其浮泛、空洞,可见其近年来功力锐减。”同时指出“尤其在使命感、现代感、思想性方面,他的得分偏低,现实性更是得分奇低”。[2]显然,这一论定是以台湾现代诗之发展主流为理论参照的,妥切与否,暂且不论,所提出的问题,确已触及到诗人所“错”之“位”的基本方面,当然,还应该加上“自然观”“语言观”等。在这里,仅就其主要方面来加以重新解读。
郑愁予诗歌的“错位”态势,从台湾现代诗的发轫之期就已持有。当纪弦“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于五十年代初掀起以强调知性、放逐抒情和音乐性等为主旨的现代诗之狂飙巨澜时,郑愁予便已在投身其中的同时,悄然“错”出主流之外,默默耕耘于他自己的天地之中了。尽管,作为台湾现代诗的祭酒人,纪弦也曾夸赞过:“郑愁予是青年诗人出类拔萃的一个。”称其诗“长于形象的描绘,其表现手法十足的现代化”。[3]但在实际上,郑愁予诗歌所呈现的整体质素与风格,与纪弦所倡导的诸“现代化”主旨可谓相去甚远、难归旗下,算是第一次大的“错位”。实则潮流之下,守住自我,在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土壤中潜心耕作,正显示了一位早慧诗人的成熟之处。
这次“错位”,使郑愁予脱逸于前卫、先锋诗人的行列,潮流之外,难免传统、守旧之嫌。这里的关键在于,所谓“愁予诗风”是对传统的殉葬还是革新?
对此,或许做一点反证,倒能更好地说明问题。
现代汉诗发展到今天,至少有三大弊病已渐为批评界所共识:一是严重的散文化,包括完全抛弃韵律之美;二是过分的翻译语感化,汉语古典诗美的语言质素几已荡然无存;三是过多的知性造作,使诗的精灵日趋干瘪和生涩。拿此三点反观“愁予诗风”,自会发现,他不但“逃脱”了上述弊端之陷阱,反以其对传统的革新和上溯古典诗美的再造,弥补了这些缺陷。正如诗人向明所言:“诗,如果是智慧的语言,郑愁予的诗就是最好的证据,充满了绘画与音乐性,郑愁予的诗和痖弦的诗,是当前现代诗坛最为人喜爱的,就因为他们的诗都具有这种美。”而另一位颇具前卫风采乃至可谓最早涉足“后现代”创作意识的诗人管管,更由衷地赞道:“现代诗人中,从古诗的神韵中走出,愁予表现了生命的完美,其语言、生活习惯、精神、风貌、能将古诗与现代协调而趋向完善,有中国古诗词的味道,但能植根于现代生活,不是抱残守缺之流。”[4]依管管之风,能作如此首肯,我们当信之不谬才对。潜心研读郑愁予的作品(这里主要指其收入《郑愁予诗集Ⅰ》中的作品),不难发现,上述两位同辈诗人的评定是中肯的。
显然,在适逢浪漫主义余绪与现代主义发轫的纷争之中,郑愁予选择了一条边缘性的,可谓“第三条道路”的诗路进程。一方面,他守住自己率性本真的浪漫情怀,去繁复而留绚丽,去自负而留明澈,去浮华而留清纯,且加入有控制的现代知性的思之诗;另一方面,他自觉地淘洗、剥离而后熔铸古典诗美积淀中有生命力的部分,经由自己的生命心象和语感体悟重新锻造,进行了优雅而有成效的挽回。由此生成的“愁予风”,确实已成为现代诗性感应古典辉煌的代表形式:现代的胚体,古典的清釉;既写出了现时代中国人(至少是作为文化放逐者族群的中国人)的现代感,又将这种现代感写得如此中国化和富有东方意味,成为真正“中国的中国诗人”(杨牧语)。试读这样的诗句:
巨松如燕草
环生满地的白云
纵可凭一钓而长住
我们总难忘褴褛的来路
——《霸上印象》
语词的运用,意象的营造,声韵的把握,都有着古瓷釉一般的典雅、清明、内敛和超逸,而内在的蕴藉却又完全是饱含现代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在郑愁予的诗中处处可得,尤其在那些为人传诵的名篇之作如《残堡》《野店》《水手刀》《赋别》《右边的人》《边界酒店》以及《错误》等诗中,更为强烈而隽永。
可以说,经由这样的一种“错位”,郑愁予不但很快形成了自己卓异不凡的个人诗歌语感,而且为现代汉诗的发展拓殖了另一片新的“传统”——这“传统”曾迷醉了几代诗爱者,或还会以它特有的质素之光,为未来的汉语诗歌映亮另一片天空。
三
关于诗以及一切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问题,一直是一个总在争论而总又不能(或许也不可能)归宗一家之定论的问题。在这样一个越来越为物质、技术和制度所主宰的世界里,诗人何为?诗有何用?
别林斯基(Belinsky)说:“诗人是精神的最高贵的容器,是上天的特选宠儿,大自然所宠信的人,感情和感觉的风神之琴,宇宙生命的枢纽器官。”狄尔泰(William Dilthey)指出:“最高意义上的诗是在想象中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而叶芝(William Bulter Yeats)干脆将诗定义为:“永恒不朽的手工艺精品。”[5]——这些过往大师们的高蹈之话,在今天的时代里还有导引意义吗?
“唯美抒情”与“缺乏思想性”,是我们重新解读郑愁予诗歌必然要面对的第二个话题。美,是“愁予诗风”的第一标志,也是惟一得以公认的价值。无论是热狂的读者还是冷静的批评家,只要打开一部《郑愁予诗集Ⅰ》,你就无法不为其惊人的意象美、和谐的音韵美、浓郁的色彩美(绘画美)所战栗、所晕眩、所沉迷,我们的想象和感觉完全被诗行中的丰繁华美的语境所浸润和渗透了:
雨季像一道河,自四月的港边流过
我散着步,像小小的舵鱼
——《港边吟》
当我散步,你接引我的影子如长廊
当我小寐,你就是我梦的路
——《小溪》
莞然于冬旅之始
拊耳是辞埠的舟声
来夜的河汉,一星引纤西行
回蜀去,巫山有云有雨
——《104病室》
每夜,星子们都来我的屋瓦上汲水
我在井底仰卧着,好深的井啊。
——《天窗》
当落桐飘如远年的回音,恰似指间轻掩的一叶
当晚景的情愁因烛火的冥灭而凝于眼底
此刻,我是这样油然地记取,那年少的时光
哎,那时光,爱情的走过一如西风的走过
——《当西风走过》
无须更多采撷取证,这随意的“抽样”已经足以令人目迷神醉——而问题在于,这是“唯美”吗?
诗以及其他艺术,总得提供两种价值:一是意义价值,一是审美价值。愈是成功的作品,愈是二者相融共生,难分形意。而愈是纯粹的艺术(诗、音乐、绘画、雕塑等),愈是见形难见意,美感成了第一位的要素,成了一片无法耕种的峭岩,一抹不能浇灌的彩虹。而诗的意义价值在于对人类精神空间的打开与拓展,这种拓展有两个向度:一是呼唤的、吁请的、吟咏的,一是批判的、质疑的、呕吐的;前者落实于文本,常以想象世界的主观抒情为重,后者落实于文本,常以真实世界的客观陈述为重。两个向度,两脉诗风,一主审美、主感性、主建构、主提升,所谓“向上之路”,一主审丑、主知性、主解构、主沉潜,所谓“向下之路”,正负拓展,本不存在优劣对错之分。然而自“现代化”泛滥之后,现代诗运似乎一直注重对后者的开拓,疏于对前者的再造,以至我们已越来越难以听到真正纯正优美的抒情之声了。
而生的乐趣在于美的照耀,以此使冰冷的存在恢复体温,使窒息的生命得以活性,使干涸的目光重现灵视。在无名的美的战栗中,参悟宇宙和人生的奥义,本是诗以及一切艺术原初而恒在的“使命”,而当知性、理性、智性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使诗人们的抒情热力渐趋消失和本色情感日益退场时,这“使命”又从何谈起?是的,过于传统、过于温和的抒情会失掉诗的力量,可由于力量而失掉美,失掉诗的感性生命和韵律的运动也同样不合算。
坦白地讲,作为一个批评家,多年来,我一直是“向下之路”的鼓吹者,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太缺乏批判意识和独立坚卓的主体人格,缺乏大师气象和大诗力量。但作为一个诗人,或一个有选择性的诗爱者,我却更倾心于在众音齐鸣中去依恋一种纯净而典雅的抒情之风,在如此沉重的人生中啜饮一杯泛着月光的醇酒佳酿。而批评的要旨在于指出文本中的特有品质,有如物理学家研究矿石旨在发现新元素,无论是个人的好恶或所谓公论性的价值判断,都是不可取的。
由此而重返“愁予诗风”,我们或可会重新认识诗人所持的立场。这里有一首意味深长的小诗《野店》,我将其看作诗人从初始到成名后一直隐存于心的诗歌观念,亦即对诗作何用的“诗性诠释”: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
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啊,来了,——
有命运垂在颈间的骆驼
有寂寞含在眼里的旅客
是谁挂起的这盏灯啊
旷野上,一个朦胧的家
微笑着……
有松火低歌的地方啊
有烧酒羊肉的地方啊
有人交换着流浪的方向……
就诗面而言,舒放展阔的情感,虚实相涵的意境,张弛有度的韵律,皆尽善尽美,可歌可吟,且有一种气韵贯通的形式饱满感,让人很难相信这竟是诗人十八岁时的出道之作(写于1951年)!而我更看重年轻的诗人在此对“诗人”这个“行业”别具深意的认知:他只是这个世界的“黄昏里”或叫着“暗夜里”(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rgger的命名)“挂起的一盏灯”,这盏灯的作用,只是给那些“命运垂在颈间”“寂寞含在眼里”的“漂泊者”(哲学家们对现代人的又一个命名)一个“旷野”(与“荒原”同构?)上的“朦胧的家”(精神的家园永远是“朦胧”的,非此在性的),且最终的作用只是,也只能是让“漂泊者”经由这盏灯下,交换“流浪的方向”……
即或是如此粗浅的诠释,我们也已发现,这样一首小小的诗中的美和其深意,已非寻常。美得感人,且美得惊人;是经典之作,亦是警世之作。而它所透显的诗美观念,更是对诗人所拓殖的“愁予风”之最恰切的注解了。
显然,所谓“唯美”(怎样的美?),“缺乏思想性”(怎样的思想性?)和“只宜于青少年做梦”云云是有失偏颇的。我们在郑愁予所创化的这些美的、精致的、弥散着灵幻之光的诗性结构中,是能够听到生命的真实呼吸和对时代脉息的潜在呼应的,只是他发出这些声音的方式与别人不同而已。诚然,我们也能间或捕捉到这声音中,有些许自恋、自慰性的成分(尤其在初始创作中),且较少能超越族群性或社区性的精神层面,以抵达更深广的现代人类意识。但这已属于另一个话题,所谓境界大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倒真是有些值得深究的地方。
四
稍作留心和归纳,便不难发现,郑愁予早期作品中确有“唯小而美”之嫌:“小溪”“小河”“小岛”“小径”“小巷”“小鱼”“小鸟”“小浪”“小帆”“小枝”“小寐”“小立”“小瞌睡”“小精灵”“小围的腰”“小街道”“小茶馆”、“小栈房”“小铃铛”以及“小小的潮”“小小的水域”“小小的茅屋”“小小的宅第”“小小的驿站”“小小的陨石”“小小的姊妹港”等等,整个一个小世界!而诗人所处的时代,又是那样一个大起大落大潮翻涌的时代——是逃逸,还是另一种“错位”?
应该说两者都是:是美的逃逸,也是精神的“错位”。
这里的“错位”,主要是指错开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所谓“时代大潮”。因为年轻,也出于天性,诗人在不完全否弃对当下历史的关注的同时,更专注于自己的命运,不甘受意识形态羁绊的纯精神的命运。作为诗人,他有权力根据自身诗性生命的天赋取向,做出这样的选择。现实很少能完全满足诗人飞腾的想象力,且与其天性相悖,而在他想象的世界中,又很少呈现出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现实性”。实则作为同一种人类诗性呼吸之不同向度与旨归,在自然/精神中歌唱与在现实/真理中歌唱,其本质上是一致的,而谁也无权将内源性不同的诗人纳入同一条诗路历程。
实则在郑愁予早期创作中,也写过诸如《娼女》《武士梦》《台风板车》以及《革命的衣钵》《春之组曲》等颇具所谓“现实性”“时代感”的作品,却顿显空泛、干涩,无法与其成功之作相比。显然,年轻而早熟的诗人很快把握住了自己只能写什么和只能怎样写,于是逃向自然(与精神家园同构),寄情山水(与诗性生命空间同构),寻找属于本真自我的“旅梦”“不再相信海的消息”(《山外书》·1952),甘为“被掷的水手”,作“裸的先知”,而“饮着那酒的我的裸体便美成一支红珊瑚”(《裸的先知》·1961)。其放浪形骸,消解社会规范和文明异化的心性可见一斑。
此后,皈依自然与性情中的诗人如鱼得水,内外世界相互打开,形神圆融,灵思飞扬,乃悟到:“既不能御风筝为家居的筏子,/还不如在小醺中忍受,青山的游戏”(《雨季的云》·1959),而“众溪是海洋的手指/索水源于大山”(《岛谷》),这里的“溪”自是个在的精神“小溪”,自我放逐于“海滨”(与上述“时代大潮”同构,故有“不再相信海的消息”之句)之外,索生命之清纯与洁净的水源于“大山”(自然与诗)的“小溪”,且向“山外人”宣称:“我将使时间在我的生命里退役,/对诸神或是对魔鬼我将宣布和平了。”(《定》·1954)
由此,“愁予诗风”又有了“浪子本色”的指称。而关键在于,这位“浪子”经由他梦幻般的抒情所给出的“自然”,是仅止于为锈死的现实注入一针迷幻剂,或“悠然神会,不能为外人说”的消闲小札,或青春梦想的催情物,还是同时也蕴涵有对现代人诗性、神性精神空间的追寻、净化和提升?或者说,作为读者,我们在“愁予风”的沐浴中,是否如同洗“森林浴”一般,赋生存之冰冷与窒息以美的照耀和自由芬芳的呼吸,从而润化生命的钙化层(块垒),将凝冻幽闭于我们心中的激情与向往释放出来,重获清明而非迷失——而以此清明之眼反观尘世,便有了另一番被提升了的心境,另一种被洗亮了的视野?
在此,我不想作什么结论。我只想指出,所谓意境,不在大小,而在真伪。我同时看到(自是从诗中看到),诗人郑愁予在本质上是一个性情中人而非观念中人,这决定了他那份美丽的“逃逸”和“错位”,是出于真心、真意、真性情,有此一真,小又何憾?我们在他所创化的“小世界”里,感到了乡愁(现实意味的与文化意义的),感到了漂泊(个人的与时代的),感到了超越(物质的与精神的),更感到了一个消失已久的诗性、神性自然——在这里,自然不再是远离我们的背景,或仅作为诗性生命的某种外在的激活物,而就是诗性生命本身,或至少是与诗性生命一起散步、一起交流谈心的伴侣、情人或老友——“大自然是一座神殿。那里有活的柱子/不时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语言”(波德莱尔Charle Pierre Baudelaire诗句),这“语言”与我们复归舒放鲜活的灵魂一起,歌而咏之,思而诗之,融洽无间,和谐共生,浑然一体,“缀无数的心为音符/割季节为乐句;/当两颗音符偶然相碰时,/便迸出火花来,/呀!我的锦乃有了不褪的光泽”(《小诗锦》·1953)。
在失去季节感的日子里创化另一种季节,在失去自然的时代里创化另一种自然——这便是诗人于“逃逸”和“错位”之中,一直苦心孤诣“编织”相送于我们的“小诗锦”,“垂落于锦轴两端的,/美丽——是不幻的虹;/那居为百色之地的:/是不化的雪——智慧。”“以诗织锦”,真是小矣!可果真能“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勃莱克Blake诗句),则小又不小、以小见大了——只是,当这位大诗人投入另一次“错位”时,却不再“美丽”而令人小憾了。
五
郑愁予成名甚早,且以一部《郑愁予诗集Ⅰ:一九五一—一九六八》,最终奠定了他在台湾现代诗坛中无可争议的前排地位,同时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精品珍藏。
诗人在结束前期十八年卓异非凡的创作生涯后,随即赴美游学讲学而客居他乡至今。其间曾停笔多年,至1980年复推出新集《燕人行》,1985年推出《雪的可能》一集,可谓其中期之作,1993年推出晚近作品集《寂寞的人坐着看花》(均为台湾洪范书店出版)。
这是一次完全不同于前述性质的“错位”——错开本土、错开母语环境、错开“梦土”、“野店”和“醉溪”,在异国他乡中创化的新的“愁予诗风”,便渐渐有些变味。其中也可略见别一番乡愁,别一种禅意,以及对文化差异的反思之绪。但纵览之下,其整体展现的精神空间反显小了,而写诗也随之成了普泛生活的记录。“客居为侨,舒掌屈指之间/五年十年的/过着,见春亦不为计/见晨亦不为计/老友相见淡淡谈往/见美酒亦不/欢甚……”(《人工花与差臣宣慰》·1983),其心境情态可见一斑。“怀拥天地的人”,何以只剩下如此“简单的寂寞”(《寂寞的人坐着看花》)?而语感也随之钝化。先前灵动飞扬的意象多为观念缠绕的事象所替代,缱绻芳菲的诗魂随之变为清淡的言说,一咏三叹的华美韵律也转为宣叙性的滞缓散板。只是到了《寂寞的人坐着看花》一集新近作品中,诗人方渐复入佳境,有了一些品格清奇的佳作。尤其一贴近大自然,那支生涩的笔又灵动起来,如《苍原歌》中,“大戈壁沿着地表倾斜/有马卧在天际昂首如山/忽然一颗砾石滚来脚下/啊,岂不就是风化了的童年”,颇具早期遗风,且添了些凝重。再如《静的要碎的渔港》中,更有“港湾弱水/静似比丘的心/偶逢一朵白云/就撞碎了”的素句,天心禅意,不逊当年。
总之,在对书斋化、学者型的新的“愁予诗风”的鉴赏中,我们时时会强烈地怀念起当年的“野店”风和“浪子本色”来。实则学者的灵魂与抒情的灵魂并非一定相悖,关键在于有无生命内在的激情以及痛苦逼你言说;或者,看你是否能在渐趋促狭的中年之旅后,化个人有限精神实体入更阔大的生命场,拓殖出一片更新的诗性生命空间来。
说到底,诗是生命的言说,是生命内驱力的诗化过程,而“错位”即是“消磁”,亦即对存在之非诗非本我非诗性/神性生命部分的剥离与重构。同时,由于各个诗人的才具禀赋的不同,每个诗人还应始终把握住自己只能写什么和只能怎样写。由此更可反证早期的“愁予诗风”,绝非简单的“唯美抒情”之一己私语,而是深具通约性和开启性的生命、自然与诗性的新牧场、新天地——那“梦土上”孤寂的幽思和奔放的梦想,实则饱含着青春的激情和生命的热忱,而那些纯正的金属般的声音、丝绸般的幻美和天籁般的意蕴,至今仍令我们心驰神往而难以缺失。
或许,不仅是郑愁予,而且是我们所有的诗人、艺术家,都将重涉一个“错位”、“消磁”而复回溯的时代!
“而所谓岸是另一条船舷/天海终是无渡/这些情节/序曲早就演奏过”(《在渡中》);
而“我的木屋/等待升火”(《雪原上的小屋》);我已回归,我本是仰卧的青山一列!(《客来小城》·1954)
【注释】
[1]借用梁宗岱论瓦雷里(Paul Valéry)语,见梁宗岱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页。
[2]转引自萧萧著《现代诗纵横观》,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48页。
[3]转引自流沙河编著《台湾诗人十二家》,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4]均转引自萧萧著《现代诗纵横观》,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8、359页。
[5]转引自沈奇选编《西方诗论精华》,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年版,第63、90、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