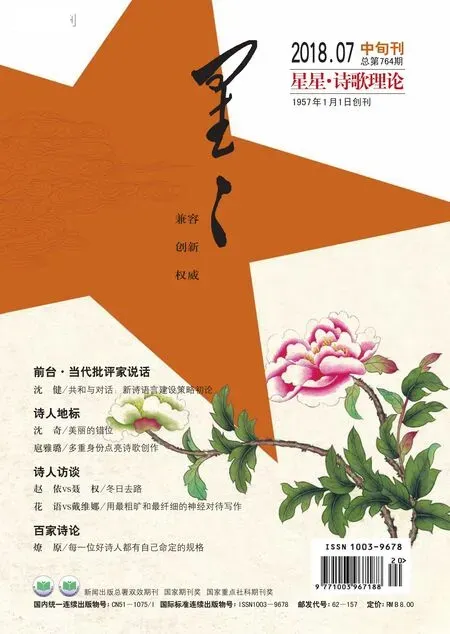用诗歌的手术刀解剖人生
——宇风诗歌艺术特色微探
陈小平
宇风说他的职业是修理工。初听时我以为他和鲁迅一样,以笔为刀来修理人的精神生活,这更加强了他在我心中儒雅的印象;深入接触以后才发现他的“修理”是真的!宇风的“诗歌”同他的“医学”有着内在的特殊联系,无论是作为职业医生还是作为诗人,他都不忘用自己包罗万象、包医百病的手术刀,既解剖病人,也解剖人生。
凌厉的文风
宇风的大量作品都表现出凌厉的文风,他的诗歌常常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表现出极强的思想穿透力和情感震撼力。他的《爱不爱都睡在一起》更是用犀利的词语来达到反讽的效果:
拉开窗帘就像褪下传统的裤子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
赤裸的商品经济象流氓一样站在那里
贪婪地窥视着处女样现代文明的身体
眼花缭乱的物价和税收丰满了国家的颜色
我们要把眼睛闭上才能看清世界的本质
金融就是枪,政治就是适时的扣动扳机
但是,爱和不爱依然睡在一起
——《爱不爱都睡在一起》
读完这些诗句使我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在他文学气质的背后,应该拥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作为背景,并由此而渗透、反映到他的审美艺术行为中。其中,解剖学对他的形象思维力和艺术感受力意义最大,他将直面生命的原生态与探取生命隐在的机理奥秘荟萃于解剖学中,使得自己对“医学术语”和“人体器官”表现出特别的关注,这些对于激活并形成他那凌厉的文风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他的诗中,“伤痕”“针灸”“血管”“产房”“体温”“伤口”“刀子”“利刃”“刀刃”“利剑”“刀锋”“全身的经络”“完整的底片”等等与解剖学相关的语词大量存在,这些都是他用医生的视角看到的特殊的意象。除此之外,“手指”“嘴唇”“牙齿”“眼睛”“面孔”“脑袋”“头颅”“骨头”“毛孔”“乳房”“小手”“胃”“脐带”等身体器官词语出现频率也异乎寻常地高。
按常理来说,把这些意象从作品中单独提出来讨论,并没有多少值得深究的意义,但是,这些意象一旦进入到他的作品当中,形成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便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形成了他诗歌最为突出的特色,让人不禁感叹他独特的想象力和对医学意象的组织能力。他诘问“谁,去为雪山包扎伤口”;他感叹“像无影的刀,割着心 /不见伤口,只见痛”;他追思“从深渊走出来,赤裸着身体 /举起我的心脏”。在不经意之中,诗人想要表现的思想情感得以更形象地突显,增添了整首诗的力量感。
宇风不喜欢用过于晦涩的隐喻和太过繁复的象征,他喜爱追随着心脏跳动的方向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凌厉的文风下流淌的是心灵的真实感觉,可见其对诗歌的热爱和独特的审美倾向。其诗作还大量借用 “阴森”的夜色(黑色),用自己不甘平庸的心和愤世嫉俗的态度来营造昏暗、悲观的感情基调,突显诗歌的张力和特点。在他看来“我们自己血管里流动的却全是夜色, /我们拿什么来哺育我们的孩子! /即使勉强哺育出来的孩子, /他们将来都会变成一个个黑暗、罪恶的化身; /这世界,有了罪恶,使一切歌颂都显得苍白”,是因为“我的两个眼球,是一双饱含黑色灰烬的果实, /再也无法阻止灵魂在黑夜中贩卖阳光,/于是,黑夜放射出黑色的光芒,更加辉映着黑色的大地”,他认为人世间是痛苦的,“不如把自己的心脏和眼睛抠下来放在荆棘上, /让纯净的心和眼睛照亮痛苦的人世”。诗歌不愧是带有神性的文学,从我国的第一位大诗人屈原开始,“疼痛感”已经成为诗人通向神灵的一大通道。宇风诗歌的“疼痛感”,让你觉得犹如被老虎抓过一样疼在在你灵魂的深处,而非是被猫挠痒痒。更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诗句都带有与医学相关的感觉特征和十分鲜明的解剖学印象,由此形成的文风使诗人想要表达的主旨生龙活虎、形神兼备,就像风雨夹着雷电、雷电裹着风雨,成倍增加文章振聋发聩的效果。
新锐的直觉
正如解剖学首先要了解正常人体结构一样,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宇风不自觉地加强了自己的文学结构逻辑。他的很多诗歌都会选取一个中心句在文中重复,如《爱,是如此复杂》中的前三小节每一节都是以“爱,是如此复杂”开头,重复并借此构成诗歌的整体结构,让读者在诗歌反复回环的过程中体会诗人想要着重表达的情感。这或许并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经过长期在医院中的实境操作、亲临体验后激起对于诗歌结构的新锐的直觉,并进而借助诗歌之“笔”化为穿透隐秘的利刃,将其转化成了某种具有文学感受和形象思维意义的惯性和定势,以此震撼人心。
如《距离》:“远远的,我站着/大地上有一片艳丽的天空/光芒的多情地四射/诱惑着许多人心/我向它走进/艳丽的天空变成了黑色的墙壁/壁上布满血淋淋的嘴唇/露出毒蛇般洁白的牙齿/我转身逃开/站在原来的地方/黑色墙壁又变成了艳丽的天空/远远地牵着许多人的目光”。这首诗仿佛有一个百脉之会、贯达全“诗”的“百会穴”。就内容而言,你“向它走进”,触碰到那个穴位,它就会变成“黑色的墙壁”,上面“布满血淋淋的嘴唇”并“露出毒蛇般洁白的牙齿”;如果你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它”就会变成“一片艳丽的天空/远远地牵着许多人的目光”。“百会穴”成为了全诗的中心点,以它为中心,本诗突然好像具有了某种中心对称的结构之美。就形式而言,由“百会穴”串起的“任督二脉”成为了全诗的中轴线,形成了“远——近——远”的轴对称结构,全诗内在也包含着一种“慢——快——慢”的轴对称节奏,这样一来,诗歌便如同人体结构一样,有了对称的美感。
《影子传奇》这首诗歌的结构更是精妙,宇风用他新锐的直觉创造了这首诗歌独特的表现形式:
比黑夜还黑的影子
浓得打不烂撕不碎扯不散的黑
影子,死于阳光的死亡
复活于阳光的诞生
被阳光拯救的影子
以摇曳的身姿在光明中歌唱
复活的影子,披着光明的外衣
在光芒中自由地穿行
站在光芒中的人们
除了看见自己,什么也看不见
而我却看见那些影子
变成把国土烧成灰
也要在灰烬中称王的人
无需做过多的解释,只看这些勾画出来的相同或相近的词语,不难发现,宇风的一系列诗歌都有着内在相关性的外围表现,可以说,宇风在诗歌风格和诗歌艺术思维上所做的探索,有一个个人化程度非常强的解剖学结构的探索方向,他的诗歌与医学之间有着某种可以捉摸的通道,并以其新锐的直觉而展现出来。
严峻的感情
宇风直言“我只是一个苦难的象征”,“我只不过是按在岁月上的一个印记”。他对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阴暗面始终持着一种批判的心态,他探讨人生,挖掘人性,结果总是看到现实的丑恶,深为痛苦和矛盾。他常常把自己当作侠客、英雄,但他又始终保持着情感、肉体、灵魂三者独立统一,他无法找到精神上的寄托来摆脱灵魂上的孤独与寂寞,所以他将自己的情感置于艺术的手术台,用他那把手术刀一般犀利的诗歌之笔去分筋剔骨,既解剖自己也解剖别人,于是“我逐渐清晰的看见,世界正在抄袭着我痛苦的表情”。
他的一切艺术情感均来源于自己,然而,他却并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我要走向哪里/我的脑袋牵着别人走/别人牵着我的脑袋走/我的脑袋不再是自己的脑袋/我的双脚不再是自己的双脚/我不知道我是谁/或者谁又是我/我只记得——/‘我是耳光同时又是脸颊’/我既是道路又是车轮/我既是刽子手又是受害者//现在 要么我滑入黑夜/要么跨进白昼/或许原地不动/站在夜与昼的夹缝中/装饰人间风景/平凡的生存又默默的消失/我很清楚 当我抛弃世界时/世界早已抛弃了我”(《我不知道我是谁》)。这无疑又是对诗人情感世界的一次严峻的考验,由此,在他的诗作中,“死”已经变成了很平常的事情。
死,只是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
爱与恨,是一道门关闭和开启的关系
我,用爱杀死你,亲爱的
这不是我的本意
至今,我也不明白,世上
最具杀伤力的不是核武器
只有真爱,能够灌溉、滋养这个世界
或者摧毁这个世界的一切
——《爱死你》(节选)
从未如此爱过
在预谋的时间里,穿越一场死亡的爱情
……
从未如此爱过
让我化作一缕轻风,悄无声息地在你的窗口凝望
或从门缝中穿进去,抚摸你冰冷的身体
在虚实和混沌的时空里无形、有形、睁眼和闭眼
如细雨潜心般宁静、禅意地进入你的身体
用我温暖而又浓浓的爱意把你包裹
让你冰冷的身体在我心里获得春阳般的沐浴
——《从未如此爱过》(节选)
这是在冬季
所有人的爱情里没有我的爱
所有人的死亡里都有我的死
——《爱比死还冷》(节选)
在宇风的艺术世界里,有很多时候“死亡”几乎与“爱情”等同,他对爱情有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观点。上面节选的几首诗都出自他的爱情组诗《爱的独白》,细细欣赏其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爱仿佛是在模仿鲁迅先生在无爱的十年婚姻后一字一顿地宣告:“我可以爱!”;也像是在读过郭沫若《维纳斯》等赞美女性肉体美的诗文之后,受到现代中国文学中歌颂现代性爱的华彩篇章的感染;更像接受了郁达夫惊世骇俗地直言呼唤来自异性的爱情的鼓舞。他揭示出自己的情欲,令自己与所爱之人无所逃匿于天地间,大胆且犀利地解剖自己的情感与肉体,刀刃所向,让灵魂里的各条神经皆裸露出来,给世人看个明白。
宇风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不断探索、追求写作诗歌的意义,一旦遇上他那异乎寻常的激情,他手中的诗便化为了解剖人生的手术刀——敏锐深刻的人性解剖刀、淋漓痛快的社会解剖刀、睿智发隐的思想解剖刀!就像取得过医学学士学位的郭沫若先生曾在《解剖室中》高呼“救亡”、“启蒙”的时代主题一样,宇风也默默地加入到现代诗人的“精神之战”之中,这使他儒雅的形象中更增添了些挺拔与傲岸。
以上都是我对宇风诗歌粗浅的看法。其实,《出版协议》《在月光中游泳的鱼》《捶洗脱下的日子》《把脚印放在文字中奔跑的人》等诗作,我也甚是喜欢,如果能把其中的有些好的诗句拿来仔细琢磨,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或许某一天,你不仅能用诗歌的手术刀解剖人生,也可以用它来反观、解剖自己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