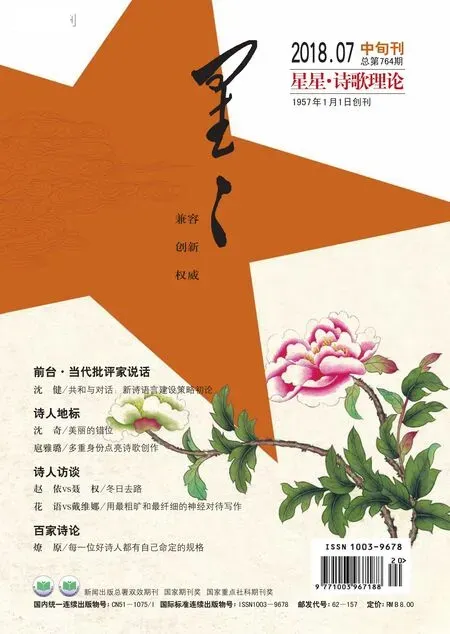边缘与坚守
——“燕赵七子”诗歌创作简论
吴 媛
关于“燕赵七子”,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说:“他们不仅代表了各个写作方向和诗歌美学,而且从河北地缘文化上而言也接续了一个坚实的诗学传统。”燕赵七子的集体出发,不仅因为他们是各自城市诗歌群落中的代表人物,更主要的是他们代表了目前河北或者说北方诗歌写作的一种姿态,一种让诗歌脱离政治,脱离娱乐,脱离哗众取宠,回归本源的写作姿态。七子里没有一个职业诗人,他们作为河北诗坛的重要力量,却只是一群“业余诗人”。或许,诗歌和诗人的所谓“边缘”其实根本无须惊慌失措,诗歌只是回到了它应该待着的地方。他们的诗歌里有独立自主的人文精神和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想象,他们批判,并且反省,在对个体与世界关系的把握中构建起独立自足的诗歌世界。
在诗歌写作私人化蔚为大观的今天,每个人都在写自我,导致对个体的书写逐渐变成了新的公共话语。貌似增强了诗人的个体辨识度,实际上千人千面,造成当下诗歌写作整体上的面目模糊,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因而,对诗人、诗歌做地域性划分、集团化推介不仅成为诗歌批评的一条终南捷径,也成为诗人在众声喧哗中确立自身写作范式,赢得更多话语权的一种快捷方式。故而河北有“燕赵七子”,甘肃有“甘肃八骏”,第二届“当代中国诗歌论坛”上则推出了“江南七子”。这样的集团推出,便于诗人迅速在广阔的地域空间和深广的时间纵深两个维度上明确自身坐标,以更加鲜明的审美追求为召唤,在诗歌创作领域寻求新的突破。但这样的推出背后往往有当地文联、作协等官方机构和诗歌批评界的大力助推,文学之外的人为因素过多,恐怕会对这类诗歌群体未来的发展产生一些当下尚不明确的影响。即如“燕赵七子”,虽然“七子”彼此之间有着密集的诗歌创作交往,有着相对一致的写作态度,但仍需注意,仅有共同的写作姿态是不够的,要真正成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写作现象之一,还要有更加明确的共同创作倾向和审美旨归。
士大夫的前世今生——东篱
在东篱身上,传统中国“士”的良知和悲悯成为诗歌的重要主题,而“士”的审美取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诗歌的风格特点。东篱也许是七子之中最注重营造诗境的诗人。与很多当代诗人强调人在世界中的割裂和荒诞不同,东篱努力地向着中华文明的上游回溯,寻找足以完善个体缺憾的民族记忆,寻找能够打开人与自然沟通之门的那把密钥,寻找更加丰富的诗歌语言并企图获得更开阔的诗歌想象能力,然后,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自足的诗歌世界,以花为媒,以爱为名,在诗的世界里修行,并完满。
东篱是爱花人,面对花和如花的生命,东篱最迷恋的一个动词是“挥霍”。诗人热爱生命,也热爱这种挥霍生命的痛快,而这种热爱的能力恰恰就是生命的本质力量之一。但东篱又是平静的。他爱过,恨过,伤怀过,人到中年,他和他的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到了静谧和安详。在他的诗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锦鳞游泳,岸芷汀兰”之类,毫不鲜见。难得的是,诗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向古典诗词致敬,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却并不令人感到违和。我想,这与他整体的诗境有关。东篱这些引用古典诗词的诗作,都极重完整性,整首诗是一个完满的圆状结构,诗中气韵一以贯之,而且在语言上通过副词、介词的使用突出句的整体性,淡化词的割裂感,使诗歌的语言形式与诗人内心世界的完满相呼应,给人以神完气足之感。
但是,在东篱的诗作中,也存在着“同质化”抒情的倾向。一些特定的题目、题材似乎自带抒情预期,在地震遗址面前感叹生命,在皇帝陵前品味今昔,都很难带给读者新鲜的体验。
知识分子的良知——晴朗李寒
晴朗李寒骨子里应该是个不安定的灵魂,就像晴朗遇到严寒,抵死纠结,矛盾丛生。晴朗李寒身上有着继承自五四时期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清醒、悲悯和难能可贵的独立人格。在晴朗李寒的作品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人的真切关注,他的诗作中往往都有一个鲜明而丰满的“我”,作为一切苦难和幸福的感受者和承担者,作为诗人与世界沟通的代言者,成为诗人为自己营造的诗歌世界中的主人。诗人有着强烈的言说欲望,他的眼睛一直热切地关注着这肮脏而又火热的尘世,他和他所观察着的众生既是同构的,又是异质的,有时候,他就是他们,有时候,他是他们身后冷静的眼睛。正是这种关照社会人生的角度,使得晴朗李寒的诗具有了较强的批判现实精神。
时间是晴朗李寒诗歌中挥之不去的主题,《流年》里,诗人站在时间的纵的坐标上,看着“后面的村庄”,前面的“单车下的道路”,以及没有来的风雪,“那些我们无法预知的事物”,短短的一首诗容纳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各种意象,自然而然生发出“尘世恍惚,时光新鲜”的感慨。诗人很少在诗中直接谈论死亡,但他也总是习惯性地探究生命的线性轨迹,从来处来,到去处去。死亡意识或者叫生命意识充满了他的诗作,而这种终极思考显然也软化了诗人的一些棱角,使他显得更温和,更包容。诗人无可避免地想到:“如果/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夜晚,啊,上帝——/也没有什么遗憾了:/最爱的人,都在一起,/最喜欢的书籍,堆在枕边,/诗歌、爱情、温暖、光明,我们都曾享有过了。/此刻,就让我们松开双手吧,/向世界告别,/疲惫而安然地入梦”(《最后》)。郁葱说,一个能记录自己心灵史、生存史、思想史的诗人一定是一个出色的诗人。他说,李寒做到了。
自然之神——北野
北野的幸运,是他不仅就生活在燕山脚下,而且有足够的力量将自己整个向燕山敞开,让这份独特的风骨为自己洗筋伐髓,铸就一副特异于整个河北的诗歌筋骨。北野,是不同的。
霍俊明说:“河北诗歌以及‘燕赵七子’是有传统的,有历史感,有地方精神支撑和文化资源的。”但是,支撑北野的燕山毕竟与太行不同,北野的诗也与很多沉实厚重、风格上倾向温柔敦厚的河北诗歌不同。诗人北野不敦厚。他的诗野性、思辨,有巫风。嬉笑怒骂,调侃戏谑皆成文章,却又鞭辟入里,令人痛入骨髓。他的诗里,融合了西方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原始的种种野记传说,即诗人大解所说:“他的诗有着复杂纠结的辩驳和互否,在意象的相互撞击和磨擦中环环相扣,强力推进,把读者推到无法置换的境地。”
如他的《家族孽运记》,将历史,信史也好,传说也罢,统统用最荒诞的笔法炖成一锅杂烩,冷眼看几千年文明,所有一切世事纷扰,离合遭逢,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终究都抵不过无意义三字,“乱纷纷都是/旧容颜”。与“他们”的“惊慌失措”“被摧毁的碎片”相对的,是“我”的完整、淡定乃至逍遥。诗在,诗心在,诗人在。此诗读罢,直欲令人抚掌大笑,当浮一大白。
诗是生命存在的支撑,是纷纷乱世中人的救赎。除了诗,更贴近根本的救赎是“空旷的田畴”“低垂的云朵”,是草原和大海,是深井和天空,是最广袤,最无私,最宽容的自然。
北野在语言上一直抗拒着传统汉语的所指惯性,并成功拓展了很多被悠久历史符号化、模式化的语词的内涵和外延。
北野就像是大自然鲁莽的孩子,在这个不洁的人生中闪躲腾挪,笑谑无忌。也许他可以写得更凝练,更纯粹,但我怀疑,那时候,他还是北野吗?
玄想之神——见君
见君说:“靠近我的拥抱,我的/被你猜测到的致命的呓语”。这句话几乎像宣言一样指示了见君整个的诗歌创作——呓语即诗语。呓语,或许在见君看来,恰恰是最接近神灵的语言,每一句都看似对抗逻辑和理性,乃至正常的语法规则和语言习惯,但其实每一句都是对现实世界痛苦最真实的折射,通过这些梦境般迷离破碎的只言片语,诗人以打破常规的姿态靠近生活的真相,描摹碎片化的生命历程。梦是见君诗歌中堪称主宰的东西,也是诗人选择和神灵沟通并向众人宣讲神示的方式。
在语言风格上,见君似乎是有些暴力倾向的。他说:“而我,依旧在院内唱十八相送/唱完了用刀剁碎,撒些盐/挂在树上(《梁兄》)”;“被暴打后的傍晚/捂着伤口,突然来临(《去南方》)”“锋利的刃/一下,一下地,割碎那张纸(《惊心动魄》)”这些坚硬、冰冷、残酷的词语在见君的诗中并不鲜见,他似乎很乐意用这样一些刚性的语言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决绝,但另一方面,似乎也是在伪装自己的柔软,一种类似于“这个杀手不太冷”一般的情感。
这样的语言习惯也使得他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较强的先锋性,从而以强烈的自在感区别于大多数河北诗人。见君是尖锐的,是冷酷的,是与温柔敦厚的大雅之风大相径庭的。张柠在评价先锋文学作家时说:“他们的形态很奇怪,既像兄弟又像父亲,所以给年轻一代留下的是一群‘恶童’的形象。他们充满了善良的恶意,并将这种特征转化为符号的编织,供人们敬仰。他们表面给人一种不稳重、不成熟的印象,但是他们的不妥协、不屈服,给了年轻一代精神成长强有力的支持。”“善良的恶意”,也正是我在见君的这些呓语中读到的。
见君把诗歌对个体的思考和表现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深度,但有时我也忍不住要追问,诗人对“个我”的探究到哪里才是边界?生命还有多少秘密可以在诗歌中言说?当我们过于关注诗歌的内指性,会不会放弃了更多?越来越深邃的理性探究会不会因为过于狭窄而失去它应有的力量?我想,诗歌终究是要从个我中升华,去寻找与大众情感的交汇,与人类思想的共鸣,在更为辽阔的空间和更悠远的时间维度上释放出亘古不变的意味。
状溢目前——李洁夫
李洁夫的诗好铺排,形式上喜复沓,回环往复的句式较多,一首诗20行轻而易举。
语言上,李洁夫的诗言之唯恐不尽其意,擅长将各种平凡朴素的语言放在一起,熔铸出华美的抒情效果,他的用语一般明白晓畅,但有时似乎过于追求语义的确定性,即使已经“状溢目前”,仍忍不住阐释的欲望。在七子之中,只有李洁夫试图在诗歌中解释词语,解说诗意。很难说这种阐释癖对诗歌来说是喜是忧,就像复杂多义的诗歌在接受领域冰火两重天一样,对于一首诗来说,最重要的从来就不是形式。李洁夫的诗中满满充溢着各种悲喜情绪,他就这么旁若无人大张旗鼓地抒情,勇敢而真诚地袒露整个内心世界,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情感王国。不过如果诗人对这些饱满丰富的情感稍加提炼,适度地给读者留下一些想象空间,也许效果会更好些。
李洁夫的诗几乎使用了所有美好的、善意的、柔软的词语来歌唱生命中的一切美好,尤其是爱情。读完见君的诗,再来读李洁夫的《突然想收起心去好好爱一个人》《梨花》和《美好》,就像从大雾弥漫的黑森林来到晨光熹微的草地,忽然间陌上花开,令人直欲潸然泪下。
从来“穷苦之言易好,欢娱之辞难工”,单凭李洁夫敢大张旗鼓地把“美好”列在诗题处,便足见其不凡。李洁夫笔下的“美好”有形状,有颜色,有味道,不是概念,不是口号,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我们很难想象怎样在一首诗里让人对美好产生具体而鲜明的印象,但自李洁夫之后,美好,也许就是“蓝色的膏体里茶洁的味道”。
意在词外——宋峻梁
中国古典诗歌讲究“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中国画也讲究留白,而要达到这种境界,避不开的途径就是炼字。放到现代汉语诗歌中,就表现为对语义的提炼,对语言的锻造和词、句的安排。于此一道,宋峻梁显然深有体会。宋峻梁的诗深邃、凝练、朴实无华,选本中十行左右的短诗比比皆是,诗中的情感和思想含蓄内敛,引而不发,有一种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底气和淡定。
宋峻梁和李洁夫都是善于并且惯于处置个体经验的诗人,但二者面向生活的姿态和处理生活经验的方式都极不相同,相比于李洁夫对生活不遗余力的热爱和歌咏,宋峻梁似乎更愿意与生活现场拉开些距离,以严肃冷峻的目光,关注并思考个体在现实中的种种存在状态和生活体验,呈现出真实而痛切的个体生活史。
个人化的生活现实必然是碎片化、场景化的,宋峻梁显然很乐于撷取这些场景入诗。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欠缺了一些主动的诗歌史意识。他似乎很满足于自己边缘化的处境和进退自如的处事方式,表现在诗歌里就是缺少了一些人间烟火气,没有对现实强烈的批判精神,也缺乏对美的热切歌颂,虽然真水无香,却到底失于太过平淡。
从诗歌语言上来说,宋峻梁像个高超的魔术师,他从不过分着迷于词语本身的隐喻性,但是通过对诗歌内容的驾驭和节奏的安排,他成功地让这些诗作达到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境界。韩文戈说:“他诗歌节奏、气息的不紧不慢、舒缓自如,语言的质朴,既是他现实生活里的真实状态,又应该看做是来源于他生活中的那种自信在他作品中的反映。”
最后的骑士——石英杰
石英杰的诗歌最大限度地呈现了一个诗人的野心,或者叫抱负,他的诗歌史抱负。他一直力图透过光怪陆离的现象直抵生活的本质;力图穿越时光之河的片段追溯这个多舛民族的历史在个体生命中的投影;力图通过种种探究将历史和现实,现象和本质叠加、对照、比较,从纵的和横的角度观照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石英杰的幸或不幸都源于他的故乡,那个以“易”为名的地方。这里足以载得起他再多再重的追思和回溯。千年前的风云变幻熔铸成诗歌中的荡气回肠,成为燕赵儿女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积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自此,这条河在两千多年的时光中被一层层反复皴染,涂成了今天堪堪代表整个燕赵风骨的颜色,成了除黄河长江之外,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河。易水,早已不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河流,它是被无数膜拜英雄的人们神化、史化、诗化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出生在易水河畔的石英杰,何其有幸,得此地利之便;又何其不幸,自人之初便被浓浓的历史人文气息包围,自觉不自觉地皈依了某种被历史认为合理的道德法则和伦理标准,再不肯将一个自然人的嬉笑怒骂、肉身欲望入诗。他几乎一直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献祭给易水,他的故乡,他的精神家园。
也正是基于这种积极主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石英杰书写的从来就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他的诗里,既是个体的人生,也是他者的人生。他致力于把自我从躯壳中剥离出来,严肃审视这出离的灵魂,同时审视无数个与他相类的灵魂,寻找千千万万个“他”身上烙印的伤痕和苦楚。但这种审视的姿态和对群体共通体验的书写却往往对诗歌中可感可触的痛感和生命的热度形成阻碍。石英杰的很多诗歌在批判现实和历史想象的维度上显得有些用力过猛,个别作品甚至出现了图解历史的倾向,牺牲了诗歌的温度和个性。
东篱、晴朗李寒、北野、见君、李洁夫、宋峻梁、石英杰,“燕赵七子”的年龄都在40岁以上,都承担了社会学意义上赋予中年人的责任担当。这也意味着他们基本上已经与生活达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和解,或者说他们找到了个体面对现实的复杂荒诞的最佳方式。这使得他们对人生、命运有了更深切的体悟,像罗兰·巴尔特说的“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转换不已。”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到中年带给“燕赵七子”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让他们不再具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尖锐和力度,稳定必然对抗动荡,和谐融化了龃龉,年龄折旧了生命本身的疼痛。缺乏鲜明独立的知识分子精神和与之相伴的对严肃社会生活的参与感、关注度,使“七子”诗歌普遍欠缺楔入现实的力度和尖锐感。
“七子”在他们各自的职业身份掩护下坚持诗歌写作最少的也要在十年以上了,民间的身份和写作过程中日渐自觉的知识分子精神构成了他们诗歌态度的主要成分,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该边缘的时候边缘,该坚守的时候坚守。并且,不彷徨,不游移,不抛弃,不放弃。我想,这就是燕赵大地上几千年传承不灭的人文精神,所谓的“燕赵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