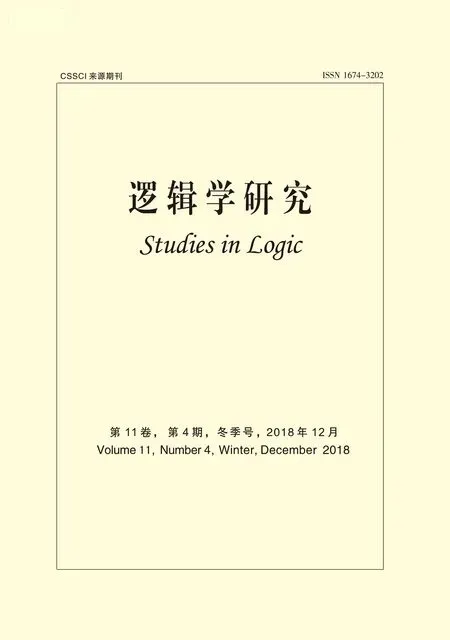分枝量词的语义解释及其本体论承诺*
颜中军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yzjstudent@163.com
1 引言
众所周知,经典逻辑恪守组合原则(又称弗雷格原则),致使前置的重叠量词的语义解释具有线性特征。在解释过程中,遵循着从左至右的原则,即“域窄的量化结构的解释是在域宽的结构所提供的定义域中进行的。”([16],第156页)不过,真正受到影响的是存在量词而非全称量词。因为全称量词的取值遍历定义域中的每一个个体,而无论其它量词取值如何。但是,如果放宽对重叠量词的线性要求,允许非线性关系存在,那么我们就得到了分枝量词。
1961年,亨金在著名论文《关于无穷长公式的几点评论》中首次提出了这种有穷偏序量词(即分枝量词,又称亨金量词)([7],第167–183页)。尽管亨金仅仅讨论了形式语言层面上的狭义的分枝量词而未深入探究自然语言层面上的广义的分枝量词,但分枝量词的研究迅速引起了逻辑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家的普遍关注和热烈讨论。譬如:分枝量词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自然语言中是否存在真正的分枝量化式?如果存在,那么怎样刻画分枝量化式?如何解释分枝量化式?它们是必要的吗?引入分枝量词将会带来怎样的哲学后果?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促进逻辑学与哲学自身的发展,而且还有助于自然语言理解及其信息化处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2 量词独立与狭义分枝量词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研究动机、历史背景与基本假定,经典逻辑亦不例外。稍微回顾历史便可知晓,现代逻辑的产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关于数学基础的大讨论密切相关。作为数学家兼逻辑学家的弗雷格改造自然语言、发明一套独特的纯粹符号——概念文字,并借用函数关系构建两个初步自足的演算系统——命题演算与谓词演算,其首要目的在于为数学奠定不可错的逻辑基础。弗雷格的逻辑学说建立在若干假定基础之上,例如组合原则、外延原则、二值原则、实无穷抽象法等等。其中,重叠量词之间的线性关系与相互依赖便是组合原则的具体表现。一阶逻辑有时被称为量化理论,因为其本质上是关于量词的。弗雷格在构建一阶逻辑时,正是通过量词之间的相互依赖来表达变元之间的函数依赖关系。例如,在公式(∀x)(∃y)Φ(x,y)中,变元y的取值受制于x的取值。“量词依赖因此成为一阶逻辑有力量的真正秘密之所在。人们几乎可以说,理解一阶逻辑就是理解量词依赖的观念。”([15],第43页)
然而,要彻底理解“量词依赖”,就必须同时理解“量词独立”,因为它们是同一范畴的两个方面,不可截然分离,更不可偏废。亨迪卡注意到,弗雷格记法犯了一个基本错误,即人为地排除了量词之间以及量词与联结词之间逻辑独立的可能性,“并且这一病毒已经感染了所有后来的一阶逻辑的表述和版本”([15],第43页)。
亨金最初是通过司寇伦函数来刻画量词间独立关系的,他将分枝量词定义为等价的司寇伦函数式。根据司寇伦范式定理可知,每个一阶公式逻辑上等价于二阶的司寇伦前束范式。([2],第275 页)例如,公式 (∀x)(∀y)(∃z)Φ(x,y,z)等价于公式(∃f2)(∀x)(∀y)Φ(x,y,f2(x,y))。函数变元f2取代了个体变元z。由于约束z的存在量词受到前置的全称量词∀x、∀y的影响,因此f2的主目包括个体变元x和y。由于标准的一阶公式具有线性特征,当公式包含多个存在量词时,在转换成司寇伦范式的过程中,本质上要求左边的存在量词的函数主目包含在右边的存在量词的函数主目之内([13],第538页)。例如,标准的一阶公式(∀x)(∃y)(∀z)(∃w)Φ(x,y,z,w)逻辑上等价于二阶的司寇伦范式 (∃f1)(∃g2)(∀x)(∀z)F(x,f1(x)z,g2(x,z)),f1的主目包含在g2的主目之中。司寇伦范式定理旨在揭示司寇伦函数与个体存在量词之间的逻辑关系,但这种等价关系并非一一对应。换言之,司寇伦范式定理的逆定理并不成立,即不是所有的司寇伦范式都可以还原为标准的一阶公式。只有那些满足线性序要求的司寇伦范式才可以转换为标准的一阶公式,否则就不能转换成标准的一阶公式。([12],第396页)例如,司寇伦范式(∃f1)(∃g1)(∀x)(∀z)Φ(x,f1(x),z,g1(z))是非线性序的,f1的主目并未出现在g1的主目之中。它表明,变元z的个体选择没有受到x的影响,因此不能转换成标准的一阶公式,而只能转换成非标准的一阶公式,如分枝量化式:

不难看出,分枝量词实际上就是对重叠量词间独立关系的刻画。如果说亨金主要从形式语言层面探讨了引入(狭义的或标准的)分枝量词的理论可能性,那么亨迪卡、巴威斯等进一步从自然语言层面(如英语)揭示了引入(广义的或非标准的)分枝量词的现实必要性。
3 “亨迪卡论题”与广义分枝量词
1973年,亨迪卡在《量词与量化理论》一文中,通过大量实例证明了部分英语句子确实具有某种偏序结构,它们不能用经典一阶逻辑来刻画,只能用分枝量化式来刻画,从自然语言层面揭示了分枝量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学界称之为“亨迪卡论题”(Hintikka’s thesis)([5],第369页)。以下便是典型的亨迪卡语句(Hintikka sentences):
(a)Every writer likes a book of his almost as much as every critic dislikes some book he has reviewed.
(b)Some relative of each villager and some relative of each townsman hate each other.
(c)Some book by every author is referred to in some essay by every critic.
(d)Some family member of some customer of each branch office of every bank likes some product of some subdivision of each subsidiary of every conglomerate.
上述例句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它们都符合英语语法规则,均包含多个自然量词,如some、every、each等,并且这些量词在语句中多次出现。很显然,同一量词的不同出现其逻辑涵义不同。以(b)为例,城里人的“某些”亲戚仅针对城里人,而下乡人的“某些”亲戚只针对乡下人。前后两个“某些”的选值相互独立,不受对方影响。如果用标准的一阶公式∀x∃y∀z∃wΦ(x,y,z,w)或者∀z∃w∀x∃yΦ(x,y,z,w)来刻画(b),都将增添不必要的依赖关系。因为它们分别等价于∀x∃f1∀z∃g2Φ(x,f1(x),z,g2(x,z))或∀z∃f1∀x∃g2Φ(z,f1(z),x,g2(z,x))。如果用分枝量化式来刻画,则可以很好地揭示重叠量词间的相对依赖与独立关系。([12],第398页)1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斜杠记法来刻画量词之间的独立关系,它与分枝量化式是等价的。限于篇幅,在此不赘述,具体可见参考文献[15]。一般地,自然语句的分枝量化结构可以表示如下:([9],第60页)

这种刻画量词独立的方式与诉诸于司寇伦函数的进路不同,因为它本质上仍然是一阶的([12],第403页)。它以更直接的方式处理自然语言中重叠量词间的独立关系,而无需使用嵌套技术来处理复杂的量化关系,避免了富考尼尔所批评的“巨核”(massive nucleus)结构([3],第560页)。
“亨迪卡论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激烈争论。部分学者否认自然语言中存在分枝量化式,或者即使存在分枝量化式,也是不必要的。主要反对理由有二:(1)从句法角度来看,它们可以化归为经典一阶公式;(2)从语义角度权衡,它承诺了高阶语义实体,需要付出比经典逻辑更多的本体论代价。
1979年,著名语言哲学家、逻辑学家巴威斯发表了《论英语中的分枝量词》一文,仔细辨析和驳斥了学界对“亨迪卡论题”的种种讹谬,捍卫了亨迪卡关于英语中存在分枝量化式的洞见。首先,他指出亨迪卡的论证中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容易招致误解。例如,亨迪卡没有区分“each”与“every”之间的异同,有时将“each”做宽域处理,有时将“each”做窄域处理,从而导致了含混。([1],第55页)其次,亨迪卡主要论及了与经典存在量词∃和全称量词∀相对应的标准自然量词,而未进一步探讨广义的、非标准自然量词,例如“many”、“most”、“quite a few”等。在巴威斯看来,不仅英语中某些包含标准量词的自然语句(例如“亨迪卡语句”)具有分枝特性,而且种类繁多的包含非标准量词的自然语句具有更加明显的分枝特性。因此,巴威斯拓展了分枝量词的范围,下列语句同样具有分枝量化结构:([1],第60页)
(e)Most relatives of each villager and most relatives of each townsman hate each other.
(f)Few relatives of each villager and few relatives of each townsman hate each other.
(g)Quite a few boys in my class and most girls in your class have all dated each other.
为了避免混淆,巴威斯严格区分了实质型分枝量化式与非实质型分枝量化式。前者不可还原或等价于标准的一阶公式,而后者可以。例如,下列分枝量化式就是非实质型的:

不少学者对“亨迪卡论题”持有异议,除了亨迪卡论证自身存在某些缺陷外,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处理的语句实际上是某种“伪装的”、非实质型分枝量化式([4],第141–157页)。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非实质型分枝量化式均可转化为标准一阶公式而不违反经典语义组合原则。
4 蒯因的责难与分枝量词的语义解释
另一种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于形而上学的考量。一方面,蒯因承认,如果要想准确刻画重叠量词之间的独立关系并且避免不必要的依赖关系,那么采用非线性的分枝量化式就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另一方面,蒯因认为这种“异常的”量化理论属于数学(集合论)而非纯逻辑,它以隐蔽的方式谈论函项,本质上是二阶的,包含了过多的本体论承诺。此外,含有分枝量词的逻辑系统不能同时具备有效性和不一致性的完全证明程序。([19],第87页)在他看来,“古典量化理论拥有一种特别的结合,即深刻性和简单性以及优美和实用的结合。在内部,它是十分活跃的;在界限上,它是十分清晰的。对比之下,偏离于它的理论可能更显得是相当任意的。”([18],第87页)基于根深蒂固的狭隘的逻辑观念,在蒯因眼里,只有经典逻辑才是最完美的,任何背离都是“非正常的”和“相当任意的”。而问题恰恰在于,分枝量词与经典量词必定存在冲突吗?二者不可协调吗?分枝量词的语义解释必定要预设高阶实体吗?一定比经典逻辑付出更多的本体论代价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如前所述,经典逻辑在语法构造上遵循递归原则,即允许由简单原子语句递归生成复合语句;在语义上恪守组合原则,即复合语句的语义是其构成部分语义的函数;并且预设了句法与语义之间的对称性。也就是说,经典逻辑公式是“一步一步”(step-by-step)建构起来的,其语义解释也是“一步一步”分析的,之后部分的建构或解释受到之前部分的影响。这大体上足以说明为何经典量化式呈现出线性特征:每个量词(最外层除外)都依赖于其左边的量词,每个量词(最外层除外)的个体域实际上仅仅是部分的、与之前量词个体域有关的,而非全域的、独立的。对分枝量化式而言,上下枝的顺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分枝公式中的左右顺序。但与经典一阶公式相比,“对分枝式不能先解释命题函项,然后就各个量词的特性由里向外地逐层解释量化结构。分枝量化式要求对各分枝一齐同时做解释。”([16],第166页)
不可否认,亨金初次提出分枝量词时,借用了司寇伦函数,将分枝量化式定e义为相应的二阶司寇伦前束范式,然后采用通常的二阶语义来解释分枝量词。蒯因正是抓住了亨金语义的特点来责难分枝量词及其语义学的。但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包含经典逻辑在内的每个一阶公式均可等价于相应的二阶司寇伦函数式。如果据此批评分枝量化式承诺了高阶实体,那么基于同样理由对于经典量化式也成立。
此外,亨金语义并非唯一的解释方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亨迪卡等人发展起来的博弈论语义学(Game-theoretical semantics,简称GTS)便是一个颇具潜力的替代选择。从博弈论语义学角度看,量化语句S的语义特性取决于相应的证实者(myself)与证伪者(nature)之间的二人零和博弈G(S)。在关于S的语义博弈过程中,S所包含的量词逐个地被局中人选定的个体专名所替换,直至消除全部量词,得到某个不含任何个体变元的原子语句。最后根据原子语句的真假来判定博弈双方的胜负,从而确定S的真假。如果该原子语句为真,那么我方胜,对方输;否则我方输,对方胜。因此,语句S的真可以定义为:S是真的当且仅当我方拥有G(S)的取胜策略。([8],第36页)显而易见,量化句的语义博弈实际上就是一场“寻找且找到”(seeking and finding)的选值博弈。
博弈论语义学比塔斯基语义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不仅适用于完全信息情形,具有与塔斯基语义学相同的真理定义功能,而且还适用于非完全信息情形,可以为分枝量词提供更为直观的解释。不难理解,经典逻辑的语义解释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完全信息博弈,即一方在做出博弈选择时,完全知晓对方之前的博弈选择,这恰好反映了量词之间的依赖关系。与之不同,分枝量词逻辑的语义解释则是一场非完全信息博弈,即一方在做出博弈选择时,并不知晓或不完全知晓对方的博弈选择,从而揭示出量词之间的独立关系。从博弈论语义学的角度看,经典逻辑可以看作是分枝量词逻辑的一个特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逻辑公式的本体论承诺与其语义解释有关,而与被解释的公式本身无关。如前所述,如果对经典量化式采取亨金语义,同样将承诺“函数”这类抽象对象存在;类似地,如果采用博弈论语义学,那么分枝量化式与经典量化式仍然将面临相同的本体论代价。因为两者只是信息状态不同,其他方面完全一致。尽管如此,佩顿(T.E.Patton)试图捍卫蒯因的观点,进一步认为博弈论语义学承诺了“策略函数”,它无论如何是二阶的。([10],第216页)然而,这个辩护理由是很容易驳斥的。因为本体论承诺与语义解释有关,而博弈论语义学既可适用于经典逻辑亦可适用于分枝量词逻辑。所以,即使存在“策略函数”,它也不是分枝量词逻辑自身导致的或者必须独立面对的,经典逻辑的博弈论语义学解释同样要面临这个问题。其次,塔斯基语义学更为直接地使用了“对象序列”这样的集合论概念,它同样具有二阶属性。([6],第428页)如果按照蒯因的评价标准,经典量化理论同样承诺了抽象的高阶语义实体,理应属于数学而非纯逻辑。这样一来,经典逻辑的“界限”就不再像蒯因所声称的那样“十分清晰”了。总之,蒯因以付出过多的本体论代价为借口而拒斥分枝量词的理由是偏狭的、站不住脚的。
实际上,蒯因也觉得这种责难似乎有些吹毛求疵并且有失公允,所以他试图诉诸于另一个自认为“更好的理由”([19],第87页),即分枝量词逻辑在元性质上存在某些“缺陷”。譬如,它不能同时拥有有效性证明程序和不一致性证明程序,而经典量化逻辑可以兼得。因为对于经典逻辑来说,证明程序的每一步都具有二重性:一个公式是有效的,当且仅当它的否定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通过证明一个公式的否定是不一致的来证明该公式是有效的,反之亦然。但这种方法并不适合分枝量化公式。因为与经典否定是一种弱的矛盾否定不同,分枝量化逻辑中的否定是一种强的对偶否定,从而导致排中律失效。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分枝量词逻辑呈现出来的诸多非经典特性?例如,它不可完全公理化、有效的公式类不是递归可枚举的等等,其中“语义不完全性是这一新逻辑最深刻的革命性特征。”([15],第47页)分枝量词逻辑的这些特性是否全都是所谓的“缺陷”?因为分枝量词逻辑的不完全性至少开辟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即对于各种足道的一阶数学理论,我们或许能够表述描述(模型论)完全的公理系统,却不违背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15],第47页)蒯因在面对分枝量词逻辑与经典逻辑之间的不一致时,极力袒护经典逻辑,罔顾分枝量词逻辑的独特性和经典逻辑已经被实质性修改的事实,试图以经典逻辑为标准来衡量一切,为所谓的“逻辑”划界。他只注意到了经典逻辑的“优点”(如完美清晰、简单实用等)或者分枝量词逻辑的“缺点”,避而不谈经典逻辑的局限或者分枝量词逻辑的贡献,并且经典逻辑是否真正具有这样的优点或者分枝量化逻辑对经典逻辑的任何修改是否都是不可取的,这些都是值得仔细商榷和有待严格检验的。
5 进一步评论与反思
综上所述,量词依赖与独立是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引入分枝量词不仅在形式语言层面是可行的,而且对于恰当理解某些类型的自然语句的逻辑涵义也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准确刻画和解释分枝量词需要比经典逻辑更加强大的逻辑。在技术层面上,分枝量词逻辑比经典量词逻辑更复杂,它为自然语言翻译和理解、实现人机会话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从逻辑发展的角度来看,分枝量词逻辑是修改经典逻辑的有益尝试,绝非蒯因所说的“任意的”背离,甚至有理由认为从线性量词到偏序量词是一种可能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经典逻辑的不足([12],第420页)。
正如苏珊•哈克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经典逻辑是如此熟知,以致于很少有人关心其起源、基础与动机([20],第47页)。然而,通过对分枝量词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经典逻辑对自然语言的刻画既不充分(至少不能刻画量词间的独立关系,表达力有限),也非必要(预设了许多与实际情形不符的假定,例如组合原则等)。不可否认,组合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是现代逻辑系统建构和语义解释的基本原则之一,能够实现句法生成和演算,较好地解释语言习得现象,有助于自然语言的计算机信息化处理等。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组合原则也存在自身局限性。组合原则要求句法规则与语义规则一一对应,要求辖域明确、语义单一、句法优先,即复合公式的每个组成部分必须界线清晰、事先确定,每个组成部分均具有独立的意义并且对复合公式的意义都有所贡献。但组合原则并不是经验原则,而是一种方法论原则。面对自然语言的复杂多样性,例如歧义现象、模糊现象、句法语义不对称等,如果强行加以组合处理,难免有矫枉过正和削足适履之嫌。我们不妨另辟蹊径,另寻出路。亨迪卡对分枝量词的处理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典范。
亨迪卡是一位极富创意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常常把自己比作“荒原狼”而不愿意成为伟大思想家的注脚。他在亨金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自然语言层面存在许多分枝量化结构,构建了信息独立友好的IF逻辑,并且在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论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博弈论语义学。亨迪卡的博弈论语义学构思巧妙。它“与塔斯基由里到外、由简单到复杂定义语句真的做法相反,GTS是反方向的,即由外到里、由复杂到简单定义语句的真。”([14],第22页)它具有许多新奇特性。例如,它无需假定原子公式的真,从而有引入无穷深度语言的可能。另外,根据博弈论语义学,当“我方”拥有取胜策略时,语句为真,而当“自然”拥有取胜策略时,语句为假。但“我方”没有取胜策略时,并不意味着“自然”就一定拥有取胜策略。换言之,语句可能既不真也不假。所以,经典逻辑的二值原则、排中律和双重否定律都失效了。([11],第39页)
分枝量词所带来的种种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逻辑的基础。因为一些学者声称经典逻辑是对自然语言的正确表达,具有不可错性,将经典逻辑面临的反例视为“异常现象”,试图通过划界而将其排除在逻辑范围之外。例如,帕顿指责分枝量词违反了组合原则,不能进行一一替换,因而不是真正的量词。([10],第221页)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分枝量词不同于经典量词,属于广义量词范畴。在逻辑发展史上,这种狭隘的逻辑观念并不鲜见。例如,康德曾断言亚里士多德逻辑已经完美无缺、无需发展([17],第11–12页),其自信结果变成了自负。无独有偶,身处20世纪下半叶的蒯因、帕顿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只不过把亚里士多德逻辑变换成了经典逻辑)。这无疑是康德式逻辑绝对主义的现代版本,也必将陷入康德式独断论的谬误。
总之,自然语言到底具有怎样的逻辑结构,恐怕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实际上,“意义的所有成分在推理和真值条件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并且只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逻辑学家才大半局限于研究比较少数的意义成分的逻辑特性。……自然语言与形式语言之间明显的差异并不证明自然语言是有缺陷的;而是证明我们对于自然语言的分析还不够充分,或者我们对于逻辑的形式化还不够充分,或者我们对于语言与逻辑之间的关系的了解还不够充分,或者我们的材料反映了语言和逻辑与我们迄今尚未作出合适解释的某一种第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4],第xiii–xiv页)逻辑学作为一门工具性科学,自身也是不断发展的。一些传统观点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例如IF逻辑对经典逻辑的批评和挑战。或者一些曾被认为与逻辑推理无关的语言要素,也逐渐受到了关注,例如广义量词、命题态度词,甚至包括语言的虚化成分(如汉语助词“的”、英语小品词“to”等)([21])。分枝量词逻辑同样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例如,从狭义分枝量词及其二阶语义解释到广义分枝量词及其博弈论语义学解释。在此基础之上,巴威斯、谢尔、范•本瑟姆等学者进一步探究了分枝量词的单调性并试图给出分枝量词的一般定义。另有学者则注意到亨迪卡语句的对称性特征,提出了一种更为直观的、双向的(two-way)一阶线性解释,从而避免使用复杂的分枝量化结构。([5])但无论持有何种立场,只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分枝量词的争论才有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借用亨迪卡的话来说,“拿出成果来,不然干脆闭嘴”([15],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