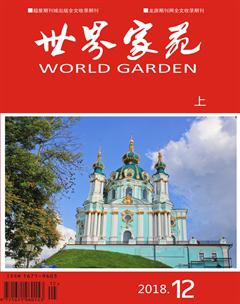语境理论对文化研究的贡献
张小鸿
摘 要:在文化研究的众多影响因素中,“语境理论”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故作为文化之一的口头史诗传承的过程中“语境理论”具有相当的影响作业,如今面临《玛纳斯》口头传承正面临着日趋式微的境况,因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释语境理论对《玛纳斯》传承的影响。
关键词:语境理论;《玛纳斯》;传承;影响
一、史诗背景
史诗《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逐步迁徙到中亚和天山南北的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这期间柯尔克孜族基本上维持着自己古老的萨满教信仰世界。因此,萨满文化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自然崇拜观念是《玛纳斯》史诗生成发展的根基,而伊斯兰教等人为宗教则是后来在史诗的口头传承过程中逐步融人史诗之中的。
在《玛纳斯》史诗的一些唱本中,英雄主人公玛纳斯所使用的阿克凯勒铁神枪、阿其阿勒巴尔斯神剑等武器被描述成是由来自麦加的伊斯兰圣徒所赐予。可以说,史诗第一部的主要英雄人物阿勒曼别特是整部史诗中伊斯兰文化色彩最浓厚的人物。他的出生以及因家庭内讧而离家出走,为了追求伊斯兰教而投奔哈萨克族汗王阔克确,后又投奔玛纳斯等情节都被描述成是与他抛弃“邪教”自愿皈依伊斯兰教有关。
在《玛纳斯》的多种变体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从其他信仰归依伊斯兰教,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教徒的人物。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身上依然折射出古代萨满文化的光芒。在史诗中还同样被描述成一个能够用砟达求雨石呼风唤雨,行使多种巫术的巫师。我们还可以从史诗的内容中随处看到伊斯兰教特有的诸如“唯一的安拉”、“胡达”、“阿克热提后世”、“扎满阿合尔(世界末日)”、“占乃提(天园)”等宗教词汇和“和卓”、“毛拉”等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特有的名称。史诗中一些重要人物们行使念经、礼拜、封斋、施舍、朝拜等伊斯兰教规定的五项基本功课的情节也十分普遍。在史诗的一些,诸如“玛纳斯的婚礼”、“阔阔托依的祭典”、“玛纳斯的葬礼”等重要章节中也有很多与柯尔克孜古老传统习俗相融合的伊斯兰教习俗。甚至在世纪的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玛纳斯奇萨恩拜奥诺兹巴克夫的唱本中,还出现了英雄玛纳斯去麦加朝圣,成为“阿吉”返回故乡的情节。
二、演唱时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史诗歌手活跃在哈拉布拉克的每一个角落,编织成哈拉布拉克人有意蕴的文化空间,调节着人们的精神生活,构成了哈拉布拉克和谐生活的基础。“逢喜庆佳节、婚丧仪典,柯尔克孜牧民不顾路途遥远,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白天举行赛马、摔跤、射箭等项群众性娱乐活动,晚上则聚集一堂听玛纳斯奇演唱史诗。歌手洪亮的歌声、优美的曲调、丰富的表情与手势,对于听众来说具有观赏、悦目悦耳之功能”。这些发生在特殊时空的表演活动,在史诗歌手听众那里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
然而,在今天的哈拉布拉克,很难见到牧民们围坐在毡房里欣赏《玛纳斯》演唱热闹场面。这种曾经被大家广为接受的表演形式逐渐被现代化的娱乐形式取代。即使在信息较为闭塞的牧区,能够看到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传统的表演时空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而改变。然而,在《玛纳斯》非遗保护的背景下,哈拉布拉克乡的这种传统文化在有别于传统的时空场域下,突破地区和民族的局限,成为更多人所共享的文化。《玛纳斯》演唱时空的变迁,史诗《玛纳斯》依然保存在原有语境中,但迫于旅游业发展、媒体的介入等现实的压力,也会在传承过程中被转换成为舞台化或文化展演的形式。探讨如何在这样的语境中保持和呈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诗《玛纳斯》的“真实性”,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三、史诗传承人
在平时舞台下的玛纳斯奇们的表演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现场发挥来决定,也是会因为旁边的观众的反应进而会决定玛纳斯奇的表演的热情度。也会因为玛纳斯奇的个人因素或者身体状况而有着种种的不确定性。以及舞台下的玛纳斯奇的肢体表演也不一定能够从始至终都是最好的,最饱满的状态。现在发展演变到的舞台化的表演不仅能够现场听到史诗《玛纳斯》而且也能因为这些演员用他们最专业的功底来表演,也能使我们观众大饱眼福,更加的感受到《玛纳斯》的魅力。
史诗《玛纳斯》表演从最老一辈的玛纳斯奇们在演唱表演《玛纳斯》的时候中单一简单小幅度的肢体动作演变到年轻一代的玛纳斯奇们加入自己的感觉以及用大幅度的肢体动作以及夸张的面部表情来表现史诗《玛纳斯》中的内容,使史诗《玛纳斯》的表演更加的饱满。在又将生活中的《玛纳斯》表演相继搬到银幕以及舞台上,用更加专业的要求以及态度来表演《玛纳斯》使我们的史诗《玛纳斯》又上了一层楼,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了解史诗《玛纳斯》,让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的学者关注去研究钻研,传承以及发展。
四、史诗听众
史诗歌手与听众是《玛纳斯》口头传承的两端,它们彼此积极互动为《玛纳斯》口头传统生长和发展提供土壤。《玛纳斯》口头传统的兴衰,听众显得尤为重要,史诗歌手与听众构成和谐的表演体系。紧张劳动一年的柯尔克孜牧民,在听史诗演唱时,思想得以放松,他们听歌手演唱《玛纳斯》,受到教育、鼓舞,情操受到陶冶。而参加这一活动本身,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艺术享受。在看到对史诗歌手的访谈中提到,如果谈到有关“演唱《玛纳斯》不如从前兴盛了”的话题,问及原因,“听众少了”几乎是每个歌手首先提及的。哈拉布拉克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工作、求学,即使在家的人也赶时髦,不愿听老人唱《玛纳斯》,加上老一代史诗歌手逐渐离去,尤其是电视普及人们唱听《玛纳斯》的就更少了。
在歌手与听众互为依存的这一结构中,听众是口承史诗的 “灵魂”。听众使史诗得到生命。吉尔吉斯斯坦20世纪40年代的功勋史诗演唱大师卡拉拉耶夫曾被邀请到电台演唱 《玛纳斯》,他对着麦克风不知所措,怎么也演唱不出来。后来电台请来了听众,面对听众,他才开口演唱起来。在看到相关田野调查报告中,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多位曾辉煌一时的有名歌手,在采访他们时,他们竟演唱不出来了,成为“失忆的歌手”。
听众是口传史诗传承的灵魂,没有听众,歌手唱给谁听呢?有位深山里的史诗歌手痛心地说:“我的子女们,看电视,我在家演唱 《玛纳斯》,连我的孩子们都不听,我就不再演唱了,时间一长,史诗也不会唱了”。有许多乡镇,有20多年没有举行过 《玛纳斯》演唱会,没有听众,就没有演唱语境,造成歌手长期不演唱史诗,这是导致歌手 “失忆”的根本原因。歌手演唱史诗时,没有听众,歌手便会停止演唱活动。歌手不唱了,史诗也会失传。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听众是史诗传承的动力,听众赋予史诗以生命。
以上,从语境理论出发,分别从史诗背景、演唱时空、史诗传承人、史诗听众等方面对史诗《玛纳斯》的口头传承的影响做了阐释。但愿在语境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口头史诗能更好的得到传承与保护。
参考文献
[1]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M]人民族出版社 2006.
[2] 薛剑莉.口传史诗《玛纳斯》的活态传承[J].文学评论 2013.
[3] 郎樱.《听众在史诗传承中的地位与作用》[J].史诗研究1998
[4] 秀梅.《从柯尔克孜宗教信仰谈其民族文化变迁》[J].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所 2007
[5] 胡振华.《伊斯兰教与柯爾克孜文化》[J].西北民族研究.2002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