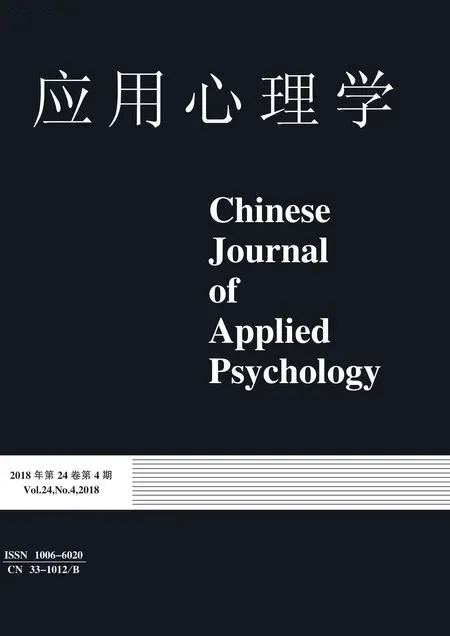旅居与杂居藏汉双文化个体认知差异的研究
,2
(1.中山大学哲学系;2.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275)
1 引 言
文化心理学领域关于文化互动的实证研究中常常选取双文化个体来研究文化适应、不同文化知识网络的表征与使用等问题。一般认为,双文化个体(bicultural individuals)指同时将自我归属于两种文化族群的双语个体(Benet-Martínez,Leu,Lee,& Morris,2002;Nguyen & Benet-Martínez,2007;Ringberg,Luna,Reihlen,& Peracchio,2010)。而这些研究中涉及的双文化个体通常是旅居者、移民或移民后代(Benet-Martínez等,2002;Huynh,Nguyen,& Benet-Martínez,2011;No,Hong,Liao,Lee,Wood,& Chao,2008)。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前述研究中主要涉及的移民国家不同,不同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互动有多种形式:不限于个体从母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生活环境到第二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生活环境(如:个体从少数民族聚居地到汉族聚居地学习、工作),还包括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群体在特定区域长期共同生活的情形(如:多民族杂居地)。上述两种跨文化互动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双文化个体:旅居双文化个体和杂居双文化个体。他们所形成的社会背景存在一个主要差异:旅居双文化个体的母文化和第二文化在其所在社会情景中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杂居双文化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中两者常常并无明显的主次之分。两种不同的形成背景,是否会形成两种具有不同认知特点的双文化个体?已有的少量研究表明这两种双文化个体在民族和双文化整合上可能存在差异。高承海和万明钢(2013)发现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个体的民族本质论水平显著高于散居少数民族个体。杨晓莉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聚居与杂居地区的藏族双文化个体在双文化整合与心理适应性的相关性上有所差异。但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直接比较这两类双文化个体,因此,目前尚缺乏严格且系统的对比。
此外,以往关于双文化个体的跨文化互动的研究常常认为双文化个体内化了两种文化构念网络(networks of cultural constructs),他们能根据不同的文化情景线索切换使用相应的文化构念网络,即:文化框架转换(cultural frame switching,如:Cheng,Lee,& Benet-Martinez,2006;Hong,Morris,Chiu,& Benet-Martínez,2000;Ross,Xun,& Wilson,2002;Wong & Hong,2005)。比如:一个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在美国文化线索下(比如:在美国的课堂上)表现出典型的美式思维与行为模式,而在中国文化线索下(比如:在和中国学生的聚会中)又表现出典型的中国模式。这些研究中的双文化个体多为上述的旅居双文化个体:由于学习或工作原因旅居到其母文化是少数文化、第二文化是主流文化的文化环境。而在我国的一些多民族杂居地,两个或更多民族长期共同生活的背景下,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甚至多向的,这些双文化个体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是否还会出现文化框架转换的模式呢?
因此,本文拟探究旅居和杂居两类双文化个体在文化和民族认知、跨文化互动过程中(文化框架转换)的差异及其差异背后的心理机制。在我们的研究中,旅居双文化个体采用的是生长于藏族聚居地、在汉族聚居地长时间生活的藏族个体,以及生长于汉族聚居地、在藏族聚居地长期生活的汉族个体;而杂居双文化个体来自我国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拉卜楞地区。夏河县拥有藏、汉、回、撒拉、蒙古、朝鲜、土等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其中藏族、汉族和回族是拉卜楞地区的主体民族,藏、汉、回三个族群间的互动是拉卜楞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
2 研究一:双文化个体的文化和民族认知差异
研究一的目的是以单文化个体为参照,考察旅居和杂居两类双文化个体在文化与民族认知上的差异。其中文化与民族认知用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和常人民族观量表分别测量。
2.1 研究对象
被试按照双文化个体类型与民族选取,3(类型:旅居双文化个体、杂居双文化个体、单文化个体)×2(民族:藏族、汉族)共六类被试,选取标准为:①旅居双文化个体,选取生长于藏族聚居地或藏汉杂居地、自我评价汉语水平为3~5分(Likert 5点计分)、在汉族聚居地生活3年或以上的藏族,以及生长于汉族聚居地或藏汉杂居地、自我评价藏语水平为3~5分、在藏族聚居地生活3年或以上的汉族为被试。②杂居双文化个体,选取一直生活在藏汉杂居地、自我评价第二语言水平为3~5分的藏族和汉族为被试。③单文化个体,选取生长于藏族聚居地、自我评价不会汉语、未曾在汉族聚居地长期生活的藏族,以及生长于汉族聚居地、自我评价不会藏语、未曾在藏族聚居地长期生活的汉族为被试。
研究一的总被试人数为468人,旅居双文化藏族被试主要来自拉萨、海南和林芝,旅居双文化汉族被试主要来自岳阳、长沙、成都、北京,杂居双文化被试主要来自夏河县,单文化藏族被试主要来自日喀则、色达和扎尕那,单文化汉族被试主要来自重庆、成都、广州、阳春和长沙。详细被试情况见表1。

表1 研究一被试的详细人口学描述
2.2 研究方法
2.2.1 常人民族观量表:民族本质论
No等人(2008)编制的常人民族观量表(The Lay Theory of Race Scale,LTRS),用于测量常人民族观(lay theory of race)。常人种族观,指人们对种族的常识性观点,即个体用以理解和解释关于种族问题的内隐知识,包括以下两种(No等,2008):本质主义观(essentialist theory of race),指个体认为种族赋予个体天生的、不可改变的特性,这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特征;社会建构主义观(social constructionist theory of race),指个体认为种族是社会建构的、动态性的,在不同社会情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使用常人民族观量表旨在探究藏汉两个民族在民族本质论水平上的差异,明晰旅居双文化个体和杂居双文化个体在这方面的差异。
常人民族观量表有8个项目,包含4个民族本质论的项目(如“一个人属于哪一民族,对他/她来说是非常基本的事情,它几乎不能被改变”)和4个社会建构论的项目(如“民族只是一些随意的分类,有必要的话可以更改”),使用Likert 6点计分。其中社会建构论的项目反向计分,最后加总为民族本质论分数。量表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民族本质论水平越高。修订后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为:χ2/df=1.48,GFI=0.95,NFI=0.91,IFI=0.97,CFI=0.97,RMSEA=0.06,因子负荷为0.53~0.86;分量表Cronbach’s的α系数为0.73和0.80,总量表为0.68,其中,藏语量表为0.60,汉语量表为0.73。
2.2.2 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
双文化认同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是双文化个体如何管理其双文化经验的主观知觉。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cale)分为两个维度:文化分离-混合分量表(Cultural Distance-Blend)、文化冲突-和谐(Cultural Conflict-Harmony)分量表(Benet-Martínez等,2002;Benet-Martinez & Haritatos,2005)。使用该量表旨在探究旅居双文化个体与杂居双文化个体在双文化整合水平上是否有差异。
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有8个项目,包含4个文化混合-分离维度的项目(如“我保持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相互分离”)和4个文化和谐-冲突维度的项目(如“我感觉汉族和藏族在为人处世的方式上是冲突的”),使用Likert 6点计分。修订后双因素验证式因子分析结果:χ2/df=1.96,GFI=0.96,NFI=0.93,IFI=0.96,CFI=0.96,RMSEA=0.07,因子负荷为0.5~0.83;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4和0.83,总量表为0.74,其中,藏语量表为0.70,汉语量表为0.78。
2.2.3 施测方式
量表均采用匿名纸笔测验的形式,部分无书面语言能力的被试使用访谈的方式完成测试。在所有的被试中,藏族被试使用藏语的材料,汉族被试使用汉语的材料。旅居双文化个体、杂居双文化个体和单文化个体三类被试均完成常人民族观量表,两类双文化个体的被试再完成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
2.3 数据分析
2.3.1 常人民族观
以双文化个体类型、民族为自变量,以常人民族观量表总分为因变量作方差分析。结果显示:①民族的主效应显著(F(1,462)=246.40,p<0.001,η2=0.35),藏族被试的民族本质论水平(M=5.25,SD=0.47)显著高于汉族被试(M=4.38,SD=0.80)。②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F(2,462)=2.67,p=0.07)。③被试类型与民族的交互作用(F(2,462)=24.41,p<0.001,η2=0.10)显著。进一步分别对两个民族使用成对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显示,在藏族被试中,三种被试类型之间两两差异显著,单文化被试的民族本质论水平最高(M=5.63,SD=0.29),旅居双文化被试次之(M=5.25,SD=0.38),杂居双文化被试最低(M=5.00,SD=0.48);在汉族被试中,单文化被试的民族本质论水平(M=4.14,SD=0.91)显著低于旅居双文化被试(M=4.50,SD=0.64)和杂居双文化被试(M=4.49,SD=0.78),而旅居双文化被试与杂居双文化被试之间无显著差异在藏族被试中,单文化与旅居双文化Z=5.14,p<0.001;旅居双文化与杂居双文化Z=3.21,p<0.01;杂居双文化与单文化(Z=8.37,p<0.001)。在汉族被试中,单文化与旅居双文化Z=2.52,p<0.05;单文化与杂居双文化Z=2.75,p<0.05;旅居双文化与杂居双文化(Z=0.12,p>0.05)。。
2.3.2 双文化认同整合
以双文化个体类型、民族为自变量,以两个分量表和量表总分为因变量,作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在文化混合-分离分量表中,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323)=19.98,p<0.001,η2=0.06),旅居双文化被试的文化混合水平(M=2.70,SD=0.93)显著低于杂居双文化被试(M=3.18,SD=1.03);民族的主效应显著(F(1,323)=5.94,p<0.05,η2=0.02),藏族被试的文化混合水平(M=2.83,SD=0.97)显著低于汉族被试(M=3.10,SD=1.04);二者交互作用不显著(F(1,323)=0.15,p=0.70)。
在文化和谐-冲突分量表得分中,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323)=31.46,p<0.001,η2=0.09),旅居双文化被试的文化和谐水平(M=2.56,SD=1.01)显著低于杂居双文化被试(M=3.19,SD=1.00);民族的主效应(F(1,323)=0.01,p=0.94)、二者交互作用(F(1,323)=0.55,p=0.46)均不显著。
在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总分中,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323)=45.73,p<0.001,η2=0.12),旅居双文化被试的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M=2.63,SD=0.72)显著低于杂居双文化(M=3.18,SD=0.76);民族的主效应(F(1,323)=2.43,p=0.12)、二者交互作用(F(1,323)=0.58,p=0.45)均不显著。
2.4 结果与讨论
研究一的结果表明:首先,藏族和汉族在常人民族观上表现了显著的民族间差异,藏族普遍持有比汉族更强烈的民族本质论。汉族的双文化被试的民族本质论水平均显著高于单文化被试,这一趋势与藏族被试相反。这可能表明两个民族受到第二文化经验的影响有所不同,藏族人群的族际边界知觉相对地降低,而汉族人群产生较高的族际边界知觉。同时,研究结果显示了藏族的旅居比杂居双文化个体具有更高的民族本质论水平,而汉族的两种双文化个体之间无显著差异。
其次,在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中,两个分量表和总量表得分中均表现为旅居双文化个体得分显著低于杂居双文化个体。可能表明旅居和杂居双文化两种个体之间在对待第二文化经验组织的感受性上不同:旅居双文化个体对于第二文化经验持有较高分离度和冲突性认知,具有较低的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而杂居双文化个体对于第二文化经验持有较低分离度和冲突性认知,具有较高的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
3 研究二:双文化个体文化框架转换效应差异
研究二的目的是初步探索旅居双文化个体与杂居双文化个体在不同文化线索启动下的文化框架转换效应的差异。
3.1 研究对象
研究二的双文化被试筛选标准与研究一一致。研究二的被试总人数为381人,其中旅居双文化藏族被试主要来自拉萨、海南、日喀则和林芝,旅居双文化汉族被试主要来自长沙、成都、北京、贵阳,杂居双文化被试主要来自夏河县。被试情况见表2。

表2 研究二被试的详细人口学描述
3.2 研究方法
与以往的研究一致,我们采用归因任务来考察文化框架转换效应(如:Benet-Martínez等,2002;Cheng等,2006;Hong等,2000)。已有的研究表明,在归因任务上存在文化差异,中国被试倾向于外部归因,美国被试倾向于内部归因。由于缺乏现有研究考察藏汉在归因任务上的差异,我们在预备测验中考察了藏汉文化的一般归因特征差异。预实验被试总人数为468人(藏族占比49.1%),给被试呈现一个静态的图片,图片上有一前一后的一条鱼和一群鱼,请被试观察1分钟后用12点评分表明,为什么那条鱼游在那群鱼前面:1表示“非常确信,因为这条鱼在带领其他鱼”(内部归因);12表示“非常确信,因为这条鱼在被其他鱼追赶”(外部归因)。结果表明,藏族被试(M=4.15,SD=3.21)在外部归因上的得分显著低于汉族被试(M=5.23,SD=3.51)(F(1,466)=12.01,p<0.01,η2=0.03)。因此,藏汉文化的一般归因特征的显著差异使该任务能够检测个体在跨文化交流中是否出现文化框架转换:如果原本倾向于内部归因的藏族个体在汉族文化线索启动后出现外部归因倾向,或原本倾向于外部归因的汉族个体在藏族文化线索启动后出现内部归因倾向,则可视为出现了文化框架转换效应;如果没有出现归因倾向的变化,则可视为未出现文化框架转换效应。
采用文化启动的实验范式,将2(双文化个体类型:旅居双文化、杂居双文化)×2(民族:藏族、汉族)四类被试随机分配到3个文化启动条件(藏族文化启动、汉族文化启动、中性启动)下。文化启动采用经过预先评估的具有相应文化寓意的清晰图片;中性启动图片则为不带有文化色彩的乌云图片。施测过程中,首先给被试呈现5张文化启动图片,并请被试描述每张图片内容并用三个词语形容,且回答一些与图片相关的问题,如:“这种活动一般在什么时候?”然后,请被试看一个GIF格式的动态图片,图片显示的是一条鱼在一群鱼前面,从画面的右边游到左边。请被试用10点评分给出那条鱼游在其他鱼前面的原因:1表示“非常确信,因为这条鱼在带领其他鱼”(内部归因);10表示“非常确信,因为这条鱼在被其他鱼追赶”(外部归因)。
3.3 数据分析
以启动条件为固定变量,文化背景、民族为随机变量,以归因分数为因变量进行一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启动条件(F(2,2.22)=3.38,p=0.21)、双文化个体类型(F(1,1.50)=0.02,p=0.97)、民族(F(1,1.03)=1.83,p=0.40)的主效应、启动条件与民族(F(2,2)=2.36,p=0.30)三者的交互作用(F(2,369)=0.04,p=0.96)均不显著,但启动条件与双文化个体类型(F(2,2)=22.85,p<0.05,η2=0.96)、双文化个体类型与民族(F(1,2)=89.96,p<0.01,η2=0.98)的交互作用显著。
启动条件与双文化个体类型交互作用的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旅居双文化被试在三种启动条件间差异显著(F(2,177)=3.18,p<0.05,η2=0.04),杂居双文化被试在三种启动条件间差异不显著(F(2,198)=0.37,p=0.69)。多重比较结果表明,在旅居双文化被试中,藏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启动条件差异显著(MD=-1.08,SE=0.43,p<0.05),藏族文化与中性控制启动条件(MD=-0.65,SE=0.43,p=0.21)、中性控制与汉族文化启动条件(MD=-0.43,SE=0.43,p=0.21)的差异均不显著。结果如图1所示。
被试类型与民族交互作用的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旅居双文化被试在民族间差异显著(F(1,178)=8.54,p<0.01,η2=0.05);杂居双文化被试在民族间差异不显著(F(1,199)=0.24,p=0.63)。

图1 旅居双文化和杂居双文化个体在三种启动条件下的归因得分
3.4 结果与讨论
研究二的结果表明,对于旅居双文化个体,其结果与以往研究(如:Hong等,2000)一致:双文化个体可以同时具有两种文化构念网络,并在不同文化线索下出现文化框架转换效应。而对于杂居双文化个体,却没有出现文化框架转换效应。这一结果可能意味着两种双文化个体对于跨文化交流有着不同的应对方式。正如前文所提到,对于长期处于主流文化为第二文化、母文化处于非主流地位的环境中的旅居双文化个体而言,融入社会的较好方式可能是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切换相应的文化观念及其所引导的行为;而对于长期处于多种文化间地位较为平等环境的杂居双文化个体而言则未必如此,他们应当具有与旅居双文化个体不同的跨文化交流方式。
4 总讨论
4.1 区分两种双文化个体的必要性
本文将藏族和汉族个体作为研究对象,针对旅居双文化个体和杂居双文化个体的认知特点差异作出的初步探索结果,支持了区分两种双文化个体的观点。
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尤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2)后,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特殊社会背景形成的双文化个体已经越来越少,其主体更多为移民、难民等旅居因素形成的双文化个体,这也是关于双文化个体已有研究的对象多为旅居者的原因。另一方面,不同文化中具有本土性特征的部分将受到更多的保护得以保留,关于多个不同文化族群长期在特定地域共同居住所形成的杂居双文化个体的研究将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正是在我国由来已久的“大杂居、小聚居”多民族格局中所应当重视的跨文化交流研究范畴。不加区分地对杂居双文化个体套用旅居双文化个体研究结果,将局限针对我国特殊国情的多民族跨文化交流研究的进展,不利于完善针对双文化个体的相关研究。
4.2 形成两种双文化个体差异的原因
双文化个体(包括旅居双文化个体和杂居文化个体)在跨文化情景中怎样交流,可能是由其文化背景特征所决定:文化背景特征决定了个体所持有的两种文化构念网络之间的冲突程度;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特征如何,个体就会如何进行跨文化交流。
对于旅居双文化个体而言,在其社会生活环境中,原文化处于非主流文化的地位,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不对等,使非主流文化个体自身成为保证跨文化交流有序进行的主体;在大部分人共享的是其第二文化,并且其原文化与第二文化在社会互动和身份认同等方面重叠性较高的情况下,旅居双文化个体为了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将动用更多的认知资源,因而容易出现文化适应困难或认知调整失败。而对于杂居双文化个体而言,其原文化与其他文化在社会生活环境中地位大致相当,各个族群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关系较为对等,因而采用不同于旅居双文化个体的跨文化交流模式,其文化和民族认知特点也与旅居双文化个体有较大差异。
4.3 未来研究展望
我们认为,在后续的研究中对于造成两种双文化个体差异的深层原因,如文化背景特征、跨文化交流模式等方面均有待进一步研究。除了各个族群在跨文化交流中的关系是否对等这一较为笼统的文化背景特征,还应从其他方面的具体情况来衡量文化背景特征。因为长期共同居住不意味着族群间必然和谐共处。除了不同文化之间本身的冲突(包括各自特有的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情感方面特点的差异,在文学、艺术、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体系、习俗传统和信仰等方面的冲突),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均影响着族群关系。在本研究中,特定两种文化的限定、杂居地区较为和谐融洽的文化气氛等因素,都决定了本研究的结果不一定能推广到其他文化条件。这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可以为跨文化交流研究提供更丰富的素材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