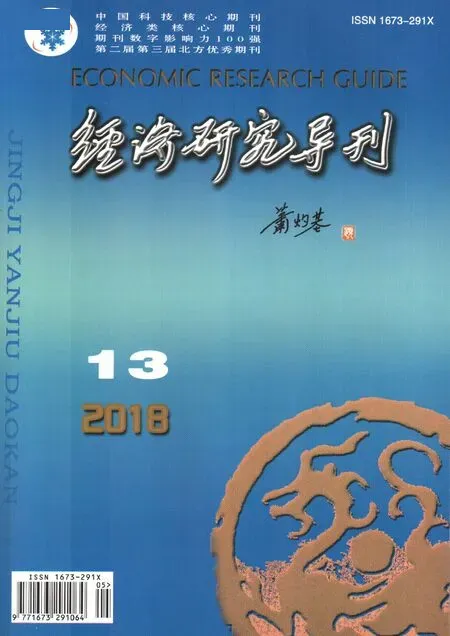见义勇为的价值悖论和政府责任的一些思考
——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关联视角
王祚远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4)
一、见义勇为是否属于刑法评价的问题
针对当前学界不断提出的应将“见危不救”上升为犯罪,在我国刑法中设立见危不救罪的提议。本文认为,其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即我国社会传统观念和古代法律中往往将“见义不为”与“见危不救”两者混为一谈,前者的范围包括了后者。本文认为,这里存在混淆道德与法律的界限问题,必须厘清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的概念,把见义不为当作刑法领域的问题而探讨的错误,其根源就在于混淆了这两者。
见义勇为是指,不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公民,为维护国家、集体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挺身救助的行为。这里的“勇”所必需的前提是对自己如果救助就有会对自己产生巨大危险的危险存在。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义”,这里的“义”绝不是“义务”的意思,否则,“见义勇为”就被理解成是特定的职务行为。这里的“义”是指“正义”,在普通的社会生活观念来看,通俗的理解是“绿林好汉式”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完全是一种朴素的英雄情结。而对于这种英雄式的救助,我们在道德情感上是完全支持的,如果这种救助没有超过相当的范围,我们是不能用刑法来考察的,因为首先刑法评价的是犯罪行为。再者,刑法的评价手段是一种“负面的评价”,往往表现为刑罚的方法。而“见义勇为”是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相反它具有的是“社会有益”性。因此,我们要考虑是如何奖励的问题,而不是惩罚。可见,见义勇为行为因为缺乏违法性而不被进入刑法考察领域。应该说,见义勇为首先是道德管辖范围,其次在见义勇为人的损害赔偿方面,一般把它归属于民法的无因管理。因此,见义勇为不是刑法上的问题。只有从见义勇为行为发动的原因来看,例如,因为人的侵害,见义勇为才和刑法有联系,但这已不是见义勇为本身所讨论的范围了。
而应该上升为刑法范围的是“见危不救”,国外刑法中的“见危不救”是指:“不负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对处于有生命危险状态中而急需给予救助的人,自己能够救助且明知给予救助对自己或他人无危险,而竟不予救助的行为。”[1]例如,《法国刑法典》第223-6条第2款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够唤起救助行为,且对本人或第三人无显著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五年监禁并科五十万法郎的罚金[2]。1980年美国《帮助临险者责任法》规定:当人们知道他人面临严重的人身危险时,而且没有相同地位的人可帮助而不具危险,或没有特定义务人对此负责,此时应给予帮助,除非已有别人给予帮助或关心,否则,处以100美元以下罚款[3]。《德国刑法典》第330条C规定:“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急难之际,有救助之必要,依当时情况又有可能,尤其对其本人并无显著危险且不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救助者,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并科罚金。”见危不救与见义勇为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是否面临一个因自己的救助行为而能够对自己产生危险的“危险源”,这个“危险源”存在,使得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分属两个不同的考察领域。笔者认为,应该上升为犯罪,用刑法来匡正的,是见危不救行为,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如果混淆了见义勇为和见危不救,就会产生将见义勇为当作是刑法评价问题的错误。
二、见义勇为的价值悖论
见义勇为行为的价值悖论表现在道德领域的正面评价和功利角度的不必要性、浪费性之间的冲突。
“成人之美,与人为善”作为我国社会公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一个人应当与人方便,切勿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或见死不救。”[4]而见义勇为恰恰是符合了社会主义公德的要求,见义勇为人特别是在见义勇为人因为见义勇为行为受伤害之后,往往受到“社会英雄”般的对待。应该说,见义勇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历来崇尚“英雄”情结的社会来说,出现是必然的。因为,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利他主义”。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家也主张:“品行是:所干的事不图个人名利;所干的事为个人名利,便是巧诈,犹如为盗。”[5]在这种氛围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自然是鼓励见义勇为的。我国古代关于见危不救的立法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在其中《法律问答》里,就记载了对见义不为的惩罚措施。其中规定:“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唐律疏议》卷27中有:“见火起,烧公私廨宇、舍宅、财物者,并须告见在邻近之人共救。若不告不救。减失火罪二等,合徒一年。”《宋刑统》卷28,见危不救的法律条款与唐代相同。《大清律例》卷24中规定:“强盗行劫,邻佑知而不协拿者,杖八十。”应该说,在上述道德氛围中出现这样的立法是必然发展的结果。
但是,从功利主义角度看,提倡和鼓励见义勇为是成问题的。首先,从法益平衡的角度看,见义勇为的情况不能排除这四种结果。一是被救者与救助者两受其害,二是被救者因救助行为反受更大侵害,三是被救助者利益获得挽救,救助者利益受损,四是救助行为未产生任何救助效果,属无用功。从这四种情况来看,见义勇为行为的“经济效益”可以说为零或是负值。因此,从法益的平衡角度看,见义勇为从总体上是无益的。其次,在一些救助案例中,救助人反受重大伤害,造成终身残疾。如果不对其进行终身治疗,那么将会造成新的道德的“恶”。但是,如果要进行终身治疗的话,这留给其本人和社会的将是巨大的财产负担。最后,如果在将见危不救行为上升为犯罪,用刑法来匡正的话,那么受见危不救和正当防卫及紧急避险的压缩,留给见义勇为的空间将更小,见义勇为在功利主义角度存在的必要将微乎其微。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的注意力应放在如何将见危不救上升为犯罪,而不是在刑法领域讨论见义勇为的问题。见义勇为确是道德上应该肯定的举动,但是基于理性和更大的怜悯,我们不应当主张提倡见义勇为。但是,如果出现了见义勇为,并且见义勇为人因见义勇为行为而使其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政府是否应该承担责任以及这种责任应如何承担。这是笔者的第三个问题。
三、对见义勇为政府责任的一些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知,笔者不赞同一般人的见义勇为。但是,如果见义勇为成既成事实并且见义勇为人在救助过程中受到重大损失的话,那么政府将承担什么责任以及这种责任承担的理由是什么?笔者认为,从见义勇为发生的情况看,有两种,一是人的原因,包括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一般的违法和民事侵权行为和被救助者自身所导致的行为;二是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等。在第一种情况下,首先应由危险肇事者承担责任,在危险源是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应由犯罪人承担见义勇为人的损害赔偿,在一般的违法和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危险来源下,应由一般的违法和民事侵权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然后由被救助人按民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在由于被救助者自身所导致的危险源的情况下,应该由被救助者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在人的危险情况下,如果犯罪人或侵权人或被救助人没有能力赔偿以及上述由于自然原因导致的见义勇为。这两种情况,政府是否要承担责任呢?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必须承担责任的,因为,见义勇为行为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道德上的美德,如果见义勇为行为人得不到最基本的救助,那么是对这个社会造成更大的恶,对人们的善良情感将会造成再次打击。笔者认为,政府的责任应该采用以下承担方式,主要有:设立各级“政府见义勇为基金会”,尽量将见义勇为者纳入革命烈士优抚范围,将一些家庭贫困的见义勇为者纳入政府社会低保范围,在指定的公立医院内减免见义勇为者的医疗费用,由见义勇为人所在的基层公安机关承担见义勇为人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保护,免受报复等等。
另外,政府应该积极和社会救助之间达成默契,形成相互促进和相互间多沟通的局面。从上述第二部分可知,笔者的观点是不赞同政府倡导见义勇为的,因此,这种责任应尽量让社会来承担。政府的救助责任,只有在其他手段用尽仍不能补偿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而受的损失时才能启动。只有一个例外,即对见义勇为人和其家人的人身安全免遭报复这一点,政府应该承担积极的责任。
参考文献:
[1]汪力,邹兵.关于“见危不救”的法理学和刑法学思考[J].刑事法学,2002,(3).
[2][德]冈特·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库伦.刑法总论I——犯罪论[M].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87.
[3][美]道格拉斯·N.胡萨克.刑法哲学[M].谢望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267.
[4]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365-367.
[5]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