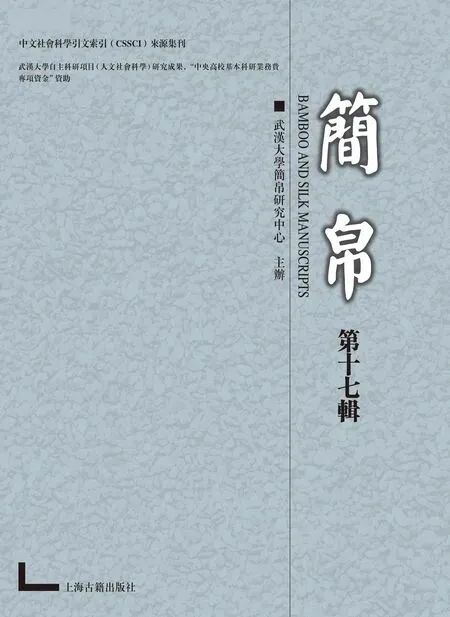秦漢“鞫”文書譾識
——以湖南益陽兔子山、長沙五一廣場出土木牘爲中心* *
徐世虹
關鍵詞: 鞫 程序 文書
秦漢訴訟制度、司法程序歷來是秦漢法制史研究的重點所在,尤其是近年來得益於出土文獻的增加,産生了不少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程序的實現必有賴於文書,文書是程序、制度的載體,因而近來有學者開始關注官文書視野下的秦漢訴訟制度研究。(1)如鷹取祐司的《秦漢官文書の基礎研究》(汲古書院2015年)以近一半的篇幅展開了對斷獄、聽訟文書的研究;劉欣寧的《秦漢獄訟中的言辭與書面證據》(李宗焜主編: 《古文字與古代史》,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措意於程序實現的方式,將視綫投向程序+文書的領域。由此也令人思考,今天我們所説的“司法文書”在秦漢審判制度的各個環節中是如何存在並運行的,這些文書具有怎樣的名稱、定義與類别。立足于此,秦漢時期“文書政治”的内涵應可獲得更充分的揭示。
2013年12月6日的《中國文物報》披露了出自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J3的兩方木牘,木牘記録了漢平帝元始二年(2)對張勳主守盜一案的審判結果;2015年出版的《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刊載的編號爲144的木牘,記録了漢安帝永初三年(108)對張雄等五人不承用詔書案的審判結果。兩方木牘皆以“鞫”字爲首,張勳案木牘還以單面大字書寫“鞫”,由此令人對秦漢時期的“鞫”産生了進一步探求的興趣。
一、 兩件文書的釋文
張勳案的兩方木牘釋文如下:
J3⑤∶1:
鞫(正面)
鞫: 勳,不更。坐爲守令史署金曹,八月丙申爲縣輸元年池加錢萬三千臨湘,勳匿不輸,即盜以自給。勳主守縣官錢,臧二百五十
以上。守令史恭劾,無長吏使者,審。
元始二年十二月辛酉,益陽守長豐、守丞臨湘、右尉顧兼、掾勃、守獄史勝言: 數罪以重,爵減,髡鉗勳爲城旦,衣服如法,駕責如所主守盜,没入臧縣官,令及
同居會計,備償少内,收入司空作。
(背面)
J3⑤∶2:
益陽言守令史張勳
盜所主守加錢論決言相府
(第一欄)
元始二年
計後獄夷(第)一
(第二欄)(2)原釋文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十年風雲激蕩 兩千年沉寂後顯真容》,《中國文物報》2013年12月6日,第6版;周西璧: 《洞庭湖濱兔子山遺址考古 古井中發現的益陽》,《大衆考古》2014年第6期,第33頁。小文《新見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元始二年張勳主守盜案牘文疏解》(“中國古代法律文獻前沿論壇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2015年。後更名爲《西漢末期刑罚一瞥——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元始二年張勳主守盜案牘文疏解》,“東亞的犯罪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日本學術振興會國際合作項目2016年)對釋文有所改動。2017年12月本文提交後,次年5月承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張忠煒副教授提示,讀到張春龍《益陽兔子山遺址三號井“爰書”簡牘一組》一文[收入]何駑主編《李下蹊華——慶祝李伯謙先生八十華誕論文集》(下),科學出版社2017年〗。徵引遺珠,有所不安。今據該文釋文,將“守令史劾”改爲“守令史恭劾”,“親(辛)酉”改爲“辛酉”,“守丞臨湘右尉□、兼掾勃”改爲“守丞臨湘、右尉顧兼、掾勃”。“守丞臨湘”之“臨湘”,張春龍認爲是人名,又以另簡“益陽丞臨湘”可證,“臨”是“顧”字之誤。(參見張春龍: 《益陽兔子山遺址三號井“爰書”一組》第861頁)
關於牘文的疏解及相關制度的探討,筆者已成《西漢末期刑罰一瞥》及《“爵減”獻疑》二文,(3)《西漢末期刑罰一瞥》見前注。《“爵減”獻疑》,“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2017年。此不贅述。
張雄等五人案的木牘釋文如下:
A面:
鞫: 雄、俊、循、竟、趙,大男,皆坐: 雄,賊曹掾;俊、循,史;竟,驂駕;趙,驛曹史。驛卒李崇當爲屈甫證。二年十二月廿一日,被府都部書,逐召崇,不
得。雄、俊、循、竟、趙典主者掾史,知崇當爲甫要證,被書召崇,皆不以徵遝(逮)爲意,不承用詔書。發覺得。直符户曹史盛劾,辭
如劾。案: 辟都、南、中鄉,未言。雄、俊、循、竟、趙辭皆有名數,爵公士以上。癸酉赦令後以來,無它犯坐罪耐以上,不當請。
永初三年正月十四日乙巳,臨湘令丹、守丞晧、掾商、獄助史護以劾,律爵咸(減),論雄、俊、循、竟、趙耐爲司寇,衣服如法,司空作,計其年。
(正面)
(一四四 木牘 CWJ1③∶201-1A)
B面:
得平。
(一四四 木牘 CWJ1③∶201-1B)(4)釋文據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中西書局2015年,第220—221頁。引用時標點有改動。
學者已對此牘做了很好的解讀,(5)楊小亮: 《略論東漢“直符”及其舉劾犯罪的司法流程》,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9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176—186頁。釋文本身或無更多剩義,不過仍有一二處可再酌。
其一,“皆坐”,釋文作“皆坐。”。或可下讀,即“雄,賊曹掾……不承用詔書”是“坐”的内容。《史記》、兩《漢書》在陳述罪狀時,一般表達是“坐某某罪”。所坐之罪名,有較簡短者,如《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元朔二年,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罪,國除”;也有較長者,如《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元封六年,坐爲太常行大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爲城旦”。這些短長之異自然與罪狀相關,但也不排除史家在撰寫時對材料的取捨。如桓帝延熹五年(162)發生的南郡太守李肅奔北案,《後漢書·桓帝紀》作“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而《天文志下》作“南郡太守李肅坐蠻夷賊攻盜郡縣,取財物一億以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敵走,不救城郭。又監黎陽謁者燕喬坐贓,重泉令彭良殺無辜,皆棄市”。“奔北”是罪名,是對“蠻夷賊攻盜郡縣……不救城郭”這一罪狀的概括。《天文志》所見,對罪狀的表述更爲具體。另以張勳案木牘行文,所“坐”之罪是“即盜以自給”。因此按“坐某某罪”的結構,“坐”可與下連讀,或將句號改爲冒號。
其二,關於“以劾律爵減論”,“以劾”可上讀,“論”亦可下讀。全句讀“臨湘令丹……獄助史護以劾,律爵減,論雄、俊、循、竟、趙耐爲司寇”。臨湘令丹等四人是該案的審理者,依據《具律》規定,“治獄者,各以其告劾治之”,“……毋告劾而擅覆治之,皆以鞫獄故不直論”,因此“以劾”説明的是丹等人立案治理的依據。“律爵減”,文面意思是“按照法律規定以爵減罪”。論某某刑,秦漢文獻不乏見,如《漢書·公孫弘傳》“詔征钜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爲城旦”,《漢書·劉輔傳》“上乃徙系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後漢書·段熲傳》“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論”上讀也不害文意,不過考慮到“爵減”只是“論”需要考慮的要件之一,“耐爲司寇”是“論”的最終結果,此處還是作下讀。
二、 “鞫”的程序意義與指代意義

從此義項出發,《封診式》6~7簡“有鞫”中的“遣識者以律封守”,應是指當事人處於案件的調查過程時,要被執行“封守”的程序,這一程序即8簡所記載的“鄉某爰書: 以某縣丞某書,封有鞫者某里士五(伍)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産”。對尚處於案件調查、審訊之中的“有鞫者”進行“封守”,應是爲判決後一旦需要執行“收”而採用的保全措施。因此這裏的鞫處於“案驗之後,判決之前的訴訟階段”,(10)于洪濤: 《秦漢法律簡牘中的“鞫”研究》第81頁。以“認定事實”解釋並無障礙。里耶秦簡8-488“户曹計録”中的“鞫計”之“鞫”,恐怕也應循此思路理解,將其解釋爲“目前有訴訟在身者的統計文書”或“對其封守的統計文書”。
然而“認定事實”的程序之義,並不是鞫唯一、排他的義項。論者在判斷《龍崗秦簡》木牘所載辟死文書的性質時,指出“秦漢之時,鞫往往就帶有一層論的意思”,“木牘性質屬法庭判決書之類的公文”,(11)劉國勝: 《雲夢龍崗簡牘考釋補正及其相關問題的探討(摘要)》,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龍崗秦簡》,中華書局2001年,第162、166頁。已經實際指出了鞫的指代意義。陶安則以廣狹之義區分鞫的用法,指出: 鞫除去論斷者的訊問這一狹義之用外,還有廣義之用。即在絶對的定刑主義下,具有論斷權限者通過訊問而認定的犯罪事實,已被機械地確定了法定刑,排除了變更量刑的餘地,因此“鞫”這一訊問便成爲斷獄程序的核心,在廣義上包含了加以訊問的論斷,有時也指由論斷者做出的整體裁定。如《二年律令·具律》93簡中的“鞫獄故縱、不直”之“鞫獄”,就是廣義的用例。(12)[德] 陶安あんど: 《秦漢刑罰体系の研究》,(東京) 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09年,第392—393頁,注釋35。
學者的見解值得重視。“訊鞫論報”之“鞫”,自然是指訴訟中的一個具體程序,然而在當時的語境中,當需要表達“一件審判案件的稱謂”時,可以用“獄”;(13)如具獄、治獄、決獄、獄已決、獄未決等,皆是此意。而當需要表達“一件案件從起訴到判決的全部程序的稱謂”時,又當如何呢?細究起來,恐怕“鞫”是指代性最强的用語。《法律答問》《二年律令》所見涉及論獄、鞫獄的罪名,有鞫獄故不直、鞫獄故縱。這裏的鞫如果只是理解爲調查、確認事實,顯然無法匹配“故不直”“故縱”的意義指向。《法律答問》93簡對“論獄”不直、縱囚的定義是: 故意將重罪定爲、判爲輕罪,輕罪定爲、判爲重罪,此是“不直”;對應當判決治罪的案件故意不判決,故意解脱罪人之罪,此是“縱囚”。無論不直還是縱囚,都已是司法官對審理案件所作出的違法裁定,因而與此組合的“鞫獄”,自然是指對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及其程序。(14)正因爲鞫獄之鞫有此指代作用,因而鞫獄故不直、鞫獄故縱成爲一個可以援引的類罪名,適用於司法活動中若干具體行爲明確的犯罪行爲。如以鞫獄故不直論罪的,有“放訊杜雅,求其他罪”“毋告劾而擅覆治之”(《具律》113簡)、“以投書者言系治人”(《具律》118簡);以鞫獄故縱囚論罪的,有“群盜、盜賊發,告吏,吏匿弗言其縣廷,言之而留盈一日,以其故不得”(《捕律》146簡),其中所涉及的具體罪名,大致是在鞫獄的範疇之内,並不僅僅是調查或認定事實。换言之,鞫可以指代所審判的案件。(15)小文《新見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元始二年張勳主守盜案牘文疏解》。
今以文中所述兩方木牘所見,秦及漢初律中鞫字的這一義項,爲後世所沿用。如張勳案的鞫辭,首先是被告的自然情況,其次是犯罪事實陳述,再次是劾者,最後是判決内容。張雄等五人案的鞫辭也大致如此: 文書層次依自然情況、犯罪事實、劾、調查(辭如劾)、判決展開。所不同者只有一點,即在判決前排除了被告“當請”的資格。應當説,兩方木牘文首的“鞫”字,是對全部牘文的指稱。張勳案之牘的正面大字書寫的“鞫”字,更是明確示人,本牘背面的文字即是鞫辭。
這樣的鞫辭,包括了一個刑事案件審判的主要程序,包含了判決所應具備的基本要件,因此並不妨礙將其視爲具有判決書性質的文書。由此再看所謂讀鞫,學界的一般解釋是向被告宣讀判決書,目前這一説法仍可成立。讀鞫,猶如唐律對“獄結竟”後的規定:“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屬,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辯。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爲審詳。”(16)〔唐〕 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 《唐律疏議》,中華書局1983年,第568頁。“具告罪名”,即是疏議所説的“具告所斷之罪名”,實際就是宣告罪名與刑罰,這自然是判決的核心部分;“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爲審詳”,即是允許在判決發生效力前乞鞫,再次確定事實。唐律之制承於晉制。《史記·夏侯嬰傳》索隱:“案: 《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這裏的“鞠語罪狀”,文面意思似乎是宣讀罪狀,然而如果“獄結竟”是指“案件已經審結”,與秦律漢初律中的“獄已斷”之意無異,“鞠語罪狀”就不僅僅是宣讀罪狀,還應包含了通過事實認定而確定的法律適用。换言之,讀鞫與乞鞫都不能排除對案件的裁決。沈家本認爲西法中的“宣告”,與周之讀書用法,漢之讀鞫乃論,(17)如果局限於“論”的性質,“鞫”的判決之意就會弱化。但是如果注意到《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法”的鄭司農注與孔疏,則其間關係尚可分辨。鄭司農注“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孔疏言“鞫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也”。“行刑之時”必是執行刑罰之時,刑罰則必由判決而定。因此所謂“論其罪”,不可解爲在行刑之時方進行判決,而應是“執行刑罰”之意。《唐六典》言“凡決大辟罪皆於市”,也是指在市執行死刑。“決大辟罪……五品已上非惡逆者,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仍日未後乃行刑”(〔唐〕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 《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第189頁),其中的“宣告犯狀”固然是宣讀罪狀之意,但這是執行刑罰中的環節,而非審判程序中的環節。唐之宣告犯狀相同,(18)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等: 《沈家本全集》(第四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752頁。正是看出了彼此的共性。簡言之,讀鞫的進行不是在審判之中,而是在做出判決之後。《法律答問》115簡:“以乞鞫及爲人乞鞫者,獄已斷乃聽,且未斷猶聽殹?獄斷乃聽之。”乞鞫在“獄斷”後方可受理,即説明鞫包含了判決程序,由此亦可反證讀鞫也是在判決後進行,如果是在判決前進行,“獄斷”便無從坐實。只是此時“乞鞫”涉及的内容,可能既有對事實認定的不服,也有對法律適用的不服。(19)關於乞鞫涉及的内容,得到齊偉玲博士的意見啓發,謹致謝意。
三、 “鞫”的文書意義
以上探討了鞫的程序意義與指代意義,鞫的文書意義實際與此密切相關,上述兩方木牘即可視爲指代意義上的鞫辭或曰鞫文書。
在既往研究中,有的學者已經在使用“鞫書”這一概念。如于洪濤指出:“鞫”書是案件審理事實過程中所形成的,從性質上來説是對案件情況的審結文書,案件中所有的訊辭,以及最終的結論部分都屬於“鞫”書的内容。(20)于洪濤: 《秦漢法律簡牘中的“鞫”研究》第83頁。這是基於鞫的程序意義的定義。如里耶秦簡中的下述簡:
廿六年八月丙子,遷陵拔、守丞敦狐詣訊般芻等,辤(辭)各如前。8-1743+8-2015

正反兩面都有記載,籾山明認爲“背面的書式與《奏讞書》的鞫獄相同,正面記録的是令和守丞訊問的結果。……縣令和丞接續獄史的訊問結果進行審問,最後確定罪行”。(21)[日] 籾山明: 《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以里耶秦簡爲例》,柳立言主編: 《史料與法史學》,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第62頁。從“鞫……審”的格式來看,該簡與《奏讞書》及《爲獄等狀四種》所見無異,“審”字表明事實認定的結束。然而遺憾的是,簡的殘斷令人無法判斷下文。《奏讞書》中的“鞫”後自然没有“論”的部分,這當然是由於“讞”因事實認定困難、法律適用疑難而爲之,“論”將取決於上級機構的裁斷。即使郡對縣呈報上來的疑案不能決斷,需要向上呈報,所提出的裁斷意見也不稱“論”,而是稱“當”。(22)如《奏讞書》案例14、15。陶安指出:“當”是在自己不能獨立論斷該案的情況下轉告給其他機關的“判決意見”。[德] 陶安あんど: 《試探“斷獄”“聽訟”與“訴訟”之别——以漢代文書資料爲中心》,張中秋主編: 《理性與智慧——中國法律傳統再探討》,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0頁。反之亦可思考,假設在司法實踐中,當一個案件不存在“讞”的必要性,而是可以由一級司法機構直接裁斷,它的鞫與論又當如何表達呢?雖然在秦及漢初的文獻中,迄今仍無一份並非出於“讞”的完整的訴訟記録,其作爲文書規範具有怎樣的“式”並不清楚,(23)例如《封診式》的文書格式涉及調查、檢驗、審訊,卻未見對鞫辭的要求。因而想要判斷“鞫書”的完整格式與内容還比較困難,但雲夢龍崗秦木牘仍是一個可以關注的例子。如前所述,學者認爲該木牘的性質爲判決書,其牘文爲:
考慮到牘文中的“丞甲”、“史丙”不是一般司法文書中審判者的實名,具有一定的借代性,因而不可徑直視爲産生於司法審判中的原件。但可以確定的是,它書寫了辟死被錯判爲城旦,又獲糾正而免爲庶人的結果,是辟死所經歷的司法審判的記録。退一步而言,即使這個“經歷”是爲了隨葬而臨時書寫的,其文書的格式也不是可以隨意而爲的。從這份文書看,内容包括了事實結論(不當爲城旦)、對錯判者的處罰(吏論失者已坐以論)以及改判(免辟死爲庶人)。由此或可推測: 日常中的鞫文書,至少應包含事實結論與裁斷這兩項要件。對辟死的改判之所以未見“論”,原因或在於這是乞鞫案件,而乞鞫案件的受理機構對乞鞫的裁斷意見,往往以“覆之”表現。如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案例17,廷尉對黥城旦講乞鞫的裁斷意見是“二年十月癸酉朔戊寅,廷尉兼謂汧嗇夫……覆之,講不盜牛。講(繫)子縣,其除講以爲隱官,令自尚……”,(25)彭浩、陳偉、[日] 工藤元男主編: 《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第360頁。《嶽麓書院藏秦簡(叁)》對隸臣得之乞鞫的裁斷意見是“·覆之: 得之去(繫)亡,巳(已)論(繫)十二歲,而來气(乞)鞫,气(乞)鞫不如辤(辭)。以(繫)子縣。其(繫)得之城旦六歲,備前十二歲(繫)日”,(26)朱漢民、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第201頁。同書載隸臣田乞鞫,最終的裁斷意見也是“覆之”云云。(27)朱漢民、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叁)》第210—211頁。
雖然覆獄結論與原審結論在程序上體現了用語差異,但就實質而言,都是對案件的裁斷。因此涉及辟死的鞫辭,可視爲包含了事實結論與裁斷要件的文書。今見新出益陽兔子山秦簡J9③∶2:
十月己酉,劾曰: 女子尊擇不取行錢,問辤(辭)如劾,鞫審。·己未,益陽守起、丞章、史完論刑尊市,即棄死市盈十日,令徒徙棄塚間。(2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陽市文物處: 《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九號井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5期,第43—44頁。
這是劾、問、鞫、論程序具備的文書。假設此案無須“讞”而是最終判決且無乞鞫,則意味着這便是現實中行用的裁斷文書,然而其文並未以“鞫”字總領。
今見二牘,可以説初次展現了西漢末期及東漢時期指代意義上的鞫文書的形態。其定名爲“鞫”,除去罪犯的自然情況與犯罪事實外,還表明一份鞫書是在若干種文書基礎上形成的,如起訴階段的劾狀(或自言),調查階段的爰書,庭審階段的記録,因而它既是一件審判案件程序與結果的完整體現,也意味着案件的原始卷宗是由若干不同種類的文書構成的。(29)籾山明指出:“訴訟的每一個手續都製作固有的書式和形狀的文書和記録。從史料的角度看,訴訟可以看作幾種文書和記録的集合體。”[日] 籾山明: 《簡牘文書學與法制史——以里耶秦簡爲例》第63頁。鞫文書的一個顯著特徵,就是文書之首以“鞫”字居先,以下依次敘述訴訟的各個程序,直至“論”。這個鞫不是發生於訴訟程序中的一個環節(如“鞫審”之“鞫”),而是發生於案件判決之後。從形制看,張勳案牘長49釐米,寬6.5釐米;張雄案牘長47釐米,寬7釐米,差異不大,且兩牘上方皆有長方形墨塊;從内容上看,它不是單獨一個程序的記録,也不是程序進行中的公文流轉,而是對已完成的一件審判案件程序的提要、概括。换言之,司法文書伴隨着每個程序運行而産生,其原貌必不如“鞫”文書所見般簡略,這些即時産生的、原始的文書,是案件卷宗的組成部分,而此類鞫文書是對案件程序與文書核心内容的概括。
當然,現在並不能斷言,所謂“讀鞫”就是向當事人宣讀這樣的鞫文書。不過對當事人而言,聽取判決結果,應當知曉案件起因、訴訟提出、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刑罰確定,這與今人相比並無二致。就此而言,二牘所見的鞫文書包含了這樣的内容並具有這種作用。
四、 鞫文書作用蠡測
如果認爲“此類文書是對案件程序與文書核心内容的概括”,則當然需要回答這類鞫文書的作用何在。對此,筆者還不能給與確切的回答。以下只是從司法權的分配及其監督略作推測。
據介紹,3號井(J3)出土簡牘約8000枚,長度一般爲23.5釐米,寬1.3至2.8釐米;特殊的大型木牘有三枚,僅一枚完整,即張勳案牘,其長寬皆爲同井所出簡牘的兩倍有餘。(3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十年風雲激蕩 兩千年沉寂後顯真容》。這8 000枚簡中是否含有張勳案的原始卷宗,目前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確的是,此牘是對該案的完整記録,並有審判者的職務與簽名。另據同出於3號井的張勳案另一木牘J3⑤∶2言“益陽言守令史張勳盜所主守加錢論決言相府”,説明益陽將張勳主守盜錢案的判決結果報告給了相府。“論決言”或“治決言”是秦漢司法、行政中常見的命令用語,意指“將裁斷(或辦理)的結果報告上來”。
需要報告的原因推測有兩種。一是案件的審判權限不在本級機構而在上級機構。如據著名的《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册書所見,居延縣向都鄉嗇夫發出指令,要求依據粟君起訴書調查被告寇恩,並命令“書到,驗問治決言”(簡22.1、22.29),而對於調查中的“疑非實”之處,縣廷會依據府“更詳驗問治決言”(簡31)的命令,要求鄉進行再調查並報告結果。該册書最後以縣給甲渠候官的移文作結,結論是“須以政不直者法亟報”。這意味着此案的審判權既不在居延縣,也不在甲渠候官,而是在都尉府。都尉府最終判決的事實依據,應當就是在居延縣與甲渠候官的調查結果。甲渠候官將調查結果向都尉府報告,故其文書形式應是以“敢言之”爲特徵的上行文書。與候粟君起訴寇恩案發生于同年(建武三年)的“駒疲勞病死”案册書,就是應府“驗問明處言”的要求而提出的上行文書。(31)關於《候粟君所責寇恩事》與《駒疲勞病死》兩案册書的研究成果與解讀,可參[日] 籾山明: 《中國古代訴訟制度の研究》第三章《居延出土の册書と漢代の聽訟》第125—164頁。以上兩件案件,縣與候官的權限都只是“驗問”,雖然也提出了傾向性的意見,但最終裁斷權恐怕還是在府,因此命令中用“治決言”而非“論決言”,也許是權限使然。
另一種情況是縣對受理的案件有審判權,但也需要“論決言”,也就是將審判結果報告給上級。《二年律令·興律》396~397簡是對縣道司法權限的規定,據規定,縣道需要向二千石官報告覆核的,只有死刑與過失、戲殺人案件。如果此條規定在後世繼續有效,對張勳主守盜案的審判權限就由益陽縣掌握,不必由府覆核。而此案“論決言相府”的原因,如果不是審判權的制度變化,就有可能是報府備案。(32)小文《新見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出土元始二年張勳主守盜案牘文疏解》。報府備案的目的,或在於接受司法監督。《嶽麓書院藏秦簡(叁)》“癸、瑣相移謀購案”本非州陵縣上報的“讞獄”,而是州陵縣日常司法活動中的一個審判案件。該案由一般案件轉换爲“讞獄”的關鍵,是監御史發現了判決不當。州陵縣在“更論”的過程中,提出疑罪上讞。這意味着監御史可以隨時審閲縣審案件的卷宗,即時對縣實施司法監督。
審判權或覆核權在府的案件,縣上報的“具獄”文書自然應當詳備。《漢書·于定國傳》載東海孝婦案,“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其中的告、捕、辭、驗治、服,即是起訴、逮捕、調查、訊問、服罪各個環節的反映。報府的也應是“獄案已成,其文備具”的全部卷宗。審判權在縣的案件,未詳報府文書是否需要將原始文書悉數呈上,但至少應當提供一個完整反映了訴訟程序、事實認定、判決結果的文本。若然,此種鞫文書也有可能成爲“論決言”的對象。當然,由於它本身不具備上行文書的文書格式,因而不是上行文書,而是上行文書的附件。
張雄等五人案不詳有無“論決言”的要求。據新披露的五一廣場簡,有一枚無疑與本案相關:
A面:
永初三年正月壬辰 朔 日,臨湘令丹、守丞皓敢言之。謹移耐罪
大男張雄、舒俊、朱循、樂竟、雄趙辤狀一編,敢言之。
B面:
掾祝、獄助史黄護(34)引自李均明: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劾”與“鞫”狀考》,“第六届中國古文書學國際研討會”論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主席團2017年。
這是呈報給上級的上行文書,文書中的人物即是張雄等五人案的判決者。不過由於日期及“辭狀”與鞫文書的關係還不明確,(35)據已披露的簡牘,張雄等五人案的進程是: 永初三年正月壬辰朔十二日壬寅,直符户曹史盛舉劾,移獄臨湘,同日拘繫五人。正月十四日乙巳,臨湘令丹等判決了此案(參見楊小亮: 《略論東漢“直符”及其舉劾犯罪的司法流程》第180—186頁)。因此“永初三年正月壬辰 朔 日,臨湘令丹、守丞皓敢言之”與前述文書的關係如何,尚待考辨。還有“辭狀”的具體含義,也有待進一步探究。此暫且擱置。值得關注的是144牘背面的“得平”二字。二字字體較大,筆迹不同,應該是後來追加書寫的評價之語。平,平端。平端是秦漢時期對官吏爲政能力與素質的要求之一。《奏讞書》228簡“……毋害,謙(廉)絜(潔)敦(慤),守吏也,平端”,《新書·等齊》“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漢書·平帝紀》“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李奇曰“吏治獄平端也”,皆爲此義。故“得平”的評價依據,應是既無乞鞫的情況,在案件的事實認定、罪名確定、法律適用上也無不直、失刑、故縱等違法行爲。(36)楊小亮指出:“如罪犯不服從判決,當可申請‘乞鞫’程序,但從簡背所書‘得平’二字判斷,此案件至此已經完結。”(《略論東漢“直符”及其舉劾犯罪的司法流程》第185頁);李均明認爲:“平,公平適中。故‘得平’是對案件處理結果的高度評價,但未知何人批示。治獄不公平亦構成犯罪……”(《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劾”與“鞫”狀考》第4頁)。這説明“得平”的評價是在判決生效並執行後獲得的,做出“得平”評價的應是上級機構。如果僅僅是以無乞鞫作爲“得平”的依據,按“气(乞)鞫者,各辭所在縣道,縣道官令、長、丞謹聽,書其气(乞)鞫,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都吏覆之”(《二年律令·具律》)這一制度規定,縣既然有聽取乞鞫的權力,即可據此進行自我評價。但是如果“得平”的標準包含了無不直、失刑、故縱等違法行爲,這個評價就應該來自上級機關。上級機關據以評價的,自然是由縣審結的案件。
由於“論決言”的文書是對案件主要程序的概括,既體現了縣司法權的運行,也是對責任主體的追究依據,因此在判決主文部分,需要審判責任人簽名。目前所見的應是留存於本級機構的副本,副本同樣也需要簽名。
結 語
益陽兔子山遺址J3木牘與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144木牘的出現,令人對秦漢時期的“鞫”增加了新認識,本文據此對鞫的義項進行了程序、指代、文書義項的劃分。對程序意義的認識認同既往的研究成果,指在判決前對犯罪事實的認定;鞫的指代意義則接續既有的廣義之説,指出它在内涵上大於單一的程序意義,可以包含一個案件的全部訴訟程序;就二牘而言,文書意義衍生于指代意義。不過張勳案木牘以單面大字書寫“鞫”,此是否就是當時鞫文書的定名,尚待探究,五一廣場東漢簡所見的“鞫狀”是程序意義還是指代意義上的文書,(37)“鞫狀”,語見李均明: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劾”與“鞫”狀考》(第3頁):“書考問朗、平、備等,辭皆曰: 正月十五日文罪定,朗、純具鞫狀。署、逢未論決。”還不清楚。另外,此類鞫文書自然是産生於一個具體、實際的訴訟案件,其中的起訴、拘繫、調查、庭審、服罪、判決各個環節,本當有其原始文書。然而不易判斷的是,鞫文書作爲這系列程序的概括與提要,是判決書的原始文書還是程序外對案件的摘録?如果是前者,當然可以視爲“司法文書”;然而如果是後者,是否可以納入“司法文書”的範疇,就需要進一步明確。當然還有時代更迭、制度改革會對文書格式帶來怎樣的變化,也是需要考慮的題中之義。
儘管僅以此三方木牘還不易對鞫文書做出一個整體、客觀的判斷,但是這類文書的出現頗令人關注。首先,此前所見出土的秦漢司法文書的時代主要是秦及漢初,西漢晚期及東漢時期的並不多見,縣級文書尤爲罕見,故内容完整的木牘無疑十分難得。其次,如文首所言,訴訟制度以及與其相應的文書制度是目前學者關注的對象之一,然而合乎規定的“具獄”文書究竟包含了哪些類别與内容,圍繞案件的起訴、審理、判決、執行以及上報、覆核、監督而産生的文書,體現了怎樣的地方司法狀況,欲知其詳,必當有賴於日常文書。因此像此類司法文書與檔案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也許伴隨着出土資料的增多,在學者已盡力復原的訴訟程序的前提下,對應程序的文書復原及其作用揭示,會有更深入的探討。
2016年6月8日—8月31日初稿
2017年9月14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