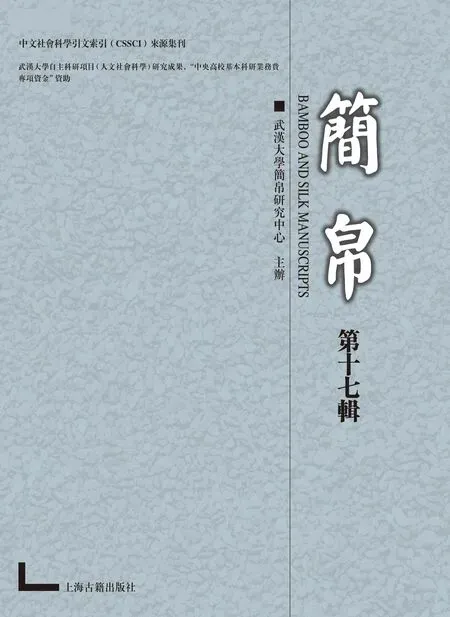從法制史角度解讀清華簡(六)《子産》篇
李 力
關鍵詞: 清華簡 子産 鑄刑書 此謂 是謂
清華簡(六)整理出版之後,其《子産》篇很快引起法制史學者的關注。究其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整理者指明該《子産》篇“可印證和補充《左傳》關於子産作刑書的記載”。(1)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册,中西書局2016年,第1頁“本輯説明”。
在目前所見有關《子産》篇的研究成果之中,與法制史相關聯的争議焦點,歸納起來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 第一,整理小組對其第9自然段“法律”(簡20)二字的釋讀是否合適。第二,關於第10自然段的理解,(2)清華簡(六)的整理者在前注所揭“本輯説明”中説,“《子産》可分爲十個小段”;又,在《子産》篇【説明】中再次强調“全篇可分爲十個小段”(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下册第136頁)。但目前所見《子産》篇的釋文其實有11個自然段。揣測整理小組在此或有所偏差導致誤算。從第2—10自然段段末所見的“是謂”“此謂”這個句式來推測,今見第1自然段(關於“聖君”)與第2自然段(關於“不良君”)當合併爲一段(詳見本文第三部分),或許整理小組起初就是這樣考慮的。這樣正好與其“本輯説明”中的《子産》全篇可分爲十個小段之説吻合。爲方便起見,本文在此暫以目前所見的自然段爲據。特别是與史載子産“鑄刑書”事件之間有無關係。第三,推測該《子産》篇“此謂”“是謂”之後的内容爲子産所作刑書之内容的説法是否可以成立。
以下,本文擬就這三個問題點,試着從法制史角度來圍繞《子産》篇談點不甚成熟的認識。
一、 關於簡20釋文“法律”二字的討論
1. 整理小組的初步意見
關於第9自然段的簡20,整理小組所作的釋文如下:(3)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下册第138頁。
2. 針對整理小組初步意見的相關討論
蘇建洲和張伯元先後在“簡帛網”上發表論文,就整理小組簡20釋文中“法律”二字的釋讀進行討論。

左旁從立比較奇特。此處有兩種考慮,一是“去”的譌寫。楚簡的“灋”有時會寫成“”,如(《陳公治兵》11),其“夫”旁也是“去”的譌變省。另一種考慮是與施謝捷先生所揭示的一方三晉璽私名璽並看:(丘)。
(2) 張伯元對“法律”二字的質疑
張伯元是最早關注到該簡20中所釋“法律”二字的法制史學者,並專門撰寫《清華簡六《子産》篇“法律”一詞考》(以下簡稱“張文”),(6)張伯元: 《清華簡六《子産》篇“法律”一詞考》(初刊於簡帛網2016年5月10日,http: //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51),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第六届“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暨慶祝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2016年11月,第46—47頁。以下所引“張文”均出於此,不再注明。認爲該簡20文字的考釋與句意的理解存在以下這樣三點異議:
其二,這樣,其後“釋爲‘律’的‘聿’字就失去了依旁”,“聿”字,又見於簡24、25,“常用作句首、句中助詞,絶大多數出現在動詞前面”。而“律”字晚出,且初非用於法律,故“‘聿’恐不能隸釋爲‘律’”。
其三,據其文意,“上下句似可斷在‘聿’字之前,爲‘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薦),聿求藎之賢’”。而“(察)”字,可從徐在國之説“釋爲‘豚’”,“讀爲‘循’”。
“張文”對簡20該“法律”二字的質疑和重新斷讀,是具有學術意義的新見,爲進一步的討論打開一個新的視野,並得到一些學者不同程度的認可。
王寧只贊同“張文”之説的一部分:“‘聿’字原整理者屬上句讀,以‘法律’爲詞。張伯元先生認爲當屬下句讀,‘聿’爲句中或句首語氣詞,其説可從。”同時,採納徐在國之説,主張“”字“當分析爲從又豚聲,可能即‘揗’字的異構,讀‘循’當是,釋爲‘遵循’之義”,其後三句的斷句從“暮四郎”説,則簡20的釋文爲:“善君必循昔前善王之法,聿求藎之賢可,以自分重任,以果將。”(7)王寧: 《清華簡六〈子産〉釋文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6年7月4日,http: //www.gwz.fudan.edu.cn/Web/Show/2851。以下所引“王寧”之説均出於此文,不再注明。
王捷則支持“張文”之説:“張伯元先生指出,此句‘法’字當爲‘薦’,‘律’當爲‘聿’,二字不連讀,當斷讀爲‘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薦,聿求藎之賢’。可從。”(8)王捷: 《何爲“刑書”——清華簡“子産”篇讀記》,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第六届“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暨慶祝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49—57頁。王捷: 《清華簡〈子産〉篇與“刑書”新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第55頁。
孫合肥也贊成“張文”的斷讀,但主張“聿,遂也”,因此這句話的意思就是:(9)尤其,認爲簡19那句話的意思是説:“古代狂妄的君王,才德淺薄而不重視其前代賢明君王的禮典模範,自以爲全知全能,臣民無法施展才能而無所治事,國家不能得到治理,以致衰敗。”進而强調,簡19與簡20兩句簡文,與《荀子·王霸》所説的(“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基本相合。孫合肥: 《清華簡〈子産〉簡19~23校讀》,《淮南師範學院學報》2017年第1期,第2頁。
古代的明君必定要明瞭其前代賢明君王的禮典模範,並且争取完全知曉,賢德的人各自分配到自己的職務,各安其位處理事務,君王治理國家的重任得以實現。
3. 對簡20整理小組之意見及其相關討論的初步評判
在此,根據目前所見資料以及上述學者的討論情況,就簡20“法律”二字的釋文,提出以下的初步判斷,並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關於“聿”字。“聿”可讀爲“律”字,在楚文字中不乏其例。例如,上博簡(三)《周易》簡7“帀(師)出以聿(律)”,其整理小組注釋:“‘聿’通‘律’,《爾雅注疏·卷二考證》:‘鄭樵曰: 律,即聿字。’楚字多以‘聿’爲‘律’,如《楚王領鐘》‘其聿(律)其言(音)’。”(13)馬承源主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45、146頁。李守奎等按:“帛本、今本皆作‘律’。”(14)李守奎、曲冰、孫偉龍編著: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第160、816頁。陳仁仁亦注釋:“‘聿’,今本、帛本均作‘律’。聿,通‘律’,訓法,此處指軍紀。”(15)陳仁仁: 《戰國楚竹書〈周易〉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41頁。
由此看來,整理小組在此將“聿”讀爲“律”字,也是没有什麽問題的,至少可成爲一説。不過,《子産》篇另見有“聿”字,並未讀作“律”字(簡25“聿參邦之型”,整理小組讀作“肄”(16)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上册第138頁。)。主張將“聿”字從下讀之説,也可以作爲一个方案來考虑。
簡言之,關於簡20“法律”二字的釋讀與理解,目前仍頗有争議,暫時難以得出比較確定的結論,有待古文字學者作進一步的研究與判斷。
此外,需要特别提到的一點,就是後來整理小組對簡18~22的釋文補正如下:(17)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讀書會: 《清華六整理報告補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2016年4月16日,http: //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trp/6831/2016/20160416052940099595642/20160416052940099595642_.html。
馬楠: 簡文應當是説先善君有儉約之德,懂得任用賢能,分擔政務。狂君“以自余智”,不能“自分”,導致邦國崩壞。果疑讀爲課,訓爲試、用,“任重不果”與“重任以果將”相對。前善王“求藎之賢”應當指前代遺賢(詳《鄭武夫人規孺子》“藎臣”條),對應子産用尊“老先生之俊”。
其補説是有理有據的。由這個補充意見亦可知,目前仍當以整理小組的釋文和斷讀爲最優的處理方案。
就出土文獻而言,迄今爲止所見最早的“法律”二字連用,出現於公元前227年睡虎地秦簡《語書》之中,即“法律未足”(簡2)。此外,另有“法律令”(簡2~5、簡9~10)之語句。(18)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15頁。從該《語書》篇的上下文意來揣度,“法律未足”之“法律”,當與“法律令”同義。(19)關於此處“法律令”一語的理解,學者有不同看法。其代表性的意見,可參見張建國《中國律令法體系概論》(原載於《中外法學》1998年第6期,後收入氏著《帝制時代的中國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2頁)、徐世虹《文獻解讀與秦漢律本體認識》(原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2分,後收入柳立言主編《史料與法史學》,《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之十七,2016年8月,第18—19頁)。尤其是,徐氏主張《語書》所見的“法律令”,就是“法律、政令的合成,不意味着法律形式上的三分”。而“張文”提出:“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裏的‘法律令’中的‘法’,毫無疑義表達的是法律或用作動詞表示統一、規範的意思。”此處“法”字“用作動詞表示統一、規範的意思”的這個説法,恐怕是不够準確的。
清華簡的“年代大約是公元前300年左右,屬於戰國中期晚段”。(20)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田樂採訪整理: 《清華簡的整理研究與學術價值——訪李學勤先生》,《中國史研究動態》2016年第4期,第81頁。若按照整理小組的釋文,則簡20所見“法律”一詞,不僅在楚簡之中是首次發現,而且是目前所知出土文獻中最早出現的,其意義自不待言,特别是聯繫到第10自然段中專談子産制定法律之事。
二、 第10自然段與史載子産“鑄刑書”事件之間的關係
1. 整理小組的判斷以及學者對此的反對意見
如前所述,整理小組力主《子産》“可印證和補充《左傳》關於子産作刑書的記載”,並專門在《子産》篇前的“説明”中强調:(21)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下册第136頁。
特别是篇中提到子産參照夏商周“三邦之令”“三邦之刑”,制定了“鄭令”“野令”和“鄭刑”“野刑”,足以印證和補充《左傳》關於子産作刑書的記載。
而其中提到的所謂“三邦之令”“三邦之刑”,就見於第10自然段:
或許限於清華簡(六)整理本的體例與篇幅,整理小組難以具體表述是怎樣將《左傳》昭公六年的這段記載與《子産》篇第10自然段聯繫起來的,也未及説明其有關的證據鏈是什麽。
後來,主持清華簡整理的李學勤在《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以下簡稱“李文”)一文中,重申這兩段記載之間的關聯性:
説到法律方面,研究子産的學者都强調他制作刑書在春秋歷史上的改革意義,然而對其刑書的内涵和結構所知甚少。按作刑書一事,見於《左傳》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云:“鄭人鑄刑書”,杜注:“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没有更多記述,而是引用了晉國叔向對此事批評的書信。《子産》簡文則有較詳細的敘説,提到子産。
其下,接着引用《子産》篇第10自然段的釋文,並重申以上兩個注釋的内容。(24)李學勤: 《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第81頁。這裏也没有展示出清華簡《子産》篇所見與《左傳》昭公六年相關記載之間的聯結點。其中説到的子産“其刑書的内涵和結構”,反而成爲後來法制史學者進一步解讀《子産》篇的立足點。
不過,王寧、王捷均贊同整理小組以上的意見,並在此基礎上作了一些補充性的闡釋。
王寧説:“《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野’與本篇‘野’同,即郊野;‘邑’即‘鄭’,指鄭的都邑’。‘鄭令’即施行於鄭國都邑内之法令,‘野令’即施行於都邑之外、郊野之間的法令。”
王捷説:“在春秋戰國時期所言的‘三邦’,即指夏商周三代,當無疑義。”又,“本段簡文提及的‘鄭令’‘野令’‘鄭刑’‘野刑’,涉及周代的‘國野’體制”。但是,“具體的‘國野’制度内容至今尚未明晰。《子産》篇本處的記載,至少讓我們瞭解到在春秋時期鄭國法律是有適用對象不同而分别制定的,‘鄭令、野令’也許正是‘子産使都鄙有章’(《左傳·襄公三十年》)的具體規範”。(25)王捷: 《清華簡〈子産〉篇與“刑書”新析》第56頁。
目前,只見到前揭“張文”對整理小組的這一判斷提出不同看法:“順着整理之後的簡文文句所做出的推想”是,“這裏的‘法律’與鑄刑鼎似無關”。這是基於對簡20“‘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律,求藎之賢’句(釋文採用寬式)”的理解,即“其義在將這裏的‘法律’意譯爲良好的舉措”。
2. 對整理小組之判斷以及“張文”反對意見的評析
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整理小組對這兩段文字記載的處理意見?進一步説,則“三邦”是指的夏、商、周嗎?“三邦之刑”即《禹刑》《湯刑》《九刑》?
爲了便於比較分析,先將這兩段記載中相關的信息點抽離出來,排列在下表之中。

Ⅰ.《左傳》昭公六年所載的相關信息點Ⅱ.《子産》篇所載的相關信息點A.鄭人鑄刑書a.善君必察昔前善王之法律B.夏/商/周有亂政,而作《禹刑》/《湯刑》/《九刑》b.肄三邦之令,以爲鄭令、野令C.制參辟,鑄刑書c.肄三邦之刑,以爲鄭刑、野刑
仔細推敲,這兩段記載之間的共同連接點,就是子産制定法律之事。由這兩種戰國時期的記述可以推定,當時的人是知曉子産制定法律之事的,並且將其視爲一種史實。但是,顯而易見,兩者的記述所關注的焦點及其所處的立場是不同的。
《左傳》關注的焦點是子産的改革,其所採用的視角是鑄刑書(於鼎)事件(即A)的反響,特别是側重於反對者晉國叔向的書信,其中透露了不少的相關信息(即B與C)。
《子産》篇關注的焦點是子産的施政業績,其敘述的角度則是從正面进行褒揚,因而其所述及的範圍相對大些(即a),但是其中並没有提到鑄刑書(於鼎),特别是b、c或可看作子産制定法律的全面性敘述,然而其信息與叔向書信中所透露的相關信息(B、C),並没有直接的交涉點與關聯性。
據此,可以肯定一點: 這兩者的記載之間,並不存在直接證據可以證實整理小組有關《子産》篇的主張,即: (1) “三邦”指夏、商、周。(2) “三邦之刑”即《禹刑》《湯刑》《九刑》。而所謂子産“刑書的内涵和結構”之説,更是無從談起。
不知是否可以這樣説,也許整理小組没有合適的機會或者適當的篇幅來交代這兩種記載之間的必然聯繫,可能還是有其自己的考慮的。因此,這裏尚留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
這二者記述之間直接的聯結點究竟在哪裏?拙見以爲,“三邦”就是這個關鍵的聯結點。
在早期的傳世文獻中,“三邦”僅有《尚書·禹貢》一見,即“三邦厎貢厥名”。(26)關於該“三邦”所指,比較費解,理解不一。或以爲,“蘇軾《書傳》謂‘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釋三邦威大中小三類,究竟多少國不定,近是。唯徑釋邦爲國,亦誤”(金景芳、吕紹剛: 《〈尚書·虞夏書〉新解》,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55頁);或以爲,“指荆州境内一些地區”(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第二册,中華書局2005年,第667—668頁)。但是,都主張“三”爲虚指,即多數。但其意義顯然與本文所論無關。此外,一提到夏、商、周的概稱,在我們的頭腦中馬上就會冒出來的是“三代”一語。在《左傳》《禮記》《孟子》中,就可以檢索到其用例。(27)葉紹鈞編: 《十三經索引(重訂本)》,中華書局1983年,第35頁。若以《左傳》爲例,則可見: (1) 成公八年:“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令。”(2) 昭公七年:“實爲夏郊,三代祀之。”(3) 昭公二十八年:“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4) 定公元年:“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5) 哀公六年:“王曰: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也就是説,在戰國至秦漢時期,一般是以“三代”指稱夏、商、周的。(28)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 《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6頁。又,或以爲:“虞、夏、商,古謂之三代。”詞例即前注《左傳》(1)成公八年條(楊伯峻、徐提編: 《春秋左傳詞典》,中華書局1988年,第14頁)。
“三邦”是否指“夏、商、周”?“三邦”與“三代”是何關係?趙伯雄的相關研究或許有助於解決這個疑難。
趙伯雄在《論三代國家的結構特徵》(以下簡稱“趙文”)一文的開篇就提出:(29)趙伯雄: 《論三代國家的結構特徵》,《河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4期,第108頁。
人們習慣稱呼三代爲夏朝、商朝和周朝,其實這時候的“朝”,與秦漢及其以後的王朝有着很大的區别。就國家的結構形式而言,三代的國家實際上是大大小小的“邦”的聯合體,而這些大大小小的原生形態的“邦”,基本上都是由血緣團體轉化而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趙文”在這裏所談到的“萬邦”這個結構特徵。其具體的論述是,由於“舊時的史家,常常用秦漢以後歷代王朝的模式懸想三代,結果很容易抹殺三代國家結構上的特點”。據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資料可知,“邦”是周人的稱法。雖然“王是天下的共主,但王也是有自己的‘邦’的”。據《尚書》記載可知,周人稱商爲“大邦殷”(《召誥》《顧命》)、“殷邦”(《微子》《無逸》)、“妹邦”(《酒誥》),稱自己則爲“周邦”(《大誥》《顧命》)、“小邦周”(《大誥》)。“周邦絶不是周政權統治的全部,周王統治‘天下’,而周邦只是天下衆邦中的一邦。”因而,“周人在敘述夏、商、周三代遞嬗的時候,實際上是在講天下居於統治地位的‘邦’的交替”。(30)趙伯雄: 《論三代國家的結構特徵》第109頁。
若根據“趙文”的這個研究結論,則“三邦”即指夏、商、周之説,確實是可以成立的。進而“三邦之刑”即指《禹刑》《湯刑》《九刑》,也是能站得住腳的一個推測。並且,還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三邦”之説大概就是周人自己使用的一個統稱,戰國秦漢時期“三代”之説出現後,“三邦”之稱就逐漸被“三代”之稱取代了。
在《左傳》昭公六年的這段記載中,有關子産“鑄刑書”以及叔向的書信内容,早已爲法制史學者所熟知。《子産》篇敘述到子産擔任鄭國執政時期制定法律的概況,並以此作爲子産政績的一個方面,在這樣的廣角鏡之下,我們可以讀到的有關子産制定法律的知識更爲豐富,相關的信息也頗爲新鮮。例如,“三邦之命(令)”即夏、商、周令,這是過去我們所不知道的信息。此外,“子産所制有關‘令’與‘刑’的區分,‘令’和‘刑’又都有‘鄭’(指國都)與‘野’(指郊野),更是從來没有人知道的”。(31)李學勤: 《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第81—82頁。對於法制史研究而言,這些知識點是極其珍貴的。
據《子産》篇所述可知,子産制定的法律包括“刑”與“令”兩個部分,且二者分别源自“三邦”(即夏、商、周)之“刑”與“令”,其各有“鄭”“野”之别。然而,在此令人困惑的問題就是,《左傳》所載的子産“鑄刑書”,究竟是對應於“鄭刑”還是對應於“野刑”?或者即其二者的統稱?或者二者都不是?王捷推測“‘鄭令、野令’也許正是‘子産使都鄙有章’的具體規範”,那麽“鄭刑”“野刑”所對應的究竟是傳世文獻所記載的哪種法律?客觀地講,目前所獲知的這些零星的知識點,恐怕暫時還難以串聯在一起。
由《子産》篇所見這種“刑”“令”的分野,至少可以推知以下三點:
第一,子産當時所“鑄刑書”(據説有三篇),其正式的法定名稱應爲“某刑”而非“刑書”(從文獻記載來看,“刑書”一詞決不是專門的法律篇名的術語),或與所謂《禹刑》《湯刑》《九刑》之類的名稱近似,但是當時其前面未必冠以“子産”之名。
第二,根據今天所擁有的常識,可知“某刑”之稱的時代要早於“某律”之稱的時代。如果這個看法没有問題的話,那麽《子産》篇中所見的這種稱法倒是保留了這種較爲古老的遺風。進而再大膽推測一下,是否可以這樣説: 《子産》篇相關的法制史料的來源應當也比較早,或許就在史載商鞅“改法爲律”之前。
第三,“令”這種形式的法律,可能最晚在春秋末期就出現了,但並不清楚其具體是怎樣的。現在所能看到的“令”之最早實態,就保存在嶽麓秦簡之中。(32)與此相關的情況,詳見陳松長: 《嶽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文物》2009年第3期,第87頁;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肆)》,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第188—224頁“前言”;陳松長: 《嶽麓秦簡中的幾個令名小識》,《文物》2016年第12期,第59—64頁。這兩種“令”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係,尚有待新資料的發現與進一步的研究。
不過,在此要明確指出的是,關於子産所“鑄刑書”的結構問題,《子産》篇本身根本没有涉及到。而與此相關的,則是叔向的書信中有“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楊伯峻注“制參辟”:(33)楊伯峻編著: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四册,中華書局2009年,第1276頁。
參同三,《晏子·諫篇下》云“三辟著於國”,雖《晏子》之三辟,據蘇輿《晏子春秋校注》乃指行暴、逆明、賊民三事,未必同於子産所制訂之三辟,疑子産之刑律亦分三大類。或者如《晉書·刑法志》所云“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扑”,或者亦如《刑法志》所述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此僅三篇耳。吴闓生《文史甄微》謂“‘參辟與封洫、謗政並言,亦子産所作之法’,是也。三辟爲刑書之内容,鑄於鼎而宣佈之,又一事也,故分别言之。”
楊伯峻在此作出三個推測: 其一,亦分三大類;其二,如《晉書·刑法志》所云“大刑”“中刑”“薄刑”;其三,如《法經》六篇,此僅三篇。(34)楊伯峻編著: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第四册第1275頁。又,在叔向的書信中,另有一處提到“三辟”,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楊伯峻注:“三辟,指《禹刑》《湯刑》《九刑》三種刑律。”
此外,《子産》篇第11自然段有“埜(野)參(三)分,粟參(三)分,兵參(三)分”,整理小組注釋〔八七〕:“野,郊野;粟,食糧;兵,武器。三分,三分之一,例見三晉系金文。按《左傳》昭公六年叔向書云子産‘制參(三)辟,鑄刑書’,疑其刑書有野、粟、兵三部分。”(35)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下册第138、144頁。
由此可見,關於叔向的書信中提到的子産所“制參辟”之“三辟”,其義甚爲不詳,學者之説因缺乏直接的證據,故多屬臆測。比較而言,楊伯峻的第三個推測,或許比較符合叔向書信之本意。清華簡(六)整理小組注釋“疑其刑書有野、粟、兵三部分”之説,則缺乏理據,顯得較爲牽强。
唯此“三辟”當不是其刑書的内容,而應是指其結構可能有三篇。正如楊伯峻注所引吴闓生《文史甄微》之語,“作封洫”並列的四者,當各爲一事。因此,子産所鑄“刑書”,即其所制“參辟”。而其刑書的内容則不甚清楚,可以推測應與子産在鄭國推行的系列改革有關。其刑書三篇,應該就是子産用法律手段維護改革成果的結果。
“張文”針對整理小組的看法所提出的反對意見,其立論的根據是建立在簡20“法律”二字爲錯誤釋讀與斷讀之基礎上的。一般而言,如果這個立論的基礎不扎實的話,就會動摇其所立之論點。對“張文”而言,恐亦當如此。然而其所説“這裏的‘法律’與鑄刑鼎似無關”的觀點,則是一個準確的判斷。在此,甚至可以這樣説,《子産》篇所述的與《左傳》所載的子産“鑄刑書”之間,並不存在直接的關聯。
三、 “此謂”“是謂”之後者是否子産所作《刑書》等的内容
整理小組在《子産》篇的“説明”中闡明:“全篇可分爲十個小段,前九段均以‘此謂……’作結。”(36)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下册第136頁;李學勤: 《有關春秋史事的清華簡五種綜述》第81頁。
針對這一語言現象,王寧在《清華簡六〈子産〉釋文校讀》中提出如下的看法:
“此謂”“是謂”之後的内容,疑都是子産所作《刑書》(包括下文所言的“鄭令”“野令”“鄭刑”“野刑”)裏的句子,《子産》篇的作者推崇子産及其所作的刑書,故用一些前人和子産的言行做根據,爲刑書的一些内容作解釋和相互的證明,就象《韓詩外傳》,講一些故事説明一個道理,最後都是以“《詩》曰”作結,是用故事説明此句《詩》所包含的道理,同時又以《詩》句證明此理之有據,“《詩》曰”後自然都是《詩經》中的文句,此篇之“此謂”疑與此類同。
古人頒佈法令之類總要説一些故事和道理作爲理由,這看看《尚書》裏的《吕刑》篇即可明白。《吕刑》是西周時期吕國的吕命(靈)王頒佈的刑書,裏面就講了不少故事和一堆大道理,子産頒佈的法令裏應該也有此類的内容,並非僅僅是法律條文。
王捷評述王寧“其説頗有啓發但不確”,並認爲“《子産》篇與子産所作‘刑書’有關係,但不是‘刑書’本身。《子産》篇前九段的‘此謂’結束句多爲某種規則或規範提煉後的表述,或即源於‘刑書’,只是《子産》篇以論述觀點爲主,在抄録‘刑書’時自然會將具體規則條款省略”。(37)王捷: 《清華簡〈子産〉篇與“刑書”新析》第54、57頁。
在這裏,有兩個問題必須進一步予以澄清: 第一,“是謂”“此謂”之後的内容究竟是否子産《刑書》(或包括“鄭刑”“野刑”與“鄭令”“野令”)的内容。第二,如何看待《尚書》之中的《吕刑》篇。
首先,審視一下《子産》篇“是謂”“此謂”這個句式及其之後的内容。爲便於討論,摘録其第二段至第十段末尾的結語如下:(38)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下册第137—138頁。
(1) “此胃(謂)才(存)亡才(在)君”(簡3)。
(2) “此胃(謂)亡好惡”。(簡4~5)
(5) “此胃(謂)不事不戾”。(簡11)
其中,(1)—(9)“此謂”,分别位於第2—10自然段的末尾;(10)“是謂”,則不在第11段末尾,而在其第二句之中。
“是謂”,亦見於傳世文獻。例如,《詩·小雅·賓之初筵》有“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而“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39)宗福邦、陳世鐃、蕭海波主編: 《故訓匯纂》第1021頁。“此”即“是”,“此謂”與“是謂”同義。
《子産》篇中所見“是謂”“此謂”的用法,正與傳世文獻所見的相同,也應是“指斥前文,總結其旨”。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若以此用法來審視《子産》篇的結構與内容,則可以得到如下兩個認識:
第一,今見第1自然段與第2自然段,當合併爲一個小段。這是由其内容之間的關聯性決定的。第1自然段是有關“聖君”的敘述,而第2自然段則是關於“不良君”的敘述,二者正好對應。因此,第2自然段結尾處才概括性地總結説“此謂存亡在君”。
第二,第3—10自然段末尾的“是謂”(或“此謂”)後的詞語,也都毫不例外地是針對本自然段前述内容的精煉概括,並非子産所制刑書或法律(乃至刑、令)的内容。可以説與子産所制定法律的内容没有直接的關聯。尤其是,第10自然段雖述及子産制定法律的政績,但其最後的概括性結語卻爲“此謂張美棄惡”。這一評價仍屬於道德性的,是針對子産立法之行爲本身而言的,絶非其所制定的法律中的詞語,更没有涉及其相關内容。同樣,即便是第11自然段“埜(野)參(三)分,粟參(三)分,兵參(三)分,是胃(謂)(處)固”,依照整理小組的理解意即: 郊野三分之一,食糧三分之一,武器三分之一,這就是“處固”(即安定穩固)。(40)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下册第144頁注釋〔八七〕、〔八八〕。這句話似乎也不可理解爲就是在講述其法律的篇章結構或内容。
在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亦不乏“是謂”這一句式。(41)關於傳世文獻的情況,詳見葉紹鈞編: 《十三經索引(重訂本)》第574頁。而出土文獻所見可檢索者,例如,長臺關楚簡:“是胃(謂)”,簡1-028、1-043(陳偉等著: 《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376頁);馬王堆漢墓帛書:“是胃(謂)”,《老子》甲本簡31、90、167,《經法》簡6、38、40、42、59、60、61(裘錫圭主編: (《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第四册,中華書局2014年,第4、6、43、127、138、143頁);銀雀山漢簡:“是胃(謂)”,簡17、184、259、327、373、656、668、687、700、815;“此胃(謂)”,簡132(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 《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釋文與注釋,第5、22、33、50、58、65、109、111、114、117、132頁)。特别是,在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這一法律文獻中,“是謂”的句式更是屢見不鮮。(42)據檢索,《法律答問》有15處: 簡28、93、108、112、126、142、176、178、180、184、188、199、206、207。此外,《日書》甲種亦有5見: 簡104正貳、108正貳、111正貳、155正、110背。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00、115、119、120、123、126、135、136、137,138、141、143、197、207、223頁。然而,除此而外,目前可見的秦漢簡法律文獻部分,都没有出現這個句式。尤其是,在摘抄的秦漢律文中,根本没有找到“是謂”或“此謂”的蹤影。其原因可能就在於,律文的行文格式不需要“是謂”“此謂”的句式,而這個句式卻是承擔解釋性任務的《法律答問》所不可或缺的。這是由“是謂”“此違”的語法功能所決定的。
爲了便於把握“是謂”這個句式在法律文獻中所發揮的作用,下面試舉一例,即《法律答問》簡93:(43)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睡虎地秦墓竹簡》第115頁。
論獄【何謂】“不直”?可(何)謂“縱囚”?罪當重而端輕之,當輕而端重之,是謂“不直”。當論而端弗論,及偒其獄,端令不致,論出之,是謂“縱囚”。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答問》所見的“是謂”: 其後,爲秦律之中的法律術語或專有名詞等(簡93下劃直綫部分);其前,則是與之相對應的解釋或者説明(簡93下劃曲綫部分,其本身並非律文,而是官府針對相關的問詢所作出的解釋或説明);而且均以“何謂”問句開始,以“是謂”結尾。這個特徵恰恰就是其語法功能的具體體現。
若比對前揭《子産》篇第10自然段的文字與《法律答問》簡93的文字,則可以更加清楚地判定:“此謂”之前的文字是對子産制定“刑”“令”之功績的描述,其後的“張美棄惡”四個字則是對該功績的高度概括。“此謂”前後的文字,都不是法律條文或者法律解釋,也並非法律的内容。這是確定無疑的。
其次,前揭有關《吕刑》的敘述,恐怕也存在欠準確之處。因爲這是其“‘此謂’‘是謂’之後的内容,疑都是子産所作《刑書》裏的句子”之説的一個論據,所以在此必須要作進一步的説明與辨析。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要先搞清楚吕侯作所《吕刑》與今見《尚書·吕刑》之間的關係。
關於《尚書·吕刑》的先期研究成果不少,目前所見最爲重要的作品,就是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四)中的《吕刑》部分。(44)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第四册第1899—2112頁。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幾個觀點與傳統的看法不同,且與本文所述相關聯,具體如下:
(1) 篇首所見“吕命王”,即吕王之稱號;而“此篇内容原與周穆王毫無關係,故先秦文獻中所引《吕刑》(或《甫刑》)共達16次,無1次涉及周穆王。及進至漢代,始盛稱《吕刑》爲周穆王之文,這是毫無根據的”。也就是説,該《吕刑》篇的篇主是吕王。(45)尤韶華不贊同此説:“關於《吕刑》的發佈,劉起釪先生自有其説,認爲是吕侯本身在吕國國内發佈的文告”。但“此説證據稍嫌不足,既不能證吕侯爲周穆王司寇以周穆王的名義發佈文告爲僞,亦不能證吕侯在封國内發佈文告爲真,且劉起釪本身考據‘命’字有三説,解命爲令只是其中一説。尤其是《周書·吕刑》的行文,諸如‘以詰四方’‘有邦有土’是否適合封國國君,劉起釪並未説明。‘邦’,劉起釪亦解爲國。按其譯文,‘有邦有土’爲‘有國有土的各級領主們’。這就出現一個問題,封國内是否還有下一級的國。此説似當存疑”。尤韶華: 《〈尚書〉所見的法律形式——〈周書·吕刑〉辨析》,楊一凡主編: 《中國古代法律形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72頁。(第1907—1908頁,第2083—2089頁)
(2) “《吕刑》篇中除談五刑部分爲現實情況外,其談歷史教訓引爲鑒戒的‘古訓’部分全由神話資料構成”。(第2089頁)
(3) “以上這一節,是《吕刑》篇的主體,是我國古代最完整的刑法總綱,作了實行贖刑的仔細規定。包括了原有五種肉刑的具體内容及怎樣從寬贖免的實施原則,成了吕王所要實行‘祥刑’的完整體系。”(第2053頁)
今文《尚書·吕刑》篇是由六個“王曰”組成的,按照顧頡剛、劉起釪該書的看法,這些應當是關於吕王制作《吕刑》過程及其文本主要内容的誥詞。而前揭(3)“以上這一節”指的就是第四個“王曰”部分,顧、劉二氏將該節全文具體劃分爲七段(第2053—2054頁)。這七段文字實際上就是《吕刑》這部法律文本的梗概。(46)尤韶華也有類似的看法:“以上是《周書·吕刑》的核心部分,敘述司法程序、量刑原則、用刑原則以及用人原則。其重點是贖刑的使用。《周書·吕刑》全文1 200餘字,這一部分僅占整個篇幅的三分之一,400餘字。”尤韶華: 《〈尚書〉所見的法律形式——〈周書·吕刑〉辨析》第74—75頁。
此外,爲了澄清吕侯所作《吕刑》與《尚書·吕刑》二者之間的關係,尤韶華曾在研究中就其結構、經典意義作了説明。具體來説,即按内容將《周書·吕刑》分爲四個部分: (1) 書序與引語;(2) 神話與傳説(幾乎占一半的篇幅);(3) 司法程序與原則(僅占三分之一篇幅);(4) 篇尾。進而説明如下:(47)尤韶華: 《歸善齋〈吕刑〉彙纂敘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2—34頁。
從結構上看,《周書·吕刑》是一篇採用階梯似的步驟,而又非常緊湊的文告,更似刑書的説明書。《吕刑》,又稱《甫刑》,或是周刑的修正案,或是專門規定。筆者更傾向於《吕刑》是規定贖刑的的單行條例,而《周書·吕刑》篇則爲條例的發佈文告。
比較以上的兩種看法,可謂仁者見仁。但是,關於《吕刑》本身的性質與《尚書·吕刑》的結構與性質,其看法的基本傾向性是一致的。
從以上關於今文《尚書·吕刑》篇的結構與内容來分析,可知吕王制定《吕刑》爲一事,今文《尚書》中存有一篇爲《吕刑》則又是一事。這兩個《吕刑》雖同名卻異實,不能籠統地將二者混淆起來。具體而言,《吕刑》是吕王所制定的法律,《尚書·吕刑》則是依據整理當時官方的檔案(以“王曰”的形式,記録了當時吕王制定《吕刑》的過程)所遺存下來的歷史文獻。但是,二者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作爲《尚書·吕刑》篇係吕王制定《吕刑》後所遺存的官方檔案文獻,經後人整理而保存在《尚書》之中,因而成爲其中的一篇;而作爲法律本身的《吕刑》,其原本雖已失傳,但其相關的内容綱要卻由於《尚書·吕刑》篇而得以保存下來。因此,今日我們才可以有機會通過《尚書·吕刑》篇來管窺《吕刑》這部法律之一斑。(48)參見李力: 《夏商周法制研究評析》,《中國法學》1994年第6期,第97頁。
在明確了這樣的關係之後,再根據前揭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釋論》(四)第2089頁《吕刑》篇中除談五刑部分爲現實情況外,其談歷史教訓引爲鑒戒的“古訓”部分全由神話資料構成,或許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判斷: 除了第四個“王曰”部分與《吕刑》法律文本有直接的關係之外,其他五個“王曰”部分的神話資料均不能説是《吕刑》法律文本的組成部分之一。因此,王寧認爲“《子産》篇的作者推崇子産及其所作的刑書,故用一些前人和子産的言行做根據,爲刑書的一些内容作解釋和相互的證明”,這一主張恐怕是難以成立的。
四、 餘 論
在此,歸納本文前面所討論的幾個問題,暫時可以得出如下三點認識:
(1) 整理小組對《子産》篇簡20“法律”二字的釋讀與理解,目前仍是最佳方案。或如學者所争議的,可能確實存在着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但有待整理小組的回應。
(2) 《子産》篇第10自然段與史載子産“鑄刑書”事件之間没有直接的關係。《左傳》與《子産》篇這兩種文本的記載,或許就是戰國時期社會上所流傳的爲數不少的相關文本中的一部分,大概是不同地區的學者以子産“鑄刑書”事件爲母本所書寫的。
(3) 以目前所見的資料,尚無法斷定鄭國子産制定的法律是由“刑”與“令”的體系組成的。《子産》篇所見“刑”與“令”等資訊的研讀與理解,恐怕要等待更爲豐富的資料問世。
(4) 推測《子産》篇“此謂”“是謂”之後的内容爲子産所作刑書或法律之内容的説法,恐怕是難以成立的。
在此,尤其要强調的是,(1)和(2)之間並無直接的關聯性。也就是説,無論簡20“法律”二字的釋讀是否成立,都難以影響到對《子産》篇第10自然段的解讀乃至其文意的理解。
最後,順便談一下王捷論文提到的長臺關楚簡戰國竹書與所謂的“周公《刑書》”這個問題。(49)王捷: 《清華簡〈子産〉篇與“刑書”新析》第57頁;陳偉等著: 《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十四種]》第374—382頁。最早就此進行具體論述,並進而推測二者之間存在某種聯係的,是史樹青於1963年發表的《信陽長臺關出土竹書考》一文。雖然他認爲從其中所用的詞句來分析,“它可能是春秋戰國之際有關儒家政治思想的一篇著述,其中心内容爲闡發周公的法治思想”,但是卻得出如下的結論:(50)史樹青: 《信陽長臺關出土竹書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3年第4期,第91—92頁。案: 該文(92頁)論述周公制刑書,據《逸周書·嘗麥解》和《左傳》文公十八年(及杜注與劉文淇疏證)、昭公六年有關“九刑”的記載,推定:“上云周公作誓命,在九刑而不忘,知‘作誓命曰’以下,皆九刑之書所載之文。從《逸周書》看,九刑當是九篇。可見,周公爲了鞏固西周的統治,確曾作過刑書,並有選擇地吸取了商代的典刑(殷彝)”。又,宋人時瀾有“周公之刑”一説,尤韶華從此説(尤韶華: 《歸善齋〈吕刑〉彙纂敘論》第120頁注釋④)。
此篇竹書,引用了不少周公關於刑罰的言論,(如“戔人(小人)格(殺)上,則刑戮至”等句),它可能是春秋戰國時人所整理、闡述的周公《刑書》,我們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測出周公《刑書》的内容梗概,如果這一推測没有問題,那麽這篇最早的竹書,也將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古的寫本法典。
經仔細研讀長臺關楚簡該篇竹書,並參考目前的研究成果之後,在此可以肯定的一點是: 該篇竹書絶不是周公的《刑書》,甚至與所謂的“刑書”也没有任何關係,其性質就是學界所認定的古書或者原本書籍,儘管現在還無法確定究竟是儒家作品還是墨家作品。(51)相關的討論情況,詳見李零: 《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修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203—207頁;楊澤生: 《戰國竹書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50—56頁。
附記: 此文以最初提交於第六届“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暨慶祝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2016年11月12—13日)之發言大綱爲基礎重新寫就,相關的認識與看法已有較大幅度的修訂。
補記: 本文39頁注①所揭張伯元大作即“張文”,後來以《清華簡(陸)〈子産〉篇“法律”一詞考》爲題,刊於王捷主編《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六輯(法律出版社2017年11月),相關内容没有變動2018年10月23日審讀清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