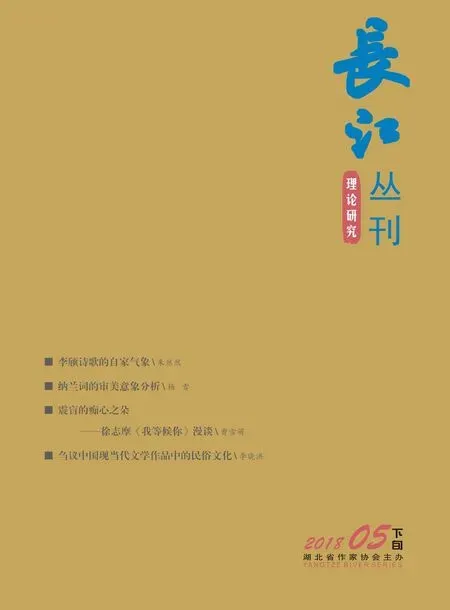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
■杨峻岭 刘 剑/铜仁学院
土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土地为人类财富的创造提供了条件,奠定了人类生存活动的物质基础,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占有了财富。正因为如此,土地问题成为建国后首要解决的问题。黔东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欠发达地区,因解放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等原因,也是全国较晚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之一。本文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所有制情况,分析其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论述了土地改革的过程、措施、不足和原因、经验和启示。以史为鉴,以期为当今代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工作提供经验和借鉴。
一、建国前黔东地区土地所有制情况
首先,建国前黔东地区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以封建地主所有制为主。黔东地区地处川湘渝交界地区,生活着土家、汉、苗、侗、仡佬等29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区域。由于境内山高路陡、峡谷深邃、滩险水急,以致实际开发较晚,社会发展也相对落后,故很长一段时期保留着原始的农村公社(家族村社)体制。西汉以后随着中央王朝经营和开发西南边疆的发展需要,这种农村公社体制也开始瓦解,逐步从土司农奴制、封建领主制、屯田制过渡到封建地主所有制。明初,朝廷一方面在境内继续推行“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笼络土著首领,封以官爵,给予“世有其土、世掌其民、世袭其职”的特权。当时朝廷以归顺的田仁智为思南宣慰使职隶属四川行省、以田仁厚为为思州宣慰使职隶属湖广川行省,两司下辖39个长官司,其地域覆盖了今天整个黔东地区境域及黔北、黔东南、湖南、重庆市的部分地域。[1]另一方面又在境内设立卫所,驻军屯田,以对土司施压和防止少数民族造反。同时,也不失时宜地开始“改土归流”,以各种方式渐次革除土司,至清雍正时期除极少数至清光绪九年,整个黔东地区基本上进入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当然,造成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明清两代为了控制境内少数民族,多次对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大规模军事进剿和屠杀。在明宣德、万历和清雍正、乾隆嘉庆年间,朝廷多次派兵进剿,“杀戮十之八九”,以致出现数十寨无一人的凄凉景象。大量田土荒芜,无人耕种,朝廷除采取军队屯田外,由实行“移民就宽乡” 的办法,招民垦种。[2]这些入境的地主、商人,或采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将空闲的荒田荒土据为己有、或出资购买贫困土司的田土、或兼并其它农民的田土,他们或招募逃荒的难民、游民垦殖、或将土地租佃给当地农民,逐步成为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例如,清乾隆年间在松桃厅的龙从云、中寨的曾正朝、瓦窑寨的欧昌德都是拥有三千多挑谷子田土的大地主。[3]民国时期,虽然政权的形式发生变化,但是农村的经济制度,特别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料仍然归地主所有,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建国初。
其次,土改前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极不合理。民国时期,由于常年的战乱和连续的自然灾害,加之土匪横行掠夺,使得土地兼并的现象十分严重。民国25年(1936年),黔东各县正式建立区、联保、保、甲作为四层基层管理组织。[4]当时,很多的区长、乡长、保长等都是由当地的大地主担任,他们把持地方基层政权,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例如,德江县在土改时有7个区18个乡镇,177个行政村,42381户,183748人,338552亩土地。其中有地主2156户,占全县总户数的5%,人口1171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6.4/%,占有土地281101挑(每挑约50公斤,下同),人均23.9挑;贫雇农23102户,占全县总户数的55%,人口94901人,占全县总人口的52/%,占有土地252855挑,人均2.67挑。地主与贫雇农人均占有土地之比为9:1,且地主占有的土地多为肥田沃土。[5]。再如沿河县在解放初调查统计,全县有地主2371户,9841人,占有耕地96842亩,人均9.84亩;富农1129户,3457人,占有耕地31768亩,人均9.19亩;中农、贫农、雇农157786人,占有耕地268671亩,人均1.7亩;其他阶层53060人,占有耕地34621亩,人均0.7亩。[6]当时像这种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的现象在其他各县均有存在。铜仁县地主占农户总数的4.61%,拥有的耕地达87940亩,占总耕地的53.2%,户均耕地61.28亩;而占总农户95.39%的农民拥有耕地77366亩,户均2.92亩。玉屏、万山在建国前人均占有土地的常年产量是:地主954公斤,富农622公斤,中农336公斤,贫雇农113公斤,其他 23 公斤。[7]
第三、地主对农民剥削的形式多样且负担沉重。由于各阶层土地占有极不合理,造成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户只能靠租佃、借贷、帮工维持生计,而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则以其土地对农民采取多种形式的剥削,主要有:(1)地租。即地主出租土地,由佃农自带耕畜、农具、种子、肥料耕种,秋后收获物按一定比例缴纳地租。其交租比例通常是:好田主七佃三,一般田主六佃四,稍次对半,差田或旱地、坡土主四佃六。全部地租,当年交清。[8]此外,有的佃农还得为地主分担苛捐杂税,承受额外的赋税。[9](2)雇工。雇工的形式主要有五种:其一是长工 ,即地主雇佣劳力强无田地的农民做工,常年干活,供饭食,每年给1—2套土布衣裤和150—250公斤大米的工钱;其二是短工,即雇佣农民干季节性农活,供饭食,每天付1—1.5公斤大米的工钱;其三是零工,即在农忙季节雇工干农活,做一天算一天,供饭食,每天付4—5公斤大米的工钱;其四是童工(放牛娃、丫头)则不付工钱,或用工抵所欠租粮或债利;其五是帮忙工,即临时请佃农干活,供饭食,不付工钱。[10]此外,农民受雇期间,除从事春种秋收等农活外,还要为地主承担沉重的家务劳动,随时听其使唤。(3)高利贷。农民向地主借贷钱粮,其月息多为“大加一”。即借谷10斗,月息1斗;借钱10元,月息1元。逾期不还,本息合计,再计利息。在每年青黄不接时的借款,利息最高。农民在农历六月向地主借谷一挑,七月下旬收获新谷还贷,仅一月时间,就要按1:1收取利息,即借一挑还两挑。如果逾期不还,就要以两挑作本翻一番还贷,农民俗称为“马打滚”或“利滚利”。此种剥削于民国33年(1944年)前后最为突出,贫苦农民常为之债台高筑。他们或变卖家产、或以房屋、财产乃至妻儿女抵交债务,甚至背井离乡[11]。
可以说,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势必造成土地占有的不合理,而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是建国初黔东地区农村封建势力强大的根本所在。地主凭借其经济地位对农民采取形式多样的盘剥,必然造成农民经济生活的极端贫困,这也无从谈及农民在政治上能够享有任何权利。其结果就是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加之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土匪横行,即便推翻了旧政权,农民的生活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变。所以要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共产党人必须将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进行调整,进行土地改革,使农民群众在真正意义上翻身解放,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
二、建国初黔东地区土地改革的现实条件
第一、土地革命的洗礼,为全面土地改革积累了历史经验。1934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进入黔东,创立黔东特区,建立苏维埃政权,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制定和发布了《没收土地和分配土地条例》,由此在整个特区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当时,根据地68个乡分配了土地,约有10万余人参加了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约680户,共没收分配土地618000 余挑,[12]特区的农民群众破天荒地实现了 “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这为后来的土地改革积累了历史经验。
第二、“清匪、反霸、征粮、减租、退押”五大任务取得很大成果,为土地改革的开展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农村股匪基本上被消灭,封建势力被初步打垮,农民觉悟开始提高,并且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这使土地改革有了执行机构和武装保障。当时,铜仁地委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国家有关土改的法规、政策,明确土改的目的、意义、原则和实施办法,同时指示各县举办培训班,培训土改工作的干部,这为土地改革的全面开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第三、普遍建立的基层政权,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政治保障。1949年10月,中共贵州省委在湖南邵阳召开会议,组建中共铜仁地委和铜仁行政督查区专员公署,任命李树荣、王立然为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此后黔东各县陆续解放,在摧毁旧政权的同时又相继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此后各县又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为土地改革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权保障。
第四、卓有成效的土改试点,为土地改革的开展积累了工作经验。1951年4月,铜仁地委根据各县社会稳定和群众发动程度,决定先行土改试点。从5月底开始,铜仁、玉屏、江口、松桃、石阡、印江、思南等县各选1个乡进行试点,德江县于8月初、沿河县于1952年1月初也先后开始土改试点。在土改试点过程中形成的好的方法和步骤,被有效的运用在之后的全面土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被及时地总结纠正,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
三、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的过程和措施
在汲取第一期土改试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黔东各县陆续开展了第二至第四期土改,到1953年5月各县的土改工作胜利完成。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宣传动员
土改刚开始时,农村中的各个阶层利益不同自然也有不同的盘算和行动。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不甘心将土地和财产拱手交给穷人,总是想方设法破坏土地改革。松桃八区甘龙乡一村田吉昌、毛银周毁烧油房一栋,分散财产百分之百,地底、墙脚、树上、山洞等处皆有,并以一点破衣破罐小恩小惠送到农民家里去,制造内部斗争。有的地主为使财产不被分配杀死耕牛、拆毁房屋,甚至收买群众当上干部,等等。[13]富农怕共了自己的产,中农怕搬家损害自己的利益,贫雇农则囿于小生产地位,主张打乱平分,不同意照顾原有耕地基础,还有的农民对分田缺乏信心,怕变天。鉴于此,地县工作组从思想宣传动员着手,针对不同对象,采取大会讲解、小组座谈、个别走访相结合的方式,采取各种方式宣传讲解土改的基本政策,逐步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和对土改工作的认知,引导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同地主“撕破脸”地斗争。
(二)划分阶级、报田评产
这一阶段是决定土改成败的关键,政策性极强。在划分阶级成分前,必须要整顿健全农民协会,并大力吸收农民参加,同时紧紧抓住政策规定,反复学习划分成分的基本依据,边学边划,把政策交给群众。在方式方法上,首先划分地主一级,明确了要斗争谁;其次划分富农,明确了要中立谁;接着依次划分中农、贫农、雇农,明确团结谁和依靠谁。这样清晰明了的划分阶级成份,让农民也了解自身的身份和应享有的权利。
由于各阶层思想难以统一,田亩的产量难以精准评估,就会存在瞒报、多报和少报等一系列问题。这就要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鼓励真实上报,经验田张榜公议、互审定案,避免过高或过低定田定产的偏差,为合理分配土地和征收公粮确立依据。
(三)分配土地和果实
这一阶段仍然以思想教育为先,首先就做了明确:先分田地,后分果实;田地已种上的庄稼,谁种谁收。通过各种会议号召群众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下酝酿具体分配办法。由于政策明确,群众发动充分,分配土地和果实进展得十分顺利。据地委《重点土改总结》中统计,就专区而言,一般每人平均分到产量400斤谷子的田,其中玉屏人口中最高分到727斤谷子的土地,最低350斤,这在各县中是最高的。[14]在确定地段方面,以乡为单位调剂、以村为单位分配的原则,好坏搭配,效率和公平兼顾,灵活的展开分配工作。其他的财产如耕畜、房屋和农具等按照人均占有量平均分配。地主除生产、生活必需品外的多余财产均没收,分配给穷人。
(四)发放土地证,转向生产
经过前面的一系列工作,黔东地区的土地改革措施基本完成,最后一步就是撕毁原有的土地契约,发放新的土地证,打消农民的不安,明确土地的所有权,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土改后,大修农田水利基础建设,大搞增产运动,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上来。
四、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划分阶级错误
在实际土改中,由于阶级划分政策标准不够完善,而且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人为因素,极容易造成划分阶级成分错误的问题。例如,但凡出现过政治问题的,都被划分为地主进行斗争,但凡经济条件较好的,都被划分为地主,这些问题都成为土改遗留下来的问题,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
2、忽略了生产问题
在土改中经常要求贫雇农进行诉苦,长此以往导致其将注意力放到对地主阶级进行诉苦和斗争,通过斗争直接获取一些现金、房屋和粮食等成果,而忽略了农业生产,偏离了土改的本质。
3、违背了民族团结的原则
例如,松桃县二区平茶乡五村在斗争苗族地主时,苗族群众不愿意参与其中,而发动汉族群众进行斗争,并且对苗族群众进行罚款;在斗争汉族地主时,发动苗族群众来进行斗争,这样往往违背了民族团结的原则,而且更容易产生新的民族纠纷。
(二)土地改革中存在问题的原因
1、干部自身原因
在土改中,很多干部是首次南下,其具有在汉族地区土地改革的经验,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还是第一次,经验尚浅,摸不清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阶级划分时,加上主观因素,导致阶级划分的错误和矛盾出现。在开展会议和听取群众意见时,由于错误估计形势,被少数积极分子的热情所蒙蔽和感染,容易只满足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而忽略了广大群众的要求。急功急利的工作心理,特别渴望一蹴而就带给农民实惠和利益,反而会造成工作的失误。
2、农民群众思想的原因
农民群众思想中贪图现利的狭窄面限制了其发展,在重新确立土地制度安排中,农民尤其是贫雇农忙着对地主阶级进行批斗,贪图眼前的小惠小利获取现金、农具、衣物等,而忽视了农业生产。农民的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导致了土改后期过度批判、斗争面扩大、斗争手段加强的特点,偏离了土改的本质目的。
3、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
黔东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有的风俗习惯,很容易引起误会。例如侗族内部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同一个村寨内的认同感很强,侗族的地主和农民之间也存在亲戚关系,他们不认为地主的一些行为是剥削,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照顾,这就给土改工作带来很大的难题,也加大了土改工作推进的难度。
(三)土地改革运动后农村问题的启示
1、农村工作要坚持稳步推进
在处理农村工作时,切记急于求成。要根据要求扎实推进工作。在土改中,不能一蹴而就,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逐步推进工作,稳扎稳打的完成工作。切不可操之过急,不顾现实情况,过分追求工作效果和速度,而忽略了本质问题的解决。
2、狠抓思想建设工作
在土改中,由于农民思想的局限性,导致后来工作偏离本质,产生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问题。所以处理农村工作时,要加强农民的思想建设工作,宣传农村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依靠群众积极完成工作。
3、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
在处理少数民族农村问题时,尤其要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维护民族团结,最大限度地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在农村工作中不能破坏民族团结和稳定。
五、结语
建国初黔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给黔东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土地改革中,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扫除了农业生产发展的阻碍,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基础,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土地改革中由于一些不可避免的主客观因素,仍然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失误,这也为我们后续农村工作的开展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回望土改的那段历史,仍有我们值得深思的地方,值得后续的持续研究。
注释:
[1][7][8]贵州省铜仁地区志编纂委员会.铜仁地区通志.军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1846~1857.
[2]贵州省铜仁地区志编纂委员会.铜仁地区志.军事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289~290.
[3][4]铜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铜仁地区志.大事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32.
[5]德江县委.土改总结报告(1951年)德江县档案馆藏,中共德江县委档案1-1-23。
[6]沿河县委:《土改总结报告》(1951年)沿河县档案馆藏,中共沿河县委档案1-1-30。
[9]江口县委:《土改总结报告》(1951年)沿河县档案馆藏,中共沿河县委档案1-1-25。
[10][11]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134.
[12][14]中共铜仁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铜仁地区历史(1921—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40.
[13]松桃县委:《土改总结报告》(1951年)松桃县档案馆藏,中共沿河县委档案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