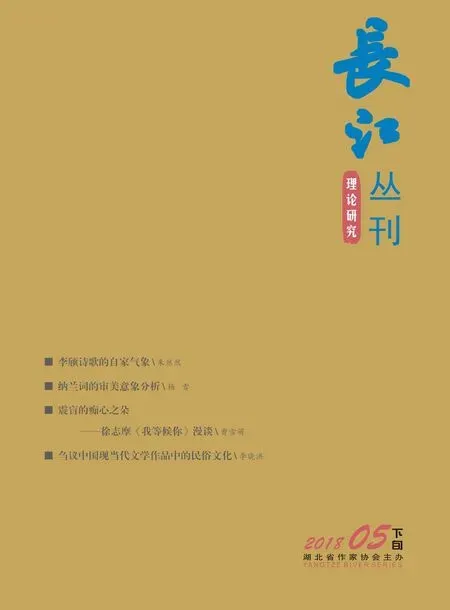试论“敦刻尔克”题材的当代银幕书写
■许若谷 梁紫微/西南大学文学院
好莱坞电影中,大多数历史题材影片能够在历史史实和艺术发挥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借助电影的视听媒介,观众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二度体验”,而电影创作者们根据主题对历史史实进行必要取舍,乃至虚构与夸张,同时不违背基本历史史实,符合电影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兼顾传奇性和真实性。由此,“命题作文”也可以充分发挥创作者的想象和技巧,最终历史史实与艺术发挥和谐相处。借助艺术创作的技巧与手段,历史的魅力穿越时空,呈现在观众面前,其震撼力度,令人过目难忘。
二战历史中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敦刻尔克大撤退”,向来是好莱坞历史题材电影创作中一个重要的题材来源。无论是将其作为故事主体——《敦刻尔克》,还是贯穿故事人物命运的重要节点——《至暗时刻》,作为一个为人熟知的历史事件,在不同的影片中,借助不同的创作手法,观众最终得以看到不同角度的解读。同为2017年上映的两部影片,《敦刻尔克》与《至暗时刻》分别以奥斯卡金像奖的八项和六项提名,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质量。两部影片,如同两面镜子,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全面的展示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历史事件本身,同时,也精彩的回应了历史史实与艺术发挥相互结合、相映成趣的过程。
一、叙事
所谓“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昭示着文本本身的多义性,同时,也隐含另外一层意义,即:文本媒介基于其本身的体裁限制,很难展示给接受主体关于故事内容的全部面貌及里层表意。除去已经表现的内容以外,始终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留白”。“留白”的部分经由“接受主体”的想象和联想填补,由此组成了每一个眼中都不一样的“哈姆雷特”。“敦刻尔克大撤退”作为历史事件,在《敦刻尔克》与《至暗时刻》两部影片中,它的最初接受者,自然是影片的创作者。如同文学作者竭力为读者展现他自己的精神世界,电影导演也通过不同的叙事角度,给观众的视线以引导和暗示。
在电影《敦刻尔克》的开场,渴望从软管中喝到水的嘴和从窗口拿烟的手,以及被枪声打断的解便、六名士兵仅一人逃生,都暗示着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即将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生存困境的故事。浸入式体验搭配汉斯·季默丢弃旋律,更贴近同期自然声的配乐,迅速让观众走进当时困在敦刻尔克中的普通人物之中。《敦刻尔克》将海滩延展至视线的极致,困境中的的英法联军无法填满观众的视线,静默的排队,被风吹起的白色海沫,隐约传来浪打沙滩的绝望嘶吼。观众将情感投入其中又被压抑,仿佛将自己置入历史又被浪花拍打在岸上,挣扎而不可脱。诺兰的《敦刻尔克》,IMAX的巨型屏幕虽然是他作为“作者”的印记之一,但就这一部的作品中的独特意义,是将观众最大限度的拖拽到敦刻尔克这一片绝望的海岸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观众借由人物对当时事件进行二度体验,成为彼时海滩上的一员,是导演诺兰展示给观众的“主观视角”。与看其他故事片不一样的是,观众不会好奇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而是看到影片中人物所看到的,感受影片中人物所感受到的——在一个孤立、危险的环境中,感受恐惧、感受绝望。影片放弃了惯常用于描绘大型场面的宏观视角,转而将视线聚焦于参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普通人——努力求生的小兵,亲身救援的船长,执行任务的飞行员……《敦刻尔克》,并非试图还原“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历史事件,而是为亲身参与其中的普通人立传。在不到两个小时的观影过程中,观众很难记得那些普通人的名字,然而那些细节——当作为道具的担架冲向想像的方舟;当冒牌货被发现;当喷火战机油尽;当“无辜”少年的尸体被轻轻移开;当啤酒瓶从车窗递进来……却令人难以释怀。作为敦刻尔克大撤退事件中,“运筹帷幄”的首相丘吉尔,仅仅是名字屈指可数的出现在人们口中,以及那篇著名的《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的演讲,由回乡的士兵朗诵,在结尾处阐明全片意旨。首相丘吉尔,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正在做什么呢?此时的他,正处于人生之中的“至暗时刻”。
与《敦刻尔克》相互映照的是在电影《至暗时刻》之中,导演乔·赖特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至高的位置,去审视、去垂怜当时背负历史责任的“大人物”。《至暗时刻》作为人物传记片,始终聚焦于丘吉尔似乎理所当然。关于丘吉尔生平的文史资料、纪录片都非常之多,丘吉尔本身也十分喜爱写传记,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此,留给乔·赖特“自由创作”的空间已然十分狭小。如何从历史中已为人们熟知的材料从提取出属于乔·赖特的“丘吉尔”?一个头发稀疏、脾气暴躁、不离烟酒、充满斗志却又会彷徨犹豫的老头,临危受命却又不得不在王室、内阁、议会间如履薄冰的故事成为导演解答这道“命题”的答案。
1940年的英国,其时,德军已经攻克丹麦、挪威、荷兰和比利时,并且绕过马奇诺防线向法国发起总攻,巴黎失守。志得意满的希特勒对伦敦进行轰炸,准备在一周之内拿下英国,是为外忧;王室的不信任、前首相张伯伦与外长哈利·法克斯等上层希望绥靖自保,民众情绪低落,是为内患。这是英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丘吉尔生命中的“至暗时刻”。
同《敦刻尔克》一样,《至暗时刻》中也充满着细节。导演乔·赖特截取了丘吉尔一生中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段生命历程,精心设计了丰富的场面调度。关于乔·赖特娴熟的调度手段,早在《赎罪》留名影史的敦刻尔克长镜头中便已经得到证明。在《至暗时刻》中,虽不强调长镜头的使用,摄影机在场面中却得到解放,在各种视角中游离。在乔·赖特的调度中,机位多次出现垂直俯拍的角度,俯拍尼克尔森准将驻守加莱牺牲时的抬首仰望天空,俯拍经受战火洗礼的法国土地,观众坐在影院,俯视处于当时历史中的人的苦难,生出怜悯,生出崇高。同样,摄影机俯拍丘吉尔陷入绝境时抬首仰望天空,但仰望上天的丘吉尔并没有得到答案,直到他再一次将视线投向街头。《至暗时刻》中曾有两个相似的镜头出现在电影的前段和后段,当他第一次作为首相乘车去唐宁街十号,他望向车外,他主观视角下的高速镜头里人群熙熙攘攘,反打回来的特写中,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悲悯,他怀着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时刻的愿望。而当影片后段丘吉尔步入了自己的“至暗时刻”,他再一次在座驾中隔着玻璃看街头的民众。同样是浮世绘长卷般的画面,此时,拥挤的人群,孩童带着希特勒的面具跑过,战争,已经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心脏。这一次,他已经知道自己不是神,也不会有神来拯救。于是他打开车门,走进人群之中。他需要他们的声音来支持,他的演讲不再囿于广播室,不再囿于议会……他,演讲于人民之中。
二、结构
对于线性结构而言,一般都会遵循单一时间向度的线性原则,按照因果逻辑进行构架,注重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叙事结构完整性。而对非线性电影叙事结构而言,单一时间向度被打破,时间成为不连贯的片段,并根据需要,按照不同顺序进行重新组合。“情节、事件和动作的事理逻辑(因果关系)被(人物的或导演的)主观心理逻辑取代,经典的事理结构就演变成为现代的心理结构。心理叙事线索的介入使得现代电影更加注重非理性的本能和直觉,逻辑性、戏剧性被淡化消解,偶发性往往发展成非线性结构的复合式多声部主题交响。”《敦刻尔克》与《至暗时刻》,恰好在线性结构和非线性结构上为观众做出了各自的回应。
在电影《敦刻尔克》中,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一如既往的展示了自己令人震惊的编织时空的能力,将“一周”“一天”“一小时”的三个不同时间单位非线性的组织在一起。与导演诺兰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在《敦刻尔克》中,诺兰着重展开的是对情绪的铺陈,寥寥数行的字幕和一张宣传单,完成了对影片历史背景进行建置的过程。安德烈·巴赞曾经说过,电影的诞生,源于人们“降服时间的渴望”。于《敦刻尔克》而言,导演诺兰通过对一个已知结局的事件,完美地颠覆线性叙事的结构,以非线性的方式,实现了对时间的“操控”。在观影的过程中,观众沉迷于导演以技术手段营造的时空迷宫之中,忘掉表演,忘掉特效,忘掉音乐,也忘掉故事,完全沉浸于被“操控”的时间之中。阴阳昏晓,今夕何夕,所谓的故事,就在这种精密的嵌套中展开。观众或许试图按照事件的时间顺序重新组织影片的逻辑,然而复杂的结构让观众的努力多少有些难以成功,从而在观影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于“非理性的本能和直觉”。实际上,这样的努力而不得,也许正中导演下怀——在时空逻辑被消解的情况下,戏剧性也被淡化,而偶然性得以放大,个体命运已然被拼接的时间,因为各种关系被再次叠加,从第一分钟到最后一分钟,如同海波连绵不已。从而实现前文所述的非线性结构叙事的“复合式多声部主题交响”。
而在电影《至暗时刻》中,导演乔·赖特多次用几乎占据整个银幕的时间字幕,反复提醒着时间的流逝对事件的发展和人物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影片从丘吉尔临危受命起,到下议院的演讲戛然而止,丘吉尔所做的三次演讲,实际上是其对战争的态度。然而,不同时间所做的演讲,听众给出的反应却并不相同。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从没坐过公交,出任首相多日也不曾进过下议院,始终与普通人群保持距离的“大人物”,在导演的刻画中,由伟人复原为常人。影片很少站在丘吉尔本人的视角来描绘他的想法和情绪,我们就像他的私人秘书莱顿小姐一般,听见他雄伟壮阔的演讲,看见他的脆弱和焦躁。最终让观众目睹了其在内忧外患的处境中,由一个充满弱点的常人,重新成为伟人的过程。同样的转变也存在于《敦刻尔克》,飞行员放弃返航的机会坠入德军包围,普通渔民乔治登上本地报纸,用尽心机试图逃离海滩的士兵,最终受到英雄般的待遇,每一次转变,都是因为他们曾直面最为黑暗的那一刻。观众的情感也在此刻经历升华,欲扬则先抑,似曾相识的故事,依赖于被讲述的方式,重新展示着自身的魅力。无论是诺兰还是赖特,他们将人面临的困境与自身的黑暗展示给观众,巧妙的将黑暗时刻与英雄时刻对比——英雄崛起于黑暗,将光明与希望带给人间。
非线性结构、聚焦于“下”的《敦刻尔克》与线性结构、聚焦于“上”的《至暗时刻》,犹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历史事件中的两面镜子,两位导演以各自不同的诠释,无意间为观众带来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多个层次的解读,构成了一个“敦刻尔克宇宙”。单以各种评分、获奖来判断这一“同题作文”的高下,无疑是武断的,因为优秀的电影,总是给人以更多的生命体验。
注释:
①游飞.电影叙事结构:线性与逻辑[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2):75~81.
——《克里斯托弗·诺兰电影文化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