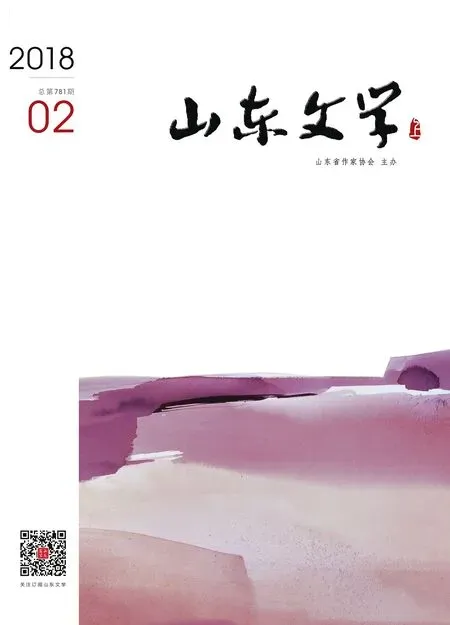鸟声中的乡愁
祖克慰
绣眼:清丽淡雅入画来
一
很偶然的,看到一幅画,是宋徽宗赵佶的《梅花绣眼图》。一只鸟、一棵梅、几朵梅花,景物虽不多,倒也淡雅,只是觉得画面有点暗。我对画不懂,看了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
再看那只鸟,觉得有趣。尤其是眼睛上的白色眼圈,画得很清晰,很显眼。看了那只鸟,感觉很熟悉,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放大仔细看,才知道,画中的绣眼鸟,就是我们家乡的“白眼圈”。
绣眼,在我们家乡叫“白眼圈”。家乡人,对不知名字的鸟,就根据鸟的特点,起个俗名。家乡的凤头百灵,我们叫“角角”;鹌鹑,我们叫“秃尾巴”;麻雀叫“小虫”。
画中的绣眼,是家乡的“白眼圈”,感觉就多了一些亲切。再看画中的梅花,也鲜活了许多,洁白鲜艳。看梅枝,梅枝瘦劲,枝上疏花秀蕊、色泽清雅、清丽脱俗。看绣眼,那鸟活得一般,蹲在梅枝上,左右顾盼,耳边就响起悦耳的鸣叫。清丽的梅花与栩栩如生的绣眼,相映成趣。
绣眼,或者是“白眼圈”,我熟悉的精灵,我应该叫它绣眼,恢复原本属于它的名字。现在,我有必要介绍一下绣眼,我喜欢的鸟。
绣眼,俗名绣眼儿、粉眼儿、粉燕儿、白眼儿等。常见的绣眼是:灰腹绣眼鸟、暗绿绣眼鸟和红肋绣眼鸟,体型及颜色像柳莺。眼睛周围被白色绒状短羽环绕,形成鲜明的白色眼圈,所以得名绣眼。绣眼,是我国四大名禽,爱者甚众。
在我的记忆里,绣眼,它娇小玲珑、羽毛光滑、动作灵活、姿态优美。它的鸣叫,声音圆润、音韵多变、婉转动听。在伏牛山区,我见过的绣眼,一种是红肋绣眼,再就是暗绿绣眼。我的印象中,红肋绣眼的鸣叫比较单调,“唧——唧唧——唧喳——唧唧喳喳”,声音短促,雄性的稍微响亮,但总感觉少了一些韵味。暗绿绣眼鸣叫连贯,节奏感更强,余音缭绕。
当然,这只是我的感觉,很多年了,已经没有听到绣眼的叫声。我现在能感觉到的声音,是二十多年前留存在我记忆中,一种声音的复原。
这么多年,总是忙碌,为生存,奔波在单位与家之间。闲暇之余,也曾无数次走进家乡的山坡,走进伏牛山的深处,追寻豹子、狼、狐狸、黄羊的踪迹。但每次进山,总是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因而忽略了这些小精灵。当我再次想起它们时,绣眼,于我而言,是那么陌生。
是的,它们真的很陌生,那些在山坡上觅食昆虫,在树枝上啄食山果,在花朵上吸食花蜜的美丽小鸟,与我渐行渐远,远得除了那清晰的白眼圈外,我对它们的印象日渐模糊。
很多时候,人都处在一种遗忘状态,那些熟悉的事物,一旦离开视觉范围,就会离开大脑,储藏在岁月的记忆里。有的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消失,在记忆里死去,有的被偶尔触碰,在记忆里醒来。
一幅图画,触碰到我记忆的神经,记忆里,那只被我遗忘的鸟,在瞬间苏醒。绣眼或者白眼圈,就这样,在历经二十多年后,再次走进我的记忆,走进我的内心,或者明天,走进我的视野。
记忆,总是美好的,它会唤醒你对一些事物回忆,让遗忘的场景再现,让枯萎的心焕发生机,让停下的脚步重新迈出。
二
我突然想回家看看,家乡的山坡上,还有没有绣眼鸟。
晚上躺在老家的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我在想一只叫绣眼的鸟。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反复地出现,可我记不清在哪里看见过它。
是在我家乡的山坡上,一片林子里?是在地处伏牛山深处的崔庄乡的某一座山林里?还是在县城的青峰山?似乎是,似乎又不是。也许,我在家乡的山坡上看到过,在崔庄乡的某一座山林里看到过,也在县城对面的青峰山看到过。我无法否认,我真的看到过它们,这些我常去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
我在无眠中,等来黎明。
窗外传来一阵鸟鸣,鸟鸣声很熟悉,是麻雀。我突然想起,这种叫绣眼的鸟,就是在我老家的山坡上看到的,我初次看到它们时,是和麻雀、百灵混在一起。那时候看到一只色彩艳丽的鸟,感到很惊奇,记忆也深。
其实,绣眼在我们家乡很容易看到,只是我们长时间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伏牛山深处有,我老家有,崔庄乡的山林里有,县城对面的青峰山也有。我在老家时,看到的绣眼,大多是红肋绣眼。在伏牛山深处的大山里,还能看到暗绿绣眼。
第一次看到他们,是在老家西沟的山坡上,那时候西沟还没人烟,西边是一片松林,东边是一片柿子林,横竖成排,一棵接着一棵,把西沟的山坡覆盖。深秋时节,柿子树上挂满了红色的果实,成群的鸟,在柿子树上蹦来跳去,吸食柿子的果浆。
柿子成熟时,我们一群孩子常到西沟摘柿子,那天去摘柿子,看到一群鸟在吸食树上的柿子。看到鸟与我们争食,很生气,就弯腰捡起一块石子,准备轰鸟。突然就看到一群色彩鲜艳的黄绿色小鸟,混在鸟群里,这是一种我们没有看到过的鸟,很稀奇。后来在山坡上也看到过这种好看的小鸟,问大人才知道,这鸟,叫“白眼圈”。
年少时,对啥都好奇,看到美丽的小鸟,总想抓一只养,但这种鸟很胆小,离人很远,稍一靠近,就惊恐而飞。那时就想,有鸟就有鸟窝,抓不到大鸟,就抓一只小鸟养养。我们在山坡上瞎逛,希望找到它们的窝。但在山坡上、树林里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它们的窝。
记得问过父亲:“山坡上那么多白眼圈咋找不到鸟窝?”父亲说:“它们的窝,在五朵山的山林里,它们到咱这里玩玩就回去了,你当然找不到。”五朵山是伏牛山的主脉,离我们家二十几里远。父亲这样说,可能是想阻止我们抓鸟。
因为找不到鸟窝,就断了养绣眼的念想。其实,我们也在山坡上看到筑在树上的鸟窝,只是树太高,又细小,我们爬不上去。现在想来,挂在树上的鸟窝,可能就是绣眼的窝。
吃过早饭,我走向山坡。山坡已不是我少年时代的山坡,原来山坡上长满了树,现在的山坡光秃秃的。山坡上的梯田,有的种着花生,有的荒废着,长满了草。一片荒地上,长着紫花地丁,开着细碎的紫花,在微风中摇摆。翻白草一棵挨着一棵,开着黄色的小花,这种草我最熟悉,小时候拉痢疾,挖几棵翻白草,用根熬茶,一喝就好。还有一棵棵的棉花条,也开紫花,一嘟噜一嘟噜地开满枝条,那紫,让人陶醉。走下山坡,是一片豌豆,还是紫色的花,风一吹,紫蝴蝶在绿叶间翩翩飞。
这都是我熟悉的植物,有的叫得上名字,有的叫不上名字。但它们还长在这里,用花一般的笑脸迎接我。可那些我熟悉的松树、槐树、柿树、酸枣、栗毛,它们已不见踪影。空落落的山坡,让我的心徒添寂寞。
有几只山雀,落在一片草地里,在草丛中啄食着什么,可能是一只虫子,也可能是去年遗落的草籽,或者是一只蚂蚁。我不知道山雀吃不吃蚂蚁,也许吃,也许不吃。这个春天,不吃点蚂蚁,山雀还能吃什么?
南洼的那座堰潭,里面长满了水草,堰潭里有鱼、河虾、青蛙、泥鳅、黄鳝,堤坝上长满了油桐、柳树,很多鸟落在树上,时不时飞到堰潭,在水中捞出一条小鱼,或者是一只河虾。每年春天,这里的鸟,叽叽喳喳,吵闹不休。
走到南洼,看到堰潭已经被泥沙淤平,只有潭底,还有一汪水。走近看,水很清,没有一棵水草,没鱼也没虾,更没青蛙黄鳝,水清无鱼,这话不假。堰潭的四周,原来都是树,现在一棵也没有,都是梯田,梯田里都是花生。堰潭里的泥沙,就是从花生地里冲下来,淤积到堰潭里。堰潭的堤坝上,还有几棵树,一棵树上有一个喜鹊的巢,一只喜鹊,蹲在巢里,看到人来,伸一下翅膀,飞走了。
绣眼,最终还是没有看到,这也在意料之中。只是,常见的百灵、鹌鹑、斑鸠、山雀,都没几只,却让我心生落寞。此刻,空旷的原野上,只有我一个人,很孤独地站在山坡上。
三
又想起宋徽宗赵佶。作为皇帝,生活奢侈,任用奸臣,仅此,赵佶肯定不是个好皇帝。是的,赵佶不是好皇帝,但绝对是个好的艺术家。他自创的书法被称为“瘦金体”,他的花鸟画自成“院体”,是少有的艺术天才。
赵佶的《梅花绣眼图》让我感到惊奇,久居深宫的赵佶,能把一只绣眼画得如此传神,没有对绣眼生活习性有着深刻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宫廷里可能会养绣眼,但圈养在笼中的鸟,不可能有大自然里的鸟那么灵动。
梅花自不用说,是宫廷的梅花,作为皇帝的赵佶,对宫梅是熟悉的。宫梅经过不断剪枝,人工修饰痕迹较重。此种梅的画法精细纤巧,敷色厚重,弥漫着一种富贵气息。风格趣味,无不代表着皇家的审美意味。
但清丽脱俗、活灵活现的绣眼,绝不是宫中笼养的鸟可比的。看了这幅画,我就觉得,赵佶在画这幅画前,是多次看到过生活在大自然里的绣眼的。开封是平原,紧邻黄河,如果去山中,也只有万岁山。万岁山是皇家园林,山不高,但树很多,有树就有鸟。赵佶看到的绣眼,大概就是万岁山中的。
对江山疏于管理的赵佶,对艺术是认真的。我想,在画这幅画时,赵佶走进了皇家园林,走着走着,就看到了一只鸟,蹲在一株梅花的枝条上,于是,就有了这幅传世之作。
也或者,赵佶看到笼中的绣眼,突然心血来潮,想画绣眼。于是,赵佶就去了万岁山,想看一眼生活在大自然里的绣眼。于是,赵佶就真的看到了一只绣眼,蹲在一株梅花的枝条上。赵佶觉得,这只鸣唱的绣眼,是那么可爱,可爱得让他心动。于是,赵佶就画了这幅《梅花绣眼图》。
再或者,一日闲来无事,皇帝赵佶带着皇后郑氏,在万岁山皇家园林散步,两人走到一株梅花树前,看到了画中的绣眼,回去后,徽宗皇帝就在皇后的协助下,完成了这幅《梅花绣眼图》。说到这里,不能不说郑皇后,郑皇后儒雅秀丽,多才多艺,对徽宗的书画词章有着独到的见解,徽宗对郑皇后十分地宠爱。我想,赵佶画这幅画时,郑皇后一定在场,而且赵佶也一定征求过郑皇后的意见和建议。
其实,这幅画是怎么画的,我也不知道。上面的几个场景,只是我的猜测,或者是我的想象。不是我不知道,大概很多人也不知道。知道的人,也随着徽宗赵佶故去,消失在漫漫黄尘中。
但这幅画还在,画中的绣眼还活着,活在一张纸上。一千多年过去了,你看到它时,它依然对着你,不停地鸣叫。
四
我看到了绣眼,它们的鸣叫,还是沉在我记忆里的声音,还是《梅花绣眼图》中那只绣眼的鸣叫声,一波又一波,一阵接着一阵,此起彼伏。
2016年5月,我登上了五朵山,五朵山是伏牛山中著名的道教圣地。南召五朵山与“南顶”湖北武当山齐名,素有“北顶”之称。山中奇峰相峙,飞瀑高挂,怪石林立,泉流潺潺,春天杜鹃烂漫,夏日绿意盎然,秋季层林尽染,冬季银装素裹,山水如诗如画,被誉为“音画山水,伏牛仙境”。
五朵山生态保护完好,山中生长着红豆杉、银杏、秦岭冷杉、水曲柳、化香、马尾松、水杉、侧柏等数百种树木,郁郁葱葱的树,把一座山遮蔽。因为生态完好,这里生活着百灵、画眉、黄鹂、绣眼、斑鸠、鹌鹑、山麻雀等一二百种鸟,走进五朵山,就走进了鸟的家园。
我去五朵山时,正值春夏之交,山中树木茂密,遮天蔽日。树下,是开满花朵的灌木和花草,不时有鸟从头顶飞过,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声。
去五朵山,似乎没有目的,就是去山上转转,放松一下心情,也似乎有着明确的目的,去寻找一只叫绣眼的鸟。与文友去五朵山时,我没有说去干什么,就是去玩。玩,大家都不反对,每个人的内心,都承受着沉重的工作生活压力。也许,只有走出去,走到大自然,才是缓解压力的最好办法。
从五朵山主峰下来,我们直接去了五朵村,那是一片玉兰林,站在山顶上,白色的花朵,格外地耀眼,吸引着我们。此时,花正开,洁白的玉兰花,散发着阵阵芳香。走在玉兰树林,就走进了花的家,香的源。走进玉兰树林,其实也走进了鸟的世界,“唧溜溜、嘀呖呖、啾啾啾”,清脆的鸟鸣,不时撞击着耳膜。鸟语花香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
山里的鸟真多,“咯咯咯咯”叫的是锦鸡,“唧唧啾啾”叫的是画眉,“嘀呖呖”叫的是百灵,“咕——咕咕”叫的是斑鸠,还有成群的麻雀“叽叽喳喳”。每看到一种鸟,大家就会发出一阵惊叫,震得树叶簌簌地舞,花瓣翩翩地飞,林子里飘着青蝴蝶、白蝴蝶。
大家疯兴正浓时,一群鸟掠过树梢,哗啦啦落在林子里,有的落在树枝上,有的落在灌木上,有的落在石头上,还有的落在草地上。这鸟,十分好看,羽色鲜艳、嘴尖细、身腰长、羽毛光滑紧凑。大家屏着呼吸,生怕惊动了鸟们。仔细看,这不正是我要寻找的绣眼吗?是的,是绣眼,红肋绣眼。
这群绣眼,有数十只,甚至上百只,这么大群的绣眼,让我惊奇。在我的记忆里,从没有见到过如此多的绣眼鸟。记得在山坡上看到最多的绣眼鸟,也就二三十只。那时候的二三十只绣眼鸟,看得我们眼珠子都要蹦出来,难怪大家看到绣眼鸟时,惊得大气都不敢出。
正在大家瞪着眼看时,突然响起一声梆子腔:“要吃还是家常饭,要穿还是粗布衣,知冷知热结发妻……”绣眼可能是受到了惊吓,鸣叫着飞走了。抬起头看,是两个砍柴的老乡,担着挑子,唱着曲走了下来。
我走过去,打声招呼,递支烟,老乡放下柴火挑子,点着烟,抽了一口说:“来玩啊!”我问:“咱山里的绣眼鸟多吗?”老乡说:“绣眼,啥绣眼?”我说:“就是刚才飞走的那群鸟。”老乡笑了:“那鸟啊,多着呢,有时候三五只,有时候十来只,有时候上百只,还有时候一天不见一只。不过,上百只的鸟群不多见。”
原来,看鸟也需要机缘,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的。我老家的山坡上,不是没有绣眼,是我没有看到而已。
这样想时,就又想起徽宗赵佶。赵佶与绣眼,就有机缘,那天赵佶去了万岁山,机缘巧遇,看到了绣眼,于是,赵佶就画了一幅《梅花绣眼图》。巧的是,这幅图保存完好,流传了下来。更巧的是,我在写绣眼之前,看到了这幅画。于是,就有了这篇文字。
据说,绣眼喜欢在灯下唱歌,鸣叫声有高、中、低三种音调,听起来有的带水音,有的似虫鸣,还有的能叫出夏蝉的音调。可惜,我没有听到,这可能是机缘未到吧。
白头鹎:飞来飞去落谁家
一
在五月的花海里,在灌木丛中,在稀疏的林子里,白头鹎,它们在飞翔。你也可以说,花丛中的白头鹎,它们与花朵,一起绽放。
白头鹎,在我们家乡也叫白头翁。如果你说白头鹎,恐怕没人知道,但你说白头翁,几乎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名字。因此,我想把它们的名字,还原成家乡人熟悉的名字:白头翁。
在伏牛山区,在众多的鸟中,白头翁是一种极其平常的鸟。它们头顶白色的羽毛,在山坡、丘陵、草地上飞来飞去。白头翁性格活泼,不大怕人,在树枝间跳跃。如果没人惊动它们,很少飞行,偶尔起飞,也是短距离飞行。更多的时候,它们蹲在树梢上,“叽叽喳喳”地叫,叫声婉转。
这种类似于麻雀的鸟,和麻雀一样,随处可见。在乡下,人们把麻雀叫作“小虫”,把白头翁叫作“白头小虫”。如果从形体上看,它们确实与麻雀无异,甚至叫声,也极其相似。白头翁与麻雀唯一的区别,是羽毛。麻雀的背部栗色,灰白相间。白头翁的腰背部则是灰绿色,翅膀和尾部稍带黄绿色。如不仔细观察,还真能把它们当作麻雀。
我一直觉得,白头翁只是乡村的鸟,它们是属于乡村的。我在乡下时,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它们的存在。只要有树林,有草地,有果园,就有它们的身影。甚至城市的公园、行道、阳台、树木上,也经常看到它们。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白头翁,它们不仅属于乡村,也属于城市,这是为数不多的寄居在城市的鸟。因此,有人把白头翁、麻雀和绿绣眼,称为“城市三宝”。
何以把白头翁、麻雀和绿绣眼称为“城市三宝”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它们之所以被城市人当作宝贝,很可能是源于它们美妙的歌声。是的,当城市人被机器的轰鸣声、汽车喇叭声、喧嚣的吵闹声淹没时,能听到美丽的鸟鸣声,该是多么幸福。也许,一声鸟鸣,唤起的是记忆中的田园风光。
我在单位的院子里,看到成群的白头翁,也见过它们筑的巢。单位在南阳市李宁体育园,这里风景秀美、绿树掩映,有数十种鸟生活在这里,白头翁就是其中之一。每年三到五月繁殖季节,总能看到白头翁在树丛中筑的巢。巢的形状碗形,多用枯草的茎和草穗。鸟巢筑在树丛中,很隐蔽,一般不仔细寻找,很难看到。甚至在阳台的花木中,你也可以看到它们的巢。
每年春天,是白头翁繁殖的季节,如果细心,你就会发现,一只白头翁出现在树枝上,不停地鸣叫,那是它们在用歌声寻找配偶。如果你看到另一只白头翁飞来,两只鸟一唱一和,那就是它们在唱情歌。接下来,它们会选择在灌木丛中筑巢,然后繁育后代。一般一年一到两次,每窝产卵3至4枚,一个月时间,就有小鸟出巢。
白头翁的食物很杂,它们喜欢昆虫,尤其喜欢蝗虫、蝇蚊、蚂蚁、蝉虫,甚至蛇、蜂、蜘蛛,都是它们喜欢的美味。它们也吃植物的果实和种子,山楂、桑葚、苦楝、葡萄等,果子成熟季节,时常飞入果园偷吃果实。很多果实上的累累伤痕,应该归功于白头翁。
现在,我们单位的院子里,还有成群的白头翁飞来飞去。我在去年白头翁筑巢的地方看了看,去年的旧巢还在,但巢的主人已不知去向,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鸟窝。看来,白头翁是没有记忆的,或者,它们没有故乡观念。作为自由的鸟,没有故乡记忆是一种大的胸怀,是四海皆我家,天涯任我行。
二
乡村是鸟的世界,在乡村大世界里,生活着无数的鸟,很多鸟,你看到过,但很快就忘记了。我喜欢鸟,对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爱,面对数不清的鸟,你很容易忽略它们。比如我,看到过很多鸟,叫不上来名字;还有很多鸟,知道它们的名字,但忘了它们的模样。
很多鸟,你之所以记得它们的模样,记得它们的名字,是因为它们的与众不同。当然名鸟是不会忘记的,它们的知名度高,早已记住了它们的名字和模样,比如孔雀,比如百灵、黄鹂。还有那些丑陋的鸟,你也容易记住,比如乌鸦、寒号鸟。还有一些鸟,是大家族,经常在你眼前晃来晃去,比如麻雀、燕子。而那些平凡的鸟,你就很容易忽略。如果一种极其平凡的小鸟,让你过目不忘,这鸟,一定有显著的标志,比如白头翁。
是的,白头翁,这是一种你看一眼就无法忘记的鸟。
我第一次在山坡上看到这小小的精灵,看到它们头顶上那片白色的羽毛,我就很奇怪,为什么它们的头顶上长着白色的羽毛,而不是红色或者绿色,再或者是蓝色的呢?
这鸟,第一次,就让我记住了它们的模样,从此就刻在了心中。
这鸟,看一眼,你就会喜欢一辈子。
这鸟,你喜欢就想拥有,就想与它朝夕相伴。
我在乡下时,喜欢养鸟,但唯独没有养过白头翁,没养白头翁,并不是我不喜欢这种鸟。记忆中,我们村庄里没有人养过白头翁,因为没有人养过,不了解它们的习性,没有经验,怕养不活。其实,养鸟对于养鸟人来说,是喜欢,但对于鸟来说,是一种伤害。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没有这样的意识,我觉得,我喜欢鸟,把它们养起来,就是对鸟的爱。
对于生命的爱,不应该是自私的,因为,生命是独一无二的,是珍贵无比的。爱不是囚禁在笼子里,爱是自由的。
我很长一段时间,盯着它们头上的白色羽毛,那片白色的羽毛,特别地耀眼。我甚至在很远的距离,在树的枝头上、在凝绿的灌木丛中、在灰褐色的土地和草丛上,通过头顶上的白,认出它们。我喜欢看它们在田野里寻找农人遗落的谷粒,在草丛中悠闲地寻觅草籽,在山坡上追逐一只蚂蚱,那活泼、伶俐的身影,总是吸引着我的目光。
那片白色的羽毛,一直让我纠结。我想,一片白色羽毛里,一定有一个故事。父亲告诉我,白头翁原来头顶上不是白色羽毛,是一片红色的羽毛,血红血红的羽毛。
父亲说,在很远古的时代,一片森林里,生活着一种聪明的小鸟,头上长着一撮火红的羽毛,模样很可爱,很多鸟看见它,都很喜欢它。
小鸟觉得,如果自己多学点本领,那不更讨大家喜欢吗?于是它决定学本领。它找到喜鹊,请喜鹊教它搭窝。喜鹊告诉它,搭窝很累,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衔树枝、草和泥巴,小鸟怕把自己的嘴啄破,就放弃了。
黄莺的歌声很美,它就想跟着黄莺学唱歌,黄莺说学唱歌要先吊嗓子。开始觉得很新鲜,但学了几天就厌烦了,于是,小鸟就不辞而别。
它后来跟老鹰学飞行、跟鸬鹚学打鱼,但都半途而废,最终一事无成。头上的红羽毛也变成白羽毛,小鸟依然没学到本领。为了让子孙后代吸取这个教训,它的子孙后代一生出来,头上都有一撮白羽毛,于是,大家都叫它白头翁。
我听后,深不以为然。我觉得,白头翁是很勤奋的鸟,整天忙忙碌碌地筑巢、孵卵、捉虫子,繁育后代。它们的歌声,优美动听,与黄莺相比,各有千秋,并不逊色。它们的飞翔,虽比不上雄鹰,展翅凌空,但也姿态优美。它们虽没有鸬鹚打鱼的本领,但捕捉昆虫的本领是鸬鹚无法可比的。
多年以后,我已长大成人,但无所事事。为了让我学到一种安身立命的本领,父亲让我跟着他学唱戏。父亲唱曲剧,从家乡南阳唱到洛阳、平顶山,又唱到湖北襄樊、老河口,唱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也唱出了家中的柴米油盐。父亲让我学曲剧,我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父亲不甘心,就在家中教我,我跟着父亲学了半月,连戏词也记不住,唱着唱着就忘了词。最终,还是放弃了。
后来母亲又让我学木匠,母亲说,木匠很吃香,谁家不用家具,到什么时候,乡村都离不开木匠,你学会了木匠,到时候吃香的喝辣的。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乡村的木匠,终究会失业的,因为我看到,家具店已经开到了集镇上,而且做工精细,花样翻新。乡村木匠用老手艺做出的家具,将逐渐被时代淘汰。
对一种事物的认知,来自于自己的判断,我对白头翁的观察,让我很快否定了父亲讲述的故事。我觉得,我所看到的白头翁,是一种美丽勤奋、活泼伶俐、机灵可爱的小鸟。而不是父亲故事中,那种懒惰、奸猾的鸟。
白头翁头顶上的白,在我看来,是一种标新立异,是一种与众不同,是一种自我个性的张扬。
三
鸟是有情感的,它们把感情融入在行动中,是无声的。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对异类带有一定的排斥性,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它们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有情义的动物。
我早年写过一篇《鸟泪》,当我们从鸟巢里抓出套住的母鸟,母鸟拼命地挣扎,最后看着鸟巢里的幼鸟,绝望地流出了一滴伤心的泪水。这篇散文很多人认为是虚构的,不停地有人质疑。他们问我:“克慰,你真的看到鸟流泪了吗?”“鸟会流泪吗?”
记得《狗能记住回家的路》发表后,也有人不停地质疑,认为一只狗离开家乡一年多后,从三四百里的新家回到原来的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乡村,有这样的俗语:“狗记千,猫记万,老母猪只记二里半。”事实上,这样的俗语,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觉得,猫根本记不住万里的家,狗就更不用说,这样的俗语,是夸张的说法,不足为信。
鸟会流泪,是因为母爱,鸟不是为自己流泪,是为巢中嗷嗷待哺的幼鸟,那是亲情,是母爱之情。狗能从数百里之遥,在离开主人一年多后回到原来的家,也是情,是感恩之情。我们不能因为它们是低级动物,就忽视和否定它们的情感。
发一则关于白头翁的信息:今年5月14日,在湖南武冈市自来水公司大院里,一只白头翁不知何故意外死亡,另外一只白头翁哀鸣着从枝头上飞下来,展开翅膀护住了众人脚边那只死去的白头翁。它抓拖着、奋飞着,想将同伴带走。可白头翁无法抓起同伴飞离,但却不甘罢休,不停地尝试着。人们发现,在白头翁的努力下,将死去的同伴拖出了二米多远的距离。每次尝试过后,它就仰头长鸣。死去的鸟儿脖子上的羽毛被抓掉,渗出血迹,拖出的距离在不断增加,最后,大院保洁员将死鸟移走了。但是,它仍然不愿离去,一整天都在院子里悲哀地鸣叫,十分凄婉。
这是我从网上看到的信息,是否真实,不得而知。但我相信,这则消息是真实的。因为去年春天,我在单位的院子里,看到了同样的一幕,不同的是,那只鸟是一只绣眼。
那天早上,一只雄性的绣眼,误入单位的走廊,走廊是用蓝色的玻璃封闭的,绣眼鸟飞进走廊后,受到了惊吓,在走廊里飞来飞去,可能是急于脱逃,误把玻璃当蓝天,一个劲地往玻璃上撞。十多分钟后,绣眼鸟从撞上去的玻璃上掉了下来。我走过去,想把它捡起来放到窗外,没等我走近它,它就惊恐地飞起来,然后一头撞在玻璃上,摔在水泥地上,嘴一张一张地呼吸。我想把它扶起来,但扶了几次又倒了下去。可能是撞晕了吧!我把它放到院子里的草坪上,心想,休息一阵,凉风一吹,它就醒了过来。
中午下班,我特意去看绣眼鸟。很远就看见,有一只绣眼鸟,在草地上蹲着,它的身边,躺着一只绣眼鸟,一动不动。我走过去,惊飞了蹲着的绣眼鸟,它“唧”的一声,飞到了草坪边的玉兰树上。而那只躺在地上的绣眼鸟,早已没了呼吸。那只惊飞的绣眼,蹲在树上,不停地凄厉地鸣叫,始终不肯离去。
几年前,我在老家的山坡上,看到两只白头翁勇斗伯劳,那场景令我震撼不已,它们让我看到了弱者面对生命,所产生的强大的牺牲精神。
那天回家看母亲,闲时去山坡上走走,在一片空旷的草地上,两只白头翁很悠闲地在草地上觅食。突然,从松树林里飞来一只伯劳,扑过来就啄一只白头翁,就在伯劳扑倒白头翁的一瞬间,另一只白头翁飞扑过来,在伯劳的头上狠狠啄了一口。伯劳放下地上的那只白头翁,反扑过来捕抓啄它的那只白头翁,而刚才被伯劳扑倒的那只白头翁,迅速地扑上去,猛啄伯劳。两只白头翁啄、躲、闪、跳,与伯劳打来打去,勇猛无比。
伯劳有“雀中猛禽”之称,但面对两只勇敢的白头翁,毫无办法,被打得身上的羽毛纷落,最后落荒而逃。两只白头翁飞落在树梢上,“叽叽喳喳”地大声鸣叫,好像是在祝贺自己的胜利。
现在单位的院子里,每天都有数十只上百只白头翁,在草坪上、在树枝上、在竹园里“叽叽喳喳”地鸣叫,我时不时走出办公室,站在院子里看着它们,与它们长久对视。
我觉得,这些小精灵们,值得我注视,或者是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