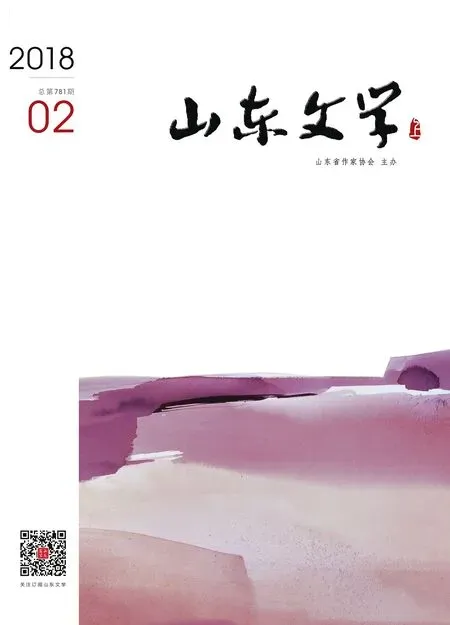消失的村庄
刘浪
一
村里最后一个年轻人走了,剩下一堆老人。这个年轻人和所有之前走的年轻人一样,轻装上路,不像要出远门。临行那天,他照例撇一句,我会回来看你们的,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老人们揉着眼睛,目送他向天地的接缝处走去。他们知道,这是最后一眼,年轻人将被永远缝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回不来了。
但是,多年后的黄昏,这个年轻人又站在了村口,身上落满尘埃。他像被一场风刮到远处,绕了一圈,又被另一场相反的风刮回来。其间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的头发变白了,视力衰退了,牙齿脱落了,身体佝偻了,成为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东奔西跑大半生,岁月还是追上了他,把他收拾成现在这样。落日如旧,老人凝视前方,浑身开始颤抖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生他养他将来也必定埋葬他的村庄,竟然消失不见了。
房子不见了,牲口不见了,树不见了,路不见了,田不见了,荒草连天,全都不见了。如果不是村后那座标志性的山坡,他几乎以为自己走错了路。但这就是他的故乡,没有错,山坡上散落的坟茔,尤其证实了这一点。
这是王木匠,这是李寡妇,韩三也在。还有刘傻子、孙独眼、周疙瘩……
老人一边走,一边弯腰去认墓碑上的文字。一个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如今都进入了文字,凑成一份死亡名单,在老人口中轻声念着。老人若干年前离开他们,从未想过若干年后会是这样的见面方式。
都死了,一个也不剩……
老人喘息着,一屁股坐在坟堆中间,喃喃道。
二
年轻人走后,这个村庄最大的事情就是准备死亡。
死亡和出生一样,是人生大事,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准备。村里曾经有一个人,忙乎了一辈子,别人都闲下来准备自己的后事,他还在忙。直到他要死了,躺在炕上,十几天都闭不了眼,村长让他安心去吧。他呆呆地望着屋顶,说现在要死了,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人到老年,就会遇到各种孤独和病痛,干什么都费劲,吃什么也没味儿,看似没啥活头。但他们很少会选择轻生,相反,他们比年轻人更懂得活着的可贵。老年是天然为死亡准备的,老年的孤独和病痛,是一种死亡训练,经过训练的人,身心得到调整,就不那么惧怕死亡了。
人到死如果还怕得要死,那就太该死了。
准备死亡,首先需要储存充足的粮食。全村的老人趁自己还能下地干活,都把余生的活放到这几年里干完了。干到啥程度才算完,这里有一笔账。先看自己还能活几年,再估摸吃多少粮食,吃多少种多少。并非越多越好,有人野心勃勃地种了够吃五年的粮食,结果第二年就死了,累死的。也有人以为自己挨不过明年,早早地收起农具,回家歇着等死,但是到了明年,没死成,后年又没死成,大后年才姗姗死掉。这种情况就要依靠别人的接济度日了,后死的有义务接济先死的。先死的若留下粮食,就要分给后死的,没有年轻人管他们,他们只能互相养老,互相继承遗产。
其次需要妥善安排死前的生活。活干完了,粮食也够了,就把圈里的牲口放出来,让它们自己去野外觅食吃。秋天割好干草,垛在棚顶,帮助它们熬过漫漫长冬。牲口为主人卖了一辈子的命,现在也该享受主人为它们做点什么了。主人也为自己劈好柴火,码在墙角,以备过冬之用。天晴的时候,就到太阳底下抽烟打盹儿,晒晒骨头里的寒气。碰到大雪封山,就糊好窗户,挂上棉门帘,坐在黑黑的屋子里,偎着火炉取暖。这点温暖虽可抵挡屋外的冬天,对于生命里的冬天,却显得无能为力。锅还能将就用两年,暂时烧不透,灶拿砖头垫垫,也没什么大问题,烟囱得趁腿脚能动爬上去捅最后一次。院墙太薄,要拍几锨泥,檩子不结实,算球了,塌了当棉被盖,就看自己和房子,谁耗得过谁。
最后需要准备衣服和棺材,衣服由老太婆亲手缝制,样式颜色任你选,保证称心如意。棺材是个技术活,一般人干不了,村里只有一个姓王的木匠能担此大任。村长提议,王木匠不用下地,就在家里做棺材,他的粮食由大伙儿分摊,众人附议。从此,王木匠家里就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和鸡鸣狗吠一起,成为这个村庄的一部分。
王木匠也有一笔账,他要赶在自己伸腿前把所有人的棺材做好。村里共有二十八个老人,要做二十八口棺材,这是一项不小的工程。王木匠夜以继日地赶工,和当年跟老婆在炕上要孩子一样的热切。老人们只要得空,就会跑来探视,递递工具,唠唠嗑,问问进度。有时他们好像等急了,一天探视四五回,生怕自己撑不到棺材做好的那一天。
一切准备妥当,心无挂碍,便把自己关在封闭的屋子里,提前适应死后的孤独和黑暗。死亡来了,就跟着它去。
三
第一个死的,是王木匠。
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人们干完活回来,村里静如太古,连鸟雀都缄默了。正常情况,是能听到王木匠敲打东西的声音的。村长瞧见刘傻子蹲在树下看蚂蚁,就问他,王木匠呢?刘傻子说,死了。全村人急忙赶过去,发现王木匠倒在一具半成品棺材旁边,手里捏着鲁班尺,脸上带有一丝余业未竟的恨意。这是第二十八口棺材。前面二十七口都已经上好漆,停在后院棚子下,用条凳搁着,像一辆辆等待客人的车。谁也想不到,王木匠会是第一个客人。
王木匠的死太突然,来不及准备。村长说,他把人生最宝贵的用来准备自己死亡的时间,都用来准备别人的死亡了。
大家念着他的好,很隆重地为他举办葬礼。
出殡那天,下着微雨,四个腰背硬朗的老头扛着棺材,向事先挖好的墓穴走去。全村人身披白色丧服,垂手跟在后面。李寡妇双目红肿,早已哭成了泪人儿,中年丧夫的她对晚年丧妻的王木匠有意,平日秘而不宣,直到今天才表露出来。走到墓穴,要下葬了,李寡妇哭天抢地,趴在棺材上,狼狈得像个乞丐。众人拉开她,七手八脚地放下棺材,铲土埋掉。李寡妇因为悲伤过度,晕了过去,最后被众人一脚水一脚泥地拎回村里。
回到村里的李寡妇水米不进,没几天就死了。全村人都说,王木匠前脚刚死,李寡妇就后脚追了上去,他们应该会在天堂相逢吧。李寡妇的遗愿是与自己的亡夫合葬,全村人却擅自把她和王木匠葬在一起,就是为了撮合这对死去的鸳鸯。
此后,死亡成了这个村庄的家常便饭,有时一个一个单独死,有时几个几个扎堆死。他们从不事先打招呼,你以为他们活得好好的,活着活着就没了。今晚有多少人合眼睡去,明早未必有多少人睁眼醒来。空气中会忽然少了一个人的呼吸,你无法察觉,死了,就抬过去埋掉。开始还有哭声,后来只是啜泣,最后无声无息。葬礼一次比一次冷清,上一次还跟在棺材后面送行,下一次就躺进棺材被人送行。
直到有一天,大家猛然抬头,村里只剩下五个人了。
村长还活着,他把另外四个人召集起来。这四个人分别是:韩三、刘傻子、孙独眼、周疙瘩。村长说,把你们叫来,是要商量几件事,现在全村死得就剩咱五个了,往后的日子咋过,得有一个规划。你们先把家里的粮食、牲口情况汇报一下,一个一个说。
韩三先说。韩三说,两缸米,半缸面,一头牛,一口猪,六只鸡。孙独眼说,一缸米,一缸面,一头驴,两只羊,四只鸡。周疙瘩说,两缸米,一缸面,一口猪,三只羊,没鸡。村长说,咋没鸡呢?周疙瘩说,吃了。轮到刘傻子,他还愣愣地看着油灯出神。孙独眼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没反应。村长说,他家的情况我知道,不用说了。照你们说的,都还够吃,啥时候不够了,再到我家来拿,周疙瘩待会儿捉两只鸡回去。
村长顿了顿,接着说,咱们都快活到头了,蹦跶不了几年,我和孙独眼、周疙瘩离得近,走两步就能到,韩三你就不行,住在村西头,隔那么远,喊破嗓子都听不见,我建议你搬过来,住在王木匠家。刘傻子他姐刚死,没人照顾,也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大家挨在一块儿,好有个照应。韩三说,我一辈子没挪过窝,对那房子有感情,就是死也要死在那儿。我每天放牛都会打这儿过,哪天你们看不见我了,就直接去我家收尸。村长等人面面相觑,默然无语。
村长又说,还有一件事,咱们要提前做。虽然咱们有五个人,但劳动力只有四个,要是这四个中间再死一个,谁来抬棺材,总不能叫刘傻子来抬吧,所以我的意思是,趁咱们还活着,提前把墓穴挖好,把棺材抬进去。谁死了,就背到墓地,在那儿入殓,背死人一个劳动力就够了,这叫人犹未死,棺材先行,出殡在入殓前面,你们看怎么样?孙独眼、周疙瘩纷纷表示赞成。韩三说,可是棺材不够,王木匠就做了二十七口,现在剩四口,那个半成品没法儿用。周疙瘩挠头说,对呀,这倒是个问题。村长说,四口先用着,我再想办法。事不宜迟,明天开始行动,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四
事实上,他们刚把墓穴挖好,把棺材抬进去,就有人死了。
死的是韩三。整个白天,村长没见他出来放牛,问孙独眼看见没,孙独眼说没看见,问周疙瘩看见没,周疙瘩也说没看见。村长说,出事了。三人去村西头,赫然望见韩三的房子倒了,四面墙只有一面站着,瓦砾撒得遍地都是。昨晚既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雨,好端端的房子,怎么就倒了呢?三人徒手挖掘,把韩三从废墟里拽出来,冷硬冷硬的,已经没救了。红日西斜,孙独眼、周疙瘩坐在地上喘气。村长说,抬去埋了吧。
对于房子为什么会倒,村长的解释是,不为什么,房子到寿数了,自然会倒。任何从土地上站起来的事物,终会归于尘土,因为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你一站起来,就会有东西消磨你。风要来吹你,雨要来淋你,阳光要来晒你,蝼蚁要来掏空你,积年累月,直到把你抹平为止。韩三的房子也许早就不行了,早就在等一个轰然坍塌的理由。韩三上炕睡觉,也许不动就没事,他一翻身,或者一打呼噜,房子就撑不住了。没人能救韩三,这是他跟房子之间的私事,谁也插不上手。
埋掉韩三,分了他的粮食和牲口,四个人继续把日子过下去。他们在墓地搭起草棚,用油布裹住棺材,以免雨水落进墓穴,将棺材沤烂。这是他们最后的住所,必须看管好。少一口棺材,村长嘴上说再想办法,其实无法可想。那个半成品已经被孙独眼鼓捣坏了,他单只眼睛看不清距离,把铆全钉歪了。赶着牛车去邻村弄吧,来回得有五天的路程,拉着棺材还要翻越沟沟梁梁,再牛的牛也办不到。最重要的是,即便有棺材,也用不上,因为最后一个死的不可能躺在棺材里把自己埋掉。所以村长说,与其想办法弄棺材,不如想办法怎么自己埋自己。
可以去邻村请个人过来埋,周疙瘩说。村长摇摇头,说,非亲非故,别人未必肯帮这个忙,况且啥时候死又摸不准,贸然把人请来,要是一时半会死不了,还让人耗在这里不成。孙独眼负气地说,我看谁活到最后,干脆搬走得了,反正埋在哪儿都没人惦记。村长说,后人不惦记我们,我们可惦记着先人呢,先人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这个问题足足讨论了两年,依然未果。
两年后,孙独眼、周疙瘩相继死去。他们想不出怎么自己埋自己,所以抢先一步离开,把这个难题抛给最后的那个人。偌大的村庄,只剩下村长和刘傻子了,俩人盯着一口棺材,看谁先躺进去。
五
村长的坟在哪儿?
老人突然想起没有看见村长的坟。他站起来,重新在墓地里转了一遍,仔细寻找村长的名字。太阳沉下去了,暮色从天边压过来,老人弯着的腰快要贴住地面了。他忽而希望下一座坟就是村长的,忽而又希望找不到村长的坟。天快黑了,老人有些焦急,他用木棍拨开蒿草,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顶登去。
山顶洒满星光。
老人坐下来,极目远眺,清澈的瞳孔里映着一轮弯弯的新月。
难道村长没有死?
老人自言自语,忽然发现山坡背面,飘浮着一团青绿色的鬼火,明灭不定,像狼在眨眼。老人觉得奇怪,全村的坟都在山坡正面,谁会埋在背面呢?他对准鬼火的方向,摸黑下山,虽然步子很轻,但还是惊起了潜伏在暗处的蝙蝠,一挫身,向月亮飞去了。等老人走近,鬼火就像宿雾见了朝阳,消散干净。
老人擦亮一根火柴,借着熠熠的火光,看见一块墓碑,斜斜地插在峭壁前。原本平缓的山坡,到了这里,急转直下,仿佛被削去一刀,形成一段两人高的峭壁。火柴燃尽了,老人又擦亮一根,凑到墓碑前。
村长的名字,一如他冷峻的面容,隐匿在蛛网之下。
村长到底还是死了,老人叹口气,可为什么埋在这里?
六
刘傻子并不操心死亡的事情,对村里其他人的生死也不闻不问,他似乎不知道年轻人都走了,老人都死了,依旧蹲在树下看他的蚂蚁。他双手支着头,一看就是大半天,谁也唤不动他。有时没有蚂蚁,他就盯着蚂蚁洞看,好像蚂蚁会从洞里运出金子似的。其实一个人真要啥事不干,一天到晚盯着一个地方看,肯定是能看出些名堂的。但刘傻子从未告诉别人,他看出了什么名堂,如果刘傻子会认字,说不定能写出一部有关蚂蚁的惊世巨作来,可惜他不会。他用他傻头傻脑的外表,藏住了一个也许足以轰动世界的秘密,藏得严严实实,藏得不露声色。
村长除了每天做好饭,端给刘傻子吃以外,其余时间都在忙一件大事。这件大事他谋划了很久,一直装在心里,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在等一个合适的实施时机。孙独眼、周疙瘩一死,剩下刘傻子,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开始采取行动。他要把整个村庄带到地下,一起面见先人。他用一个月的工夫,推倒所有的房子(除了他住的那间),砍掉所有的树(除了刘傻子看蚂蚁的那棵),毁坏一切道路,又用半年的时间挖坑,清扫,掩埋。他把村里十几代人的生活痕迹,全部埋入土里,插上荒草,伪造成荒无人烟的假象。年轻一代已经远走,年老一辈也已经死去,没有谁会找到这里,它将成为消失的记忆永存于地底下。
村长站在山坡上,扫视一周,对自己的成果很满意。等刘傻子死了,他再把残留的一屋一树埋掉,就齐活了,那时即便自己投胎转世,骑着马匹经过这里,也不会认出来了。
然而,村长刚干完这件大事,就病倒了。他过分透支自己的体力,身子已经大不如前。刘傻子却傻人有傻福,虽然头发和胡子看起来比过去更苍白蓬乱,但脸上没有病容,四肢也还康健,一副很耐活的样子。村长怕自己熬不过刘傻子,死在他前面,那就麻烦了。一来刘傻子啥都不会,自己肯定要落个暴尸荒野的下场;二来自己一死,不仅村庄的掩埋工作无人收尾,刘傻子也会活活饿死,他的后事也同样无人料理。想到这里,村长不得不强打起精神,争取多活。
一天,村长赶着牛车,要出远门,他对蹲在树下的刘傻子说,我去趟野地,三五天后回来,屋里有米有菜,饿了自己做。刘傻子闷哼一声,算是回应。村长目视前方,抛了几声响鞭,牛车吱呀吱呀地出村而去,把刘傻子一个人丢在村里。没走多远,村长跳下牛车,原路小跑回来,躲在一滩深草后面,偷窥刘傻子。他以为刘傻子会不安地四处张望,但刘傻子没有,他还是那样蹲在树下,纹丝不动,像只鸵鸟。
村长解开包裹,里面有干粮和水。他打算驻扎下来,看看刘傻子在没人伺候的情况下,会不会饿死。
两天过去了,刘傻子不吃不喝,仍然蹲着,白天蹲着看,晚上蹲着睡,没人喊他吃饭睡觉,他就原地不动。村长有点泄气,几次想出来,但都忍住了。有时他会故意弄出点声响,让刘傻子听见,可刘傻子不知道是没听见还是听见了假装没听见,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到第三天,村长忍不住了,忽然从深草里钻出来,想给刘傻子一个惊喜。村长喊,刘傻子。没有回应。村长走过去,碰了他一下,他就像一堵破墙,直直地栽到地上,再也起不来。
七
村长背着刘傻子,踉踉跄跄地走到墓地。风在怒号,从天上掼下来,搅得大地一片凌乱。村长费了很大的劲把刘傻子拖进棺材,合上盖,铲土埋掉。隆起的新坟,像刚出生的婴儿,很扎眼地挤在林立的旧坟中间。
刘傻子,我对不住你,也对不住你死去的姐姐,你姐临死前憋着最后一口气把你托付给我,我却这样平白无故地让你饿死了。你姐在天上,肯定都看见了,我不知道死后怎么面对她,怎么面对你。你俩要是碰上了,就商量一下怎么罚我,扮成鬼来吓我,设道坎来绊我,或者直接把我带走,都没有问题。要是还不够,等我死了,我会去天上继续受罚。希望你们给我时间,容许我做完最后的一点事情,再去找你们。我已经把村庄埋了,你们早该找到自己的房子,住进去了吧。村里一定很热闹,每家都是十几代人,吃着累积几百年的粮食,养着漫山遍野的牛马猪羊,无忧无虑地生活,生孩子。大家肯定快乐得忘了我这个村长,这个村长生前管束着大家,大家不想死后还受他的管束,如果是这样,你们就托梦告诉我,我会留着房子,当个孤魂野鬼,决不跑去打扰大家。你喜欢那棵树,过两天我把它埋给你,你一进村就能看见,不过你要答应我,往后多陪陪你姐,别还跟过去一样,只知道看蚂蚁,对谁都爱搭不理。
村长这样想着,离开了墓地。
最后的一屋一树村长忍着病痛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掩埋完毕。多余的粮食埋了,没来得及吃的牲口也拿绳子勒死,刨坑埋了。村长踏着步子,四处打转,把土踩瓷实。
这个曾经生活了十几代人、炊烟不断、充满鸡鸣狗吠牛哞马嘶的村庄,现在就剩下村长、村长身上的衣服和村长手里的铲子。很快,他会带上这些东西从这个世界里彻底消失。
黄昏,村长扛着铲子,要去埋自己了。他绕着山坡走了好几圈,终于在山坡的背面,找到了一处峭壁。打量周围,环境还不错,当下就决定埋在这里。村长爬上山顶,把预先准备好的墓碑推下来,栽在峭壁前。栽得有点歪,村长歪头一看,挺直的。接着开始挖洞。洞的直径只有一米,村长弓背缩头,跪着往里挖。他怕直径大了,会塌下来。洞内潮湿阴冷,挖到两米深的时候,抛出去的土几乎把洞口堵死了。村长放下铲子,转身趴下,头冲外,透过缝隙看了一眼美丽的晚霞,然后抓几把土,将缝隙塞住。村长翻个身,黑黑地躺在洞里,什么也没想,就像躺在自家炕上一样,沉沉地睡去了。
八
老人带着疑问,也睡去了,睡在村长的墓碑前。
从此,再没有任何黎明能使他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