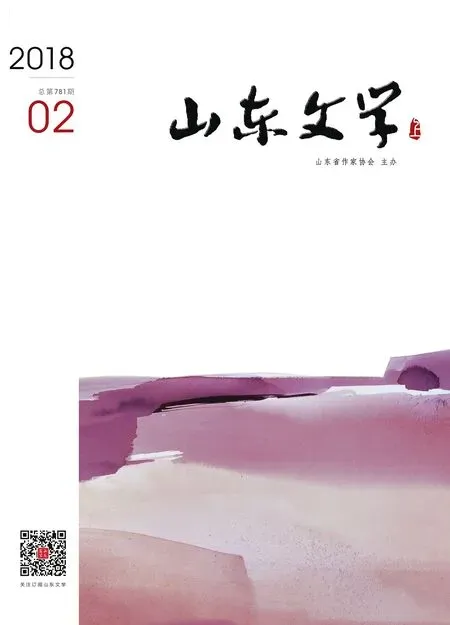回来
刘会然
我回来了。
还在客车上时,我就想,我回到秧村,秧村人会闹翻天么?要知道,我从里面出来时,门口的那些人闹翻了天。闪光灯像一记记闪电,吓得我频频捂眼塞耳。那些人把我团团围困,一个个话筒,像一截截甘蔗往我嘴里送,他们互相推挤,和马蜂打群架没有两样。我曾经被马蜂蜇怕了,这阵势,吓得我抱头鼠窜,落荒而逃。
在车站旁的路边店,我买了一顶灰色鸭舌帽,盖满头颅。弯七拐八,几经辗转,我终于踩在了秧村厚实的土地上。
村子里出奇地安静。在村口,我只听到一对黄雀在桑树上鸣叫。我把鸭舌帽飞到桑树上,那对黄雀扑扇着翅膀飞远了,我的鸭舌帽却牢牢吊在树梢。
我还以为,我回来,会和我离开一样闹腾。我离开那年,村口是人挤人,集市般喧闹。我不像是去坐牢,像是去参军,要不是顾忌我寡母的脸面,我猜秧村人放爆竹的心都有了。
也难怪,秧村人都是预言家,他们说,一个整天顶着光溜溜脑袋的人,不是和尚,就该是罪犯了。我的离去,让村人预言成真,他们大快人心,有理由敲锣打鼓,张灯结彩。
没错,我就是以罪犯的身份离开秧村,而且是让人最难以启齿的强奸犯。
那还得从我十八岁那年说起。
十八岁那年,我傻傻地爱上了张雪草。
可张雪草却不喜欢我,张雪草说,你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
张雪草说得没错,我就是一只癞蛤蟆。父亲早逝,母亲寡身一人,东拼西凑,才把我抚养成人。我家里也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住在摇摇欲坠、阴森森的祖屋里。和我们一起住祖屋的那些邻居,早就搬进了新建的砖瓦房。更可恶的是,我都十八岁了,还慵懒疲沓,整天在巷弄里东流西荡。
张雪草的确是天鹅。张雪草的父亲张三牙,在偌大的秧村,开着唯一的小卖部。多年下来,零敲碎打,张三牙就成了村里的首富。在秧村,张雪草家是第一家盖小洋楼的,三层的平顶小洋楼。张雪草家的小洋楼灯笼高挂,瓷砖亮堂,像一只站在母鸡群中的公鸡。张雪草呢,要说缺憾,也就是她母亲没了,在生养二胎时,因难产而逝。
父富女贵,张雪草自然是一枝梅花压桃李,她小学毕业后,就在父亲的小卖部里帮忙。其他女孩,谁不跟随父母下田辛苦劳作?泥里来,土里去,皮肤晒得黝黑。张雪草不管刮风下雨,都在小卖部里闲坐。张雪草像一枚雪梨,水汪汪的,甜丝丝的。张三牙每次去城里进货,看到漂亮的衣服,就给张雪草带回来,什么连衣裙,吊带装,秧村女孩只是在电视里看到过,张雪草是穿过一套又一套。
那时,张雪草这枚雪梨,引得十里八乡的小伙子垂涎。来她家提亲的,一拨接一拨,她家的台阶泛着白光,寸草不生。这些年,张三牙忙活着小卖部,一直没有再娶,店里哪能少了张雪草?张三牙死活不肯把张雪草这颗宝贝,早早搁别人家。
可我还是想娶张雪草为妻。
背地里,我希望母亲去提亲。但转眼一想,就是刀架在母亲脖子上,母亲也没这胆量。母亲是又怕又想见张三牙,如果在路上偶遇张三牙,母亲会低头快步游走,可又控制不住自己,偷偷回头瞄看张三牙几眼。
母亲说,年轻时,张三牙也看上了她,张三牙还去相亲过。可我母亲的母亲嫌弃张三牙油嘴滑舌,不稼不穑。母亲的母亲看上我父亲老实本分,是个勤耕苦种的好手。可现在,我母亲的母亲哪里会想到,张三牙发达显赫了,我父亲却患痨病早早入土了。母亲时常絮叨,要是当时嫁给张三牙就好了。
我知道,我娶不到张雪草,但我总可以看看张雪草。有事没事,我就往小卖部跑,多看张雪草几眼,至少晚上能做个美梦。
小卖部门口摆着三张松木长凳,村里那些老人,喜欢坐在长凳上东拉西扯。渐渐地,我也混在老人堆里。张雪草开始还觉得新奇,一个小伙子,鬼混在老人堆里,真可笑。后来见我每天都来,上班一样,她就不开心了。那些老人偶尔还会花上几块钱,给孙子孙女们买上几颗糖或几块饼,我却一毛不拔,只是盯着张雪草傻看。
这终于惹火了张雪草,张雪草说,你不买东西,呆坐在这里是想偷东西吗?张雪草这小妞,其实是知道我喜欢她,故意说这样的气话来激将我。我本来就被村人骂为“一根筋”,也懒得辩解,就说,是啊,我是想偷东西,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
张雪草嗔视道,你敢。
那次,是个夏天的晚上,天气异常燥热,我照常在村里的巷子里转悠。路过小卖部,店门关了,可屋里还亮着灯。我捡来三块砖头垫脚,往窗户里一看。我看到了张雪草的胸部,蚕茧般透亮。很可惜,张雪草洗完了,正往身上套连衣裙。
我抡起手,给了自己一巴掌,惩罚自己来晚了。张雪草从窗台里看到了我,脸红得像梅花一样。
第二天,张雪草告诉张三牙,说我整天绕着小卖部,鬼鬼祟祟的,肯定想偷什么。张三牙气汹汹来我家,说要是我敢偷小卖店的东西,就把我的双手剁了。张三牙背后,歪歪扭扭站着几个闲汉,一个个虎背熊腰,阴骘可怖。母亲吓得秋风中的枯叶般,全身颤动。我鼻孔朝天,心里满是冷笑。
张雪草有一个习惯,黄昏喜欢去秧溪散步。每次,我看到张雪草去秧溪散步,我也故意往秧溪跑。秧溪边有我家的一个菜园,我有充分的理由去菜园子里拔草或浇水什么的,这没有人可以管,就连我母亲也无话可说。
那天,是个黄昏,晚霞漫天,稻田里飘荡着谷穗的清香。我看到张雪草穿着一条印花裙,扬起双臂在溪边漫步。晚风吹拂着禾苗,稻浪翻滚,溪水叮当。晚风也把张雪草的衣衫吹成了晚霞,张雪草就像一位下凡的仙女,来到溪边汲水。
风越来越大,张雪草衣衫飞舞,脚步如鼓点一样沿着溪岸飞奔。
我担心张雪草会飞上天。我急匆匆跑过去,扯住张雪草的裙裾,我带着哭腔,说,你不能上天,你要嫁给我。
张雪草一愣。随后,她妩媚一笑,说,嫁给你?
我风吹稻穗一样,点头哈腰。
张雪草哈哈大笑,笑得像一道彩虹。
我说,你不嫁给我,我去做和尚。
张雪草说,和尚?哈哈,和尚又不怕多你一个。
第二天凌晨,我就赶往枣花镇,央求剃头匠铁拐李给我剃个光头。铁拐李说,光头有什么好?现在的小伙子,脑袋就是不灵清。我把钱拍在铁拐李胸脯上,说,钱和你有仇吗?铁拐李磨磨叽叽,很不情愿帮我刮了一个光头。
我光芒四射,顶着脑袋回来了。我却没有当成和尚,是母亲阻拦了我,母亲说,你狠心的父亲丢下我走了,你又要丢下我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说着,母亲提起农药瓶子,就往嘴里灌。我一个箭步,把母亲手里的农药瓶子打翻在地。母亲哭丧着脸,像唐僧念紧箍咒般,絮叨我不该剃光头。我很头痛,娶不到张雪草,又当不成和尚,我感觉自己真是无用。
整天顶着和尚头,在村子里晃荡。秧村人都笑我,说“一根筋”,你和尚不是和尚,罪犯不是罪犯,顶个秃瓢脑袋干嘛?
张雪草看到我,也哂笑,说你怎么还没有去少林寺呢?
我说,我要是能去少林寺,还需你提醒?反正,我是去不了少林寺,但我还是喜欢整天顶着光头。每半个月,我就去央求铁拐李,帮我把头皮刮得精光。我喜欢让脑袋赤裸裸地出现在张雪草面前。张雪草以前不太理我,自从我光头后,她喜欢逗笑我了。
那次,张雪草在秧溪边散步,张雪草突然向我招手。我像一条饿坏的土狗看到了肥肉一般,冲到张雪草面前。
张雪草露出一个妩媚的笑容,说,一根筋,你真的爱我吗?
我说,真的。
张雪草说,你肯为我去死吗?
我说,肯。
张雪草说,我不会要你为我去死,你就从这里往溪水里跳下去。
我二话没说,往溪水里一跳。谁知,是秋天,水浅得只能掩盖脚踝,我几乎是把脑袋栽在泥沙里。
我看到张雪草哈哈大笑,头也不回离开了。
我摸着光秃秃的脑袋,一股鲜血流了下来。很快,我就痛得嘶牙咧嘴。但转眼一想,为了张雪草,死都可以,这点痛又算什么,说不定是张雪草考验我呢。
我往脑袋涂抹了一层黑泥巴,也吹着口哨回家了。
几天后,张雪草看到我,露出一个妩媚的笑容,说,一根筋,你真的爱我吗?
我说,真的。
张雪草说,你肯为我去死吗?
我说,肯。
张雪草说,我不会要你为我去死。张雪草用手一指,说,树上那个马蜂窝,整天嗡嗡叫,吵死了,你去把它端下来吧。
我二话没说,噌噌噌,就爬到树梢,双手扯着马蜂窝就往下扔。
成球的马蜂向我发起进攻,我抱紧脑袋,在草地上打滚。最后,我还是昏死过去。等我醒来后,头顶的月亮正灿亮着。我四处找张雪草,可哪里还有她的影子。
我全身肿胀,火辣辣的,一碰就刺骨痛。但转眼一想,为了张雪草,死都不怕,这点刺痛又算什么,说不定是张雪草考验我呢。
后来,好多好多次,张雪草都露出妩媚的笑容,说一根筋,你敢吃蜈蚣么?你敢掏蛇洞么?你敢吻青蛙么?你敢和疯牛干架么?
都被我一一挺过来了。
终于,最大的考验到了。
那天,我去小卖部,老远就看到了一群人在窃窃私语。我挤进人缝,看到张雪草白猫一样,蜷缩在小卖部的木床上。张三牙站在床边,声嘶力竭地喊,快说,是谁?是谁?
可张雪草眼睛迷茫。我看到地上,有一截拇指粗的绳索和一条带血的白毛巾。
村口,很快就传来了警笛声,五个警察来到小卖部。两个持冲锋枪的站在门口,一个拿着相机拍个不停,一个在屋里四处找寻,一个在本子上描描画画。
围观的村人都远远站着,掩嘴耳语。五个警察忙活了老半天,最后,他们带着张雪草和张三牙,一起上了警车。
当张雪草经过我身旁时,她飘来一个妩媚的笑容。
第二天,张雪草和张三牙回来了。我却被警察押走了。
以前,村人只是在电视或电影里看到过警察逮人。这次,就在眼前,村里人又恐惧,又兴奋。有人躲在门缝里窥视,有人躲在墙角偷看,有人站在自家楼顶上或树杈上俯视。有几个青皮后生嬉皮笑脸,紧跟在警察身后。他们跃跃欲试,很想摸一摸我手上那副锃亮的手铐。
在审讯时,我才隐隐约约知道,张雪草被人玷污了。
警察说,想不到你年纪轻轻,手段如此残忍,经验如此老到,几乎没留下作案线索。
警察说,要不是张雪草在慌乱中,摸到一个光头,我们还无从下手呢。
听如此说,我就觉得应该是我干的,因为秧村就我一个人顶着光头。而且这些天,我常做梦。在梦中,张雪草这小妞还是不喜欢我,我就生气了,我只能强行闯进她店里,蛮干了。我这人一根筋,做事颠三倒四,说不定,现实和梦也被我搅混了。
警察问我,是你干的吗?
我本想说,不。可我总觉得隐隐约约干过这事,而且不止一次。我又想起那天,张雪草对我妩媚的一笑。
我就说,是我干的。
要不是那个真正的强奸犯,十年后重出江湖,我或许还昏睡在梦中。
真相大白后,政府放了我。政府还说,会为我申请国家赔偿,有几十万呢。
我对赔偿没兴趣,没牢可坐了,我只能回秧村了。
我回来了。
走到晒谷场上时,几个孩子朝我涌了过来,大喊,光头强,光头强。他们叽叽喳喳地问,熊大熊二呢?我挺纳闷,我大名叫袁全,外号一根筋,不叫光头强呢。
可光头强又是谁?
进了家门,母亲在灶台做晚餐。她看我回来了,愣了一下,说,回来了。这口气,就好像我刚从枣花镇赶集回来。有阳光从窗台跑进来,跳在母亲脸上,我看到藤蔓爬满了母亲的脸。我离开那年,母亲刚满四十岁,如今,母亲像一个暮年老太了。
吃饭时,我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母亲。母亲眼泪汪汪看着我,就像看一件稀世珍宝一样。母亲哽咽着,说,我就知道你是冤枉的,我生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呢。母亲泪水涟涟,把我眼泪也引逗出来了。
我回来后,村人津津乐道,夸耀我登上报纸了。在村人眼中,上过报纸的人,不是当官的,就是英雄人物。我不是当官的,自然就是英雄人物了。
国家的赔偿金额很快到了。母亲和我商量,得建幢新房子。祖屋的四个角落,已经败坏了三个,只有我们住的那个角,用几根实木硬撑着。母亲说,这些年,秧村外出打工的多,赚了钱,都建了砖瓦房了,最矮的两层半,高的有五层了。
母亲四处张罗建新房。半年不到,一栋三层半的水泥板新房就建好了。
我和母亲住进新房后,一个个媒婆就开始来我家登门拜访了。在秧村一带,还流行着十八岁左右就开始处对象、二十岁左右结婚的习俗。三十岁后若还没对象,基本就是打光棍了,即使要结婚,也只能娶有残疾的女子或寡妇。
现在,我三十了。可来我家的媒婆蚂蚱般,一个跳走,一个跳来,介绍的对象也是十八岁上下的女子。甚至还有一个在读初三的女孩,她母亲也托媒婆来相亲,说这女娃子,初中毕业就可以嫁过来。好笑的是,一位媒婆来我家,说有个新寡的妇人想嫁给我,还水灵灵的。母亲用扫帚,直把这媒婆追打了好几条巷子,才罢休。
这些天,母亲嘴里念念叨叨,这个女孩不错,那个女孩还行,你自己也看看吧。我谁也不想见,我最想见的人是张雪草。像电影一样,我每天都会不断回放,十年前,张雪草最后留给我的,那个妩媚的笑容。
我下定决心,去找张雪草。
我想张雪草一定还在小卖部。我沿着旧巷弄,一直走到小卖部。我看到小卖部变成了一个猪圈,几条猪仰着鼻孔,盯着我吼叫,一副饿死鬼的模样。
我向附近邻居打听,这小卖部搬哪里去了?
邻居说,早就关了,快十年了。
我绕道去张雪草家。我看到张雪草家大门紧锁着,门口的台阶上爬满了杂草。张雪草家的房子,挤在新建房屋之间,好似一只母鸡,站在一群红冠子的公鸡群中。
没有见到张雪草,也没有看到张三牙。我只好回家。
母亲问我,你去哪里了?
我说,我去找张雪草了。
母亲张大嘴巴,说你还去找她干嘛,这毒蛇一样的女人,她害你还不浅吗?
我斜了母亲一眼,然后用眼睛一轮,朝整个新房转了一圈。
母亲噎住了,说,你找她也没用了。母亲唉了一声说,你哪里知道啊,你关了十年,她也差不多像坐牢。
母亲开始讲张雪草。她说,那年,张雪草被祸害以后,整天就躺在家里,木头人一般。张三牙开始百般安抚,满以为张雪草会慢慢鲜活过来。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张雪草还是枯树一样,除了吃,就是发傻。为了照看张雪草,张三牙小卖部的生意也荒废了,袁老六趁势也开了一家小卖部。张三牙恼羞成怒,把一切罪过都怪在你身上,时不时来我们家摔东西,说是你毁了张雪草和他们一家。就这样,家里的东西都被张三牙毁过几轮了,可张雪草还是木头人一样。渐渐地,张三牙发现张雪草是个累赘,张三牙赶紧张罗着,请媒婆把张雪草请出去。可张雪草,谁还肯娶?张三牙只好让张雪草嫁给铁拐李。那个铁拐李,你也知道,脚一瘸一拐,近五十的老男人,比张三牙还大三岁呢。一个如花似玉的宝贝女儿,竟沦落到如此田地。张三牙也绝望了,整天喝酒,喝得烂醉,开了二十多年的小卖部也关了。
我哦了一声,又哦了一声。
母亲继续说,张雪草嫁给铁拐李后,日子过得真凄惨。开始,张雪草不让铁拐李碰,一直没有生孩子,铁拐李对张雪草不是打就是骂,骂自己捡了人家的破鞋。两年前,张雪草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女。可铁拐李摔了一跤,中风去世了。如今,张雪草继续开理发店。张三牙呢,整天倦狗一样,倚靠着张雪草过活。
母亲叹息了一声,说,真是冤孽啊。母亲问我,现在,你……你还去找她……找她……干嘛……
母亲还没有说完,我就迈开步子,向枣花镇走去。母亲在我身后摇头,跺脚,仰天长叹。
我很快就找到张雪草的理发铺子,我看到了张雪草正对着大镜子,给一个老头在理发。我蹲在门口候着,那老头一出来,我就立即钻了进去,坐在转椅上。
张雪草整个人都在镜子里,脸色焦黄,两个眼袋上像各挂着一枚青枣。张雪草帮我系好围裙,在我头上摸了一下,说,剪长还是剪短?
我说,剃光头。
张雪草扯下我身上的围裙,说,光头不剃,出去。
我对着镜子里的张雪草,飘出一个妩媚的笑容。
张雪草一怔,说,怎么是你?
我说,怎么就不可以是我?
张雪草说,你来干嘛?
我说,来剃光头啊。
张雪草说,我这一辈子都不帮人剃光头。
我说,要不,你帮我剃光头,要不,你嫁给我。
嫁给你?张雪草哈哈大笑,笑得像一张弓。
我说,你不嫁给我,我去做和尚。
张雪草说,你不是做了十年和尚,刚回来么?
我说,为了你,我死都不怕,十年算什么。
张雪草挤出一个妩媚的笑容,说,一根筋,你真的要娶我么?
我说,真的。
张雪草说,你肯为我去死么?
我说,肯。
张雪草说,我不会要你去死,只是,我两个孩子没有父亲了,你愿意做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吗?
我说,死都不怕,还怕做两个孩子的父亲。
张雪草说,你先把两个孩子接到你家里去,一年后,他们愿意把你当爸爸,我就嫁给你。
这又是张雪草在考验我。我二话没说,把正在墙角玩沙子的两个孩子,一左一右,夹在腋下就走。
这两个孩子一离开妈妈的视线,就哇哇大哭,我只好不断从店铺里,买好吃好玩的东西,逗他们开心。好不容易,我哄着两个孩子到家了。
母亲问我,你把张雪草的一对儿女抱过来干嘛?
我说,从今天起,他们就是我的儿女了。
母亲骂我疯了,说他们是铁拐李和张雪草的儿女,怎么变成了你的儿女。
我说,铁拐李死了,他们就是我和张雪草的儿女了。
母亲破口大骂,骂我是混账东西。
我懒得理母亲,我得把这对儿女哄好。
开始,这对孩子总是闹着要回去找妈妈。我不断哄骗,说我是你们的爸爸,爸爸在就不用叫妈妈了。
孩子说,你不是我们的爸爸,我们的爸爸是铁拐李。
我说,铁拐李是你们以前的爸爸,我是你们现在的爸爸。
两个孩子半信半疑。我源源不断地用零食和玩具做武器,两个孩子小小的城堡很快就攻破了。
母亲整天忿忿不平,骂张雪草,也骂这两个孩子,最后骂我死去的父亲。骂着骂着,母亲就呜呜哭起来。母亲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在秧村,她这个年龄,早该是几个孩子的奶奶了。可母亲膝下还如此孤寂,看到人家儿孙成群,她也心生凄凉。只是,母亲会不断叹息,说真是造孽啊,张雪草要害袁家几代人了。
很快,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去找张雪草。
我对张雪草说,你和我们一起回家吧。
张雪草挤出一个妩媚的笑容,说,一根筋,你真的要娶我么?
我说,真的。
张雪草说,你肯为我去死么?
我说,可以。
张雪草说,我不想你为我去死,可我跟你回去后,我那醉生梦死的父亲,可活不下了,要不,你把我父亲也接到你家里去,一年后,他还愿意在你家,我就嫁给你了。
这又是张雪草在考验我,我说,死都不怕,还怕你父亲,就把他当父亲服侍好了。
我用新买的摩托车,立即把张三牙载到家。
母亲急得四肢乱颤,说,你把小的接来就不该,你现在把老的也接来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说,我不是没有父亲嘛,就把他当父亲侍候吧。
母亲骂我是真疯了,说,你死去的父亲,死也不瞑目啊。
我说,父亲看到你一个人过,才死不瞑目呢。
母亲知道我是一根筋,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她只好对我忍气吞声,对张三牙骂骂咧咧。张三牙软塌塌的,再也没有先前的硬气和牛气了,面对母亲的责难,他只能低眉顺眼,小心翼翼,酒也不敢沾。
母亲和张三牙身处一屋,都过得提心吊胆。慢慢地,两位老人都认命了,一起抚养着那对孩子,一起去菜园里忙活。
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又过去了。
我去枣花镇找张雪草,说,你嫁给我吧。
张雪草挤出一个妩媚的笑容,说,一根筋,你真要娶我么?
我说,真的。
张雪草说,我嫁给铁拐李的时候,就像一只死狗扔给屠夫一样,现在,我要新娘子出嫁一样。
这又是张雪草在考验我。要知道,在枣花镇一带,寡妇二婚,是被人耻笑的事,都是暗地里过去,不摆宴席,不请客,不张扬。
我和母亲商量,要选定良辰吉日,举办婚宴,邀请了亲朋好友来闹腾。
母亲说,你娶张雪草也就罢了,还非得闹得沸沸扬扬,你就不怕人家耻笑,丢袁家的脸?
我为张雪草死都不怕,还怕耻笑、丢脸?再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城里人离婚都大办宴席,热闹非凡,还不要说张雪草是梅开二度,我是新婚呢。
我跑到枣花镇,把婚宴的日期告诉了张雪草。
张雪草挤出一个妩媚的笑容,说,一根筋,你真要娶我么?
我说,真的。
张雪草说,我嫁给你后,你和我自然幸福。可我父亲和你母亲,一辈子守独,你让他们也结婚,好事成双,可以么?
母亲肯嫁给张三牙么?这又是张雪草在考验我。
但一想,我为张雪草死都不怕,母亲嫁给张三牙比死还难么?
我把这事和母亲说了。
母亲大哭了一场,嘟哝着,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
我说,死去的爹什么都不知道了,对得起你自己就行了。我说,你以前不是时常骂父亲,说你瞎了眼,要是嫁给张三牙这辈子就好了嘛。如今,不是等到机会了么?
母亲羞红着脸,挥起双拳,往我背上乱砸。
张三牙自然心欢,他不也娶到曾经想娶的人了嘛。
我和张雪草结婚的日子到了。
一大早,母亲和张三牙就披红挂彩,肩并肩,笑盈盈地站在大门口,迎接来参加婚宴的亲朋好友。
我焕然一新,带着唢呐班子和迎亲队伍,一路热热闹闹,朝枣花镇走去。
路上,我脑中突然有了这么个念头:母亲嫁给了张三牙,我娶了张雪草,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我没想到我会有这么个念头。这念头一闪,欢喜的唢呐声轰轰烈烈地响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