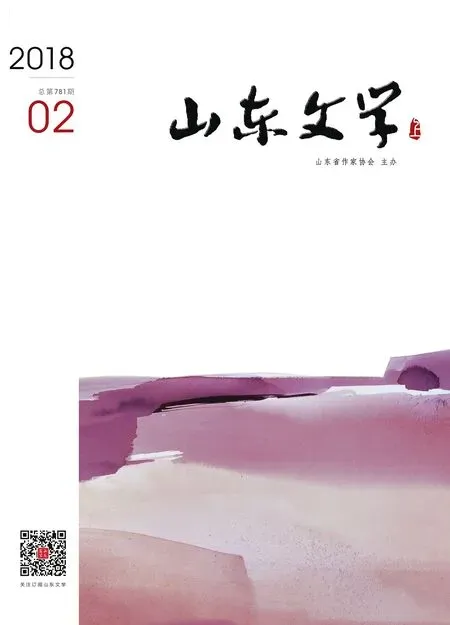词语之谜(组诗)
侯存丰
公园
雾深一些,南湖公园就如仙境了
从曲曲折折的水中回廊向外望,白茫茫一片
唯岸边垂柳,身后数尺,隐约可见
偶尔一声水哗,想来亦是近处迷鱼翻身
四下阒然、冷清,这恰好贴合了深秋的主旨
另外,还有我这个异乡游子,大口吞着浓雾
那雾中游荡着诸如乡村、老屋之类的小金鱼
不曾想,这烟波湖上也会惹出几多愁
一念
去年,我换下褶皱的车间呢绒服
感觉一身轻松,在钦州世博园
宽敞的热带雨林小道,迷人的气息
我打算读一篇《一点墨》
给她听,给她红墨水的小脸蛋
而我为什么又听到工牌号的摩擦声
橘黄色厂房,套着白锡纸的钢管
我不是轻松了吗,这摩擦声让我困扰
直到一天夜里,读到“是身如丘井”
我才恍然:当初在钦州,饭馆的螺蛳粉
吃起来,既非沈园,亦不是漆园
若兰
石阶上的花生鼓胀着,长出白须
几棵榛木,一旁的坡地上,斜进枝桠
凉亭巍巍峨峨,叶影里隐现
两只白鹅,仿佛依然卧眠
在清凉的木柱边,如如不动
那个骑单车的少女,一副慵懒的样子
她抚抚长颈,细绒里抽出红蹼
便把它们枕在身下,闭目嗑起花生来
柏木
一阵轻鼾从屋中传出,女人放下线团
给熟睡中的孩子掖掖被角,理理额发
桌上,五寸相框里镶嵌着青春缩影
那个人,脖颈缠白围巾,身宽体泰地
望向,女人身后,墙上张贴的旧报纸
一副整齐的田垄、麦茬,涂满1997年盛夏
屋外,雪停了,瓦楞上、院落里,满满覆着
再过几个小时,开年的鞭炮声就要响起了
薄云
红的触须,立在水面的蜻蜓
塑料荷叶上,三只、四只
围着的孩子,清水眼睛
抓下,连同网兜丢进水里
一对恋人,站在不远处
榕树凉荫下,静静看着
初秋的游乐园,太阳熹照
望去,一岁、两岁模样
草庵
走进东间里来,右手一副黑枣木桌子
削损的棱角,剥落的漆点,以及耷拉的抽屉
散发出一种生蛋黄的腐衰气息,尤其是
紧挨着常年不见阳光的窗棂,潮湿、昏暗
仿佛冬日的水鸭,颤动不止,这颤动
从桌子开始,延伸到三脚柜、满是补丁的棉被
发愣当儿,屋外传来母亲的喊叫,这才记起
要吃年饭了,正等放炮,于是从桌上取了匆匆走出
月夜
煤屑周围,小而发亮的墨块
在村外小路边沿,零零散散麋集
紧挨着的,是叠峦般的白色大棚
一位头戴纱巾、背上负着喷药桶的农夫
远处,一根烟囱直入云霄
砖窑厂的生活,从那些古旧的烟开始
春天似乎从未远去,村庄里
一个女孩,赤脚,自梧桐树后面走出来
清明
蒿草返绿了,在原先根茎处
一株、两株、七株……覆满园子
安推开门,便望见石碾,变了方向
在那片荒置的菜园,木轱辘亦滑进槽里
多少往昔,那开垦者古铜色身影
曾一度占据,这狭小画卷
安倚在门框边,视线越过小径、竹篱,落向原野
在那片空旷里,有她熟悉的烟熏味,他还会回来
所咏
春天天气暖和,放下粪铲,在榆树下
卷一根草烟,拇指和食指抖动不止
也许幻觉。浓荫里,那饼状牛粪
在竹篮里慵懒地仰躺,下一刻,燃烧
少年时,风里黄鬃,田间蟋蟀
老之将至,喜午后走走,右胳窝夹一木铲
桔梗
好色之人,穿中山装,或直筒长衫
于傍晚,来到桑麻田地,嗅气味
四野蒙蒙,远山、近树、低屋,犹似一粒冰片
亦是赶鸭的人、掏粪的人、咬樱桃的人
天黑了,拿一盏灯放在桌上,坐着或站着
不去想,镜中花香,缘自窗外哪户人家
轻盈
钩针停了下来,校园林荫道上
那蓝格白底衬衫,飘将起来
太阳已经在落下去,黄昏的阴影
在屋里铺开,围巾织法的书页
渐渐模糊不清。窗外的那片云杉
亦安静了,枝梢漏下微细的踱步
春天逝去,初夏来临,那毛线团
滚落床脚,散发出一股厨房油渍的气味
林荫
仲夏的一天傍晚,灶台烛光明亮
起锅的一笼白面馒头,热气腾腾
解下围裙,母亲洗罢手,走出厨房
斜阳的余晖在屋顶、烟囱上泛出金光
2003,一条条麦茬在幽径中燃烧
成群的麻雀飞上楝树,雾霭遮没天空
想到这里,母亲阖上眼睛,摇了摇头
堂屋几台上,正中摆放的神龛,炉香乍热
初忆
薹草合围的水田上,两只蜻蜓在飞
鼓圆的头端,时而从叶杪触及脚趾
钟响了三下,手托着脸,望向窗外
远处,牙白的巴洛克教堂圣龛隐现
盛夏侵晨,乡村小道,还不见行人
令人颤动的稻米香,已由窗牍爬进
便趿拉着凉鞋,穿过菜圃,出去了
在水田边,她抬起眼睛,看见了山
东屋
雪盖没了积水沟,连同废弃的锈铁堆
国营颖泉印刷厂大门外,棉布鞋浸透了
就在昨晚,一封电邮从湖南拍来,顿时
油墨气息翻飞,水泥地板上,青春粼粼
又一个不眠之夜,翻开蒲宁文集,想起
平日他阅读后,喜欢把书摊在肚子上
转眼坐在屋外,孩子们在院子里做游戏
她摘下眼镜,一抹残阳映在她的脸上
第宅
那是九月的一天傍晚,几只滨鹬飞翔在
离海滩不远的桅船帆布上,鸣声刮擦着
海面。那个幸福得慵懒的女人,晚饭后
坐在客厅里,翻阅着旧画报,浑身散发
出一股帽子里边的气味。朝向海的窗户
洞开,穿堂里飘来:我心花怒放地走进
夜来临了,褐黄色的岛屿闪烁着
青春?碧绿树林里,青春驾着二轮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