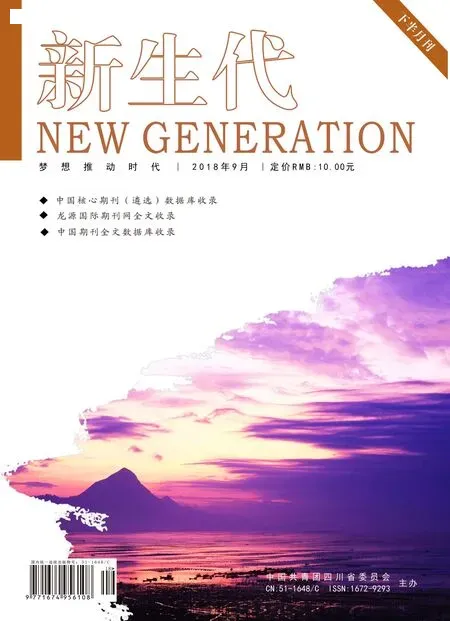《金锁记》中的“帘”意象浅析
赵蕾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119
《金锁记》是张爱玲女士的得意之作,发表以来获得的赞誉多不胜数。其中,海外学者夏志清教授曾特别地对张爱玲小说中所运用到的意象大加赞扬:“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我们可以看到,《金锁记》中使用的意象非常丰富,如:月亮、镜子、太阳等。其中,“月亮”和“镜子”两个意象曾被学者广泛研究。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论中的重要概念。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中第一次使用到了“意象”这个词,其中谈到了“神与物游”,便是对意象的初步认识。所谓意象,即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杨义《中国叙事学》中指出:“意象不是某种意义和表象的简单相加……从而使原来的表象和意义都不能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异和升华,成为一个可供人反复寻味的生命体……”
张爱玲小说中这些明显具有女性化倾向的意象便是那“可供人反复寻味的生命体”。它不仅营造出了独特的美感,更是在文中形成了不同的象征意义,使小说所具有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美丽苍凉”的女性世界。作为张爱玲小说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这些具有典型性的意象与小说的叙事、人物塑造密不可分。但是笔者认为在对《金锁记》这个文本的意象研究中还存在着被以往研究者所普遍忽略的一些重要意象,比如:“帘”、“帐”等。笔者认为此小说中的人物除了抬头望月与低头照镜之外,他们还喜欢在“帘”内外活动,“窗帘”、“珠帘”都是他们所钟爱或者说是作者所钟爱的意象。“帘”作为古代家庭中的一种室内装饰用品,在这里被作者赋予了深刻的含义,那就是距离、隔阂和权力。而正是由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从而形成了《金锁记》中那个无情无爱,只有金钱横行的世界,这便是文中“帘”多次出现的深刻意蕴。
笔者通过对《金锁记》进行文本细读和不完全统计,发现文本中共出现十五次“帘”,其中:“布帘子”(1次)、“帘子”(8 次)、“翠竹帘子”(2 次)、“窗帘”(3 次)、“珍珠帘”(1次)。这些形形色色的“帘”在文本中不仅象征着距离和权力,同时它围绕着主人公——曹七巧的生活(被束缚于帘中、在帘内外展现真情、将一双儿女缚于帘中)不断地进行场景转换,在文本中起着不同的作用。
一.象征距离和权力
从古到今,“帘”这个意象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从实用角度来说,它是起着挡风、遮光作用的物品。《说文·竹部》解为:“帘,堂帘也。”段玉裁注解为:“帘,施于堂之前,以隔风日而通明;帘,析竹缕为之,故从其字从竹。”从文学角度来说,它是古人作诗填词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意象,从唐诗到宋词,“帘”也产生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宗法父权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国家,统治思想为儒家礼教思想,讲究“男女之大防”、“三从四德”等封建男权思想。“帘”作为一种具有间隔作用的物品,它的产生恰好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要求。“帘”代表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明显的的分界线,是父权社会距离和权利的象征物。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父权社会将女性束缚在“帘内”这样一个狭小封闭的空间,是女性与外界社会隔绝的界线。《释名·释床帐》指出:“帘,簾也,自障蔽为廉耻也。”古人将“帘”与“廉耻”相联系,所以,挂帘便表示着对女性的操守保护。
《金锁记》开头便以“帘”寓距离和权利。早起,众人在帘外等着给老太太请安,起坐间的“帘”在这里就发挥着距离和权利的功效。首先,作为一个女性,老太太需用“帘”将自己和外界间隔开来,时时刻刻保护着自己的“隐私权”。其次,姜家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在没有了老太爷这样的男性统治者之后,作为一个女性的老太太便掌控着姜家实际的权利,她处于帘内,象征着自己高人一等的等级地位。这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形类似,“帘”内之人手握重权,处于下层的人们便只能来请安争宠。
小说中对七巧在姜家十年生活的描写也是很典型的一处:“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翠竹帘子”在此便是“囚禁”了七巧十几年的父权礼法的象征,它囚禁着女性的热情,吞噬着女性的生命。这帘子十年褪色,暗喻着旧的父权社会统治阶层将死而未死。七巧的悲剧还没结束,结束不了,封建礼法对七巧的压制只是换了不同的实施者而已。
二.展现人物情感
“帘”谐音“怜”,作为一种古代闺阁专属物品,多被诗人用在表现女性生活上,常常用来表现女性闺阁生活的孤独和寂寞之情,营造出一种距离、隐秘、朦胧的美感。《金锁记》中作者几度用“帘”这个意象来烘托人物的出场——曹七巧掀帘而现,给人一种未见其人,但觉我见犹怜的娇弱之感。除了塑造人物上的艺术效果,“掀帘而现”这个动作总是将我们的视线聚焦于帘内的画面里,使读者可以仔细的端详和思考里面的人和事。
《金锁记》中有三处这样的描写。这三处描写都是对曹七巧内心真实感情的描摹,其中前两处描写是对曹七巧恨丈夫而恋姜季泽的直接展示,另一处则是对曹七巧念哥嫂/亲情的生动刻画。
小说开头没有直接让曹七巧为自己言说,而是借助了旁人的言语对曹七巧的形象进行了初步刻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微言轻的姜家二奶奶。紧接着,作者便让曹七巧“掀帘而现”,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曹七巧的风韵:丫头榴喜替七巧掀起帘子,这时“帘”后的七巧是那群人关注的焦点,但她并没有按规矩“贤良淑德”,而是一出场便尖牙利嘴地将自己心里的苦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从此处开始,读者关注的焦点也一下子被“帘”所产生的放大作用拉到了七巧那畸形的婚姻上了。
第二次掀帘的则是七巧自己,掀帘后她随即便发现了坐在椅子上的季泽。于是略施小计,将旁边坐着的季泽太太“挤走了”,这时便只剩下了这单独的各怀鬼胎的两人。于是在这没有外人的场合下,七巧的情感迅速升温,一字一句直指季泽。帘内便是老太太的卧室,前一秒她还在老太太跟前怂恿着云泽的婚事,扮演着一个压迫者的角色,后一秒帘外便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重新做回了那个楚楚可怜的被压迫者。帘内是虚情假意,帘外则是真情实感的显现。这里“帘子”的内外构成了两个奇异的世界,毫不夸张地说:进则“鬼”,出则“人”。《金锁记》中,作者就是这样用“帘”这个意象营构着处于那个荒唐的世界里的分裂的七巧。
第三处是七巧对哥嫂真情的流露。哥哥和嫂子来姜家探望七巧,作者在这里也安排了一个“帘”的出现,将七巧和哥嫂分隔在两个世界里。从七巧这边隔帘望去,只见嫂子在检查着饭篮子里面带来的小菜,哥哥在旁佝偻着腰默默地看着。两位至亲的一举一动都在那一刻温暖着身在这没有人情味的姜家的七巧,使帘外的她不禁打湿了眼眶。
通过小说前一部分的叙述,我们仅仅看到了七巧生活中的一个侧面,但是在此处,作者寥寥几笔便把七巧整个的感情生活展现了出来。这里的“帘”相对于第二处的“帘”更为私密,是七巧自己闺房内的帘,所以在这时透过那一层薄薄的“帘”往事涌上她的心头,对亲人的思念夹杂着对自己所受苦难的无奈,众人面前那么一个牙尖嘴利的人儿竟然情难自禁留下了泪水。通过这里的“帘”,作者让我们将目光全部集中在七巧的真情流露上面,让我们对她又加深了一层认识。
三.营造苍凉意境
“帘”可以隔绝人与人,有时隔绝的对象也是人与自然,当“帘”隔绝的是人与自然的时候,帘内外自动分化成两种时空,而小说中仅有的两次都是帘内外同悲苦,形成了一种悲则同悲的苍凉之境。这样的情况在《金锁记》中围绕着七巧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她骂走姜季泽,另一次是她骂走春熹,这两次直接地和“金钱的枷锁”相联系。
第一处:“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戳穿姜季泽名为情而实为钱来的目的后,曹七巧决绝地痛骂季泽,终于他要永远地离开了。可七巧顿时又心生悔恨,去窗前进行最后的道别。此处“帘子”的两种状态形成了一种对比。揭开那帘,最后望着曾经心爱的人;放下那帘,从此浮沉各异势。这时作者又借七巧的目光为我们展示了帘外的那另一个世界:一个晃着膀子的巡警、黄包车在巡警身上辗过、小孩奔出视线、邮差的影子复印在巡警身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亦真亦假的帘外之景道出了七巧内心的挣扎:自己骂走季泽,揭开他的假面具到底是对还是错。此处出现多次的“帘”伴随着曹七巧在相同的场景里(即和姜季泽的对话)前后两次出现,它将曹七巧的爱情生涯前后串联了起来,不禁让我们回想起了他们第一次对话的场景。那次是七巧真心实意的告白,被姜季泽搪塞了过去;这次是姜季泽虚情假意的情话,却被七巧一眼看穿。决绝而又自私的姜季泽一点也没有变,七巧却已经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许前一次的结果就已经预示了这一次的结果。作者两次安排“帘”见证着这一切,不能说是没有深刻含义的。
第二处:“屋里暗昏昏的,拉上了丝绒窗帘。时而窗户缝里漏了风进来,帘子动了,方才在那墨绿小绒球底下毛茸茸地看见一点天色。”
这是七巧在骂走春熹后,和女儿长安在屋里的场景。由于前面“姜季泽事件”在七巧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所以侄子春熹和长安的正常交往都在她的眼里变了味道,以为春熹是和父母蓄谋接近女儿长安,进而算计着她的钱。此处和上一处同样都用了“风”作为“帘”的搭配意象,风吹帘动,可是这次只能看见一点天色,却还是“白色的寒天”。这里深化了“帘”的隔绝作用,将人物和外界环境完全的分隔开来,暗示着七巧的“完全异化”和对女儿长安人生的过度干预。母亲的权利在小说中被一步步强化,长安长大后放弃学业、放弃爱情的那“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就说明了一切。
小说中曹七巧是被父权社会所压抑的一代,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爱情,失去了一个正常的美好的人生,但同时她也作为一个实施父权压制的角色而存在着。分家之后的七巧在自己家里俨然扮演起了父权社会父亲的角色,她戴着“父亲”这个面具毁掉了儿子的家庭,也毁掉了女儿的爱情。此时期,她身旁的“帘”也完完全全地象征着权利和她本人与外界的隔绝。
结语
《金锁记》中的意象选择流露出作者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而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宗法父权下女性压抑与被压抑的故事。象征着距离、隔阂和权利的“帘”就是宗法父权下对人特别是对女性群体的压抑和戕害,它和小说标题“金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不仅是《金锁记》一篇,《传奇》中的大部分小说都应用到了“帘”这个意象,它在不同的情境中产生着不同的作用。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对“帘”这个意象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曹七巧形象的另一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