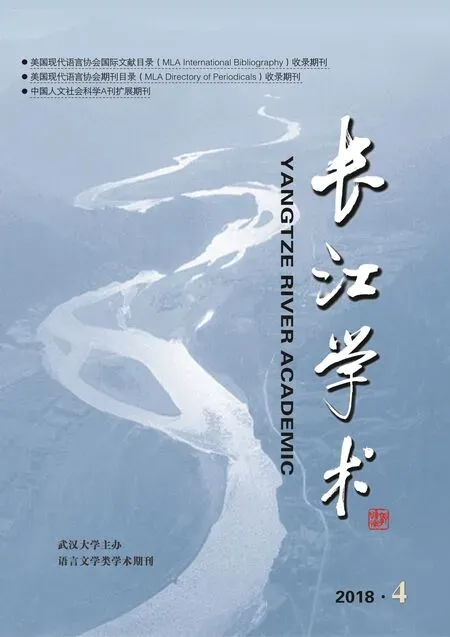论清代论词书札及其词学史意义
祝 东
(兰州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清代词学号称中兴,清人的词学研究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献资料。清人论词的形式极为丰富,词话、选本、论词诗词等不一而足。有关词话、词籍序跋、词学选本以及论词诗词的词学史意义,学界业已做了不少研究。相对而言,对于论词书札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论词书札的词学史意义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试就清代以书札论词这一独特的论词形式进行探析,研究其在清代词学史研究中的作用。
一、论词书札的渊源及界定
书札,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书信,在古代也称作书牍、书简、尺牍等。明人吴讷指出:“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书札原来总称君臣、朋旧之间来往的书信,后一分为二,应用性质的公牍书信被称为奏疏,朋旧之间的书信被称为书信、书札。书札这种文体容量很大,结构灵活,写法自由,兼议论、抒情、叙事于一体,适宜于表达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如刘彦和言:“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这种文体能够“尽言”,可以尽情抒写一己之情,表达“心声”,达到“尽其委曲之意”。且由于书札一般是写给亲朋师友的,故而能够尽情直言,绝少伪饰,更能够见出作者的真实情感和思想。
在文学批评史上,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想都是通过书札的形式记载流传下来的,如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曹丕的《与吴质书》、白居易的《与元九书》、苏轼的《答谢民师书》、何景明的《与李空同论诗书》。到了清代,学术文化集古代之大成,文人学士之间的交流往来益发频繁,各种文学思想的交流碰撞也都是通过书札的形式进行的,如顾炎武的《与人书》系列、魏禧的《答施愚山侍读书》《答蔡生书》、袁枚的《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与稚存论诗书》、姚鼐的《复鲁絜非书》、阮元的《与友人论古文书》等,不可胜数。可以说书札在清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
具体到书札论词而言,其实宋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如朱熹的《宋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书中就曾论及读东坡晚年所作小词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材料总体上还不多见。随着清代词学的兴盛及书札批评的流行,一向少为文人士子关注的词体文学也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以书札论词也出现在清人文笔之下,或许是由于这种论词形式相对较少,并且散见于清人文集、笔记、诗话、词话之中,不易寻觅,故而论者较少,迄今见到的对此关注较早的是孙克强先生的《清代词学的文献整理和研究》一文,其中指出:
清代论词的形式也有发展,如论词文、论词书札也都是清代新出现的形式。论词之文,不仅有书札形式的如顾贞观的《论词书》,毛先舒的《与沈去矜论填词书》,沈谦的《答毛稚黄论填词书》,吴锡麒的《与董琴南论词书》、王晫的《与友论选词书》,潘德舆的《与叶生名沣书》。……论词书札尤以晚清为盛,成为晚清词学的一道亮丽的风景,亦可视为晚清词学的一大特色。晚清四大家及其周围的词学家如夏敬观、张尔田、夏承焘、龙榆生之间经常以书札的形式探讨词学,极具理论价值。例如郑文焯与友人的书札仅存于世的即多达125则,郑氏的词学理论主张主要体载于此。清人的论词书札兼有私家信函和公开发表的双重性质,因而虽然语气婉转客套,但主张鲜明,批评尖锐,辩论激烈,是词学理论的特殊形式。
该文从文献学的角度指出了清代论词书札的特殊意义,并且初步梳理了一些论词书札文献,虽然没有具体展开,但亦导夫先路。
在笔者看来,论词书札不应仅仅拘泥于篇目上有“论词”字样的书札,凡是涉及词学问题的书信都应该纳入论词书札研究的视野。古人论学,往往没有现代的学术专著、论文那么集中专注,但是其间凡有只言片语涉及词学问题,都应该进行观照,考察其中的词学思想。如毛先舒的《与邹訏士书》《答孙无言书》、沈谦的《答丁飞涛书》《与李东琪书》《与邹程村》等、郑燮的《与江宾谷江禹九书》《与金农书》等、谢章铤的《答黎生》、郑文焯的《与王半塘书》《与吴伯宛书》等,也皆曾论及词学问题,纵是吉光片羽,也弥足珍贵。叶恭绰在《全清词钞序》中也曾记载儿时见其先祖与谭献、张景祁等人用书札讨论词学问题,可惜诸多书札流失不传。以书札形式论词至现代亦有学者沿用,如夏承焘就有《与龙榆生论白石词谱非琴曲书》《与张孟劬论〈乐府补题〉书》等多篇,可谓流风余韵,连绵不断。
二、清代论词书札的词学功能
清代学术文化发达,学术信息交流频繁,学者们改变了传统学术研究中独守书斋的钻研模式,更加注意与学界时贤、师友交流学术思想。清人在进行词学研究的时候,也经常将自己的学术理论主张通过书札与亲朋师友交流,由是论词书札得以兴起发展。综观清代论词书札,主要就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词学思想交流切磋:
其一,用论词书札批评词坛流弊。清初词学复兴与清初词选的推扬关系密切,清初重要词派皆有选本,如阳羡词派的《荆溪词初集》《瑶华集》、浙西词派的《词综》《明词综》等、京华词人群体的《今词初集》等,一时蔚为风气,各种词选跟风而上,数量跟进了,但是质量却没有保障,故而顾贞观在《答秋田求词序书》中有云:“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严、倦圃,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担簦才子,并与燕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书札回顾了清初作词兴盛的因由,并直言当时词坛流弊,即词风竞起之时,无论是创作还是选本,皆妍媸杂陈,影响了词体文学的健康发展,可谓针砭时弊。清初王晫在其《与友论选词书》中也指出当时词人选词黯于己见,喜欢周、柳之词者,尽黜苏、辛,爱好苏、辛者则尽弃周、柳,这种“执一以概百”的做法不利于多样词风的发展。
随着词学的发展,浙西词派逐渐成为词坛主流,他们标举醇雅理论,审音辨律,清代近两百年来的词坛基本为浙西词风所笼罩,但是浙派末流却逐渐将词体文学发展成一种徒具华彩的艺术品,缺乏真情实感,所以谢章铤在《与黄子寿论词书》中严厉批评了这种词坛流弊:
国初诸老奋兴,宗唐祖宋,词学固为最盛,复古不已,继以审音,持论愈精,用功愈密矣。然渐流渐衰,耳食之徒或袭其貌,而不究其心,音节虽具,神理全非,题目概无关系,语言绝少性情,未及终篇,废然思返,岂按吕协律之作必如是,味同嚼蜡而后可乎?甚且冷典卮词,轇轕满幅,专以竹垞、樊榭咏物为宗,则尤为黄茅白苇矣。
在书札中谢章铤指出了清初词学复兴的原因,但是笔锋直转,痛斥词界末流只注重词作的音韵律吕,而缺乏真实性情。谢章铤论词不拘泥于浙、常二派,曾自谓其论词“颇与时流不同”,
其二,用论词书札阐述自己独到的词学观点,交流词学思想。清代词派林立,各个词学流派无不注重推扬自己的词学主张,因此论词书札在清人手中不仅是为了批评词坛流弊,更重要的是标举自己所秉持的词学观点,通过书札的形式,有效传达到师友手中,以期引起共鸣。
如清初毛先舒的《与沈去矜论填词书》及沈谦的复信《答毛稚黄论填词书》即是词学史上有名的以书札论词、交流词学思想的史料。毛氏在书札中就曾直接点出自己的词学观点:“大抵词多绮语,必清丽相须,但避痴肥,无妨金粉。故唐宋以来作者,多情不掩才,譬则肌理之与衣裳,钿翘之与鬟髻,互相映发,百媚斯生,何必裸露,翻称独立。且闺襜好语,吐属易尽,巧竭思匮,则鄙亵随之。真则近俚,刻则伤致,皆词之鄙也。”毛氏认为词体文学本来就是语言绮丽、情思风致的文体,因此词中出现“金粉”修饰是不足为怪的。关键是在语言上应该自然平淡,而不要刻意雕琢。此在其《词辩坻》中亦有申述:
词家刻意、俊语、浓色,此三者,皆作者神明。然须有浅淡处、平处,忽著一二,乃佳耳。如美成《秋思》,平叙景物已足,乃出“醉头扶起寒怯”,便动人工妙。
在作者看来,词的语言可以浓丽,但不应雕琢,于平淡处见奇崛方是杰构。与其论词书札中的词学主张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书札直接寄送给师友,思想观点易于交流碰撞,沈谦的回信就是在这种交流下产生的词学主张。沈谦在复信中云:“夫宣姜好发,不屑髲髢;虢国秀眉,并损黛粉。丹漆白玉,永谢文雕。吾恐西施蒙秽,湔涤尚堪;嫫母假饰,訾厌百倍。以仆向作,政复病此,不图足下反以单情见让也。”针对毛先舒不妨“金粉”的论点,沈谦提出异议。沈谦与毛先舒同为西泠词派的成员,但是并没有互相标榜,而是各抒己见,畅言自己的词学观点,这在当时尤为难得。
如前文所云,浙派末流笼罩词坛,遂有淫词、鄙词、游词之讥,武进张惠言起弊振衰,倡导意内言外之说,用比兴寄托论词,并编辑《词选》(亦名《宛邻词选》),在常州词派后学的不断推扬之下,在词坛逐渐引起轰动,常州词派很快成为词坛主流,但对常州派词论亦不乏异见者,潘德舆即是其中之一,他在《与叶生名沣书》中即直言张惠言的疏漏之处:
叶生足下,昨论诗偶及词。承以阳湖张氏《词选》见示。其序颇为大言,谓词学亡于宋末,四百年来,作者安蔽乖方,不知门户,因选此编,塞流导源,使人知风雅,惩鄙俗,可谓抗志希古,标高揭已者矣。仆究其所录,则宏音雅调,多被排摒,纤猥之作,时一采之……窃谓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张氏于北宋知名之篇,削之不顾,南宋尚何问焉?
盖张氏论词,推尊唐五代、北宋,试图恢复古词面貌,但是其选中不乏淫艳之词,如温庭筠的《菩萨蛮》之属,但是张氏却认为有“离骚初服”之意,此论难以服众。潘氏此书札即是就此而论,在信中他批评了张惠言选词的弊端:“宏音雅调,多被排摒,纤猥之作,时一采之”,特别是温庭筠的词作,本是绮靡之语,属于张皋文所批评的“雕琢曼词”之属,却入选了18篇。在潘氏看来,词滥觞于唐,盛于北宋,如欲复古,当以北宋词为取法对象,这也是潘氏论词的基本主张,其《养一斋词自序》中亦有表述:“窃论词莫备于宋,莫高于北宋。词尊北宋,犹诗崇盛唐,皆直接‘三百篇’、汉魏乐府者也。”潘德舆用此书札批评了张惠言的词学主张,并藉此推扬了自己的词学论点。这篇书札应该流传甚广,谭献在《箧中词》评语中还援引了这封书札部分内容,并指出:“张氏之后,首发难端,亦可为言之有故。……然其针砭张氏,亦是诤友。”在《复堂日记》中亦论及潘氏的观点,谓“其持论颇訾议《宛邻词选》,以北宋之词当盛唐之诗,不为无见。而理路言诠终非直凑单微之手”。尽管谭献不完全同意潘德舆的观点,但还是肯定了其论词观点可为一家之言。
其三,用论词书札交流切磋词学疑难问题。由于受诗尊词卑传统观念的影响,词体文学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致使资料散佚太多,学术积累相对不足,此皆为后来词学研究留下诸多难题,如词的本体性问题、起源问题、声韵音律问题、校勘辑佚问题等,皆是清代词学界面临的亟须解决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也见诸清人论词书札之中。如词的本体性问题,它与诗、曲的关系如何,都常见于清人的词学论述之中。如郑板桥的《与江宾谷江禹九书》讨论了词与诗的不同,《与金农书》则探析了词与曲的差别。又如沈谦在《填词杂说》中云:“承诗启曲者,词也,上不可似诗,下不可似曲。然诗曲又俱可入词,贵人自运。”一方面指出诗、词、曲之差别,另一方面又认为诗曲可以入词。针对这一论点,毛先舒在《与沈去矜论填词书》中就提出异议:“足下论曲与词近,法可贯通,鄙意仍谓尚有畦畛,所宜区别。”并在信中进一步申述了诗、词、曲语言风格上的差别,即对词的本体性这一疑难问题展开讨论。
词的起源问题被认为“是我国词学中的老大难问题之一”,也一直是词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谢桃坊甚至将这一问题列为词学研究第一大疑难问题。于此,前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特别是关于词体文学起源的时间问题,更是难以统一。如宋人朱弁《曲洧旧闻》、明人杨慎等皆主张创始于六朝;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张炎《词源》认为始于隋唐;宋人张侃《拙轩词话》、清初丁澎《药园闲话》、汪森《词综序》等又云滥觞于《诗三百》,见解差距之大,可想而知。此在清人论词书札中亦有探讨,如沈谦的《答毛稚黄论填词书》就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仆惟填词之源,不始太白。六朝君臣,赓酒诵色,朝云龙笛,玉树后庭,厥惟滥觞。流风不泯,迨后三唐继作,此调为多。飞卿新制,号曰《金荃》,崇祚《花间》,大都情语。艳体之尚,由来已久。”在沈谦看来,词之起源,不应始于唐代,而应追溯至六朝的玉树后庭之曲,唐五代词体文学的艳丽之风,也是沿袭了六朝风流。其主张与朱弁、杨慎基本相同,但是其立论的角度是文学风格,却与朱、杨异趣。
词体文学发展至晚清,更加兴盛。晚清学者用书札交流词学、探析词学疑难问题则更为普遍。据孙克强辑纂的《大鹤山人词话》一著统计,仅郑文焯的论词书札就有162篇之多,郑氏与当时词界名流王鹏运、朱祖谋、张尔田、夏敬观等皆有论词书札往来,可以说论词书札至晚清已经发展到极致。晚清学者通过书札交流词学,切磋辩难,举凡词学中的词律、词韵、校词等疑难问题,在他们的书札中皆有反映。
词在唐宋属于合乐可歌的音乐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曲乐的兴起,旧有的燕乐逐渐失传,词由音乐文学也慢慢演变成一种供诵读的案头之什。一般说来,唐宋词人的“按谱填词”乃是词的音律之谱,而明清之后的“按谱填词”一般为平仄格律之谱。由于词乐音律的失传,词乐遂成疑难问题。郑文焯审音识律,曾完成过《词源斠律》,词律、词韵问题在他的书札中皆有探讨,如在给张尔田的信中曾言到:
声调从律吕而生,依永和声,声文谐会,乃为佳制。然词源于燕乐,非专于乐府中求生活者。自古音谱失图,所可见只《词源》一书耳。故凌次仲《燕乐考原》,苦无图说,以阐发秘奥。至晚岁,始得玉田书,研究之,颇有创获。虽仲子书不为词旨昌明,而其所造,终不出燕乐章本,会心正不在远。曩尝博征唐宋乐纪,及管色八十四调,求之三年,方稍悟乐祖微眇,悉取《词源》之言律者,锐意笺释,斠若画一,岂旦夕能毕其说耶?
书札指出词的音乐文学这一本质特征,只有“声”(音律)与“文”(辞采)配合和谐,才称得上是好的作品,并指出词体文学与燕乐的紧密关系,这在当时是具有先见的。关于词韵问题,郑氏在给张尔田论词韵的信札中曾言到:
余旧纂词韵辨例,即据北宋晏、柳、周,南宋吴、姜诸名家韵例,历驳戈氏巨谬,极辨《广韵》古通转音例,仅可论诗,不可绳词。《菉斐轩韵》,亦未得幼眇,平水韵部,更不足征……近以同人说词中韵例,颇尠折中,爰尽发梦窗用韵微意,举似音谱,证以白石旁缀字律,案之五音,悉相吻合。
由于词体文学文体卑弱,素来不受校勘学家重视,辗转传抄,鲁鱼亥豕,在所不免,致使校词显得尤为困难。晚清词学家王鹏运、朱祖谋等于校词之学颇为用力,在理论与实践上皆有创获。郑文焯在论词书札中也多次论及校勘词籍的问题,如他在给夏敬观的信中曾论及校苏轼《南柯子》中“仙村”一词的问题,引证苏轼诗歌中的语词证明别本“仙材”之误;在给朱祖谋的信中探讨了致使校词困难的原因,指出旧谱零落、音吕失久、硕彦鸿儒不够重视、翻刻失误等造成了校词的困难,在给吴昌绶的信札中亦曾探讨过斠词审律的困难问题。词体文学的音韵格律之学及词籍校勘之学,正是在晚清学者的积极发掘中逐渐成为词学中的专门学问,在这种学问的发展过程中,论词书札起到了交流经验、切磋辩难的作用,有效推动了晚近词学的发展。至民国,词学才真正独立为一种专门之学。
三、清代论词书札的词学史意义
通过以上对论词书札作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论词书札在清代词学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有效推动了词学思想的交流,在推动词学复兴发展的过程中也功不可没。
首先,论词书札继承了书信这一文体的实用性特征及写法自由灵活的优点,因此可以从容不迫地表达自己的词学观点与思想。
书札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一种工具,其主要作用是互通有无,交流思想。清代词学研究繁盛,词学批评方式多样,与论词诗词相比,它不受韵律的限制,因此写法灵活自由,可长可短,其涉及内容可以更加广泛,便于研讨各种词学问题;与词话相比,论词书札作为单篇通信,其论点可以相对集中,便于对方接受;与词学选本相比,论词书札具有直接明了的特征,选本毕竟主要靠所选词作来彰显词学观,寓意于选,是一种间接传释,读者要从所选作品的数量、风格等方面的作品去间接领悟选者的意旨,而书札则可以方便迅捷地把自己的思想观念传递给想要交流的学人,如前文中毛先舒与沈谦的论词书札,通过书信直接把自己的词学观点传递给对方,方便快捷。
其次,由于书札一般是写给亲朋师友的私人信件,具有相对较强的私密性特征,故而论词书札更能直抒己见,秉持公心,而避免了沦入声气标榜的恶习之中。
清代词学流派林立,各词派为了推扬自己的词学主张往往借助群体的力量加以宣传、鼓吹,由于门户之见,在词学批评的时候难免入主出奴。如蔡嵩云所言:“自来评词,尤鲜定论。派别不同,则难免入主出奴之见。往往同一人之词,有扬之则九天,抑之则九渊者。”随便翻开清人选清词中的评语,以及清人词话、序跋中的对时人的词学的批评,都容易找到这种声气标榜的痕迹。如杜诏在给顾贞观《弹指词》写序时谓:“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顾、杜有师生之谊,杜序云此难免有溢美之嫌,此类似于今天的“红包批评”。这种状况之所以常见,很大原因上在于这些评语本身即是作者要求评者为其所作的批评,虽然作者评者双方不一定就如何作评明确商谈,但评者仍多会心照不宣地褒奖赞美,夸大作品的优异之处。以至于今人在编纂《全清词》的时候,对这种序跋文字进行了全面删汰:“清人词集序跋菁芜不一,本书一律不录。清初风气,刻本每详列师友评语,类多应酬,亦从删略。”虽有些过激,但足见对这种不良风气的厌弃。其实对这种现象,清人也多有批评,如《四库全书总目·十五家词提要》即指出其间的点评是“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四库全书总目·词苑丛谈提要》亦云其“标榜以借虚声”。虽然批评激烈,但是没有刹住序跋批评中的这股歪风。
而且书札作为私人之间交流思想信息的工具,具有相对较强的私密性特征,故而清人在论词书札中一般能够真诚地阐述自己的词学观点和主张。标榜声气的现象在论词书札中很少见到,如我们在前面论及的毛先舒与沈谦的论词书札,双方各持己见,互相辩难;潘德舆的《与叶生名沣书》中也可以看到他对张皋文《词选》的激烈批评;郑文焯的论词书札中也可看到这种情况。这些都可证明清人在论词书札中秉笔直言的特征,绝少谀词,这些正是书札文体的特征。如褚斌杰言:“我们可以从书信中,比较多的看到生活的真实和思想感情的真实。”因此从论词书札中更能见出词论家真实的词学思想,确实难能可贵。
第三,清代论词书札在促进学术交流,推动词学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类似现代学术期刊杂志的功用。
清代的学术尽管号称鼎盛,但是当时并没有现代意义的学术交流平台,如学报、报纸杂志、网络等,论词书札在此环境下,实际上起到了这种交流传播的作用。梁启超在论及清代的“学者社会”时就曾指出清人不像宋明时人聚徒讲学,也没有欧美之种种学会、学校作为讲习之所,但是他们在学术上每有新解,则“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清代学人的这类函札补充了他们之间缺少聚居辩论交流的不足。无独有偶,美国学者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一著中也曾关注到这个问题,他援引大卫·尼维森、奥泽·瓦莱的观点,指出清代没有学术期刊,学者之间学术交流的书信在当时广为传播,其实就弥补了这种学术交流的缺憾,“当时,各种信件文稿常为朋友传抄,甚至交给他们阅读、讨论。章学诚采用这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如钱大昕都以这种形式发表自己的书信。许多学者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学术界中肯的评价、认可和广泛注意。”词学作为当时一种比较边缘的学术门类,其实也是通过书札的形式在社会上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如前文所引潘德舆批评张惠言的书札就得到了谭献的关注,并在《箧中词》批注与《复堂日记》中进行了阐释;而晚清朱祖谋的论词词《望江南》其十二论张惠言词谓:“回澜力,标举选家能。自是词源疏鑿手,横流一别见淄渑。异议四农生。”不仅指出了张皋文别裁伪体的识鉴能力,更兼顾了不同的批评声音,其中“异议四农生”,即是对潘德舆(按,潘德舆字四农)《与叶生名沣书》的吸收,足见潘氏的这封书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词学家的论词书札在缺乏学术期刊交流的时代起到了交流词学思想的作用,这种交流有效扩大了词学在学术圈中的影响,有效推动了词学的复兴与繁荣。
总之,论词书札与论诗文书札意义一样,起到了传递学术信息、交流学术思想的重要作用,并且它与词话、词籍序跋、词学选本以及论词诗词等一起对清代词学的互动交流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清代词学也在这些合力之下走向兴盛。清代论词书札文献亟须系统蒐辑整理,其词学史意义亦当受到应有的重视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