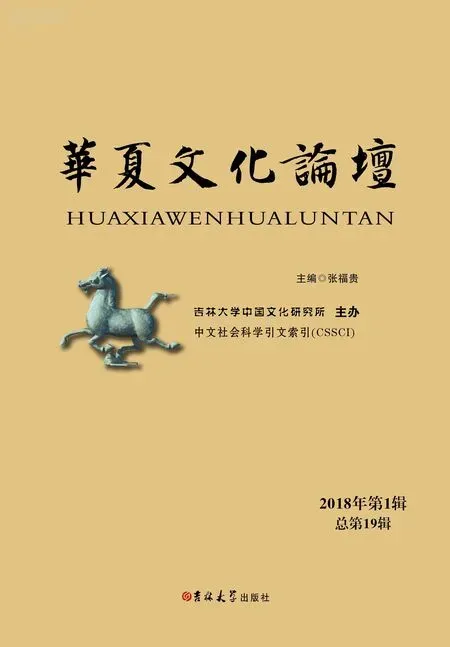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特点及价值
谭中华 彭 爽
【内容提要】北京话是普通话的最重要来源。近年来,人们对北京话的关注越来越多。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是研究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话词语的重要语料。研究发现,小说中的词语呈现出儿化词众多,同素逆序词和异形词并存,重叠词使用频繁的特点。并且小说中的词语可以丰富北京话词语乃至汉语词汇史研究,对北京话辞书编纂具有补充价值,同时对研究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地区的民俗社会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是1919年7月至1921年10月间,发表于《京话日报》上的报刊连载小说,属于蔡友梅的晚年力作。鉴于《京话日报》这类报刊连载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为普通北京市民,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其主要内容基本上也是围绕着普通北京市民,特别是中下层市民为主题展开的,它着重于对普通民众开展启蒙教育,力图广开民智,改变民众愚昧无知的状态。
蔡友梅,本名蔡松龄,号“友梅”。因其对梅花情有独钟,故有多个以“梅”命名的别号,如“老梅”“梅蒐”“梅叟”“松友梅”等,其晚年所作小说自称常以损人为能事,故又有“损”“损公”等别号。其生卒年月,以往均语焉不详。近几年,刘云、王金花、刘一之等根据相关资料考证,认为他生于1872年,卒于1921年,但在具体日期上也存在分歧。
关于蔡友梅的生平,我们目前所见资料记载的并不多。从小说中的部分记载资料来看,其早年接受过一些传统教育,从事过中医行业。后来随父亲上任,做过文案委员。1904年开始直至其去世,蔡友梅在《京话日报》《公益报》《进化报》《顺天时报》《白话国强报》任职,期间有大量作品问世。目前所能见到的有一百多部,其中最早的小说是1907年连载于《进化报》的《小额》,最晚的是1921年连载于《京话日报》的《鬼社会》,《鬼社会》还没写完,作者阖然辞世。
一、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语料概况
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共27种,目前存世的有26种,缺第二十三种。这26种分别为:《姑作婆》(第一种)、《苦哥哥》(第二种)、《理学周》(第三种)、《麻花刘》(第四种)、《库缎眼》(第五种)、《刘军门》(第六种》、《苦鸳鸯》(第七种)、《张二奎》(第八种)、《一壶醋》(第九种)、《铁王三》(第十种)、《花甲姻缘》(第十一种)、《鬼吹灯》(第十二种)、《赵三黑》(第十三种)、《张文斌》(第十四种)、《搜救孤》(第十五种)、《王遯世》(第十六种)、《小蝎子》(第十七种)、《曹二更》(第十八种)、《董新心》(第十九种)、《非慈论》(第二十种)、《贞魂义魄》(第二十一种)、《回头岸》(第二十二种)、《方圆头》(第二十四种)、《酒之害》(第二十五种)、《五人义》(第二十六种)、《鬼社会》(第二十七种)。这26种小说,作者又分为警世小说(《姑作婆》《张二奎》《小蝎子》《曹二更》《回头岸》《方圆头》)、社会小说(《苦哥哥》《麻花刘》《库缎眼》《刘军门》《董新心》)、伦理小说(《理学周》)、哀情小说(《苦鸳鸯》)、实事小说(《非慈论》《贞魂义魄》)等几类,其他未列作品作者没有指明类别归属。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所能见到的公开出版发行的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主要有如下两个版本:
1997年11月出版的由于润琦任主编的《清末民初小说书系》中《社会卷》和《警世卷》简体横排本,共刊载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10种,分别为(按此书刊载顺序)《搜救孤》(第十五种)、《刘军门》(第六种》、《赵三黑》(第十三种)、《非慈论》(第二十种)、《董新心》(第十九种)、《花甲姻缘》(第十一种)、《库缎眼》(第五种)、《铁王三》(第十种)、《小蝎子》(第十七种)、《曹二更》(第十八种)。
2014年8月出版的由周建设任主编的《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损公作品》繁体竖排影印本,共刊载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24种,除第二十三种缺失之外,第二十六种《五人义》、第二十七种《鬼社会》也未刊载,具体原因不详。
二、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概貌
从词语的音节结构来看,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北京话词语中复音词占绝对多数,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话的真实面貌。单音词中动词占多数,也有少量的名词、副词、介词和语气助词。多音节词(三个音节及以上的词)以名词居多。
单音词:炸、杓、寻、瞧、搭、拍、敬、露、拧、净、竟、刚、将、所、很、狠、罢、哪、啦等。
复音词:打起、伴宿、帮喘、耍话、存立、抓弄、撞钱、告帮、具贴、办地、搂搂、瞧瞧、挑眼、骨立、烈害等。
多音节词:房折子、活局子、大清早儿、屁股蛋儿等。
从词语的语义内容来看,由于小说描写的大多是普通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家庭琐事,所以小说中出现的更多的是有关日常生活的常用词语,涉及面比较广,展现了清末民初普通北京市民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
有关时间的词语:晌午、晚晌、大天白日、多早晚儿、多喒、多会儿、见天儿、工夫/工夫儿、功夫儿、从前、从先、趁早儿、这会儿子等。
有关食物的词语:落花生、煮饽饽、肉面、馄饨、炒里脊、肉皮辣酱、窝窝头儿、菠菜汤、鱼翅、鸭果羹、四大海、点心、皮酒等。
有关行业的词语:饭馆子、茶馆儿、烟馆、宝局、当铺、果摊子、煎炒铺子、大戏院、铁铺、煤铺等。
有关称谓的词语:奶奶、嬷嬷、姑爹、姑爸爸、二爹、公母俩、老两捆子、伊罕、夸兰达、库兵、三小儿、姑娘儿、乡彆子、无赖子等。
小说中还出现了许多当时北京话中的成语、俗语和歇后语。正如作者在小说《库缎眼》中所言“本报既开设在北京,又是一宗白话小说,就短不了用北京土语”。
成语:痰迷心窍、哓哓不休、痴若木鸡、千感万谢、就棍打腿、粘牙倒齿、指天画地、千载一时等。
俗语:医不扣门;老怕伤寒少怕劳;吃王莽的饭给刘秀办事;杀人得闹两把血;英雄爱好汉,孟良爱焦赞,无来由专交不要脸。
歇后语:一跟耙齿儿——不用搂了;黄连擦粉——苦捣扯;武大郎服毒——吃也死,不吃也死;吊死鬼儿诈尸——挂不住了。
这些词语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现实状况和人们的文化心理,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今天,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词语绝大多数已经消失了,有的虽然还在使用,但语素发生了改变。如“痴若木鸡”,现在则改为“呆若木鸡”。
三、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特点
(一)儿化词众多
小说中,儿化词最为常见,“儿”在词语中的位置也多样,有的附在末尾,有的位于两个或多个语素中间,其语用也非常灵活,带有浓郁的北京话色彩。这些儿化词,大多数至今仍活跃在北京人的口语中,很多北京方言词典也有收录,如贾采珠《北京话儿化词典》。但也有一些当时的儿化词,如“一场儿”“乱际儿”“夫人儿”,现在不再儿化了;有些当时未儿化或儿化不彻底的,如“信”(表示消息、口信)、“工夫/工夫儿”(表时间)、“有点/有点儿”现在已经彻底成为儿化词;还有一些当时的儿化词,“儿”的位置在词中,如“爷儿俩”“猫儿眼”“老哥儿们”,现在则一般说“爷俩儿”“猫眼儿”“老哥们儿”,“儿”的位置挪到了词尾。不过这些儿化词大多数在儿化前后或改变“儿”在词中的位置后仍然词性相同,语义相近。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儿化词,在儿化前后词性、语义、感情色彩、组合搭配上都发生了变化。
1.词性转变。
有些词在儿化之后,词性发生了转变。如有些动词儿化后明显具有了名词的性质,如: “借着忙乱之际,我带着孩子由后门儿溜出去,我们就出城,把他掐死扔在护城河里,也就完啦。”(《搜救孤》353页)这里“溜”是指偷偷离开逃走的意思。而其儿化后,“溜儿”成为名词,表示附近的意思。如:“老曹向来得人,那溜儿街坊,不差甚么他都给作过活。”(《曹二更》83页)再有一些形容词儿化后,也具有了名词的性质。如:“发引的那天,好不热闹。库缎眼打发他傻儿子拴头前来送殡,到底他也没露。”(《库缎眼》238页)这里的“热闹”明显是形容气氛浓烈,是形容词。而其儿化后,“热闹儿”则指热闹的景象,转变为名词。如:“后来喊伺候坐堂,委员已然入座。瞧热闹儿的人,围了个风雨不透。”(《赵三黑》68页)
2.语义转变。
有的是词语儿化后语义色彩发生转变,“小人”表示品行拙劣的人或用于地位低下的人自称,如:“库缎眼原是势利薰心的小人,小靴子儿一耍他,听着也倒有理,当时回嗔作喜,连连的点头。”(《库缎眼》231页)而儿化后“小人儿”则表示招人喜爱的人,多用于称呼小孩子。如:“王四说:‘这个小人儿,你别瞧他当巡丁,相貌很好,志向也不错,将来一定有起色。’”(《刘军门》289页)有的词语儿化后语义范围发生转变,“功夫”表示本领造诣和耗费的时间精力,如:“这小子一耍骨头,毛豹倒乐啦,说:‘孙子,我领教领教你的真功夫。’”(《小蝎子》35页)而儿化后“功夫儿”则仅仅表示耗费的时间精力,语义范围缩小。如:“记者担任四处报馆的小说,还有三处讲演,本来没功夫儿看义务病。”(《库缎眼》251页)不难看出,儿化造成的这种语义转变,带着浓郁的京味儿,体现了北京话俏皮、诙谐的特点。
3.感情色彩转变。
小说中有些词语儿化后,往往附着以疼爱、亲昵等感情色彩。小说中许多称谓词语都被儿化,如姓名称谓“小毛儿”“小常儿”“招哥儿”“三房儿”“丁儿”“更儿”等,亲属称谓“哥儿们”“娘儿俩”“姑娘儿”“姪女儿”等。这些词语儿化后,让人们觉得更加温和、亲切,也使得北京话不断地被激活、刷新,更加丰富,表达更细密,因而更具活力。虽然也有“死心眼儿”等表示贬义的词语,但出现数量和频次很少。
4.组合搭配转变。
小说中有些词语,单独使用不儿化,而在和某些词语组合使用后,则必须儿化。如“庙”“钱”“买卖”单独使用时一般不儿化,如:“老曹又应了两号阔买卖,这两年很积蓄了几个钱。”(《曹二更》81页)但它们与“小”组合构成“小×”时则必须儿化,如:“他赠了小的二十两银子,新倒的这个小买卖儿。”(《刘军门》292页)而在和“大”及其他词语组合时则不儿化。
从词汇的层面看,儿化的使用增强了北京话的表达功能,丰富了北京话词汇,使北京话更加诙谐、生动,富有表现力。
(二)同素逆序词、异形词并存
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的思想文化在中国传播得更加广泛,加之“五四”运动后白话文不断兴起,这些都影响推动着北京话词语乃至汉语词汇在不断地产生、演变、保留和淘汰中向前发展,形成了同素逆序词、异形词不断涌现并存这样的一种局面,是当时的汉语词汇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典型表现。
1.同素逆序词
同素逆序词是指构成语素相同,但顺序相反的词。小说中出现的同素逆序词主要有直简—简直、较比—比较、败失—失败、欢喜—喜欢、改悔—悔改、康健—健康、竞争—争竞,等等。这些同素逆序词,有的语义完全相同,如:“每年虽然也开山,比较从先,虽不至一落千丈,也够一落五百丈的资格。”(《苦哥哥》76页)“丁狗子要是来了,虽然也欢迎,较比从先就淡了许多。”(《库缎眼》266页)这里“比较”和“较比”语义及用法完全相同,都是“与×相比”的意思。从小说中出现的频次看,“较比”频次远远大于“比较”,现代汉语中则一般用“比较”,“较比”很少出现,一般用于方言。有的语义相近,如:“那天到了太原,打听有范三的铺子,二人一见,好几年没见的朋友,彼此非常的欢喜。”(《铁王三》104页)“硕卿听罢一切的情形,当时又喜欢又难过,当时也掉了几点眼泪。”(《搜救孤》97页)“曹大进屋里就给师娘磕头。富二太太也很喜欢他。”(《曹二更》85页)《铁王三》中的“欢喜”和《搜救孤》中的“喜欢”都是表示“愉快、高兴”的意思。而《曹二更》中“喜欢”则表示“喜爱”的意思。从小说中“喜欢”出现的频次看,表示“愉快、高兴”这一语义的出现频次远远大于表示“喜爱”的。现代汉语则相反,“喜欢”表示“愉快、高兴”这一语义远远没有表示“喜爱”出现的频次高。
2.异形词
异形词是具有同一种意义及几种书写形式、读音相同或相近、内部结构相同的一组词,是同一个词位的不同变体。小说中使用的一些异形词主要有简单截说—简段捷说、钱粮—钱糧、名词—名辞、嘴吧—嘴巴、这挡子—这档子、净—竟,等等。有些时候,甚至在一句话内,就同时存在着两个异形词,如:“吴寿花了没有几天,早已完了,一时摘借无门,急中生巧,指着他那分马甲钱粮,借了十五两银子(还是那个年月,搁在如今,一分马甲钱糧,也就借上十块钱,这辈子也就算逃不出来了)。”(《苦哥哥》63页)汉语词汇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大量的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假借字,相应地造成了一个词语对应多种书写形式的情况长时间大量存在,但这些不同的书写形式所要表达的意思几乎没有太大区别,这些异形词都是历时的语言现象在共时层面的反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词语的语源信息。如尖团音的分化归流,是近代汉语声母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清中叶开始,北京话精组和见组的细音全都因腭化而合流。小说中范围副词“净”,几乎都写作“竟”,反映了精组和见组合流的语音演变特点。
汉语中同素逆序词、异形词的存在由来已久,清末民初时期使用更加频繁、广泛,对这些同素逆序词、异形词进行深入研究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汉语形成初期的词汇状态,对统一和规范现代汉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重叠词使用频繁
汉语是一种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但小说中,出现了很多重叠词,用法上也比较复杂,这些重叠词中的大部分在现代汉语中已不再重叠。如:“他给大家作了个罗圈儿揖,说了吴大爷一套万恶,又哭了一鼻子(这块骨头)拿着十五吊钱,抱抱怨怨的去了。”(《苦哥哥》61页)这里重叠词“抱抱怨怨”在现代汉语中则不再重叠。小说中名词性重叠词、动词性重叠词、形容词性重叠词居多,按照构成形式,大体又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AA式
名词性AA式重叠词主要集中在亲属称谓词语的使用上,如“妈妈”“奶奶”“叔叔”“爸爸”等,这些亲属称谓词语的重叠式与非重叠式相比,比较亲切,一般用于面称,使用场合也比较正式。动词性AA式重叠词数量较多,往往表示尝试,试一试的意思,如“瞧瞧”“讲讲”“说说”等。形容词性AA式重叠词,一般表示一种程度上的加深,如“好好儿”“大大”等。
2.AABB式与ABAB式
名词性重叠词仅见AABB式,而没有出现ABAB式。如“男男女女”“祖祖辈辈”“老老少少”“花花草草”等,往往表示全部、周遍这样的一种整体意义。如:“第二天一清早,男男女女全来啦,这个就抱布,那个就扛麦子,银子也到了手啦。”(《铁王三》100页)动词性重叠词一般采用ABAB式重叠,如“商量商量”“打听打听”“领教领教”“劳动劳动”等,往往表示动量或时量上的减少,含有稍微的意思。小说中还有一些动词性AABB式重叠词,如“唙唙咕咕”“抱抱怨怨”,往往与“的”一起连用,表示的动作行为是能够持续反复进行的,口语色彩非常浓厚,如:“大家的视线,一齐注射吴大爷,甚至于还有唙唙咕咕的,吴大爷满心里的话说不出来。”(《苦哥哥》57页)形容词性重叠词,AABB式的较多,如“忸忸怩怩”“庸庸碌碌”“浑浑实实”“纯纯厚厚”“大大咧咧”,等等。
3.AAB与ABB式
名词性AAB式与ABB式重叠词主要集中在饮食和称谓词语中,如:“窝窝头”“嬷嬷爹”“煮饽饽”“姑奶奶”“叔爸爸”等。动词性AAB与ABB式重叠词很少,往往表示尝试试探的意思,如:“试问问共和国妇女的资格,你们准够吗?不学好处,竟上坏毛病,还不及人家不够资格的好哪! ”(《花甲姻缘》80页)形容词性重叠词以ABB式最常见,如:“醉醺醺”“恶狠狠”“好端端”“白花花”等。如:“王九赖喝了个醉醺醺的告辞而去,王英跟着也就走啦。”(《铁王三》106页)这种ABB式的形容词性重叠词,从语义层面上看,单音节语素A承担着整个语义的最主要部分,而叠音语素BB则只起到了补充解释说明的作用,增加了形象色彩。如果把叠音语素BB去掉,其基本语义变化不大,不过其形象色彩却大打折扣。
不难看出,小说中的重叠词形式比较丰富,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些重叠词的使用,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四、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价值
(一)对北京话词语乃至汉语词汇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早期北京话词语的研究,多以19世纪以前或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文献为主要参考语料,清末到民国初年的北京话面貌,自然就出现了断层。因此,要想窥见早期北京话全貌,必须下大力气寻找19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北京话语料。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恰好处在这一时间段上,具有极其重要的语料价值。
蔡友梅在北京生活多年,京腔京韵顺手拈来,并且限于报刊连载小说的阅读对象是中下层市民,作者在语言选择上尽可能地通俗化与口语化。大量口语化语言的使用使小说十分贴近日常生活,显得自然生动。尤其是很多词语的选用上,大都是北京方言土语,其中有些方言土语,现代北京人仍在使用。但是绝大多数词语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和演变,几乎不再使用,甚至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都不能准确地说出它们的含义。认识和了解这些北京话词语发展演变的过程,对这些北京话词语进行准确地描写分析,可以为北京话词语乃至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大量的词汇发展演变的直接证据,从而为全面地疏理、描写、归纳与阐释汉语词汇史服务,为词汇史的分期提供直接的语料依据,具有重要的汉语史价值。
(二)对辞书编纂具有补充价值
小说中的词语资料,对北京话辞书乃至汉语辞书都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蒋绍愚指出“构成一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系统的主要的东西,还是那个时期中使用得较多的常用词。而近代汉语中的常用词,还有不少保留在现代汉语中。这些词,我们一看就懂,不需要考释;如果从阅读作品的角度看,似乎不需要进行研究。但从汉语历史词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还要研究这些词语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如果要编纂一部说明每个词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的汉语大词典,也需要进行这种研究”。以北京话辞书为例,目前主要有金受申《北京话语汇》、陈刚《北京方言词汇》、宋孝才与马欣华合编《北京话词语例释》、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杨玉秀《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齐如山《北京土话》、傅民与高艾军合编《北京语词典》、董树人《新编北京方言词典》等。这些辞书对北京话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然而我们也发现以上辞书在收词、书证、释义等方面也有疏漏之处。小说中的词语实例能够补充辞书词条数目,补充提前辞书词条例证,补充辞书词条义项,具有重要的补充价值。
1.补充辞书词条数目
蔡友梅在小说行文中有加括号注释的习惯。“近来动笔,但能不用土语,我是决不用。实在必得用土语的时候儿,费解的不用,太卑鄙的不用,有该注释的,咱们加括弧”。这些用括号注释的土语,可以补充现有辞书的条目。如《北京土语辞典》收录“喝儿呼着”“喝儿了蜜”两条,《北京话词典》收录“喝高了”“喝了蜜”“喝礼”三条,而小说中“孙四哈哈一笑,说:‘我喝碗冬瓜汤罢’(北京土话,管说媒叫作喝冬瓜汤。直言之,冬瓜汤就是谢媒的酒席)。”(《花甲姻缘》85页)可以补充“喝冬瓜汤”一条。其他还有 “拜门墙”“办地”“出倒”“灌米汤”等在上述词典中都没有收录,将这些词条补充进来,可以丰富北京话辞书词条数目。
2.补充提前辞书词条例证
现有的几部北京话辞书中,《北京话词语例释》《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北京语词典》这三部对很多北京话词语列出了一些书面例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傅民与高艾军合编的《北京语词典》中引入了蔡友梅《小额》中的部分例证,但都没有涉及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大量词条例证。如“爽得”在小说中频繁出现,如:成氏冷笑了两声,说:“好事多磨,迟则生变,一不作二不休,这档子事爽得由你一个人儿包办。”(《搜救孤》98页)《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没有收录该词。《北京话词典》收录该词,所举书证却是老舍1927年作品《赵子曰》中的用例,用例稍晚,小说中大量的词条例证可以丰富提前辞书中的词条例证。
3.补充辞书词条义项
义项是辞书的核心部分,是体现辞书实用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关键所在。前文所列这些辞书,从整体上而言,对北京话词语的释义都是很精当、完备的。但也偶有疏漏的情况,如对“搭”的释义,《北京土语辞典》仅有“加、添”一个义项;《北京方言词典》和《新编北京方言词典》都有“贴、饶、赔”“相互替补,交替”两个义项;《北京话词典》主要有五个义项:1.数量的添加,财物的耗损;2.丢掉性命;3.因由的增加;4.硬性搭配;5.联系。小说中“当时收拾了一间屋子,知会了几家儿至近的亲友,预备了几桌酒席,草草的就把人搭过来啦。”(《苦哥哥》54页)再有,“定下媳妇儿没过门,因为老亲病重,赶紧搭过来,北京俗话叫作暴搭,又叫作暴抬。”(《库缎眼》258页)这里,“搭”明显有“迎娶”的意思,可以丰富补充上述辞书词条义项。
(三)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
词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小说以中下层普通北京市民为主要描写对象,出现了大量与其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相关的词语,如“相亲”“前途”“放定”“过礼”反映的是婚礼举办前的一些事项,“迎娶”“谢亲”“迎亲”“送亲太太”“官客”“鼓手”“送子(曲牌子)”“吃子孙饽饽”等则是对整个婚礼过程的描写。不仅这样,小说中还出现了“晚婚”“断弦”“续弦”“小星”“童养媳妇”“三妻四妾”等词语,这些词语对当时男女婚姻习俗做了忠实而全面的记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的婚姻文化习俗。
小说中,还出现了一些特殊的称谓词语,如“叔爸爸”“姑爸爸”等,作者蔡友梅在小说中也提到“要说一切的称呼,北京最为复杂,因为这个地方,是全球相见,五族杂处的地方儿,什么称呼都有。即如父母的称呼,父母固然是正义啦,可是有称呼爹娘的,有称呼爸爸妈妈的,在旗朋友们,称呼阿玛奶奶,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都是那档子事,至于叔父一节,有叫叔叔的,有叫爹的,最可笑是有叫叔叔爸爸的。叔就是叔,爸爸就是爸爸,叔爸爸我摸不清怎么讲。诸如此类,不可枚举。这和当时北京地区的社会风俗密切相关。”陈鸿年也指出“不知道哪儿传下来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兴的,在北平好像人人都喜欢当爸爸,变着法儿的,叫人管他叫爸爸”。这些特殊的称谓词语反映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称谓习惯,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价值。
蔡友梅“新鲜滋味”系列小说中的词语忠实地记录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话的真实面貌,特点鲜明,价值重大。全面、科学地调查和描写北京话,及时抢救北京话方言资料,对北京话乃至汉语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