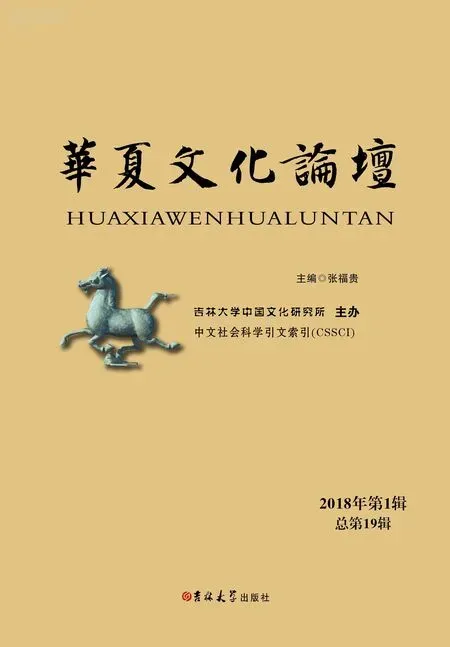论严歌苓《芳华》中的后革命叙事
戚 萌
【内容提要】对于“文革”的伤痕记忆使书写革命成了几代作家笔耕不辍的主题,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编织着特殊时代的“文革记忆”,从最初的宏大叙事到后期的日常叙事,革命历史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遭遇了多重书写,进入了后革命叙事时代。旅美作家严歌苓以其童年亲历“文革”的经历一次次将目光聚焦于20世纪中国政治的波诡云谲、风云变幻。她用狂欢的故事与狂欢的语言,细数不仅仅是“芳华”时代的美好青春韶光,更为重要的是展示出了我们从未曾发掘的内心黑洞到恍然的幽秘心理。在严歌苓笔下恣肆飞扬的文字中,有举重若轻的幽默、攻城略地的反讽、最终审视于“人性”这个终极的命题,审视于我们终归与心同在、难以启齿、难于关注的“自我”。当日常隐于荒诞,荒诞形变为日常,穿梭周而复始在不同年代,但不可或缺的是清醒、批判以及反思和救赎。严歌苓正是以其深切的人文关怀,透视人类生存的本质,深度剖析了个体在群体强权面前的无助以及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沦丧,边缘身份以及双重文化的视野更是拓宽了严歌苓独具的视野,使其新作《芳华》更加凸显出其独特的后革命叙事特征。
旅美作家严歌苓的新作《芳华》承袭了其一贯对于故土——中国历史的回望,尤其在新世纪之后,她一次次将目光投射于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写出了其间中国革命的波诡云谲、风云变迁。更为重要的是,严歌苓独辟蹊径,没有遵循以往传统对于革命的叙事模式,而是消解了对于革命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的是它带给平凡百姓生活的巨大冲击和变化,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是革命风卷残云之后个体的真实生存状态。这具有典型的“后革命叙事”的特征,诚如陶东风所言:“这些小说虽然不是重在再现革命历史事件,但是却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作为激进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给人,特别是普通人带来的影响。”虽然,特殊时期的革命历史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遭遇了多重书写的困境,很多作品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对革命历史的意识形态,或冷静叙述、或变通扬弃、或消费戏说、或解构颠覆,但共通之处是都从不同程度上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经典革命叙事,进入了“后革命叙事”时代。严歌苓的《芳华》并没有陷入光怪陆离戏说革命的漩涡之中,她逃离了消费革命的的媚俗套路,始终秉承着的是对于人性的深刻挖掘,重新审视革命年代所带给人们心灵上的异化。
从《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白麻雀》《雌性的草地》《一个女人的史诗》等作品开始,严歌苓的很多作品都是以军旅题材为背景,但多是以一个作家的客观身份来为那个时代的军人塑像。而她的长篇小说《芳华》则是具有浓厚的自传色彩,是以第一人称来描绘她当年亲历的部队文工团生活。在1970年时,严歌苓参军入伍,成为一名原成都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那年她仅仅12岁。在文工团期间她随部队多次入滇藏,在1979年,她甚至还主动请缨,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她在部队献出了整整13年的青春年华,她自己也直言:“那段生活对我太重要了,她左右我一生的走向。”
《芳华》可以说就是以这段文工团的亲身经历为原型模板而形成的小说。“写这个故事所有的细节不用去想象、不用去创造,全是真实的,我写这座楼,就回忆这里的地形地貌,哪里是排练厅,哪里是练功房,脑子里马上还原当时的生态环境。”严歌苓认为《芳华》是一次非常自然的写作,是她最诚实的一本书。作为走遍了大半个地球的作家,有能量去不断挖掘别人背后的故事,而今却再也不仅限于旁观,这一次严歌苓终于也“触摸”了自己。即使经过岁月漫长淘洗历练,但这段军旅生涯却像鹅卵石一样愈经打磨,却愈发变的光亮如新,在她生命的卷轴里熠熠生辉,这束光辉指引着严歌苓终于找寻到了写作的意义,作品也直抵心灵的叩问。
一、扭曲与“阉割”:荒诞时代的人性书写
严歌苓年仅八岁时恰逢“文革”开始,浩浩荡荡的大革命使她文人的父亲、舞蹈家的母亲迅速成了专政对象,小小年纪的她就饱尝人情冷暖。在她的短篇小说集《灰舞鞋》中,严歌苓就曾化身小穗子,她以纯真的儿童视角透视了那个荒诞的时代,小说中小穗子的爸爸就是一个被扣上“走资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形象,“穗子爸胸口贴个白牌子,上面写明他是什么罪名,第一、第二、第三,按罪大罪小排下来。”“没人要做穗子的朋友,因为她有个罪名是‘反动文人’的女儿”。这段孤独而难忘的个人经历,留驻在严歌苓的整个青春记忆里。过了四十余年再次回望儿时的种种经历,严歌苓坦言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是一个荒诞的时代。在她的新作《芳华》中,我们尤其能感受到革命时代某种强大的力量使人异化成为“非人”,使健康活泼的青年变成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的全过程。不禁让人想起鲁迅曾描述的那个年代:“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满页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芳华》中的刘峰是一个像雷锋一样的好人,他帮孤儿“括弧”无偿挑水、安慰因父亲“反动”身份而被战友排挤的“我”、亲手打造木质沙发送给要结婚的战友做贺礼、在别人都嫌弃何小曼身上有怪异味道时,他还主动化解尴尬完成了对她的托举动作。他乐善好施,是军中的楷模,在那个信仰“平凡即伟大”的岁月里,他一次次地被推举成为“雷锋”榜样,获得了诸多殊荣。然而就是这样近乎完美的人,却因为一次“触摸”事件,而断送了军旅生涯,刘峰所有之前的荣誉与光环全部淹没在了林丁丁声嘶力竭的救命呼喊声中。这“触摸”实际并未掺杂龌龊的想法,仅仅是慌乱之中不小心触碰到了脊背而已。可在那个荒诞的时代,有谁愿意去理解一个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又有谁还记得所谓“英雄”也不过是肉体凡胎呢?对于人们心中的“英雄”形象来说,他是不可以有私情的,肉体与灵魂全部被打上了镣铐,献上了祭坛,这无疑于是对男性的一种人性阉割。所有曾经刘峰帮助过的人,全都不分青红皂白地跳出来批判指责他,因为在那个时代“‘讲坏话’被大大的正义化,甚至是荣耀化了。谁谁敢于背叛反动老子,谁谁敢于罢领导的官,谁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从讲坏话开始;”“一旦发现英雄也会落井,投石的人格外勇敢,人群会格外拥挤。”或许,荒诞时代阴霾笼罩下的不仅仅是对平凡人物情愫的阉割,而个体在群体强权面前的无助以及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沦丧,才是这场浩劫最大的人性缺失。
然而严歌苓并没有停下笔触,她在荒诞时代继续剥离层层虚伪谎言的外衣,自觉于人性“吊诡”的探寻:从小生活在“变形”家庭中的何小曼,一直谨小慎微地活着,极度渴望被爱,甚至不惜装病来博取大家的眼球。但不经意间的善举将小曼推到“英雄”的领奖台前时,从未得到过关注的她在这种荣誉的强压攻势之下竟然疯了,她不能相信报纸图片中那个像白衣天使般的女孩就是一直生活在黑暗中渺小的自己;何小曼的父亲因为“右倾”被逼无奈自杀,何小曼的母亲无端承受着丈夫“污点”所带来的阴影改嫁,在新家里“母亲的变形必须随时,在不同的亲人面前要拿出不同形状。能够想象,每变一次形,都不无疼痛,不无创伤。”也可以想象,家庭中本该弥漫着的亲情温暖,就在这一次次的“变形”之中消耗殆尽;萧穗子的父亲在被“改造”之后不得不学会的人学庸俗、拉拉扯扯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辛酸与无奈;郝淑雯对于萧穗子友情的出卖与背叛、大家集体对于何小曼的欺侮与排挤、对于刘峰不实的批判与指责,这些本该享受青春阳光的他们却都被种种怪异荒诞的阴霾所支配、笼罩,被政治无情倾轧之后而失去了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盘剥众人后,我们发现无人幸免,《芳华》中似乎所有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都被异化成“非人”。《芳华》是一张人性的展示台,是一个不断碾压、拷问人性的砧板,荒诞时代中对于人性的扭曲与“阉割”,对于“性”的不可名状与压抑,被严歌苓悉数剥落蒙昧的外衣,她冷静执笔,似剑一般刺入那个时代的一团暗黑之中,手起刀落,不着痕迹,展示给我们的是却是人性的皮开肉绽,丑陋不堪。文学归根结底是人学,它所关注的对象始终是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莫言在谈及自己为何会获奖时说:“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族群的局限。”严歌苓深谙这一道理,因此她的新作中有着对人性更为深刻的剖析和解读,有着力透纸背的力量。
二、反思与救赎:开在废墟之上的花
(20世纪)“90年代以降,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消费主义思潮极度高涨,同时兴起了一种游戏人生、游戏革命、游戏历史的文化态度和审美姿态。”后革命氛围语境下,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都为了迎合大众而出现了戏谑式的革命书写,网络文学更是此类革命书写的主力军,《样板戏之〈宝黛相会〉》《新版白毛女》等更是将严肃革命的“样板戏”“文革批斗”等进行了滑稽模仿的颠覆性书写。严歌苓的很多作品如《陆犯焉识》《柳腊姐》《白蝶标本》《黑影》《老囚》乃至于新作《芳华》,都是在用她特有的方式来书写革命。但在市场经济泥沙俱下的大浪潮之下,严歌苓却与其分道扬镳:她着墨于冷静的后革命叙事书写中,没有呐喊、没有怨怼,也没有戏谑,种种惨烈情状在她心中虽留下了无法抚平的伤痕,但揭露伤痕却并不是严歌苓写作的终极目的。细细品读,在《芳华》这本自传体小说娓娓道来的叙述之中,情节故事并不复杂,也没有过多的阴谋吊诡潜藏暗涌,但读毕给人感觉却是沉甸甸的,这种内心的沉郁压抑来自于严歌苓文字中渗透着的对于“集体主义”的过度崇拜、“英雄主义”的祛魅与瓦解、“人本主义”扭曲与缺失的重重反思。严歌苓在《芳华》的现场签售会曾表示,这本书有她的反思忏悔在里面,当年欺负战友黄丽丽(即何小曼原型),也有她的一份罪恶,严歌苓希望能用她现在的文字诠释来给出一份忏悔和一份批判。
为什么?凭什么?这是童年亲历文革的严歌苓始终萦绕于脑海中的问题,哪怕几十年后,她还是有着对于那个时代的疑问和反思,因此也才会有郝淑雯和“我”在她空荡荡的别墅中叩问着的那个最原始也最无解的问题:“我们干吗都那么对刘峰?” 集体本应是一个温暖的代名词,然而这个“集体”却让刘峰无辜承受了如此大的伤痛,让蒙昧的世界更加远离了文明、礼貌、道德,它披着伪善的外衣,实质却是极少数人或者集体的利益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权利的无情剥夺。人们只有在融入“集体”中时,才仿佛获得了众力,可以相互借胆又肆无忌惮的迫害他人。“集体”让我们信奉“平凡即是伟大”,却忽视了人们的非凡之处,将“时代英雄”塑成平凡的塑像,搁置在冰冷的大理石座上供人们传唱敬佩,但丰盈的人性也随之变成了“英雄”的牺牲品。从刘峰与何小曼两人双双成为时代的“英雄”,到最终二人艰难凄苦的生存困境,便是严歌苓对于革命“英雄主义“祛魅的良证。
“文学不能失去质疑生活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勇气。质疑不单单是为了批判,而是批判之后的构建;揭露也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而是展示之后的救赎。”《芳华》中的男主人公刘峰就是用他这一世来替世人赎罪,用这一生来渡人渡己。文工团里的战友们对刘峰的情感可能是复杂的,仿佛对他博爱到人人有了困难都情不自禁地呼喊“刘峰”来解决,又仿佛对他不爱到在“批斗大会”上的句句诛心。反观刘峰,他却好像自始至终都那么善良、平淡如水。无端突然从云端之上跌落至万丈深渊,他没有怨怼,安静地接受了这一切,还参加了中越自卫反击战,为国奉献了一条手臂。他即使是对失足的妓女也倾囊相助、对待大家都排挤的小曼,他也会去医院探望、多年之后偶遇当年迫害他的战友,他也一直面带着微笑、在哪怕是断了一条手臂在红蚁满布的血泊中垂死,他给运输司机的指引仍然是向着这个世界的。
在满目疮痍的回忆叙事中,严歌苓是用个体的牺牲来唤回群体的震撼、用个体的救赎来唤回群体的反思,以此强烈的对比给读者产生巨大的心理冲击。不论是对于书中的“萧穗子”抑或是作者严歌苓而言,“文革”的回忆宛若一片废墟,而刘峰的救赎就像废墟之上开着的艳丽的花儿,这光鲜而又艳丽的花朵,不仅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严歌苓创作中不断向深切的人文关怀发起的探索,又何尝不是让我们在这强烈反差的刺痛中思考避免再度受到伤害,从伤痕根源上警示后来者呢?
三、批判与狂欢:举重若轻的叙事策略
严歌苓的小说叙事策略总是将沉郁悲观杂糅于明快活泼的笔触中,在轻快文风的背后却隐含着悲悯主题的情怀,表面看似矛盾重重,实质上却是似于米兰昆德拉“轻”与“重”变奏序曲的续写。诚如一位批评家所言:“读她的小说,我们发现很难从中感到快乐,几乎所有的人物的精神背景都来自痛楚和伤感,只是这‘痛楚’另一面也被她纤细的笔精致化和美化,即便‘伤感’,也是冷静成‘诗化’的忧伤。”可以说这是严歌苓一贯的文风了。在《芳华》中,她更是娓娓道来,把一切背叛写成了笑谈,把批判写成了狂欢。诸多像革命年代下的物质极度匮乏、教育惨遭荼毒等阴郁悲剧的主题在严歌苓的《芳华》中都是轻描淡写的一代而过:如对于物质匮乏,是借刘峰的口说出自己童年的经历:“有人穷的光腚呢!”、对于人们长期极度饥饿、食不果腹的现状书写,也是借闯入靶场偷红苕的老太太之事,由刘峰一语道破这其中暗含的玄妙:“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饿你们一冬,看你们落后不落后,偷不偷公家红苕?”从而刻意规避掉异常政治状态的“权利失语”造成的长久物质匮乏,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生理上的切肤之痛以及心理上的扭曲异常;而对于当时教育事业的现状描绘,严歌苓也是自如地穿插在行云流水的文字中从而简单提了一下:“沟那边是一所小学的围墙,从来听不见念书声,总是咚咚呛呛地敲锣打鼓,给新下达的‘最新指示’报喜。”一座城市中的普通小学尚且如此,政治高蹈的重压可见一斑,不禁让人响起那句殷切的呼喊:“救救孩子!”严歌苓似乎从来没有刻意着墨于宏大悲怆史诗性的革命书写,她跳脱的语言思维下所编织的故事,有时让你忍不住发笑,有时觉得荒诞不经,有时一笔带过甚至“轻”得让你不小心忽略,但抚卷长思时又让你有绵里藏针的刺痛感,逼迫你转过头来进行再一次慎重的思索。
在后革命叙事的氛围中严歌苓更是有着与其他作家不一样的书写视角,这主要得益于她多年旅居海外并走遍了大半个地球的丰富经历。空间上的断裂加之异域文化的冲击,使她吸纳并贯通了东西方文化之精髓,融东西方文化于一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隔岸”的疏离感使她的文学呈现出独特的色彩。诚如她自己所言:“所谓当事者迷,道德的、政治的,就因为你在局内所以你不能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不是控诉就是揭露,要不就是讴歌……但这都不是文学的功能。局外一点,边缘一点,就会不同。像加缪那样站在局外,这样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在写作的时候我再把心里的感觉告诉别人,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荒诞的,有游离于所有主流生活的感觉。”因此,严歌苓的很多作品都有着刻意的“去政治化”倾向,刻意地与政治历史事件拉开距离,跳出政治的枷锁与藩篱,政治事件在小说中充当的角色仅仅是为了必要的故事叙述而铺垫的大背景而已。严歌苓自己在采访中直言她并没有写任何“运动”,她也没有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革命,她只是通过自己客观冷静的笔触写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而已。《芳华》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但是其中的很多政治事件,如林彪坠机、唐山大地震、改革开放大潮等都是一笔带过,并没有进行过多的描述。她的笔锋向内转,转向了人性最深处的挖掘和对历史的反思,填补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巨大缝隙。
从1973年4月7日有雾的成都调转镜头到2015年寒冬的北京,跨越了四十余载的少男少女的爱恨情仇、背叛狂欢,结局都会像红楼里四十八个大小不一的房间一样,被宽大的马路碾压在地下,被时间的洪流所无情湮没。在故事的最后,严歌苓也没有慷慨地给故事的男主角刘峰一个完满的结局,迟暮“英雄”的退场戏显得潦草而又仓促:追悼会只有不到五分钟。在他侄子侄女都没到的情况下,在小曼紧握着密密麻麻悼念词都没来得及轻轻读给他的情况下,我们就这样跟刘峰告了别,跟那个时代告别。那些翻腾着不甘的岁月,那些狂欢背后的背叛,都化成了灵堂中的那株冬青,化作了一抹扎眼的绿色。故事在这里轻描淡写的戛然而止,严歌苓这“轻轻”的背后却隐藏着作家对于某种荒诞逻辑的严词拒绝和更为深刻的人性担当,她悲凉的底色之下交织着的却是温暖关切,冷峻的语言背后涌动着的更是灼灼热血,“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重”的超越,此番逻辑之下隐匿着的叙事张力更是让我们看到了作品文本之中凝结着的巨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关切,这也正是严歌苓对“后革命氛围”下的当代中国文坛的贡献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