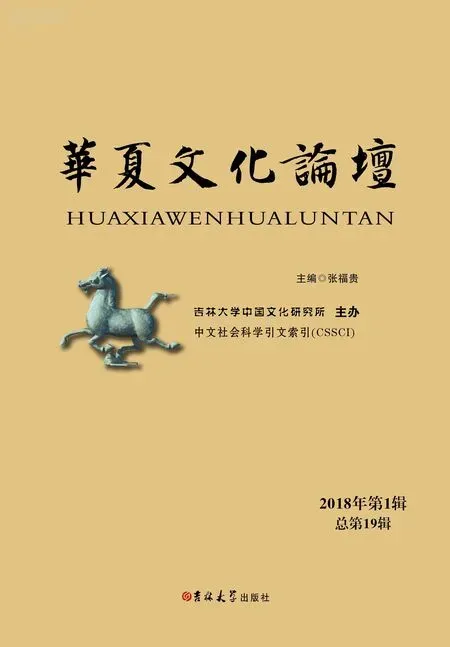鲁迅小说的情节结构与戏剧结构的关系
孙淑芳
鲁迅小说的情节结构,作为构成鲁迅小说艺术特点与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内外对其研究的成果不说已经达到了汗牛充栋的程度,起码也已经十分可观了。但在这些可观的研究成果中,却鲜有研究成果在“跨艺术”的框架中,自觉地关涉过鲁迅小说的情节结构与戏剧结构的关系问题,更没有一项研究成果从这样一个“关系”的角度来透视鲁迅小说情节结构的独到匠心与特有魅力。正是有鉴于学界的这样一种研究历史与现状,本文拟定了这样一个题目,以期通过对这样一个题目的研究,开辟一个透视鲁迅小说情节结构特点、魅力的新角度,形成研究鲁迅小说情节结构的一种新格局,即“跨艺术”的研究格局。
一、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与戏剧的外结构
综观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从形式上来看,是有始有终、时空狭小、首尾呼应的封闭结构;从内容上看,是单纯明朗、转换迅速、富于戏剧性的完整故事。鲁迅小说的这样一种情节结构,如果置于“跨艺术”的框架中进行透视,我们则可以发现,它不仅与戏剧外结构的美学特征类同,而且具有与其相似的审美效果,而这也正是鲁迅小说情节结构新颖性的一个具体方面。
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大体上来说属于画面结构,即以场景为主体的画面式情节单元组合而成的结构,这种画面结构,一般都具有场景化与时空高度浓缩化的特点,正是这样一种特点,使鲁迅小说在叙事时距、叙事时态、叙事空间及由首尾呼应所形成的“封闭结构”方面,都呈现出与戏剧叙事时间及叙事空间上相似的审美特色。
就叙事时距的处理来看,鲁迅小说往往有意识地弱化一般小说处理叙事时距时常用的“概要”“停顿”等方式,主要采用了一般小说中不常采用,而戏剧处理叙事时距时常常采用且特色鲜明的“场景展示”与“省略叙事”两种方式,从而使小说呈现出戏剧叙事场景组构的客观性和场面结构之间的跳跃性的审美特点。如《起死》本就是以话剧剧本形式写成的小说,整篇小说用四个对话场景构成,在叙事时距上明显呈现出戏剧的审美特点。《长明灯》《药》等小说均在叙事时距上采用以“场景”和“省略”交替的戏剧化节奏,突破了小说的常规,形成了以场景展示为主的叙事结构,具有西方话剧叙事的特点。
就叙事时态来看,鲁迅小说突破了一般小说常用的“回忆模式”,构建了一个以“现在”为核心,包含“过去”和“将来”时间的叙事范式,而这一范式,正吻合了戏剧常常立足现在时间的叙事范式。也许正是因为观察到了鲁迅小说在叙事时态方面的这样一种戏剧性的特点,所以,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基于西方戏剧外部时间结构的特点观照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的时间框架,不仅认为鲁迅小说外部情节的时间框架具有戏剧的审美特点,而且十分认可其审美效果,他指出:“让我们用‘时间框架’这个词来指主要的或总的情节发展的时间。如果有—个充分戏剧化的叙述者,时间框架就会是他讲述故事所需要的时间,次级的时间框架则是他所讲述的情节发展的时间。回忆、插叙或倒叙以及对未来的展望,都可能处在时间框架之外。这样看来,鲁迅小说完全遵守一种不寻常的笔墨经济的原则;后期作品中的时间框架一般都保持在古典主义戏剧批评所主张的地点、时间和情节的三一律之内,再加上回忆和倒叙。《祝福》虽然使读者感到写的是祥林嫂痛苦的一生,主要的时间框架却只是一天,其余一切都是回忆和倒叙。”确如帕特里克·哈南所言,在叙事时长上,鲁迅小说除了《阿Q正传》这一中篇外,其他篇幅都比较短小,情节延续的实际时间也普遍比较短,有三分之一篇目的故事时间都在一天之内。在帕特里克·哈南来看,鲁迅小说的时间结构正像西方戏剧的时间结构一样:“即使上承了他事——远前史,也要把它包进‘身’去,形成一个头、身、尾圆滑连接的封闭结构,这正是希腊美学的要求。”帕特里克·哈南的观点虽然是一家之言,但却不仅持之有据地指出了鲁迅小说的叙事时态及其外部结构与西方戏剧的叙事时态及其外部结构特征的一致性,而且也指出了其中所体现的鲁迅崭新的时间观及其所带来的良好的艺术效果。
就小说的叙事空间的设置而言,鲁迅小说叙事展开的空间一般都比较狭小,情节发生的地点的转换也很少。鲁迅小说中五分之三篇目的叙事空间基本都是固定的,小说叙事都在一个空间里完成。有些篇目叙事虽然是在移动空间里完成的,但其关涉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几个空间,最多不超过三个。根据近现代艺术理论来看,小说属于时间艺术,而戏剧归为时空艺术。戏剧的结构即“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对戏剧行动的组织”。但是,作为舞台艺术的戏剧在时间和空间上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戏剧结构在时空上要高度集中,空间具有固定的特性,因而戏剧不容易自由转换场景。鲁迅小说不仅在叙事时距上采用西方戏剧以“场景”和“省略”交替为主的叙事手法,而且在叙事空间的设置上也类似西方戏剧是有限且固定的,力求场景的高度集中。鲁迅小说将故事情节浓缩在高度集中的时空之中,体现了鲁迅在外部情节结构构思上的戏剧化追求。
鲁迅小说首尾呼应所构成的“封闭结构”与西方戏剧的封闭结构的关系,在我看来,则更为明显。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十分赞赏鲁迅小说首尾呼应的特点,认为其是鲁迅在外部情节结构上的匠心独运,他曾经指出:鲁迅小说“结构匀称,有意识地把故事安排得使结尾与开头相呼应。这一点最先可以从《明天》里酒客唱的小曲里体现出来,收在《彷徨》里的《弟兄》《长明灯》《祝福》和《示众》,这种匀称就更明显了。”他不仅罗列了鲁迅小说首尾呼应的例子,也不仅指出了鲁迅小说首尾呼应所使用的主要手法——重复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构上的良好效果——结构匀称,而且认为,首尾呼应,正是形成鲁迅小说“封闭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封闭结构及首尾呼应所采用的“重复”的手法,又正是西方戏剧外部结构的特征及主要手法。美国的另一位批评家威廉·莱尔就曾指出:“把重复的因素放在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的开头和末尾,使这个重复因素起着戏剧开场和结束时幕布的作用”是西方戏剧普遍采用的结构方法。这种结构方法的作用是使作品能够形成一个“封套”,让作品的叙事能相对集中地展开。而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正具有这种“封套”的特点。王富仁在威廉·莱尔对鲁迅小说结构特点研究基础之上,将《呐喊》与《彷徨》中所形成的“封套”具体分为六种:一是生命的封套,以主人公的死亡将小说封闭起来。这是鲁迅常用的、也是最硬性的一个封套。二是精神状态的封套,主人公从进入某种精神状态开始,到离开某种精神状态结束。三是场景的封套,由回到某一地域始,到离开某一地域终。四是谈话的封套,由引起谈话的兴致起,到谈话终止结束。五是事件的封套,由事件开始始,到事件结束止。六是动态的封套,由静态描写始,静态描写终,将小说当中的动态封闭起来,从而形成了静——动——静的完整结构形式。王富仁由此得出结论:“以上各种各样的封套,有时单独使用,有时结合使用,把《呐喊》和《彷徨》的各篇都封闭得严严的”,从而使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具有了封闭性的特征。
进一步地考察我们则可以发现,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不仅在形式上如同西方戏剧外结构一样,具有封闭性、整一性,而且从内容上看具有西方戏剧“三一律”在情节要求上的特点。鲁迅小说外结构的情节线清晰明了,发展迅速,转换突然,节奏鲜明,故事完整,它是直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具体可感的,根据场景的组构顺序可以明确完整地概括出情节发展的脉络。《高老夫子》中高老夫子的一天活动通过三个主要场景展示出来:场景一,高老夫子在家照镜、备课;场景二,高老夫子在贤良女学校上课、逃走;场景三,高老夫子在黄三家里打牌,决意不再去女学堂上课。《药》中用四个场景叙写了华家的生命故事:华老栓到刑场为儿子买“药”——华小栓在家里吃“药”——茶客们在茶馆谈“药”——华大妈到坟场给小栓上坟。《起死》中则主要用三个场景展示了庄子的“超现实主义”行为:庄子将一个骷髅起死回生——庄子问询汉子死时候的有关情况——庄子禁不住汉子索要衣物的纠缠在巡士的帮助下逃走。从这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小说采用场景叙事的情节发展是单纯明朗、转换迅速、有始有终并富于戏剧性的。
综上所述,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与西方戏剧锁闭式结构类同,在时空结构上力求紧凑精炼、集中整饬,注重场面和情节的集中,体现了西方戏剧结构上封闭性、整一性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采用这一戏剧式的外部情节结构是有着深刻用意的。鲁迅小说外部情节发展尽管迅速,有始有终,但对于现实的改变并没有什么意义,因此,鲁迅小说封闭的外部情节结构实则蕴含着鲁迅深沉的批判。《风波》中,鲁迅对中国农村广大群众麻木闭塞落后思想的巨大隐忧,和对仍然占优势的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猛烈批判,就蕴藏在以平静始、以平静终的封闭情节结构中。《起死》中,鲁迅对像庄子之类的那些圆滑、随便,无是非观念,自命超现实的“第三种人”尖锐的讥讽,以及对他们险恶用心和没有真本领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的堕落倒退本质的揭露,就蕴藏在以庄子停下赶路始、以匆匆逃离继续赶路终的封闭情节结构里。
二、鲁迅小说的内部情节结构与戏剧的内结构
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看起来很简单,小说里引进的次要人物也仅限于和主人公有密切关系的人,但是,在鲁迅小说表面看起来简单的结构背后却蕴藏着作家巨大的技巧。这一技巧主要体现在内部情节结构的设置上。鲁迅小说独特的外部和内部并存的双线情节结构,使主题意蕴得以深广的开掘。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固然显示一定的意义,参与主题意蕴的建构,但是,如果仅仅从外部情节结构去理解鲁迅小说的主题意蕴的话,那么鲁迅小说也就失去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意义,其厚重的思想内涵也无法得以彰显。其实在鲁迅小说中还存在着内部情节结构,这种内部情节结构,无论在特征还是在功能方面,都与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结构不同。就特征来看,鲁迅小说外部情节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封闭性与整一性的统一,而鲁迅小说的内部情节结构则是开放的、不完整的、缺少变化的,其结果是不明确的,其存在的时空是相当阔大的;从功能来看,鲁迅小说外部情节结构主要承担的是叙事的功能,而鲁迅小说内部情节结构的功能所承担的则主要是主题意蕴的开掘。而鲁迅小说内部情节结构的这种特点及功能,正与西方戏剧不谋而合。
戏剧的结构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只是在舞台上“做表面文章”,它有着自身巧妙而独特的构成机制。施旭升在《戏剧艺术原理》中指出:戏剧结构有“内结构”与“外结构”之分,戏剧内外结构的功能侧重是不同的,戏剧的外结构重在组织情节、安排场面;内结构重在创设主题立意。那么戏剧在内蕴方面又如何去开掘,才能使主题立意更为深广呢?谭霈生在《戏剧艺术的特性》中进一步指出:戏剧由于具有固定空间与延续时间的特性,所以戏剧结构必须遵循时空高度集中的原则。戏剧固定空间的特性,使其不容易自由转换场景,舞台延续时间的特性,又使得不应该轻易打断动作的持续发展。戏剧固定空间和延续时间的特性,还要求戏剧结构应该遵循大实大虚、虚实结合的原则。任何艺术都应该讲究虚实结合。但话剧在结构方面的虚实结合,却有着特殊的含义。处理空间的虚实结合,指的是明场戏与暗场戏的辩证统一;处理时间的虚实结合,则是指一场(幕)戏中写实性的时间延续与场(幕)间包含的时间流逝的结合。戏剧结构方面的虚实结合,正是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内容。虽然戏剧在时空上高度集中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家表现广阔而丰富的现实生活,但是,运用虚实结合的原则正好可以弥补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扩大时间和空间的容量,从而扩大生活的容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戏剧结构在时空高度集中原则的限制下,是如何尽可能地扩大时空与生活的容量并深入开掘主题意义的。实际上,戏剧结构的“实”体现的是戏剧的“整一性”,而戏剧结构的“虚”则对主题意蕴的深化起着重大的作用,它使戏剧突破了狭窄的时空和封闭的结构,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说,尽管戏剧外结构表现出来的“实”受限于演出时空,但是,戏剧内结构却以“虚”与整个生活相沟通,因此有“戏剧小天地,人生大舞台”的说法,即通俗地概括了戏剧集中、快捷反映广阔生活的艺术审美特点。
从外部情节结构上来说,鲁迅小说如同戏剧一样,都戴着镣铐舞蹈,然而鲁迅别具匠心地设置了内部情节结构,从而使其能够突破外部的束缚、破茧化蝶,使小说的主题立意更为深远而丰厚,这一内部情节结构所体现出的具有崭新生命的主题立意渗透着作者热切的期望。下面,我们以上文提到的小说为例做进一步的分析。
《药》的外部情节结构是关于华家的生命故事,而随着华小栓的死亡,这一故事也就结束了。单纯地来看这一故事的情节发展,它是完整的、明朗的,并没有留下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值得思考的东西。小说的主题意蕴主要体现在内部情节线上,这是一条敞开的情节线,我们只能通过外部情节结构中的客观描写勾勒出大概的情形:夏瑜革命——夏瑜被杀——以夏瑜为代表的革命者将来的命运。这一内部情节线尽管只是虚写,且没有结果,但却包含了鲁迅的真正立意,也使外部情节线的存在具有了更大的价值和意义。革命者将来的命运如何,这不仅是鲁迅也是他所预设的广大读者应该关心并积极思考的问题。
《起死》虽然在庄子的逃之夭夭和巡士的狂吹警笛中落幕,但小说的内部情节却没有丝毫的发展,汉子的生存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这一情节上,时间仿佛被凝固了似的,只有开始,没有发展和结局,时间一直停留在汉子被起死回生之后生存无着的困境之中。而在外部情节结构上,时间的流逝和事件的转换不仅迅速而且有始有终,从庄子因好奇与爱管闲事而让司命大神将一个骷髅起死回生,到庄子问询汉子死时候的有关情况,并教其忘却是非得失,最后到庄子禁不住汉子索要衣物的纠缠仓皇逃走。整个事件就发生在庄子去见楚王的路上,从停下赶路到继续赶路,事件的首尾是闭合的,事件的起讫虽然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但对现实生活环境没有任何意义。庄子的言行对现实状况没有任何改变,他既不能掌管人的生死,也不能解决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而真正体现鲁迅对于发展变化的渴望与企盼的则是内部情节结构,其中提出的远未结束的问题就是小说所要表达的深层意蕴。除了以上两篇小说外,在鲁迅的其他小说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内部情节线。
由以上可见,鲁迅小说内部情节结构的设置如同戏剧一样,对于拓展、深化主题意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相对于外部情节结构而言,它所表现的事件都发生在暗场,所表现的时空也是虚的。鲁迅小说中的内部情节都是不完整的,零散而模糊的,从来没有被正面展现过,只能靠读者从叙述语言和人物言行中间找寻和想象,但它却是小说主题立意的根本之所在。鲁迅设置内部情节结构意在深入开掘和创设小说的主题立意。鲁迅小说的外部情节展示出来无一不是悲剧的结局,而内部情节提出的引人深思的问题才是鲁迅关注社会现实、期待真正改变的深切希望。《药》中外部情节结构在情节与场景安排上以华家为主,华小栓的死展现了大众的愚昧与悲哀,然而内部情节所透射出来的革命者的命运与前途才是作者要引起读者着重关注的主题。《药》正是巧妙地运用了戏剧的内外结构,通过设置戏剧常用以开掘、深化主题意蕴的内部情节结构,从而使仅由四个场景组构的关于华家的生命故事能够呈现出深广的意蕴。
三、鲁迅小说双重情节结构的隐喻意义及与戏剧的关系
鲁迅小说中的外部情节结构和内部情节结构,分属于实虚、明暗两个不同的时空和层面。从外部情节结构来看,它是封闭的、完整的,其呈现具有客观性。这一结构时空狭小而集中,事件发展迅速、因果分明,问题得到解决,但社会现实状况却没有任何的改变。从内部情节结构来看,它则是开放的、未完结的,其呈现具有主观性,饱含着鲁迅对于社会现实真正发展变化的热切期望。这一结构时空阔大,事件发展十分缓慢或陷于停滞,其中提出的问题远没有结束,然而这一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却很大,这是鲁迅个人的发现。
鲁迅运用双重情节结构方式是有着他自己的深远意旨的。鲁迅曾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鲁迅看来,殊途同归,最终都指向一个终点,那就是“坟”。鲁迅小说外部情节结构的封闭性使事件的结束又轮回到了开始,一切都未曾改变,似乎就喻指这“坟”。从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坟”和“死”的偏爱与执着,日本学者将其这种思想归结为“终末论”,从中挖掘出鲁迅的思想与人生哲学的独特性。伊藤虎丸指出,“终末论”实际上是要“确保乃至恢复历史,以作为主体‘个’的爱与决断之场”。伊藤虎丸这话也是从熊野那里获得启发的,熊野认为“终末论是希望之学……”。终末论“不是从生来思考死的,而是从死来思考生”,人在“固有一死”当中,才能获得“个体”。鲁迅在小说中即巧妙地运用情节结构体现了这一深刻而独到的哲学思想。鲁迅小说封闭的外部情节结构不仅隐喻缺少变化、沉闷僵死的社会现实状况和只有“轮回”没有“发展”的社会群体时间观念,还隐喻鲁迅迫切希望这种无变化、无发展现状的终结。而建立在这种终结基础之上的,即是体现鲁迅个体发展变化思想观念的内部情节结构,隐喻鲁迅对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殷殷期望。
从表面上来看,鲁迅小说情节的内外结构与戏剧的内外结构具有同构性,它们的构成形态都属于“完成性和非完成性之间辩证的统一”。霍洛道夫认为戏剧的这种辩证统一主要体现在最后一幕:“最后一幕一方面结束了剧情,另一方面又仿佛使剧情仍旧没有结束,让观众来揣度剧中人物的命运。”“最后一幕一方面是剧本的结尾,另一方面也是剧中人物在剧本范围以外继续生活的开始,生活绝对不是随着帷幕的降落而遽然中断的。因此,最后一幕可以从两种观点来着眼,一种是把它当作剧中事件的终结,另一种是把它当作向未来前进,当作各种新关系的开始。”鲁迅小说形式上的封闭性与主题意蕴的开放性同样集中体现在结尾。结尾与开头的照应意味着事件叙述的完整性,而小说中所发现并提出来的问题却没有随着形式上的封闭而得到解决。
但从构成的意义上来看,它们又具有根本的异质性。作为形式的外结构与体现主题意蕴的内结构,对于戏剧来讲,是对立统一的,它们都处于同一时空之中,主题意蕴依靠形式来表达,形式依靠主题意蕴来统领。作者体现在主题意蕴中的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与社会群体的意识必定是相契合、相一致的。因为戏剧是一种群体艺术,戏剧的观演是一种集体的体验,在剧场中,观众的个体意识被群体反应所同化,都随着剧情的展开朝向同一个方向按照同一个节奏而激荡起伏。剧中具有民族传统的心理原型常常引发观众心灵深处的共振。“观众的集体经验在这里发生作用,观众,也就与戏剧的创作者们融为一体,走入了同一个梦境”。“戏剧家必须让其剧作宣泄出某种群体的意识、渗透着某种民族的精神,否则,它就很可能被接受者所排斥。”然而,在鲁迅小说中,外部情节结构是对社会群体意识的展现,而内部情节结构则是鲁迅个体思想的呈现,小说中的主题意蕴不仅不与社会群体意识相契合,而且显现出水火不容的背反姿态。因为外部情节结构与内部情节结构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时空,社会群体与鲁迅个人的意识同样分属于这样两个不同的时空——轮回与发展。在小说中,鲁迅对群体意识的批判,对国民性的解构,正是为了将读者引向自己的个体意识的一面,期待读者与自己共同思考未完结的问题。这就是鲁迅选择小说而一生中都未进行真正意义上戏剧创作的根本原因。
总之,鲁迅小说的内外情节结构与戏剧的内外结构既具有同构性,又具有根本的异质性,体现了鲁迅在追求别样艺术风采基础上的创新精神。鲁迅小说这一独具匠心的结构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结构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外部情节结构也就是完整的故事情节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只是为小说的主题意义服务的,故事情节的结束,也就是小说内容的结束,主题意义完全包含在故事情节之中。而鲁迅小说则由外部情节结构与内部情节结构共同参与主题意义的建构,主题意义并非完全包含在外部故事情节之中。由此看来,鲁迅小说的双重情节结构成为鲁迅开掘丰厚而深邃主题意蕴的有力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