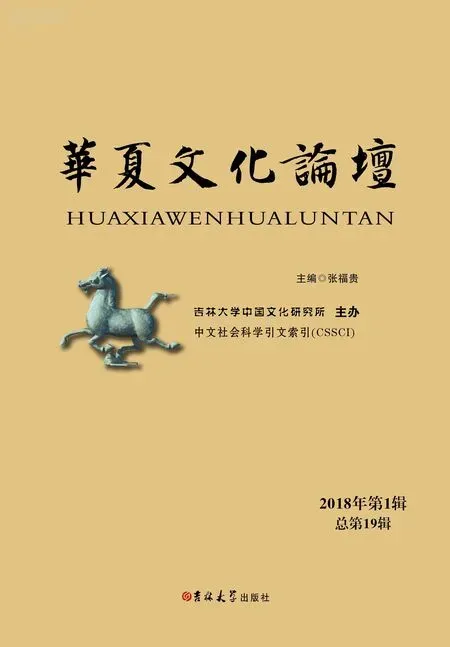“寻梦者”的创造、超越之旅
——鲁迅《过客》与尼采的超人哲学
王学谦
【内容提要】《过客》是能够体现鲁迅思想性格的重要作品。《过客》的“反抗绝望”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具有密切关系。超人哲学是尼采在上帝死了之后对人的价值呼唤,是强劲而积极的个性主义精神。超人哲学的核心就是不断超越:生命是有限的,人应该不断创造自我、创造世界,永不止息。鲁迅“过客”的不断行走,是这种不断超越、创造的精神写照。拒绝同情,不断进取,在没有路的地方开拓出道路。
之所以要专门分析《过客》,是因为自李泽厚将鲁迅看作是“提倡启蒙 超越启蒙”的作家以后,再经由汪晖的《反抗绝望》对《野草》的阐释,《过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受到特别的重视和固定的解读,被普遍看作是“反抗绝望”的经典作品,却很少有人看到这种“反抗绝望”恰恰是浪漫主义——尼采式的“精神界之战士”的精神境界。李泽厚在他的《现代思想史论》中认为,鲁迅之所以超越一般“五四”作家,“这当然与他早期接受尼采哲学作为人生观有关。贬视庸俗,抨击传统,勇猛入世,呼唤超人,不但是鲁迅一生不断揭露和痛斥国民性麻木的思想武器(从《示众》到《铲共大观》《太平歌诀》),而且也是他的孤独和悲凉的生活依据(从《孤独者》到《铸剑》到晚年的一些心境)。”但是,鲁迅与尼采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却并没有具体分析。本文认为,《过客》更直接地显示了鲁迅与尼采超人哲学的精神联系。它贴近于浪漫主义“寻梦”的精神,同时又有尼采的“超人”的“不屈的意志”,即“精神界之战士”的风采。
一
在《过客》发表不久,鲁迅曾经向一个青年解释《过客》的意思:“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过客”象征着个体生命的有限性,而他的不停地“走”则暗示着生命的超越性,无限性。世界是变化、运动的,个体生命也是变化的、运动的,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个体生命总是要死去,死后便一切归于虚无,一切皆空,历史也不会到达“黄金时代”,但是只要活着就永不停歇地“寻找”。这种“寻找”既是自我不断创造的过程,也是自我创造历史的过程。这显然具有尼采“超人”——不断超越自己的意味。尼采说,上帝死了,不存在永恒的天国,世界是生成的,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是,没有上帝指引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他无限自信而充满着力量,不断创造自己,也创造世界。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人是桥梁而非目的。人是一个能够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通向没有终点的远方,人的精神应该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不断超越自我,不断达到新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宗教意识,更没有永生的观念,因而死并不会引起他的太大痛苦,鲁迅在《死后》中说自己对于“死”的观念,是个“随便党”,但活着应该怎样却和尼采一样,坚守自我,并不断寻求、超越。
鲁迅早在1918年就流露出“过客”的心态。他的诗歌《梦》是他“寻梦”的精神象征:
很多的梦,趁着黄昏起哄。
前梦才挤却了大前的梦时,后梦又赶走了前梦。
去的前梦黑如墨,在的后梦墨如黑;
去的在的仿佛都说,“看我真好颜色。”
颜色许好,暗里不知;
而且不知道,说话的是谁。
暗里不知,身热头痛。
你来你来,明白的梦。
这是带着焦虑、迷惘的“寻找”、渴盼。在“五四”时期,鲁迅文学中关于“路”的意向也是这种“寻找”或“寻梦”的表现形态。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人生最大的悲剧是“梦醒了无路可走”,1925年,鲁迅曾经翻译伊东干夫的诗歌《我独自行走》,表达的是近似于《过客》的精神:
我的行走的路
险的呢,平的呢?
一天之后就完,
还是百年的未来才了解,
我没有思想过。
暗也罢,
险也罢,
总归是非走不可的路呵。
我独自行走,
在沉默着,橐橐地行走。
即使讨厌,
这也好罢。
即使破坏,
这也好罢。
哭着,
怒着,
狂着,
笑着,
都随意吧!
厌世呀,发狂呀,
自杀呀,无产阶级呀,
在我旁边行走着。
但是,我行走着,
现今也还在行走着。
《彷徨》的题词是“路慢慢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这也是《野草》的重要题旨。
在“五四”时期,由于传统社会及其价值的崩溃,现代性价值的输入,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个人价值重建的焦虑、渴求也异常强烈,浪漫主义的“寻梦”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种心态、精神特征在许多作家那里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周作人的《歧路》,“荒野上许多足迹,/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有向东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我相信是这样的。/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周作人的《寻路的人——赠徐玉诺》所表达的意蕴近似于《过客》,只是前者更伤感、痛苦、绝望: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
胡适散文《我的歧路》、刘半农的长诗《敲冰》、朱自清的《毁灭》,都是“寻梦”的主题。“寻梦”也是徐志摩诗歌的主题之一。徐志摩的《为要寻一颗明星》也颇有崇高、悲壮感。“我骑著一匹拐腿的瞎马,/向著黑夜里加鞭。”“为要寻一颗明星。”最后,“我”“马”都累死之后,“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徐志摩的“康桥”并非政治的象征,而是其浪漫主义理想的象征。《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是迷惘、困惑的,也是寻找的。和鲁迅比起来,新月派显得比较保守,他们的确浪漫,但总是忘不了理性的制约,相信理性过滤之后的情绪更纯正,但也仍然有着这种“寻梦”的冲动,“无常是造物的喜怒,茫昧是生物的前涂,临到‘闭幕’的那俄顷,更不分凡夫与英雄,痴愚与圣贤,谁都得撒手,谁都得走;但在那最后的黑暗还不曾覆盖一切以前,我们还不一样的得认真来扮演我们的名分?生命从它的核心里供给我们信仰,供给我们忍耐与勇敢。为此我们方能在黑暗中不害怕,在失败中不颓丧,在痛苦中不绝望。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不仅暗示我们,逼迫我们,永远望创造的,生命的方向走,它并且启示我们的想象,物体的死只是生的一个节目,不是结束,它的威吓只是一个谎骗,我们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众星相感召的。”更著名的“寻梦者”是戴望舒,他的“寻梦”更趋柔美的感伤主义,情感纤细、精致,虽然不无悲壮,但往往悲哀大于悲壮,但也是在焦虑地寻找。《雨巷》渴望遇到一个丁香般结着愁怨的姑娘,《乐园鸟》永无休止的飞翔,为的是寻找那天国的花园,戴望舒使用了《圣经》里关于伊甸园的典故,更典型地散发着浪漫主义的精神氛围。《寻梦者》却是很悲壮的:梦会开出花来的,但是,这花却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在寒冷的冰山上,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可是,一旦你寻到梦中之花,你的生命也耗尽了。还有写《画梦录》的何其芳也大体上属于这类“寻梦者”,他的“梦”和戴望舒颇为相似。七月派路翎的“寻梦”也许更近似于鲁迅的“过客”,他的蒋纯祖甚至可以看作是“过客”在20世纪40年代的变形。他流浪、奔走,焦虑、迷茫,却又异常坚定,孤独而执着寻求着自己的梦想。王西彦四十年代末期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叫《寻梦者》,故事近似于柔石的《二月》,而主人公康农信却笃信叔本华、尼采。仔细地清理,这种“寻梦”在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中也具有重要的位置。
二
鲁迅的《过客》所表达的是浪漫主义的母题,也是尼采主义的重要精神。“过客”孤独而执着地朝前“走”,他仿佛被一种声音所招呼、吸引。无论承受多么大的苦痛、艰难,也绝不停止自己的脚步。这恰好是“超人”式的精神体现。尽管鲁迅曾经说尼采的超人有些渺茫,但是其骨子里仍然流淌着超人的血液。
浪漫主义有一个“寻找”“回家”的强烈冲动。这或许和康德的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康德认为,我们根据自己的感觉、经验所能够认识的东西,只是“现象”,“现象”能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但是,现象却是相对的、有限的。“物自体”却是不可认识的。艺术的关键不是模仿现实——现象,而是写出人的内心对世界本质——“物自体”的追求,是对无限的永远渴求。这种“寻梦”是诺瓦利斯诗歌的基本思想,也是他未完成的小说《海因里·封·奥夫特丁根》的主题。小说中的奥夫特丁根是一个漫游者,其精神的基本特征是“寻梦”。他做过一个梦,梦里看见了一朵蓝色花。“蓝色花”便成了他永远的憧憬,蓝色是遥远的天际的象征,是永远追求却又无法获得的事物的象征,也是著名的浪漫主义理想的象征。诺瓦利斯的《夜颂》《圣歌》都是浪漫主义的回家主题,只是诺瓦利斯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但是这种宗教非中世纪的宗教,而是个人化的新的宗教。德国浪漫主义的另一位著名诗人布伦塔诺也有类似的宗教情结,他的寻找、家园/获救也总是和宗教有密切的关系。
尼采也曾写过不少诗歌,其早期诗歌也带有早期浪漫派色彩,“寻找”“归家”的渴望弥漫期间,甚至也带有宗教、感伤的情绪。《当钟声悠悠回响》是赞颂天国的永恒家乡,“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家乡。/谁人在每时每刻/挣脱大地的羁勒,/唱一支家乡牧歌/赞颂天国的极乐!”《无家可归》则表现的是浪漫派的“寻找”主题,“我骑着骏马/无惧无怕/向远方飞奔。/见我者称我,/无家可归的人。”“我终有一死,/与死神接吻,/可我岂能相信:/我会躺入丘坟,/不能再啜饮/生命的芬芳?/嗨嗒嗒!/我的幸福,绚丽的梦幻。”后来,这种寻找、回家/获救的宗教色彩荡然无存,感伤主义色彩也被淡化到最低程度,代之而来的是强悍、悲壮的寻找,不是走向天国、彼岸,而是孤独地在“大地上”游荡,漂泊。《漂泊者》:“一个漂泊者彻夜赶路/迈着坚定的脚步,/他的伴侣是——/绵亘的高原和弯曲的峡谷。/夜色多么美丽——/可他健步向前,不肯歇息,/不知他的路通向哪里。”“而且永远不能停顿!”在《新哥伦布》中,他渴望做一个精神的哥伦布,探索精神的新大陆,“他始终凝望着碧波,/最遥远的地方已使他迷魂。”
尼采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语言,来表达自我不断超越的过程。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这种“寻梦”的精神变成了“超人”的重要品质之一。查拉图斯特拉也是一个寻求者、“寻梦者”或“漫游者”。他30岁时离开自己的故乡,“遁入山林隐居起来。他在那里享受自己的精神和孤独,历经十年之久而乐此不疲。但终于他的心灵发生了转变,”变成了“孩子”,变成了一个觉醒者,达到了最高的人生境界,获得人生、世界的真相。于是他下山,要将自己的真知告诉世人。他告诉人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消息就是如何做超人。“我来把超人教给你们。人类是某种应当被克服的东西。”因为,“人是一根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绳索,——一根悬在深渊之上的绳索。一种危险的超越,一种危险的路途,一种危险的回顾,一种危险的战栗和停留。人身上伟大的东西正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不是一个目的:人身上可爱的东西正在于他是一种过渡和一种没落。”查拉图斯特拉是不断游走,也是不断超越的象征,或者说,尼采喜欢用不停地行走来象征超人的精神。在《漫游者》中,“我是一个漫游者和登山者,他对自己的心灵说,我不喜欢平原,而且看起来,我不能长久静坐。而且,无论我还会遭遇什么命运,获得什么体验,——其中将不免有一种漫游和一种登山:因为说到底,人们还只能体验自身。”他告诉自己,必须走上最艰难的道路,必须不断超越,拒绝柔情、安逸。“如果你现在没有了全部梯子,你也必须懂得依然登上你自己的头顶,不然你想要怎样向上登呢?登上你自己的头顶,超过你自己的心灵吧!现在你身上最温柔的东西还必须成为最坚强而冷酷的。……赞美那使人坚强的东西吧!我并不赞美那国度——那流溢着奶油和蜂蜜的国度。”在《返乡》中,查拉图斯特拉把孤独作为自己的故乡,他感觉到,在孤独中,他真正属于自己,因为他在众人中间,感到更寂寞。在孤独中,仿佛一切都获得了新生、自由,可以骑乘着每一个比喻的骏马奔向真理,可以敞开心扉,不必像在人中间那样装饰自己。在尼采那里,孤独也是一种超越性的境界,不能享受孤独的人,不算强大的人。在《正午》中,查拉图斯特拉抛开自己的影子,抛开了自愿的乞丐,奔跑起来,跑了几个小时之后,在正午的时候,在安静中他躺下来,他睡着了。但是,他的心灵却没有睡,也没有安静,他享受着这美好而安静的中午,感到自己的幸福,感到全世界都变得美好起来,可是心灵又发出另一个声音:起来。“你这小偷,你这个白日小偷!怎么?还伸懒腰、哈欠、叹息,掉落到深井里吗?”这和“过客”也是一样的精神,即使疲惫也仍然拒绝休息,必须要朝前走。在《高等人》中,查拉图斯特拉说告诫那些高等人,要把自己的灵魂抬得更高,要高到能够够得着闪电的地方,“我的弟兄们啊,提升你们的心灵吧,更高些!更高些!也不要忘记你们的双腿!也提升你们的双腿吧,你们这些优秀的舞蹈者,更好地:你们也倒立起来吧!”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首篇《三种变形》则以另一种方式表达超人精神。“三种变形”是人的精神的三个不同时期的姿势或风貌,是一个不断提升、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平行的过程。第一变,是精神变成骆驼,像骆驼一样,满载重负,就是坚毅地负起最大的使命,人类的使命和历史的使命,即使遭到他人、社会的蔑视、嘲讽和抛弃,也在所不惜,何为重负?“抑或它就是:跃入肮脏的水中,如果那是真理之水,而并不拒绝那冰冷的青蛙和温热的蟾蜍?抑或它就是:热爱那些蔑视我们的人们,当鬼怪想要惊吓我们时,伸手给它?”第二变,是精神变成狮子,“精神在这里变成狮子,精神想要夺取自由而成为自己的沙漠的主人。在这里,精神寻找它最后的主人:它意愿与之为敌,与它最后的上帝为敌,它意愿与巨龙争夺胜利。精神不想再称为主人和上帝的巨龙是什么呢?这巨龙就叫‘你应当’。但狮子的精神却说‘我意愿’。”所谓“你应当”就是传统的稳定的价值,它告诉人们,一切都已经被创造好了,只要按照这种既定的价值秩序生活就可以了,而“我意愿”却是抛开这一切,创造自己的自由,这是创造新的价值所必需的,“为自己取得创造新价值的权利”。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前言”中,谈到如何成为“自由人”的问题,似乎是骆驼变狮子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他认为要想成为“自由人”就要“大解脱”,彻底把自己解放出来。对于一个优秀的人来说,他总是要肩负起一定的义务,这些义务将他五花大绑在某个角落里。这些义务就是年轻人特有的敬畏,在长者、尊者面前的羞怯和温柔,是那种感恩心理,是那种对神圣事物的顶礼膜拜。这些义务也可以理解为骆驼的精神——责任与使命。但是,当“大解脱”降临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则仿佛被一种力量所推动,步入另一种状态。他推开一切义务,点燃激情,勇敢地出发,踏上新的征程,渴望战斗和胜利,挑战一切权威。第三变,狮子变成孩子。为什么狮子必须变成孩子呢?尼采说,“小孩乃是无辜和遗忘,一个新的开端,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原初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的确,兄弟们,为着创造的游戏,需要有一种神圣的肯定:精神现在意愿它自己的意志,丧失世界者要赢获它自己的世界。”其实,“三种变形”不过是象征,尼采是一位非体系哲学家,其思想的变化十分复杂、丰富,它没有一条线性的过程,而是一种近乎线团一样绕来绕去的纵横交错的变化。他有着强烈的认知欲望和好奇心,却并不驻留在任何的认知结果上。查拉图斯特拉作为尼采的化身,“他只能催逼自己启程,给人们指出一种超越现今人生状态的人生状态。他的讲话只有在涉及摆脱什么而获得自由时才是确定的,可以理解的;反之,当涉及自由要达到什么时,他的讲话就是不确定的,空洞的。但通篇说的就是亟须为拥有血肉之躯和生存意志的人寻找自由,而且不是在彼岸寻找,而是在大地寻找。通篇也都在为自我决定而呼吁。但自我决定如何创造或达到,则只以同错误的形态和外部决定(理想和教士的统治)划清界线来表达。有一个东西在否定的漩流中似乎可以触摸到,而且这这东西是持久不变的:这就是从未沉寂的创造要求。”
三
反抗绝望,比因为希望而反抗者更难,更勇敢,更悲壮。这是为什么呢?通常,人们是按照实现的可能程度来设计自己的追求的,实现可能性越大越是值得追求,比如,革命文学提倡者将无产阶级革命看成是一种历史必然规律,这就是因为希望去反抗。这也是一切乐观的理想主义者的基本思路,无论历史怎样复杂、曲折,但是,总会通向更高的阶段,但是,在鲁迅那里,是怀疑这种历史目的的——没有“黄金时代”,即使是“黄金时代”也会将叛逆者处死。因而,这种“希望”是一种虚假的自欺欺人,以这种“希望”为依托的反抗极大地降低了反抗者精神价值,而且很容易走向反面,丧失反抗精神。“过客”的“走”“寻找”“寻梦”是开拓自己的“路”,不是寻找某个现成的“路”,是不断战斗、开拓、创造的路。“路”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并非现成的铺在那里等着人去发现,去走。鲁迅在《故乡》中说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也是这个意思。这背后有一种浪漫主义—尼采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启蒙理性主义将世界看成是一个既定的理性秩序,甚至是机械的存在物,它有自己的固定的结构、本质,人的使命就在于认识、掌握这种结构、本质,按照世界的结构行动、思想,就可以通向一个理性王国,也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就是尼采在《三种变形》中所说的“你应当”。但是,在一些浪漫主义者那里,在尼采主义那里,世界根本不存在着固定的结构、本质,这是理性对世界的阉割、扭曲。上帝死了,理性王国根本不存在,一切价值需要重估。人要回到“大地”——世界之中,“大地”是有机体,是生成的,不断变化的,是没有规律或本质的,是一片“混沌”的,甚至是这种“混沌”、混乱还要重复——永恒轮回。人所存在的大地是生气勃勃的,同时也是悲剧性的,人生的最高价值就在于敢于直面这种生存状态。“你应当”是传统的、虚妄的,是离开生存的大地的,应该抛开“你应当”,重要的是像狮子一样“我意愿”,就是按照我的意志、选择行动,世界是人的心灵创造物,真理或价值不是被发现,而是被创造出来。查拉图斯特拉说,“创造者曾寻求过同伴以及他的希望的孩子:而且,看哪,他发现他找不到他们,除非他首先把他们本身创造出来。”
“过客”拒绝女孩儿的“布施”,也是为了保持“精神界战士”的独立性和永远进击的精神。当“过客”喝下女孩递过来的水以后,心中充满感激,但老翁却告诉过客:不要这么感激,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过客觉得老翁说得有理。老翁后来对过客说,你也会遇到同情的:“你也会遇见心底的眼泪,为你的悲哀。”过客回答说,“不。我不愿看见他们心底的眼泪,不要他们为我悲哀。”女孩儿递给过客布片,“过客”起初欣喜,但立刻变得警觉起来,他说,“但是我不能。我怕我会这样: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诅咒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但是我还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有这力量,我也不愿意她有这样的境遇,因为她们大概总不愿意有这样的境遇。我想,这最稳当。(向女孩)姑娘,你这布片太好,可是太小一点了,还了你罢。”
“过客”为何有如此心态呢?因为对布施的接受,很容易使“过客”与布施者建立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密切的关系也会使“过客”有所眷恋、顾惜,陷入一种情感、伦理牵连之中,对自己也就是一种约束。鲁迅在给一位青年的信中解释说,“无非说凡有富于感激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感激,那不待言,无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譬如,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鲁迅曾经向许广平说,“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同我有关地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在《过客》中说过。”“同我有关地活着”便有一种牵挂,虽然是一种温情、惦念,却对自己是一种约束,而“死了”便无牵无挂,也便是一种自由,所以“我就安心了”。鲁迅这种自由伦理,和尼采主义的自由伦理——“超人”精神有相似性,虽然鲁迅没有尼采走得那么远,却基本上在同一条线路上:为了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应该减少同情、感激一类相互牵挂的情感。我们在鲁迅的《孤独者》《在酒楼上》这样的作品中很容易感到魏连殳、吕纬甫所承受的束缚和压力。魏连殳为了表达对老祖母的感情,不得不去参加族人的丧葬仪式,不得不顺从族人的一切安排,这种丧失自我的压抑使他爆发出狼嚎一样的哭声。吕纬甫为了满足母亲的意愿去给早已死去的小弟弟迁坟,给原来的邻居小姑娘阿顺送剪绒花,他觉得这些无聊的事情毫无意义,却不能不满足母亲的意愿。作品中有一个细节,很有意味,可以说明鲁迅为何要拒绝同情或感激,阿顺为我那碗荞麦粉,特意多加一些糖,“我”尝了尝,并不爱吃,但是,“实在不可口,却是非常甜。我漫然地吃了几口,就想不吃了,然而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地站在屋角里,就使我立刻消失了放下碗筷的勇气。我看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我知道如果剩下大半碗来,一定要使她很失望,而且很抱歉。我于是同时决心,放开喉咙灌下去了,几乎吃得和长富一样快。我由此才知道硬吃的苦痛。”他感到自己就如同苍蝇一样,飞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就是感激或亲情所带来的束缚。在《过客》里,鲁迅却试图甩掉这些情感,以便独自超然远行。
从“过客”拒绝女孩儿的布施上看,也可以理解为何《求乞者》中的“我”拒绝布施,厌恶布施。“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厌恶他这追着哀呼。”“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于烦腻,疑心,憎恶。”鲁迅始终有着“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在此,无疑个人主义占据了中心位置,拒绝同情,而且明显具有尼采式的倾向。对于乞丐,查拉图斯特拉给予极大的蔑视,查拉图斯特拉下山的时候,遇到一位隐士,隐士劝告他,什么也不要给人类,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不施舍,要施行施舍,我还不够贫穷呢。”赠予者的赠予应该是赠予友人,“对于求乞,却是我们应当完全取缔的!说真的,无论是给予他们还是不给予他们,都令人生气。”不给予他们让他们受到伤害,而给予他们也同样是伤害,因为施舍、同情求乞者本身,就不是平等行为,是居高临下的恩赐,真正的强者对人的尊重,首先应该将他当成一个和自己平等的个人,而不是依附于自己的人。因为尼采恐惧自己被他人、众人所牵制,也不想牵制他人。在尼采那里,如若被众人牵制,就会陷入大众化的温柔之乡无力自拔。因而,乞丐,也被看作是缺乏生命力量的人。有一篇题为《自愿的乞丐》是专门写查拉图斯特拉与自愿的乞丐的对话的。为什么叫自愿的乞丐呢?因为这个乞丐把自己的一切财富赠给了大众,但是,却仍然不被社会接受,他厌倦了一切,对一切已经绝望,他要寻找“大地上的幸福”,转而面对牛群学习牛的反刍。他认为在大地上寻求幸福,就要向牛学习,学会牛的反刍。这里,牛在阳光下卧着、安静的状态,暗示着一种宁静的幸福。但是,查拉图斯特拉用自己的鹰和蛇否定了这种宁静的幸福。他觉得,自愿的乞丐无法消受激烈、坚硬的东西,只能接受柔软的东西。在尼采看来,安然宁静地生活着,无疑是平庸、懒散的代名词,缺乏自我的生命力量。强者应该表现出一种非凡的力量。鲁迅在《求乞者》说,“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者之上的烦腻,疑心,憎恶。我将用无所为何沉默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即拒绝求乞,却至少可以得到“虚无”,可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承担孤独者的孤独,宁可被忽略,被憎恶。
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需要重估。人必须独立地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基于基督教的道德,诸如爱——要向爱自己一样爱邻人,乐善好施、奉献、同情、怜悯等等,这些所谓的传统美德都在尼采的反思、批判的火力之下。尼采对道德起源、性质和功能的考察遍布在他的大量文字之中,这种文字在尼采的著作中占有相当的分量,而《道德的谱系》则是尼采颠覆传统道德的代表性著作。在尼采看来,道德无非是人类陈陈相因的习俗的产物。人类的利他性行为,一方面是复杂的,另一方面却是遮遮掩掩的利己主义。这些所谓传统美德在尼采那里是“末人”的道德,是“奴隶道德”,是人生的陷阱,它让人堕落、平庸,让人成为驯服的工具,因为这些道德人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上帝死了:上帝死于他对人类的同情。”“同情是一种情感挥霍,一条危害道德健康的寄生虫,‘增加世上的祸害,这不可能成为义务’。如果人们只是出于同情而行善,那么人们就不会对自己有益,也不会对他人有益。同情并不基于准则,而是基于情绪;它是病态的;别人的苦难感染了我们,同情是一种传染。”道德是否定生命的本能,为了解放生命,为了自由创造,必须否定道德。而尼采的理想人格——狄俄尼索斯、“超人”都是与这种传统道德相对立的。因此,尼采也被认为是非道德主义者。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邻人之爱》,是对邻人之爱的否定,“你们簇拥在邻人周围,而且以美好的说辞来表达这一点。但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的邻人之爱乃是你们对于你们自身的糟糕的爱。你们从自身逃向邻人,想从中为自己搞出一种德性:但我看透了你们的‘无私忘我’。”“你们忍受不了自己,没有充分爱自己:现在你们想把邻人引向爱,用邻人的错误来为自己镀金。我希望,你们忍受不了任何邻人,以及邻人之邻人;于是你们就必须从自己身上创造出你们的朋友及其洋溢的心灵。当你们想要说自己好话时,你们便邀来一个证人;而当你们引诱他从心里称赞你们时,你们本身就从心里称赞自己。不光那个违背自己的知识而说话的人在撒谎,而且尤其是那个违背自己的无知而说话的人在撒谎。你们就在交际中这样谈论自己,用自己来欺骗邻人。”“这个人走向邻人,是因为他在寻找自己,而那个人走向邻人,是因为他想忘却自己。你们对自身的糟糕的爱,把你们的孤独搞成了一座监狱。”创造者是寻找通向自我的道路,是单独的个体,拒绝众人,要承受孤独,要勇敢,爱自己,“对于有的人,你不可伸手相迎,而只可伸出巴掌——而且我愿你的巴掌还长有利爪。”对于创造者而言,爱,“这种爱是最孤独者的危险,这种对一切只要活着的东西的爱!我在爱中的愚蠢和谦卑真的是可笑的!”“伟大的义务并不让人感恩,倒是使人生出强烈的报复欲;而如果细小的善举不被忘记,那就会从中生出一条啮蚀的蠕虫。”